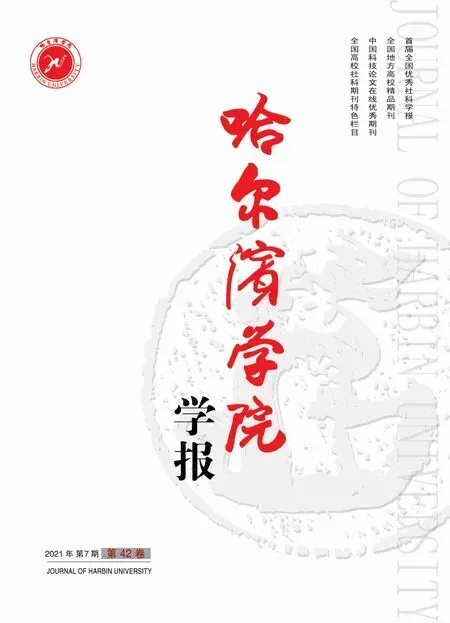“俗文學”視角下的“雅俗”美學之辯
劉 迅
(哈爾濱學院 藝術與設計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6)
我國的俗文學家族龐大,上溯堯舜神話、先秦史傳寓言、兩漢樂府民歌、魏晉志怪小說、唐代文言傳奇,下至宋元戲曲雜劇、講史話本,明清世情與章回小說,以及少數民族民歌、說唱、散曲等,都屬于俗文學范疇。民族化、大眾化是俗文學的本質特點,通俗性是俗文學的一大特色。鄭振鐸先生在《中國俗文學史》中談到:“俗文學就是通俗的文學,就是民間文學,也就是大眾文學。”
廣義上講,“俗”與“雅”是相對的,談“俗”,必讓人想到“雅”,而“俗文學”也成為了對“雅文學”而言的一種范疇和概念。“雅”“俗”之辯、“雅”“俗”之爭綿延了中國幾千年,觀點眾多,難以統一。之所以出現“辯”與“爭”,根源是將二者放置在了“對立”的關系之中,一旦關系對立,便會出現爭論與思辨。那么,文學中的“雅”與“俗”是對立的關系嗎?如用俗、雅的美學審美觀對文藝作品進行評價,劃分標準只能是“非雅即俗”嗎?文藝作品中“雅中之俗”與“俗中之雅”的邊界該如何把握?這三個問題是筆者從文學范疇,對“雅”“俗”博弈之美學思考。
一、“雅”“俗”的對立博弈與融合互補
在美學史、文學史上,“雅”與“俗”既是對立、博弈的關系,也是融合、互補的關系。
對立、博弈反映的是“雅”“俗”在表象含義上的相異性。《毛詩序》云:“雅者,正也。”“雅”在古代最初的本義是“正”,而“俗”,《說文解字》中云:“俗,習也。”這里的“習”,指習俗。“雅”與“俗”的對立最早發生在音樂領域,“雅”指周朝王畿地區的曲調與當時的俗樂鄭聲相對,后“雅樂鄭聲”成為了儒家的傳統審美標準和文藝標準。春秋、戰國以后,直至魏晉、唐宋元明清各代,“雅”的范疇不斷發展,其審美內涵得以不斷豐富,形成了以“雅”為核心的概念群,如“高雅”“典雅”“清雅”“古雅”等。“雅”的審美內涵被抽象的定義為“超曠清逸,高尚脫俗”。而“俗”,也由習俗逐漸發展為“大眾的”“通俗的”“庸俗”“低俗”等含義。
融合、互補反映的是“雅”“俗”在內在關系上的聯系性。回望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的體式,某種程度上說,都是由俗文學“升格”為雅文學的。我們看西周至春秋的《詩經》、戰國的《楚辭》這兩部詩歌總集,就會發現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雅俗并存”。仔細辨識,其“雅”的成分無一不是由“俗”轉化而來。《詩經》由《風》《雅》《頌》三部分組成,《風》中所錄詩歌多來自民間,而《雅》分為《大雅》和《小雅》,其中《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唯《大雅》多為西周王室貴族作品,《楚辭》更是來源于楚國民間的祭歌。
由西周春秋的《詩經》到戰國的《楚辭》,由漢魏六朝的樂府民歌直至唐傳奇、宋元話本、宋詞、元曲以及明清的戲曲與小說等,眾所周知的《孔雀東南飛》《木蘭辭》《西廂記》、馮夢龍的“三言”、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施耐庵的《水滸》、吳承恩的《西游記》、曹雪芹的《紅樓夢》、蒲松齡的《聊齋志異》都是俗文學作品,確切的說都是傳統的俗文學作品,它們無不起源于民間,無疑應歸屬當時的俗文學范疇,只是由于時代的發展及文學的流變改變了它們的分野,“今”逐漸成為“古”,“俗”也逐漸成為“雅”。至近代,俗文學(近代俗文學)在通俗小說(特別是武俠小說和世情小說)領域有了較大的發展,出現張恨水、宮白羽、金庸、梁羽生等通俗小說家。由于近代的“雅”“俗”文學有意識地相互吸取對方長處,從而創造出很多“通俗型的雅文學”或“雅致型的俗文學”,這種形態構成了中國文學發展史的另一種重要表現形式,趙樹理的小說就屬于這種類型。[1](P5-6)
可見,文學中的“俗”與“雅”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兩者之間并沒有嚴格的界限。一方面,雅文學不斷從俗文學中吸取營養,另一方面,俗文學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取代雅文學的地位,或“升格”為雅文學。所以,“俗”“雅”之間并不是對立與博弈的關系,反而是融合與互補的關系。
二、“雅”“俗”的相對性
“雅”“俗”的融合互補使雅文學與俗文學的邊界變得模糊,但是對“雅”“俗”表象含義中存在的博弈與對立的理解容易使我們在對具體文藝作品評價時,陷入“非雅即俗”的劃分標準之中。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沒有考慮到雅俗的相對性問題。
何謂相對性?相對性是指在衡量某種事物時,由于采用的標準不是絕對的、唯一的,而是相對的、變化的,標準改變了,結論也會隨之發生相應的改變。
王國維《宋元戲曲考》中有一段話有利于我們對“雅俗之間相對性”的理解,“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獨元人之曲,為時既近,托體稍卑,故兩朝史志與《四庫》集部,均不著于錄;后世儒碩,皆鄙棄不復道。”這段話的前半段王國維做出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判斷,無論楚辭、漢賦、魏晉六朝五言、唐詩、宋詞、元曲,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文學樣式,所以,不能夠說后人不如前人。后半段,王國維闡述了如下觀點:元曲源于民間通俗文學,開始時文學地位比較低下,在明清兩朝沒有得到正史和學者的承認與重視,《元史·藝文志》及《四庫全書》都將元曲斥于之外。但是,元曲和唐詩、宋詞一樣,都是一個時代文學成就的代表,應該賦予其較高的文學地位。
王國維的這段話很好地說明了雅俗的相對性。即:相對于明清戲曲小說之輝煌成就,元曲略顯黯淡,但是,相對于整個中國文學發展史,元曲的地位卻是獨樹一幟的,容不得小覷。這就是參考的標準變化了,對所衡量的事物的結論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
還要注意的是,雅俗文學不僅在時間上表現出相對性,而且在空間上也表現出相對性的特征。“例如美國作家賽珍珠的《大地》這樣的文學作品,在美國就是俗文學,在中國卻已然接近雅文學了。”[1](P4)
分析“雅”“俗”的對立博弈與融合互補以及相對性問題,有助于我們理解“雅”“俗”之間的辯證關系。然而,過多的進行“雅”“俗”之間辯證關系的討論,對今人看待“雅”與“俗”的美學思辨,只是起到了客觀上對美學知識的普及作用,而對如何將雅之風氣在文藝作品創作實踐中進行表達以及對如何處理在文藝創作中“雅中之俗”與“俗中之雅”的邊界問題,意義并不深遠。因為,對“雅”與“俗”美學理論的探討一旦離開了文藝作品創作本身,就陷入了純粹的理論研究范疇。關于在文藝作品創作實踐中如何處理“雅中之俗“與“俗中之雅”的邊界,實現雅與俗的高度統一,筆者借助清代戲曲家李漁“俗中之雅”的觀點,以“追求有深度的通俗”做為雅俗審美的最終判斷。
三、在文藝作品中實現李漁的“俗中之雅”觀
李漁是明末清初的文學家、戲劇家、戲劇理論家和美學家,為中國古典戲曲批評做出了重要貢獻。“俗中之雅”是李漁在其戲劇理論代表作《閑情偶寄》之《演習部》“劑冷熱”中提出的一個觀點,在藝術作品創作中實現“俗中之雅”的理想追求是李漁劇論的重要藝術批評思想之一。在《閑情偶寄》談到戲曲的藝術效應時,李漁將“俗中之雅”的觀點一帶而出。他說:“傳奇無冷熱,只怕不和人情。……為人所必至……即使鼓板不動,場上寂然,而觀者叫絕之聲,反能震天動地。……較之滿場殺伐,鉦鼓雷鳴,而人心不動,反欲掩耳避喧者為何如?豈非冷中之熱,勝于熱中之冷;俗中之雅,遜于雅中之俗乎哉?”上述文字表述的是,表演者的表演要符合人情,表演內容應與劇情相符,要充分考慮到與觀眾的情感共鳴,如做到了這一點,雖然臺上的劇情、演員的表演是寂靜無聲的,但臺下觀眾的反應卻能很熱烈;當劇情與演員表演不符合人情時,“臺上雖然鑼鼓喧天,臺下的觀眾不僅不叫好,反而將此視為噪聲,掩耳目以避之。前者就是‘冷中之熱’,后者就是‘熱中之冷’”。[2](P508)“這冷與熱,就好比文藝作品傳達出的雅俗之風格,可以說,俗是外在的、形式的、具體的,大眾可以接受的;而雅是內在的、精神的、抽象的,是存在于大眾需求感基礎上的精神的升華。”
關于“雅”“俗”在一部文藝作品中的具體實踐方法以及想要達到的表現效果,李漁談到:“科諢之妙,在于近俗,而所忌者,又在于太俗。不俗則類腐儒之談,太俗即非文人之筆。”這段話說出了“雅”“俗”邊界把握問題。那么,如何處理“雅”“俗”邊界?又如何實現“俗中之雅”呢?李漁提出要“重關系”。
怎樣理解“重關系”?這要從話中提到的“科諢”二字說起。科諢,戲曲術語,又稱插科打諢。“科”是指滑稽動作,“諢”是指戲曲語言。在中國戲曲中人物角色有生、旦、凈、末、丑之分,生、旦有生、旦的“科諢”,凈、末有凈、末的“科諢”。在戲曲中,凈、丑這類角色本身帶有詼諧的意味,但是生、旦等卻是很文雅莊重的。所以,做生、旦的“科諢”更難,需要雅中帶俗,又于俗中見雅。為了讓本身不帶幽默特質的角色幽默起來,只能“于嬉笑詼諧之處,包含絕大文章;使忠孝節義之心,得此俞顯”。[3](P76)如此,將這些嚴肅、毫無幽默詼諧之感的正面角色的對白巧妙進行設計,轉化為帶有幽默詼諧色彩的臺詞,進而巧妙、自然地完成了“俗中之雅”的轉換。這就是李漁在戲曲藝術中闡述的“俗中之雅”觀。
試想,李漁的“俗中之雅”觀不也同樣適用于文學創作嗎?文學之中的“俗”“雅”邊界把握的核心也在于“重關系”,這里的關系指的是俗與雅的邊界關系,多一分即俗,少一分或許近雅。如林語堂在《寫作的藝術——文學之欣賞》中的一句:“論文字,最要知味。平淡最醇最可愛,而最難。何以故?平淡去膚淺無味只有毫厘之差。”所以,只要抓住“俗”與“雅”的本質內涵,文藝創作中的藝術語言、藝術形象、藝術題材內容,都可以實現“俗中之雅”。
四、追求有深度的“通俗”
有深度的“通俗”主要是針對文藝作品的寫作風格而言,“追求有深度的‘通俗’”是雅俗審美的最終判斷。說一篇文章“通俗”易懂,往往指的是“有深度的通俗”,它具有耐讀性,值得反復閱讀卻不覺乏味。還有一種通俗,我們稱為“膚淺的通俗”,這種文章讀起來味同嚼蠟,會使我們產生一目十行、敷衍了事的閱讀感受,讀過后不想再讀。讀文如識人,但凡能夠讓我們重讀的文章,都是好文章,但凡讓我們為之駐足的人,都是具有精神魅力的人。所謂經典之作能讓人讀上幾遍甚至十幾遍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我國著名的哲學家馮友蘭、作家錢鐘書等人的寫作風格就是這種“有深度的通俗”。他們的著作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通俗易懂。因為他們的思維清澈,文字表述起來自然如行云流水、通暢自如。摘一個片段,與讀者共同分享,感受一下何謂有“深度的通俗”。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簡史》中論述魏晉清淡名仕時寫道:“究竟‘風流’是什么意思?這是一個含義豐富而又難以確切說明的詞語,從字面上說,‘風流’是蕩漾的風和‘流水’,和人沒有直接的聯系,但它似乎暗示了有些人放浪形骸、自由自在的一種生活風格。”“我對英語中‘浪漫’(romantic)和‘浪漫主義’(romanticism)兩個詞的含義還未能充分領略;但我大致感覺到。這兩個詞和‘風流’的意思頗為相近。”
如果我們認真讀過《世說新語》,就會體會到魏晉名士會林山水的任放為達與琴詩自樂的高雅飄逸。“濯濯如春月柳”“朗朗如日月之入杯”這份發自內心的關于“美”的贊嘆,是魏晉人用自然美形容人情美的高尚情懷,有了對魏晉時代精神的整體感受,再來看馮友蘭先生對“風流”一詞的解釋,才會感到他對“風流”和“浪漫”的解釋是何等簡潔曉暢,然而又蘊含著豐富的內容。
中國現代作家、文學研究家錢鐘書先生,寫作風格也是典型的“有深度的通俗”,他在《論俗氣》一文中就“俗”“雅”問題進行了集中論述,他說:“俗氣不是負面的缺陷,是正面的過失。”同時借助《儒林外史》第29回中杜慎卿所謂“雅的這樣俗”的一段話,讓我們理解了“俗中之雅“與”雅中之俗”的邊界問題。這段話是這樣說的,《隨園詩話》所謂:“人但知滿口公卿之人俗,而不知滿口不趨公卿之人更俗。”這種現象是起于不自然的裝腔作勢;俗人拼命學雅,結果還是俗。
錢鐘書還寫到,“英國作家夏士烈德的俗氣說便是以此為根據。夏士烈德以為一切天然的、自在的東西都不會俗的,粗魯不是俗,愚陋不是俗,呆板也不是俗,只有粗魯而裝細膩,愚陋而裝聰明,呆板而裝伶俐才是俗氣。所以俗人就是裝模作樣的人。一切裝腔都起源于自卑心理,知道自己比不上人,有意做出勝如人的樣子,一舉一動,都過于費力,用外面的有余來掩飾里面的不足……”[4]如此通俗易懂的文字,任何人都會讀懂,也會愿意再讀,用以揣摩,用以修身。這就是“有深度的通俗”的不“俗”之處。
綜上所述,雅俗之辯構成了文藝批評范疇對稱性的兩方面,從其審美屬性上看,從最初只表達音樂聲調性質的“雅樂”和“鄭聲”的遠古審美分野,在經歷了不同歷史時期文化的洗禮后,已然轉變為具有雅俗觀念體系的兩大文藝批評范疇。從審美功能上看,對雅與俗的評判體現出人們對美的感受的特殊指定性。“雅文學”表現的是文人階層或少數人的審美趣味和審美價值,“俗文學”則以大多數群眾為審美主體。無論是“雅文學”,還是“俗文學”,圍繞其展開的雅俗之辯,終歸是個體“人”的思想與文藝作品創作實踐過程之辯,這個古老的美學命題,需要在當代文藝創作實踐中不斷調和與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