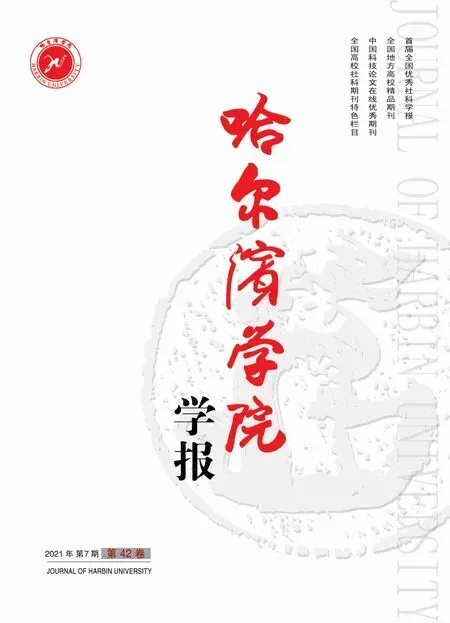論《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分工概念
宋雨勃
(黑龍江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6)
分工(Teilung der Arbeit)本身是一個經濟學的實證概念,這一概念在馬克思進行經濟學研究過程中進入了他研究的領域。就《德意志意識形態》這一文本而言,分工概念在使用頻次和邏輯地位上都非常重要。假如說,馬克思哲學新視界的天才提綱為《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那么《德國意識形態》就是此新世界觀的首次系統且具體的一個闡發。[1](P422)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分工概念是理解這一世界觀,即唯物史觀的關鍵。
分工這一概念在唯物史觀中所具有的核心性和基礎性的地位已經取得廣泛共識。如張一兵在分析《德意志意識形態》時寫道:“分工將之前在人本主義話語當中的異化規定取代。”[2]又如王南湜指出,“從分工來說明私有制的起源,便構成了一種唯物主義的邏輯”。[3]再如韓慶祥提出,“馬克思主義分工理論與唯物史觀形式,內在的聯系是不可分割的——形成唯物史觀與具有科學的分工理論不可分割,科學分工的理論僅在唯物史觀指導下才能制定。”[4]總體而言,分工概念及圍繞這一概念所產生的理論無論是就馬克思思想進程總體而言,還是對于唯物史觀自身而言,都有著邏輯上的重要地位。
但是,誠如阿爾都塞所言,人們“可能在分工的問題上受騙”。[5](P20-21)分工概念作為經濟學概念被橫向移植進入唯物史觀,其概念內涵及演進邏輯都值得考察。因而有必要回答的問題是,《德意志意識形態》時期的馬克思究竟在何種意義上使用分工概念,而“消滅分工”命題的內涵又是什么。
一、作為實證批判基礎和真實歷史邏輯的分工
分工概念在馬克思的視野中并非一直處于重要地位。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之前,馬克思已注意到分工概念。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寫作過程中,馬克思開始意識到了穆勒對于“分工”和“交換”這兩個概念的討論,這種注意的興趣也在后續的較長一段時間保留在馬克思的腦海中。他說道:“考察分工和交換是很有意思的。”[6]但是,這種興趣仍然服務于當時馬克思所關注的人的類本質之“喪失—復歸”或“人性—非人性”的邏輯,所以馬克思在表述這種興趣之后仍然回到了對于人本質概念的敘述上:“分工與交換為人活動與本質的力量——作為類的活動與本質力量——的顯著外化表現”,同時指認“分工和交換是私有財產的形式”。[6]由此可見,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之前的文本中,分工概念屬于從屬性地位,它還不是作為勞動過程的重要形式, 構成各時代的社會基礎,制約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的存在,而是一種從屬于人本主義異化勞動史觀的一般概念。
而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理論語境下,分工概念成為了分析和解釋歷史的基礎概念,這也就意味著馬克思的理論取向從哲學批判轉向科學批判,理論建構從價值評判轉向了對現實經濟社會結構的理論分析。在馬克思自身的理論架構中,對“人”“人的意識”以及所謂“人本能的意識”,或者說“人被意識到的本能”,這幾者的變換和發展,與生產效率的提升、需求的增多和作為兩者基礎的人口的增加相互關聯且在一定比例上成正相關。這意味著在討論意識本身時,馬克思已將其置于生產情境的基礎之上進行闡釋,而進一步來講——“分工只有從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的時候才真正成為分工”,而“它是與現存實踐的意識不一樣的某種事物”。[7](P26-27)
在撰寫《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時期,馬克思仍認為,“動物與自身生命活動為直接同一。動物不將自身同自我生命活動進行區別。它僅是自身的生命活動,人則讓自身生命活動本身演變成自我意識的對象。”[8](P57)而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注解到:“之所以人們存有歷史,就是由于他們一定生產自身生命,且一定用相應的方式來表達:這被他們自身肉體組織所牽制,人的意識也因此受到制約。”[7](P25)可以看到,對于人、人的意識而言,馬克思已不再預設存在一種具有先驗本質的(自由自覺活動)抽象的人,取而代之的是“有生命的個人”,并從其物質生產形式——分工進行解釋。從這個意義而言,分工不再是一種與人的本質相對立的生產組織形式,而是一種進行實證歷史分析的基礎。
此外,筆者認為,分工概念同時也是“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原則的邏輯構件。這集中體現于馬克思對歷史不同階段的劃分是從不同歷史階段中分工的邏輯劃分的。按照社會分工邏輯的逐層演變,馬克思將西歐非原始社會時期的歷史分成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部落所有制”時期的歷史,這個時期分工的邏輯還沒有完全形成,現實的分工狀態不發達,但在家庭成員中自然的分工已經形成,并在進一步擴大;第二階段是“公社和國家所有制”時期所代表的歷史,此時分工的形式已經相對發達起來;第三階段是“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開始興起。在這一時代,封建制度繁榮,但“分工是很少的”;第四階段就是“資產階級所有制”或者說“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在這一階段,分工的邏輯已經發展得逐漸完備。事實上《德意志意識形態》“相當于改寫了一部資產階級社會經濟的發展史,也是一部當代生產發展致使交往關系產生變革的歷史”。[1](P481)這一時期由于生產方式和貨幣制度的原因,資本的流動仍然相當有限,最后進入到馬克思所謂的“大工業”發展階段,也就是“生產力的要素主要是勞動力、土地、機器、設備和資本等”時期。[9]因此,資本主義或資產階級社會瓦解的原因也不再是因為其與“類本質”的對立,而是依循分工邏輯得出的必然結果。“整個人類社會歷史,不過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交互作用中,在人與自然的矛盾和人與人的矛盾的斗爭中,不斷通過創造性的歷史實踐而自我誕生和不斷生成的過程。”[10]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福柯指出:“馬克思用對生產的分析來代替對掠奪的譴責。”[11](P37-38)
從上文的論述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所使用的分工概念首先是實證意義上的批判基礎,另外則是在歷史解釋意義上的“邏輯”。
二、消滅分工的類型及其原因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尚未對分工進行社會分工、勞動分工和企業內部分工的區分(這一部分在1857年后的經濟學研究中才完成),但是仍然可以從馬克思對消滅分工的經典表述中確定其所針對分工類型——“只要不是自愿分工,屬于自然所形成的,那么人自身的活動對于人來講,就是異己的、和他對立的一種力量,此力量壓迫人,而非人在駕馭此力量。”[7](P19)可見,馬克思在這里所針對的分工就是自發性的社會分工。
值得考察的問題是,馬克思為何要消滅這一種分工,又或者說馬克思怎樣提出“消滅分工”的命題。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關于為何要消滅掉分工,馬克思這樣進行解釋:“由于分工不但使精神活動與物質活動、享受以及勞動、生產還有消費通過不同的個人進行分擔此情況成為一種可能,而且成為現實,而要使此三因素彼此不產生矛盾,則只有再進行分工消滅”。[7](P28)
具體而言,分工的以下特性是消滅分工的根本原因:其一,分工導致勞動及其產品最終走向了分配的不平等,也就是產生了所有制。以家庭為例,作為分工的家庭實質上構成了丈夫對于其他家庭成員的奴役,或勞動力的支配,而這正是現代經濟學對私有制的概念。所以,“這有力的論述表明了一種思想 :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分工只能是一種束縛人的奴役性的異己的社會分工。”[12]其二,分工致使個人、家庭與一切人的共同利益相對立,在國家、法之中,統治階級將“自己的利益也說成是普遍的利益”,[1](P477)但是在現實中,所謂普遍的利益往往與個人相對峙。其三,自發性的社會分工也就是說“社會活動的固定化”會讓社會中重新出現對自由人的奴役。馬克思對此進行了單獨的解釋:“受分工所制約,不同個人的共同活動形成一種社會力量,就是擴大了的生產力……關于此種力量的起源與發展趨勢,他們了解的非常少;所以他們不再對此力量有駕馭能力,相反此力量現在卻在經歷著一系列獨特的、不僅對人們意志與行為沒有依賴性,反而成為能夠支配人們的意志與行為的一個發展階段”。
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在論述分工之后在反面意義上使用了“異化”概念,這種反面意義體現在他指出之所以采用“異化”概念是“用哲學家易懂的話”,表明“異化”概念并非一個具有實際意義的邏輯規定,同時也意味著存在一個新的邏輯規定取代了它,這就是分工。
另一個被遮蔽的,但卻非常重要的線索是馬克思思想中對黑格爾歷史主義的繼承。從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對于古典經濟學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出黑格爾對于市民社會的基本態度——黑格爾將國家與法律界定為對市民社會的“否定性的制約和超越”。他將亞當·斯密理論中“看不見的手”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市場規律視為絕對精神異化自身的一種體現,而相對的絕對精神在這一層面如果想要向自身歸附,就需要一個更高階段的“絕對精神”來對上一層面的自由精神進行歸附。“國家與法的自覺調節”是絕對精神實現自我的一種呈現。這樣的觀點再回到馬克思廣義的唯物主義哲學上來說,《德意志意識形態》在同等意義上指出導致自發性社會分工的客觀力量同樣不是永恒性的,而是歷史性的。而二者的差別在于,黑格爾所運用的是抽象的思辨邏輯,在物化的必然王國之后是觀念的自由王國,而馬克思則從還原于實證的經濟現實出發,在物化的必然王國之后是現實的自由王國,但是可以從中看出二者共有的歷史主義基礎。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寫作時期,對于“消滅分工”這一概念的表述,其實質上是對于歷史過程中自發形成的社會分工的一種批判性分析,而“消滅分工”的命題源于經濟學科學中的確認而非價值判斷,同時這種經濟學科學的研究中伴隨著黑格爾式歷史主義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