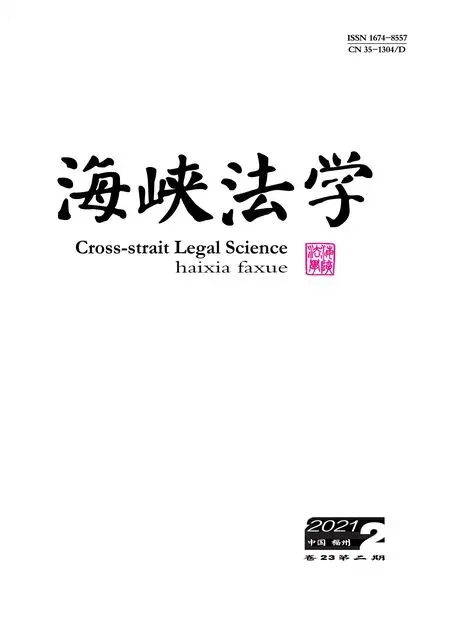思想得以表達
——著作權法中創作行為之客觀考察
陳馳
“創作”在著作權法中是產生作品的行為,《著作權法實施條例》將其定義為:“直接產生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的智力活動”。而作品“是指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具有獨創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現的智力成果”。通過行為的結果來界定行為,再分析行為結果的性質,邏輯的層層推進使得“創作”“作品”的認識主要著落在了“獨創性”概念上①筆者注:依據現行《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2條,關于作品的定義,“可復制性”與“獨創性”同為作品應符合的條件。但在現有技術條件下,沒有什么作品不能得以復制,“可復制性”也就失去了作為條件的意義。在《著作權法》第三次修正討論中,學者們主張去除這一條件。參見李明德、管育鷹、唐廣良著:《<著作權法>專家建議稿說明》,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另可參見劉春田:《知識財產權解析》,載《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4期,第109~121頁:“無論是文學藝術作品,還是創造發明,或是工商業標記,只要描述出來,在空間上就可以無限地復制自己”。在2020年11月通過的《著作權法》第三次修正案中,作品被定義為:指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具有獨創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現的智力成果。。依此,學界通常將其作為揭示著作權法保護對象的關鍵詞匯,卻也使它成為背負諸多困惑與爭議的概念。
關于著作權客體的思考,不論是經典的“思想與表達兩分原則”,還是作品與相近概念的區分,如創意、構思、素材、載體等,都關乎“獨創性”的解讀,通過回溯智力創作活動的過程可以獲得認識。在確認著作權主體時,同樣要探析創作過程中,誰貢獻了其智識并影響著作品的最終形成。不論是從個人作品、職務作品到法人作品之區分,還是合作作品作者的認定以及委托作品的著作權歸屬,乃至于著作權的內容的明晰,尤其是在理解著作人身權時,何以賦予創作者發表、署名、修改及保護作品完整權,都還是要從作品的創作過程來體悟。在當前對于著作權法中的“獨創性”普遍作客觀判斷的趨勢下,從創作過程入手來分析獨創性表達的形成,將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把握著作權法保護的客體范圍與著作權人權利的界限。
在創作活動中可對獨創性展開三個方面的客觀考察。首先,創作意味著創作者思想的外在呈現,他人可感知的符號組合形式承載著創作者內在的思想,思想是創作的基礎;其次,表達意指通過創作者的行為將其思想呈現出來,思想與表達融合于創作過程,由此,創作成果烙印上創作者個性;第三,思想之表達受到內部或外部種種限制,只有存在創作空間,即給創作者留有選擇可能的情況下,創作者才能通過表達呈現其思想。對創作過程進行回溯,這三個方面的考察交織融合,可實現對獨創性的客觀認識。
一、創作體現了“思想”
(一)天才之創造——文藝創作理論視角下的創作
蘇格拉底認為“詩人寫詩并不是憑智慧,而是憑一種天才和靈感;他們就像那種占卦或卜課的人似的,說了很多很好的東西,但并不懂得究竟是什么意思”。①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古希臘羅馬哲學》,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47頁。柏拉圖繼承了蘇格拉底的文藝創作“靈感說”,“凡是高明的詩人,無論在史詩或抒情詩方面,都不是憑記憶來做成他們優美的詩歌,而是因為他們得到靈感,有神力憑附著”。在柏拉圖看來:所謂“靈感”,就是詩神憑附后的神力驅遣,創作過程是一種“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的狀態。②同上,第18頁。在如此認識之下,文藝創作物與作者并無關聯,完全是外在的不可知的力量通過作者這一媒介向世人傳播訊息。詩人不但無法決定訊息的內容如何,甚至無法決定是否傳達,處于完全被動的地位。
亞里斯多德雖與柏拉圖都主張文藝的本質是模仿,但他認為文藝模仿要創造形象,故而提出“天才創造說”。此后,文藝創作者個人的天賦與努力才受到社會的認可。即便在神權統治的中世紀,無論是奧古斯丁的“模仿上帝式的自由創造”,還是托馬斯·阿奎拉所主張的“藝術作品是起源于人的心靈,但人的心靈又是上帝的形象和創造物,因而上帝的心靈才是自然萬物的源泉”③參見章安祺、黃克劍、楊慧林著:《西方文藝理論史——從柏拉圖到尼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90~101頁。,在強調上帝的終極性和本源性時都沒有對創作者進行完全否定,甚至進一步宣揚了創作者的理性意識和思維能力,突出創作主體的重要性。
到了文藝復興時期,教會權威的垮塌,使得“這一時期的確形成了對人的新看法。這種‘新人’被認為是世界的主人,他有理性和創造性,有能力參透任何奧秘,創造出新的東西”。④[荷]彼得·李伯庚著:《歐洲文化史》,趙復三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2005年版,第223頁。從而使得對文藝作品創作的認識擺脫了神學的桎梏,作者也獲得了最終的自由和獨立。⑤就不同文學藝術形式而言,獲得社會對其藝術性和創作者創造性勞動的認可在歷史上并非同時。貢布里希1960年對美第奇家族早期贊助的研究表明,直至15世紀,人們仍然認為“藝術作品是捐贈人的作品”。也就是說,被視為創作者的是贊助人而非藝術家,因為是贊助人全盤控制了題材和媒介。從存世的作品和其他文字記載(如傳記、合同、書信)中都驗證了他的結論。參見宮政:《淺析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贊助》,載《藝術探索(廣西藝術學院學報)》2006年第2期,第27~29頁。此后,在英國光榮革命后的現代版權確立過程中,丹尼爾·笛福明確提出“作者都應依法對其圖書享有毫無爭議的專有財產權”,雖在書商們的阻擾下,《安妮女王法》未將作者置于首要位置但也明確了他們的權利。⑥參見易健雄著:《技術發展與版權擴張》,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7~47頁。1767年,狄德羅公開發表了“就書商貿易而寄予司法官員的一封歷史的和政治的信件”。我們可以從中讀到,除了以啟蒙之名對該英國王室法令的頌揚之外,更有為了作者對其作品的控制而進行的熱忱辯護:“若一個精神作品——源于他受的教育、他的學習、他的時間、他的觀察、他的辛苦工作而得的獨特成果,若他生命中那些最美好的時光、最美妙的時刻,若他自己的思想、他心底的感觸,這些他自身最珍貴的部分,這些不會消亡的、使其不朽的,不屬于他,人與人之間可做怎樣的比較?!”⑦Alain Strowel.Droit d'auteur et copyright.Bruxelles: Etablissements Emile Bruylant, 1993, p.87.此后立法的歐洲大陸各國,作者權多被認為包含著人身權利與財產權利雙重內容,文藝創作者獲得了更全面的尊重和保護。
(二)文化之創造——符號哲學視角下的創作
現代解剖學發現任何生命體都有著一套察覺之網和一套作用之網——一套感受器系統和一套效應器系統,生命體都依賴著它們協同工作。而人除了有任何動物種屬都具備的感受器系統和效應器系統之外,還擁有著可被稱之為符號系統的環節。這就意味著人不再生活在一個單純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個符號宇宙之中。語言、神話、藝術和宗教都是這個符號世界的組成,人類在思想與經驗上取得的任何進步都將使得這一符號世界更為精巧和穩定。這使得我們應將人定義為符號的動物,從而理解對人開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①[德]恩斯特·卡西爾著:《人論》,甘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7頁。在卡西爾看來,進化論抹殺了人與動物之間的區別,人所擁有的智力與動物之本能在本質上不同②同上,第92~93頁。,就像人類獨有的命題語言區別于動物也能擁有的情感語言,及相應的符號世界區別于信號或信息世界③同上,第38~43頁。。故而“人——符號——文化”成了三位一體的東西。人的突出特征就是勞作。如果“人性”一詞指稱著任何什么東西的話,那么它就指稱著:盡管在它的各種形式中存在這一切的差別和對立,然而所有這些形式都是向著一個共同目標而努力工作——這個共同目標就是創造人自己的歷史,創造一個“文化的世界”。④同上,中譯本序。
知識產權的對象在形態上都表現為符號組合。著作權法維護著良好的符號生活之秩序:創作行為,就是組合符號的行為;作品就是由語言、文字、音符、線條、動作等被設定了意義的符號構成的。⑤李琛著:《論知識產權法的體系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133頁。任何人都不能過著他的生活而不表達他的生活,這些不同的表達形式構成了我們的符號世界。經由符號組合到文化創造,人才能面對其生存意義之追問,因為個體短暫生命歷程中獲得的每一點完善得到了鞏固與傳播并使其種屬獲益,從而個體也就具有了某種不朽性。⑥參見[德]恩斯特·卡西爾著:《人論》,甘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07頁。
(三)思想之表達——著作權法中的創作
首先,創作可被理解為思想的外在化呈現。一方面,思想是內部于人的,從現有的技術手段來看,我們還無法感知具體的和確切的大腦活動。思想屬于精神領域,不屬法律可以介入的范疇。只有將思想通過行為表現于外部,即精神領域中的符號組合形式投放于外部物質世界,才有法律控制之可能。另一方面,不包含思想的外部行為將不構成創作,如幼兒的信手涂抹,隨機的字符組合等。
其次,當我們認為只有人才擁有符號世界,而思想,即符號之選擇與組合,是人所獨有的能力與活動時,也就意味著創作的主體只能是人。故而創作不可能是任何動物或者人工智能所能從事的。這里的人還意味著是自然人,而非法律擬制的主體。法人作品則是著作權法基于便利生活的考慮而特別設立的。
再次,受思想支配之行為,并非都是創作。這里我們遭遇體力勞動與智力勞動之區分。創作行為應從智力因素加以把握,但這種智力與體力勞動之區隔卻又不宜絕對化,如繪畫作品、雕刻作品等可能既需要智力與又需要體力,故應從個人之技能或巧思的展現層面來把握創作。另一方面,個人之行為難以直接且徹底地歸屬于智力勞動或體力勞動,故而這種區分并未能為識別創作或作品提供太多助益。即便是智力勞動還有著“創造”與“創作”的不同,通常認為前者包括作品的形成,還包括發明創造的產生;智力勞動還包括著“創造”之外的揭示自然規律的“發現”等。
最后,當我們認為不同個體基于其出生、成長、經歷等的不同而有著各自不同的思想時,也就意味著不同個體有著各自不同的思想表達。故而,著作權法意在鼓勵多元化、多樣化的表達,是所謂“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在這樣的意旨下,思想內容如何與是否能構成作品無關。法官將被禁止去評價作品的價值或者作者的價值,因為評判作品的或其作者的天才的藝術價值、文學價值或美學價值將會導致著作權制度的保護與專斷而易變的標準結合在一起。①Michel Vivant.Les grands arrêts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Paris: Dalloz, 2004, p.119.甚至有學者認為,藝術創作領域實際上不存在客觀的價值評判標準,所謂價值并不屬于智力創作的客體。②[德]M.雷炳德著:《著作權法》,張恩民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頁。的確,我們無法就此指望立法者或者司法者能給出一個妥當的價值標準并執行之。因此,著作權法在決定是否給予保護時,自然只得保持謙卑而中立的態度而就思想之表達給予保護。
只是,個體擁有各自思想,卻并不意味著思想的表達必然呈現為相互區別的狀態,相互近似甚至相同的表達是可能的。著作權法并未如專利法那樣要求新穎性——即新的技術方案之前所未見。成為受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也可以相近甚至相同。
二、創作是一種“表達”
(一)創作行為與法律行為
在著作權法中,創作是產生作品的行為,作品生成,著作權即告產生。因而,從引發權利之發生的結果上看,創作是為法律事實。在民事法律領域中,能引發民事法律關系變化的法律事實包括自然事實和人的行為。前者指人的行為以外,能夠引起民事法律關系發生、變更或消滅的一切客觀情況;后者指人的有意識的行為。③梁慧星著:《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4~55頁。行為者,人之精神作用,意識的現于身體之狀態也。④史尚寬著:《民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頁。法律行為與創作行為同屬行為,但它們之間存在著不同。
為避免人們的自由限于是否接受國家分配的資源這一極端的狀況,法律必須肯定每個人的行為之自由,而法律行為是行為自由的最重要體現。正基于此,我們說,法律行為是實現私法自治的制度工具。法律行為是指私人的、旨在引起某種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此種效果之所以得依法產生,皆因行為人希冀其發生。換句話說,法律行為之所以產生法律后果,是因為行為人想引起這種后果,并且把這一意愿表達了出來。⑤參見[德]迪特爾·梅迪庫斯著:《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42~147頁。法律行為的本質在于意思表示,二者甚至被認為是同義之表達方式。⑥[德]迪特爾·梅迪庫斯著:《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頁。法律行為制度圍繞著意思表示展開,故而要分析表意人是否具有行為能力,即要求對行為主體作年齡與理智狀態的考察。換句話說,法律行為要求行為主體有著相應的意識能力。這與自己行為自己負責的現代民法原則相關聯,為的是保護相應的民事主體。
學者多認為著作權法中之創作屬于民事法律事實中的事實行為⑦佟柔著:《中國民法學·民法總則》,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頁。。事實行為的法律后果完全產生于法律,因而與行為人的意思毫無關系。⑧[德]迪特爾·梅迪庫斯著:《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59頁。這意味著法律并不考察行為人的行為動機或目的,相應的法律規范呈現為:一個典型的事實構成與一個法律后果表述。故而,事實行為之重心在于行為人之行為的客觀分析,只有在行為符合法定之構成時,才會引發法律確定的后果。正因此,就創作行為而言,著作權法將其確定為產生了作品的行為,相應的法律后果則是著作權的產生。故而,不同于法律行為要考察行為人的行為能力,著作權法并未就創作主體課加條件,而重在考察創作行為本身。
(二)創作意思與表達
創作作為事實行為,法律不考察行為人之意思,似乎邏輯上就要求考察相應行為的結果是否符合法律的規定。但是,在行為人不具創作意思或者意識狀態存疑的情形下,如夢游或精神錯亂狀態下的囈語與繪畫、幼兒的信手涂鴉,如果僅僅看最終的行為結果,將可能確認其為作品。因為,即便是專業人士有時亦難以區分幼兒的信手涂鴉與現代藝術畫作。將唐宋詩詞中的詞匯按出現次數而排出次序,而后任選數字串找到對應序號的高頻詞也能形成似是而非的詩句。在文藝表現形式如此豐富之現下,單就客觀結果來看,任何符號組合都可能滿足著作權法對作品的要求。因為,我們本就無法判定文藝之天份以什么樣精神狀態才能承載,又是在何等的年齡足以表現。
故而,只從行為之結果來判定是否構成創作存在障礙。我們應回溯行為過程,考察創作者的思想如何與物質載體相結合而呈現于外部。
創作行為被確定為“直接”產生作品的智力活動①《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3條:著作權法所稱創作,是指直接產生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的智力活動。為他人創作進行組織工作,提供咨詢意見、物質條件,或者進行其他輔助工作,均不視為創作。。直接,意味著對行為結果與創作者智力貢獻的密切關系,還意味著那些只從事間接的、輔助性工作的主體未能將其思想表達匯入最終的結果,因而不是創作者。以雕塑作品為例,通常要求藝術家親力親為,要求最后作品的每個細節、每一線條出自藝術家之手;而為完成那些以山體為載體的巨型雕塑,著作權法則不會要求藝術家們親自搭建腳手架并完成每塊山石的處理。就像是建筑師的作品可能是在龐大的建筑施工隊伍協同工作之下呈現為建筑實體。究其原因,著作權法保護的是那些承載著作者個體思想、觀點、技能等的表達,這包括著小型雕塑的每處細部而不包括大型雕塑的那些輔助性的處理。
2008年的方正“倩體字”著作權糾紛中,就該字體中的單個字是否構成受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引發學界討論②參閱《知識產權》雜志2011年第5期所組織的眾學者關于方正倩體字一案的專題評述。。多位學者都從字庫的形成過程即創作行為來考察。字庫的制作包括多個環節:設計同一風格之字稿;確定字體結構與基本筆畫;將這些字體構件輸入電腦,由電腦組合成字;人工修正美化;質檢。③劉春田:《論方正“倩體字”的非藝術性》,載《知識產權》2011年第5期,第9~10頁。正是通過回溯方正字體的形成過程,劉春田、李琛教授認為字體的形成只是普通勞動的結果,沒有形成作品。許超教授主張不能作為美術作品受保護,但可探尋其他的保護制度。李雨峰教授認為字庫不是傳統的書法作品,也不是實用藝術品,賦予字體私有權利將會產生壟斷結果,最終會損及公共利益。張平教授引入了客觀性較強的“識別性”概念,來幫助判斷是否具有原創性。雖然學者們的結論不同,但都從字體的形成過程出發,探求創作意思的呈現及可能的保護。
三、創作要求思想“得以”表達
當我們接受行為是思想的外在化表現,基于我們警惕藝術價值判斷將我們導向武斷而采納對于獨創性的客觀化考察立場時,我們卻可能會陷入任何表達行為都可能構成創作的迷惑。因此,從創作表現了“思想”,創作是一種“表達”這兩個論斷出發尚不足以把握創作行為。我們需要一個合適的,與藝術價值無涉的外在立足點,具體分析地個案中的創作行為,進而判定是否產生作品。
(一)限制條件與創作空間
在創作者進行思想之表達時,總是存在著種種限制,或者是外在的或者是內設的,創作則是在這些限制條件下進行選擇,在可能的空間中展現主體之思想。客觀上看,在限制條件增加到極致的情形下,可能的表達空間極度受限而將使得創作者個人化的思想無從表達,創作無法實現,作品也就無從生成。
我國古文通常沒有使用現代標點符號,為方便人們閱讀欣賞,需要許多專家學者依據其專業知識,增加標點符號,并斷句分段。就如“中華書局訴大眾文藝出版社案”中,法院提出:“所謂古籍點校,是點校人在某些古籍版本的基礎上,運用本人掌握的專業知識,在對古籍分段、標點,特別是對用字修改、補充、刪減做出判斷的前提下,依據文字規則、標點規范,對照其他版本或史料對相關古籍劃分段落、加注標點、選擇用字并撰寫校勘記的過程”。①參見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 2008) 東民初字第 09562 號民事判決書。這一過程是一個智力勞動的過程,但就加注標點、斷句、分段的工作來看,雖有依據點校者利用其淵博的知識探究古籍原意,進行深刻思考和仔細斟酌,但就點校的結果來看,很難說是包含了點教者的個性化思想而成其為作品。就如王遷教授所言,“只要對一種思想觀點只存在一種或極為有限的表達方式,就發生了思想與表達的‘混同’,該表達就不能受著作權法的保護。至于對某一問題客觀上是否只存在一種思想觀點,還是每個人都可以提出各自獨特的思想觀點,則在所不問”。②王遷:《古文點校著作權問題研究——兼評“中華書局訴國學網案”等近期案例》,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第11~19頁。這正反應了客觀上的限制,導致創作空間受限以至于無法形成作品的認識。當然,在點校古文中,將包含加注標點、斷句、分段的選擇依據和思考過程綜合而形成的文獻,則毫無疑問是受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
(二)思想未得表達與著作權法無從保護
1.單純事實消息
《伯爾尼公約》第2條第8項規定:“本公約所提供的保護不得適用于日常新聞或純屬報刊消息性質的社會新聞”。1967年斯德哥爾摩會議報告指出,“本款的含義是:本公約不保護單純的新聞或各類事實,因為這類內容并不具備構成作品所需的特征。”③王遷:《論<著作權法>中“時事新聞”的含義》,載《中國版權》2014年第1期,第18~21頁。說是事實,強調的是它的共有資源的性質,作品都蘊含著對共有資源的運用,但單說事實不夠直接,這里的正確理解,應該是時事新聞不具有獨創性。
“單純事實消息”在我國著作權法第三次修改前原為“時事新聞”,這樣的改變只是措辭上的變化。按《著作權法實施細則》的規定:時事新聞,是指通過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等媒體報道的單純事實消息。其意指由直接反映事實情況的信息要素構成的消息。通常是消息制作者為盡量快地發布而又讓人一目了然地獲取事實狀態的目的而制作出來的。這里的限制主要源于消息制作者之自我設限,克制自己的個性表達,依據其工作經驗對發生的事件抽取關鍵要素組合而成的,通常表現為字數極為有限的簡訊。就同一事件進行快速的消息傳遞,消息制作者可抽取的要素必然十分有限,當總體信息量縮減到一定程度,將會使得信息要素及其組合的形式只有有限的可能空間。在外在事件的客觀實際與內在于消息制作者的自我克制之雙重限制的情況下,單純事實消息未能成為制作者思想之表達,也就不成其為作品,無法獲得著作權法的保護。
如何能在有限的字符數量之內抓住重點準確傳遞信息,毫無疑問反映著信息發布者的技能與智力投入。相較于作品之標題也可能符合獨創性的要求而獲得著作權之保護而言④《十二國著作權法》翻譯組編:《十二國著作權法》,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65頁:法國知識產權法典,L.112-4。,我們知道,實踐中著作權法不予保護的單純事實消息定然十分有限,消息發布者進行自我限制以致其所發布的信息不再體現其思想的終究是極端的情形。
2011年6月23日北京地區的一場暴雨過后在網絡上出現的“地鐵瀑布”照片引發了人們對網絡圖片著作權的諸多爭論。曹新明教授提出,我國臺灣地區“著作權法”將時事新聞限定于語文著作(文字新聞),不包括其他形式的新聞報道著作,是一種可取的做法。⑤曹新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5條第2項之修改》,載《法商研究》2012年第4期,第17~20頁。王遷教授同樣認為,就照片來看,“除了為了精確復制而進行純粹復制型的翻拍,以及完全由機器自動拍攝,各種照片幾乎都被認為是符合獨創性要求的作品”①王遷:《論<著作權法>中“時事新聞”的含義》,載《中國版權》2014年第1期,第18~21頁。。因為,始終給拍攝者留有選擇空間的普通照片難以被判定為單純事實消息。
2.歷法、通用數表、通用表格和公式
公式,一般指用數學符號或文字表示各個數量之間的關系的式子,具有普遍性,適合于同類關系的所有問題;亦可泛指可以應用于同類事物的方式、方法。②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第6版)》,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451頁。公式排除著作權法保護的原因在于:就一個給定的情形要求進行抽象,并用公式正確地呈現其中多個要素之間的關系,可供選擇的公式表現形式非常有限③典型的例子:愛因斯坦提出的質能公式:E=MC2,反映的是質量與能量之間的關系。正確反映質量與能量之間關系的公式表達只有寥寥幾種罷了:E/M=C2; E/C2=M ……就愛因斯坦揭示的質能關系而言,毫無疑問是其偉大的思想活動的成果,可就該質能關系的公式表達來說,無法容納著作權法下作品所要求的“思想”。,以致于公式制作者完全沒有空間表達其思想。故而這一公式不是其思想的表達,不是作品。歷法,指用年、月、日計算時間的方法。④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第6版)》,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797頁。歷法同公式一樣,正確表達的空間非常有限,抹殺了思想表現之可能性。表格,指按項目畫成格子,分別填寫文字或數字的書面材料。⑤同上,第86頁。立法者用“通用”為限定詞,還是反映此類“通用表格”沒有給制作者留下思想表達可能性。與時事新聞在制作者自我設置限制的情形下成為單純事實消息不同,公式、立法與通用表格無法成為作品是因為外在的限制使得作者欲表達思想而不能,從而不是作品。
正因此,李琛教授將獨創性表述為“作品的表達有取舍余地”,只要客觀上作品的表達并非“必然如此”就具備獨創性;而在判斷作品時,是先判斷表達中是否包含了取舍空間,再認定產生該表達的行為是否構成創作。只是,究竟在怎樣的取舍空間中獲得結果,卻終究要回溯創作的過程,未必如李琛教授所言能直接從結果得知。⑥參見李琛:《謝綰樵與獨創性》,載《電子知識產權》2005年第8期,第58頁。
采用上述方法對掘進工作面風筒布置方式及高壓外噴霧降塵系統進行優化后,掘進工作面進風側及回風側測點處硫化氫濃度及凈化效率檢測結果見表1。可以看出,經過風筒位置優化后硫化氫治理效率在原有基礎的平均值上提高6.3%,進風側掘進機司機及其后5 m處硫化氫體積分數均降低到了3.6×10-6以下,在調整風筒位置情況下,對外噴霧布置調整后進風側硫化氫體積分數降低到了1.8×10-6以下,回風側體積分數降低到了6.1×10-6以下,對硫化氫的治理效率均值達到了95.6%。
正基于上述這兩類對象處于智力活動無獨創性可能的極端狀態,學者主張在未來的《著作權法》修訂時,無需明示它們不適用《著作權法》,因為按照《著作權法》,它們本就不符合作品的要求。⑦參見李明德、管育鷹、唐廣良著:《<著作權法>專家建議稿說明》,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14~216頁。
四、獨創性客觀化考察之影響
隨著知識產權保護的不斷發展,以及新型作品(尤其是計算機軟件)的產生給著作權法帶來的變化,著作權法中的獨創性呈現出一個客觀化的趨勢⑧參見[德]M.雷炳德著:《著作權法》,張恩民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頁;Michel Vivant.Les grands arrêts de la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Paris: Dalloz, 2004, p.121~123.,從理論上降低保護門檻。而另一方面,著作權人所擁有的權利則隨著傳播技術的發展而不斷擴展。著作權法不斷降低的作品要求與不斷豐富的作者的權利體系雙重變化下,引發公共領域受到侵蝕的擔憂。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加以分析,一方面是獨創性門檻之降低與相應作品所能獲得的保護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是平凡的智力勞動成果獲得著作權的保護是否會使得后來者的智力創作活動受到阻礙,后來者可能運用的文藝資源是否受到侵蝕。
(一)著作權法之保護門檻與人工智能“創作物”
本文所主張的創作行為意味著“思想得以表達”。僅就“思想”與“表達”展開的探究難以使我們擺脫判斷主觀化、評判標準搖擺不定的狀況,并極易使我們錯誤地從創作者本身或作品的藝術、社會價值的角度找尋答案。因此我們轉而考察思想表達之可能性的問題,探尋創作者是在怎樣的限制條件下、何等的選擇空間中,是否“得以”表現其思想。由此,我們不是主觀地考察創作者或者作品,而是聚焦于創作行為之客觀過程。在限制條件未使選擇空間極端受限,而是有充足的選擇度的情形下,我們認為作者的思想獲得表達,構成創作,成為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
對于創作行為的客觀考察對應著獨創性的客觀化,卻并不必然地意味著獨創性的低要求。“限制條件——創作空間”的關系可以容納對于獨創性或高或低要求,就如張平教授對于方正倩體字的考察,基于與劉春田教授相近的對于字體制作過程的認知,卻主張一種相較于后者而言較低的作品要求①張平:《再談計算機字體的法律保護》,載《知識產權》2011年第5期,第19~23頁。。亦如李琛教授主張只要“表達并非必然如此”就具備獨創性,但在方正倩體字一案中認為“字庫設計中沒有任何超越漢字本形設計的整體創作”,“字庫作為一種智力成果需要得到法律的保護,但其與書法作品無關”。②李琛:《計算機字庫中單字著作權之證偽》,載《知識產權》2011年第5期,第28~31頁。
顯然,獨創性之客觀化考察并非決然地去除了主觀之判斷。個案中,怎樣的限制條件下或多大的創作空間才能符合獨創性的要求顯然仍有著不同的認識。只不過獨創性之客觀化要求我們回溯作品的創作過程,盡量擺脫基于創作者或其行為結果的預判而產生的對于我們判斷的扭曲。
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與應用手段的不斷成熟,人工智能在音樂、新聞、視覺藝術等各個領域中參與到創作活動的現象引發社會各界的關注。美國人工智能機器人通過學習己經能夠生成極具藝術性和美感的美術作品,并在畫廊和博物館展出。美聯社與人工智能公司合作開展的人工智能新聞寫作平臺Wordsmith,如今己經達到每季度三千余篇的產量。在財經和體育等需要大量數據分析的新聞報道領域,人工智能在利用大數據和大規模分析數據等方面的優勢,使其成為最先介入“創作行為”的領域。我國騰訊等互聯網公司也自行開發了Dreamwriter等軟件來批量撰寫財經類新聞報道,并已能根據不同受眾群體生成差異化的風格和版本,由此引發了人工智能將代替記者的討論。③參見熊琦:《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著作權認定》,載《知識產權》2017年第3期,第3~8頁。著作權法中如何認定“人工智能”及其“創作物”也成為一時之熱點問題。
易繼明教授主張,雖然人工智能不是“人”,但也不是“物”。不能因為人工智能創作物的創作主體不是自然人,就否定其可版權性。“從客觀性判斷標準來說,智能作品完全可以滿足獨創性要求。版權的目的是明確包含創造力本身,而不僅僅保護由人類產生的創造力,故創造性來源于計算機而非人類,并不影響其獲得版權法的保護”。“總的來說,對創作物可版權性進行檢驗,還是要回歸到版權法的基本目標:法律賦予相關主體一定期限的獨占權,最終是為了激勵更多的創作物產出和傳播,增進社會整體福社。對于人工智能創作物版權問題的討論,以及對版權法規則的解釋和拓展,自然也因循這一基本方向”。④易繼明:《人工智能創作物是作品嗎》,載《法律科學》2017年第5期,第137~147頁。易繼明教授對版權立法目的之認識是公共利益、社會利益為基點的,這樣的認識使得其更接近于英美版權體系的功利主義傳統,而不是以人的權利、人為主體的法德作者權傳統的立場。
易繼明教授同樣注意到了獨創性標準的客觀化趨勢,但本文主張的客觀化在于避免主觀的價值判斷與文藝創作的多樣性之間的沖突,強調對思想表達之個性化的尊重和保護。易繼明教授所重視的創造力與著作權立法目的沒有關聯。就如王遷教授旗幟鮮明的立場: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在表現形式與人類創作的作品類似,如機器人繪制的圖畫、寫出的新聞報道或譜出的樂曲,則需要從其產生過程判斷其是否構成作品。迄今為止這些內容都是應用算法、規則和模板的結果,不能體現創作者獨特的個性,并不能被認定為作品。在不披露相關內容由人工智能生成時,該內容可能因具備作品的表現形式而實際受到了保護,但該現象是舉證規則造成的,并不意味著著作權法因人工智能而改變。⑤王遷:《論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在著作權法中的定性》,載《法律科學》2017年第5期,第148~155頁。
吳漢東教授同樣認為,“人工智能生成之內容,即‘機器創作的作品’,實為人機合作的智力成果,并沒有離開著作權法的人格主義基礎”。張平教授更提出,“從學理上看,著作權法是為了保護并激發創作者創作的積極性,促進經濟、科技的發展和文化、藝術的繁榮。機器的實際控制人利用機器創作,將權利歸屬于該實際控制人就是對其創作的肯定。肯定其擁有著作權,就是肯定其相應的人格權和財產權都會受到法律的保護。這樣的保護又能激勵控制人的創作熱情,繼續利用機器創作出新的作品,形成一個良性循環,最終達到增加社會精神財富的目的”。①吳漢東、張平、張曉津:《人工智能對知識產權法律保護的挑戰》,載《中國法律評論》2018年第2期,第1~24頁。的確,計算機技術所帶來變化并沒有動搖著作權法,考察作品的生成過程,能為我們判斷是否構成作品及著作權歸屬提供清晰指引。
(二)著作權之擴張與公共領域之維護
如前所述,獨創性的客觀化并不必然導致獨創性標準的降低。然而,著作權隨著技術的發展而不斷擴展和豐富則是事實。②參見易健雄著:《技術發展與版權擴張》,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這種擴張由兩個方面構成,一方面,思想表達的可能手段隨著技術發展不斷豐富,新的作品類型不斷涌現。照相機、留聲機、攝影機、錄音機、收音機、電視機、電子計算機等都不斷地推動著著作權客體范圍的擴展;另一方面,這樣的技術應用同時意味著對作品的傳播、利用的方式在不斷豐富,這要求這著作權法肯認相應的權利來順暢文化、商業之發展。這樣的著作權之客體與內容的雙重發展自然會不斷地沖擊獨創性標準,深刻我們對其的認識。客觀化的立場,能使得我們謹守不對行為結果進行價值之判斷的立場,保持著作權法的健康發展。
獨創性之客觀化考察從理論上的確為降低著作權保護之門檻提供可能,而創作水平的較低要求是否會導致公共領域中的資源被占據而成為這些作品的組成部分,進而成為私權客體,從而構成后續文藝創作的巨大障礙?這樣的疑慮可以從創作行為之解讀而獲得消解。
當我們從“限制條件——創作空間”的關系入手來把握創作行為之可能性時,我們知道作者之思想在限制條件所框定的選擇空間內獲得表達。另一個方面,這意味著作者的選擇與取舍之外的作品之組成要素是為公共資源。通過存在創作空間的肯定,我們確認相應的創作行為,進而承認行為結果是作品。就如,游客們同一時間在同一地點拍攝所得的黃山迎客松的照片,即便相似甚至相同,著作權法理論上都賦予這些照片以作品之身份并給予保護,卻又不妨礙未來的人們在此各自再拍攝出同樣受到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著作權法保護門檻之降低并不必然導致公共領域遭到侵蝕。
總之,當前的現實發展不存在因著作權之擴張而導致其他人既有利益受損的問題,就目前的形勢而言,包括著作權在內的知識產權保護不力仍然是中國面臨的嚴重問題。③參見李明德、管育鷹、唐廣良著:《<著作權法>專家建議稿說明》,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08頁。而通過對創作過程展開考察,秉持獨創性分析的客觀立場,不失為問題的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