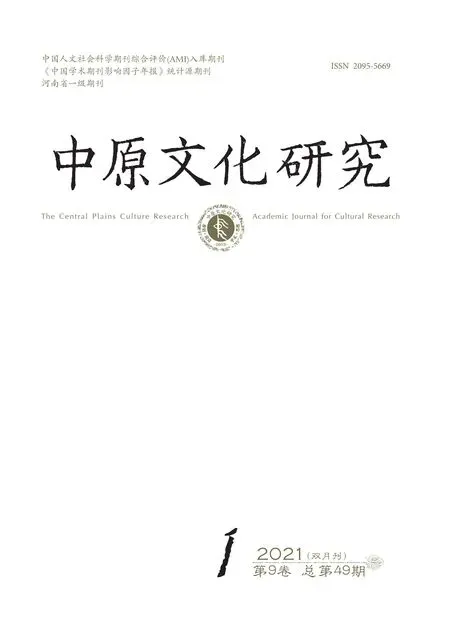漢代鄭州的“薄亭”與“亳聚”
張立東
經過30多年來的資料積累和研究討論,鄭州商城即商代亳都的說法已經成為學術界的主流①。然而學無止境,此說的一些細節仍有待進一步完善。
鄭州商城的廢墟在春秋晚期仍被稱作“亳城”。戰國中期韓國占領這座廢都之后,即全面修繕其內城,并命名為“管”。此后鄭州之“亳”名逐漸被世人遺忘,到西漢中期人們已不知鄭州地區曾經名“亳”,從而導致了諸多亳說的不斷創立[1]213-226。不過,漢代的鄭州地區仍有包含“亳”字的亭、聚之名,這些小地名為我們探討鄭州商城的本名提供了重要佐證。
傳世文獻將“薄亭”歸于滎陽,而考古資料表明“亳聚”就在常廟城址。綜合考察這兩個小地名,有助于整合傳世文獻、出土文獻和遺跡遺物,以推斷兩者的具體位置,從而考察鄭州商城留在漢代地名方面的遺痕②。希望我們的努力能為完善鄭亳說、厘清鄭州的歷史沿革略盡綿薄之力。
一、薄亭
《后漢書·郡國志》:“熒(滎)陽有鴻溝水。有廣武城。有虢亭,虢叔國。有隴城。有薄亭。有敖亭。有熒澤。”[2]3389
“薄”即“亳”。此兩字的通假是沒有任何問題的,而且“薄”是“亳”的通假字中使用頻率最高者。鄒衡師曾羅列關于湯都亳的先秦文獻,其中《孟子·滕文公下》《墨子·非命上》《荀子·正論》《荀子·王霸》《戰國策·楚策四》《淮南子·泰族》等為“亳”,而《逸周書·殷祝》《墨子·非攻上》《荀子·議兵》《管子·輕重甲》《呂氏春秋·具備》等為“薄”[3]185。
關中地區有“亳亭”。《史記·封禪書》:“于(社)[杜]、亳有三社主之祠。”集解:“韋昭曰:‘亳音薄,湯所都。’瓚曰:‘濟陰薄縣是。’”索隱:“徐廣云:‘京兆杜縣有亳亭,則“社”字誤,合作“于杜亳”。且據文列于下皆是地邑,則杜是縣。’案: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社。皇甫謐亦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而臣瓚以亳為成湯之邑,故云在濟陰,非也。案:謂杜、亳二邑有三社主之祠也。”[4]1376《漢書·郊祀志》:“于杜、亳有五杜主之祠、壽星祠。”師古曰:“杜即京兆杜縣也。此亳非湯都也。不在濟陰。徐廣云:‘京兆杜縣有薄亭,斯近之矣。’”[5]1208同為徐廣之語,《史記》索隱引為“亳亭”,《漢書》顏注則引為“薄亭”。
由《史記》《漢書》和《后漢書》的記載來看,漢代通行的寫法似乎是:關中者為“亳亭”,鄭州者為“薄亭”。漢代的“亭”與當時的郵驛系統關系密切[6]162-164,其定名應當比較系統化,有可能刻意用不同的字將兩者區別開來。
當年鄒衡師曾把鄭州地區的“薄亭”作為鄭地之亳的補充證據[3]196,筆者則直接將滎陽的薄亭、敖亭與湯都亳、仲丁都隞相聯系,以與偃師的湯亭對讀[1]225,現在看來,這種聯系值得進一步討論。
關于薄亭的具體位置,很少有人論及。李維明斷定漢代的薄亭就在鄭州的漢城:“《后漢書志》第十九郡國一河南尹:‘滎陽……有薄亭。’……按:東漢時無‘鄭州’名,此地時屬河南尹滎陽轄域。鄭州市內存有依據東周城址南部修建的漢代城址,因其附近出有商代‘乇’字刻辭和大量東周‘亳’字陶文,與《后漢書志》記滎陽薄亭相合。據此判斷鄭州市東漢時期為薄地,曾設有‘薄亭’,歸滎陽所轄。”③劉余力則推定薄亭在今河南滎陽市西,但并未列出任何證據[7]。
雖然現在還無法準確考定漢代“薄亭”的確切位置,但是可以根據《后漢書·郡國志》的記述,大致推定其范圍。《郡國志》:“中牟有圃田澤。有清口水。有管城。有曲遇聚。有蔡亭。”其中的管城應即疊壓鄭州商城內城的戰國韓城。對照上引的“滎陽縣”條,可知《郡國志》將“薄亭”“管城”分別列入滎陽、中牟兩縣,兩者顯非一地。換言之,漢代的“薄亭”與“管城”之間必有一定距離,“薄亭”不可能位于“管城”之內。
只是分屬兩縣的兩地未必相距很遠。如果兩者都位于兩縣交界地帶,其間的距離也許很近。鑒于漢代已經不知鄭州乃早商亳都,“薄亭”之定名或許依托某個與亳都相關的地名,而不一定與亳都直接相關,因此其與鄭州商城的內城有一定距離也是可以理解的。與郵驛關系密切的漢代之亭一般位于居民點之外的道路之側,而且取名明顯偏愛古地名,因此“薄亭”不一定直接因商代亳都而得名。
二、亳聚
“亳聚”陶文是1985年張松林在常廟城址采集的。該城位于鄭州市二七區馬寨鎮的常廟村周圍,距鄭州韓城西南角約10 公里。總體為長方形,南北長約2000 米,東西寬約500 米[8],周長約5000 余米。當初調查時城墻仍高達10 余米,基寬20 余米。城內散落有大量戰國秦漢陶片和瓦片。在10 余枚豆柄上發現有戳印陶文,內容有“公”“亳”等。
根據調查報告的文字描述,“亳聚”應為戳印而成,只是發表的拓本上僅見左側上部和下側的邊欄。兩字均為陰文,上下排列,其間未見邊欄,因此兩者應是同章雙字,而非同器雙章。對于陶文的出處和時代,報告無詳細說明。陶文是在“戰國秦漢遺址與城址”一節報導的,而在“遺址概況”一節里列舉的六處“遺址”與“城址”中,僅“常廟城址”部分提到出土有陶文,故此“亳聚”陶文應出自常廟城址[9]。靠上的“亳”字與鄭州戰國韓城出土的印文“亳”字極似。靠下之字右半有所殘缺,但左上角的“耳”是比較清楚的,釋“聚”應是目前的最優選,已為《陶文字典》等采納[10]231。
關于陶文的具體年代,學者之間有不同看法。鄭杰祥提到“在今鄭州市的西南隅,發現印有‘亳聚’二字的秦漢時期的陶器文字”[11]232,但附圖之名則是“鄭州西南郊出土秦代‘亳聚’二字合文”[11]239。綜合以上兩點,可知是將其定為秦漢時期,而更傾向于秦代。李維明、袁廣闊等則視之為東周遺物④。
我們認為“亳聚”陶文很可能屬于漢代。首先,“聚”字的寫法近于漢隸,而異于戰國文字和秦篆。楚系簡帛文字的數例,上部大多是左“耳”右“又”的“取”字,下部為三“人”,與“眾”字下部相同。睡虎地《日書》乙本和楚帛書也有下面從二“人”的例子[12]45,[13]386。《說文》所收秦篆也是下從三“人”。漢隸中的“聚”字下部的主體為一豎劃,上有帽狀短劃,左右各有兩劃,雖然是由早期的“三人”之形演變而來,但字形已有很大變化[14]129下。常廟出土“亳聚”之“聚”,下部中間的豎劃很清楚,其左右各有兩個近乎平行的斜劃,總體與漢“聚”近而與楚、秦之“聚”遠(圖1)。

圖1 戰國秦漢之“聚”
作為聚落名稱的“聚”盛行于漢代,見于《漢書·地理志》和《后漢書·郡國志》,而未見先秦和秦代聚落稱“某聚”的材料。《說文解字》釋“聚”:“會也。從,取聲。一曰邑落曰聚”。段玉裁注:“邑落謂邑中村落。”[15]387《漢書·平帝紀》:“立官稷及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顏師古注:“張晏曰:‘聚,邑落名也。’師古曰:‘聚小于鄉。’” 班固《東都賦》:“是以四海以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唐李善注:“韋昭曰:‘小于鄉曰聚。’”[16]38王先謙認為韋昭之語是顏師古注之本[17]142。《史記·五帝本紀》:“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正義:“聚……謂村落也。”[4]34
綜合以上諸釋,可知聚是村落,而且是“邑中村落”,規模小于鄉。王彥輝斷定:“‘聚’‘聚落’……就其概念而言是戰國以后的新名稱,具有自然形成的聚居地的含義;‘里聚’‘聚邑’‘××聚’則是國家行政管理下的稱謂。其中‘里聚’指的是開放式的村落,‘聚邑’則屬于具體的行政村,‘××聚’則是名都大邑周圍的衛星城或縣屬的鄉鎮。由‘聚’而發展為‘里聚’‘聚邑’‘××聚’,是由‘聚’、‘邑’演變為鄉鎮的大體路徑。”[18]綜合段玉裁所說的“邑中村落”,以及王彥輝所歸納的自然居地、衛星城或縣屬鄉鎮等,我們似可將“聚”理解為自然形成的、類似城鎮化的、有較多非農業人口的居民點。
明確了“聚”的意義之后,就可以深究“亳聚”兩字的含義。就像《漢書》《后漢書》中的眾多某聚一樣,亳聚應即名亳之聚。關于以“亳”為聚名的原由,鄭杰祥認為:“聚即作為居民點的城鎮村落,聚落以亳命名,可見秦漢時期人們仍然知道這里原是古代的亳地。聯系上述資料,‘亳丘’‘亳聚’所以以亳命名,都應是沿襲了這里的商代亳邑的名稱,正如同現代的鄭州市有一條稱做‘商城路’的道路一樣,它無疑是因為這里有座商代城址而命名。但是由于文獻記載西周管叔封于此地,因此后世就管城名顯而亳邑名隱。”[11]232李維明則謂“‘亳聚’指亳地之居邑”[19]。二說有所區別,鄭說強調聚用亳名,李說則強調亳地之聚。二說的共同之處是認為“亳聚”中的“亳”是指整個鄭州商城區域,而且都認為“亳丘”“亳聚”的命名方式是一樣的。這兩種說法顯然都是值得商榷的。
其一,“亳丘”“亳聚”的命名方式有相似之處,但從本質上是不同的。“亳丘”主要用來指稱亳城故址,對于當時的城邑來講主要是虛稱,而非實稱。“亳丘”之稱與現代漢語中的“殷墟”有一定相似之處。“殷墟”雖然在有些語境中可以代替安陽,但主要用來指稱商都遺址,并非現代的行政機構或聚落名稱。“亳聚”則是實打實的聚落名稱,“亳”只是這個聚落的名稱,或許與亳都故址有關,但不一定直接相關。
其二,鑒于上文所論“聚”這種聚落的性質,“亳聚”的具體所指應是某個小聚落,規模上要遠小于鄭州商城或戰國韓城。換言之,亳聚應是漢代“管城”之外的一個聚落。
至于亳聚的具體所在,首先應該考慮陶文所出的常廟城址。近年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對常廟城址進行了發掘,新的出土資料對我們推定亳聚的位置頗有助益。目前看來,將亳聚指認為常廟城址一帶是可行的。發掘者斷定此地在戰國時期“是專業的制陶城,因為處處都有制陶作坊和陶窯的遺址”。發表照片的豆把之上有兩個單獨的印文,上一個是“亳”字,確與鄭州戰國城東北隅出土的亳字陶文頗似(圖2)。可見此處制陶作坊至少是鄭州韓城“亳”字陶豆的制造地之一。若用現代語言表述,似可將此處制陶作坊理解為“亳”字陶器的特供作坊。

圖2 常廟古城出土印有“亳”字的陶豆
將亳聚定位于常廟城址,也有利于重構其命名過程。雖然最初調查時常廟城址“內散落有大量戰國秦漢陶器殘片和瓦片”,但后來發掘的陶片卻“多為春秋戰國時期的遺物”[20]303,并有報道將城址明確稱作“戰國古城”。由此可以推斷常廟城址的年代很可能與鄭州韓城相當,漢代已成廢墟。城內出土的漢代陶片,包括印有“亳聚”者,則反映了漢代仍有人居住。雖然已有資料尚不足以說明該地漢代聚落的規模與性質,但受戰國制陶業的影響,可能仍有不少的非農業人口,與上文所論“聚”以非農業人口為主的慣例相符。至于其以“亳”為名,很可能與曾經長期大量生產戳印“亳”字的陶器有關。作為“亳”字陶器的特供作坊,原來的地名中也可能包含“亳”字。鄭州亳都舊城被韓國人改造為管城之后,“亳”之舊名逐漸淡出人們的記憶,至西漢中期的董仲舒時代鄭州的亳都已鮮為人知了。此時,作為曾經的“亳”字陶器特供作坊,即便以前沒有以“亳”命名,當地俯拾即是的“亳”字陶片也可能引導人們將此處制陶之聚命名為“亳聚”。
結語
漢代鄭州的“薄亭”與“亳聚”是鄭州商城在地名方面的遺痕,兩者是可以整合的。當時坐落在鄭州商城遺址之上的是歸屬中牟縣的“管城”,與歸屬滎陽縣的“薄亭”應有一定的距離。將“亳聚”推定在“管城”正西偏南的常廟城址,且認定“亳聚”與滎陽縣的“薄亭”相距不遠,正與滎陽縣在中牟縣之西的相對位置相合。只是“薄亭”與“亳聚”屬于不同的系統,兩者有可能位于同地,也有可能是相近的兩地。
“薄亭”與“亳聚”位置的推定對鄭州商城即商代亳都的討論頗有助益。戰國中期韓國占領鄭州商城的廢墟之后,對內城進行了全面修繕,并命名為“管”。此后,已成為古地名的“亳”僅在一些特定的場合,例如紀念晉悼公十一年亳城之盟的儀式上使用,因此鄭州商城為商代亳都的認識逐漸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董仲舒《春秋繁露》和司馬遷《史記》對鄭地之亳絲毫未提,說明當時已經不知“管城”就是商代的亳都。“薄亭”與“亳聚”為我們留下了漢代居民對商代亳都的點滴記憶,這些記憶碎片對于我們確認鄭州商城的真實身份大有助益。
注釋
①鄒衡:《鄭州商城即湯都亳說》,《文物》1978年第2期。中國古都學會、鄭州古都學會編:《中國古都研究:鄭州商都3600年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古都學會2004年年會論文集》,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②“遺痕”一詞參見徐蘋芳:《現代城市中的古代城市遺痕》,《遠望集》,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年版,第695 頁。③參見李維明:《鄭地亳城文獻補正》,《中原文物》2009年第6 期,第49 頁,注釋40。④李維明:《鄭州出土商周時期“乇”聲字辭與湯亳探尋》:“鄭州市區西部常廟所存東周城址當屬‘乇’聲‘亳’邑落,其規格低于‘亳丘’……鄭州商城據地約方76 里,東周2 座分別出土‘亳丘’‘亳聚’相鄰城址聯地不小于方87 里,與東周文獻記載商湯亳地域相近。”詳見《故宮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1 期。袁廣闊:《鄭州商城與偃師商城關系的考古學觀察》:“鄭州一帶出土東周時期帶‘亳’‘亳丘’‘亳聚’……等陶文。”詳見《鄭州大學學報》2004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