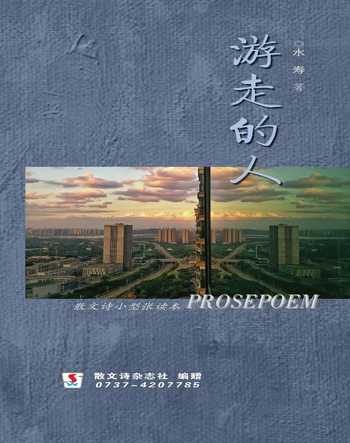雨的重奏
王瑤宇
小舟上
不在地上,離世俗太近
也不在天上,不食煙火。
坐在一葉小舟上,溫點(diǎn)酒,剛剛好。
靜靜地聽著,微雨用牛毛縫補(bǔ)萬物的聲音。
水鳥不安地拍著剪刀形的翅膀,濺起的水花剛剛落定,便飛遠(yuǎn)了,盡頭只有亭子屹立在那里,背后仿佛藏著一個隱約的朝代。
荷葉接收了所有的旋律,并進(jìn)行了改編,使耳膜的聽覺,不斷地上漲。
水位也不斷地上漲——
你知道,雨正在下著,打在身上的牛毛,正在變成晶瑩的珍珠,水位遲早會漫過你的心臟。
于是你飄著。
春天的船帆,駛進(jìn)了秋天。
行 走
我不需要避雷針,繞開受傷的閃電和被驚醒的靈魂。
我也不需要撐開的雨傘,握在幸福的手中,好過握在絕望的手中。
我不停地穿過雨的簾子,后面還是雨的簾子;穿過淚水的皺痕,后面還是淚水的皺痕。
嗚咽聲,回憶的種子,連綿不絕。
我就這樣不停地走著,與晃動的寒冷、幽暗的光、廢棄的寧靜擁抱在一起。
腳下的路區(qū)別于往常的路——
像一條鞭子,與遠(yuǎn)處的燈光扭打了起來。
前 奏
狗吠的聲音,悠遠(yuǎn)粗獷,像一匹打開的布匹,裹住了整個袖珍的村莊。
風(fēng)也織著布匹。
一張張,一次次,很快地涂抹了一輪均勻圓潤的月亮。之后,風(fēng)更大了,老屋背后的竹葉相互鼓掌,仿佛在鼓勵它的囂張。
整個世界的草木樹葉都在飛。橫飛。
聲音嘈雜。很少有這么熱鬧的會議,供沒有到過鄉(xiāng)下的城鎮(zhèn)居民聆聽。
再之后,便是雨水。將空氣淋濕。將心臟淋透。
躺在床上的人,焦躁不安,翻了翻身子,令大地微微地傾斜。
往上面灑
春天已經(jīng)踩到了冬天的尾巴,雨,還在跟一堆柴禾較勁,稀稀疏疏地往上面灑。
劈柴的周老頭在咳嗽。
坐在病椅上的周老頭,沒有坐在病椅上。
連椅子也消失了。
雨,還在稀稀疏疏地往上面灑。
壩子上什么都沒有,除了那堆雨中的柴禾。
整個院子里什么人都沒有,除了周老頭的老伴兒。
日子如此灰暗漫長——
冬天已經(jīng)踩到了春天的尾巴,雨,還在跟一位老太太較勁,稀稀疏疏地往她心里灑。
太陽
一個下雨的晴天,或者一個晴天下著雨,思想,都會長出它的胚芽。
胚芽震顫。
陰與陽,一與二,水與火,生與滅,動與靜,走與停,物質(zhì)與精神,終于放下了宇宙大爆炸以來產(chǎn)生的頭疼與偏見,友好地交融在一起。
那一天是奇跡的一天。
那一天是一個完整的圓。
我,小小的人類與山河,與天地,進(jìn)行了交匯。
少 女
春雨被墨客比作少女,是否抽象了一些?
想想,纖纖的步履,催眠的含蓄,久違的浪漫,足以淹死一個人,仿佛懂了,卻又不懂。
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形單影只,窗外的一縷縷春風(fēng),在桃花上寫著一闋闋宋詞,春雨被比作少女,可能清晰了一些;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已有所愛,卻在遙遠(yuǎn)的地方,隔著數(shù)重山,與一張張信紙,春雨被比作少女,可能又清晰了一些。
春雨是不安的老虎,是萌動的情詩……
過 河
以天空為鏡的河流,橫在眼前,像一句橫在眼前的、波光粼粼的誓言。
那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決絕。
一個七歲半的孩子,在回家的路上,用腳探了探,再探了探,勇氣驟減,決絕的也就更決絕了。
就連雨季的空氣也缺氧了起來。
他想,還是等爺爺來背他過河吧,時間的指針轉(zhuǎn)得很慢,而爺爺也一定會來的。
他在爺爺?shù)谋成希w會到了溫暖。
而爺爺?shù)纳眢w讓他想到了樹干——山里才有的百年老樹干。
那是他第一次為爺爺撐傘,大雨已經(jīng)變小,他的手,緊握著傘不放。
劇 場
雨夜,窗外的萬物醒著,并排且圍著圈,以黑夜與雨水為墨,在大地上一遍遍地寫著寒冷又饑餓的自傳。
我在桌前讀著一本書,從果皮讀到果核,曲折的歷史,作為精確的預(yù)言,仿佛暗示著雨變成雪之必然,雪壓斷樹枝之必然,樹枝新生之必然。
當(dāng)然,在夜里看書之必然,正如在雨天看書之必然。
就是這樣的一個雨夜,將被我牢牢銘記。
那天,我讀的是一本歷史之外的歷史,自由中帶點(diǎn)拘謹(jǐn),窗外的群山,像陡然的心跳,卻被紀(jì)律,輕輕地按住。
之 后
雨后,雨水的刷子,將大自然的皮層進(jìn)行了清洗,空氣關(guān)上了舊空氣的大門,而孔雀般的彩虹卻沒有在目光的上游出現(xiàn)。
夢沒有消失——
“如果說彩虹是雨的后裔,
那么,夢就是肉體的精魂……”
不能像失望的畫家那樣失望。
不能像氣餒的音樂家那樣氣餒。
“如果彩虹沒有掛起,野花,一簇簇,還在開著;鳥群,一排排,還在飛著……”
雨后,一道思辨的彩虹升起,不用心,看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