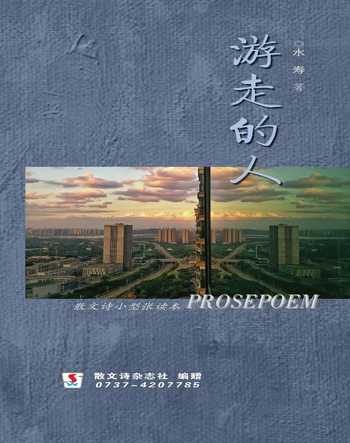大家說
尹紅 顏炯 傅艦軍 王魯湘 彭代英 蕭紅亮



王魯湘:可以這么說,19世紀末,20世紀初,國人心目中都隱隱然期許著湖南人能以鐵血精神和大無畏的犧牲勇氣,扛起民族崛起的重任。湖南人亦是這般自許,楊度就在他的《少年中國歌》中慷慨高唱:“中國苦為德意志,湖南當為普魯士”“若教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死光!”尤其在湖南士人身上,這種原始的野蠻性同湖湘文化的“衡山正氣”結合起來,竟然充溢著奇特的精神張力,發散出令人著迷的人格魅力。齊白石之所以在舊北京文化人的圈子中獲得激賞,并最終征服整個士林,其實就因有這樣的背景。
你看小奇筆下這三個老倌子,多愜意,多自在,不僅眉眼嘴角鼻翼有表情,所有肢體都在釋放信息,連腳趾頭也在說話。我們也看到,小奇的筆墨也似乎受到這三個老倌子的情緒感染,不由自主地灑脫搖曳起來,筆墨語言與人物性格完全合二為一,它們同時迸發出快活的信息,尺幅不大的畫面居然有了一個氣場,瀟灑詼諧,像快樂的湖南花鼓戲,讓我們身體里快樂的多巴胺源源不斷分泌。
彭代英:《失眠者》以一種先鋒、前衛、鮮明的態度,張揚水墨的表現主義,如席勒式的大膽直白、犀利冷峻、洞穿人性,又堅守著水墨藝術的蘊藉空靈、神秘浪漫與內在張力,化三維空間為二維平面,創造了一種獨具意味的現代水墨圖式……內部結構的枯榮穿插,空間留白的式樣對比,線條組織的疏密,畫面構圖的完整與殘缺,點線面與黑白灰的碰撞與交錯,有如騎士般縱橫馳騁,以一種震徹心靈的節奏,奏響了一曲東方文化殿堂里的《命運》。
失眠者頭上那抹令人驚悸的藍,讓人想起《百年孤獨》,馬貢多小鎮那個傳染了失眠癥的布恩迪亞家族特有的表情,那是一種天生驚訝的目光和孤獨的神情……《失眠者》顛覆了常見的繪畫作品中的文學意義上的敘事性表達,通過對人物形象符號化的刻畫與表達,特別是眼神中所透析出來的空茫、無奈、惶惑、驚悚、惆悵、疲憊、憂傷,直接叩問人的內心,撞擊人的靈魂。這種獨特的符號化釋義,表達的不只是作為個體的人的現實意義上的失眠,更關注的是整個人類的精神意義上的失眠。
在藝術的殿堂里,小奇是一個失眠者。他始終保持一份繁華背后的冷寂與孤獨,有如一條寂靜深邃的河流,賦予了他的畫作蒼涼深沉的底色;而對于藝術,他又深懷一種宗教信徒般的忠誠與熾熱,執著地在探索的暗夜里仰望燦爛的北斗,那北斗,其實就是自己的內心,這是失眠者的靈魂,也是藝術的靈魂。
正因為有了靈魂,所以,失眠者不朽。
蕭紅亮:以苦澀為底色的浪漫的表達,是成熟男性畫家站在高處的藝術剪影。我用兩個詞進行概括,一個是“詩人”,一個是“歌者”,這是詩意的引入和歌者的吶喊。
尹紅:整個長卷用傳統的筆墨方式傳達出一種現代人的生活感悟和體驗。畫面通過粗細長短曲直干濕濃淡變化不一的線條組合,構成畫面節奏,并巧妙、自由地運用這些線分割成的面,以一種類似蒙太奇的方式,將不同時空的人和事、歷史人文、風土人情,神秘而合理地統一在一起,畫面中出現的帶有傳統文化符號的劃龍舟的龍的形象、傳統樣式的石獅形象、年畫中的門神形象……這些夸張的人物造型、平面帶有裝飾感的場景,充滿著浪漫、神秘、豪爽、詭異。
顏炯:那貌似縱情粗放的筆墨間,一個個鮮活的生命躍然紙上,或男女老少、漁樵耕讀、士子商賈,或滄桑已久、夢寄春秋、春懷蕩漾,或蹈舞恣意、醉眼迷離、南柯初就……須臾間,一河江水,一世情愁,由一個個形象次第演繹。
傅艦軍:讀陳小奇的畫,總有一種強烈的代入感。因為生活的年代差不多,又有一樣的故鄉,我們懷有同樣的鄉愁,他畫中的人物、場景和細節,我感覺那么熟悉和親切。
他畫過一組《鄉村樂隊》。我總覺得那個鼓起腮幫子吹嗩吶的,就是我二爺爺;那個打鼓的,就是我父親。父親的鼓點堅定而連貫,鼓槌起落間,下巴同步微微上下,目光掃視左右,所有動作和表情絕對都在同一個節奏上。樂隊的每一個人都隨著他,時而如熱鍋炒豆,時而如細雨滴答,時而聲震如雷,時而如竊竊私語,結尾處總有一聲清脆而短促的鼓點,除拇指和食指外,其余三指順勢按在鼓皮上,所有響器齊齊地,戛然而止。我在《鄉村樂隊》里清晰地看見了自己的親人。
陳小奇曾經是鄉村樂隊里的重要成員,撞鈴、木魚、鼓手、小鑼、大鑼,甚至二胡、嗩吶、笛子,樂隊里哪個位置缺人,他就頂哪個位置。操鈸的有兩個,一個叫牛四卵彈,一個叫貓屎,都兇神惡煞,照那臉相畫下,貼在門口可以當門神。吹嗩吶的叫細山癲子,兩條瘦長腿,走起路來像搓草繩,家里出身不好,愛罵沖天娘,要是喝二兩,會罵個通宵。打大鑼的叫二駝子,平日里,除了拾狗糞,便是打大鑼,50歲了,光棍。陳小奇畫的是自己的鄉村樂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