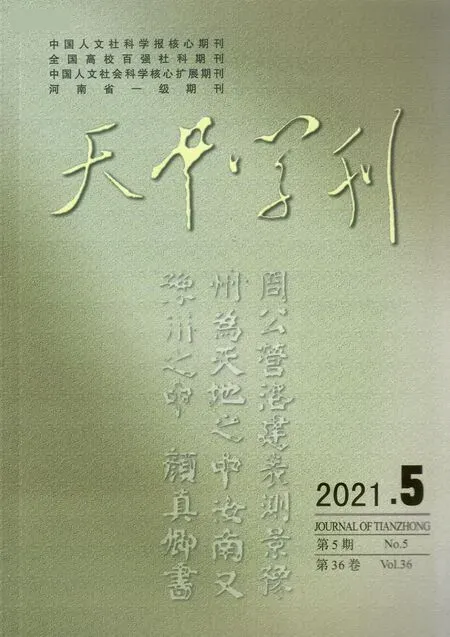個體詩意與共同體想象
——李佩甫創作論
王華偉
(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 外國語學院,河南 鄭州 450046)
李佩甫涉足文壇30余載,其創作緊扣時代脈搏,與新時期尤其是21世紀以降中國社會的大發展彼此呼應。作為地地道道的城里人,李佩甫的文學世界卻能同時從城鄉兩大空間汲取用之不竭的養分與力量。即便遠赴省城生活和工作,其創作的坐標系也從未離開平原這一獨特的審美空間,直至“平原三部曲”,李佩甫為自己貼上了平原敘事代言人的詩意標簽。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李佩甫將對平原的想象與書寫視作自己的文學使命與美學追求,不論是對共同體的想象還是對個體的述說,無不代表他對中原人性格抱有的詩意化理想。所謂的“一方水土”指的是共同體,所謂的“一方人”指的是個體,共同體和個體交織于由李佩甫建構的鄉土文學空間中。
李佩甫的創作往往超越個體的得失,站在重構共同體的高度,在個體與共同體的碰撞與交織中反思時代精神與現實存在,想象并找尋回歸家園的詩意道路。共同體是人類社會重要的存在形態與組織形式,在推動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功不可沒。共同體包含了人類存在的集體化傳統常態與個體化新形態,以及整體與個體之間的博弈,是理解李佩甫文學創作的重要線索。李佩甫通過自己建構的文學世界完成了對共同體的詩意化想象。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全球化、商業化和城鎮化的持續發展,傳統個體和共同體都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變化甚至蛻變與衰落,如何在充滿碎片、解構與異化的當下繼續表達鄉土社會的共同體意識與集體精神,是李佩甫一直在深入思索的問題,也是其共同體理想主義的想象根基。
一、小人物,大英雄
生長于城市的李佩甫是標準的城里人,但其創作的源頭卻是中國社會的底層鄉村。李佩甫擅長描寫底層勞動人民的現實體驗與邊緣生活,其作品因對中原鄉土文化母題以及中原人遭遇的空間擠壓、身份迷茫、倫理選擇等的深刻書寫而備受關注。“作為人,我們既不能實現希望,也不能不再希望。”[1]李佩甫在掙扎,其作品在掙扎,作品中的小人物也在經受著來自靈與肉的雙重考驗與內外掙扎。李佩甫作品中的小人物大都是殘缺的,有的生理上有殘缺,有的精神上有殘缺,有的身份上有殘缺,但面對現實的苦難與命運的不公,他們又不得不承載中原人身上獨有的堅韌、不屈與坦然。李佩甫試圖借助小人物為中原底層人民發聲,揭示中原文化及其地域精神本質上根植于小人物的自我肯定。對于小人物而言,他們對集體或共同體的本能渴望更加強烈,面對生存的壓力和生活的重擔,他們需要彼此守望相助以實現屬于他們的共同生活。“就其存在而言,人是來自共同體的存在,他受到共同體的照料,并面向共同體的存在。對人來說,存在(to be)就意味著同其他人共存(to be with)。他的實存就是共處(coexistence)。”[2]共同體已經成為李佩甫筆下小人物最渴望獲得的基本存在方式,他們看似個體化自由化存在的事實背后掩藏著對重構共同體的期待與堅持,與之相伴而生的是對未來的大膽設想和對命運的英勇抗爭,他們成為來自底層有理想、敢行動的“大英雄”。
在李佩甫的小說中,各式各樣的小人物形象、日漸凋零的鄉村世界以及與鄉村剪不斷理還亂的城市邊緣地帶,無不給人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李佩甫小說中的小人物大都曾經經歷過或正在經歷著不同的城鄉空間錯位感與地域陌生感,基于尋夢的渴望抑或迫于生存的壓力,他們從鄉村涌至城市,又從城市逃回鄉村,在經歷無數次往返之后,他們不僅為城市發展貢獻了巨大力量,同時也給鄉村空間帶來了現代性甚至后現代性的騷動,這或許正是他們在夾縫與掙扎中的生存之道。《城的燈》的主人公馮家昌是標準的底層小人物,他利用參軍等形式完成了從鄉村到城市的遷徙和身份轉變,成為4個弟弟心中八面玲瓏的大英雄。“鄉下小子”馮家昌雖有成功的驕傲與自豪,但作為鄉村逃離者的他,最終還是因為在城市遭遇身份迷失和在故土遭遇精神困境而自責與懺悔,但已無法回到逃離前的過去。所以說,這種看似瑣碎雜亂的城鄉底層語境的建構,不經意間拉近了廣大讀者與小人物們之間的心理距離,也縮小了藝術審美與現實世界之間的空間阻隔,使讀者在無形之中感受到小人物背后的分裂、無助與漂泊,以及他們對平原精神的守望和平原人性格中的堅守。鄉土是真正屬于小人物的精神共同體,這同時給予他們成為時代英雄的巨大力量。
李佩甫大部分的小說都把小人物經歷的現實磨難作為對中原精神的忠誠踐行以及幫助他們實現從小人物到大英雄蝶變的必經之路。小人物的生活似乎總是不如意多于如意,盡管他們不得不忍受身體或精神層面的煎熬與摧殘,但總是忍辱負重前行,延續著自己作為小人物應有的擔當,并對由“真善美”構成的鄉土共同體保持著堅守的初心,無論身處城、鄉都表現出英雄般的責任感與使命感,這多少帶有古希臘神話的悲劇色彩與英雄情結。《生命冊》中身材異常矮小的蟲嫂,外表看起來侏儒,內心卻非常強大。為了供養三個孩子上大學,她放棄臉面與尊嚴,甘愿收破爛,以卑微的一生換取兒女的出人頭地,最后用小人物的卑賤鑄就了大英雄的崇高。李佩甫筆下的小人物有著很多共同的生命體驗,他們大都生活在社會底層,有著不愿提起的過往;他們大都承受著現實的重壓,有著不想觸碰的靈肉傷疤;他們大都背井離鄉懷揣夢想,有著不堪回首的經歷與體驗。他們是堅守鄉村共同體的“老實人”,面對鄉土巨變與時代機遇,拼命想成為時代的弄潮兒,雖有猶豫、膽怯與退縮,但他們依然對未來抱有期望,希望自己踏出一條屬于時代英雄的道路。小人物的一生雖缺乏真正的壯舉,甚至處處留有悲劇的色彩,但正是這種悲劇化的體驗為他們增添不少英雄的力量與氣質。
古希臘以降,英雄在西方世界莫不遵循神話學大師約瑟夫·坎貝爾提出的“隔離-啟蒙-回歸”模式,這樣的英雄養成之路在中國底層英雄身上同樣可以找到蛛絲馬跡,甚至已經被貼上類似的標簽。與毀于欲望的駱駝不同,《生命冊》中“喝百家奶,吃百家飯”長大的孤兒吳志鵬雖有知識分子的尊嚴和回饋故鄉的決心,卻一生漂泊于城鄉之間,游離于自我之外,始終難以獲得真正屬于自我的身份認同,默默承受著小人物的酸楚與無奈,但其守護故土家園的靈魂卻從來沒有迷失。對李佩甫筆下的小人物而言,隔離意味著背井離鄉擠進城市,努力為自己建構新的生活方式;啟蒙則更多地體現為一種掙扎,一種“留而不能、走而不愿”的痛苦與徘徊;回歸指的是在經歷了城市的排擠、失落與失敗之后,又一次回歸曾經屬于自己的現實空間,并希冀再次獲得靈肉與身份的雙重認同。毋庸置疑,小人物已經具備了成為“大英雄”的潛質,在他們看似平凡的空間經歷中,內在精神的凝聚與升華被凸現出來。事實上,他們對鄉土世界的逃離,是一種看似解構的重構,在經歷一番或波瀾壯闊或迷失自我的城市空間之旅以后,他們逐漸成為守護鄉村共同體最后的英雄,這是一種滕尼斯式的對共同體的前現代解讀。滕尼斯認為,和他人共處的愿望普遍存在于所有人心中,共同體如守望相助的和諧家園一般成為人們的集體精神與共存意志,并最終成為默認一致的存在狀態與空間形態,具體到小人物身上正是英雄之間的“惺惺相惜”,以期建構一種屬于他們自己的獨特規范體系和空間秩序。
小人物身上的鄉土標簽應該呈現更深層的隱喻意義,也就是通過在城鄉間的徘徊和掙扎,他們準確詮釋了自己才是鄉村共同體真正的守護者以及小人物身上具有的英雄精神。小人物建構了鄉土文化的精髓,善良、淳樸、勤勞、正直的鄉土品格在他們身上盡顯,其內心對鄉村共同體的共識早已形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小人物代表著鄉土世界最原始最自然的力量,與鄉村渾然一體,并由此獲得詩意化的個體存在感與歸屬感,盡管這樣的感覺并不一定真實可靠。李佩甫正是通過小說人物頻繁地在城鄉空間位移及隨之做出的種種選擇,一步步把生在農村的小人物練就成有擔當、有情懷的“大英雄”,樹立起一個個底層英雄形象。小人物的價值在于他們對內心的堅守、對責任的擔當和對英雄的崇尚。李佩甫正是以小人物的視域,書寫著底層個體對英雄主義的詩意想象與追求。
二、小體驗,大倫理
小說是現實體驗的記錄,也是倫理精神的文本。李佩甫的創作聚焦于中原大地,以對中原人性格、精神和倫理的挖掘見長,作家本人對現實的情感體驗與審美觀照充滿明顯的倫理想象,李佩甫“50后”和知青的雙重標簽為其文學創作中的倫理書寫提供了現實契機。李佩甫善于捕捉各色人物的道德體驗,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建構起帶有“平原”氣質的倫理精神。在其首部長篇小說《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孫》中,李佩甫已經試圖以倫理的視域看待商業浪潮對鄉土世界的沖擊與破壞。所以,“小說所敘之事,往往是處于特定的倫理關系和道德情景之中的人的事,而這些事里不僅包含著小說中人物的道德反應,也反映著作者的道德態度和道德立場”[3]。倫理共同體在李佩甫的作品中呈現出兩極分化的局面,既有對傳統倫理的堅守與升華,也有對新型倫理的解構甚至消解,或許這種包含著倫理異化元素的共同體更有可能再構成另一種形式的倫理共同體,因為共同體不僅是對共同點的概括,同時也是對異質性的吸納與融合。基于此,倫理也好道德也罷,在李佩甫的小說中“并不意味著李佩甫是在鄙夷或要抽離道德,恰恰相反,在他的創作中,道德一直處于敏感的核心部位”[4]3。實際上,李佩甫在其作品中呈現出的道德觀很多時候會被外界曲解甚至誤解,他的本意絕不是要解構道德在當下社會的存在感與合理性,也不是要為道德式微找到現實的根基,而是努力為道德重構與復興進行詩意化的想象和審美化的再構。基于此,鄉土被李佩甫賦予倫理秩序重建的重任,這一點非常符合涂爾干對共同體的道德性期待。然而,鄉村社會在變革和進步的過程中出現道德失范、倫理失序等不和諧現象在所難免。涂爾干指出:“要想治愈失范狀態,就必須首先建立一個群體,然后建立一套我們現在所匱乏的規范體系。”[5]這種規范體系正是一種道德共同體。很顯然,與滕尼斯相比,涂爾干對共同體的態度更加積極和樂觀,因為滕尼斯認為共同體“解構”本質上就是家園衰落與關系解體。
李佩甫在懷念或追憶傳統倫理共同體的同時,也在努力將凌亂不堪的倫理碎片重新置于某種合乎理想或逼近現實社會的共同體框架內加以重組。正如滕尼斯從理論層面分出共同體與社會一樣,其本意是為了在金錢至上、人情冷漠的現代社會中尋找記憶中守望相助的共同體生活方式。“呼家堡人早已經習慣了這種只有一個聲音的日子,如果這聲音突然消失的話,呼家堡人倒不知道該怎么活了。”[6]呼家堡這種自上而下“步伐一致”的生活模式明顯受傳統文化的影響,而絕非僅僅是作家個人的倫理理想,中原大地深受儒家傳統思想影響,李佩甫也早已形成儒家共同體的慣性思維,并直接影響其文學創作。“我的源頭,也許緣自儒家文化的浸泡或者說是桎梏,這是鎖鏈也是營養體”[7]。與儒家文化一樣,李佩甫習慣將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放在倫理的框架下建構,他們很難擺脫各種倫理阻力甚至困境,誠如《生命冊》中被嵌進城市的吳志鵬,盡管已經擁有城里人的地位和身份,但是依然無法割裂與農村故土鄉親的倫理關系,他的肩上扛著自己根本無法承受的倫理之重。但是,這樣的倫理壓迫于他們而言既是壓力也是動力,其中還包含著李佩甫對基于倫理共同體的詩意想象。
知青和生于20世紀50年代的獨特經歷,使得李佩甫對瑣碎生活的倫理化想象交織著詩意與糾結。這種個性化的倫理表達,精準表現出作家對平原大地做出的道德反應與倫理判斷,詩意與糾結絕不是彼此對立的兩級,而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共存關系,這是作家賦予鄉土世界的倫理理想。李佩甫指出,像他這樣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人,“都是受過理想主義熏陶或夢想教育的一代。這代人有底線,是相對保守又不甘沉淪的一代。在單一的年代,我們渴望多元;在多元化的時期,我們又懷念純粹”[8]。這種看似矛盾的倫理理想,不僅是對鄉土精神家園的守護,而且是對記憶中現實體驗的回望,盡管在李佩甫看來它的根基已經被動搖,甚至搖搖欲墜。在《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孫》中,盡管李氏的血脈依舊代代相傳,但是困頓、逃離和遺忘已經充斥鄉土世界變遷的全過程,傳統經驗不再是現實的參照,倫理道德不再是空間的秩序。李佩甫通過對傳統與當代、祖輩與后代的糅合,實現了對家族變遷和時代裂痕的精神叩問與道德評判,其內心雖充滿苦楚與感慨,卻依然真誠而詩意地再現了鄉土世界發展變化歷史進程的原本面目,看似感性批判的背后蘊含著理性的審視。《城的燈》凸顯了作家對倫理式微和精神貧瘠的深度思考,作品中的劉漢香正是作家力圖通過審美再造拯救倫理共同體于深度解構的詩意努力。作為李佩甫心中倫理的詩意化身,劉漢香被放在一個不是圣女勝似圣女的位置上,身上被賦予太多的傳統優點,這樣的重壓使得她無力承擔,最終香消玉殞,但也因此成為作家筆下的詩意傳說。縱觀李佩甫的小說創作,他從未停止找尋道德復興道路的努力,他的倫理理想在其對紅旗渠精神的謳歌中抵達高潮。紅旗渠精神不再只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其現實意義與時代價值在今天被進一步凸顯出來,抑或說紅旗渠精神絕對配得上我們生活的當下時代,我們的時代更需要紅旗渠精神來滋養。從這個視角來看,紅旗渠精神是李佩甫對道德倫理的理想化重構與詩意致敬。
李佩甫試圖通過自己的作品建構一個詩意化的倫理空間,盡管他同時受困于自己想象的審美世界,但這似乎并不影響他通過倫理拯救現代性道德困境的詩意努力。《城的燈》中被馮家昌拋棄的劉漢香,身上有著諸多中國傳統的鄉土美德,她勤勞勇敢、胸懷寬廣,用個體的力量苦苦支撐著日漸衰落的傳統倫理共同體,她不只是鄉土倫理的挽歌,更是李佩甫拯救傳統倫理的詩意吶喊。正因如此,倫理在李佩甫的文學空間中不只是一種規訓力量,更多的是一種拯救手段。雖然這種對倫理的審美化重構不一定真實可靠,但卻直逼作家內心為倫理保留的詩意空間,這絕不是李佩甫一廂情愿的吶喊,相反承載著整個時代對倫理的呼喚。面對現實倫理的無力甚至異化,或許審美化、詩意化的想象與努力更具震撼力,也更加符合時代的聲音與期待,盡管這樣的想象多少帶有悲觀的色調。《金屋》是一部充滿焦慮、迷惘和恐懼的作品,在其中,傳統的倫理共同體正在悄然坍塌,另一個由金錢架構而起的利益共同體正在迅速崛起,缺少了倫理支撐與精神支柱的鄉民在尋求命運共同體的道路上弄丟了過去、迷失了自己。李佩甫對轉型時代的揭露與批判可謂直指人心,在作家的心中,“金屋”正是對無法預言的平原大地的空間化美好愿望,然而理想再豐滿,最終還要面對現實的慌亂與失序、過去的解構與逝去。“如果要為李佩甫的小說世界找到一個精神象征的話,那么這個形象就是大地。諸如《紅螞蚱 綠螞蚱》中童稚天真的土地,《李氏家族》里埋葬先祖、繁衍生息的大地等。”[9]從這個意義上講,平原大地正是托起李佩甫倫理理想的詩意空間,所有的倫理事件、道德實踐都建立在這片大地的基礎上。如此眾多的瑣碎化生活體驗,背后承載的是作家內心一直努力重構的大倫理。李佩甫對倫理的詩意想象雖遭遇過瓶頸卻一直都有突破和超越,他試圖以讓筷子立起來的決心為這個社會想象并建構一個充滿詩意與美好的倫理大廈。
三、小空間,大時代
李佩甫雖沒有農民的身份,卻有著對鄉土世界的偏愛與執著,他對自己曾經生活的中原大地有著無限忠誠,這一切都取決于李佩甫的內心藏著一個童年的夢想。“在人類的心靈中有一個永久的童年核心,一個靜止不移但永遠充滿活力、處于歷史之外且他人看不見的童年,在它被講述時,偽裝成歷史,但它只在光明啟示的時刻,換言之,在詩的生存的時刻才有真實的存在。”[10]李佩甫始終把自己看作鄉下人,流連忘返于狹小而又狹隘的鄉土空間,對中原鄉土世界的講述充滿著詩意與美好。李佩甫養成了每天飯后散步的習慣,“很多個晚上,我穿越大街小巷,像狼一樣在各個街頭徘徊,想寫好作品,想找好素材,想找好方向,這種狀態持續了很多年”[11]。正是由于頻繁游走于城市的每一個角落,李佩甫才能在其作品中完成對鄉土空間的詩意想象與審美再現,使得其作品以小空間見證大時代,呈現出不一樣的厚重與深度。
共同體空間和個體空間在代表客觀存在事實的同時,也象征了一種精神層面或者文化意義上的營構。基于這樣的認知,空間不再只是背景架構或方位參照,而是價值或意義關系建構的過程。李佩甫曾經說過,他的根在中原大地,他是這片土地的兒子,雖然他已經離家多年,但其內心一直都為記憶中的故鄉留有空間,關于鄉土的記憶揮之不去。與其他鄉土作家不同,李佩甫的故鄉既是城市的又是鄉土的,出生在城市和下鄉當知青的雙重經歷給他的創作帶來更多、更大的空間想象。自帶中原氣息的《羊的門》,雖以“呼家堡”村這一小空間為主線,但它的外延卻很大、很廣,與外界的縣、市、省甚至國家都有密切關聯,所有發生在村子里的事情,都是對現時代的真實呈現。所以,李佩甫對鄉土的記憶與想象表現為一種視域上的融合,換句話說,李佩甫對鄉村的書寫帶有城市的痕跡,對城市的再現帶有鄉土的味道,這就使得其筆下的創作空間能夠以小見大,真正做到基于某一空間點反映大時代。這種視域融合讓作家游離于城鄉空間之外的同時,也為其提供了真正近距離感知城鄉迥異文化的機會。
空間是承載小說敘事的地理性共同體存在形態。李佩甫始終在尋找不同空間下的共同體驗,其作品包含的詩意既是語言層面的,更是情感層面的。雖然李佩甫的文學創作更多地聚焦于鄉土空間,但他并沒有無視城市化帶來的空間位移與情感錯位,無論其創作的背景在鄉村,還是書寫的對象是城市,讀者都可以輕易感受到“城中有鄉,鄉中有城”的城鄉共同體意象,這就使李佩甫在創作中呈現出更為廣闊的視野和更加寬廣的胸懷,他可以將復雜的現實和偉大的時代濃縮于某一特定的空間,借此賦予城鄉巨變以共同體經驗和詩意價值。《生命冊》承載的現實空間明顯要大于李佩甫過去的作品,在這部小說中,城市與鄉村渾然一體、難分彼此,共同的命運推動城鄉共同體的加速成型。城鄉空間雙重體驗不僅呈現整體意義上的普遍性,而且具有個體層面上的獨特性,這種對城與鄉的雙重體驗和記憶同時蘊含著差異與融合的二維含義。換句話說,城鄉共同體絕不僅僅建立在彼此融合的基礎上,它們之間的差異在城市化快速推進的現實背景下為共同體關系重構提供更大的可能性。
李佩甫將創作的視域定格于鄉野村莊或大街小巷這樣的小空間,通過以小見大見證大時代所包含的溫情與苦楚、現代與傳統、詩意與失落,作家用自己既恢宏又細膩的筆觸描繪了一個處在頻繁巨變中的大時代,將敘事的背景設定在看似狹小的復雜空間中,通過山川河流、村舍和大街小巷等小空間折射出大時代的眾生百態和復雜人性。倫理裂痕、城鄉差異、貧富懸殊、觀念沖突和夢想迥異建構起一個充滿選擇、迷失和醒悟的現實漩渦。在復雜多變的小空間中,大時代的千姿百態得以全面呈現,既有人性的險惡與自私,更有生活本身的真善美。李佩甫筆下生存于各式小空間的人物,雖自帶底層人的劣根,但他們人性的底色依然溫暖有光,他們身上無不體現大時代所需要的勇氣、擔當與使命。作家正是從一個個個體身上展開對共同體的詩意想象與理想化重構,其筆下的小人物雖來自底層、缺少話語權,卻在大時代的洪流中生生不息,他們甚至已經超越個體的意義,具備了詩意想象和建構生命共同體的內涵。李佩甫用自己詩意化的情懷和樸實無華的想象講述著屬于中原人的好故事,卻講出了一個耐人尋味、不失美感的大時代。
四、結語
共同體作為一個現代產物帶有明顯的時代印跡,它與作家想象的文學世界有著內在的復雜關聯。從某種程度上講,現代性和后現代性已經成為個體化凸顯和共同體式微的現實表征,個體逐漸脫離共同體并開始擁有更大的自由空間、自主權利與獨立地位,個體的凸顯導致共同體的暗淡與衰落。但是,這一歷史進程又是一把雙刃劍,個體在擺脫共同體限制的同時也失去了來自共同體的庇護,從而導致個體落入一種充滿無序、不確定與不穩定的生存狀態中。跳出共同體舒適圈的個體,看似獲得了個體意義上的自由空間與自主生活,卻不知不覺陷入另一個漩渦。現實的殘酷和精神的迷失,使得李佩甫作品中的人物在逃離傳統共同體后又開始懷念過去的美好與和諧,雖然身體與精神都難以再度返鄉,但他們內心對共同體的想象與渴望卻有增無減。
共同體和個體一道成為作家想象與敘述世界的兩極,所有的人物都游走于兩極之間,所有現實問題都與共同體和個體密不可分。于共同體和個體而言,它們之間唯一的區別就是它們屬于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兩者并無絕對差異與割裂。于李佩甫而言,鄉村共同體象征著更多的東西,而非地理層面上的空間存在,正在“消失”的中原鄉村被他以一種詩意的方式呈現出來,更像是身體與靈魂的詩意棲息地和無法舍棄的家園。作家以詩意想象的方式藝術再現的鄉村共同體世界,既是一首傷感的田園詩,也是一首夢想的搖籃曲,正因如此,李佩甫對中原大地的藝術性想象與審美化再現的同時表現出深刻的批判意識與拯救精神。在看似“反鄉土”的敘事過程中,李佩甫表現出對鄉土世界極富詩意的懷舊與回憶,個體在迷失和逃離傳統共同體的同時,又期待一個屬于未來的全新共同體的出現。或許,李佩甫想要的正是一種身體上離鄉而精神上返鄉的詩意理想,這樣的“矛盾體”使得作家在文學想象的世界里更加接近共同體。李佩甫小說中的人物在個體獨立和集體認同的兩難選擇中,試圖脫離某一個共同體的同時也在回歸另一個共同體,這是作家的尖銳批判,更是作家的詩意想象。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共同體與個體在李佩甫的審美世界里就是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個體對共同體的想象一直充滿深情與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