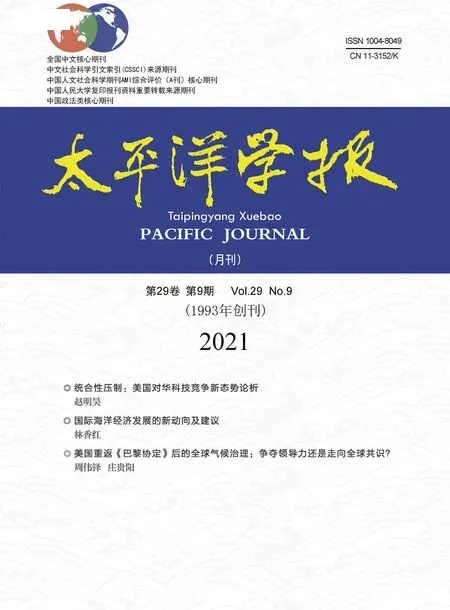上海合作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特征、限制與改進路徑
李孝天 陳小鼎
(1.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北京 100029;2.蘭州大學,甘肅 蘭州 730000)
自成立以來,深化安全合作始終是上海合作組織(以下簡稱上合組織)的優先發展方向。作為歐亞地區安全治理重要行為體的上合組織,填補了冷戰結束后在歐亞地區出現的地緣政治和安全空白,對維護地區安全與穩定作出了突出貢獻。①Michael Salter and Yinan Yin,“Analysing Regionalism with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Relations: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as a Grossraum?”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3,No.4,2014,p.871.時至今日,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已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
首先,上合組織應對地區安全問題的地理范圍和議題范圍明顯擴大。擴員后上合組織開展地區安全合作的核心地區從中亞擴展至南亞,致力于應對的地區安全問題也不斷增加,主要包括“三股勢力”、跨國販運毒品、非法販運麻醉藥品、非法販賣人口、有組織犯罪、信息通信領域犯罪、地區沖突、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能源安全、發展不平衡、糧食市場波動、氣候變化、飲用水短缺和疫病蔓延等。其次,上合組織應對地區安全問題的機制不斷完善,“大體形成了定期會晤決策機制、條約法律保障機制、聯合反恐合作機制三者聯動、相互促進的關系”①曾向紅:“上海合作組織安全合作機制的建設成就、不足與建議”,載李進峰主編:《上海合作組織發展報告(201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127頁。。再次,上合組織應對地區安全問題秉持規范的內涵趨于充實和成熟,涵蓋了新安全觀、“上海精神”、“不干涉內政”原則、“協商一致”原則、亞洲安全觀、新型國際關系、人類命運共同體等諸多理念。最后,上合組織在地區安全合作上取得的成效頗顯,除維護中亞成員國政權穩定和積極推動阿富汗和平進程外,在聯合反恐和緝毒兩大合作領域取得的成果尤為顯著,主要包括發布相關法律文件、建立合作機制、舉行反恐聯合軍演、挫敗和防止恐怖活動、繳獲毒品、抓捕恐怖分子和非法制販毒人員等。②詳情可參見中國上海合作組織研究中心編著:《上海合作組織:回眸與前瞻(2001—2018)》,世界知識出版社,2018年版,第37頁;Wang Jin and Kong Dehang,“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n States i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Vol.5,No.1,2019,pp.65-79.
盡管成果豐碩,但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特征仍需明晰、內在限制亟待突破。本文嘗試探討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主要特征,在此基礎上剖析其參與地區安全治理面臨的內在限制,并提出可行的應對方案,以期有助于更加深入地認識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狀況并進一步提升其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成效。
一、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主要特征
全球化背景下新安全問題的出現和擴散改變了安全的傳統內涵,使得單個國家難以獨自妥善應對,在一定程度上突顯出國家的局限性。為更好地應對日趨復雜和嚴峻的地區安全問題,國家間共同建立地區安全合作組織作為地區安全治理的制度框架,在國家和全球制度之間充當橋梁。這種現象被西方學者稱為“治理轉移”(governance transfer)或“沒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地區安全治理也隨之被定義為,公共和非公共行為體在地區層面通過協調的互動方式共同應對地區安全問題的實踐,并體現三方面特征:其一,公共與非公共行為體并存的多中心協調形式;其二,行為體是相互依賴的、獨立的和平等的,正式和非正式機制相結合;其三,傾向于合作性的“自下而上”實施方式,而非“自上而下”的命令與控制。③Kees van Kersbergen and Frans van Waarden,“‘Governance’as a Bridge between Disciplines:Cross?Disciplinary Inspiration regarding Shifts in Governance and Problems of Governabili?ty,Accountability and Legitimacy,”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43,No.2,2004,pp.151-152.由于這種理解與歐洲地區安全治理實踐的契合程度較高,故其一度成為地區安全治理研究的主流核心內涵。不過,以歐洲為中心的地區安全治理研究與實踐并不具有普適性。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主要特征就與其不盡相同。
1.1 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主體以成員國為主、非官方機構為輔
既有歐洲中心的地區安全治理研究反映出對國際關系的后威斯特伐利亞理解,忽視了主權國家仍是國際關系中最主要行為體的客觀事實。尤其在應對安全問題時,國家作為主導行為體的地位毋庸置疑。國家作為安全提供者,具有兩大鮮明優勢:在理念上,只有國家具有最高權威與合法性;在物質上,只有國家具有有效應對多元威脅的充足資源。④Bill McSweeney,Security,Identity and Interests:A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86-87.上合組織作為政府間合作組織,成員國是其主導者,各國的(共同)安全利益訴求塑造了該組織的地區安全治理議程,各國的相關政策和行為能夠對該組織的發展產生顯著影響。成員國在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進程中占據主導地位,上合組織的行動能力和權威主要源自成員國。上合組織不能脫離成員國獨立參與地區安全治理,其首要功能是滿足成員國的共同利益訴求。換言之,上合組織開展相關實踐具有濃厚的國家中心色彩。
在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進程中,上合組織主要遵循成員國主導的“自上而下”方式,并形成了下設機構“梯次”與“平行”相結合的布局。就上合組織的會議機制而言,成員國元首理事會是最高決策機構,可決定該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所有重大事務;外交部長會議、國家協調員理事會及其他各安全相關部門領導人會議平行處于第二梯隊,負責該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具體協調工作。上合組織還設有秘書處和地區反恐怖機構兩大平行常設機構。其中,秘書處可為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提供協調、信息分析、法律和組織技術保障等;地區反恐怖機構則專門負責打擊“三股勢力”的具體工作,是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重要實體依靠。自2002年以來,上合組織舉行了多次成員國聯合反恐軍事演習,不僅強化了各國之間的軍事安全互信,還對以恐怖主義為代表的“三股勢力”形成強有力的威懾,為該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樹立了合作典范。
為更好地應對日益復雜和嚴峻的安全威脅,上合組織還積極支持非官方機構。上海合作組織論壇作為上合組織下設的多邊學術機構和非政府專家咨詢機構,目前已舉行了十六次會議。其與會人員主要包括各成員國的上海合作組織國家研究中心、觀察員國與對話伙伴國的專家學者、上合組織秘書處和有關國家的外交官等,為上合組織的發展(包括參與地區安全治理)提供了諸多具有前瞻性、針對性和實用性的政策建議。上合組織秘書處還不時協同其他非官方機構舉辦會議,致力于為該組織的發展提供智力支持。例如,2020年8月11日,上合組織秘書處、上海合作組織中國睦鄰友好合作委員會、上海外國語大學以及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聯合召開視頻會議,討論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對上合組織框架內合作的影響、挑戰和機遇,尤其是民間外交發揮的作用。非官方機構是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有效補充。總體而言,在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進程中,以成員國主導的“自上而下”的正式實踐為主,以非官方機構開展的“自下而上”的非正式實踐為輔。
1.2 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進程由大國引領、中小國平等參與
在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進程中,上合組織成員國無論大小、強弱和舊新,均享有平等的地位。在進行決策時,上合組織奉行“協商一致”原則,任何成員國都有一票否決權。該原則的存在使得擴員前上合組織的權力結構并非簡單的“2+4”(中俄+中亞成員國),中亞成員國擁有與中俄兩個大國平等的地位以及踐行多邊平衡外交的機會。①Neil Renwick,“Contesting East Asian Security Leadership:China and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in Christopher M.Dent,ed.,China,Japan and Regional Leadership in East Asia,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8,pp.219-222.上合組織擴員后,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樣享有平等的權利和地位,“協商一致”原則使得該組織的權力結構亦非簡單的“3+5”(中俄印+中亞成員國與巴)。當然,同為正式成員國的大國與中小國在綜合國力和影響力等方面存在客觀差異,雖然各國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權利,但在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進程中扮演的角色并不相同。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主要致力于解決功能性問題,并提供有效與合法的協調。為確保治理的有效性與合法性,上合組織在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進程中形成了由大國引領、中小國平等參與的合作格局。這種合作格局既不同于北約式的大國主導格局,也不同于東盟式的“小馬拉大車”格局。
在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進程中,中國與俄羅斯扮演引領者的角色,為上合組織提供了主要的行動能力和影響力,如物質資源、行動倡議以及理念規范等,秉持“協商一致”的決策原則引領該組織和中小成員國共同開展地區安全治理實踐。除承擔較大比例的經費和提供較多的物質支持外,中俄還將兩國關系踐行的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原則引入上合組織的發展中,作為本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重要遵循規范。在理念規范的貢獻上,中國無疑是最主要的引領者。中國已陸續將新安全觀、亞洲安全觀、新型大國關系和新型國際關系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等與上合組織的發展對接,為本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提供了強大的智力支持。與中俄相比,同為大國的印度成為正式成員國的時日不長,尚未(準備好)成為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進程中的引領者,暫時只是平等的參與者。
在中國和俄羅斯的引領下,綜合國力相對較弱的中亞成員國積極扮演著平等參與者的角色,對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意義同樣重大。中亞成員國主要通過特殊的地緣戰略價值、多邊平衡外交、作為沖突與動蕩的前沿以及群體數量優勢等途徑,不時對上合組織的發展產生不亞于大國的顯著影響。①詳情參見曾向紅、李孝天:“中亞成員國對上海合作組織發展的影響:基于國家主義的小國分析路徑”,《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第116-130頁。對于上合組織而言,中亞始終是該組織聚焦的地緣安全核心區,②楊恕、王琰:“論上海合作組織的地緣政治特征”,《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第54頁。中亞成員國的安全問題是該組織的重要治理對象。為維護本國及周邊地區的安全與穩定,中亞成員國為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提供著不可或缺的支持。就巴基斯坦而言,雖然成為正式成員國的時日尚短,但它對上合組織的認知相較印度更加積極,正逐步適應平等參與者的角色,與中亞成員國一樣能夠為該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提供有力支持。
1.3 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踐行以“不干涉內政”為核心的主權規范
在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進程中,上合組織始終堅持踐行以“不干涉內政”為核心的主權規范。在《上海合作組織憲章》中,成員國堅持的首要原則便是“相互尊重國家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及國家邊界不可破壞,互不侵犯,不干涉內政,在國際關系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不謀求在毗鄰地區的單方面軍事優勢”。因此,上合組織一直致力于確保成員國主權完整和政權穩定,堅決反對干涉成員國內政。例如,在“郁金香革命”等重大安全事件爆發后,上合組織向事件發生國提供了及時的政治與外交支持以及適當的人道主義援助,為事件發生國的局勢穩定、秩序恢復以及和平實現作出了積極貢獻。同時,為確保中亞成員國的主權完整和政權穩定不再受美國推行的民主改造進程的直接威脅,2005年舉行的上合組織阿斯塔納峰會上首次提出了美國主導的“反恐聯盟有關各方”從中亞撤軍的問題,并表示“在人權領域,必須嚴格和始終尊重各國人民歷史傳統和民族特點,堅持所有國家主權平等”。針對2010年爆發的吉爾吉斯斯坦動蕩,上合組織也重申了“支持國家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的原則立場,反對干涉主權國家內政”。③“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宣言(2005年7月5日,阿斯塔納)”,“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次會議宣言(2010年6月10日至11日,塔什干)”,上海合作組織官網。事實上,歷年的上合組織成員國元首宣言均強調對“不干涉內政”原則的堅守。
此外,當成員國涉足外部重大安全事件時,上合組織既不干涉相關各方的內部事務,也不“偏袒”任何一方。例如,對于俄羅斯出兵格魯吉亞和克里米亞,上合組織扮演第三方的角色,持相對中立的立場,僅致力于推動問題的和平解決。就俄格戰爭而言,2008年8月28日舉行的上合組織杜尚別峰會通過的宣言表示,“本組織成員國對不久前圍繞南奧塞梯問題引發的緊張局勢深表擔憂,呼吁有關各方通過對話和平解決現有問題,致力于勸和促談。本組織成員國歡迎2008年8月12日在莫斯科就解決南奧塞梯沖突通過的六點原則,并支持俄羅斯在促進該地區和平與合作中發揮積極作用。”就俄出兵克里米亞而言,2014年9月12日舉行的上合組織杜尚別峰會通過的宣言表示,“元首們支持盡快在烏克蘭恢復和平,繼續旨在全面解決該國危機的談判進程。元首們歡迎2014年9月4日三方聯合小組簽訂的關于落實烏克蘭總統和平計劃和俄羅斯總統倡議共同步驟的磋商紀要。”①“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杜尚別宣言(2008年8月28日)”,“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杜尚別宣言(2014年9月12日)”,上海合作組織官網。此后的上合組織成員國元首宣言中也都不斷重申,應在盡早全面執行2015年2月12日明斯克協議的基礎上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
1.4 上合組織進行的地區安全治理是綜合性的規范框架與實踐進程
新安全問題的出現和擴散顛覆了以軍事安全為核心對象的傳統安全治理形式,促使綜合性地區安全治理形式生成和發展。這種綜合性地區安全治理既是理念,又是經驗事實。或者說,這種綜合性地區安全治理是一種更加全面的規范性政治實踐,關涉對復雜安全風險進行有效、合法管控的不同理念。②Hans-Georg Ehrhart et al,“Putting Security Governance to the Test:Conceptual,Empirical,and Normative Challenges,”Europe?an Security,Vol.23,No.2,2014,p.121.上合組織進行的地區安全治理便是綜合性的規范框架與實踐進程。在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進程中,作為最主要安全提供者的成員國通過協調和規范指導的方式開展治理實踐,各國聯合建立的正式與非正式制度共存并相互交織形成網絡,以應對更加廣泛、復雜的地區安全問題。
首先,上合組織進行的地區安全治理是一個相對完備的規范框架,囊括了“上海精神”、“不干涉內政”原則、“協商一致”原則、新安全觀、亞洲安全觀、新型國際關系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等諸多安全治理規范。在此規范框架內,“上海精神”無疑處于核心地位。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言,上合組織“始終保持旺盛生命力、強勁合作動力,根本原因在于它創造性地提出并始終踐行‘上海精神’,主張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③習近平:“弘揚‘上海精神’構建命運共同體——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八次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海外版》,2018年6月11日,第2版。從這個角度來看,上合組織更多依靠成熟的規范而非垂直的權威體系去指導地區安全治理實踐,踐行一種“軟治理”(soft governance)形式。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秉持規范的合理性與正確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治理機制的合法性,從而促使成員國遵守治理機制的規范。此外,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秉持的規范內嵌于物質結構,能夠反映并重新塑造組織內部的權力關系,指導成員國的互動行為,協調成員國的安全利益糾紛。
其次,上合組織進行的地區安全治理還是具體實踐進程。雖然規范能夠指導實踐并反映和塑造權力關系,但規范卻不可脫離實踐成為空中樓閣。在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進程中,安全治理規范始終與經驗性的安全治理實踐緊密結合,既適用于本組織覆蓋地區的具體安全形勢,又能部分滿足成員國的合理安全利益訴求。得益于此,上合組織才能在地區安全治理上取得顯著的合作成效,并保持著十足的后勁。概言之,功能性的實踐是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基礎,而指導性的規范是確保實踐有效性與合法性的關鍵,二者相輔相成。
二、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面臨的內在限制
雖然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但也面臨著亟待突破的內在限制,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2.1 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行動能力與方式有待進一步提升完善
如前所述,上合組織進行的地區安全治理既是規范框架,又是實踐進程。其中,規范關涉合法性,主要取決于外部承認;實踐關涉有效性,主要取決于行動能力。合法性與有效性是治理的兩大核心要素。
“上海五國”協同烏茲別克斯坦簽署《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時,就已將各自的權威與合法性(部分)賦予上合組織。歷經多年發展,成員國通過《上海合作組織憲章》以及一系列應對地區安全問題的正式文件,賦予了上合組織更多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合法性。例如,《上海合作組織憲章》明確指出,上合組織作為國際法主體,享有國際人格,擁有在各成員國境內為實現其宗旨和任務所必需的法律行為能力,還享有法人權利,可簽訂條約、獲得并處置動產或不動產等。同時,上合組織始終堅守本組織聲明的相關原則和《聯合國憲章》規定的相關原則,如以“不干涉內政”原則為核心的主權規范等,從未做出有損地區安全治理合法性的行為。鑒于此,上合組織無疑是具備高合法性的地區安全治理主體。
相比之下,上合組織應對突發重大安全事件的能力雖不斷發展,但仍有較大提升空間。“9·11”事件爆發后,美國于2001年10月7日發起了針對塔利班政權的阿富汗戰爭。戰爭持續到11月中旬結束,塔利班政權被推翻。同一期間,遵循“不干涉內政”原則的上合組織未介入阿富汗事務,更多是表明立場。例如,9月14日,上合組織發布了《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總理聲明》,對“9·11”事件表示強烈憤慨,對美國及其公民表示慰問和同情,并表示將“同所有國家和國際組織密切配合,采取有效措施,為根除恐怖主義帶來的全球性危險而進行毫不妥協的斗爭”。①“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總理聲明”,2001年9月14日,上海合作組織官網。作為新生地區安全合作組織,上合組織此舉符合其宗旨要求與當時實際。盡管上合組織能夠迅速表明合作反恐的決心和立場已屬難能可貴,但依舊被西方媒體智庫等苛責,認為上合組織沒有太多實質性參與,而質疑其行動能力。②Sean Yom,“Power Politics in Central Asia,”Foreign Policy In Focus,July 1,2002.
此后,上合組織的制度框架逐漸成形,如通過了《上海合作組織憲章》、建立了地區反恐怖機構和秘書處兩大常設機構等,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本組織的行動能力。到2005年“郁金香革命”和安集延事件爆發后,上合組織作出了比較及時的反應,在同年7月舉行的阿斯塔納峰會上要求美國主導的“反恐聯盟有關各方”撤出中亞軍事基地,并接納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為觀察員國。上合組織的行為既表達了對維護地區安全與穩定的決心,又表達了對美國在中亞軍事存在的排斥以及對美國推行“顏色革命”的不滿。與“9·11”事件發生時相比,上合組織此次的行為顯然更積極。不過,吉爾吉斯斯坦發生政權更迭以及烏茲別克斯坦出現大規模騷亂和人員傷亡,對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行動能力和提出了更高要求。
2010年吉爾吉斯斯坦動蕩發生后,俄羅斯、中國和哈薩克斯坦都對吉進行了人道主義援助。其中,俄強烈譴責巴基耶夫政權,積極支持反對派,是吉的最主要援助者,③Stephen Aris,“The Response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to the Crisis in Kyrgyzstan,”Civil Wars,Vol.14,No.3,2012,p.463.向吉提供的援助包括2 000萬美元資助、3 000萬美元優惠貸款以及超過2萬噸石油產品等;中國為吉提供了數百萬人民幣的緊急人道救援物資后,又陸續提供了大額資金援助;哈為吉提供了近700萬美元的人道主義援助。上合組織對吉國內動蕩多次發表聲明表示嚴重關切,呼吁制止犯罪和違法行為,希望盡快穩定局勢、恢復法律秩序、實現民族和解。此次動蕩的結果是吉國再次發生政權更迭。趙華勝認為,吉動蕩對上合組織形成了嚴重的負面沖擊,再次顯露出該組織缺乏行動能力和資源的缺點,僅用囿于“不干涉內政”原則來解釋其表現顯然是不夠的。④趙華勝著:《上海合作組織:評析和展望》,時事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頁。
由此,如何在堅持“不干涉內政”等一貫原則的基礎上,不斷提升和完善上合組織應對地區突發重大安全事件的能力與方式、提高其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有效性,是上合組織需要解決的內在困境之一。
2.2 除中國外的其他成員國對上合組織的認同程度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作為成員國主導的地區合作組織,上合組織的發展受到成員國對本組織認同狀況的顯著影響。成員國的高程度認同,是確保上合組織行穩致遠的關鍵所在。然而,目前除中國外的其他成員國對上合組織的認同程度仍有較大提升空間。這已成為眾多國內學者的共識,也是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面臨的又一內在限制。成員國對上合組織的認同程度,主要體現在它們對該組織的認知、利益訴求及行為上。
中國在認知上對上合組織抱有特殊情結。上合組織是唯一在中國境內建立、以中國城市命名、總部設在中國的地區合作組織。中國始終是上合組織發展的最主要推動者。除將上合組織視為維護新疆及其周邊地區安全與穩定的平臺外,中國更加重視其承載的“崇高的價值理想、政治理念和歷史使命”①趙華勝著:《上海合作組織:評析和展望》,時事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頁。,將其視為踐行新型國際與地區秩序觀的載體。中國不斷賦予上合組織以新的戰略內涵,積極推動該組織踐行本國倡導的重大理念。近年來,新型大國關系、新型國際關系、人類命運共同體等重大理念陸續與上合組織對接,為該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的方向性建議和選擇。中國始終與上合組織保持高頻互動,積極參與該組織開展的地區安全治理實踐,如打擊“三股勢力”、舉行反恐聯合軍演、建設地區反恐怖機構、敦促重大安全事件發生國和平解決矛盾與沖突等,致力于推動地區安全問題的良治。某種意義上,中國與上合組織互為標簽。②有巴基斯坦學者持類似觀點,認為上合組織以中國為標簽。參見Baber Ali Bhatti,“SCO:Aims and Objectives,”Pakistan Observer,October 10,2017.因此,中國對上合組織保持高程度認同。
總體來看,俄羅斯官方對上合組織的態度一直比較積極,但重視程度與中國相比較為有限。上合組織成立初期,雖然俄官方對該組織持正面評價,但對提升其“決策能力和發揮實質性政治作用則關注不夠”③王曉泉:“俄羅斯對上海合作組織的政策演變”,《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07年第3期,第67頁。。同時,需要指出的是,俄在中亞留有軍事存在。例如,俄在除烏茲別克斯坦外的三個中亞成員國境內都設有軍事基地,其邊防軍曾一度在各國的邊界巡邏。俄的這種行為有悖于上合組織秉持的“不干涉內政”原則。另外,俄出兵格魯吉亞和克里米亞的行為一度致使上合組織陷入兩難的境地(支持俄有悖于“不干涉內政”原則,不支持俄容易引發俄的消極態度),對本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
在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進程中,俄羅斯對上合組織的安全利益訴求帶有明顯的零和色彩。俄的安全利益訴求至少有五:第一,遏制美國與北約在中亞的影響,抵制促使俄與中亞國家出現非正常政權更迭的“顏色革命”;④Aijan Sharshenova and Gordon Crawford,“Undermining Western Democracy Promotion in Central Asia:Chinas Countervailing Influences,Powers and Impact,”Central Asian Survey,Vol.36,No.4,2017,p.455.第二,將上合組織當作抵御伊斯蘭極端主義的緩沖區,借助該組織打擊“三股勢力”及其他跨國犯罪,維護國內及周邊地區的安全與穩定;第三,加強與中國的聯系,在安全上服務于“東向戰略”以期“借東制西”;第四,鞏固在中亞的既有影響并嘗試平衡中國的影響力;⑤Marcin Kaczmarski,“Russia Attempts to Limit Chinese In?fluence by Promoting CSTO-SCO Cooperation,”CACI Analyst,October 17,2007;Alexander Frost,“The 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the Shanghai Cooperation,and Russias Strategic Goals in Central Asia,”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Vol.7,No.3,2009,pp.83-102.第五,借助上合組織實現“大歐亞伙伴關系”(Greater Eurasian Partnership)構想。⑥呂萍:“俄羅斯學界及媒體對上海合作組織的最新評價”,載李進峰主編:《上海合作組織發展報告(201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281-283頁。基于功利性的認知,一方面,俄有選擇地積極參與上合組織開展的合作實踐;另一方面,俄不希望上合組織在中亞及其周邊地區的影響力超過自身主導建立的地區合作組織,尤其對“中國倡議”持復雜多變的立場,經常發揮否決作用。⑦朱杰進、鄒金水:“對‘中國倡議’的不同反應——俄羅斯在上合組織中的國際制度行為選擇”,《俄羅斯研究》,2020年第3期,第54-79頁。在安全領域,俄將集體安全條約組織作為第一選擇,視上合組織為補充性機制。為平衡中國在上合組織的影響力,俄在擴員條件不夠成熟的情況下積極支持印度和伊朗加入該組織,“無視”此舉或將使該組織面臨“論壇化”或成為“象征性的組織”(symbolic organization)①Linda Maduz,“Flexibility by Design: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and the Future of Eurasian Cooperation,”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CSS),ETH Zurich,May 2018,pp.1-28.的風險。概言之,如果說中國對上合組織的態度是“全心全意”,那么俄的態度則是“半心半意”。②盧海清:“俄羅斯對獨聯體與上海合作組織的政策比較”,《戰略決策研究》,2015年第5期,第70-80頁。
中亞成員國對上合組織的認同程度仍有較大提升空間。盡管當前各國對上合組織的態度積極,將參與該組織框架內的合作視為重要外交工作之一,③詳情參見高焓迅:“中亞國家視閾下的上海合作組織擴員:收益認知與戰略考量”,《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8年第5期,第121-122頁。但對該組織的重視程度仍相對有限。④例如,哈薩克斯坦出臺的《2020—2030年哈薩克斯坦外交政策綱要》僅在表示“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在亞洲的活動”時提到上合組織。在應對新冠病毒疫情方面,中亞成員國主要依靠的地區合作組織也并非上合組織,而是歐亞經濟聯盟。各國對上合組織的共同安全利益訴求至少有三:第一,打擊“三股勢力”及其他跨國犯罪,管控或解決中亞的諸多爭端,維護國家及周邊地區安全;第二,抵制來自西方的民主、人權批評與干涉,獲得集體外交支持,維護國家主權與政權穩定;第三,借助上合組織平衡中國和俄羅斯,尤其是削弱俄在特定事務上的外部影響,⑤Roy Allison,“Virtual Regionalism,Regional Structures and Regime Security in Central Asia,”Central Asian Survey,Vol.27,No.2,2008,p.195.推進“去俄羅斯化”⑥楊成:“去俄羅斯化、在地化與國際化:后蘇聯時期中亞新獨立國家個體與集體身份的生成和鞏固路徑解析”,《俄羅斯研究》,2012年第5期,第93-154頁。進程。在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進程中,各國對上合組織秉持的“不干涉內政”原則、“協商一致”原則等規范比較認同,因為這些規范能夠確保它們在該組織內部不受干預且擁有與大國平等的地位;但各國嘗試借助上合組織平衡中俄的安全利益訴求,也側面體現出本組織內部缺乏積極的地區認同構建。⑦Timur Dadabaev,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CO):Regional Identity 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entral Asia State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8,No.85,2014,pp.102-118.大體而言,各國對上合組織的態度和行為主要取決于后者能否滿足它們的利益訴求:利益滿足程度越高,它們就越“親近”上合組織;利益滿足程度越低,它們就越“疏遠”上合組織。這種功利性態度和行為,是各國對上合組織認同程度較低的主要表現。
印度對上合組織的認同程度最低。與其他成員國相比,印度對上合組織的認知和利益訴求更具零和色彩。印度加入上合組織主要是基于地緣戰略競爭的考量,相比之下反恐等訴求并沒有那么迫切。⑧丁新科、秦云周:“上海合作組織‘外溢’效應初探”,《太平洋學報》,2006年第1期,第66頁。一方面,印度將上合組織界定為中國主導的、優先服務于中國在歐亞地區擴張其影響力的地區合作組織,認為自身在該組織內部所能發揮的作用十分有限,擔心在該組織內部可能被邊緣化;另一方面,印度也將上合組織當作滿足本國地緣戰略利益訴求的工具,嘗試借助該組織構建歐亞地區戰略伙伴關系網絡并制衡中國和巴基斯坦,以期成為具有顯著影響力的歐亞大國。⑨詳情參見李孝天:“印度對上海合作組織的認知、利益訴求及其影響”,《國際論壇》,2019年第6期,第50-61頁。中印邊界沖突產生的持久消極影響、中巴友好合作關系的持續深化以及中印戰略互疑,也使得印度對上合組織的態度相對謹慎和消極。在印度看來,上合組織的重要性不如金磚國家集團等多邊機制,而印巴沖突帶來的負面影響可能使得印度成為該組織效力低下的“替罪羊”。⑩Phunchok Stobdan,“India?s Accession to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Au?gust 20,2015.除以上消極認知、利益訴求和行為外,印度在克什米爾地區以及洞朗和加勒萬河谷地區主動挑起消極沖突和對峙,亦表現出該國對上合組織的忽視。
同為新進成員國,巴基斯坦對上合組織的認同程度要高于印度。與印度相比,巴更多關注的是加入上合組織對于促進地區和平與本國發展的積極意義,?Zahid Shahab Ahmed et al,“Conflict or Cooperation?India and Pakistan in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Pacific Focus,Vol.34,No.1,2019,pp.5-26.更加重視對地區安全問題進行有效治理。基于此種動機,巴致力于深化與上合組織創始成員國的合作關系,共同應對“三股勢力”、非法販運毒品與武器等非傳統安全問題,如積極參與聯合反恐軍演等反恐活動、與中國和俄羅斯就阿富汗問題舉行三方會談等。巴與創始成員國(尤其是中國)的友好合作關系,也使得巴比印度更加認同上合組織。不過,印度對巴的制衡戰略,促使巴采取相應的反制措施,如在克什米爾問題上與印度針鋒相對、堅決拒絕印度借道與阿富汗交往等。印巴之間頗具零和色彩的交往方式,使得兩國加入上合組織的諸多共同利益反而變得相互沖突,進而導致它們在中亞、阿富汗和伊朗的戰略競爭難以避免。①Shahram Akbarzadeh,“India and Pakistans Geostrategic Ri?valry in Central Asia,”Contemporary South Asia,Vol.12,No.2,2003,pp.219-228.從這個角度來看,巴對上合組織的認同程度將受到印度在該組織內部地位的顯著影響。在上合組織框架內,如果印度成為與中俄相同的“引領大國”,那么巴大概率不會甘于作為中小成員國認同并積極參與由印度引領的地區安全治理進程。屆時巴對上合組織的認同程度可能會有所下降。
除中國外的其他成員國對上合組織認同程度差異,以及各國對該組織所持認知和安全利益訴求的異質性,限制了該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行動能力和效力。其中,中俄印三個大國對上合組織的認知和安全利益訴求的鮮明異質性,或將導致本組織治理權威的碎片化,從而對本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有效性與合法性構成嚴峻挑戰。此外,印度的消極認知以及基于零和思維的安全利益訴求和行為,可能導致中印邊界爭端和印巴沖突長期存在、上合組織內部出現選邊站的分裂現象等嚴重后果,進而削弱本組織的凝聚力,危及本組織內部關系的和諧穩定,對本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有效性與合法性構成嚴重威脅。
三、提高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能力的路徑
3.1 構建上合組織地區沖突預防機制
促進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合法性與有效性平衡發展的關鍵在于,在堅定支持“不干涉內政”原則的基礎上提升該組織應對地區重大安全事件的能力。為此,早在“郁金香革命”發生后的2006年,成員國就通過《上海合作組織五周年宣言》表示,“將研究在本組織框架內建立預防地區沖突機制的可能性”。對于上合組織官方文件釋放的積極信號,國內學者是響應的最主要群體。例如,許濤闡述了在上合組織框架下建立預防地區沖突機制的基礎和意義。2010年吉爾吉斯斯坦動蕩后,趙華勝提出應與時俱進地看待“不干涉內政”原則的內涵與外延,在上合組織框架下建立應對地區重大安全事件的相關機制,探索“建設性介入”地區沖突的可能性。張曉慧和肖斌對上合組織如何通過沖突管理在確保中亞地區安全上發揮更大作用進行了分析。②許濤:“上合組織建立預防地區沖突機制的實踐意義”,《現代國際關系》,2006年第12期,第12-16頁;趙華勝:“不干涉內政與建設性介入——吉爾吉斯斯坦動蕩后對中國政策的思考”,《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第23-28頁;張曉慧、肖斌:“地區安全主義視野中的上海合作組織”,《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1年第4期,第64-68頁。在上合組織開啟擴員進程前后,考慮到印巴沖突可能產生的消極影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提及強化該組織管控地區重大安全風險的能力。③參見薛志華:“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組織的原因、挑戰及前景分析”,《東南亞南亞研究》,2015年第4期,第34頁;張寧:“關于上海合作組織擴員的戰略方向的分析”,《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第153頁。首次擴員完成后,李進峰提出建立上合組織預防沖突管理協調與監督機制,發揮協調成員國間矛盾與沖突、協助處理成員國內部突發事件、監督成員國落實相關政策等功能。李亮對建立上合組織成員國間沖突調解機制進行了專題研究,闡明了建立該機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針對調解成員國間沖突的障礙提出了機制建設的具體思路。④李進峰:“參與全球治理:上海合作組織面臨的機遇與挑戰”,載李進峰主編:《上海合作組織發展報告(202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43頁;李亮:“上海合作組織建立成員國間沖突調解機制初探”,《俄羅斯研究》,2020年第3期,第19-53頁。
可以看出,建立相關機制以提升上合組織應對地區重大安全事件的能力十分必要,部分國內學者對此提出的一些思路也頗具啟發性。不過,嘗試探索在不違背“不干涉內政”原則的前提下使上合組織介入地區沖突或在該組織框架下建立成員國間沖突調解機制的可行性不高。相比之下,遵循上合組織官方倡議研究建立地區沖突預防機制無疑更加可行。當然,本文無力就地區沖突預防機制的建立提出較為完備的設計方案,只能在既有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嘗試性地提出一些想法,以期為該機制的建立以及提升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有效性提供些許參考。
考慮到地區重大安全事件對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行動能力構成嚴峻挑戰,可嘗試在該組織框架下建立地區沖突預防機制,并考慮給予該機制與地區反恐怖機構同樣的常設機構地位。地區沖突預防機制的主要目標是預防地區沖突發生與緩和相關各方的矛盾糾紛。該機制的構建和運行務必由所有正式成員國共商、共建、共享,堅持踐行“協商一致”原則和“不干涉內政”原則。在各成員國元首擁有最終決定權的基礎上,其他重要具體事宜,如承擔經費和工作人員的總數與比例、總部設立地點、具體行動決策等,要根據各成員國元首協商的具體結果而定,務必做到公平、公正、合理和一致通過。地區沖突預防機制負責人的任命可采取“輪流制”,由各成員國選派人員輪流擔任。同時,該機制的運行可嘗試“上合組織成員國+”的形式,允許觀察員國和對話伙伴國參與地區沖突預防事宜,提供建議和意見以供參考。
為確保地區沖突預防機制順利建成和運行,上合組織可以《上海合作組織憲章》《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長期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關于構建持久和平、共同繁榮地區的宣言》等綱領性文件為基準、結合不斷變化的地區安全形勢修訂《上海合作組織關于應對威脅本地區和平安全與穩定事態的政治外交措施及機制條例》,進一步明晰如“重大安全事態”、“采取必要措施”等表述的具體內容。在此基礎上,上合組織還需制定與預防地區沖突直接相關的具體指導性文件,與既有文件共同為地區沖突預防機制開展相關實踐提供規范性指導。出臺相關文件的一般流程是,提出草案—聽取和審議—表決—通過—公布。在出臺文件的過程中,各成員國元首擁有決定通過和一票否決的權力。
為更好地實現預防地區沖突發生與緩和相關各方矛盾糾紛的目標,地區沖突預防機制可設置兩個具體機制。其一,成立地區沖突預防研究所,負責搜集、整理和備份相關信息,在此基礎上進行追蹤研究并提供政策建議。在相關各方允許的情況下,研究所成員應定期前往多次發生重大安全事件的地區進行實地考察,確保獲得及時、有效的信息。研究所的主要成員,可采取任命和聘用相結合的方式,吸收各成員國從事相關領域研究的學者及其他專業人士擔任。在開展工作時,研究所應積極與上合組織秘書處進行協作,在汲取經驗的基礎上為地區沖突預防機制提供信息分析、組織技術保障等方面的服務。其二,建立專門的多層級會晤機制,給予預防地區沖突更多重視,通過多邊協商促進成員國間信息對稱與相互信任,以期減少由戰略誤判引發的沖突。其中,成員國元首會晤可在每年上合組織峰會前后舉行,作為各國交換相關立場、提出沖突應對方案以及達成和平承諾協議的多邊平臺;成員國外長和安全部門負責人會晤可根據現實情況決定時間和次數,作為各國進行具體協商的多邊平臺。
同時,地區沖突預防機制參與地區安全治理時應堅持采用以“自上而下”為主、“自下而上”為輔的方式。一方面,在應對地區重大安全問題時,各成員國元首一致通過的相關決策,下達至地區沖突預防機制協同各國共同付諸實踐;另一方面,在不違背上合組織秉持地區安全治理規范的前提下,地區沖突預防機制與各成員國也可主動提出“自主貢獻”承諾,為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作出更多力所能及的貢獻。這種“軟硬結合”的運行方式,無疑有助于提升地區沖突預防機制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有效性。以“自上而下”為主、“自下而上”為輔的形式,則可確保地區沖突預防機制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合法性。在構建地區沖突預防機制時,應以成員國為主,以非公共行為體為輔。如此有助于均衡提升該機制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合法性與有效性。在具體的制度設計和實踐中,可改變固守統一規則的僵化模式,嘗試設立靈活的、可協調的標準,根據具體情況踐行之。換言之,地區沖突預防機制的實踐要以解決問題為主,走“經驗主義治理”的道路,通過復合、多層次平臺集體解決地區安全問題。此外,上合組織還應強化與聯合國、東盟、獨聯體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的交流與協作,在有選擇地向后者學習的同時,積極探討合作預防地區沖突的可能性。
3.2 培育求同存異的協調互動理念,內化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
在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進程中,除中國外的其他成員國對本組織的認同程度相對較低,各國對本組織所持認知和安全利益訴求的異質性,不時導致該組織在應對重大安全事件時難以形成有效的共同政治意愿。鑒于此,還有必要進一步提升成員國對上合組織的認同程度,統籌各國相關認知和安全利益訴求的異質性,以期在該組織內部形成應對地區安全問題的有效共同政治意愿,進而為其提供充足的行動資源或能力。倘若成員國能夠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合力,外界對于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有效性的質疑亦將不攻自破。欲達成此目標,需真正做到“務實”與“務虛”相結合。其中,地區沖突預防機制建設屬于“務實”范疇,理念培育和內化屬于“務虛”范疇。雖然上合組織存在“說得多做得少”的問題,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放松在“務虛”方面的工作。在某些情況下,理念培育和內化能夠對上合組織的發展產生更加實質性的影響。在“務虛”方面,至少應做到以下兩點。
第一,進一步培育辯證的求同存異協調互動理念。隨著上合組織不斷發展壯大,成員國對本組織的認知和利益訴求越發多元,異質性愈加突顯。某種程度上,這種異質性已成為上合組織持續深入發展的結構性障礙,短時間內難以清除。不過,由于各國在所處地緣環境、發展模式、發展程度、所屬文明等諸多方面都不盡相同,因而它們對上合組織持不同認知和利益訴求也屬正常現象。鑒于此,在正視問題的同時,需堅持在上合組織內部培育辯證的求同存異協調互動理念,積極推動各成員國對本組織的認知達成基本一致并擴大安全利益訴求交匯面,保留或擱置難以調和的認知和安全利益訴求。遵循此種思路,共同點無疑是基本的,分歧只是局部的。培育辯證的求同存異協調互動理念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促使各成員國對上合組織的認知和利益訴求完全一致,而在于在尊重和包容差異的基礎上實現共同安全和共同發展。如果成員國的共同利益訴求能夠得到基本滿足,那么各國的相關認知將會變得更加積極,對上合組織的認同程度也會明顯提升。過度追求成員國之間的“同一性”將威脅到各國的“獨特性”,①有關認同框架下“同一性”與“獨特性”的辯證關系的討論,可參見李孝天:“國家集體認同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階段”,《社會主義研究》,2020年第3期,第133-135頁。容易引發部分成員國的猜疑和反感,反而會產生與預期相反的消極影響。
與此同時,在涉及成員國核心利益的原則性事宜上,擱置爭議并不代表任何一方作出妥協,或者放棄緩和乃至解決分歧。各成員國仍要繼續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的“上海精神”,不斷嘗試化解分歧。成員國之間分歧的化解將使得客觀同質性增強,進而減少由異質性引發的沖突,②[美]亞歷山大·溫特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2-343頁。有助于提升各國對上合組織的認同程度。此外,當某一成員國的核心利益與上合組織的核心利益發生沖突時,在不損害其他成員國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應優先考慮該成員國的核心利益,而后兼顧本組織的核心利益,盡量將損失控制到最小限度。因為上合組織的首要任務本就是滿足成員國的合理利益訴求。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成員國可以凌駕于上合組織之上,二者之間更多是一種合法的委托—代理關系。成員國的共同利益與上合組織的發展利益在根本上應當是一致的。在秉持求同存異協調互動理念的基礎上,上合組織可積極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安全治理理念,擴大地區安全公共產品供給,以期更快和更好地實現維護地區安全、促進共同繁榮發展的目標。
第二,內化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培育求同存異的協調互助理念是統籌成員國對上合組織認知和利益訴求異質性的有效策略,內化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則具有顯著提升各國對本組織認同程度的巨大潛力。鑒于此,上合組織應繼續宣傳并倡導成員國內化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以平等、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安全為基礎,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觀,共建上合組織命運共同體。只有全體成員國在主觀上都能認同客觀命運共同體的存在,各國才能真正做到擯棄分歧、精誠協作,不斷致力于提升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的有效性與合法性。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言,“要繼續在‘上海精神’指引下,同舟共濟,精誠合作,齊心協力構建上海合作組織命運共同體,推動建設新型國際關系,攜手邁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①習近平:“弘揚‘上海精神’構建命運共同體——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八次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海外版》,2018年6月11日,第2版。
欲在上合組織內部成功地內化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需使用合理、有效的方略進行宣傳。就宣傳渠道而言,除官方宣傳外,應開辟更多非官方宣傳渠道,“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雙管齊下,確保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成員國的官方與民間深入、全面地內化。同時,應以靈活、公開的辯論形式對各成員國進行宣傳,要以各國能夠理解的方式進行宣傳和探討,尊重不同的文化和聲音。這有助于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不同成員國的內化進程,提升各國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認同。在宣傳過程中,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可能面臨其他規范的競爭。鑒于理性的國家往往會主動地接受最佳規范,故還需在理論上進一步豐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內涵,努力使其成為國際社會公認的最佳規范。就宣傳的核心內容而言,應著重宣傳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原則化信念”和“因果信念”。其中,原則化信念指涉“詳細說明區分對與錯、正義與非正義標準的規范性觀念”。②[美]朱迪斯·戈爾茨坦、[美]羅伯特·基歐漢:“觀念與外交政策:分析框架”,載:[美]朱迪斯·戈爾茨坦、[美]羅伯特·基歐漢主編,劉東國、于軍譯:《觀念與外交政策:信念、制度與政治變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頁。它是指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運行與發展的核心規范。成員國對原則化信念的態度深刻影響著它們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態度。因果信念指涉有關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因果關系的看法,如為何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原則化信念和因果信念能夠為維護地區安全、促進共同發展提供“路線圖”,推動上合組織地區安全治理體系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四、結 語
當前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與地區層面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越發明顯。作為歐亞地區安全治理的重要行為體,上合組織在維護地區安全、培育治理理念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然而,在回顧業已取得的成就時,不應忽視上合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面臨的內在限制和舊新安全挑戰。在上合組織覆蓋地區,既有重大安全問題如“三股勢力”以及非法販運毒品和武器等跨國犯罪尚未得到完全解決,又有新冠肺炎疫情等安全挑戰接踵而至,對本組織參與地區安全治理構成新的嚴峻挑戰。就抗擊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而言,上合組織迄今還未發揮太多實質性作用。多數成員國似乎也沒有對上合組織寄予厚望。相比之下,俄羅斯和中亞成員國更多寄希望于歐亞經濟聯盟應對疫情,且歐亞經濟聯盟的確作出了實質性貢獻。換言之,上合組織應對此類突發重大公共衛生安全問題的能力和效力仍有很大提升空間。此外,考慮到塔利班重新執政后阿富汗國內形勢具有高度不確定性,上合組織還要謹防阿富汗國內安全風險向周邊地區外溢。為妥善應對既有、突發和未來可能出現的地區重大安全挑戰,上合組織需做到與時俱進和未雨綢繆,結合不斷變化的地區和全球安全形勢,著力推進地區安全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