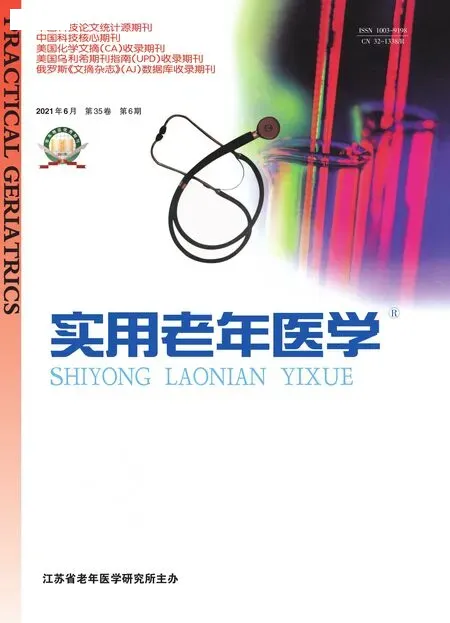腦白質變性與阿爾茨海默病相關性的研究進展
侯永蘭 朱愛琴
AD是一種進行性神經退行性疾病,是癡呆最常見的類型,約占癡呆病例的70%[1]。目前對AD的發病機制、早期診斷和治療仍未取得理想進展,關于AD的發病機制主要有以下幾種學說:β-淀粉樣蛋白(Aβ)毒性學說、tau蛋白過度磷酸化學說、炎癥學說、氧化應激、線粒體功能障礙學說等[2]。最新研究提示,AD病人腦中廣泛存在微血管病變,主要包含腦白質病變( white matter lesions,WMLs)、腦淀粉樣血管病變、腦內微出血、腔隙性腦梗死、血-腦脊液屏障的破壞等[3]。WMLs的存在可能是輕度認知障礙(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進展為AD的危險因素[4],白質( white matter,WM)微結構改變被認為是神經退行性疾病早期診斷的一個潛在的附加生物標記物,但具體影響機制尚不清楚,本文就WMLs與AD相關性作一綜述。
1 WMLs概述
WMLs又稱為腦白質高信號(white matter hyperintensity, WMH)、腦白質疏松(leukoaraiosis, LA),其屬于腦小血管病變(cerebral small vessel lesion,CSVD)的一種。根據發病部位不同,參照Fazekas評分,WMLs可分為腦室旁白質病變(periventricular lesions,PVLs)和皮質下深部白質病變(deep white matter lesions,DWMLs)的彌漫性斑點狀或斑片狀改變,CT表現為低密度,MRI在T1加權像表現為偏低信號、液體衰減反轉恢復序列,T2加權像表現為斑點狀或斑片狀腦白質高信號。WMLs常見于正常衰老、存在血管危險因素、AD和血管性癡呆病人中, 目前病因不明確, 臨床表現復雜多樣,人們普遍認為,WMLs與認知能力下降、抑郁、步態紊亂和跌倒、卒中風險增加相關。
2 WMLs的病因
年齡增長被普遍認為是WMLs發展最重要的危險因素,隨著年齡的增長,WMLs的患病率也隨之升高,因此WMLs又常被稱為 “年齡相關性白質病變”。然而,目前尚不清楚WMLs在什么年齡段開始發展。大多數研究表明,WMLs至少在50~65歲以后出現, 65歲以后,隨年齡增加患病率增加[5],WMLs病變體積隨年齡增長而增大,而且變得越來越普遍和嚴重。關于性別與WMLs患病率之間關系的研究顯示了相互矛盾的結果。有些人發現女性LA的患病率有上升的趨勢[6],但另有研究發現男性患病風險更高[7]。
流行病學資料表明,高血壓是CSVD的主要危險因素,尤其與WMLs的發生密切相關。血壓增高導致內皮細胞受損,使血漿蛋白漏入血管壁,管壁發生透明變性和纖維化,造成血管壁增厚、管腔變窄、血流減少,可導致腔隙性腦梗死及大腦深部白質的缺血性脫髓鞘。SPRINT研究小組發現在高血壓病人中,將SBP控制在<120 mmHg與<140 mmHg相比,白質病變體積增加較小[8]。Lucatelli等[9]研究發現WMLs的體積和數目與糖尿病顯著相關,糖尿病病人有更多的全腦和皮質下腦萎縮、更大體積的WMLs,這可能與長期血糖升高導致大中動脈粥樣硬化,腦局部發生低灌注有關。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癥是重度 WMLs的危險因素,研究發現,同型半胱氨酸還可通過抑制血管新生而促進WMLs的形成[10]。
以往的遺傳研究表明,WMLs的遺傳力高達80%,一項多民族全基因組關聯研究確定了4個新的基因位點( Chr10q24、Chr2p21、Chr2p16和Chr1q22)與WMLs發生有關[11]。 研究還發現血管緊張素轉換酶(ACE)或載脂蛋白A、血管緊張素原、載脂蛋白E、甲基戊烯醇酯還原酶等基因多態性與WMLs有關[12]。
3 WMLs的病理機制
從解剖學角度來看,半卵圓中心和腦室周圍區域的血液供應來自長的穿孔支小動脈,很少有側支代償,因此,這些區域被認為是分水嶺區域,發生低灌注時該區域容易發生缺血性改變,重復的缺血、缺氧可引起炎癥反應,導致蛋白酶和自由基生成, 順向分解髓磷脂,產生 WMLs并不斷擴散[13]。彌漫性細動脈硬化引起的慢性缺血可能與WMLs的存在有關。 血腦屏障位于內皮層,能阻擋病原微生物及其代謝產物從血流進入腦組織或腦脊液,血腦屏障功能障礙導致血管“滲漏”,是多種炎癥性和退行性腦疾病的特征,包括多發性硬化(multiple sclerosis,MS)、腦瘧疾、HIV腦炎和AD[14]。腦白質缺血缺氧性繼發炎癥反應與氧化應激是引起WMLs發生發展的重要機制之一。炎癥反應的特點是白質內星形膠質細胞和小膠質細胞反應性增生并釋放炎癥因子,導致相關軸突退化、脫髓鞘,破壞白質完整性。 Huang等[15]首次提供了中國人群中WMLs的全基因組DNA甲基化分析,揭示了 WMLs的發生和發展與 DNA的廣泛甲基化有關。研究發現細胞凋亡可能在WML的發病機制中起一定作用。 Simpson等[16]采用RNA微陣列和路徑分析技術提取WMLs和無WMLs腦組織 RNA發現,凋亡相關基因 caspase-2和組織蛋白酶B在深部皮質下病變(deep subcortical lesions, DSCL)中的表達較正常WM組織增加,DSCL的細胞周期基因較正常WM組織降低,其可能導致髓鞘降解、細胞外基質破壞和血腦屏障破壞。
4 WMLs的診斷
彌散張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是在磁共振擴散加權成像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成像技術,可定量分析水分子在不同方向上擴散的各向異性,從而觀察組織的細微結構,無創性提供更多常規MRI無法獲得的諸如人體組織微觀結構、神經纖維走向及受損情況、膜滲透性等方面的信息。常見的定量測量方法是分數各向異性(fractional anisotropy,FA)和平均擴散率(mean diffusivity,MD),它們提供了關于體內WM微結構的信息。FA是一種各向異性水擴散的度量,反映了WM擴散域內細胞結構的方向性程度,其范圍為0~1,取值越大表示各向異性越大,組織排列越緊密規則;其值越小表明各向異性越小,組織排列規則越差。MD為非共線方向的平均擴散率,增大表示水擴散的增加。在受損的WM中,由于軸突壁的破裂和液體的堆積,可導致MD增加FA下降[17]。一項縱向研究表明,DTI對WM超微結構的年齡相關變化很敏感,在較短的時間內(2年)可以檢測到DTI參數的變化[18]。此外,在對CSVD中/重度WMH和腔隙性腦梗死病人DTI研究中發現,WM和WMH的FA降低,MD增加,表明WM的組成和完整性下降[19]。
5 WMLs與AD的相關性
WM纖維束決定信號的傳導速度,負責傳輸和控制信號,認知功能的實現依賴WM纖維束對神經信號的有效傳導能力。有研究發現MRI中觀察到的 WMLs數量隨AD的進展而增加,高達89%的病例發現了 WMH,其嚴重程度高于非癡呆老年人[20],WMLs體積與整體認知評分呈顯著負相關[21],提示WMLs與整體認知功能下降有關。而 Vibha等[22]發現 WMLs對總體認知功能的影響較小,只有WMLs嚴重到一定程度導致腦體積縮小才會引起臨床上可發現的認知功能減退。一項系統回顧性研究表明,WMH增加癡呆和AD的風險,WMH的存在可能增加個體進展為MCI或認知測試成績下降的風險,與整體認知能力以及執行功能和處理速度的快速下降有關,可能的機制是皮層下神經網絡直接受損,執行功能下降(被認為依賴于穿過WM的皮質下回路)[23]。
關于不同腦區的 WMLs與認知障礙間的關系存在爭議。一項長達13年的研究對104名認知正常的男性和女性隨訪并進行3次MRI掃描發現, DWMLs與認知功能減退有關,可能是DWMLs破壞短連接,從而損害由特定腦區支持的認知功能[24]。更多的研究發現,與 DWMLs相比,PVLs會破壞與空間上較遠的皮層區域的較長連接,從而可能導致多個領域的認知能力下降(記憶和執行/處理速度兩個領域)[25]。顳區WMLs聚集的模式可以識別出 MCI或AD風險增加的個體,額葉(特別是前額葉和背外側) WMLs體積與執行和記憶功能降低有關,頂葉和枕葉WMLs體積的增加與處理速度得分降低相關[26-27]。有研究通過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室周WM的WMH體積對控制性口語聯想和顏色Stroop測驗表現有很強的預測作用。頂枕葉和室周WM區域的WMH的范圍和分布,與疾病嚴重程度和認知能力下降有關[28]。
對于WMLs病人WM纖維束與AD之間的研究尚未形成統一定論。一方面因為WM纖維束與MCI和AD全腦體素研究很少,另一方面認知單元構成比較復雜,通常需要多個腦功能區的相互配合。DTI的應用揭示了AD早期和MCI病人的微觀結構變化和各向異性降低。對AD的DTI研究表明,胼胝體、扣帶、穹窿、鉤狀束、上下縱行束等后腦區參與了早期的神經退行性變[29],而MCI病人邊緣和連合束的WM改變似乎是評估AD進展的重要標志[30]。關于WM損傷主要累及胼胝體是AD中最一致的發現之一,而關于胼胝體具體位置的證據存在矛盾[31-32]。
高原具有低氧、低氣壓、高寒、輻射、風速大、晝夜溫差大等特點,動物和人體研究發現,長期處于低氧環境中的人,大腦可出現記憶、學習等認知功能損害,高海拔地區老年AD的發病率與內地相比明顯升高,提示了環境因素對AD的發病有重要的影響[34]。即使從高海拔地區返回海平面后,神經心理缺陷也可能持續存在。研究發現WM中最豐富的細胞類型少突膠質細胞對缺氧的影響高度敏感,持續的缺氧會選擇性地殺死少突膠質細胞,導致脫髓鞘。少突膠質細胞可能在缺氧條件下通過瞬間受體電位離子通道(TRPA1)導致細胞內鈣的致死性H+門控增加而死亡[35]。慢性缺氧可能上調蛋白激酶,包括糖原合成酶激酶3β(GSK-3β)和細胞周期依賴性激酶5(CDK5),抑制蛋白磷酸酶2(PP2A)導致tau蛋白磷酸化增強[36]。缺氧情況下,與Aβ清除相關的酶如中性化鏈內切酶(NEP)、胰島素降解酶(IDE)、內皮素轉化酶(ECE)等活性下降[37],Aβ經酶代謝清除減少,過多的Aβ可通過氧自由基代謝、細胞調亡等作用產生神經毒性導致 WMLs加重。另外,慢性缺氧狀態下機體交感系統激活,氧化應激、炎癥及神經體液改變,慢性彌漫性皮層下缺血、缺氧使腦細胞線粒體代謝紊亂和葡萄糖代謝減低,使膠質細胞脫髓鞘、軸索缺失,破壞了大腦皮質與皮質下的纖維聯系,從而導致認知功能減退[38]。
綜上所述, 盡管WMLs與 AD之間的具體發病機制仍不清楚,通過WMLs檢查可能有助于識別 AD或認知能力下降的風險人群,針對相關危險因素采取行動控制可能使他們從早期干預中受益并減緩疾病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