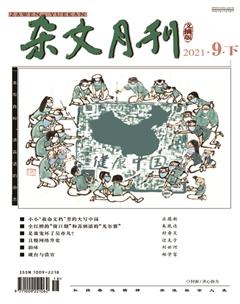別在“過度反思”中失去人情溫度
曹林
看到一個(gè)網(wǎng)紅學(xué)者的自述,覺得挺心酸。人與人之間將心比心的理解太重要了,千萬別在自以為是的過度反思中失去人情溫度。
這位學(xué)者常出現(xiàn)在各種節(jié)目和平臺(tái)中,講課、演講、視頻很多,被認(rèn)為是出場費(fèi)最高的文學(xué)教授之一。人紅是非多,出場費(fèi)高,自然就有人不滿,有人當(dāng)面質(zhì)疑他:你的課程很好,但是你這樣為了錢到處走穴,有一個(gè)文人學(xué)者的風(fēng)骨和風(fēng)范嗎?作為知識(shí)分子,更應(yīng)該懂得“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道理吧?這位學(xué)者在節(jié)目中無奈地解釋:我夫人得了肺癌,一盒抗癌藥51000元,這是我?guī)讉€(gè)月的工資你們知道嗎?很多人批評(píng)我到處賺錢沒有文人風(fēng)骨,可是如果丟了妻子,我要文人風(fēng)骨做什么?有一次,他回到家后發(fā)現(xiàn)妻子正號(hào)啕大哭,原來一顆藥掉在地上找不到了,一顆藥就是上千元錢,太傷心了。他知道夫人不是心疼錢,是心疼他這個(gè)年齡還為了治病四處奔波賺錢。
聽到這位學(xué)者的講述,可能就明白那種站在道德高地的所謂“文人風(fēng)骨”是多么空洞,自以為尖銳的道德批判和“反思”是多么無力。要文人風(fēng)骨,還是治病救命?這不是一道哲學(xué)倫理題,不是脫口秀或吐槽大會(huì)的抽象辯題,在一個(gè)家庭的、具體的生命世界中,就是一個(gè)人的生命,是“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的夫妻情感。不需要高談闊論,也無須什么“深刻反思”,本能是不惜一切代價(jià)去為妻子治病。何況,學(xué)者靠自己的本事去講課賺錢,本就是很有知識(shí)分子尊嚴(yán)的事,沒有丟知識(shí)分子的臉,絲毫未失文人風(fēng)骨。那種用抽象的“文人風(fēng)骨”把文人綁架在貧困、寒酸、落魄的形象上,制造文人與財(cái)富的對(duì)立,把“要風(fēng)骨還是要生命”變成非此即彼的對(duì)立選項(xiàng),是對(duì)人的貶低。
倫理規(guī)范啊,性別意識(shí)啊,階層流動(dòng)啊,文人風(fēng)骨啊,總感覺公共討論中這種“大詞”太多了,背后是一種“什么事都往抽象處內(nèi)卷”的過度反思。哲學(xué)家陳嘉映在《走出唯一真理觀》中批評(píng)了當(dāng)下社會(huì)的“過度反思”,他引用威廉斯的話說,無所不在的反思會(huì)威脅和摧毀很多東西,因?yàn)樗鼤?huì)讓原本厚實(shí)的東西變得薄瘠。
抽象的道理不能脫離基本的生活語境,不能不考慮人情常理。一個(gè)年輕人得了絕癥,家人傾家蕩產(chǎn)砸鍋賣鐵籌錢治病,你作深刻反思狀,說什么“面對(duì)絕癥要坦然面對(duì)生死”“要意識(shí)到醫(yī)學(xué)的有限”“尊重自然規(guī)律、放棄不切實(shí)際的幻想”等,這種冷冰冰的、抽象的大道理,顯然也是悖離人性的過度反思。
如何防止過度反思?陳嘉映開出的藥方是,停下來,跟自己的經(jīng)驗(yàn)對(duì)勘,不能只循著道理去反思。跟不那么好反思的人交談,多與人交流,用厚實(shí)的生存托起反思,否則反思會(huì)飄起來。我的理解就是,多面向生活,在生活的情境中去思考問題,而不是在抽象邏輯中陷入概念內(nèi)卷。
維特根斯坦也很反感“過度反思”導(dǎo)致的混亂,提出一些根本就不存在的問題,并為解決這些問題而痛苦不堪。對(duì)這種人,維特根斯坦說了一段常被引用的名言:一個(gè)人陷入哲學(xué)混亂,就像一個(gè)在房間里想要出去又不知道怎么辦的人,他試著想從窗子出去,但窗子太高;他試著從煙囪出去,但煙囪太窄;其實(shí)只要他一轉(zhuǎn)身,就會(huì)看見房門一直開著的。很多事情,反思反而搞復(fù)雜了,搞出很多偽問題,為了解決一個(gè)問題制造了更多問題。學(xué)者塔勒布提到過“布里丹之驢”:一頭又饑又渴的驢剛好站在距離食物和水一樣遠(yuǎn)的地方,由于在先喝水還是先吃草這兩個(gè)選擇間難以取舍,它不可避免地死于饑渴。但,問題其實(shí)很簡單,這頭驢啥也不想,隨機(jī)地往水或食物的方向走出一步,問題就解決了。
人是萬物的尺度,生活之樹常青,保持跟常識(shí)、常情、常理、常人對(duì)話的能力,永遠(yuǎn)不要讓對(duì)抽象道理的關(guān)心高于對(duì)人的關(guān)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