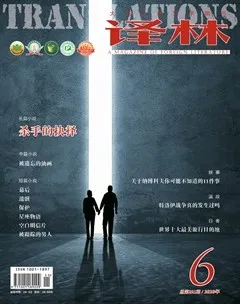幕 后
“辯護方傳喚埃米莉·福里斯特。”
我站起身時,律師捏了捏我的手。如果有人注意到這點,他們可能會認為這是一種安慰。我心里更清楚,鮑勃是在勸我遵尋他的計劃,而不是我的計劃。很遺憾,鮑勃,這是對我的謀殺審判,所以要以我的方式來行事。
我高昂著頭,嘟著嘴巴,走向證人席。我必須看起來得體,無辜卻難過。這并不難。我的確是無辜又難過。我從來沒想過要殺死丈夫。嗯,在他逼我這么做之前沒有想過。
宣誓后,我鎮定地坐下來,手指滑過證人席前面的木柵欄。那平滑而有光澤的表面,讓我想起了幾年前我們主屋的地板是多么漂亮。一旦從這件事情中脫身,我就要把家里里外外重新裝修一下。
律師桌后的鮑勃向前傾著身子。我希望他能站起來靠近陪審團,這樣他們才能完全聽清他說的話。鮑勃是那種很招女性喜愛的男人,高個子,黑頭發,有著花崗巖般的下巴,睿智的藍眼睛,筆挺的炭灰色西服。不幸的是,正如我本周所了解到的那樣,北卡羅來納州對律師的管控很嚴格,鮑勃在向我提問的時候只能坐著。
他微笑著說:“請報一下你的名字。”
“埃米莉·福里斯特。”
“你是亞倫·福里斯特的妻子嗎?”
“是的。”
“你們有孩子嗎?”
“兩個,”我微笑著回答,“塞思17歲,露西16歲。”
“你們住在哪里?”
我回答了鮑勃這個問題——實際上我有兩處房產,一處是位于維克森林的主屋,一處是日落海灘附近的海濱房。亞倫就是在海濱房露出了本來面目。
鮑勃又問了幾個簡單問題,然后說:“你能告訴我們去年8月3日發生了什么事嗎?”
我點了點頭,“我——”
“反對!”作為公訴人的地方檢察官柯克·杰勒德拍了拍桌子。他的銅色假發散落在額頭上——他以為戴上那蹩腳的東西就能騙到誰??
就是否允許我以自己的方式——鮑勃稱之為“陳述式證詞”——來講述案情,而不是回答一個又一個枯燥乏味的問題,鮑勃和杰勒德在法官面前展開了激烈爭論。對此我只能無奈地嘆了口氣。鮑勃已經預料到了這一點。他說,控方不喜歡陳述式證詞,因為他們無法預料證人接下來會說些什么,不利于他們提出異議。我認為,正是出于這一原因,鮑勃喜歡這種形式的證詞——激怒杰勒德,讓他敗下陣來。當然,我只想對陪審團敘說。我一直善于說服別人,而且我知道,如果不是經常被打斷,在此處我可以做到這一點。最終,幾分鐘后,法官做出了對我們有利的裁決。或許,鮑勃配得上他高昂的律師費。
“福里斯特夫人,你可以繼續說下去。”法官說道,蒼白的嘴唇露出一絲笑意。
我感激地點點頭,轉向陪審團,開始講述我的故事。我很快就直奔主題,“人們一直在說,我丈夫死了我很高興。因為那筆壽險賠付金,地方檢察官稱我是‘有錢的寡婦’,還聲稱我不是受害者,而是整件事的策劃者。”
我直視著杰勒德那雙刻薄的棕色眼睛。他從未相信過我的故事,堅持認為我編造了一切,認為我為錢財謀殺了亞倫并偽造了犯罪現場。不過我知道,一旦我解釋了一切,陪審團里的女人們就會相信我。女人都很務實,我把目光緩緩轉向了她們。
“甚至我的朋友們都說,沒有亞倫我會過得更好。我認為,他們提醒我他如何酩酊大醉,如何沒有全心全意地愛我,只是想讓我心情好點。想想他企圖殺死我這件事,顯然他們說的沒有錯。”我有意停頓了一會兒,好讓那些話語的影響力深入人心,“但是深夜睡不著的時候,我明白了其他一些真相。真相是這樣的:我知道從我們相遇的那一刻起,亞倫就是我的意中人,我的未來——”
“法官大人,”檢察官說,“我反對。這是謀殺審判還是愛情告白?被告人——”
“駁回,”法官說,“這個問題我們已經解決了。允許福里斯特夫人以敘事的形式作證。”他轉向我,“你可以繼續講。”
“謝謝你,法官大人。”我看著陪審員們,“不過即使亞倫是我的意中人,他也并不完美。這就是我現在站在這里的原因。作為妻子,幫助亞倫在生活的各個領域取得成功是我的本分。正是在我的激勵和堅持下,我們才有了那座海濱房。我們是一個成功的家庭,有兩個學習成績優異的孩子,有位于理想社區的豪宅。漂亮的海濱房是我的另一個目標,盡管亞倫并不想買。”
我拍了拍手。亞倫不愿意我們擁有該有的社會地位,這事仍然讓我感到困擾。
“他喜歡宅在維克森林的家里,”我說道,“但是我們應該往上走,這就是美國夢,要比父母走得更高遠。所以,我們在日落海灘購買了海濱房。一段時間以來一切都很美好,直到我們的股票投資出現下跌。因此,我鼓勵亞倫申請升職。更高的管理層,更高的聲望,更高的報酬。他做到了。就像丈夫們應該做到的那樣,我的丈夫成功了,我很高興。”
我再次停下來,想起了我們在一起的最后的日子,亞倫讓我感到意外,“當然,亞倫對成功的看法與我不同,那時我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我只是覺得他有些懶散,而我必須敦促他發揮出全部潛力。”
當我說出懶散這個詞的時候,我可以發誓,我聽到了婆婆發出的噓聲。她坐在地方檢察官身后的那排椅子上,瞪著我,淺褐色的眼睛里充滿了仇恨。我總想讓她喜歡我,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結果怎么會如此糟糕?哦,是的,我原以為我可以促使亞倫成為一個更優秀的男人。
“相反,我把他變成了一個不快樂的人。”我告訴陪審員們,“在我們的婚姻初期,亞倫下班回到家時,雖然常常顯得很疲憊,卻充滿活力,急于告訴我他和他的團隊新制定的一些財務策略。后來我的丈夫回家越來越晚,脾氣也越來越壞,心情不佳時就借酒澆愁。他討厭作為高管的所有文書工作,痛恨官僚主義,而且我認為他開始恨我。當然,我當時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我搖了搖頭,“最終,因為我一直試圖把他變成我認為他該有的樣子,而不是接受他本來的樣子,我們的婚姻失敗了。”
我從旁邊的水罐里倒了一些水,好讓陪審員們有時間思考我說的話。鮑勃曾建議我不要說這個,不要對發生的事情擔責。他一直在提醒我,這是自衛。不要給陪審團定罪的借口。但是鮑勃錯了,多數陪審員是女性。她們會理解,要幫我的家庭興旺發達,就需要我促使亞倫抓住機會。她們會明白情況怎么會變得一團糟。
我喝了一點溫水——你可能以為他們會提供冰水——然后再次轉向陪審員們。
“不管怎樣,去年夏天,我安頓好孩子們,就開車去日落海灘的海濱房。我要跟鎮上的女人們參加慈善活動。星期四上午,我會在海濱市場買新鮮水果和蔬菜,那個時候大家都購買有機食品。”幾個陪審員點了點頭。“我涂上防曬霜,戴著帽子坐在海灘的大遮陽傘下面,看著最新的熱門小說。我等待著周末亞倫的到來。我計劃著我們的日子,從日出開始,該參加的活動,該見的人,該出席的聚會。他想跟孩子們一樣,在家睡覺,不過我堅持要他早早起床。如果周末我獨自一人在城里閑逛,那像什么樣子?所以,他陪伴我外出,我鼓勵他要更熱心。不過我能看出來他不高興。”
我開始觸及事情的核心,于是又仔細地觀察了一番陪審員們。他們的心思比我預想的更難看懂。不過,至少有幾個人似乎有同情之心——歪著腦袋的離婚女人,滿臉皺紋的白發老太,以及像我一樣40歲出頭的媽媽。
“7月下旬,我再次安頓好孩子們,向南驅車三個小時到達父母在查爾斯頓附近的養老院。我母親的生日就在那一周。在那期間,她肯定感覺到了我婚姻中的緊張氣氛。她問起了我臉上的皺紋、我恍惚的眼神。”
我瞥了一眼媽媽。在整個庭審過程中,她一直勇敢地和爸爸坐在鮑勃的身后。她為出庭而穿的禮服堪稱完美,量身定做,富有品位。她的銀發經過精心梳理,不過額頭上也新增了一些皺紋。
“我告訴媽媽一切都很好,沒有必要讓她擔心。我知道可以通過與亞倫度過一個完美的周末來修復我們的婚姻,讓他記住我們是天生的一對。因此,母親生日后的第二天,我告訴她,我要回日落海灘,和亞倫共度一個浪漫的周末。”
想起那一天我的心里并不好過。現在我的目光掃過法庭,無法專注于任何人或任何東西。我的思緒回到了海邊,海鷗鳴叫,空氣潮濕,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
“我在海濱房附近的一家便利店停下車,買了紅酒、鮮花和一些不錯的鮭魚排。傍晚,我把車開進車庫的時候,感到很驚訝,亞倫的車在那里。我本以為要比他早到幾個小時。我整理了一下上衣和裙子,走進屋子,喊道:‘亞倫,我回來了。’可是他沒有回應。
“我把魚排和紅酒放進冰箱,把鮮花插進水晶花瓶,然后放在樓梯旁的桌子上。我正準備去屋后的平臺上找亞倫,這時聽到樓上傳來了音樂聲,輕柔而性感。我意識到,亞倫就在那里。他計劃了一個魅惑之夜。他終于有所行動了,本來就應該那樣子的。
“我匆匆上樓,松開頭發,很高興自己穿著漂亮的性感內衣。只有幾步就到臥室了,這時有什么東西重重地砸在我的后腦勺上,我一下子昏了過去。我認為我昏迷的時間并不太長,不過足以讓亞倫把我綁在角落的軟墊扶手椅上。繩子繞過我的肚子——隔著衣服,所以不會留下痕跡。我醒來時,頭暈眼花,困惑不解。他站在我旁邊,眼露兇光,舉槍對準我的臉,那是一把為保家護院而準備的槍。”
那一刻仍然讓我心有余悸。我應該起訴那家槍械公司,不過現在還是回到亞倫身上吧。
“他用冰冷的語氣告訴我,他要殺了我。‘不過在殺你之前,’他說道,‘我想讓你知道這是為什么。’然后他非常詳細地告訴我,我每次催促他實現目標時,都會惹惱他,好像那是一件壞事。他繼續說著,聲音不斷抬高,直到對我大聲吼叫。他罵得很難聽。我第一次希望,我們買的房子有近鄰,有愛管閑事的人,他們會打電話報警。”
我從來沒有想過,隱私會成為問題。
“不管怎樣,一開始我抗議過。但是他把槍向前伸了伸,所以我就不吭聲了。槍指向你時,槍口似乎更大了。”我嘆了口氣,“亞倫咆哮著數落了一會兒我的缺點。然后,就在雷聲把窗戶震得嘎嘎作響時,他解開了我身上的繩子,讓我站起來,說我們要去兜風。”
我差點笑出來,仍然難以置信。“他真的打算殺我。不管我為他做過什么,他就這樣回報我。我們開始下樓,槍抵在我的后背上。
“‘走!’他說道,推著我走快些。
“我轉向他,懇求道:‘求求你不要這樣。我們可以解決問題。你愛我。我知道你愛我。’
“他冷漠地笑了,沒有改變主意。
“下到最后一級樓梯后,我再次轉過身。可是我還沒開口,他就大喊:‘閉嘴!埃米莉,我煩透了你的嘮叨。’他沒有看到那個花瓶,而我則像發現救命稻草一樣,抓起花瓶砸在他頭上。
“亞倫倒下了,槍掉在了地上,水和鮮花飛落。有那么一刻,我呆呆地站著,但只是一會兒,因為亞倫睜開了眼睛,撲向那把槍。我從地板上一把抓起搶,瞄準,然后開了槍。
“我以前從來沒有開過槍。槍的震動撼動了我的身體。但是,最讓我震撼的是看著亞倫癱倒在大理石地板上,開始流血。我跑過去打電話報警,手里仍然拿著那把沉重的槍。”
現在我淚如雨下,就像那天晚上傾瀉在海濱房屋頂的大雨一樣。我再次看向陪審員們——眼睛睜大,嘴巴張開。那個孕婦把手掌放在胸口上,那個離婚女人,就像一些男人一樣,給了我一個傷心的微笑。
“這是自衛,”我繼續說道,“不過這仍然是我的過錯。我不夠愛他,沒有接受本來的他,因而逼得他那么做。我為此感到抱歉。”
現在,陪審員們肯定明白了為什么亞倫企圖殺我,他們會相信發生的事情,相信我為何除了自衛之外別無選擇。他們肯定會的。
有幾秒鐘的時間,除了我的抽泣聲,法庭里靜默無聲。
“福里斯特夫人,你想休息一下嗎?”法官問。
“是的,”我點了點頭,“不過我說完了。”
“吉爾摩先生,你還有其他問題嗎?”法官問鮑勃。
“沒有了,法官大人。”
“好,”法官說,“現在休庭,明天上午9點繼續進行質證。”
到第二天庭審繼續進行時,我已經控制住了自己,并為應對檢察官做好了準備。好事。杰勒德猛烈地攻擊我,說什么亞倫的薪水不能支撐我的“高昂品位”。他聲稱我驅使亞倫尋求升職,從而他才有資格獲得大額人壽保險;聲稱在亞倫死去的那個周末,我有意不讓孩子們在海濱房,所以沒人能反駁我的說法。感覺好像陪審員們對我的看法開始轉變了,他們朝我看的時候,皺起了眉頭。
杰勒德對我的質詢終于結束了,他和鮑勃進行了最后的辯論。最終,法官對陪審團下達了冗長的指令,陪審員們被派到外面去商議。鮑勃和我回到他的辦公室等待。爸爸媽媽想過來,但我不能跟他們相伴。鮑勃叫了午餐,我卻吃不下。既然我再也無法控制裁決結果,我的精力也就消失殆盡了。
不到三個小時,法院的職員就打來了電話,陪審團回來了。
“商議的時間這么短,可能意味著有罪裁決,”?鮑勃說道,“你應該做好心理準備。”
不,不可能。
我平靜地和鮑勃一起回到法庭。爸爸媽媽朝我微笑,不過恐懼已經讓他們面無血色。我很高興孩子們不在現場,看不到這些。很高興我的妹妹丹妮爾同意在庭審期間讓塞思和露西跟她一起待在維克森林的家里。甚至,我一度很高興,丹妮爾跟亞倫一樣,酗酒無度。我知道這很難聽,但是孩子們足夠聰明,從來不上丹妮爾的車,所以他們會很安全。而且他們會心無雜念。除了我的事情之外,他們還要擔心丹妮爾的酗酒問題。
不久,陪審員們回到各自的座位上。法官開門見山,直奔主題。
“陪審團有裁決結果了嗎?”他問道。
“是的,法官大人。”陪審團主席回答道。
他身材瘦長,是個木匠——作證時我無法看透的陪審員之一。鮑勃本來不想讓他出任陪審員,說他會恨我。現在,陪審團主席不愿跟我對視,我擔心這事讓鮑勃說對了。
當法庭職員把寫著裁決結果的紙條交給法官時,我和鮑勃站了起來。他摸了摸我的胳膊,這讓我感覺很好。這時我想起來,在婚禮上亞倫曾經這樣摸過我的手腕,使得我確信我們的婚姻會幸福。看看結局又怎樣呢。
法官看了眼裁決書,點了點頭,職員把紙條還給了陪審團主席。他從陪審席上站起來,開始大聲宣讀。
“我們陪審團,認定被告埃米莉·福里斯特——”他抬起頭,目不轉睛地看著我,“無罪!”
我用手捂住嘴。媽媽說:“感謝上帝!”旁聽的人群發出夾雜著驚訝、高興以及——主要是憤怒的嘈雜聲。然而我才不關心別人說什么呢,腦海中只回蕩著陪審團主席最后說出的兩個字。
無罪!無罪!無罪!
我癱倒在椅子上,眼睛濕潤,悲喜交加。陪審員們理解了,即使那些我無法看懂的人,也理解我。
恬淡寡欲的人就是這樣,你永遠不會真正地知道他們在想什么。
審判已經過去了幾個月,我也變得恬淡寡欲了。所以,我很高興,今晚有機會坐在父母的鄉村俱樂部游泳池旁,看著太陽落山,身邊沒有任何閑人,為了讓我心情舒暢,而不斷地問這問那,或告訴我一些趣事。為確保明天爸爸的70歲生日聚會一切順利,媽媽和爸爸去做準備了。孩子們正在看電影。至少,俱樂部的其他成員都是那種跟我微笑著揮手致意的人。沒有閑聊,我喜歡這點。我很高興有時間思考。
自判決以來,我花了很多時間來思考自己的生活。我意識到,自從我和亞倫相遇的那一刻起,我的婚姻就注定要失敗。我把他推到了懸崖邊上,我確實要為此負責。
但并非負全責。
亞倫死亡的那天,在他的咆哮和怒吼中,透露了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大學三年級的時候,他追求我,因為他認為我適合他。我符合他各方面的要求,迷人、聰明、果決。他說過,我會成為完美伴侶,幫他建立起完美的家庭。我倆的相似度比我預想的還高。
然而,事實證明,我有比他更大的夢想。我想住海濱房,想去歐洲旅游,想讓孩子們上昂貴的私立學校,還想有漂亮衣服和珠寶首飾。而亞倫想要的只是一個小賢妻,一個穩固的管理職位,以及時不時地來一點小刺激。我猜他認為有個情人會使他成為一個真正的男人。
雪上加霜的是,他不是隨便和哪個女人搞婚外情。他是跟我的妹妹!他們已經相好了很多年。他說,丹妮爾喜歡他原本的樣子,他們在一起很開心。而且他最終決定要跟她廝守一生,再也不聽我嘮叨了。和她在一起非常快樂,他不在乎別人怎么看。所以,經過一段適當的哀悼期之后,他會跟丹妮爾結婚,沒有與離婚及撫養費相關的各種麻煩和支出。
這件事我沒有向任何人提及,不論是我的律師、家人,還是我的朋友或陪審團。甚至對丹妮爾,我都沒有提起過。一個小時前,就在我去俱樂部之前,在父母家的樓梯上,我把她絆倒,她摔下了樓梯。她踉蹌一下,開始滾落,那從不離手的杜松子酒杯摔碎在鋪著地毯的臺階上。當丹妮爾的頭撞到樓梯口的木地板上時,發出了令人愉悅的撞擊聲。她的脖子像樓梯一樣扭曲著,鮮血從耳朵里汩汩地流出來。我很高興,不必親自動手把她的頭顱往地板上撞,盡管我已準備必要時那么做。
現在,爸爸媽媽應該已經發現了我那因醉酒而死的可憐妹妹,隨時都會給我打電話。讓他們承受這些,我很難過,可是真的沒有別的辦法。在亞倫出事之前,就不光只是我一個人發現她在破壞我的家庭。此外,爸爸媽媽都很堅強,在我的庭審過程中他們證明了這一點。他們能夠處理這件事。
至于我,我不確定接下來要做什么。塞思和露西將來會進入常春藤大學,亞倫的人壽保險賠付金足以支付他們的學費,并讓我保持我應有的生活方式。我的前途一片光明。我已經向世人表明,我能夠成為一位成功的妻子和母親——幕后的終極力量。現在,我要把這種力量釋放出來,提升一下多年來一直被我忽視的那個人——我自己。
不知道怎么直到現在我才意識到這一點。生活本該如此吧。
(劉葆花:青島理工大學人文與外國語學院,郵編:266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