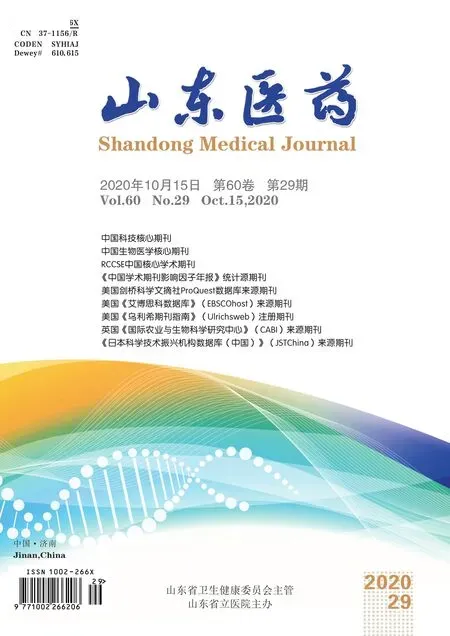二酰甘油激酶家族在神經系統中的功能與相關疾病研究進展
劉亞青,令調文,王天成
蘭州大學第二醫院,蘭州730000
甘油二酯(DAG)是細胞膜上重要的第二信使,其重要作用之一就是激活蛋白激酶C,在基因轉錄、細胞膜運輸和神經遞質釋放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在體內,DAG水平主要通過被二酰甘油激酶(DGKs)磷酸化為磷脂酸或被DAG脂肪酶代謝來調節。磷脂酸作為磷脂酰肌醇4,5-二磷酸的代謝前體,能夠激活磷脂酰肌醇激酶并參與調節細胞內多種信號通路,如雷帕霉素靶蛋白和Ras鳥嘌呤三磷酸酶激活蛋白等,同時也被認為是影響神經傳遞的重要調節因子。DGKs通過磷酸化DAG生成磷脂酸在細胞內發揮作用,由于其底物和產物均是細胞內重要的第二信使,因此對其結構、功能和調控的研究近幾年來備受關注。DGKs家族的一個重要特性是其不同亞型在中樞神經系統具有各自的時空表達特異性和疾病相關性,被認為可能是某些神經系統疾病的潛在治療靶點。迄今為止,已在哺乳動物中鑒定出10種DGKs亞型,目前主要根據其調控域不同將其分為5種亞型。現就DGKs不同亞型在神經系統中的功能與相關疾病研究進展綜述如下。
1 Ⅰ型DGKs
1.1 DGKα DGKα是惟一在中樞神經系統中發現的在膠質細胞而非神經元中表達的DGKs亞型,尤其是在少突膠質細胞中表達,而少突膠質細胞負責中樞神經系統中髓鞘的生成并與炎癥反應相關。同時,研究顯示DGKα與髓鞘的主要成分之一髓鞘堿性蛋白共定位,表明DGKα可能參與少突膠質細胞髓鞘的產生、調控或維持過程[1]。Poli等[2]發現,核內DGKα活性或表達的改變可以改變視網膜母細胞瘤蛋白的磷酸化,從而調節細胞周期的G1期向S期轉換,而這種細胞周期轉換停止通常會導致凋亡或自噬,提示核DGKα參與調節細胞周期的重要作用。此外,研究發現維生素E可以通過激活DGKα減輕野生型小鼠糖尿病神經病變的部分癥狀,而在DGKα-/-鼠中并未發現這種現象,提示DGKα為糖尿病神經病變免疫治療的潛在靶點[3]。目前關于DGKα的研究更多集中于腫瘤和免疫領域,而在神經系統中的研究相對較少。
1.2 DGKβ DGKβ在神經系統中主要表達于嗅球、皮層、紋狀體和海馬神經元中,隨著突觸的發生、發育表達水平逐漸增高,并在小鼠出生后14 d腦內突觸形成的過程中顯著升高,具有獨特的膜定位[4]。研究顯示,在海馬和紋狀體中,DGKβ主要積聚在神經元樹突棘的突觸周圍[5]。在DGKβ敲除小鼠的海馬中,隨著DAG的累積和磷脂酸含量的降低,神經元樹突分支和棘突的數目均少于野生小鼠。此外,在原代培養的DGKβ敲除小鼠海馬神經元中,神經元樹突分支和棘突數量明顯減少,而這種情況可以被過表達的DGKβ所挽救,過表達的DGKβ可以促進體外培養第7天的樹突生長和第14天樹突棘的成熟,后續研究也得到了同樣的結果,表明DGKβ在神經突觸形成中的重要作用[6,7]。事實上,早在2001年人們就已經發現了人類DGKβ的16個剪接變異體,而其中一個位于C末端的35個氨基酸缺失的剪接變異與雙相情感障礙(BD)相關[8]。此外,研究顯示DGKβ可能通過影響中間神經元參與癲癇易感性過程,經戊四氮和海人酸點燃的DGKβ敲除鼠較野生型表現出更嚴重的癲癇發作,這些敲除鼠海馬CA3區的小白蛋白陽性中間神經元數量明顯減少,這對小鼠癲癇易感性的增加作出了部分解釋;同時,在敲除鼠的腦皮質中發現皮質棘密度較野生型明顯降低,小鼠表現出躁狂樣行為,而這種異常行為可以被鋰劑或哌甲酯部分逆轉[9]。以上結果均提示,DGKβ通過影響神經突觸或中間神經元參與多種神經精神疾病,可能是研究BD和注意缺陷/多動障礙的有效動物模型。
1.3 DGKγ 免疫組化結果顯示,大鼠出生后的腦中即存在DGKγ免疫反應性,在嗅球、中隔核、海馬和小腦中發現其強烈的免疫反應性,表明DGKγ在這些腦區高表達。出生后隨著腦發育,DGKγ的免疫反應性逐漸增加,但直到第28天的小腦浦肯野細胞中才出現DGKγ顯著表達,與浦肯野細胞樹突狀分支的生長時間段一致,這提示DGKγ可能與神經元形態發育相關。亞細胞定位研究發現其位于浦肯野細胞的胞體和樹突胞質。類似的研究顯示,在人神經母細胞瘤細胞SH-SY5Y中DGKγ定位于細胞胞質,海馬神經元中定位于胞質和近端樹突。然而,Matsubara等[10]研究發現DGKγ隨時間存在細胞內易位,C1結構域在這種核轉運過程中不可或缺。研究顯示,DGKγ激酶陰性突變質粒轉染的細胞體積變大、增長速度變慢、S期延長,表明核內DGKγ參與調節細胞周期,與同屬Ⅰ型DGKs的DGKα在核內的研究結果相一致。在神經母細胞瘤細胞N1E-115中的研究發現,DGKγ的C端與神經元軸突末端的絲狀偽足生長有關,在胞質內與微管微絲肌動蛋白F-actin共定位,提示其可能對神經元形態發育有影響[11]。截至2018年,從運動協調功能受損的DGKγ敲除鼠中分離出小腦浦肯野細胞進行原代培養,發現敲除鼠較野生型的樹突分支數量和長度減少,再次從體內研究證實了DGKγ對神經元形態發育的影響[12]。
2 Ⅱ型DGKs
2.1 DGKδ Natalia等[13]在1例12歲患有癲癇伴發育遲緩史、先天性毛細血管異常、輕度肌張力低下并伴有肥胖的女性患者中發現了染色體t(X;2)(p11.2;q37)的平衡易位,該斷點破壞了位于2q37的DGKD(編碼蛋白為DGKδ)。通過原位雜交檢測成年小鼠腦內DGKδ的表達模式,發現在孕12.5 d的小鼠中腦和前腦組織中DGKδ顯著表達,其在大腦皮層和海馬錐體神經元以及小腦顆粒細胞神經元中尤為突出,提示DGKδ與神經發育和腦病理生理相關;研究同時發現,GKD純合子突變小鼠的前腦和中腦組織中無DGKδ表達,小腦中僅有微弱表達,而其中50%的突變小鼠表現出異常的癲癇樣放電和癲癇發作,這些研究結果表明DGKδ參與癲癇發作的過程。此外,DGKδ還與脂肪生成和2型糖尿病相關,或許可以對前述提及存在DGKD破壞患者[13]的表型做出部分解釋。
2.2 DGKη DGKη在腦中表達最為豐富,在大腦皮層、海馬(CA1、CA2)和齒狀回區域、嗅球以及1~32周齡小鼠的小腦浦肯野細胞中均有高表達。目前,關于DGKη與疾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BD和腫瘤兩個方向。Baum等[14]在對兩個獨立BD病例樣本進行全基因組關聯研究時,在DGKη的第一個內含子區發現最強關聯信號,首次提出DGKη與BD的相關性。此后,多項不同國家的病例研究均證實了兩者之間的相關性。Isozaki等[15]通過構建DGKη敲除小鼠并對其進行行為學測試發現,小鼠表現出類似于BD躁狂狀態的總體行為學特征如多動、焦慮減少和抑郁狀態減少,而這些表型通過服用鋰劑后明顯改善,再次證實DGKη與BD相關,然而具體的病理生理機制尚未明確闡明。
2.3 DGKκ DGKκ在中樞神經系統中幾乎沒有表達,但在睪丸中尤其是初級和次級精母細胞中表達最高,胎盤中也發現有表達[16]。目前,尚未發現DGKκ在中樞神經系統與疾病相關的研究。
3 Ⅲ型DGKs(DGKε)
DGKε是目前已知所有DGKs中最小且結構最簡單的亞型,不同于其他DGKs亞型,其分子結構沒有調控域而是具有一個疏水域,特別偏好在sn-2位置帶有花生四烯醇(20∶4)基團的二酰甘油底物,是所有DGKs中惟一具有底物特異性的亞型,也被認為與其他DGKs亞型之間的功能重疊最小。DGKε在神經系統中主要表達和分布于小腦浦肯野細胞、海馬錐體細胞、嗅球和黑質神經元,由于其在腦組織中高表達,表明它可能在神經系統中發揮重要作用。事實上,早在2001年Turco等[17]就已經發現DGKε-/-小鼠較DGKε野生型小鼠表現出對電休克更高的抵抗力、更短時間的強直發作和更快的恢復時間。與此相一致,Musto等[18]在類似的研究中得到同樣的結果,通過進一步的研究發現DGKε是通過調節花生四烯醇肌醇脂質信號和突觸的長時程增強來參與癲癇易感性的發生過程。此外,Zhang等[19]研究顯示編碼DGKε的DGKE shRNA在果蠅亨廷頓病(HD)模型中的表達挽救了亨廷頓蛋白(Htt)毒性所致部分運動損傷,還在HD小鼠模型的紋狀體中發現DGKE mRNA表達水平較高(Htt過度表達)。這表明DGKε的活性增強在HD發病過程中也起一定作用,可能與Htt N端的多聚谷氨酸擴張導致紋狀體和皮層神經元大量丟失有關。
4 Ⅳ型DGKs
4.1 DGKζ DGKζ也是在中樞神經系統中研究最深入的DGKs亞型之一,在小腦、海馬錐體細胞和齒狀顆粒細胞、嗅球以及致密大腦皮層中高表達。在神經元內,DGKζ通過其PDZ結構域與突觸后支架蛋白PSD-95相互作用,并在興奮性突觸中特異表達。DGKζ過表達可導致樹突棘數量顯著增多,而敲除后則樹突棘減少,這種效應主要依賴于DGKζ的催化活性和與PSD95的結合[20]。類似的研究顯示,DGKζ的過表達不僅可以通過影響前白蛋白(PA)水平,還能與Rac1、PAK1等相互作用或形成復合物來參與誘導N1E-115細胞的軸突生長[21]。在DGKZ(編碼蛋白為DGKζ)敲除小鼠的海馬切片中發現,CA1區神經元樹突棘密度顯著降低,Schaffer側支CA1區錐體突觸顯示出長時程增強(LTP)和長時程抑制(LTD)作用減弱,提示DGKζ在神經元突觸可塑性中的重要作用[22]。行為學觀察顯示,經海人酸誘導的DGKZ 敲除癲癇小鼠模型相比于野生型小鼠表現出嚴重的驚厥發作和海馬神經元細胞死亡,表明DGKζ同前述部分DGKs亞型一樣與癲癇易感性有關[23]。另一方面,最近在非神經元細胞中也檢測到DGKζ的免疫反應。最新研究顯示,DGKζ在人膠質母細胞瘤的增殖和致瘤性中起至關重要的作用,膠質母細胞瘤組織中DGKζ的mRNA和蛋白水平均顯著高于癌前病變,進一步通過慢病毒shRNA干擾DGKζ后發現膠質母細胞瘤細胞的增殖速度減慢并誘導細胞G0/G1期停滯。這表明DGKζ可能通過調節細胞周期影響細胞增殖,從而參與膠質母細胞瘤的形成過程,提示DGKζ可能作為惡性膠質母細胞瘤治療的潛在靶點[24]。
4.2 DGKι DGKι因其羧基末端含有4個類似于DGKζ的錨蛋白重復序列,因此與DGKζ同歸為Ⅳ型DGKs亞型。Ito等[25]通過Northern免疫印跡分析其在腦組織中的分布及mRNA定位時發現,在所檢測的11個組織中,僅在大腦和眼組織中檢測到其mRNA表達,提示DGKι可能具有某些神經元特異性功能。通過原位雜交分析DGKι在成年大鼠腦中的mRNA定位,發現其在小腦皮質、嗅球和嗅結節、海馬神經元層高表達,與先前通過區域性Northern免疫印跡分析檢測到的人腦表達模式大致相同。此外,在小直徑背根神經節(DRG)神經元中也發現了DGKι高表達,該處神經元主要處理瘙癢和疼痛刺激;而且,DGKι敲除小鼠顯示對組胺的敏感性增加,表明DGKι參與調節對組胺的感覺和行為反應[26]。DGKι敲除鼠模型的研究顯示,海馬神經元中突觸前釋放概率增加,而突觸后代謝型谷氨酸受體依賴性長時程抑制(mGluR LTD)作用減弱,提示DGKι的突觸前定位以及DAG信號的突觸前改變影響突觸后的機制;進一步的行為學分析表明,DGKι敲除鼠適應新環境需要的時間更長,但運動活動、焦慮行為或空間學習和記憶方面無明顯變化[27]。另一項研究則顯示,DGKι在與DGKβ的協同作用下共同參與調節小鼠的躁狂和焦慮行為,因為在DGKι和DGKβ雙敲除小鼠中觀察到了明顯的焦慮和躁狂表型,而這在上述兩者任何單一的敲除小鼠中均未觀察到[28]。
5 Ⅴ型DGKs(DGKθ)
DGKθ在發育早期的大腦中表達顯著,并一直持續到成年,提示其可能參與大腦發育。進一步對小鼠胚胎發育過程中不同腦區的定位表達研究發現,DGKθ在海馬和小腦皮質中呈高表達,嗅球和腦干核呈中度表達,并且主要定位于突觸前和突觸后的興奮性神經元,在膠質細胞中的表達量極低[29]。DGKθ敲除小鼠或shRNA干擾DGKθ的小鼠神經元與野生小鼠相比,神經元經過刺激后的突觸小泡內吞速率顯著增加,且隨著刺激程度的增加內吞速率進一步增加,該效應可以通過野生DGKθ恢復,突出其在神經元刺激中的重要作用[30]。據此,Barber等[4]提出DGKθ可能參與突觸后AMPA受體內吞速率的調節,這為認識神經突觸可塑性的調節提供了一個新方向。此外,如前所述DGKθ在強烈的神經元刺激中發揮重要作用,那么在神經元刺激的病理生理條件下如癲癇疾病模型中研究其特異性抑制劑將是一個潛在的治療靶點,但這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證實。
綜上所述,目前已知的10種哺乳動物DGKs亞型有8種均在中樞神經系統中表達且顯著高于其他器官中的表達水平,這些同工酶在結構域上具有共同保守的催化結構域使其能共同參與調節細胞內DAG和PA水平的平衡,在神經系統中與細胞周期的調節、神經元形態發育以及突觸可塑性等密切相關。此外,因其蛋白調控結構域的不同決定了其在神經系統中具有不同時空區域與亞細胞定位的表達模式,并與特定神經精神疾病相關,如DGKβ與BD和癲癇易感性、DGKδ與癲癇、DGKη與BD、DGKε與癲癇易感性和HD、DGKζ與癲癇易感性和惡性膠質母細胞瘤等。這些研究結果均提示,DGKs在神經系統中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隨著近年來對DGKs的重視與研究深入,其有望成為神經系統某些疾病的治療靶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