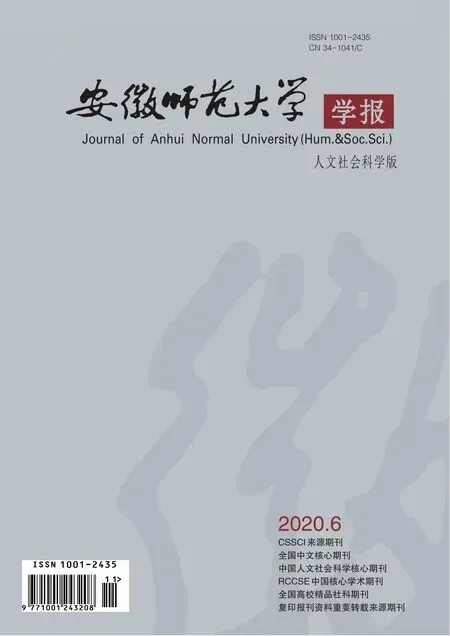從蕭齊宗室之爭考察劉勰之丕植優劣論*
周興陸
(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100871)
曹丕與曹植的兄弟恩怨、才性高下,為世人所津津樂道,是政治史和文學史上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總體上看,揚植抑丕者多,褒丕貶植者少。劉勰《文心雕龍》對曹氏兄弟多有評論,特別是《才略》篇尤為詳細。劉勰說:“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于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懵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為篤論也。”[1]700《才略》篇以1423 字簡要品評98 位文人的文才識略,竟花費90 個字來辨析曹氏兄弟,而且采用的是辯駁口氣,可謂是具深心,有用意的。
劉勰論文學,“同之與異,不屑古今”[1]727,富有獨立不倚的精神,因此不滿于“雷同一響”;他所持的是大文學觀,把《典論》之類子書也納入范圍,不同于他人僅僅就詩賦衡量曹丕、曹植的高下。但這還不足以徹底解釋為什么劉勰如此嚴正地批駁“舊談”“俗情”而對曹氏兄弟作出新的評判。劉勰的深心用意,還需要作一番剖白。
一、曹氏兄弟恩怨的“舊談”建構
劉勰所謂的“俗情抑揚,雷同一響”,是指此前長期存在的揚植抑丕論,而這種抑揚是建立在關于曹丕、曹植為世子立嗣問題產生恩怨的“舊談”上的。歷史上是否真的發生過曹丕和曹植為立嗣世子而發生的爭斗?這且不論,從文獻記述上看,在劉勰之前,曹氏兄弟的恩怨是“箭垛式”的被建構出來的。
早在三國鼎立時期,魏、吳之間爆發了激烈的輿論戰,相互誣蔑,“污名化”對方的國君。像《三國志·吳書·孫晧傳》載孫晧燒鋸斷陳聲頭等事,應該是敵方過甚其辭的誣蔑,很難說是歷史真實。《曹瞞傳》出自吳人之手,此書雖佚,但是書名就是對曹操的誣蔑,殘存的片段多是給曹操的身世和人品編排一些猥瑣的故事,奠定了曹操在后世“奸詐”形象的基礎。
較早記載曹操立嗣問題的史書,是魏末晉初魚豢的《魏略》。此書今雖不存,但裴松之注《三國志》多有摘引。試看《魏略》這幾則:
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有高元呂者,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乃不可言。”問壽幾何,元呂曰:“其壽,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也。”后無幾而立為王太子。至年四十而薨。(《三國志·魏書·文帝紀》注引)[2]57
(曹)彰至,謂臨菑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三國志·魏書·任城威王彰傳》注引)[2]557
太子嗣立,既葬,遣彰之國。始彰自以先王見任有功,冀因此遂見授用,而聞當隨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同上)[2]557
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著關東,單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清河長公主,欲因主謝。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為自殺也,對帝泣。會植科頭負锧,徒跣詣闕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為不樂。詔乃聽復王服。(《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注引)[2]564
從這幾則傳記可以看出,曹操的確在立太子問題上猶豫不決;曹丕也一度為此緊張和不安;曹彰性格急躁,義憤于顏;曹植沒有爭奪立嗣的意圖,為此前的任性而悔過不安,文帝待之嚴苛。但魚豢《魏略》沒有涉及曹丕與曹植為立嗣直接爭斗的情形。
魚豢撰《魏略》,動筆于魏末,成書于晉初[5]16-23。他是站在司馬氏的立場上來寫曹魏歷史的,如他詳細地記述太祖如何納何晏之母,收養何晏,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2]292等等,明人陳絳就說:“此《魏略》用司馬家誣說耳,豈信史乎!”①陳絳《金罍子》,明萬歷34年刻本,中編卷五,第10a頁。意謂這是魚豢站在司馬集團的立場上對曹魏君主的誣陷。就是這樣一部對曹魏沒有好感的史書,也沒有渲染曹丕與曹植的王位之爭。
比魚豢撰《魏略》稍晚,陳壽在西晉滅吳的280 年后鳩合魏、吳、蜀三書成《三國志》,其中也屢屢提及曹操為立太子事的躊躇,如:
(曹)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并為之說,故遂定為嗣。(《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2]557
時未立太子,臨淄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于外。(《三國志·魏書·崔琰傳》)[2]368
時太子未定,而臨淄侯植有寵。(《三國志·魏書·毛玠傳》)[2]375
是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淄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三國志·魏書·賈詡傳》)[2]331
陳壽的這些記述,強調曹植有才,受到曹操的寵愛,差點兒被立為太子,曹植和曹丕兩邊都各有黨與。曹植任性妄動,而曹丕矯情自飾,善于謀劃,結果立定了曹丕為太子。陳壽還記述了曹植的怨望之情,特別是在《文帝紀》末評曰:“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2]89既稱贊曹丕近乎古之賢主,又遺憾他氣度褊狹,待諸弟無誠愛之德。
陳壽和魚豢的記述,恐怕不是空穴來風。亂世里,在立嗣的問題上立長還是立才?往往是諸侯們格外費神的事。傳統的禮制是立長,但亂世更需要有才干的君主起來創立基業。當時袁紹、劉表、孫權都在立嗣的問題上反復猶豫過,曹操在曹丕、曹植之間舉棋不定,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另一方面,魚豢《魏略》定稿于晉初,陳壽撰成《三國志》在晉初太康年間。西晉初年的司馬皇室遇到了與曹魏當年一樣的問題。早在司馬昭掌握曹魏實權的魏末,就為司馬炎和司馬攸誰立為世子的事費盡腦汁。司馬炎代魏建晉即位后,對弟弟齊王司馬攸處處防范,即使知道太子“不慧”,也不忍心廢掉。結果齊王司馬攸被排擠出朝,在外發病而死。晉初司馬氏在立嗣問題上的猶疑,是陳壽和魚豢記述三國歷史時關注立嗣之爭的現實語境,甚至可以說他們記述三國時曹操、孫權等在立嗣上的教訓,暗含警示晉文帝或晉武帝以及朝臣殷鑒不遠的用意。魚豢曾說:“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于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2]577這話與其說是在責怪曹操,不如說是講給晉文帝司馬昭聽的。《三國志》的一些記載,裴松之就曾說是“存錄以為鑒戒”[2]1235。甚至我們可以大膽地類比,晉武帝司馬炎、齊王司馬攸、晉惠帝司馬衷三人之間的關系,不就是曹丕、曹植和魏明帝之間關系的翻版嗎?如果說司馬氏代魏是曹魏代漢的重演的話,未嘗不可說司馬皇室的立嗣問題是曹氏宗室立嗣問題的重演。
但陳壽只點出了曹植的任性和文帝的機謀,兄弟之間存在“攜隙”,并沒有記述曹植和曹丕之間發生沖突。隨著晉武帝去世,晉惠帝繼位,晉皇室的矛盾從爭奪立嗣轉為宗室向皇權發難。參加“八王之亂”的,除了晉惠帝的叔伯外,還有親弟楚王司馬瑋、長沙王司馬乂和從弟齊王司馬冏,兄弟之爭成為皇室內的嚴重問題。相應地,對曹魏歷史的敘事,重心也就從曹操立嗣的猶豫轉向了曹丕、曹植兄弟之間的斗爭。陳壽只說曹丕“御之有術”,從西晉郭頒開始,就敷衍出了各種機詐謀略。郭頒《世語》載:
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淄侯植并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吳質耳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2]609
這就正面描寫了曹丕與曹植之間的勾心斗角。裴松之批評郭頒《魏晉世語》“蹇乏全無宮商,最為鄙劣,以時有異事,故頗行于世”,或許就是指這一類的記載。東晉孫盛《魏氏春秋》載:
植將行,太子飲焉,逼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三國志·陳思王植傳》注引)[2]561
王指魏王曹操。這里就把曹操對曹植的疏遠歸咎于曹丕的故意陷害。到了宋初劉義慶撰《世說新語》,進一步衍生為曹丕有意要置弟曹植于死地。《尤悔》第一則:
敘述曹丕用藥棗毒殺了任城王曹彰,又想毒殺曹植事。最著名的“七步詩”故事,就首先見載于《世說新語·文學》,故事一方面是表彰曹植才思敏捷,另一方面揭露了曹丕對兄弟的狠毒。《世說新語》對曹操、曹丕竭盡揶揄諷刺之能事。《賢媛》第4則載: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直侍并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嘆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3]669
這是《世說新語》最為辛辣的一則,以其母親的口吻把曹丕的人品貶至豬狗不如。《惑溺》第一則載曹丕破袁紹鄴城得甄后事: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為奴。”
這個故事,《魏略》和《世語》都有記載,但只是描寫曹丕如何欣賞甄氏的美貌而納之;《世說新語·惑溺》的記載竟然轉化為曹操、曹丕父子之間爭搶甄氏。可能因為這種改編過于不倫,后來再衍化為“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廢寢與食”[6]895云云,變成曹植、曹丕與甄后之間的三角戀愛,并以《洛神賦》相比附。
《世說新語》關于曹魏皇室的記載,多是“小說家言”,有的是根據前代史書的記載而大加發揮;更多的則完全缺乏歷史根據。那么劉義慶組織文士編撰《世說新語》為什么要如此誣蔑、作踐曹操、曹丕父子呢?這可從兩方面解釋,一方面,南朝宋武帝劉裕自稱是西漢楚元王劉交之后,自然對竊取劉漢江山的曹魏沒有好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劉裕建立宋政權后,苛刻地對待劉宋宗室,嚴加防范;特別是宋文帝劉義隆的猜忌,使諸王和大臣都懷有戒心,惴惴不能自保。[7]55-64劉義慶撰《世說新語》借敘寫曹丕對兄弟的猜忌和惡毒來隱射他對宋文帝的不滿。
從《魏略》到《世說新語》,我們可以清晰地梳理出曹丕、曹植兄弟的恩怨是如何被建構起來的。曹操在立嗣問題上猶豫不決,曹丕為捍衛世子位置而花費心思,應該是史實;至于毒棗事件、七步詩、乃至曹植與甄妃的不倫之戀等等“舊談”,不過是小說家言,是后世文士從當下現實處境出發對歷史事件的某一方面的強化和夸張。時代越久,細節越生動,離歷史真相就越遠。這正如劉勰《文心雕龍·史傳》所言,“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于是棄同即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1]287在同一篇里,劉勰就批評魚豢《魏略》、孫盛《魏氏春秋》等雜史“或激抗難征,或疏闊寡要”,魚豢、孫盛、劉義慶等對曹丕、曹植等的記載,大約可當此批評。
在曹丕、曹植沖突的建構中,人們的褒貶愈益分明,往往是出于同情弱者的心理,為有才不獲馳騁的文士鳴不平,曹丕的文才遭到貶抑,曹植任性和才氣得到夸張和提升,所謂“八斗才”“七步之才”“才若東阿”在南北朝時成為文才穎異的代名詞。這都應了劉勰所謂“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的俗情。
二、蕭齊宗室爭斗是劉勰重評丕植的現實考量
曹丕曹植優劣論,體現出人們同情弱者這一普遍的“俗情”,這是由來已久的“舊談”。劉勰為什么要花費筆墨來對此加以辯駁呢?除了劉勰“同之與異,不屑古今”的獨立的文學批評精神外,還有他的現實考量。這需要聯系宋齊,特別是齊代的宗室爭斗情況來加以推測。
劉宋、蕭齊都是素族豪強憑借其武功而取得政權,劉宋宗室成員多不讀書,粗野鄙陋,如《宋書·劉道憐傳》謂其“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施為,多諸鄙拙”[8]1462,出身低微,生性鄙拙,而貪婪無度,動生釁端,覬覦皇位,多不臣之心。因此,宋齊帝王對宗室藩邸管教尤為嚴格,齊武帝時,“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只能看孝子圖而已”[9]1088,不得習學弓箭騎馬,并設有典簽給予嚴密監視。宋齊之典簽,近乎曹魏時期曹植、曹彰等人身邊的監國使者。即便如此,也不能消泯宗室的猜忌之心。兄弟之爭,叔侄相斗,宗王叛亂,骨肉相殘的鬧劇,劉宋和蕭齊的皇室一再上演,特別是劉宋孝武帝時期的大肆殺戮和蕭齊明帝對武帝子孫的屠滅,最終導致了兩個朝代的衰落,可以說劉宋和蕭齊不是敗給對手,而是宗王內斗,自取滅亡。清人汪中《補宋書宗室世系表序》統計,劉宋六十年中,皇族129人,被殺者121 人,其中骨肉自相屠害者80 人。羅振玉《補宋書宗室世系表》更詳細地統計,皇族158人,子殺父者1 人,臣殺君者4 人,骨肉相殘殺者103人,被殺于他人者4 人,夭折者36 人,無子國除及出奔者34 人,其令終者3 人,其令終與否不可知者2人。[10]劉盼遂統計,蕭齊七世24年,其本支人物之可考見者,約得100 人,而被誅夷者57人。[10]從整個中國歷史來說,劉宋和蕭齊是皇室骨肉相殘最為殘酷的朝代,其國祚之不長,原因也正在此。劉勰約生于劉宋前廢帝永光元年(465),《文心雕龍》約作于蕭齊和帝中興元年(501)。這30 余年時光,他耳濡目染了宋明帝劉彧瘋狂屠戮宗室、蕭齊代宋、齊武帝與蕭嶷的斗爭、齊明帝對武帝子侄的屠殺。現實中的皇室政治斗爭不能不影響到他對歷史上的宗王問題的關注和認識。
蕭道成趁劉宋皇室無人而奪取其江山建立南齊朝,因此在臨終時告誡武帝:“宋氏若骨肉不相圖,它族豈得乘其弊?汝深戒之。”[9]1080但是他自己埋下了宗室相斗的隱患。建元年間“世祖(武帝蕭賾)以事失旨,太祖(高帝蕭道成)頗有代嫡之意”;[4]409“豫章王(蕭)嶷素有寵,政以武帝長嫡,又南郡王兄弟并列,故武帝為太子,至是有改易之意”。[9]1170高帝蕭道成既立了蕭賾為太子,又寵愛次子豫章王蕭嶷,有改易之意,這不完全是在重復魏王曹操當年的錯誤嗎?結果導致了武帝蕭賾與豫章王蕭嶷兄弟之間為皇位繼承權的斗爭。[12]武帝對幾個弟弟時刻防范,不加親寵。蕭嶷“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4]414蕭晃少有武力,太祖蕭道成常曰:“此我家任城也。”[4]624就把他比作曹操之子曹彰,但得不到武帝的親寵。蕭曄有非常之相,“執心疏婞,偏不知悔”[9]1082,武帝對他頗有忌諱,故無寵愛,未予重任,蕭曄曾抱怨說:“陛下愛其羽毛,而疏其骨肉。”[9]1081武帝不悅。武帝對蕭晃、蕭曄諸弟都未加重用,“當時論者,以武帝優于魏文,減于漢明”[9]1080。指齊武帝蕭賾對待諸弟既不像曹丕對待曹植、曹彰那樣刻薄,也不如漢明帝那樣愛護多次造反的弟弟劉荊。蕭子顯在《南齊書·齊高帝諸子傳》后“論曰”中特別引了曹植《表》所謂“權之所存,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的感慨,并肯定說:“曹植之言,遠有致矣!”[4]1093可見當時人在議論皇室時就已拿漢魏作比較,那么劉勰評論曹魏宗室時含有對現實政治的考量,也是合乎情理的推斷。
齊武帝對兄弟寡恩,已導致宗王離心離德。特別是他臨死前,走了一步敗棋,直接引起蕭齊皇室大亂。當時文惠太子早薨,武帝臨崩前,眾論物議,以為當立次子蕭子良。寧朔將軍王融就想到要矯詔擁立蕭子良即位。從當時的政治格局上說,要想鎮住諸宗王和名士大姓,的確需要一位年長成熟的繼位者。正如當時袁彖所說:“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盡,命之所馀,政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安四海。王融雖為身計,實安社稷,恨其不能斷事,以至于此。”[9]1105結果沒想到武帝遺詔將皇位傳給了剛弱冠的皇太孫郁林王蕭昭業,讓蕭子良輔政。而蕭子良素來仁厚,不樂時務,又將輔政實權讓給了武帝的從弟蕭鸞,于是大權旁落。蕭鸞貪狠殘暴,連續廢掉郁林王蕭昭業、海陵王蕭昭文,自己稱帝,即齊明帝。他一登基,就于建武初(494、495)大肆殺戮高帝、武帝的子孫。“自建武以來,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9]1105,皇室成員人人惶惶不可終日。而“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4]749,導致宗王叛亂此起彼伏。至明帝臨崩的永泰元年(498),他又擔心“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再次大開殺戒,將高帝、武帝和文惠太子的子孫殺戮殆盡,蕭齊的根本也就動搖了。明帝駕崩時,年長的兒子蕭寶卷、蕭寶融才十余歲。于是,宗室之爭再次興起。東昏侯蕭寶卷在位時,三弟蕭寶玄“恨望有異計”,參與崔慧景的叛亂,兵敗被殺,蕭齊皇室已虛弱且混亂至極。結果梁武帝乘虛而入,取代了蕭齊。宗王之爭像解除不開的符咒一樣,蕭齊犯了與劉宋一樣的錯誤,落得與劉宋一樣的下場。
蕭齊政權的短暫收場,就歸因于宗室的內亂。朝廷是權力斗爭場,人人覬覦權杖,都想稱帝,必然導致兄弟叔侄之間骨肉疏離,甚至自相殘殺。從個人立場看,世道艱難,政治險惡,逞才使氣容易招致禍端。如齊武帝五弟蕭曄,擅長詩文,執心疏婞,偏不知悔。武帝臨崩,大行在殯時,竟然于眾中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立太孫。”[9]1083結果于隆昌元年不明不白地死去,年僅28 歲。齊武帝第八子蕭子隆,性和美,有文才,娶尚書令王儉女為妃。武帝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就把蕭子隆比作東阿王曹植。“明帝輔政,謀害諸王,武帝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鏘同夜先見殺”。[9]1113史書載齊高帝凡十九子,唯有蕭軒“以才弱年幼”得全,但明帝臨死之前還是把他毒死了,以防后患。蕭齊宗室與劉宋宗室相比,更飽學擅文,有才華,但以才貌招致禍端的慘案比比皆是。武帝之弟蕭鏘“性謙慎,好文章”,曾與蕭子隆計劃廢掉蕭鸞,結果被明帝蕭鸞殺害。另一弟蕭鋒善書法,能文章,時鼎業潛移,蕭鋒獨慨然有匡復之意,也遭明帝毒手。這些血的教訓,不能不影響到劉勰,而提出對宗室成員逞才任氣的警戒。曹植與上列諸人一樣,既是文士,更是宗王。像曹植那樣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便是引頸承戈,自取滅亡。
整個蕭齊的皇室中,唯有蕭嶷一支保存完好。蕭嶷是高帝蕭道成次子,輔佐父兄代宋建齊,建立功勛。兄長蕭賾繼位后,蕭嶷“常慮盛滿”[4]413,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蕭嶷常警戒諸子曰:“凡富貴少不驕奢,以約失之者鮮矣。漢世以來,侯王子弟,以驕恣之故,大者滅身喪族,小者削奪邑地,可不戒哉!”[4]1065臨終時,召子蕭子廉、蕭子恪曰:“吾無后,當共相勉勵,篤睦為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富貧,此自然理,無足以相陵侮。勤學行,守基業,修閨庭,尚閑素,如此足無憂患。”[9]1066蕭嶷在齊皇室中的處境非常近似于曹丕登基后的曹植。而且當時人也是這么看待的。梁武帝取代蕭齊后,對蕭嶷的兒子蕭子恪說:“曹志親是魏武帝孫,陳思之子,事晉武能為晉室忠臣。此即卿事例。”[13]509曹志是曹植次子,蕭子恪是蕭嶷次子,梁武帝不正是把蕭嶷比作曹植了嗎?蕭嶷飽讀詩書,靜默退素,以文史傳家,十六個兒子都全身入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云、子暉。子恪亦涉學,頗屬文”[13]509。其中蕭子顯還撰著了《南齊書》。尚文而謙退,是蕭嶷一支的門風,為宗王在亂世中的行為舉止樹立了典范。劉勰在論曹丕曹植時,有意地矯正過去揚植抑丕的“舊談”,對曹植任性使氣、憑文才盛滿而有競心加以貶抑,實際上就是為當時的宗室子弟標尚一種謙退收斂的處世態度,畢竟曹植身份是宗王,而非一般的文人。劉義慶撰著《世說新語》采取揚植抑丕的態度,是因為他的身份也是宗王,與曹植的立場和處境近似,借揚曹植以吐氣。劉勰撰《文心雕龍》,則著眼于對政局的關注和擔憂,借重新評價曹植兄弟,以在蕭齊的政治格局中抑制宗王的任性狂悖。這不論對宗王的全身遠害,還是朝政的和諧穩定,都是不無意義的。正是有這一層現實的考量,劉勰才一反傳統的“揚植抑丕”論,對曹植顯有微辭。
三、結 語
在《文心雕龍》的文體論各篇中,劉勰“揚丕抑植”的立場都是比較明顯的。如《明詩》篇曰:“暨建安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1]66把曹丕列在曹植之前。其實,就五言詩來說,曹丕的成績不足以與曹植并列。《誄碑》篇論誄體曰:“陳思叨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末,旨言自陳,其乖甚矣。”[1]213《封禪》篇曰:“陳思《魏德》,假論客主,問答迂緩,且已千言,勞深勣寡,飆焰缺焉。”[1]394《雜文》篇曰:“陳思《客問》,辭高而理疏。”[1]255《論說》篇曰:“曹植《辨道》,體同書抄。言不持正,論如其已。”[1]328曹植不善持論,《辨道論》比不上曹丕“辨要”的《典論》。但曹植之上表,獨冠群才,詩體四言與五言兼善,這二體的成績是曹丕不可比擬的。兄弟二人在文體上“迭用短長”,各有偏擅。這與稍后鐘嶸《詩品》專論五言詩把曹植置于上品,曹丕置于中品,顯有不同。
如前所論,劉勰“揚丕抑植”,不只是對歷史上的曹丕、曹植作出高下之分,還體現出他對當時蕭齊宗王內亂政局的關注和擔憂,暗含的用意是,有文才的宗王在亂世中應收斂個性,明哲保身,維護朝政的穩定。這里表現出劉勰論文的淑世情懷。“淑世情懷”在《文心雕龍》里隨處可見。如劉勰對近世文風的批評,《程器》篇強調文士“達于政事”的實際才干;《史傳》篇感嘆“勛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的不合理,無不具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又《史傳》篇曰:“及孝惠委機,呂后攝政,班史立紀,違經失實。何則?庖犧以來,未聞女帝者也。漢運所值,難為后法。牝雞無晨,武王首誓;婦無與國,齊桓著盟;宣后亂秦,呂氏危漢,豈唯政事難假,亦名號宜慎矣。”[1]285而劉勰撰著《文心雕龍》 時正是“宣德太后臨朝,入居內殿”。[4]《和帝本紀》114如果聯系這一政治格局來看,他用70 余字議論“婦無與國”的事,就不是無的放矢的。這些居今論古、借古指今的地方,劉勰說得不太直白,后世研究還不夠充分,有待發覆,須要聯系當時的歷史作出合理的推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