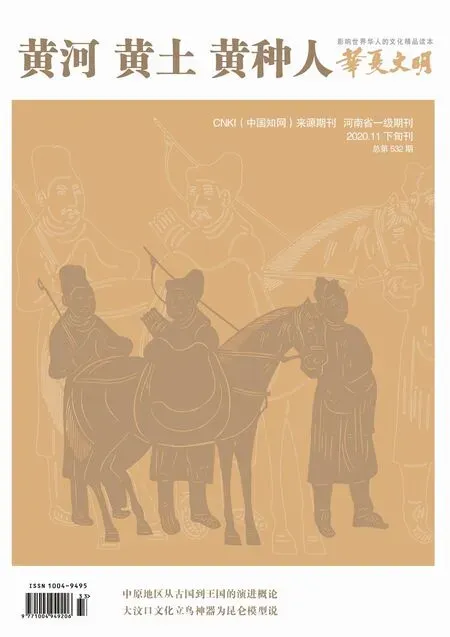裴李崗、后李文化生業經濟模式比較研究
□陶治強
一、概述
“生業”一詞,較早出現在西漢晁錯的《守邊勸農疏》,文曰:“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后漢書·光武帝紀下》:“徙其魁帥于它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后漢書·循吏傳·仇覽》:“(仇覽) 選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于果菜為限,雞豕有數。”“生業”有產業、資財和從事某種產業的多重語義, 本文中指人賴以生存的職業,包括漁業、狩獵、采集和農業等。
生業經濟,有學者稱經濟生業,“指的是在特定環境中,人們以何種手段來進行生產、分配與交換,以獲得生存資源”[1]。“廣義的生業經濟,指人類資源生產的不同手段和謀生方式,例如采集、狩獵、漁業、畜牧、農業等社會生產活動,涉及人類的衣食住行等諸多方面。 ”[2]6史前生業經濟的研究離不開古聚落出土的豐富文化遺存,包括動植物遺存和生產工具等。 史前生業考古是獲取珍貴資料的重要手段,也是當前考古界十分重視的重點研究的內容。 生業經濟是史前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也是先民生業方式、經濟模式、地區差異和社會文明進化程度的集中反映。
二、兩地文化生業遺存的發現與意義
裴李崗文化,是我國黃河中游地區的早期新石器文化。 1977 年,河南新鄭裴李崗遺址發現以后,又在新鄭沙窩李、新密、登封等多地發現了此類型的古文物點160 多處。 這類遺址多分布在山前洪積扇區或淺山區的河旁階地上,有著共同的文化面貌。 裴李崗文化距今9000—7000 年,處于以原始農業、手工業為主, 以家畜飼養和漁獵業為輔的母系氏族社會。 裴李崗文化的分布范圍,以新鄭為中心,東至河南東部,西至河南西部,南至大別山,北至太行山,它與同時期的河北磁山文化和陜西老官臺文化相比,處于領先地位。
裴李崗文化居民住著單間、雙開間、三開間或四開間的方形或圓形茅屋,均是半地穴式。 男人們耕田、打獵、捕魚;女人們加工糧食、飼養畜禽,還帶著孩子在家里用鼎之類的陶器在灶上做飯,用陶紡輪和骨針等制作苧麻一類的衣服。 當時人們居住的房子面積小,房基內發現有圓形燒火面或箕形灶塘。有公共墓地,墓穴排列有序,流行單人葬。 男性和女性葬俗有所不同。 出土有陶碗、缽、雙耳壺、圈足壺、三足壺、三足缽、深腹罐、鼎、盤、盆、勺;石磨盤、石磨棒、石鏟、石斧和石鐮,石器以磨制為主,少量打制石器,典型器類有帶足石磨盤、帶齒石鐮和雙弧刃石鏟。 裴李崗文化的發現和認識, 為史前農業、 陶器文化、手工業生產、建筑、文字、音樂、家畜飼養史等的研究,提供了豐富而珍貴的文物資料。從聚落內建筑布局、墓葬習俗、農業生產和陶器的形制、紋飾來看,裴李崗文化后期發展演化為仰韶文化后岡類型,裴李崗文化與河北的磁山文化關系較為密切。
裴李崗文化的發現填補了我國仰韶文化以前新石器時代早期的一段歷史空白。
后李文化,絕對年代為距今9000—7300年。 同一文化的古遺址50 多處,科學發掘的遺址有14 處之多, 它是黃河下游山東地區發現的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遺存。 房址有橢圓形和圓形, 半地穴和淺穴式結構,多見柱洞,地面建筑少見。 門向東和東偏南,面積一般在5~10 平方米。有壕溝,流行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墓穴排列整齊。 陶器有泥質和夾砂陶,陶色呈黃褐色,手制。 器物有釜形鼎、紅頂缽、三足缽、小口雙耳罐、三足罐、碗、器蓋、支座等,多素面,后李遺址內發現有陶窯,陶器就地燒造。 石器有打制和磨制兩種。 打制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盤狀器等,磨制石器有斧、鏟、刀、鐮、磨盤、磨棒等。何德亮通過對后李文化遺存中孢粉、 動物、硅酸體的鑒定分析, 發現了禾本科植物花粉,形態近似現代的谷子(粟)。 他依據提取的自然環境信息,判斷后李時期先民可能學會農業栽培, 食物來源主要靠谷物種植,輔以狩獵和捕魚[3]。經鑒定,前埠下遺址動物遺骸有麗蚌、青魚、草魚、雞、狗、家豬、野豬、鹿、水牛等。 前埠下一帶為大河入海處的森林—草甸環境,野生動植物資源比現在豐富得多,年平均氣溫可能比現在高出4℃~5℃,大致與福建一帶的氣候類似。 后李文化小荊山遺址發現了717 件動物遺骸, 有家豬、家犬,還有狼、狐等野獸和雉、蚌類。 從家豬遺骨看,屬于較原始類型或半馴化類型。 山東大學靳桂云認為,后李文化的先民已過上了定居的生活,生業經濟模式具有由采集漁獵向穩定的農業經濟發展轉變的特點。 后李文化先民的食物獲取方式是多樣的, 有捕撈、狩獵、采集,還有初級的食物生產活動,可能出現了人工栽培水稻和粟(黍)[4]。 在后李文化的山東長清月莊和章丘西河遺址發現了稻作遺存。 多處稻作遺存的出現正在改變以往學術界認為的全新世以來長江流域是野生稻的分布范圍,也正在動搖稻作起源和最初發展于長江流域, 距今7000 年左右才傳到黃河流域的觀點。 后李文化稻作遺存的發現,打破了學界的思維定式,將以全新的視角和全面的考量,重新認識全新世東亞地區稻屬植物資源利用、稻的初期栽培以及稻作農業起源問題。
三、中國粟和稻作農業的出現與研究回顧
中國是世界上粟的起源地、栽培粟最早的國家之一。 原始社會粟的馴化種植來之不易。 原始先民在長期的采集過程中發現植物的果實, 種子落地又重新發芽生長的規律,逐步學會了農作物的栽培種植, 改變了采集、狩獵索取性食物模式,在經濟活動中更具主動性和創新性。 無論是動物還是植物,都要在人類的干涉之下發生基因和表型特征突變,達到馴化的程度,進而提高產量,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比如小麥和水稻的馴化需要1000 年至2000 年的時間才能具有顯著的馴化特征[5]。 1987 年,考古人員在河北南莊頭遺址發現了陶器、石磨盤、石磨棒,家畜豬及狗的骨骼,植物種子。 衛斯據石磨盤、石磨棒,家畜飼養和農作物之間的關系認定中國北方農業在1 萬年前已經發生[6]。 山西吉縣的舊石器晚期的柿子灘遺址,距今2 萬至1 萬年間,遺址出土的2 個石磨盤和2 個石磨棒的微痕分析和淀粉粒分析結果表明,柿子灘居民是 “最后的采集狩獵者之一,他們采集野生植物并最終馴化了粟”[2]22-23。
黃河上游地區的陜西寶雞關桃園遺址,出土了許多用牛或鹿的肩胛骨制成的骨耜。這些骨耜都埋在灰坑里,形狀大同小異。 與骨耜一起出土的還有石斧、石碾盤、刮削器、骨鏟、骨錐等生產工具。 骨耜的發現說明在距今7000 多年的我國西北旱作農業區域內出現了與長江流域河姆渡文化相似的耜耕農業,在當時已經是先進的農耕方式。
學界比較贊同粟是狗尾草馴化來的,北方人稱這種作物為谷子、小米,它耐旱喜溫,春種秋收,在干旱土壤中亦能正常生長,產量高。 新中國成立后,在12 個省區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和墓葬中發現不少粟的痕跡[7],有學者統計目前考古發現有60 處左右粟的遺存[8]。粟作遺存分布區域遍及整個黃河流域。 1931年,在山西荊村瓦渣斜遺址出土的“粟稷和高粱的遺存”,年代在公元前5000—前4000年,屬仰韶文化類型[9]。 1934 年,在陜西寶雞斗雞臺戴家溝史前遺址中,在一瓦鬲中發現谷子粒[9]。1954 年,西安半坡遺址出土一些陶罐和窖穴,里面遺留有谷類遺存,有的保存較好,經檢測為粟。 此外,還發現了芥菜或白菜的種子[10]。 在黃河中游的老官臺文化、裴李崗文化和磁山文化發現了新石器早期晚段的粟作物遺存。 磁山文化遺址自1976 年發掘以來, 發現了大量的黍和粟的文化遺存,“呂厚遠等人測定了磁山遺址六個窖穴中的相關遺存,發現了粟的植硅體,數量比黍少許多”[11]。 從年代上看,東北地區的內蒙古赤峰興隆溝和中原地區的磁山、裴李崗發現了我國最早的粟遺存。 在我國原始社會,粟的種植年代跨度大,空間分布廣泛,從最初的萌芽和形成,到逐步擴大種植規模,優化種子質量, 再到原始社會后期大面積耕種,走過了一條漫長的發展進化之路。 李根蟠等認為:“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的粟作農業處于由山地農業向低地農業的過渡時期,起源于山地,河南的嵩山地區有可能就是原始農業的發源地。 ”[12]世界上的印度和埃及,種植粟的歷史也十分久遠,經過生物學家測定后認為, 粟最早馴化和栽培于我國的黃河流域。吳梓林認為:“從中國多地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和墓葬出土古粟的地點分布情況看,有河北、山西、河南、陜西、甘肅、青海、新疆、江蘇、山東、遼寧、吉林、黑龍江等地都出土有古粟。 這些遺址和墓葬都出現在中溫帶、暖溫帶和亞熱帶的地域內,尤以暖溫帶分布最多。 西起新疆哈密,東到山東膠縣,南至河南淅川,北達黑龍江寧安,在這大約三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區域內都有粟的蹤跡。 中國廣大北方地區早在7300 年前,已經開始種粟,到距今五六千年時期,已廣泛種植了。 ”[7]
粟作物的成功種植,大大豐富了新石器時代先民的食物來源,呂厚遠利用植硅體和淀粉粒分析方法,證明了世界上第一碗面條是用粟類作物加工來的[11]。
稻作起源,嚴文明依據水稻首先在其野生祖本分布范圍的邊緣被栽培的事實,提出了“邊緣起源論”[13]。 他認為栽培稻最早發生在長江流域偏南的地方,位于這個區域的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稻作遺存,時間約在公元前一萬二三千年。 目前,考古界較為認同長江中下游地區是稻作農業起源的中心。 學術界對稻作農業起源的動力機制提出了“競爭宴享”“環境壓力”“共同進化理論”等觀點[2]2。
四、裴李崗、后李文化生業經濟的內容與特點
1.裴李崗文化生業經濟
生產工具:裴李崗文化時期的遺址出土了比較多的農業生產工具, 如有肩石鏟、骨耜、兩端舌形刃石鏟、橢圓形石斧、齒刃石鐮、四足或無足橢圓狀石磨盤、圓柱形石磨棒等。 在鄭州南陽寨、郟縣水泉等遺址發現加工谷物的工具石磨盤、石磨棒,在新鄭裴李崗、舞陽賈湖等多處遺址發現翻耕土地的石斧和石鏟,在新鄭裴李崗、新鄭沙窩李等遺址出土了農業收割工具齒刃石鐮。 賈湖遺址還出土了骨鏃和骨鏢,有人對這些工具進行了分期和統計分析, 認為賈湖遺址在前一、二期以狩獵、捕撈為主,種植為輔,在三期時農業種植取得快速發展,超過了狩獵和捕撈,成為人們食物的主要來源。
動物遺存:在舞陽賈湖遺址的廢棄窖穴和房基內,發現有眾多的動物骨骼,種類有家豬、野豬、狗、梅花鹿、四不像鹿、小麂、獐、貉、紫貂、狗獾、野兔、象、天鵝、環頸雉、丹頂鶴、青魚、草魚、鯉魚、揚子鱷、龜、鱉、蚌、螺、蜆、羊、黃牛、野兔、野貓等。 班村遺址:豬占到全部動物個體數量的59%,可提供肉食量的71.96%, 而以鹿類為主的野生動物數量僅占41%,顯示家豬已經成為肉食的主要來源[2]180-182。 瓦窯嘴遺址:豬、狗、牛、羊、鹿、兔、鼠、雞、鳥、蚌、螺、魚。 水泉遺址:豬、鹿、麂。沙窩李遺址:豬、鹿。莪溝北崗遺址:貓類、鹿類。 中山寨遺址:豬、鹿、楔蚌、榧螺。
植物遺存: 粟作物遺存在塢羅西坡、新鄭沙窩李遺址和許昌丁莊等遺址有發現,新鄭沙窩李遺址粟的炭化顆粒密集,分布面積為0.8~1.5 平方米。對1000 粒淀粉粒取樣測定后,可知新鄭裴李崗遺址,橡子占比46.3%,小麥族占比24.3%, 粟或黍或薏苡屬占比12.1%,根莖粒占比0.4%[5]。在賈湖遺址內發現紅燒土塊上有10 枚保存較好的稻殼印痕,經測定,為栽培水稻[14]。 舞陽賈湖遺址發現有未帶殼斗的櫟的半炭化果核。 經孢粉鑒定,知道賈湖遺址內木本植物有櫟屬、胡桃屬、粟屬、柳屬、楓香屬、山毛櫸屬等常綠闊葉樹種,松屬、鐵杉屬等常綠針葉樹種,草本灌林蒿屬、蓮屬、茜草科、水鱉等,蕨類、石松屬、水龍骨科、水蕨屬、環形藻類,還有野生大豆,禾本科植物種子馬唐屬、稗屬雜草、葡萄屬植物種子、構樹、苘麻等。 在塢羅西坡遺址浮選出2 粒粟和1 粒黍,在唐戶遺址發現黍和稻的植硅體[5]。 橡子在八里崗遺址、石固遺址、水泉遺址、莪溝北崗、裴李崗、賈湖都有發現,在植物遺存中占比最高。 此外,還有胡桃科、酸棗和梅子遺存。賈湖類型位于淮河流域, 這里氣候熱多雨,氣溫比現在高出2~3℃, 降雨量高出200~300mm,適宜水稻種植和生長。 賈湖先民種植水稻的歷史比長江流域的河姆渡早出1000 多年。 裴李崗類型位于黃河流域,屬暖溫帶氣候中的大陸東端,氣候特點是冬春缺水干旱,夏季雨水增多,粟的生長習性是耐旱,屬春播秋收,一年一茬,適合在黃河流域的自然氣候下播種。
生業經濟特點:裴李崗時期的先民種植作物不局限于粟,還有黍、小麥族、薏苡屬之類。唐戶遺址出現了黍、稻混作模式。裴李崗文化賈湖類型位于淮河支流沙潁河流域,氣候溫暖,雨水充沛,較早地種植了水稻。 裴李崗文化先民制作了翻土播種工具石鏟, 碾谷工具石磨盤和石磨棒,開墾工具石斧,收割工具石鐮,還有漁獵和紡織工具等。 石鏟發現最多,其次是石磨盤、石磨棒和石鐮,石斧、石鋤、石刀、石矛也有少量發現。 石器材質有較硬的石灰巖或砂巖, 石灰巖用于制作石鏟、石斧和石鐮, 而石磨盤和石磨棒多用砂巖。說明先人已能區分石頭的性能并因材而制。他們對生產工具的形制和使用方便性特別講究。 石磨盤和石磨棒成套出現,配套使用。石磨盤多帶有四個足,呈頭寬尾窄的細腰橢圓形, 石磨棒的長度都會大于石磨盤的寬度。 石鐮刃部打成了鋸齒狀,以增加摩擦力。石斧、石鏟刃部寬而上部窄,這樣便于嵌在木柄卯眼內。 “裴李崗文化的工具品類滿足了當時農業生產的需要,個別類型可能處于耜耕農業階段。”[5]裴李崗農業生產工具數量多,漁獵工具相對較少;“加工糧食工具的比重是加工肉食工具的9 倍左右”[15]。 棗、核桃、麻櫟等炭化果核的存在,說明農業經濟不是唯一的食物來源, 采集是必要的補充。這時期家豬飼養是裴李崗先民主要的肉食來源。
裴李崗時期的墓葬已初具制度化,有公共的墓葬區,與生活區是分開的。 隨葬品有固定的位置和數量的講究,說明人們已經對死亡和埋葬有了新的認識。 墓葬隨葬工具組合很有特點,男性墓隨葬生產工具而不隨葬糧食加工工具, 而女性墓隨葬糧食研磨工具。 隨葬品的不同反映了男女從事勞動種類有別。 有人根據女性墓葬中比男性墓葬多出一件三足缽,判斷當時社會處于母系氏族的繁榮階段,女性受到敬重。 男人負責干農活、打獵和制陶;女人生孩子、加工糧食和在家做飯。
賈湖遺址周圍可獵取的野生動物種類繁多,有水生、陸生和飛鳥等,捕食最多的是魚類和哺乳類。 豬、狗已經馴養,有的墓葬隨葬豬下頜骨,狗一般用于祭祀。 裴李崗時代的古人常狩獵、漁獵補充和改善飲食,魚和鹿類吃得較多。[16]
裴李崗文化圈內各地人們獲得肉類的食物途徑不同, 家畜和野生比例也不相同。“有人認為牛和羊也已經被馴化, 但根據考古材料可知,飼養的牛、羊都是在青銅時代遺址才發現的。 ”[5]
2.后李文化生業經濟
生產工具:后李文化中發現的石器有石斧、錘、研磨器、石刀、石磨盤、石磨棒、石鑿、石鐮、支座、錛、球。骨角蚌器多為鑿、匕、錐、鏢、刀、鐮等。 石磨盤中以無足磨盤居多。 磨棒的石料來自當地, 較多的磨盤雙面使用,以減少磨盤的損耗,延長使用壽命,足見磨盤加工制作難度大,來之不易。 王強認為月莊遺址的工具套并不完整,完整的工具套應該包括從事農業耕種、收割和加工的全部工具[17]14,如遺址中明顯缺少鏟、犁、刀、鐮等工具,骨角質地的也沒有。 月莊遺址石磨盤和石磨棒出土數量最多,共出土90 件,占全部石制品的66.6%,其中磨盤50 件,無足磨盤37 件,有足磨盤13 件,均為石英砂巖制品。石磨棒以石英砂巖為主, 也有少量的花崗巖、閃長石等。 月莊早期的人們使用的大多是無足磨盤, 后來覺得有足磨盤性能優越,就大量制作有足磨盤,但總體來說,有足磨盤也明顯少于無足磨盤,而在裴李崗文化和磁山文化中無足磨盤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從磨盤發展的歷程來看, 早期的磨盤是無足的,下川遺址和南莊頭遺址出土的磨盤都是無足的。
動物遺存:月莊遺址發現有陸生哺乳動物、爬行類和淡水魚類。 陸生動物有麋鹿、斑鹿、貓科、狗、牛、豬、小型鹿等,禽類有雉科,爬行類有鱉和龜,淡水魚類有草魚、鯉魚和青魚等。 哺乳類動物中野豬、牛和斑鹿比較多。 魚類骨骼中大多數嚙齒比較大。 小荊山遺址出土動物骨骸品種有五大類,分別是軟體動物、魚類、爬行類、鳥類和哺乳類。 軟體動物包括圓頂珠蚌、珠蚌、扭蚌、劍狀毛蚌、楔蚌、麗蚌、籃蜆。 魚類有青魚和草魚。 爬行類有鱉。 飛禽有雉。 哺乳動物有鹿、羊、牛、馬、野豬、家豬、狼、家犬、狐、貉。淡水軟體動物類比較多見,可見先民食用較多。 魚類也是居民主要的捕撈對象。 發現的十多個家豬的下頜骨較長,牙齒十分粗大,野性特征明顯,屬于向家豬過渡的半馴化或比較原始類型。 宋艷波對后李文化動物遺存研究后認為“家豬還具有明顯的野生性狀”[18]。 胡耀武等學者利用C、N 同位素, 得出后李文化中野豬利用數量要多于家豬[19]。 經鑒定,前埠下遺址動物遺骸有麗蚌、籃蜆、青魚、草魚、鲇魚、鱉、雞、中華鼢鼠、狗、狐、貉、狗獾、家豬、野豬、梅花鹿、水牛、虎、貓、獐等。 章丘西河遺址動物遺存:牛、麋鹿、斑鹿、小型鹿、豬、小型犬科、鳥等。 宋艷波認為:“西河遺址的豬可能已經被馴化了, 尚處在馴化的初期,在所有的豬遺骸中所占比例較小。 從哺乳動物的肉食量分析,野生動物為主,約占60%以上。 ”[20]歷城張馬屯遺址發現的動物遺存有斑鹿、狗、狗獾、龜、貉、狐、麋鹿、鳥、牛、小鹿、豬、魚、劍狀矛蚌、麗蚌、圓頂珠蚌、矛蚌、小型犬科等。 宋艷波認為張馬屯遺址的豬也可能屬于馴化的早期家養動物。
植物遺存:后李遺址發現有谷子(粟),張馬屯遺址種植有黍和粟。 在后李文化的山東長清月莊和章丘西河遺址發現了稻作遺存。 后李文化月莊遺址浮選出26 粒炭化稻,絕對年代為公元前6060—前5750 年。 陳雪香等學者認為“月莊水稻很可能是人類栽培的產物”[21]。 西河遺址的第三次發掘中也發現了炭化稻。 靳桂云認為“后李文化稻作可能是栽培,后李文化處于低水平食物生產階段”[22]。
后李遺址的孢粉分析結果顯示,草本植物占比高達76.3%~91.1%。 種類有蒿、喬本科、藜科、蓼、莎草、香蒲。 木本植物占比居次,主要以針葉松居多,其次為闊葉植物樺、櫟榆和胡桃。 蕨類植物孢粉最少,有卷柏、水龍骨科。 后李遺址的植被具有明顯的草原特征,草本植物豐茂。 氣候環境溫和稍干中摻雜著暖濕,屬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 這一時期氣候暖濕,可能比現在高2~3℃。前埠下遺址一帶為大河入海處的森林—草甸環境,氣候溫和,年平均氣溫可能比現在高4~5℃,相當于今天福建一帶的氣候,先民在這里從事漁獵和農耕生活。 小荊山遺址的氣候溫暖濕潤,年平均氣溫要比現在高4~5℃。
生業經濟特點:后李文化遺址大多分布在沖積平原上,周圍水資源豐富,還有豐富的麗蚌等淡水水產品。 后李文化的氣溫比現在高出4~5℃,大抵相當于今天的長江流域。后李文化遺址的面積4 萬~6 萬平方米。 在小荊山遺址發現有房屋、灰坑、墓葬和壕溝,房子出現有序排列。 西河遺址房子也是有序排列,房址皆是單間半地穴式。 后李遺址發現有灰坑、灰溝、房址、墓葬和豎穴式陶窯。已經科學發掘的文物資料顯示,后李文化先民過上了定居生活,有環壕圍繞聚落,聚落內有規劃有序的房屋、儲藏室、陶窯和墓葬,有的房屋內有加工食物的灶。 有學者根據房屋的建筑格局,認為后李文化時期的婚姻生活狀態是公房制走婚生活,屬于母系氏族的一個分支,人口在20~40 人[23]。 張學海認為西河遺址中的大房子是核心家庭的居住地,小房子可能用于儲存或婚姻生活[24]。 魏俊認為后李文化的墓葬同排之間具有更密切的關系[25]。
后李文化的使用工具有石器、 骨器、陶器。 陶器主要是生活用器,用于盛儲、炊煮和盛食。 石器和骨器用于獲取食物,比如狩獵、捕撈和植物栽培。 石器有石斧,可能用于砍伐樹木,開墾荒地。 石鑿和石錛用于木料加工,石鐮用于植物的收割。 石磨盤分有足和無足兩類,無足居多。 石磨盤和石磨棒用來研磨植物果實的種子,如谷子、水稻、黍和櫟果,鏟少見,鏃用于狩獵,魚鏢用于捕撈,錐和針用來縫制衣服。 有學者對月莊遺址的石磨盤、 石磨棒進行了微痕和淀粉粒分析后,認為它們既用來加工野生堅果,又用來加工谷物類作物[17]33。 吳文婉認為張馬屯和西河遺址的居民以豐富的野生植物為主的植物性食物結構, 栽培植物在人類食譜中占比50%以下,未能超過野生植物[2]285。 后李文化居民擁有豐富的動植物資源, 并廣泛利用,狗也是人類馴養的對象之一,野生動物為后李文化居民提供了60%以上的肉食來源。
五、兩地生業經濟構成的異同與聯系
從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兩地自然環境和生業模式具有較大的相似性,這應該與兩地文化地域相近,緯度類同,氣候溫暖濕潤,同處在黃河流域的中下游有密切關聯。
裴李崗文化與后李文化居民過上了定居生活,居住在半地穴式茅屋內,開始了早期的農耕經濟,種植粟和水稻,使用磨制石器收割和加工糧食或野生果實,石質生產工具都以石斧、石鐮、石磨盤、石磨棒組合形式出現。 它們都有氏族公共墓地,死后葬入規劃好的家族墓地,墓穴有序排列。 兩地文化社會形態屬于母系氏族社會時期。 采集漁獵、旱作農業、家畜飼養、稻作等生業經濟形式并存。 袁靖認為后李、裴李崗、磁山、興隆洼等不同地區家豬的飼養行為都是獨立起源的[26]。 黃其煦說“以粟為代表的作物群反映的農耕類型是黃河流域從采集經濟向農耕經濟的過渡過程中的形式”[27]。
兩地文化由于先民主體、歷史和自然環境的因素影響,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 裴李崗文化發現有野生大豆,禾本科植物種子馬唐屬、稗屬雜草、葡萄屬植物種子、酸棗、梅子、橡子、核桃遺存,這在后李文化中少見或未見。 動物遺存中,家豬在兩地文化中已經出現,裴李崗文化中出現了大象、丹頂鶴、揚子鱷等,在后李文化中還沒有發現。 而后李文化中發現的斑鹿、狼、老虎、狐、麋鹿在裴李崗文化遺址中少見或不見。 裴李崗文化中的石磨盤多見帶足,出現了有肩石鏟、骨耜,而后李文化的石磨盤很少帶足,未有發現骨耜和石鏟,石支腳在裴李崗文化中未發現。
后李文化中無足石磨盤較多,王強認為“無足石磨盤受到了裴李崗文化有足磨盤文化的影響”[17]38,兩地文化居民在各自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長期且充分的交流互動關系。 邵望平、高廣仁認為后李文化的來源除本地因素外,可能還受到裴李崗文化賈湖類型的東遷影響[2]58。 韓建業說裴李崗文化晚期,向東擴張遷徙,滲透到黃河下游地區[28]。裴李崗文化的東遷影響了后李人的生產生活,帶來的炊煮器鼎、生產工具石鏟以及房屋建筑風格都與后李文化迥然不同。 裴李崗文化地處黃河中游的平原地區,具有強大的核心作用,將黃河流域文化緊緊地聯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