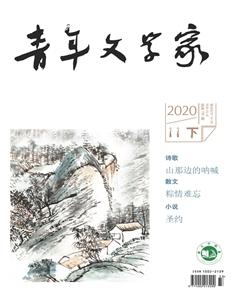《洛麗塔》的游戲性與人性問題
摘? 要:“游戲”是納博科夫文藝觀之中的重要概念,也是其代表作《洛麗塔》文本結構的一大特點。《洛麗塔》所描寫的倫理關系一方面展現了對道德規范的逾越,另一方面又體現了對傳統倫理秩序的尊崇,在倫理關系的處理上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游戲態度。本文認為,小說的這種游戲性描寫既不是對傳統倫理秩序進行批判性的調侃和嘲諷,也不是要設想某種新的道德準則,而是體現了作者對人性復雜性的冷靜反思,以及對人性完整性的執著追求。
關鍵詞:納博科夫;《洛麗塔》;游戲;人性
作者簡介:李舒眉(1999.11-),女,漢族,貴州貴陽人,重慶市西南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本科生。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33--05
1962年納博科夫在接受BBC一檔訪談節目的采訪時說道:“我喜歡國際象棋,但象棋中的騙局,就像在藝術中,只是游戲的一部分。”[1](P011-012)納博科夫視自然界為騙局,在作品中喜好制造“文學騙局”,而這些欺騙現象在他看來只是組成游戲的一部分。可以說,游戲觀念對納博科夫的藝術觀念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許多學者將其代表作《洛麗塔》視為后現代主義的代表作,從文體角度闡釋《洛麗塔》中的游戲精神,主要集中在該書的不確定性、元小說性質、戲仿、和反諷等性質[2],但實際上該作品的游戲性除了在文體層面體現得淋漓盡致之外,也明顯體現在作品對倫理關系的處理上。作品中的那些人物形象及其關系似乎都有一種“玩”的意思。一切文學皆是人學,納博科夫對人物及其關系的如此處理反映出的正是他對于人性以及基于人性的倫理關系問題的深刻思考。他雖然也關心文學是什么、藝術是什么等問題,但他更想告訴我們人是什么。
一、《洛麗塔》中倫理關系的雙面性
倫理關系同經濟關系、政治關系一樣,也是社會關系中極為重要的一個方面,并且倫理關系滲透并存在于諸如政治關系、經濟關系等具體社會關系之中,并使之擁有價值屬性,成為可以進行道德評價的關系。倫理關系對于具體個人而言,是在先的社會性規定[3](P257)。換句話說,倫理關系是我們身處其中的社會的一種具有一定強制性的秩序規范或情感與行為準則。沒有這種規則和秩序,社會就會處于混亂之中,違反這種關系規則,行為就會被評為“不道德”。對于我們每一個具體的個人而言,親人、戀人、朋友之間的關系無疑是決定我們生存秩序的一個十分重要的部分。《洛麗塔》發表以來被很多人認為是描寫“不道德”行為的小說,首先就在于它所描寫些的親人、戀人和朋友等普通人的重要社會關系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位移”,超出了我們一般人所理解的正常的關系界限,在行為和情感上越過了道德的準則。
首先,《洛麗塔》中描寫的親子關系是“非正常”的。洛麗塔與母親夏洛特爭奪同一個男人的喜愛,使親子關系異化成為類似于“情敵”的那種競爭關系。小洛在媽媽單獨約亨伯特外出時擠上車子搗亂,在媽媽對亨伯特賣弄風情時朝媽媽的腦袋扔網球。夏洛特視女兒為一個小惡魔,總是和她作對。女兒讓她在亨伯特面前頻繁出丑,攪擾她與亨伯特的“二人世界”,她送女兒去夏令營懷有調走女兒的想法:“洛麗塔也已決定星期四走,不必像先前計劃的那樣等到七月。”[4](P59)
其次,《洛麗塔》也典型地描寫了夫妻關系的“非正常”狀態。瓦萊里婭是亨伯特的第一任妻子,她有了另一個男人,向亨伯特提出離婚,她的情夫還羞辱了一番亨伯特。而亨伯特最初認為瓦萊里婭擁有模仿小女孩的才能,才與瓦萊里婭結婚,婚后他發現瓦萊里婭只是一個平凡的成年女子,轉為對瓦萊里婭極盡貶低,還向她施加肉體暴力和冷暴力。瓦萊里婭婚內出軌固然有錯,但亨伯特的態度和行為是造成她不幸福的根源。亨伯特第二次結婚是抱著接近小洛的目的。他一邊接受著夏洛特的照顧,一邊又像貶低瓦萊里婭那樣侮辱夏洛特,在日記里稱呼她“大母狗”“老貓”“又老又蠢”。他多次幻想著除掉妻子,這樣就能方便他占有繼女。例如,他看到夏洛特游泳想到要淹死她:“我需要做的只是重新跳出去,做一次深呼吸,然后抓住她的腳踝,迅速帶著我俘虜的尸身潛下去。”[4](P84)
第三,《洛麗塔》中描寫的朋友關系也超出了我們一般認為的界限。小洛在比爾茲利上學時結識了朋友莫娜,成為了她“最親密的好友”。但是,小洛所做出的一系列行為和對莫娜表現出的情感態度,卻常常令我們對這種“親密關系”感到疑惑和意外。小洛在迫切需要什么東西的時候,就會告訴亨伯特莫娜的桃色事件中各種令人咂舌的細節,將“最冰冷、最下流、最老練的年輕女性特征統統加之于她最親密的好友”[4](P191),為此她能得到亨伯特優厚的報酬,這讓亨伯特在與莫娜獨處時感到小洛在“拉皮條”。同時,莫娜清楚小洛與奎爾蒂的關系,“幫助”他們一起欺騙、捉弄亨伯特。莫娜在寄給小洛的信中嵌入了奎爾蒂的名字“Quilty”,顯然是在用文字游戲揶揄小洛和亨伯特。
最后,在小說重點關注的戀人關系的描寫上面,我們卻很難體會到戀人之間通常應有的甜蜜關系。亨伯特對小洛瘋狂迷戀幾乎充斥了整部小說,稱她為“生命之光”“欲念之火”“我的洛麗塔”“熱辣辣的小寶貝”“我的小卡門”。他也愿意花費大量錢財和精力,想方設法地討得小洛的歡心。然而在這些“甜蜜”的語言下面,常常是強烈的占有欲,甚至是令人恐懼的人身控制。亨伯特懼怕小洛曝光他們的關系,使用暴力手段控制小洛,并且威脅恐嚇她:“每當我要制止她發作的風暴,便把車開上高速公路,暗示她我要一直把她帶入那個黑沉沉、陰暗的農莊”[4](P149),不僅如此,他們的關系中還存在非常明顯的性暴力:“四肢粗重、氣味惡臭的中年人那天一早晨就和她有過三次交歡”[4](P139)。甚至為了獨占小洛,他采用了一種嚴格的監視約束方式,禁止小洛的社交:“只要我的政權在握,就永遠,永遠不會允許她和春情勃發的年輕人去看電影,或在小汽車里卿卿我我,或到同學家參加男女混雜的舞會,或在我聽力所及之外沒完沒了地進行男女電話交談。”[4](P187)。亨伯特把自己心愛的情人就像囚徒一樣對待,顯然越過了戀人關系的邊界。
在小說中,小洛與奎爾蒂之間的感情初看起來似乎是真正的愛情,然而我們從字里行間卻感到小洛的愛情帶有明顯的功利性。小洛很清楚她和亨伯特做情人是一種“亂倫”,但是她仍然“挑逗”亨伯特,對她來說“這只不過是一個無知的游戲,是在編造的浪漫行動中對某些偶像進行模仿的一點點少女的傻氣”[4](P110-118)。同樣,小洛迷戀奎爾蒂,除卻“偶像光環”,是因為奎爾蒂可以帶她逃離亨伯特的魔爪,還能幫助她實現長久以來的明星夢。
如果《洛麗塔》對倫理關系的描寫僅僅是這些超出常規倫理秩序的方面,那么說它是一部宣揚“非道德”的小說或許就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問題在于,作者所描述的這些關系又在一定程度上是非常“正常的”。首先,小洛其實很愛媽媽。她在從夏令營寄回家的信中祝福他們,表示對媽媽與亨伯特結婚感到高興;她聽亨伯特騙她說媽媽生病了(其實媽媽已經死了),和亨伯特發生關系后,在深感不適的情況下想給醫院打電話求助媽媽;在與亨伯特爭吵時,她猜到是亨伯特“殺”了媽媽;讀到一本講母女關系的書,她聯想到自己的境遇,去問亨伯特媽媽葬在哪里。夏洛特對小洛事實上也十分關心與愛護,她身上體現了我們所理解的一位正常母親的典型母愛。她不喜歡小洛,仍然負起了養育的責任,承受著喪夫喪子的痛苦獨自將女兒帶大,而沒有選擇拋棄女兒。她將女兒送進夏令營,也主要是因為夏令營在當時是一種流行的教育方式,她身邊的家長們也同樣選擇將孩子送進夏令營。“在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命題指導下,當時許多機構利用學校假期大量開辦各種活動營地。像夏洛特·黑茲夫人一樣的學生家長相信,夏季宿營是健康的。”[5]她發現亨伯特對女兒心懷不軌后,想要去夏令營接上女兒一同逃走,以免女兒受到傷害。“夏洛特想帶洛逃至帕金頓,或回到彼斯基,以免兀鷹般黑心的家伙劫走她的寶貝綿羊。”[4](P96)
同樣,不幸婚姻之中也有著夫妻關系的真誠。夏洛特作為妻子非常愛慕和關心丈夫。她在外人面前總是稱丈夫為“亨伯特先生”,早上會為丈夫做豐盛的早餐。游泳是他們的共同愛好,她送丈夫防水的手表做禮物。她婚后還把家翻新了一遍,換上新窗簾、新沙發布和新床墊。她在思想上把丈夫美化了:“我(指亨伯特——引者注)嚴肅的憤怒在她看來卻是愛情的沉默。我將菲薄的收入她的更有限的收入中,竟使她感動得像是發了大財。”[4](P74)這些行為都表明,夏洛特在她的第二段婚姻中重新感受到了生活的熱情,她真心實意地想要維系好這段婚姻。
從一些細節來看,小洛的友誼仍有天真無邪的一面。小洛還在念書時,朋友們會來家里找她玩。小洛的腳背被水果刀打到,露出痛苦的表情,隨后單腳跳著走了,小伙伴阿維絲則“立刻追著她進了廚房,去安慰她”[4](P294)。小洛離開學校后接到莫娜的來信,莫娜表達了對小洛的思念:“生活確實隨風飄去了。一切都結束了,學校,演劇……我還有更壞的消息告訴你。多麗-洛!當你回到比爾茲利的時候,我可能還回不來。”[4](P224-225)小洛和朋友們之間有著正常的交往和關心,也沒有達到完全相互敵視的地步。
對于奎爾蒂,小洛的愛情也是真誠的。奎爾蒂是才華橫溢的成功劇作家,小洛從兒時開始就視其為偶像。他出現在小洛的生活中,深深地吸引了小洛,使她不自覺地體現出一種戀人才有的癡情。奎爾蒂跟蹤“父女”二人的時候,小洛涂改亨伯特記下的車牌號,與亨伯特同居的日子里,她一定明白這樣的行為會招致亨伯特的暴力,事實上她的確遭到了亨伯特的毆打。亨伯特發現車牌號被涂改,“一言不發,用手背猛劈一掌,這一掌噼啪打在她熱辣辣堅硬的小頰骨上”[4](P229)。但她寧愿自己忍受,也一定要保護奎爾蒂。亨伯特下車想要查出跟蹤者的真面目,她悄悄地把車往反方向開走,阻止他看清奎爾蒂。
二、納博科夫思想之中的游戲性與人性
從以上情節和描寫我們可以看到,納博科夫所描寫的人際之間的倫理關系處于一種模棱兩可的“游戲性”狀態:所有關系似乎是“越界”的,同時又似乎是正常的。如果我們從這種關系出發去理解作者的態度,我們同樣可以見到這種模棱兩可的情況:作者似乎是在嚴肅“批判”這些“失范”的倫理關系的“不道德”,但對這些人物的描寫似乎又包含著作者的同情甚至是贊同。小說對亨伯特初戀遭遇造成的精神創傷的描寫,似乎是對其后“變態”行為的一種精神分析和辯護,好像只是一個偶然的病理個案,但卻又像是在揭示和批判真實普遍的人性的復雜狀況,等等。目前的一些研究注意到納博科夫在文體形式方面存在的這種戲仿游戲(參見趙君《互文網絡與文學空間的無限拓展——以<洛麗塔>為例》, 《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6月),也有的研究者也從“后現代”的角度闡釋了《洛麗塔》具有的“多元化”和“不確定”的藝術特點(參見徐靜《后現代主義視角下<洛麗塔>藝術特色解析》,《新余學院學報》,2018年第1期)。但實際上從人物的倫理關系的描寫方面看,小說同樣具有不確定性和模糊性的特征。這種“不確定性”、“模糊性”或者說“多元化”特征,我們可以用“游戲性”一詞來進行概括。那么,作者對倫理關系的這種游戲性描寫究竟體現了怎樣用意呢?
倫理關系包含了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性質和處理這些關系的行為規范和情感態度等方面。可以說,倫理關系涉及到的是一個社會特有的規范性秩序,具體的個人總是生活在這種關系之中并按照一套確定的、理性的價值準則行事。納博科夫對倫理關系的這種游戲性描寫使得倫理規則和秩序問題凸顯在讀者面前,首先反映的正是作者對倫理秩序和規則的特殊看法。
一方面,《洛麗塔》中的倫理關系明顯打破了常理,甚至挑戰到社會公德的底線,這樣的越界現象源于納博科夫對個體自由的高度重視。在納博科夫看來,客體的真實面貌不可知,人只能在信息和知識逐漸深化的過程中盡可能極限地接近事物的全貌與本質。“你離真實越來越近,因為真實是不同階段、認識水平和‘底層的無限延續,因而不斷深入、永無止境。”[1](P011)他認為現實是一種非常主觀的東西,每個人都可以從自己的認識出發,對現實做出一番解釋。但是,人不會始終以個體的方式存在。一旦進入群體性的社會生活,理性就出面要求把多樣的個人利益歸為統一。要讓人類社會得以運行,就不得不假定這種理性規則的存在。這意味著人不可能僅憑個人的意愿為自然立法,每個人的個體自由也就喪失了一部分。納博科夫曾在美國《威爾斯利雜志》上說過:“民主最大的矛盾就是,在強調整體規則和共同權利的平等時,個人可以從中獲取他特殊的、非共同的利益。”[6]納博科夫也深感人一面受制于想象性的理性規則,一面卻又執著于個體自由的矛盾。即使可能染上偷偷摸摸的色彩,人為了維護個人的利益,不會完全順從公共秩序,而是想方設法地在規則之中突破規則,追求個人利益的實現。
回到最初帶給納博科夫創作《洛麗塔》靈感的那個小故事:“巴黎動物園的一只大猩猩,經過科學家數月的訓練,最終用碳筆畫出了動物的第一張圖畫,這張素描印在了報紙上,畫的是這個可憐生物所居住的籠子的柵欄。”[1](P015)每個人都是這只大猩猩,都是納博科夫口中的“可憐生物”,因為在這個世界里,人始終會被囚禁在由理性規則所組成的牢籠之中。然而在《洛麗塔》的世界里,那些人物都打破了倫理道德規范。中年男子對未成年少女的性欲望和性行為,是一條非常明顯的倫理禁忌,但是《洛麗塔》涉及的亂倫不僅在于愛情,還包括了親情、友情,幾乎一切的人類倫理關系。《洛麗塔》曾一度被公認為色情作品,評論家約翰·戈登甚至說這是他讀過的最骯臟、最淫褻的書;一些人認為《洛麗塔》是個寓言故事,說它寫的是“古老的歐洲誘奸了年輕的美國”,或是“年輕的美國誘奸了古老的歐洲”。這些解讀其實都反映了我們把納博科夫筆下的那個世界當作是真實存在的。人性之中本來就含有突破禁忌的強烈欲望和強大力量,只是我們自己不愿意承認,也不愿意面對這個事實。《洛麗塔》的世界顛覆了我們這個世界之中的倫理規范,帶給我們危機感,所以面對那個世界,我們反而感到羞恥和恐慌。納博科夫通過《洛麗塔》,實際上對所有讀者都提出了非常嚴肅的問題:人為什么一定要服從于那些假定的理性概念?人為什么不能夠按照個人規劃的一套準則進行自我主宰?這就是《洛麗塔》從出版到現在仍然會被人們在心里當作是“禁書”的深層原因。
納博科夫曾在《堂吉訶德講稿》中說:“實際上,讓人覺得非常奇怪,這些教士以及受教會束縛的作家怎么會讓理性——人為的理性——占據了主導地位,而想象力和直覺的能力卻都遭到禁錮。”[7](P65)他不止是對文學創作,也是對人的生存狀態發出了這樣的感慨。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他創作《洛麗塔》就是在表達他對理性束縛個體自由感到的不滿。《洛麗塔》于1958年在美國一經出版就大獲成功,高居暢銷書排行榜首位高達半年之久;一些學者還認為《洛麗塔》對20世紀60年代流行于美國文壇的“黑色幽默”具有啟迪意義:“如果說黑色幽默是關于被社會所禁止的事情的喜劇,是對道德界限進行試探、把禁忌打碎的喜劇的話,那么《洛莉塔》就是黑色幽默的一個縮影。如果沒有《洛莉塔》……也就很難想象得出品欽、海勒、馮納格特和菲力浦·羅斯的作品是什么樣子。”[8](P220)《洛麗塔》從被視為“黃書”到被主流文化所認可的命運,以及它對于美國文化產生的影響,都說明人們對它的態度從忌諱轉為接受,證實了人們破禁意識的復蘇。
另一方面,打破規則的束縛固然是《洛麗塔》的顯著特點,但是通過細致梳理小說涉及的各種倫理關系,不難發現,《洛麗塔》中的倫理關系仍有非常“正常”的一面。納博科夫在小說的后記中談到,人們把《洛麗塔》當成色情作品,抱著這種先入為主的印象,他精心打造過的一些細節會被草草翻過,或者不受關注,甚至從來不會被翻到。然而這些細節,在他看來卻是“小說的神經,神秘的節點,小說情節得以連綴”[9]。關于那些“神秘的節點”,納博科夫就提到了夏洛特說她送給亨伯特游泳的手表是“防水的”。納博科夫以“愛”作為書寫這部小說的基點,他的這種態度就隱藏在那些被忽略的細節中:洛麗塔與夏洛特彼此牽掛,她們的行動印證了親情的難以分割;夏洛特作為妻子真情實感地愛亨伯特,愿意為他無私地付出;小伙伴們對洛麗塔的關愛,體現了孩子之間友情的純真;洛麗塔愛奎爾蒂,配合著奎爾蒂的意愿一起捉弄亨伯特,還不計后果地保護奎爾蒂。“在虛構的帶有普遍性的特點與生活的帶有普遍性特點之間,卻有著某種聯系。以生理或心理的痛苦為例,或像善良、仁慈、正義這樣一些情感為例,研究這些情感由虛構作品的大師轉化為藝術的手法,一定是一件有益的工作。”[6](P5)盡管納博科夫否認文學反映“現實”生活,但是他在《堂吉訶德講稿》中的這段話表明:“現實”世界與虛構的藝術世界之間并非完全決然對立,溝通二者的橋梁就是人類共享的一切情感。《洛麗塔》中的親子之愛、夫妻之愛、朋友之愛與戀人之愛都有著真摯的一面,它們能夠被我們感知和認同,也符合我們對于倫理關系的美好想象。
納博科夫肯定人性之愛。即使是亂倫之愛,他也并沒有橫加指責。“并不是我認為亨伯特和洛麗塔之間的關系不道德,是亨伯特自己這么認為。他在意,我無所謂”[1](096)。但他認為亨伯特是個自負、冷酷的壞蛋,不同意人們視亨伯特為感人的、固執的藝術家[1](097),他對亨伯特的否定態度似乎又與他對愛的肯定態度起了沖突。我們可以從他提到的另一個“神秘節點”中正確理解他的用意:小說里的一位理發師在為亨伯特剪頭發時一直絮絮叨叨地談論他的兒子,亨伯特對此心不在焉,直到理發師指著兒子的相片,他才驚訝地發現原來理發師的兒子已經去世三十年了。子女、兒童的死亡,在納博科夫看來是人類所能承受的痛苦的極限。這個細節揭示了亨伯特的問題在于,他只關心他個人而總是漠視別人的處境,等到他理解別人時卻早就為時已晚。他在日記里竭力渲染夏洛特和洛麗塔的關系不好,自己才有了可乘之機,后來他發現她們之間仍然存在著真誠的愛,感嘆道從前“過于相信夏洛特和她女兒以前的那種不正常的冷冰冰的關系”[4](P460);他不愛瓦萊里婭和夏洛特,覺得她們不管做什么都很愚蠢,夏洛特對他的關愛卻狠狠地反襯出他的冷漠;他想表現洛麗塔道德敗壞,甚至用“拉皮條”這樣的詞語來形容她和朋友的關系,而忽視了孩子之間友誼的純潔性;他將年少時失落的情欲強加給一個毫無防備的小女孩,占有她后又用無恥的手段控制她。他最后才承認這一切對于這個小女孩而言是不公平的,然而她的童年早已被毀滅了。
納博科夫使用“冷酷”“自負”“壞蛋”這樣帶有厭惡情感和道德判斷的詞語評價亨伯特,不是因為亨伯特對幼女懷有迷戀,而是因為亨伯特為了維護他的個人自由就隨意地去侵犯他人的自由。愛欲沒有道德之分,然而行為有道德和不道德之分。一旦涉及行為,就會有某種標準來指導行動。盡管納博科夫不認為人必然要遵守假定的理性規則,但是他也肯定規則對于人的約束作用:“常識是被公共化了的意念……罪犯通常是缺乏想象力的人,因為想象即使在常識最低限度上的發展也能阻止他們作惡,只要向他們靈魂的眼睛展示一幅描繪手銬的木刻;有創造性的想象力就能引導他們從虛構作品中找到排泄口,并讓書中人物做得比他們自己在真實生活中能拙劣做到的更徹底。”[10](P421-425)如果說納博科夫寫《洛麗塔》是為了告誡人們要遵守規則,那么《洛麗塔》就變成了他蔑視的道德說教小說,顯然違背了他的原意。但納博科夫愿意相信,由超越規則而導致的最惡劣的結果只能在虛構的世界里存在,也就是說,在我們生存的這個世界里,在能夠指導我們更好地生存的方式還沒有出現之前,納博科夫認為理性規則仍然不可以被完全打破。正如研究納博科夫的權威專家博伊德指出的那樣:“在這個世界,在這個生活里,沒有任何人可以享受責任豁免權。如果那些聰穎的想象天才(指納博科夫筆下的藝術家主人公——引者注)都不能做到滴水不漏,我們又能如何呢?”[11](P10) 納博科夫見出打破規則將會帶來嚴重的后果,他最終還是把打破規則的人拉回了規則的框架之中。洛麗塔放棄了青春期的叛逆和“早熟”的愛戀,與一個年紀相仿的男孩結婚,過上平淡卻穩定的家庭生活;亨伯特終于直面他對洛麗塔造成的傷害,帶著父親的身份去找奎爾蒂復仇,最后因殺人罪被捕入獄。《洛麗塔》兩位主人公最后的選擇,實際上都回歸了倫理的秩序。
三、總結
從以上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出于人性自身的自由和完整,人的欲望和感性既是普遍必然的,也是值得同情和理解的,但是出于人生存的社會性需求,人與人之間的行為才具有了進行倫理規范的必然性。納博科夫對倫理關系的游戲性描寫,不是要根據某種既定的規則去批判某種行為,也不是用一種既定的準則去進行道德審判,他要向我們展示的也許正是這種自由和規則、感性和理性相互嵌套的模糊狀態。從這個角度看,人類的倫理秩序也就是一種人類為其社會性生存所劃定的一種游戲規則,它具有假定性和游動性而不是絕對性。納博科夫因此既不是要維護一種現有的道德規范,也不是要打破這種規范而提出一種新的明確的準則,他的這種態度這也使得我們當初對文本的閱讀始終難以捕捉到一個確定的道德立場和情感態度。這也許就是《洛麗塔》問世以來,人們對它的看法始終難以獲得道德情感統一性的原因。
在西方哲學史中,“游戲”一直是一個備受關注的術語和概念。近代哲學家們從人性的角度探討游戲。康德注意到藝術與游戲的聯系,他在說明藝術與手工藝的區別時指出:“藝術還有別于手工藝,藝術是自由的,手工藝也可以叫做掙報酬的藝術。人們把藝術看作仿佛是一種游戲,這是本身就愉快的一種事情。” 康德認為藝術的精髓就在于自由,正是在自由這一點上,藝術與游戲是相通的。藝術與游戲都標志著“活動的自由和生命力的暢通”。自由游戲促成了健康的感覺,帶給人滿足感。[12](P374-375)
康德將藝術的自由特征與游戲的自由特質相結合,進而揭示了人的自由本質。相較于康德,席勒所討論的“游戲”更深入“人”的層面。席勒認為,在高度抽象的條件下,人的身上區分出兩個東西:固定不變的人格和經常變化的狀態,由此人的身上產生出兩個相反的要求。一個是要有形式性,要使千變萬化的現象變為可理解的或是合理的,就必須把物質世界歸為統一的形式;一個是要有實在性,要把統一的形式帶入物質世界中,把形式的東西轉化為實在。這是人的理性本性與感性本性的兩項基本法則。因此,人的天性中存在著兩種相反的沖動:理性沖動(形式沖動)要求人將變化的現象賦予形式、歸為統一,感性沖動要求人把通過理性形式感知的內容變為實在。但是依席勒的看法,這兩種沖動原本不是相互對立的,它們是因為搞亂了各自的邊界才表現出沖突狀態。理性沖動要求統一,但它不要求狀態和人格一起保持不變,它不要求感覺的同一;感性沖動要求變化,但它不要求人格同狀態一起變化,它不改變理性的原則。如果它們越過各自的邊界而產生沖突與強制,就會帶來人性的分裂。此時,就需要在它們之間確定一個界限,保持它們各司其職,這個界限就是“游戲”:“在形式沖動和感性沖動之間應該有一個集合體,這就是游戲沖動,因為只有實在與形式的統一,偶然性與必然性的統一,受動與自由的統一,才會使人性的概念完滿地實現”[13](P45)。人性的分裂不可避免地使理性沖動與感性沖動產生對抗,游戲沖動作為調和這兩種沖動的一個中間地帶,既保留它們的沖突性,又恢復它們原本的互補性。游戲同時融合了理性與感性,也就消除了來自理性方面和感性方面的強制,給予人自由的滿足感,使人處于理想的生存狀態之中。
誠然,《洛麗塔》對倫理關系的游戲性描寫,并不是體現作者的一種解決方案,而是依舊揭示了在一個秩序社會中感性與理性的分裂情況,從這個意義上說,作者的游戲性描寫本身也具有一種引導我們走向錯覺的游戲性。我們可以說《洛麗塔》中的人性是“游戲”的嗎?納博科夫把話語權交給了亨伯特,巧妙地把自己的意見藏在背后。讀者透過亨伯特這個“氣喘吁吁的瘋子”的敘事,很容易看到“任性的孩子,自私的母親”[4](P4),那些“感性”到極端的人性,難以發現納博科夫對于理性的堅持與部分認同,包括他對愛的肯定態度與他的道德批判態度。席勒認為游戲可以恢復完美的人性,但這樣的理想主義與納博科夫呈現的嚴酷現實仍然相去甚遠。納博科夫宣稱自己的小說沒有社會意圖或普遍意義上的道德,他關心的問題不在為人們提供某種生存的方式,而是重在揭示人的生存狀態。一方面,人受制于倫理、道德等假定的理性規則,渴望打破規則獲得個體自由。盡管人的這種意愿具有潛在的破壞性,但不可否認,它是人性的一部分。《洛麗塔》倫理關系的反常表現就是還原了這一部分,并讓我們意識到它的存在。另一方面,人如果完全打破規則,將會造成毀滅性的后果。在優于理性規則的替代品出現之前,人仍然要接受規則的約束。《洛麗塔》的結局以及納博科夫的思想暗示的或許正是這種根植于人性深處的分裂性悲劇。
參考文獻:
[1]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著,唐建清譯.《獨抒己見》[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2.
[2]李瑩.2000 年以后國內外關于《洛麗塔》的研究綜述[J].世界文學評論(高教版),2013(01):243-250.
[3]朱貽庭主編.《倫理學大辭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
[4]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著,于曉丹譯.《洛麗塔》[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
[5]王青松.回歸現實主義——《洛麗塔》的一種解讀[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02):88-93.
[6]于曉丹.《洛麗塔》:你說是什么就是什么[J].外國文學,1995(01):75-80.
[7]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著,金紹禹譯.《堂吉訶德》講稿[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
[8]薩伯科維奇主編,孫宏主譯[M].《劍橋美國文學史·第7卷》.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9]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著,周麗華譯.談談一本名叫《洛麗塔》的書[A].《洛麗塔》[M].南京:譯林出版社, 2003.
[10]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著,申慧輝等譯.《文學講稿》[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
[11]博伊德著,劉佳林譯.《納博科夫傳:俄羅斯時期》(上)[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12]朱光潛著.《西方美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13]席勒著,張玉能譯.《審美教育書簡》[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