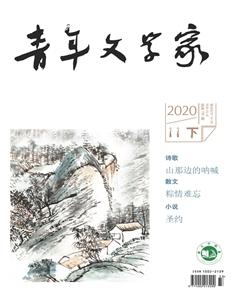論“性三品說”的繼承與發(fā)展
摘? 要:自古儒家論“性”,春秋戰(zhàn)國時期便有論述,最早見于孔子《論語》之中,后至唐宋時期共大約1500年間各代文人思想家皆對“性”有所論述。古人論“性”即討論人性的善惡,而儒家思想中的人性論也在各個時代的思想家的主張中不斷變化發(fā)展。從孟子的“性善說”,荀子的“性惡說”,到漢代董仲舒的“性三品說”,再到中唐時期韓愈“性三品說”皆是在孔子《論語》中人性論的繼承與發(fā)展。
關(guān)鍵詞:人性論;性三品說;發(fā)展因素;崩潰
作者簡介:徐晗(1996-),女,漢族,遼寧省海城人,沈陽師范大學(xué)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唐宋文學(xué)方向。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33-0-02
一、人性論的提出與發(fā)展
自古儒家思想論“性”,春秋戰(zhàn)國時期就有論述。“性”即人性,最早見于孔子《論語》中,后至唐宋共約1500年間各代文人思想家皆對“性”有所爭論。最早出現(xiàn)“性”思想討論專著普遍被認為是孔子的《論語》,而《論語》中孔子言“性”的語句也成為了后世儒家思想人性論發(fā)展的基礎(chǔ)和依據(jù)。如《論語·陽貨》中所提及的“性相近也,習(xí)相遠也”[1],意思是人的先天本性是相近的,但可以經(jīng)過后天的“習(xí)”產(chǎn)生極大差異。孟子“性善說”就是根據(jù)孔子的這一觀點逐漸發(fā)展而來,孟子作為第一個將人性進行具體闡釋的儒家思想家,他認為人生來便具有“不忍人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而這四心便是人生而性善的依據(jù),《告子上》就曾說道:“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 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2]由此可見孟子的人性論思想則是由孔子的“性相近也,習(xí)相遠也”繼承發(fā)展而來。然而先秦時期關(guān)于人性論的觀點并不止孟子一家學(xué)說,荀子的“性惡論”便是對人性的另一種解答。荀子認為性是人生來就存在的自然本性,認為性“不可學(xué),不可事而在天者”,其人性論最突出的思想便是提出將欲包含到性中,荀子對于“惡”的理解不是直接的惡,而是由“情”和“欲”所產(chǎn)生的不滿足,進而轉(zhuǎn)為惡。
到了西漢時期人性論又有所轉(zhuǎn)變,儒學(xué)的主導(dǎo)地位使儒家思想更加確認了為統(tǒng)治階級服務(wù)的方向,而董仲舒“性三品說”的提出對傳統(tǒng)儒家人性觀思想有了新的闡釋。董仲舒將人性分為上、中、下三品,并闡釋為圣人之性、中人之性和斗筲之性。這三品論思想的提出更多是受到了孔子的影響。如《論語·陽貨》中所提出的“唯上智與下愚也”[1]181,《論語·雍也》中“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生而知之者上也,學(xué)而知之者次也, 困而學(xué)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xué),民斯為下矣”[1]61都對董仲舒“性三品論”有著直接影響。董仲舒認為生而有善且不教便善,謂之圣,斗筲之徒欲望極多且不可教化,而中性之民數(shù)量最多,且具有可教性,所以在董仲舒的人性論思想中將“中人”作為人性的代表,認為要治理好國家百姓必須要經(jīng)過教化,而教化他們的人就歸于君王之權(quán),以此達到政治上強化了君主權(quán)力,道德上中央集權(quán)的目的。
顯然性三品說的提出對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央集權(quán)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至于性三品說自西漢董仲舒提出之后便一直被各代沿襲,唐朝時期韓愈對董仲舒性三品說就有著高度認可,在繼承董仲舒性三品說的基礎(chǔ)上,韓愈對孟子、荀子、楊雄等人的人性理論進行了篩選與發(fā)展,將他們的理論與性三品論相結(jié)合,完善了性三品說,在《原性》中論述了“情”與“性”的關(guān)系。而此時韓愈所提出的“性三品論”在一定基礎(chǔ)上修改了董仲舒理論的弊端,至此,“性三品論”的思想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完備。到中唐時期李翱在《復(fù)性書》中提出“性”上萬人平等的主張時,儒家思想中人性論的形而下開始有所轉(zhuǎn)變。
二、“性三品說”的發(fā)展因素
(一)封建統(tǒng)治的需求
西漢時期,封建中央集權(quán)的思想主要是沿襲秦朝的“大一統(tǒng)”思想,雖然中央集權(quán)得到了鞏固與發(fā)展,但地方與君主專制中央集權(quán)的矛盾、農(nóng)民和地主的階級矛盾仍在不斷加劇。不僅如此,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矛盾的加劇和嚴重的社會階級剝削壓迫,致使國家對君主集權(quán)有著前所未有的強化需求。由于在西漢初期,為了吸取秦朝嚴峻法治導(dǎo)致社會矛盾激化的滅亡教訓(xùn),實行了“法自然,尚無為”的黃老思想作為治國思想,使戰(zhàn)后時期的西漢得到了發(fā)展,但西漢中期由于儒家思想的崛起和在黃老之學(xué)“重道輕君”等思想的局限性下,儒學(xué)發(fā)展成正統(tǒng)思想。而董仲舒所提出的“天人感應(yīng)”“君權(quán)神授”正是符合當時統(tǒng)治者加強君主專制的重要武器。“性三品說”作為董仲舒思想體系中的一部分,其思想的實際意義便是將統(tǒng)治階級定為“圣人之性”,將反對剝削統(tǒng)治階級定為“斗筲之徒”,而將廣大百姓成為包含善惡且能夠被教化的“中民”,認為專制君主可以承擔統(tǒng)治教化百姓的職責(zé),這一思想直接將當時西漢時期專制君主的權(quán)利和權(quán)威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在西漢之后的各朝代,對“性三品說”的繼承與發(fā)展或明或隱都是為了封建統(tǒng)治階級所服務(wù)。
(二)儒學(xué)主導(dǎo)地位的推動。
“性三品說”的形成與發(fā)展與儒家經(jīng)典地位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人性論作為儒家思想中重要部分,其發(fā)展必然離不開以儒家經(jīng)典為依據(jù),而文人對于儒家經(jīng)典的熟知和引用程度與儒家思想的社會地位密不可分。如在西漢以前,儒學(xué)在政治、社會上不占主導(dǎo)地位,不論是孔子、孟子還是荀子等思想家們的人性論也只是作為各自理論的輔助支撐,所以在西漢初期的“性三品說”早期萌芽時期并不是以孔子《論語》等儒家經(jīng)典作為依據(jù)。西漢武帝之后,儒學(xué)確立社會思想主導(dǎo)地位,作為“性三品說”的儒學(xué)經(jīng)典依據(jù)也在不斷增多。如《論語·雍也》中“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陽貨》的“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后來《論語·季氏》中的“生而知之者,上也;學(xué)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xué)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xué),民斯為下矣。”[1]177都成為了支撐“性三品說”的儒家經(jīng)典依據(jù)。此外,在三國魏王肅的《論語注》梁皇侃《論語義疏》中都對《論語》中孔子論“性”的語句進行注釋來反映“性三品說”的思想。到了唐代初期,《五經(jīng)正義》成為了法定教科書后,儒學(xué)地位又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性三品說”的理論也因此不斷地進行完備,直到韓愈《原性》的出現(xiàn),使“性三品說”有了最完備的理論思想。由此可見,隨著人性論從先秦諸子時期的“性同一”到西漢武帝后的“性三品說”的不斷發(fā)展與深化,儒家思想的社會地位也呈現(xiàn)出一種上升趨勢,而唐中期乃至宋代時期“性三品說”逐漸受到質(zhì)疑,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為佛教、道教思想的傳入,儒家思想的絕對主導(dǎo)地位的消失而造成,可見“性三品論”的發(fā)展與儒家思想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
(三)宿命論思想的傳播與深化。
先秦時期人們對“性”的理解是:“性”是可以經(jīng)過后天的學(xué)習(xí)和修養(yǎng)而改變的。與此相反,西漢時期董仲舒的“性三品說”的思想則是認為“性”是很難改變的,尤其是上品的“圣人之性”和下品的“斗筲之性”是像宿命一樣不可教化,可見西漢時期就已經(jīng)有了宿命論的思想。到東漢時期,王充《論衡·本性》中將宿命論與“氣”聯(lián)合在一起,更加強化了宿命論的思想,提出了“人之善惡,共一元氣。氣有少多,故性有賢愚”[3]的主張將“性三品論”宿命化。這一主張后來得到了很多思想家的認同,如皇侃在《論語義疏·陽貨》中對“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的注釋中,對“氣”、“宿命論”、和“性三品”之間的關(guān)系闡釋為“夫人不生則已,若有生之始,便稟天地陰陽氛氳之氣。氣有清濁,若稟得淳清者則為圣人,若得淳濁者則為愚人。愚人淳濁,雖澄亦不清。圣人淳清,攪之不濁。故上圣遇昏亂之世,不能撓其真。下愚值重堯迭舜,不能變其惡。故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也。”[4]而后對宿命論的觀點在各代的儒學(xué)思想家們的沿襲下不斷的傳播與發(fā)展,“性三品論”也在宿命論的深入影響下被人廣泛接受。
三、性三品論的崩潰
人性論這一思想從先秦諸子時的“性同一”到董仲舒時期的“性三品說”正是一個由高到低的思想轉(zhuǎn)化的過程,顯然這種等級思想與儒家思想中的“仁”是不相匹配的,對儒家文化的發(fā)展是不利的,但由于其特殊的政治服務(wù)性,“性三品說”又有其存在的獨特性。“性三品說”思想的崩潰在唐中期時便露出端倪,唐代韓愈《原性》中對“性三品說”思想的論述達到了完備頂峰的程度,但其弟子李翱在《復(fù)性書》中提出的“性善情邪”說表達了自己對“性三品說”的質(zhì)疑與反對。不僅如此,李翱在復(fù)性書中更加明確直白地提出人性萬人平等的觀念直接說出“百姓之性與圣人之性弗差也。”[5]這樣的主張。這種質(zhì)疑出現(xiàn)的原因正如上文中多提及的,中唐時期佛老思想的傳入導(dǎo)致儒學(xué)思想的主導(dǎo)地位受到了很大的威脅,宿命論的思想也在佛教、道教的影響下所減輕,儒學(xué)思想家家們受到佛老思想的影響后對自己的主張有所修正革新,顯然李翱《復(fù)性書》中人性的思考受到了當時佛教眾生平等思想的影響。
“性三品說”被儒學(xué)思想家們徹底的放棄則是在宋代時期,宋學(xué)時期“性三品說”已然陷入了一種僵局,而在這種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新儒學(xué)時期,顯然“性三品”已經(jīng)失去了主流地位。作為宋代新儒學(xué)的代表人物程頤和朱熹,在“性”這一觀點上繼承了佛道兩教所信奉的萬人平等的思想以及可變論的思想。至此也就代表著“性三品說”這一影響中國古代1500年的思想就此結(jié)束。
總之,在人性論的發(fā)展中,每個時代都有著對人性的不同探討,時代之間的不同思想也在不斷地融合,盡管“性三品說”經(jīng)過漫長的時間過后逐漸被萬物平等所取代,但我們并無法否認其在歷史上所作出的貢獻與影響,每一個被時代所認可的思想那歷史上的某一時期都是適應(yīng)時代發(fā)展需求的產(chǎn)物,人性論也是如此,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性三品說”有著不可否認的價值與影響。
注釋:
[1]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2.
[2]楊伯峻.孟子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9:286.
[3]黃暉.論衡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1990:142.
[4]皇侃,撰. 高尚榘,點校.論語義疏[M].北京:中華書局.2013.
[5]李翱.李文公集:第二卷[M].四部叢刊:第119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