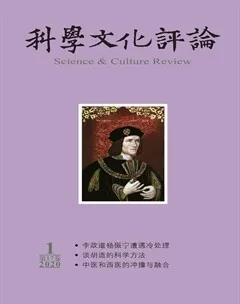談胡適的科學方法
摘 要 以門捷列夫發明的化學元素周期表等為例,說明早年胡適所提“細心搜求事實,大膽提出假設,再細心求實證”三階段科學方法的正確性。但簡化成“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則易招致誤解。他后來說的“勤、謹、和、緩”也是符合上述的科學方法與正確態度。筆者討論了一些與他人的不同見解。
關鍵詞 科學方法 治學態度 胡適 門捷列夫 馮勞厄
中圖分類號 N092
文獻標識碼 A
一 引言
2019年是兩個與科學史有關的重要紀念年。一個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從“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學生運動轉成提倡“民主”與“科學”的新文化運動,到2019年已100周年。另一個是1869年,俄國化學家門捷列夫(Dmitri I. Mendeleev,1834—1907)正式提出報告,宣布化學元素周期律之發現與元素周期表之發明的150周年紀念。由于門捷列夫對科學發展的這一巨大貢獻①,聯合國訂定2019年為“化學元素周期表國際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Periodic Table of Chemical Elements)。
然國人談五四運動,一般皆少涉及“科學”,而正確的科學方法與態度至今似猶未完全融入文化之中①[1]。本文擬拋磚引玉,簡述胡適所提的科學方法,以門捷列夫周期表為例說明,并就后人的一些辯難予以討論。
二 民國初期的“科學方法”
中國文明里原有許多應用科學技術,但未發展成有系統知識與理論的近代科學。直到清末民初,對于近代科學仍少了解。新文化運動首先提出民主和科學的是陳獨秀(1879—1942)。早在1915年9月的《青年雜志》(第二年改名《新青年》)創刊號里,他就倡言“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并說:“科學者何?吾人對于事物之概念,綜合客觀之現象,訴之主觀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謂也。”又說如果士、農、工、商、醫各行不知科學,則將如何如何[2],并沒說清楚科學究是甚么。1919年初,他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中說“本志同仁……擁護那德謨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并宣稱:“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3]但他仍未說清楚究竟甚么是科學,什么是以科學來救治中國的方法。
另一方面,也在1915年,由中國科學社創辦的《科學》雜志正式出版,目的是傳播科學新知與介紹外國科學新聞。至于什么是“科學”?其發刊詞說:
科學者,縷析以見理,會歸以立例,有?理可尋,可應用以正德利用厚生者也。百年以來,歐美兩洲聲明文物之盛,震鑠前古,翔厥來原,受科學之賜為多,科學之為物,未可以一二言盡也。[4]
任鴻雋(1886—1961)于第1期《科學》的《說中國無科學之原因》中又說:
科學者,智識而有統系者之大名。就廣義言之,凡智識之分別部居,以類相從,井然獨繹一事物者,皆得謂之科學。自狹義言之,則智識之關于某一現象,其推理重實驗,其察物有條貫,而又能分別關聯抽舉其大例者謂之科學。是故歷史、美術、文學、哲理、神學之屬非科學也,而天文、物理、生理、心理之屬為科學。今世普通之所謂科學,狹義之科學也。持此以與吾國古來之學術相較,而科學之有無可得而言。[5]他推崇歸納法于科學之重要,并在結束時說:
要之科學之本質不在物質,而在方法。今之物質與數千年前之物質無異也,而今有科學,數千年前無科學,則方法之有無為之耳。誠得其方法,則所見之事實無非科學者。 [5]
任鴻雋還在1919年10月發表過一篇“科學方法講義”,是在北京大學論理科的講演內容。仍是用外國的例子說明觀察、試驗,強調歸納邏輯[6]。似也都不能讓一般國人了解什么是科學或什么是科學方法。
1919年 3月,胡適(1891—1962)曾講過一篇《少年中國的精神》[7],提到了“科學方法”并略說科學方法的要點為:注重事實,注重假設,注重證實。年底的《北京大學月刊》刊載了胡適于8月中國科學社年會中發表的“清代漢學家的科學方法”一篇論文①[8]。他認為科學方法“是演繹和歸納互相為用的”,并且舉例說明中國舊有的學術——清代的“樸學”(包括文字學、訓詁學、校勘學和考訂學等)是用科學方法,確有科學精神。但他此文并未寫完,1920年春和1921年11月分別續完[9, 10],并于結集時改篇名為《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在完結章(八)中說:
我想上文舉的例很可以使讀者懂得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了。他們用的方法,總括起來,只是兩點:(1)大膽的假設,(2)小心的求證。假設不大膽,不能有新發明。證據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11]
似是他首次用淺顯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當作治學的科學方法。
胡適又在1922年6月18日的《努力周報》之《我的歧路》②中說他談政治和談白話文是實行他的實驗主義。他說:
實驗主義只是一個方法,只是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細心搜求事實,大膽提出假設,再細心求實證。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只是參考的材料,暗示的材料,待證的假設,絕不是天經地義的信條。實驗主義注重在具體的事實與問題,故不承認根本的解決。他只承認那一點一滴做到的進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導,步步有自動的實驗──才是真進化。[12]
還說:
我這幾年的言論文字,只是這一種實驗主義的態度在各方面的應用。我的唯一目的是要提倡一種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種注重事實,服從證驗的思想方法。[12]
“細心搜求事實”相當于了解、掌握相關問題的背景資料,然后才有資格提出假設而試予求證。這和他在少年中國學會上所講,須“注重事實,注重假設,注重證實”,是一致的。雖然他只提到“實驗主義”,身為一個曾從事化學研究約半世紀的科學工作者,淺見以為胡適當時所說的“三階段”──“細心搜求事實,大膽提出假設,再細心求實證”,是完全正確的科學方法。唯他用中國古代學者治學的例子解說,一般國人能否了解與接受,仍為可疑。下節將以現今中學教材即有的門捷列夫周期表為例說明,進一步討論見后文。
三 細搜事實與大膽假設──門氏周期表
約150年前門捷列夫的周期表是“細心搜求事實,大膽提出假設”的好例證。門捷列夫是圣彼得堡大學1865年的科學博士,1867年在該校講授無機化學。依化學史書[13—15]的敘述,他和當時好幾位化學家一樣,從事化學元素的性質與分類的研究。他匯集了英、法、德和瑞典等國已發表當時所知63種元素的有關原子量、物理性質和化學性質的數據,分別寫在不同的卡片上。經過排比與思考,曾于1868年寫過一張將化學元素符號排成六行的草稿(圖1),是后來周期表的雛形。1869年俄歷2月17日他完成了直式六行的表(圖2)①。然后撰寫《元素原子量與性質的關系》一篇論文,說明化學元素的許多性質乃隨原子量增加而有周期性變化,3月6日在俄國化學會中宣讀,并發表于當年的《俄國物理及化學會志》。同時,德國的《化學雜志》(Zeitschrift für Chemie)上也刊出了一則有關的簡報(圖3)。
他再繼續研究,1871年又發表了橫式八行周期表的長論文。將原來的排列方式,改直為橫,使性質相似的元素處于同一行中,更凸顯元素的周期性質(圖4)。其德文譯文近一百頁,于第二年刊出[16]。除明確顯示元素性質周期性的變化外,門捷列夫還提出三項“假設”[17]:
(1)修正某些元素的公認化合價,并將其調整在合理的位置。
例如當時以為銦(In)是兩價而其原子量為75.6;另外鈾(U或Ur)也一向被認為是三價,原子量為116( 圖3)。但是門捷列夫認為銦應為三價,故原子量須改為113在周期表中也須放在鎘(Cd)與錫(Sn)之間。根據此一修正, 則原在鎘、錫之間的鈾也必須隨之移動。他從氧化物的性質,認為鈾和鉻、鉬、鎢應屬于同一族, 故將之改為六價,假設原子量240而移到第六族(圖4)。后人的研究證明這些假設都是正確的。
(2)修正某些元素的公認原子量,以符合周期性。
例如當時公認的原子量是金(Au) 197 ,鋨(Os)199 ,銥(Ir) 198 ,鉑(Pt)197.4 (圖3)。但門捷列夫從周期性認為其順序應是鋨、銥、鉑、金,原子量也應調整為195、197、198、199 (圖4)。后之實驗雖未獲近似的原子量,但順序卻完全符合假設:鋨(190.2)、銥(193.1)、鉑(195.2)、金(197.2)。
(3)在周期表中留下多個空位,預期將有尚未發現的元素,并預言其性質。
雖然預言并非完全正確。例如原子量146的“類鈮”(eka-niobium) 并不存在,原子量100的“類錳”(eka-manganese)乃1937年發現之人工放射元素鎝(Tc,或稱锝),原子量98。但“類鋁”即鎵(Ga)于1875年發現,“類硼”即鈧(Sc)于1879年發現,“類錫”即鍺(Ge)于1886年發現。后三者所表現的性質,幾乎和門捷列夫假設的完全一致。
由此可知,門捷列夫是經過“細心搜求事實”,逐次修訂后才“大膽提出假設”。例如1868年他已有六行直式依原子量排列為周期表的雛形,鈾的原子量到1871年的論文里才從當時公認的116改為他假設的240,而后來的公認值為238。都可說明并非1869年之某“一天”就想出來的,而所謂“偉大發現的一天”之說[18]可疑。從隨后其他化學家的實驗結果,證實了他的許多假設,而鞏固了對元素有周期性變化的認識。至1913年后科學家證明許多化學元素有同位素之存在,爾后發現元素之性質實乃隨原子序呈周期性變化①,皆是“再細心求實證”階段。因此可以說明“細心搜求事實,大膽提出假設,再細心求實證”三階段科學方法的正確性。
四 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或許他認為從事“治學”的人應已充分了解、掌握相關問題的背景資料,無庸再提,胡適后來省去了“細心搜求事實”,又回到簡化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他在1928年寫的《治學的方法與材料》里說:
科學的方法,說起來其實很簡單,只不過是“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在應用上,科學的方法只不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19]兩年后他的《介紹我自己的思想》文中又說:
科學精神在于尋求事實,尋求真理。科學態度在于撇開成見,擱起感情,只認得事實,只跟著證據走。科學方法只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沒有證據,只可懸而不斷,證據不夠,只可做假說,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后,方才奉為定論。[20]
胡適在北京大學文學院長(1931年起)任內,曾與人合授“科學概論”一課。他的第一講“科學方法引論”里也說:
科學方法的要點,只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 科學方法只是“假設”(Hypothesis)與“證實”(Verification)的符合。
假設不妨大膽,但必須細心尋求證據,來試驗所立假設是能成立。凡不曾證實的 假設都只是待證的,不能認作定理。[21]
但他又將1919年介紹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思想時所提的五個階段[22]當作科學方法的“五步”:
(1)問題的發生;
(2)疑難的認定;
(3)假設幾個可能的解答;
(4)決定一個最滿意的解答;
(5)證實這個解答是最滿意的。
其中(1)(2)兩步不就是“假設”的前提——搜集事實而察知問題之所在嗎?
20年后,1952年12月1日胡適在臺灣大學講“治學方法”的第一講,還是以“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為“講治學方法的一種很簡單扼要的話”[23]。1959年7月16日在夏威夷大學公開演講“杜威在中國”時仍說:“科學方法的精神就在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24] 11月29日講“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他也是用“拿證據來”講“科學精神”,與“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講“科學方法”[25]。但同年7月7日的第三屆東西哲學家會議中發表“中國哲學里的科學精神與方法”時指出那些專心盡力研究經典大書的人,“必須懂得要有證據才可以懷疑,更要有證據才可以解決懷疑”①[26, 27],又強調若要懷疑與假設,須先有證據,解決問題更須有證據。
然而真能領悟其理的人,恐也不多。依著名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費孝通(1910—2005)的回憶,美國芝加哥大學帕克(Robert E. Park,1864—1944)教授1932年在燕京大學教學時,“用具體例子說明從具體生活中看到的生動事實要經過分析和歸類,進一步去理解其意義。他鼓勵大家要大膽提出假設,然后再用觀察到的生活事實來肯定或否定這些假設”[28]。費孝通說:
我們聽了帕克老師開門見山的第一堂課,覺得大有道理和正中下懷,具有聞所未聞的新鮮感。其實這種實證主義的科學方法論,我們在五四運動時早已由胡適等人傳入了中國。……我們這批大學生應當早就聽過這些“科學方法論”,但是不幸的是這種其實巳是“老生常談”,我們在從帕克老師口上聽到時還是那樣激動。這說明這套話并沒有進入我們這批學生的頭腦里,被讀死書、死讀書的傳統卡住了。帕克老師把這個障礙給踢開了,把我們的腦門打開了,老話變新變活了。這一變就把我們這批學生帶入了一個新的境界。以我個人來說,不能不承認這句話為我這一生的學術經歷
開出了一條新路子。[28]
19世紀80年代帕克就讀美國密歇根大學時深受杜威的影響,轉入哲學系,1887年畢業后工作多年,1904年獲德國海德堡大學社會學博士②。可以說與胡適先后同門,所傳授之方法亦一。然只有帕克講的能為費孝通接受,當時一般人感覺“遠來的和尚會念經”,或許是原因之一吧。
但是仍有大師級的科學家是服膺這兩句話的。如名揚國際的物理學家吳健雄(1912—1997)1962年2月23日下午在臺灣大學講“對等律”,據胡頌平的記載:
她先從空間與時間講起,再談起左右的觀念在自然律中是不存在的。后來講到楊振寧、李政道兩人當時推翻了物理學上基本的對等定律的時候,好像在一座漆黑的大房子之中,知道有一個地方可以出去,但不曉得從什么地方出去,于是她怎樣的把它驗證出來。她一邊講演,一邊用幻燈片來解釋。說她當時差不多有幾個星期睡不著,終于把它實驗出來。最后說:“科學不是靜的,是動的,而是永遠不停地在動的;要有勇氣去懷疑已成立的學說,進而去求證。”就是胡院長說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29]
五 勤、謹、和、緩
胡適于20世紀30年代又用過《三朝名臣言行錄》中北宋人李若谷對劉安世等人說的“勤、謹、和、緩”四個為官之道[30]講治學方法。1943年5月30日致王重民(1903—1975)的信里說:
勤,謹,和,緩,我十年前曾借用此四字來講治學方法。勤即是來書說的“眼勤手勤”,此是治學成敗第一關頭。凡能勤的,無論識小識大,都可有所成就。謹即是不茍且,一點一筆不放過,一絲一毫不潦草。舉一例,立一證,下一結論,都不茍且,即謹,即是慎。“和”字,我講作心平氣和,即是“武斷”的反面,亦即是“盛氣凌人”的反面。進一步看,即是虛心體察,平心考查一切不中吾意的主張,一切反對我或不利于我的事實和證據。拋棄成見,服從證據,舍己從人,和之至也。……“緩”字在治學方法上十分重要。其意義只是從容研究,莫匆遽下結論。凡證據不充分時,姑且涼涼去,姑且“懸而不斷”。……此事似容易而實最難。科學史上最有名的故事是達爾文得了他的生物演變的通則之后,幾十年中繼續搜求材料,積聚證例,自以為不滿意,不敢發表他的結論。[31]
淺見以為“細心搜求事實”和“再細心求實證”都是“勤”和“謹”,門捷列夫的63張元素卡片就是“勤”和“謹”,而“細心求證”也是“和”。“緩”則是等證據充足后方下結論之意,亦即言必有據,不可夸張。門捷列夫以兩年時間(1869—1871)寫成的長論文也是例證。
后來胡適于1952年 12月5日在臺灣大學講“治學方法”的第二講“方法的自覺”時[32] 又說明要養成“自覺”的習慣──時時刻刻自己檢討自己,也說“要嚴格的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更強調他思想的演進,他說:
從前我們講治學方法,講歸納法,演繹法;后來年紀老一點了,才曉得做學問有成績沒有,并不在于讀了邏輯學沒有,而在于有沒有養成“勤、謹、和、緩”的良好習慣。[32]
他解釋了“勤、謹、和、緩”的意義,并強調:
做學問要能夠養成“勤、謹、和、緩”的良好習慣;有了好習慣,當然就有好的方法,好的結果。[32]
同年12月27日他在臺東講“中學生的修養與擇業”時也說:
“勤謹和緩”這四個字,大家稱為做官秘訣,我把它看作做人、做事、做學問的秘訣。[33]
這當然也是他治學的科學方法與態度,唯一般人較少言及。
著名的天文學與科學史家席澤宗(1927—2008)晚年時曾說:
我個人十分推崇胡適所說的“勤、謹、和、緩”的做學問的方法、態度。指導研究生時,通過言傳身教,我實際也要求他們這樣做。這四個字原本是宋朝的一位參政(副宰相)做官的秘訣,胡適把它們拿來作為做學問的方法,我覺得很好。這四個字對做學問很重要。勤,就是不偷懶,要下苦工夫。一個人再有天才、再聰明,如果不勤奮,那就聰明反被聰明誤了。 一般人的智力水平都相差不多,成功的人通常都很勤奮。謹,就是不茍且,不潦草。孔子說"執事敬" 就是這個意思;胡適所說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中的“小心”也是這個意思。和,就是虛心,不固執、不武斷、不動火氣。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說:“科學好像教訓我們:你最好站在事實的面前,像一個小孩子一樣;要拋棄一切先入的成見,要謙虛地跟著事實走,不管它帶你到什么危險的境地去。”這就是和。緩,就是不著急,不輕易下結論,不輕易發表。凡是證據不充分或是自己不滿意的東西,都可以“冷處理”“擱一擱”。達爾文的進化論擱了 20年才發表,就是“緩”的一個典型。胡適認為,“緩”字最重要,如果不能“緩”,也就不肯“謹”,不肯“勤”,不肯“和”了。現在的中國,整個社會風氣很浮躁,更需要“緩”。[34]
筆者認識席澤宗,知道他的確是如此做學問。他在自傳中引用胡適的話,直言無諱,也是有感而發了。
六 討論
胡適的科學治學方法曾因政治因素在某一時期遭受許多的抨擊與謾罵,乃眾所周知,毋需重提。但因他省略了“細心搜求事實”這一前提,只一再宣揚“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也招致許多誤解,例如耿云志在1979年時說:
胡適概括他的治學方法叫做“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他的根本謬誤是在于,它的公式掩蓋了最重要的前提,即任何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必須是詳細地占有材料。假設必須建立在對大量材料進行研究的基礎上。沒有材料,或材料甚少,或沒有把握足以反映事物本質的材料,在這種情況下作出假設,必然使研究工作陷入主觀唯心主義,最后得出不合實際的結論。[35]惟又說:
胡適在另外的場合也講過“細心的搜求事實”等類的話,但都不是在講科學方法的情況下說的,凡是專講科學方法的文章,如《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治學的材料與方法》《介紹我自己的思想》等等,他都明白地強調,科學方法只是十個大字,“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而根本不提占有材料和研究材料的問題。[35]
竊以為,這是因為他寫該文時限于環境,只有《胡適文存》可供參考,未能見到上文之其它信息,故即使對胡適的批評稍有偏差,亦無可厚非。
有些人從哲學的方法學(methodology)觀點評論“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意義和作用。殷海光(1919—1969)1958年曾說:
如果從它對于社會思想效應來觀察,那么“大膽假設”與“小心求證”對于中國社會簡直是“對癥下藥”,利莫大焉。[36, 37]
這是因他認為中國沒有“為知識而知識”的致知傳統,也缺少正確懷疑傳統。提倡“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則能產生“重致知”和“發揮適度的懷疑心理”之效應,也能持有“不信一切沒有證據的話”的態度。看起來,這不就是采用科學方法的處世方式嗎?
但又有一些人,在文字上挑剔胡適的“科學方法”,例如林毓生說:
胡適說我們如要學習科學,首要之務是要學習科學方法。照他說,科學方法的精義可由十個大字來說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我們要認清,胡適倡導科學方法的方式與商人做廣告,政客搞宣傳,在思想層次上沒有多大區別。……然而,科學方法是不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呢?科學的發展是不是要依靠“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呢?在科學研究的時候,工作人員是不是要在假設上看誰膽子大,誰就容易有成績?你的膽子大,然而我的膽子比你還大,所以我的假設就容易導使重大的科學發現?……胡適談“大膽假設”的時候,只注重提倡懷疑精神,以為懷疑精神是科學的神髓(這是對科學很大的誤解),故提“大膽”兩字以示醒目,他卻沒有仔細研究科學假設的性質到底如何?因為科學假設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錯的;但都必須是夠資格的假設(competent hypothesis)。但經他提出“大膽”兩字,情況就變得混淆了 ,因為這種說法,如不加以限定(qualify), 使人以為越大膽越好,豈知許多大膽的假設,雖然發揮了懷疑的精神,卻并不夠資格成為科學的假設,此種假設是與科學無關的。([38];[39],頁26—27)
實際上,胡適說的“大膽”實是“無畏”的口語(白話),不是要比誰的“膽子大”,也強調了若要懷疑與假設,須先有證據。1959年7月胡適在夏威夷的兩次英文演講中都提到“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在夏威夷大學所講“杜威在中國”中說:And the scientific method is only “a boldness to suggest hypothesis coupled with a meticulous care in seeking proof and verification”[24, 40]。
故知他沒弄清楚胡適用詞的原意,只從字面上來批評。由前述門捷列夫的周期表之例可知,胡適的說法并沒錯,絕不是什么“商人做廣告,政客搞宣傳”。林毓生還說:
胡適終生所宣揚的科學方法,雖然形式上包括歸納法與演繹法,但實際上,他十分強調的只是歸納法,再加上一點心理上或精神上的大膽(他認為那樣的心態便能在科學方法中扮演假設,演繹的功能──實際上“大膽”與演繹推理并無關系)。[41]
其實,胡適并未強調歸納法(見前文),顯然他并不了解胡適的科學方法本意是什么。他也不甚了解科學及科學史,蓋他又說:
另外還有一點需要特別說明:科學史上有不少重大的發現與“頑固”的關系很大,而不是與大膽的懷疑有關。有的科學家硬是特別信服他的老師的學說或一般人已經接受的理論。他覺得這種理論底蘊涵比別人所發現的還要豐富,還要更有意義。從這種觀點出發,有時會獲得極為重大的發現。例如,在一九一二年數學家Max von Laue對結晶體使X光折射(diffraction of x-rays by crystals)的發現,便是對已經接受的,有關結晶體與X光的理論,更具體的信服的結果。( [39],頁29—30;[42] )
然這一說法完全不合實際,因為[43]:
(1)馮勞厄(Max von Laue,1879—1960)是物理學家,不是數學家。
(2)馮勞厄對于傳統的光學、熱力學和當時新興的相對論、輻射理論都有深厚的了解與研究。
(3)晶體格子的假說觀念當時尚未獲得證實,1895年發現的X射線(或稱X光)性質亦未確定。
(4)馮勞厄推想如果X射線是波長很短的光波,則射向結晶體時,很可能穿過晶體格子中微小孔隙發生繞射(diffraction,或譯為衍射,但非“折射”)①。但他的資深同事包括著名的索莫菲(A. Sommerfeld,1868—1951)和1911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偉恩(W. Wien,1864—1928)最初都不置信。
(5)1912年的實驗結果發現微小的硫酸銅晶體格子確能使短波長的X光發生繞射。由此不僅確認了X射線的波動性,也證明了晶體的晶格結構假說之正確性。因此,馮勞厄獲得了1914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淺見以為,馮勞厄的這項成就也符合“細心搜求事實,大膽提出假設,再細心求實證”——胡適所說的“三階段”過程。是門氏周期表外另一正確的科學研究方法之佳例,而與馮勞厄是否“頑固”無關。
七 結論
新文化運動提倡之“科學”迄今已逾百年,“科學”方法與態度猶未為人認識清楚。拙見以為當年胡適所言“細心搜求事實,大膽提出假設,再細心求實證”三階段是恰切、實用的科學方法,可泛用于一般情況。但不宜簡化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以免有所誤解,或藉此在文字上做些糾纏。他說的“勤、謹、和、緩”也是符合上述的科學方法與正確態度。科學史里150年前門捷列夫研究發展出來的周期表,與后人之證明和改進,以及一百多年前馮勞厄發現X射線對晶體會發生的繞射現象,均可說明胡適所言之正確性。
參考文獻
[1]簡明海. 五四意識在臺灣[M]. 香港: 開源書局, 臺北: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2019.
[2]陳獨秀. 敬告青年[J]. 青年雜志, 1915, 1(1): 13—18.
[3]陳獨秀. 本志罪案之答辯書[J]. 新青年, 1919, 6(1): 16—17.
[4]任鴻雋. 發刊詞[J]. 科學, 1915, 1(1): 3—4.
[5]任鴻雋. 說中國無科學之原因[J]. 科學, 1915, 1(1): 5—10.
[6]任鴻雋. 科學方法講義[J]. 科學, 1919, 4(11): 1035—1051.
[7]耿云志. 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12冊)[M]. 合肥: 黃山書社, 1994. 3—9.
[8]胡適. 清代漢學家的科學方法[J]. 北京大學月刊, 1919, 1(5): 23—37.
[9]胡適. 清代漢學家的科學方法[J]. 北京大學月刊, 1920, 1(7): 49—54.
[10]胡適. 清代漢學家的科學方法[J]. 北京大學月刊, 1922, 1(9): 21—23.
[11]胡適. 胡適文存[M]. 臺北: 遠東圖書公司, 1953. 383—412.
[12]胡適. 通訊——我的歧路[J]. 努力周報, 1922, (7): 3—4.
[13] B. Jaffe. Crucibles: The Story of Chemistry(4th Ed)[M].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76. 150—163.
[14] A. J. Idh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emistry[M].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84. 231—251.
[15] W. H. Brock. The Norton History of Chemistry[M]. W. W. Norton & Company, 1993. 311—326.
[16] D. Mendeleljeff. Die periodische Gesetzm?fsigkeit der chemischen Elemente. (Aus dem Russischen von Felix Wreden)[J]. Justus Liebig Annalen der Chemie und Pharmacie, 1872, VIII Supplementbandes: s.133—229.
[17]劉廣定. 門得列夫周期表問世一百二十年[J]. 科學月刊, 1989, 20(3): 197—204.
[18]劉則淵. 紀念門捷列夫元素周期表150周年──凱德洛夫《偉大發現的一天》中譯本撮要[J]. 科學文化評論,2019, 16(1): 5—21.
[19]胡適. 胡適文存(第三集,第二卷) [M].臺北: 遠東圖書公司, 1953. 143—156.
[20]胡適. 胡適文存(第四集,第四卷) [M].臺北: 遠東圖書公司, 1953. 607—624.
[21]耿云志. 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9冊) [M].合肥: 黃山書社, 1994. 533—538.
[22]胡適. 胡適文存(第一集,第二卷) [M]. 臺北: 遠東圖書公司, 1953. 320—329.
[23]胡頌平.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六冊) [M]. 臺北: 聯經出版公司, 1984. 2243 .
[24]胡適. 杜威在中國[J]. 夏道平譯. 自由中國, 1959, 21(4): 8—11.
[25]胡頌平.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八冊) [M]. 臺北: 聯經出版公司, 1984. 3076—3081.
[26]胡適. 中國哲學里的科學精神與方法[J]. 徐高阮譯. 新時代, 1964, 4(8): 3—7;4 (9): 11—16.
[27] Hu Shih. The Scientific Spirit and Method in Chinese Philosophy[A]. 胡適英文文存[C]. 臺北: 遠流出版公司, 1995. 1553.
[28]費孝通. 師承·補課·治學[M]. 北京: 三聯書店, 2002. 214.
[29]胡頌平. 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M]. 臺北: 聯經出版公司, 1984. 311.
[30]三朝名臣言行錄(朱熹輯錄)[M]. 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6. 卷第十二之三, 頁二十九下.
[31]胡適王重民先生往來書信集[M]. 北京: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09. 81—84.
[32]胡適演講集 (一)[M]. 臺北: 遠流出版公司, 1986. 14—27.
[33]胡適演講集 (二)[M]. 臺北: 遠流出版公司, 1986. 199—208.
[34]席澤宗. 席澤宗口述自傳[M]. 長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1. 241.
[35]耿云志. 胡適與五西時期的新文化運動[J]. 歷史研究, 1979, (5): 59—79.
[36]殷海光. 論“大膽假設. 小心求證”[J]. 祖國周刊, 1958, 23(8, 9).
[37]殷海光. 殷海光全集(卷12)[M]. 臺北: 臺灣大學出版社, 2013. 276—307.
[38]林毓生. 思想與人物[M]. 臺北: 聯經出版公司, 1983. 19—20.
[39]林毓生. 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增訂本)[M]. 北京: 三聯書店, 2011. 26—27.
[40] Hu Shih. John Dewey in China[A]. 胡適英文文存[C]. 臺北: 遠流出版公司, 1995. 1523.
[41]林毓生. 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M].臺北: 聯經出版公司, 1989. 297.
[42]林毓生. 思想與人物[M].臺北: 聯經出版公司, 1983. 24.
[43] Nobel Lectures, Physics, 1901—1921[M].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1998. 341—359.
On the Scientific Method of Hu Shi
LIU Kwang-Ting
Abstract: Taking the periodic table of chemical elements invented by Mendeleev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correctness of the three-stage scientific method proposed by Hu Shi in the early years, “Searching for information carefully, putting forward hypotheses boldly, and seeking proof with meticulous care”. But it is misleading to simplify it into “bold assumptions and careful verification”. What he later emphasized “diligence, discreetness, gentleness and gradualness” were also consistent with his scientific method and correct attitude mentioned above. Some other peoples different opinions we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scientific method, research attitude, Hu Shi, Mendeleev, von Laue
收稿日期:2020-01-10
作者簡介:劉廣定,1938年生,臺灣大學化學系名譽教授。Email: ktliu@ntu.edu.tw。
① 早年的周期表中元素乃依“原子量”排列,而現代的周期表乃依1913年才發現的元素“原子序”排列,但“周期性”觀念在化學發展史上極為重要。
① 至少在臺灣地區是如此,參見[1]。
① 原載于《北京大學月刊》,1920年又刊于《科學》(1920年第5卷第2期:125—136頁;第5卷第3期:221—228頁)。
② 1922年6月18日第7號《努力周報》的“通訊”,胡適以《我的歧路》為題答復梅光迪、孫伏廬、常乃惪三位先生的來信。又收入《胡適文存》第二集,第三卷,但臺北“遠東圖書公司”版未收。
① Chemogenesis, Internet Database of Periodic Tables.
① 例如門氏周期表中原子量較小的鎳(58.693),按照化學性質應該排在原子量較大的鈷(58.933)之后。莫賽萊(Henry Moseley, 1887—1915)1913年由X射線光譜提出“原子序”的觀念,證明鈷和鎳的“原子序”分別為27和28,原子量順序顛倒是因所含質量不同的同位素數目不同所造成。此后,周期表中元素咸依原子序排列。
① 這句話的原文是:they had to learn to doubt with evidence and to resolve doubt with evidence.
② 見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E._Park#Education。
① 繞射(衍射)與折射(reflection)是完全不同的光學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