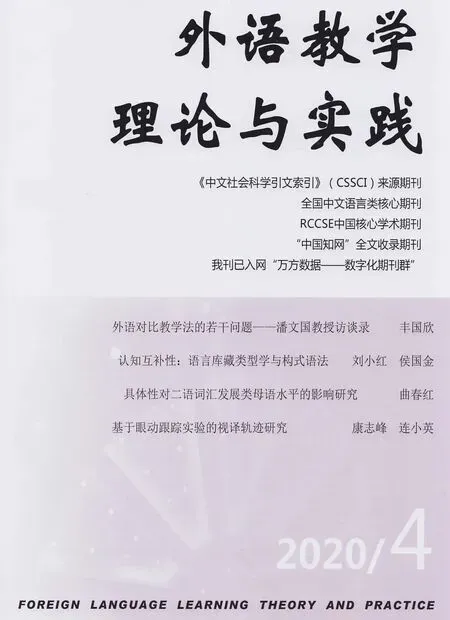認知互補性:語言庫藏類型學與構式語法*
劉小紅 侯國金
南京大學/云南經濟管理學院 華僑大學
提 要:探討了語言庫藏類型學與構式語法的關系。通過簡介語言庫藏類型學與構式語法,對比二者在研究目標、研究對象、語用性、功能性、獨立性、跨語言性、形義配對、可解釋性等層面的相似點和不同點,發現二者最好作為認知語言學陣營內部的姊妹范型,可互補互助直至更完好地解釋語言系統的“雙贏”前景。
1. 語言庫藏類型學掠影
何為“語言庫藏類型學”?“語言庫藏類型學”(linguistic inventory typology,下稱LIT)是劉丹青先生(2011,2012a)倡設的語言類型學分支或研究視角。總體上,LIT注重語言中的形式手段“庫藏”對語言類型特點的制約,認為一種語言的庫藏中所擁有的語言形式手段及其語法屬性會對該語言的類型特點,尤其是該語言的形義關系類型,產生重大影響。
LIT最重要的核心概念是“語言庫藏(linguistic inventory)、顯赫范疇(mighty category)”。“語言庫藏、語言庫藏清單”是指“特定語言系統或某一層級子系統所擁有的語言手段的總和,包括語音及韻律要素、詞庫、形態手段,句法手段,包括虛詞、句法位置等”(劉丹青,2011:289),尤其包括語法庫藏。語言不同,“庫藏”不同。所謂“顯赫范疇”,簡單地說,是在一種語言中既凸顯又強勢的范疇,如漢語的話題優先(topic-priority)特點及體貌(aspect)特點,英語的時態特點,法語、俄語等的語法“性”(gender)特點,不少西方語言的冠詞特點。假如某種范疇語義由語法化程度高或句法功能強大的形式手段表達,并且成為該手段所表達的核心(原型)語義,該范疇便成為該語言中“既凸顯又強大的”(prominent and powerful)范疇,即“顯赫范疇”(劉丹青,2012a:292)。顯赫(的)范疇其共同特點在于:一是語法化程度高、句法功能強、使用頻率高;二是它們除了用于該范疇本身的原型功能外,都能表達其他相鄰甚至有一定距離的語義語用范疇,這些范疇在很多甚至大部分其他語言里則是由其他范疇的語法手段擔當,究其動因,“物盡其用原則”使然(劉丹青,2014:387)。
2. 構式語法一瞥
何為“構式語法”?作為認知語言學研究的一種全新理論范式,“構式語法”(construction grammar,下稱CG)在傳統和生成語言學的反思和批評中應運而生。
“構式”是CG最重要的術語,存在多種定義。(1)根據Goldberg(1995:1),“構式”(construction)是任何形義配對體(form-meaning correspondence)(另見侯國金,2015:98),包括語素(如anti-)、詞(如and)等等,其意義特性不能從其構成成分中推導出來,即構式義獨立于其構成成分,具有不可預測性。受到索緒爾符號觀的影響,Langacker設立了“象征單位”(symbolic unit)、“音位單位”(phonological unit)和“語義單位”(semantic unit)。他將音位單位和語義單位的結合體稱為“象征單位”,且認為任何語言表達式:詞素、詞、短語、句子、語篇,都是“象征單位”。在Langacker看來,假如一個音位配對體叫做一個“象征單位”,那么由兩個(以上)象征單位所形成的結構就稱之為“構式”。Croft(2001:17)說,“構式是約定俗成的形義配對的復雜句法單位。從語詞、詞組、句法到語義規則,都可表征為‘構式’”。出于對喬姆斯基轉換生成語法(TG)學派模塊論的懷疑,認知語言學學者們認為大多習語具有規約性,不能單從句法或語義角度做出細致分解,例如英語習語“let alone”(何況)、“kick the bucket”(一命嗚呼)、“by and large”(大體上)等。CG始于對“習語”的解釋而閃亮登場,并能擴展用來表征一切句法結構,如“The X-er, the Y-er.”(越是X就越Y)和“A is to B as X is to Y”(A之于B猶如X之于Y),等等。隨著理論的發展,有些學者注意到句式的習語性是一個連續統,只有程度的差異,因而認為CG應將所有句法結構都納入其研究,并將所關注的構式層面向上下拓展,包括比“句式”更小和更大的單位,如語素、單詞和小句。而在實際操作中,CG學界的主要研究均猬集于兩個(以上)單詞(語符)構成的語法結構或句型,如致使構式、動結構式、雙及物構式等,鮮有涉及小到詞素、大至超句的語言層面(參見侯國金,2013:5)。
3. 語言庫藏類型學與構式語法的相似點
綜觀語言庫藏類型學論斷和構式語法觀點,本文從宏觀至微觀分析二者的相同點,具體維度如下:研究目標、研究對象、語用性和功能性等。
首先,論基本目標,LIT和CG都試圖研究整個語言系統。根據上文的語言庫藏定義:“庫藏”指語言手段及其用法之總和。由此可見,LIT覆蓋語言的所有事實,形成一種涉及整個語法乃至整個語言的研究視角和框架。與LIT類似,CG將一切語言單位視為“構式、象征單位”,包括語言的不同層面,如語素、單詞、短語、習語和分句等,強調將句法、語義、語用等因素緊密結合起來對“構式”進行系統分析,從而對整個語言系統做出全面且統一的論述。
其次,論關注對象,LIT和CG二者都關注語言學的根本問題,即形義關系。LIT認為,語言形式庫藏對語義范疇有很強大的制約(反作用力)。跨語言視角下的形義關系,不是傳統設想的那么簡單,即普遍性的語義范疇在不同語言中用不同的形式手段表征。實際上是形式庫藏的存在及其所在范疇的顯赫程度影響著人類交際對語義范疇(而不只是對形式手段)的選擇,特定語種的顯赫范疇常常強勢地擴展其語義域,表達很多在其他語言中歸屬其他范疇的語義,在語言庫藏(“物盡其用原則”)的驅動下呈現出“越常用,就越顯赫;越顯赫,就越常用”的“雙向馬太效應”(bothway Matthew effect),使得語言之間常常存在跨范疇對應(trans-categorical correspondence)(或巧合)(劉丹青,2017a:1;2017b)。
而根據CG,語言由“構式”網絡構成,構式具有獨立性和網絡/系統的關聯性,如近義性、反義性、傳承/繼承性,等等。CG強調形義匹配,認為語言中所有形式,從最小的語素到句子結構,都是形義或形功配對體。一個構式可能由兩個(以上)子構式組成,構式中的子構式因處于不同句法空位而處于不同構式層級及其不同構式節點,其形式、角色/作用、語音特點(如輕重)、意義(包括含義)、功能(含交際功能、修辭功能等),也就各不相同。傳統語法的一個選擇問句在CG這里就是一個選擇問句構式,內包多個子構式、孫構式,如名詞短語構式、動詞短語構式(動補[構]式、動結[構]式、連動[構]式等)、形容詞短語構式、A或B構式,等等。
再次,論“語用性”(pragmaticity),LIT和CG都有“語用”,但都不是全面徹底的語用。LIT提出庫藏的語用性,在定義上可見“語法庫藏是用來表達各種語義范疇或發揮語用功能的”,“顯赫范疇的顯著特征之一是能擴展其語義語用用途的范疇”之類的表述(劉丹青,2013:194)。在具體研究中,劉先生以不同語言中的指示詞為例,論證了某些語法手段會擴展其原型用途。如漢語指示詞“這”,可表示類指,還可標記話題或弱化動詞的謂詞性。英語定冠詞the作為強制性專用有定標記,有很多與定指有關的話語功能——情景作用、語篇作用、示蹤作用、認同作用。但因為所有這些作用既不需要推理也不需語境,故本質上都是缺乏語用精神的。CG研究構式時也常提到“語用”二字,而其實際分析遠非徹底,屬姑且用之(甚至姑且言之)的“權宜語用”,“不是徹底的語用”(侯國金,2013:9)。不論是在形式還是意義上,CG論著者筆下的構式多半是脫離真實語境的“純理”或默認構式,如習語構式“monkey business”(兒戲/胡鬧),“Easy does it!”(悠著點!),“我去!”“走你!”,其語用前提、語用功能、語用信息都是非語用的,正如董燕萍和梁君英(2002:150)所言,至多算作“常規語用信息”(stereotypical pragmatic message)。其“語用”不是建立在“推理模式”基礎上,一般并不涉及即時/在線語境、認知語用理據、社會語用策略、語用修辭手法使用策略等。
最后,論功能性,LIT和CG都沒有高度重視所研究對象的各種功能。雖然LIT除了關注語義外,同時也考察了語法形式的其他功能,但并不全面。例如,上述的the至少表達四種話語功能,至于用作什么句子成分或實現什么人際功能等,還需要探索。CG眼中的構式是“形義配對體”,而“形義配對體”重在信息內容的交流,形功配對重在相關構式的語法分布(即該構式所作的句子成分)以及所擔當的表意作用。實際上,CG比較看重構式(意)義,比較忽略構式(的語法)功能,遑論可能的“語用”特性,如人際功能、語篇功能、修辭功能等。
4. 語言庫藏類型學與構式語法的差異
如上述,語言庫藏類型學與構式語法在研究目標、研究對象、語用性和功能性等方面存在相似點。然而,二者在獨立性、跨語言性、形義配對、可解釋性等層面側重點不一,詳述如下:
首先,關于獨立性與非獨立性,二者存在差異。LIT傾向于非獨立性,CG則兼顧獨立性和非獨立性。在LIT及其顯赫范疇觀看來,所謂的“非獨立性”意味著,對于那些語法化程度高或功能強大的顯赫范疇,他們具有向其他范疇擴張的能力,富有類推性、能產性和使用強制性,且具有該語法形式的原型或核心范疇的地位,還能用來表達與其原型范疇相關而又不同的范疇,表達的范疇在其他語言中可能屬于或趨向毫不相干的其他語義語用范疇。如,話題結構作為漢語的顯赫范疇,可用來表達多種語義范疇,漢語的差比句構式(如例1))就是這一顯赫范疇功能擴張的典型個例。因此,話題結構和差比句在現代漢語中就形成了這樣的一種“顯赫范疇-擴展功能”的關系(劉丹青,2012b:1)。相比而言,其他語言的差比句并沒有體現出與話題結構的關系。CG則認為,語法是一個構式連續體,該連續體的一端是能產性強的構式(如主謂構式和左偏離構式),另一端是相對固定的構式。前者具有概括性和傳承性(參見董燕萍、梁君英,2002:149;侯國金,2015:113),而對于相對固定的“另一端”構式,他們之間具有非轉換性,皆為獨立的個體。如王寅(2011:17)所言,“英語中有些主動態不能轉換成被動態,很多被動態語句也不能轉換成主動態”,又如漢語的“新被字句”構式(如例2)),也不能主動化。
1) 張三高 /大 /強李四一大截。
2) a. 他被聽課了。b. 她被高鐵了。
其次,關于跨語言與非跨語言研究,二者也不盡相同。LIT討論語言庫藏的多語言差異,揭示語言間因庫藏而導致的類型差異,并關注語言庫藏差異中表現出來的語言共性。正如句法結構是比較普遍的語言現象,大凡語言皆有主謂、動賓、定中、狀中、并列等結構,但不同語言的句法結構仍然存在顯赫度的差異,而且構式的形成與擴展同語言的類型特點有密切關系。漢語的受事話題句、動詞拷貝句、話題句等都建立在話題優先的類型基礎上,即使非典型“連”字句的“連XP”已沒有其原有的對比話題性,仍被編碼為這種特殊的對比話題,顯示了話題結構在漢語結構系統中的強勢地位。比較3a-b)(劉丹青,2005:1,4),前者是典型的“連”字句(預設霍恩等級的低端),后者則是非典型“連”字句(無此預設):
3) a. 老王連老鼠肉都敢吃。b. 結婚一年了,感情反而更好,連架也不吵了。
另外,“同一性話題”(identical topics)或名詞性或動詞性重言構式,是話題優先語言的一種典型特征(如例4)),在主語優先語言系統(如英語、法語)里則很難找到對應項(Liu,2004:22;馮梅、侯國金,2020):
4) a.去就去。b.星星還是那個星星,月亮還是那個月亮。
比較而言,CG著重解釋某種語言中所出現的特定句式結構,如漢語的話題結構構式、英語的使動構式,卻無法解釋兩種語言里的某個類似構式之間的差異(參見鄧云華、石毓智,2007:328)。英漢語的雙賓構式就有很大的差別(侯國金,2013:8):假如說英語是單向,即客體從主語向間接賓語移動,如“borrow(from)”和“lend(to)”,那么,漢語則是雙向,除了跟英語雙賓語構式一樣的客體移動方向以外,還可以相反,從間接賓語向主語移動,如“借”組成的句子(例5a))中,客體“車”既可以從間接賓語“我”移向主語“你”(例5b)),也可從主語“你”移向間接賓語“我”(例5c))。CG也無法解釋兩種(以上)語言的詞匯系統,諸如英語具有完備的“全-有-無”三分量化詞匯系統,如“all, not any, no”,漢語的量化詞庫中只有表示“全(全量肯定)”(如“所有”)和“有(部分/存在量)”(如“不是所有”)的詞匯庫藏,而表示“無(全量否定)”的全量否定詞闕如,需要借助“否定詞+最小量”結構(白鴿、劉丹青,2016:26)。我們說CG“著重解釋某種語言中所出現的特定句式結構”,一般不做跨語言研究,并不排除或反對一些CG學者的跨語言異同對比研究(Hoffmann & Trousdale,2013:引言第4頁)。
5) a. 你借我一輛車。b. 什么時候還給我?c. 你不能著急要我還哦!
再次,關于語義與形式,二者有不同的側重。LIT和CG各有所長的領域和視角。LIT不僅注重從語義到形式表現的路線,而且也關注語義語用范疇和形式手段的雙向互動,尤其關注形式手段及其顯赫性的差異對范疇表達的影響,即從以形式到語義語用范疇的視角為出發點——因為庫藏首先是形式手段。具體而言,LIT采用兩種觀察角度:一是從庫藏形式出發觀察語義-語用范疇在不同語言中的語法實現狀況及顯赫度;二是考察哪些語義-語用內容能在大量語言中進入語法庫藏,甚至成為顯赫庫藏,哪些語義-語用內容沒有機會或只在極少語言中得以“入庫”(in(to) inventory),而需要靠庫藏中其他語義-語用內容的表達手段來兼顧。這是LIT跨語言視角的重要基礎。CG最大的亮點則是明確提出構式的意義不能從其組成部分或已有的構式推出,CG關注哪些語義內容在語言中被形式手段凝固下來,從而得到一個構式,即“構式化”(constructionalisation)。(2)所謂“構式化”,指的是“由原先獨立的語言素材構造出一個全新的語法模式或構式”或“對一個既有構式進行重組從而導致越加模糊的結構意義”(Hoffmann & Trousdale,2013,第五章23.3節)。因此,CG偏重于從語義到形式的視角。由此可知,CG所擅長的是整合度高、習語性強、難以分解的結構,為特定語言的構式提供一套特定的句法規則和語義理據解釋。比如“連”字句構式的強調義,其實是得益于該構式的整體構式義(劉丹青,2005:1)。
最后,關于可以解釋的語言現象,二者也不一樣。LIT重點關注語法庫藏,主要包括“形態庫藏類型學、詞類庫藏類型學、句法結構庫藏類型學”。雖然LIT同樣也宣稱適合語音層面(劉丹青,2011:289)并正在進行嘗試性研究,但顯然不易操作。CG為生成語言學提供補充,拓展了語法研究視野,很好地解決了一些語法難題,如詞義歸屬問題、價位循環論證問題、存現句施事-受事問題、動賓和述賓的語義問題、詞類劃分等語法標記問題,也解釋了不同句式產生的社會歷史理據(象似性)。再者,對于LIT而言,并非一切語言現象都適于其分析。例如,關于顯赫范疇的超范疇擴張問題,是顯赫范疇擴張至其他范疇,還是其他范疇進入顯赫范疇,LIT往往三緘其口。對CG來說,也是并非一切語言現象都適于其分析。例如,CG不能充分解釋跨語言的相關構式,并且也只擅長解釋部分句式。對于構式的語義,怎樣確定哪些是基本語義,哪些是通過“轉喻”和/或“隱喻”引申出來的結構意義,似乎還是未知數。
為了更清楚地體現LIT與CG的異同,筆者以表格示之(表1):

表1. 語言庫藏類型學與構式語法的同與異
(3)這里的“隱-轉喻”指的是隱喻或轉喻引申,不是“隱轉喻”(metaphtonymy)的引申。“隱轉喻”是既有隱喻引申又有轉喻引申,如“母機、腦橋、頁腳、劍眉、network、bottleneck、footnote”(黃潔,2008)。
5. 語言庫藏類型學與構式語法的互補
筆者認為,基于共同的目標,即對整個語言系統做出全面且統一的解釋,LIT與CG可達到和諧互補的元科學生態狀態。這是因為:
第一,在對待形義問題上,雖然二者都重視這一根本語言問題,但具有不同的研究出發點。LIT關注形義雙向互動,其出發點是常規語言現象,如復數形態或復數量詞表類指;CG偏重從語義到形式的視角,著重考察非常規構式,如習語構式和修辭構式。Fillmore和Kay等著意研究邊緣構式(如“make do”(湊合著用)),最為突出的便是詞匯語義和標記性構式的研究。LIT認為,“語言的類型特點對構式的存在發展有至關重要的制約作用,而這種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又是超越具體構式的”(劉丹青,2005:11)。我們認為,側重語言的常規或非常規現象,并不能達到研究整個語言系統的總目標,在這里二者可以相互借鑒和補充。
第二,CG的多數原理和概念可以直接被LIT借用(見例15)及其解釋),同樣,LIT的“顯赫范疇”及其擴展功能、邊緣功能和跨語言比較,CG也可借鑒。如果認定英語雙賓構式的原型義表示“傳遞”,即“X使得Y接受Z”,如6a)所示;6b)(原文源于董燕萍、梁君英,2002:145)在6a)“傳遞”義的基礎上,增加了“瞬間引起的強烈移動”,相當于“gave me a pillow by tossing”(通過甩的動作給予),6b)漢譯中“甩給”的補語小品詞“給”語法化地保留了6a)的動詞“給”的部分特征——那么,該新增義是否為原型義的擴展版,而英語雙賓構式是否可認定為“顯赫構式”,英語雙賓構式與其他語言類似構式有何區別和聯系,等等,也能如此“順藤摸瓜”“依葫蘆畫瓢”地研究。
6) a. Patgaveme a pillow. (帕特給我一個枕頭。)
b. Pattossedme a pillow. (帕特甩給我一個枕頭。)
第三,有趣的是,某些語言現象可用LIT解釋,某些則可用CG解釋(甚至還可運用其他語言學理論),或者是互相借鑒地解釋同一語言現象。例如,在研究詞類方面,LIT以量詞為個案研究對象,考察哪些語言存在量詞,以及量詞的顯赫度問題。如英語沒有漢語那樣的個體量詞,而是用數詞直接限制名詞。而與官方普通話相比,粵語等方言則是量詞強勢的方言。在CG的框架下,詞類范疇被認為是“從語言使用中涌現出來的圖式性范疇,它們是形式與意義的結合體,語言表達式所屬的詞類范疇與其所在的語法構式不可分割”(高航、張鳳,2008:1)。因此,根據所在的語法構式,一個形式可能屬于多個詞類范疇。如water大體被當作名詞,而當它用在“waterthe flower”((用水)澆花)這一語法構式時,water已轉化為動詞,故(其)詞類具有靈活性。同理,在CG視角下,根據不同的使用現象,量詞也可轉化為其他詞類,如“aroundof drinks”(一輪飲料,斜體詞為量詞),“roundthe clock”(晝夜不停地工作(環繞鐘表,從一點做到十二點),動詞),“aroundpond”(圓池子,形容詞),“walkroundandround”(轉來轉去,副詞),“strollroundthe corner”(溜達繞過街角,介詞)。顯而易見,LIT和CG從不同的視角分析了詞類(量詞),如果將二者結合,既有跨語言的對比分析,也含某一特定語言的近距離考察,詞類的語言學分析將趨近完整。
LIT是跨學科的新范型,對語言類型學、認知語言學、詞匯學、語義學、句法學等進行了旁征博引般的借用,既能做形而上的元語言學研究,也能做形而下的具體字詞句研究,非常適合話題顯赫、連動顯赫、體貌顯赫、含蓄顯赫的東方語言。當然LIT作為新型范式,也有自身的缺點。首先,LIT沒有澄清和認知語言學的一切關系。考慮到其自知的認知性(見表1),我們認為最好把LIT納入認知語言學,使之成為和CG并列的范型。CG是開放包容性的范式,自身擁有眾多路徑和流派(侯國金,2015:115-131),除了“四大流派”(4)“統一構式語法”(unification construction grammar,UC(x)G),“認知語法”(cognitive grammar,CG),“激進構式語法”(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RCG),“認知構式語法”(cognitive construction grammar,CCxG)。以外,還有“語核驅動的短語結構語法”(head-driven phrase structure grammar,Pollard & Sag,1994),“動變/動態構式語法”(fluid construction grammar,Steels & de Beule,2006),“體驗構式語法”(embodied construction grammar,S?gaard,2006),“語符構式語法”(sign-based construction grammar,Boas & Sag,2012),等等。
其次,LIT對跨語言研究所跨語言的數量和屬性的限制不夠。假如著力于LIT的跨語言對比,漢語的某個庫藏和什么語言的庫藏進行對比比較合適呢?漢英?漢法?漢韓?再次,LIT忽略隱喻和轉喻的作用,對構式語法及其所屬的認知語言學的繼承多于所承認的程度,批評也多于適度。例如批評CG過于頻繁地把各種語義擴展歸結于隱喻或轉喻引申,而我們知道CG并沒有把一切引申歸入隱喻或轉喻引申,而是說隱喻化或轉喻化思維是構式的語用法拓展的常見機制。如例6b)的“Pat tossed me a pillow.”,不僅是給予構式,還是轉喻構式,即以形象的toss方式轉喻了“給予”,toss(甩)改成kick(踢)、throw(扔)、head(頭球攻門(一樣)頂)、hand((用手)遞(給))、mail(郵寄)、express(快遞)、shunfeng(順豐快遞)、buy(買(給))等,都是如此。若讓LIT解釋,就要說該例是顯赫的給予結構擴張,然而,如何擴張?為什么不能擴張成table(桌子)、chair(椅子)、prototype(原型)、sing(唱)、eat(吃)等?好像非得借用轉喻機制不行。
CG是歷史上最根本的(fundamental)語言描述的工具(Michaelis,2008:73;另見侯國金,2015:163-186,408-415)。CG有很多優點和優勢,它“拓寬了語法研究的視野”,“為喬姆斯基語言學等語言學研究提供了補充”(侯國金,2014:34-38;2015:163-186),很適合作為“高語境語言”(high-context language)的漢語的結構分析,甚至能夠令人信服地解釋漢語的一些老大難問題,諸如相異主位近義句(如例7)),“有+光桿名詞”構式(如例8)),三價差比句構式(如例1)),近義存現句構式(如例9)),“吃N”構式(如例10)),還有Yuan(2017:9-97;121-197)闡釋的所謂“雙價名詞”構式(如例11)),“單價名詞”構式(如例12)),“隱性動詞”構式(如例13)的“提出”),相異話題化近義句(如例14)),以及Liu(2004)、馮梅、侯國金(2020)討論的同一性話題構式(重言構式)(如例4),見§4),等等。不過,CG也有缺點,例如CG內部“派別林立”,各家“觀點不一”,有時“觀點不清”,有時“過分強調構式的單層面性和獨立性”,有時“過分強調語法系統的開放性”,有時“過度夸大語法和語義的關聯性”,“無法解釋一個具體實體構式的跨語言差異”,“構式語法的原則有過于絕對之嫌”,其語用為“姑且用之的‘權且語用’”(侯國金,2013;2015:189-240;另見鄧云華、石毓智,2007)。正是因為CG的包容性和開放性,我們才得以構擬“詞匯-構式語用學”的框架(侯國金,2015):夯實以語用支配原則、詞匯和構式的“七原則”、語用制約/壓制假說、構式網絡語用觀、CG的互補觀等,實現了“三個學科過渡”(侯國金,2015:241-408)。
7) a. 雞不吃了。b. 不吃雞了。c. 我不吃雞了。d. 不吃雞了,我。
8) (某某)有錢/有風度。
9) a. 門口坐著(一個)人。b. 一個人坐在門口。c. 一鍋飯吃八個人。d. 八個人吃一鍋飯。
10) (某某)吃水餃 /吃盒飯 /吃食堂/吃父母/吃文化。
11) (張三對李四有)敵意/好感。
12) (這個人)性子(急)。
13) (這是)小王(提出)的意見。
14) a.錢包呢,我被人偷過好幾回。b.我呢,錢包被人偷過好幾回。
綜上,對人類語言的全面認識,既需LIT的宏觀對比,也要CG的微觀分析,也即需要二者的良好協作。請看:
15) a. Ifoundmywaytothe exit. (我找到出口(的路)了。)
b. Iliedmywaythroughthe interview. (采訪中我一路撒謊。)
c. The government tried tospenditswayoutofrecession. (政府竭力刺激消費以走出蕭條。)
d. Hewormedhiswayintoher affection. (他一寸一寸地蠕行,終于走進她的心里。)
若按CG的常規解釋,例15)都是“V one’s way PP”構式,15a)是原意/刻意用法,即“真走”,動詞換成walked(走)亦然。15a)的動詞改為elbowed(肘推)、squeezed(擠)、threaded(穿過)、crawled(爬)、jumped(跳)等,則是轉喻性用法的“真走”,指的是當事人用肘部推擠他人(或爬,或跳)前行的樣子;15b-d)(5)原文(斜體除外)源于Taylor(2004:339)。是隱喻性用法,是“假走”,指的分別是“一直編造謊言,直至采訪結束”,“消費和刺激消費,直至渡過蕭條”,“如同蠕蟲之蠕行,慢慢獲得女方好感”。換言之,“V one’s way PP”構式可表達真走(15a))和假走(15b-d)),后者是對前者的隱喻性延伸,是修辭(構式)用法,都傳承了“真走”類“V one’s way PP”構式的根本、原意即非隨意/寓意特征和用法。旁注的譯文就是基于以上的CG解釋和理解,才做到構式形-義-效等值的譯法——每個譯文都有(或隱含)“走”,15a)的譯文是真走,余下的是假走。以上CG解釋若輔之以LIT的解釋,自然用到“顯赫范疇”及其擴展功能、邊緣功能和跨語言比較(6)例略,見劉丹青(2017b)。,就會更全面、更徹底。
總之,由于LIT和CG在研究目標、研究對象、認知性、功能性、語用性、修辭性方面的共同特點以及共同缺點,如“不注重”(表1中間),或者說,二者都忽略了語言的人際功能、語篇功能、語用性、修辭性等,那么,二者均需加強這些方面的攝入和研究,借鑒語用學、社會語言學、篇章語言學、功能語言學、修辭學、傳播學等,再進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雙贏”的新認知研究。
6. 結論
“語言知識是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的產物,而語法構式又是句法之基礎”(Michaelis,2008:83);任何語詞和構式都要受到語義限制和語用限制(pragmatic constraints),解釋其意義,或者其音、形、義、功、效等,都需要認知的手法和話語-功能的(discourse-functional)路徑(同上)。鑒于語言的復雜性,任何語言理論都要不斷發展自己的理論和觀念,包括形式派和功能派的一切范型。新興的語言庫藏類型學(LIT)和已有二三十年歷史的構式語法(CG)有同有異(不論優缺點),同者使之局部重疊和互洽,異者使之并置和互補。本文初步考察了LIT和CG的四大相似點:研究目標和研究對象的交點、語用性的缺失和語言功能(性)的不全面,及其四大差異:維度為獨立性與非獨立性、跨語言研究與非跨語言研究、語義與形式、可以解釋的語言現象(雖然表1有七同六異)。我們認為,LIT和CG可以聯手,但首先要認清共同的認知源頭,認清自己的弱項和對方的強項,共同借鑒可以為自己“充電”的語用學、社會語言學、篇章語言學、功能語言學、修辭學、傳播學等,再進行認知語言學陣營內部的“雙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