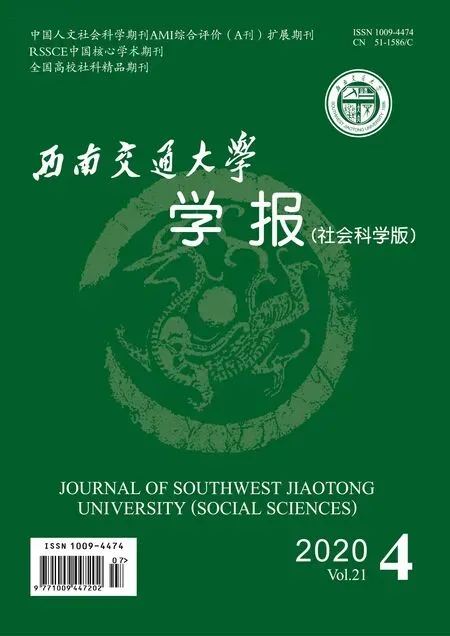敦煌《孝經注》殘卷的文獻價值
呂冠南
(山東大學 國際漢學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 250100)
儒家經典《孝經》自漢代以來便備受推崇,有今文《孝經》鄭氏注與古文《孝經》孔氏傳兩種主要注本。胡平生先生曾對《孝經》舊注的散逸情況作過言簡意賅的介紹:
五代之亂,鄭注與孔傳都亡佚了。北宋時,日本奈良京大寺高僧奝然出使中國,所獻古書有《孝經》鄭注,其事約在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大概到北宋末年,《孝經》鄭注又在戰火中佚失。〔1〕
如今,孔氏傳的播遷已無跡可尋,鄭氏注則不然。日本光格天皇寬政五年(1793),岡田挺之(1737—1799)自日藏《群書治要》中輯出《今文孝經鄭注》一卷,此書后傳入中土,鮑廷博重刻于《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一集中,從而使清儒輯《孝經》鄭注生面別開,嚴可均以岡田本為主,重輯鄭注《孝經》,成為清輯之最完備者。光緒二十一年(1895),今文經學大師皮錫瑞以葉德輝增補嚴可均輯本為底本,為《孝經》鄭氏注作疏,是為《孝經鄭注疏》〔2〕。此書是清代《孝經》鄭氏注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清儒治鄭注《孝經》的最高成就。但由于其使用的底本主要取自《群書治要》,故鄭注殘缺較重,這為皮錫瑞的疏解制造了文本困難。今觀皮疏,于所輯鄭注每有“語未竟”“鄭義不完”“鄭注殘缺,未審其意云何”等慨嘆,故只好使用“推鄭義”“(鄭注)蓋以為”等揣測式的字眼去推測鄭注之真意為何。很明顯,這種受制于文本的疏解,不免包含著較大的主觀性。
幸而地不愛寶,敦煌藏經洞出土了9件唐寫《孝經》鄭氏注殘卷②,據許建平先生《敦煌經籍敘錄》卷八的介紹:
P.3428+2674號是鄭注《孝經》的最長卷,雖非完璧,但所存已占鄭注的四分之三。經過林秀一《敦煌遺書孝経鄭注復原に関する研究》及陳鐵凡《孝經鄭注校證》的輯證,鄭玄《孝經注》的絕大部分已得到復原。〔3〕
在同卷第二節中,許先生對P.3428和P.2674之外的7件鄭注《孝經》殘卷也進行了詳細說明。這些說明,以更精簡的篇幅保存到了2008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群經類孝經之屬·孝經注》題解中〔4〕。至此,敦煌《孝經注》殘卷在恢復鄭注原貌方面的價值,已被完善地揭示出來。
上引許先生提到的林秀一、陳鐵凡二先生的著作,為還原鄭注《孝經》之原貌做出了杰出貢獻,亦為繼續深入探討鄭注《孝經》的諸多價值提供了可靠的文本依據。但目前的鄭注《孝經》研究尚存在繼續開展的余地,這著重表現在對鄭注《孝經》進行完善的整理之后,如何在新文本語境下實現與前人研究的對接。換言之,即在擁有更為完善的鄭注文本的今天,應如何用這套新文本去檢驗前人相關著作的得失。管見所及,目前尚未有論著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探討。茲以皮錫瑞《孝經鄭注疏》為代表,將其與敦煌《孝經注》殘卷進行對比研究,以便在更寬廣的層面上揭示敦煌《孝經注》殘卷的文獻價值。
一、敦煌本《孝經注》在注文還原方面的價值
由于《孝經鄭注疏》所輯鄭注采自多種典籍,故不可避免地牽涉到注文順序的安排。如果在這一環節出現問題,那么整條注文便會存在錯簡的情形,在某種程度上便降低了注文的可靠性。以敦煌本《孝經注》(以下簡稱“敦煌本”)與《孝經鄭注疏》(以下簡稱“皮疏本”)對勘,可發現后者存在較為普遍的錯簡情況,可借敦煌本加以還原。今舉三例以證之。
1.《開宗明義章》“《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注
敦煌本:《大雅》者,詩之篇名。云,言也。無念,猶無忘。祖,先祖。聿修之理。厥,其。為孝之道,無敢忘爾先祖,當修治其功德。不言《詩》而言《雅》者何?詩者通辭,雅者正也。方始發章,欲以正為始。〔5〕
皮疏本:《大雅》者,詩之篇名(《治要》)。雅者,正也。方始發章,以正為始(《正義》)。無念,無忘也。聿,述也。修,治也。為孝之道,無敢忘爾先祖,當修治其德矣(《治要》)。〔2〕
按:從皮錫瑞在注文后提供的文獻來源看,可知是兼采《群書治要》與《孝經正義》而成。今觀敦煌本鄭注原本,則《群書治要》所錄注文為原貌之前半,《孝經正義》所錄注文為原貌之后半,二者序有先后,加以拼合則恰為原貌。而皮氏將采自《孝經正義》者插入《群書治要》注文中,遂造成此條注文的錯簡。這一錯簡在變亂鄭注原貌的同時,也掩翳了鄭氏注詩的體例。由敦煌本原注可知,鄭氏注詩均先逐字詮釋字義(如“云,言也。無念,猶無忘。祖,先祖”),再疏解全句之義(如“為孝之道,無敢忘爾先祖,當修治其德矣”),最后闡發全句之義理(如“不言《詩》而言《雅》者何?詩者通辭,雅者正也。方始發章,欲以正為始”)。這與鄭玄箋釋《毛詩傳》的體例相同,以《周南·葛覃》“服之無斁”為例,鄭箋曰:“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之以絺绤煩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顯然“服,整也”為詮釋字義,其后“女在父母之家”至“是其性貞專”則是詮釋句意〔6〕。清儒戴震《與是仲明論學書》有“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之語〔7〕,此論頗得漢學之三昧。以敦煌本鄭注而論,字義到句義屬“通其詞”,字句義到闡發則屬“通其道”,次序井然,不可躐等。
2.《孝治章》“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注
敦煌本:古者天子五年一巡狩,勞來諸侯。諸侯五年一朝天子,貢國所有,各以其職來助祭宗廟,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5〕
皮疏本: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各以其職來助祭宗廟(《治要》)。天子亦五年一巡狩(《王制》正義)。勞來(《釋文》)。是得萬國之歡心,事其先王也(《治要》)。〔2〕
按:兩本對斠,可知皮疏本所輯“天子亦五年一巡狩”及“勞來”之文存在錯簡,當置于“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之前。皮疏引嚴可均校語謂“勞來”之文“上下闋”,今觀敦煌本原注,知其上不闕,其下則闕“諸侯”二字。“勞來”亦作“勞俫”,《漢書》卷七一《平當傳》:“舉奏刺史二千石勞俫有意者。”顏師古注:“勞者,恤其勤勞也;徠者,以恩招俫也。”〔8〕“勞來諸侯”之說對后世注家解讀《詩經》有一定影響,如《國語》卷十《晉語四》記狐偃使重耳“賦《黍苗》”,韋昭注:“《黍苗》亦《小雅》,道邵伯述職,勞來諸侯也。”〔9〕再如《左傳·閔公元年》管夷吾引《小雅·出車》:“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杜預注:“《詩·小雅》也。文王為西伯,勞來諸侯之詩。”〔10〕在這些注釋中,均可以看到《孝經》鄭氏注的影響。
3.《圣治章》“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注
敦煌本:文王,周公之父。明堂即天子布政之宮。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明堂之制,八窗四闥,上圓下方,在國之南,故乃稱之曰明堂。〔5〕
皮疏本:文王,周公之父。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治要》)。明堂之制,八窗四闥(《御覽》一百八十六),上圓下方(《白孔六帖》十),在國之南(《玉海》九十五)。南是明陽之地,故曰明堂(《正義》)。上帝者,天之別名也(《治要》)。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史記·封禪書》集解)。〔2〕
按:觀敦煌本原注,可知鄭注依此解釋經文“文王”“明堂”“上帝”三詞,隨后就“明堂之制”加以介紹,因《孝經》本文并未涉及“明堂之制”,故此節訓釋屬字義訓詁后的推衍。皮疏則將“明堂之制”插入“明堂”字義之后,打亂了鄭注先訓字義而后涉推衍的體例。
實際上,上揭三則錯簡之例已能證實《群書治要》所錄注文最接近敦煌本原注,故凡皮氏以其他輯佚材料割裂《群書治要》之注,則常造成錯簡。換言之,皮疏本的錯簡是伴隨割裂《群書治要》注文而產生的。廖群先生在《“文學考古”與文獻考據的互補性》中曾提及出土文獻對于傳世文獻具有佐證和反證的作用〔11〕,這一灼見在梳理《孝經》鄭氏注的問題上也同樣適用,因為通過比勘,既可佐證《群書治要》之非偽,亦可反證皮疏本的注文輯錄存在錯簡。
另外,敦煌本還可糾正皮疏本某些注文的互乙現象。如《孝治章》“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皮疏本自《釋文》輯鄭注:“侯者,候伺。”〔2〕考敦煌本鄭注作:“侯者,候也。當為王伺候非常。”〔5〕據此,可知皮疏本“候伺”二字互乙。這一現象與錯簡相類似,故附帶論之,亦可彰顯敦煌本的文獻價值。
二、敦煌本《孝經注》在注文辨偽方面的價值
在敦煌藏經洞開啟之前,《孝經》鄭氏注一直是以佚書的身份存在于學者的視野中,故清儒對此書的研治主要體現在輯佚方面。呂思勉先生《群經概要》謂“清《孝經》鄭注有八輯”〔12〕,這一數目并不完全,據舒大剛統計,清儒“輯錄鄭注成專書者不下三十家”〔13〕,其盛況可見一斑。至皮氏為鄭注作疏,雖屬輯佚以外的工作,但仍是在葉德輝增補嚴可均輯本的基礎上完成的,所以仍存在或多或少與輯佚相關的問題。通過敦煌本《孝經注》殘卷與《孝經鄭注疏》的比對,可以發現皮疏所用鄭氏注存在誤輯的情形。注既為偽,則解注之疏的價值亦無處安置。皮氏誤輯之文雖然數量不多,但仍有以下兩個較為明顯的例證:
1.《孝治章》:“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皮疏本據《公羊序》疏輯鄭氏注:“昔,古也。”〔2〕
按: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卷首序:“昔者孔子有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疏曰:“《孝經》云‘昔者明王’,鄭注云:‘昔,古也。’”〔14〕此為皮氏所本。然考敦煌本原注全文為:“古者諸侯歲遣大夫,聘問天子無恙,天子待之以客禮,此不敢遺小國之臣。”〔5〕并無“昔,古也”三字。可知此注并非鄭注之文。徐彥所謂“鄭注”,或因鄭注以“古者”解原經之“昔者”,遂以鄭氏訓“昔”為“古”。
2.《感應章》:“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皮疏本據《禮記·祭義》正義輯鄭氏注:“謂養老也。”〔2〕
按:孔穎達《禮記正義》卷四八《祭義》:“食三老五更于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正義曰:“案《孝經》云:‘雖天子,必有父也。’注謂養老也。”〔15〕此為皮氏所本。然考敦煌本原注〔5〕,并無此四字,則孔氏所引或非鄭氏注。
上揭二例均體現出敦煌本《孝經注》在注文辨偽方面的價值,這看似屬文獻學層面的問題,但已關涉到皮疏本的可靠性。因一旦注文判定為偽,則以注文為旨歸的疏解無論多么淵博,都是對假材料的闡發,并不具備疏解鄭氏注的意義。昔馬國翰嘗輯《韓詩故》二卷,江瀚所撰提要有“著書難,輯書亦正不易”之語〔16〕,以此論分析皮疏本所輯偽鄭氏注,確有“斯言良是”之感。
三、敦煌本《孝經注》在注文校勘方面的價值
敦煌本《孝經注》的出土,在還原與辨析前人所輯鄭氏注的意義外,還有校勘學方面的意義,即可用敦煌本檢驗前人校勘鄭注佚文的得失。皮錫瑞撰《孝經鄭注疏》,其自序曾言:“近儒臧拜經、陳仲魚始裒輯之,嚴鐵橋《四錄堂》本最為完善。錫瑞從葉煥彬吏部假得手鈔《四錄堂》本,博考群籍,信其塙是鄭君之注。”〔2〕可見皮錫瑞在底本選擇方面頗費了一番苦心,他在參酌多種清輯本之后,選擇以葉補嚴輯本為底本,系因此本“最為完善”,故可將疏解工作建立在相對可靠的文本基礎上。在這一選擇上,皮氏的做法是相當穩健的。
但是,敦煌本《孝經注》重見天日之后,無論是嚴輯本對注文的校勘,還是皮氏對嚴輯注文的續校,均面臨著不可回避的挑戰。通過敦煌本與皮疏本的對斠,可發現嚴氏所校鄭注悖于敦煌本者蓋十之八九,皮氏補校雖較嚴氏為勝,但也存在不少問題。茲就嚴、皮二氏校勘有誤者,舉六例以證之;二氏合于原注者則不再費辭臚列,因既合于原注,則無從展現敦煌本在證誤方面的文獻價值。
1.《庶人章》:“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無終始。”注:“總說五孝,上從天子,下至庶人,皆當孝無終始。”〔2〕
按:皮錫瑞引嚴可均所作校語“兩‘無’字并宜作‘有’。”依嚴氏之說,則此章經文當作“孝有終始”,鄭注當作“皆當孝有終始”。今考敦煌本原注,經文作“孝無終始”,鄭注作“皆當行孝無終始”〔5〕。可知嚴氏校語誤。經、注“孝無終始”之“無”并無問題,汪受寬先生注為“實行孝道,沒有開始與終結的區別”〔17〕,此解甚愜經、注之義。
2.《孝治章》:“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注:“當為王者。……伯者,長。”〔2〕
按:皮錫瑞引嚴可均校語謂注文“當為王者”后“當有‘公者,通也’”,又謂“伯者,長”后“當有‘子者,字也’”。依嚴氏之說,則此注應作:“當為王者。公者,通也。伯者,長。子者,字也。”皮疏曰:“‘公者,通也’,與《白虎通·爵》篇同,嚴說是也。”〔2〕又謂嚴氏所補“子者,字也”之文“與疏引舊解同”〔2〕,“疏”即邢昺《孝經注疏》,該書卷四確引舊解云“子者,字也”〔18〕。可見嚴氏為注文所作校補皆有古籍上的依據。然考敦煌本,原注實為:“公者,正也,當為王者正行天道。……子者,慈也,當為王者慈愛人民”〔5〕。不僅推翻了嚴氏“公者,通也”及“子者,字也”的校勘,還證實了“公者”之文并非嚴氏推斷的在“當為王者”之后,而是在前。由敦煌本原注,可知嚴氏所校此條注文不僅校勘有誤,還存在錯簡。皮氏贊同嚴氏“公者,通也”之說,但對“子者,字也”之說則不以為然,認為當依《春秋元命苞》等書作“子者,孳也”〔2〕。今觀敦煌本,可知皮氏校語亦皆未安。按:鄭訓“公”為“正”,可獲他書之印證。如《呂氏春秋·貴公》:“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高誘注:“公,正也。”〔19〕再如《淮南子·原道》:“與民同出于公。”高誘注亦為:“公,正。”〔20〕。鄭訓“子”為“慈”,并釋句意為“當為王者慈愛人民”,可知此“慈”為“慈愛”之義,此說亦于他書有征。如《戰國策·秦策一》“蘇秦始將連橫”章:“子元元。”高誘注:“子,愛也。”〔21〕“愛”即“慈愛”之義,與鄭注字異義同。
3.《孝治章》:“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之心。”注:“男子賤稱。”〔2〕
按:皮錫瑞引嚴可均校語“此注上當有‘臣’字,下當有‘妾,女子賤稱’。”依嚴氏所校,則此注當為:“臣,男子賤稱;妾,女子賤稱。”今考敦煌本原注作:“臣,男子賤稱;妾,婦人名。”〔5〕則嚴氏之得在補“臣”字,其失則在補“妾,女子賤稱”,此校得失各半。
4.《紀孝行章》:“居則致其敬。”注:“也盡禮也。”〔2〕
按:皮錫瑞引嚴可均校“也盡”曰:“‘也’當作‘必’字。”校“禮也”曰:“‘禮’上當有‘其敬’。”依嚴氏所校,則此注當作:“必盡其敬禮也。”今考敦煌本原注作:“盡其禮也。”〔5〕與嚴校有別。
5.《五刑章》:“非孝者無親。”注:“己不自孝,又非他人為孝,不可親。”〔2〕
按:皮錫瑞引嚴可均校“又非他人為孝”曰:“《釋文》作‘人行者’,一本作‘非孝行’,合二本訂之,或此當云‘又非他人行孝者’。”今考敦煌本原注作:“既不自孝,又非他人為孝,不可親也。”〔5〕可知嚴氏校為“又非他人行孝者”,有悖于鄭注原貌。
6.《喪親章》:“陳其簠簋而哀慼之。”注:“簠簋,祭器,受一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2〕
按:此處注文為陳鱔所輯。嚴輯本注文為“內圓外方曰簋”,輯佚來源為原本《北堂書鈔》。皮錫瑞謂:“嚴氏過信《書鈔》原本,原本有誤。”遂采陳氏自《北堂書鈔》卷八十九所輯者入書,并爬梳典籍,為陳氏張目。今考敦煌本原注為:“簠簋,祭器之名,受斗二升,內員外方。”〔5〕“內員外方”與嚴輯“內圓外方曰簋”相近③,而較陳輯“方曰簠,圓曰簋”為遠。可證此處皮錫瑞以陳輯本為依據的校勘是錯誤的,反以嚴校更接近原貌。但嚴校于“內圓外方”之后衍“曰簋”,尚未能盡善。考嚴氏校語,有“《考工記·旊人》疏引‘內圓外方’者”之文,按此文見《周禮注疏》卷四一:“《孝經》云:‘陳其簠簋。’注云:‘內圓外方。’”〔22〕今有敦煌本為據,可知此文為傳世文獻最合于原注者。
由上揭六例,可知清儒在鄭注校勘方面存在較多問題,這些失誤或由不通經義而起(如例1),或因理校所不可避免的主觀性所致(如例2-5),也有部分緣于所據底本有誤(如例6)。幸有敦煌本原注,可將這些校勘失誤加以糾正。
四、傳世文獻對敦煌本《孝經注》的補充
上述三節以具體案例揭出了敦煌本《孝經注》殘卷的重要文獻價值,即對傳世文獻所輯鄭注佚文的錯簡進行還原,對所輯偽注進行辨別,同時可用于檢驗前人校勘佚注的得失。但敦煌本《孝經注》殘卷也并非盡善盡美,這首先表現在部分注文存在脫漏的現象;同時,殘卷本身也有不少文字存在殘泐現象,雖經林秀一、陳鐵凡諸學者校補,仍有繼續填充的余地。因脫文與殘泐皆為敦煌本《孝經注》文獻學的題中之義,故略舉數例,附論于此。
(一)補充脫文
敦煌本《孝經注》的注文存在一定數量的脫漏,這可在傳世文獻中得到證實。茲舉二例以證之。
1.《群書治要》卷九《孝經·圣治章》:“嚴父莫大于配天。”注:“尊嚴其父,莫大于配天。生事敬愛,死為神主也。”〔23〕
按:《孝經鄭注疏》據此輯入鄭注〔2〕。今考敦煌本原注僅有“尊嚴其父,莫大于配天也”〔5〕,可知殘卷抄手脫去“生事敬愛,死為神主也”二句。又考敦煌所出無名氏《孝經注》(P.3382)恰有《圣治章》,其注曰:“尊嚴其父,大于配天神也。”〔24〕此注當系承襲鄭注而來,亦無“生事”二句,可知此二句在唐寫本鄭注中脫去甚早,故承襲鄭注的無名氏注本亦無。幸有初唐《群書治要》之保存,猶能知鄭注原貌。
2.邢昺《孝經注疏》卷五《圣治章》:“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正義曰:“鄭玄以《祭法》有周人禘嚳之文,遂變郊為祀感生之帝,東方青帝靈威仰,周為木德,威仰木帝,言以后稷配蒼龍精也。”〔18〕
按:《孝經鄭注疏》據此輯鄭注曰:“東方青帝靈威仰,周為木德,威仰木帝,以后稷配蒼龍精也。”〔2〕今考敦煌本原注并無此文〔5〕,初頗疑其為皮氏誤輯。后讀敦煌所出無名氏《孝經鄭注義疏》(P.3274),始知此數句實為鄭注原文。因《義疏》系闡發《孝經》鄭注之作,往往先錄鄭氏注文,復于其后撰作疏語,故對于鄭注的保留相對完備。該書《圣治章》“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之義疏曰:
“天,謂東方青帝靈威仰。”是帝而為之天者,尊之也。周公于郊祭所出之帝靈威仰,而用于始祖后稷配之而祭,故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靈威仰木帝,周木德王。”是木德而生后稷也。〔25〕
其中“東方青帝靈威仰”及“靈威仰木帝,周木德王”之句,均見于上援邢昺所引鄭玄說,可定其為鄭注。而“是帝”至“配天”“是木德而生后稷也”兩節則為《義疏》對鄭注的疏文。
(二)補足殘泐文字
敦煌本《孝經注》有部分注文殘泐,傳世文獻有載錄者,即可用于補充。茲舉二例以證之。
1.《卿大夫章》:“《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按:敦煌本鄭注:“夙,早。”許建平先生校勘記謂“夙早”后“殘缺約二十四個注文小字的空間”〔5〕,今考皮疏本據《群書治要》及《華嚴經音義》輯鄭注:“夜,莫也。匪,非也。懈,惰也。一人,天子也。卿大夫當早起夜臥,以事天子,勿懈惰。”〔2〕注文凡二十九字,表示語辭的四“也”字或非敦煌本鄭注所有④,略去后為二十五字,與許先生“約二十四個注文小字”的統計相合。
2.《喪親章》:“毀不〔滅性,此圣人之政也。〕”敦煌本鄭注已殘泐。
按:許建平先生校勘記謂:“經文下應另有注文二十字左右。”〔5〕皮疏本據李善《文選注》輯鄭注曰:“毀瘠羸瘦,孝子有之。”〔2〕雖未能將“二十字左右”的注文全部補出,但對還原鄭注部分面貌仍有裨益。
上揭四例彰顯出傳世文獻在補足敦煌本《孝經注》殘卷方面的價值。由此可見,對于鄭氏《孝經注》的研究,仍需兼顧傳世文獻與出土材料,若無法將二者結合起來,便會對后續研究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陳寅恪先生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曾言王氏治學擅長“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26〕,毫無疑問,對于新材料語境下的《孝經》鄭氏注研究,這一方法也同樣有效。
注釋:
①按:關于鄭氏究竟為鄭玄,還是其孫鄭小同,學術界存在爭議。因本文旨在探討敦煌《孝經》鄭氏注的文獻價值,故對于這一聚訟已久的作者歸屬問題不加討論,行文僅泛稱“鄭氏注”。
②分別見P.3428、P.2674、Дx.02784、Дx.02979、Дx.03867、S.3993、S.9213、P.2556p、S.3824/1。
③敦煌本之“員”與嚴輯本之“圓”可通,參宋人王觀國《學林》卷九“省文”條:“《周禮·考工記》曰:‘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而《史記·禮書》曰:‘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員。’用‘員’字者,省文也”(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314頁)。
④敦煌本鄭注在注釋章末引《詩》《書》的字義時,存在不少省略“也”的情形。茲略舉數例:第一章“無念爾祖,聿修厥德”,鄭注:“祖,先祖。厥,其。”(第1926頁)第二章“一人有慶,兆人賴之”,鄭注:“一人,天子。”(第1927頁)第三章“戰戰兢兢”,鄭注:“戰戰,恐懼。”(第1927頁)第七章“赫赫師尹,民具爾瞻”,鄭注:“赫赫,明威皃。師尹,大臣,若冢宰之屬。”(第1929頁)第九章“淑人君子”,鄭注:“淑,善。”(第1931頁)參張涌泉主編審定《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4冊,中華書局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