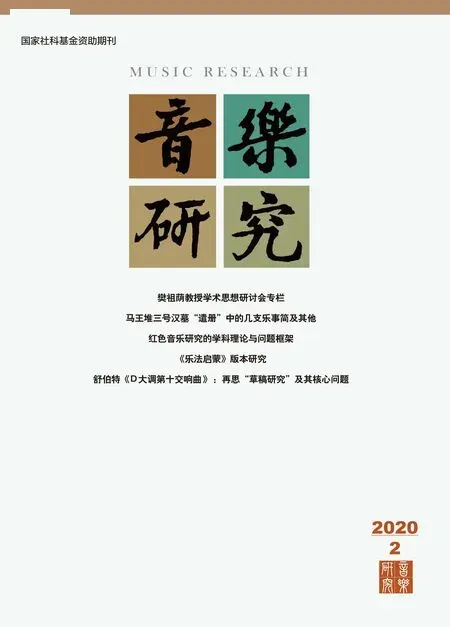李叔同、曾志忞樂歌思想之異同
——從《申報》刊發《論學校音樂之關系》說起
文◎陳艷秋、李 巖
李叔同和曾志忞是樂歌運動的先驅,二人的樂歌思想對中國近代音樂教育、音樂創作產生了深刻影響。他們的樂歌思想雖有分歧、嬗變,但更多是對音樂歷史、現狀及發展的共識。《申報》一篇名為《論學校音樂之關系》的政論,以“新聞人”視角,將二人思想熔于一爐,用以闡發報社的立場并鮮明表達了報界對教育的關注。以此為切入點,可辨李、曾思想之異同及清季社會音樂的思潮動向與價值觀。
一、由《論學校音樂之關系》說起
1906 年5 月3 日,《申報》在第二版顯著位置刊登了一篇題為《論學校音樂之關系》的政論(下稱“政論”),全文958 字,未署名。此后,更名為《研究學校音樂法 論》,分別被北洋報局主辦的《北洋學報》①1906 年第36 期,第27—28 頁。(天津)及嚴復主編的《國文報》②1906 年第16 期,第7—8 頁。(天津) 全文轉載,可見該政論之巨大社會反響。兩份轉載同樣未注作者,僅在正文開頭加“申報云”作為文章來源。通過閱讀發現,該政論結構嚴謹、行文流暢,但內容和觀點卻與李叔同《音樂小雜志》③1906 年2 月8 日在日本印刷,2 月13 日運回上海發行。(下稱“李文”)中《序》《昨非錄》《論音樂感動力》《嗚 呼!詞章!》四篇文章及曾志忞《音樂教育論》④載《新民叢報》1905 年第14 號(2 月4 日)、第20 號(5 月4 日)。(下稱“曾文”)高度相似,可以說是兩者的合輯。本文首先對政論的來源和內容,進行考證和甄別。
(一)佚名政論來源
首先,就作者角度,李或曾都不可能在撰文時大量引用對方原文,所以該政論應不是二人所作。其次,在清末中文報紙中,佚名文章多為編輯或記者撰寫。該文是一篇典型的對社會熱點——科舉廢除、新學制初興、樂歌課蔚然成風——進行深入探討且尚不被學界所知的政論體文章。而政論代表了報社的觀點和立場,在報刊評論中居于主導,作為當時影響最大的綜合性報紙,《申報》政論多由編輯部固定的主筆或編輯撰寫;除此,政論稿件亦有來稿或約稿,但一般也不注明作者,僅標“來稿”或“來稿代論”,而該文并沒有此類標注,據此分析,應為《申報》編輯部所為。再次,恰在該政論發表前半個月(1906 年4 月19日),《申報》在“贈書志謝”欄目中提到李叔同的《音樂小雜志》并進行了評介:
昨承李君叔同由東瀛郵贈第一期《音樂小雜志》。書中闡發聲音之理,極為精辟,各歌曲亦哀感頑艷,足以陶冶性情。欲研究音樂者,不可不一瀏覽也。⑤載《申報》1906 年4 月19 日,第4 版。
向報社贈書在當時較為普遍,報紙的贈書志謝往往對書籍進行簡要介紹,這也是變相推書的“軟廣告”。《申報》編輯部無疑在受贈后留意了該書,并與曾文進行了合并輯錄,借以闡發報社對學校音樂的建議與批評。
(二)政論內容甄別
該政論的輯錄分為兩種:其一,直接輯錄二文詞句和例證,但行文時略做刪減和修改;其二,援引二人觀點,并做總結和點評。
1.對李文的輯錄
(1)政論:“歐西音樂,濫觴希臘,希臘人以音樂為上古女神之遺,故沿用至今,猶名曰謬塞克爾(MUSICAL)列入學科。”源自李文《序》:“繄夫音樂……實祖印度……逮及希臘,迺(乃)有定名(希臘人謂音樂為上古女神Muses 之遺,故定名曰Musical)。”兩者對照:編輯顯然對李文中音樂源自印度的觀點,進行了刪減。這一觀點現在看來與史實不符,卻在當時的日本異常盛行。
(2)政論:“昔觀日本音樂學校,玩其唱歌,詞意激昂。其沿襲我國之古詩謠者,殆十而八九也。”源自李文《嗚呼!詞章!》:“予到東后,稍涉獵日本唱歌,其詞意襲用我古詩者,約十之九五。”顯然政論對李文中的比例進行了修訂。
(3)政論:“今之學唱歌者,音階略通,即唱男兒第一志氣高之歌。譜表未熟,即手揮五五六六五五三之曲。”該段直接引自李文《昨非錄》,但將李文中“此為吾樂界最惡劣之事”的評價,改為“欲速不達,弊在躐等⑥“躐等”指逾越等級,不按次序。出自《禮記·學記》。”。值得玩味的是,此后李叔同在寫給劉質平的信中,曾多次提到“勿躐等急進……欲速則不達矣”⑦郭長海編《李叔同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203 頁。“B 氏⑧貝多芬(Beethoven)的簡稱。曲君習之,似躐等”⑨同注⑦,第260 頁。的相似話語,李叔同是否看過該篇政論無法考證,但政論點評之精準可見一斑。
(4)政論將李文所載《論音樂之感動力》(村岡范為馳著)一文中的兩段話刪減合并為:“又言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謂有此音樂感動之力也。哥倫布豪杰之歌,能鎮北美合眾國之爭亂。馬賽之歌,能激法國之大革命。”
2.對曾文的輯錄
(1)政論:“如學校音樂,則有侍座鼓瑟、武城弦歌之類,社會音樂,則有若朝廷祝祭,采詩夜頌之類。”源自曾文:“如侍座鼓瑟,武城弦歌,此得謂之學校音樂,蓋六藝之一也。至若朝廷之祝祭,庶民之冠婚,此乃社會音樂。”此處在回顧歷史之時,明確將音樂劃分為學校與社會兩類,并就此切入相應批評。
(2)政論:“嗚呼今日社會音樂,流入卑靡者,已至無可挽救。吾人所首當研求者,其在學校音樂乎?”“至于音樂發達,而社會上一般淫靡不正之樂,將受天然之淘汰,而歸于劣敗。即現在學校中所唱五更調者,亦可因之而消滅。吾所謂學校音樂,足以挽回社會音樂者,此也。”兩段話改編自曾文第一章《緒言》。政論選錄此段對社會音樂的淫靡之風提出批判,也是學校音樂風格宜莊(重)、不宜諧(趣,甚至淫邪)的《申報》態度之表述。
(3)政論:“今之學校,皆以洋曲填國歌,識者方議其不合。”源自曾文:“有識者于是以洋曲填國歌,明知背離不合,然過度時代,不得不借材以用之。”這顯然是對“洋曲”的態度,并在不得已而為之時刻,“借材以用”之妥協抑或變通。
3.對主要觀點的援引
經甄別,政論主要觀點來自曾文:學校音樂足以挽回社會音樂之頹廢;樂歌創作分為歌學和曲學兩方面;發展音樂要先明確音樂的功用、材料及與國家的關系。但在歌詞方面,政論贊成李叔同的“雅言”主張,并結合曾文提出《申報》的建議:“何不令國學深邃之人,專修音樂,究其旋法進行之微妙。歸而以素所蓄積者,譜為歌謠,為之培養生徒之美感,喚起全國之精神乎?”值得注意的是,政論將曾文和李文中的所有相似觀點,都進行了合并輯錄。
由以上考辨顯示,政論輯錄了二文的觀點,可以說是李文和曾文思想被《申報》的首次肯定。以此為線索,追蹤李叔同和曾志忞樂歌思想中的共識、分歧與嬗變,可以對應當時社會之中西、雅俗、古今問題的態度和立場。
二、中與西:對待西方音樂的共識與分歧
學堂樂歌三位先驅中,沈心工長于實踐(樂歌創作突出),李、曾文論則為研究這一時期樂歌思潮的重要文獻。在李、曾二人對待西樂的共識與分歧之中,可見當時社會對于學校音樂教育的認知和訴求。
(一)共識
李叔同在1904 年參加沈心工“速成樂歌講習會”⑩陳凈野《李叔同與沈心工——兼議李叔同〈送別〉研究中的若干問題》,《人民音樂》2007 年第5 期,第30 頁。之后才開始樂歌編寫,他高度贊揚沈心工和曾志忞“紹介西樂于我學界”?《國學唱歌集·序》,參見注⑦,第21 頁。之舉,并認為這是我國樂界新階段的序幕。結合政論內容可以辨析出,在1905—1906年間,李叔同和曾志忞樂歌思想之共識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近采日本
政論稱:“殆在十六世紀以后,至日本向用中國十三弦箏……乃彼以后起者而漸精漸進,感精神之粹美。我以先覺者,而日漸日滅,失音聲之效用。其故匪他,蓋習與不習之區別也。”此話,以日本為參照和目標的立場十分鮮明。“近采日本”是曾志忞早期贊同并提倡的樂歌發展之路,曾文認為,為中國音樂“求發達之利器”,應該研究、推廣日本學習西樂的方法和材料,而非僅設立學校唱歌課。
對此,李叔同的態度更為直接。在李文中,共載七篇完整文論,其中四篇出自日人之手,還刊載日人圖畫二幅及日人歌詞二首。此外,在《嗚呼!詞章!》中列舉中國音樂弊端時,也多以日本作為比較對象,均可見他對“近采日本”之贊同。
2.音樂感動力
誠如前述,政論輯錄了李文《論音樂之感動力》(村岡范為馳)中關于“音樂感動力最大”的觀點。此外,李文《序》中還贊嘆道:“嗚呼!聲音之道,感人深矣!”曾文也多次表達了類似觀點:“故其發達力最普,能感能與”“能使英雄泣、鬼神驚,天地之調和因之而發揮”“然教育之最易感化者莫如音樂”。二人都在強調音樂教化功能的同時,注意到音樂的情感審美功能。
3.德性涵養而非心情娛樂
政論稱:“音樂列科之目的,大致在德性之涵養,而不在心情之娛樂。”該觀點出自李文“吾國學琴者,大半皆娛樂的思想,無音樂的思想”?出自李文《昨非錄》。之表述。認為音樂只是娛樂,而非學問和技藝,所以不用刻苦研習,這一輕視音樂的現象在當時比較普遍。曾文亦有相似看法:“西人言日人無音樂思想,至今且有譏者;今日人更以是譏我,果我輩之不能耶!”進而又告誡世人學習音樂要慎重、刻苦,不能抱以玩樂的心態。
4.循序漸進
針對普遍存在的“躐等”現象,李文《昨非錄》提出應遵循音樂學習的規律及原則,不能以歌曲代替發聲練習,以樂曲代替練習曲。曾文第四章《音樂之實修》中也多次抨擊:“自速成二字出,學界大歡迎之”“吾國學者,往往以不求甚解之良箴,銘諸座右”“習得一知半解好為人師……其罪不可恕”。他還以“告化胡琴半黃昏”之諺語,來諷刺寄希望于數旬間學會一門樂器的急于求成者。
(二)分歧
李、曾二人對借用西方曲調的態度基本相同,但在如何處理西方曲調這一問題上存在分歧。李叔同對待西方原曲的態度較為靈活,他曾細述自己的編寫過程:“余曾取《一剪梅》《喝火令》《如夢令》諸詞,填入法蘭西曲譜,亦能合拍。可見樂歌一門,非有中西古今之別”,而所選歐美曲調可隨時編訂,“如略有參差,則稍加點竄,亦無不可”?李惜霜(李叔同)《學堂用經傳宜以何時誦讀何法教授始能獲益》,《東方雜志·附錄》之《商務印書館征文》1905 年第2 卷第4 期,第4 頁。。他認為“詞曲合一”是樂歌藝術性的重要標準,根據歌詞對西方原曲進行修改是非常必要的,而固執拘泥原曲而不知變通,無異于膠柱鼓瑟。他此后經“稍加點竄”而達到詞曲高度統一的樂歌作品,足以證明該觀點的合理性。
在李文發表的24 天前,曾文第五章《音樂之于詩歌》也談及“詞曲不可背離”的觀點。他同時提出,借用西方曲調時要遵循幾點原則,其中第一禁例即為“不可改人原曲”,“一曲有一曲之體式,一曲有一曲之情態,體式情態,萬不可改刪添注”。從此后樂歌編寫的亂象看,曾志忞所持原則并非“呆板”,且具一定的預見性。
對西方原曲調的“可點竄”與“不可改”皆有道理,而導致分歧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歌詞選用不同。李叔同傾向于選擇古詩詞或藝術性較強的新詩為歌詞,而曾志忞多用“淺白”語言作為歌詞。古詩詞不宜修改,為了配合固有詩詞結構和格律,曲調修改勢在必行;而淺白歌詞則可以根據原曲調重新創編,或進行較大幅度的調整。第二,對詞、曲的本位認識不同。根據二人的表述,李叔同的樂歌編寫是“依詞選曲”,即以詩詞為體(本),歐美曲調為用,用在這對二元關系中顯然處于從屬地位。而從“不熟讀全曲得其全神,不可填歌詞”可以看出,曾志忞的編寫是“選曲填詞”,即以歐美曲調為基礎,再配以新詞,在此情況下,“不改人原曲”而實現“詞曲不背離”也是可行的。第三,文化訴求不同。李叔同追求樂歌的藝術性,而曾志忞更注重樂歌的教育功能,不同的文化訴求帶來不同的藝術主張。綜上所述,李、曾處理西方曲調方法上的不同,根源來自二人不同的音樂價值觀,以及對雅俗、中西問題的認知分歧。
在樂歌曲調這一問題上,政論支持學校音樂借用西方曲調作為權宜之計。此外,政論還強調了“歌與曲合并為一”的重要性,但并沒有論及原曲調是否更改等具體編曲技術問題。
三、雅與俗:樂歌歌詞的“淺白”與“雅言”
樂歌歌詞主要有“淺白”和“雅言”兩種風格趨向。20 世紀初,以曾志忞為代表的淺白化風潮占據樂歌編創的“正統”。曾志忞認為,古今詩人之詩“婦孺皆不知,惟詞章家獨知之”,并以歐美、日本為標本,號召“以最淺之文字,存以深意,發為文章。與其文也寧俗,與其曲也寧直”?曾志忞《教育唱歌集·告詩人》,載梁啟超《飲冰室詩話》第九十七條,時代文藝出版社1998 版,第82 頁。。
李叔同在樂歌歌詞方面,則一直堅守“雅言”而鮮見例外。在1905—1906 年間,他有三篇文論涉及樂歌歌詞的“雅言”問題,皆體現出其“和而不同”的音樂觀。1905 年 5 月,他發文抨擊學界“鄙經傳若芻狗”的現象,并特別指出:《詩經》內容豐富、體裁合適,“益用之為中學唱歌集”?同注?,第3—7 頁。。同年,他反潮流而行之發表《國學唱歌集》,在《序》中言明發行歌集的目的和對樂歌界拋棄傳統文化的擔憂。《歌集》所載的21 首歌詞如同“簡易版的中國文學史”?朱興和《李叔同學堂樂歌中的近代思想意味》,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5 年第10 期,第105 頁。,其中雖然沒有排斥近代詩,但接續傳統、宣揚國學的文化取向已然清晰。
到日本后,李叔同曲調態度之轉變已于李文中明確顯現,但其歌詞觀念是否產生了位移,學界所持觀點不同。戴嘉枋以 《嗚呼!詞章!》的觀點為依據,以其之后的樂歌編創為實例,認為李叔同“對于樂歌歌詞的觀念幾近始終如一”?戴嘉枋《李叔同——弘一法師的音樂觀及其學堂樂歌創作》,《中國音樂》2002 年第1 期,第1—4 頁。;而李靜則認為李叔同將雅言的《隋堤柳》歸為別體唱歌,并寫道“此歌仿詞體,實非正規”,是認同了淺白化“教育唱歌”的“正體”地位。?李靜《樂歌中國——近代音樂文化與社會轉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版,第158 頁。第一種觀點顯然無法解釋李叔同對樂歌的分類行為。而第二種觀點稱李叔同就此承認“雅言”樂歌的非正體,也和《嗚呼!詞章!》中的言論相悖。綜合各家觀點和當時出版物,筆者認為李叔同此時對“雅言”未改初衷,但受日本學校唱歌的影響,開始適度修正對淺白化樂歌的批判態度:他將樂歌的教育功能和藝術性進行了區分,既承認了淺白樂歌所具有的啟蒙意義,同時堅持對樂歌藝術性的追求;對歌詞來源做了調整,不再大量選用古詩詞,而是選擇自己創作的古韻盎然而又淺白易懂的歌詞;不再就此問題發表文論,而是在實踐中尋求樂歌功能性和藝術性的平衡。
李叔同意識到音樂藝術的本位價值,也敏銳發覺音樂藝術接續傳統的重要性,他對音樂藝術性的追求和對文化傳承性的堅守,在啟蒙時期看似“保守”而不夠新潮,但于歷史視域中,又何其“前衛”和先知先覺。從政論兩處談及樂歌歌詞的言論可見,其顯然贊成李叔同所提倡的“雅言”觀點,這與《申報》迎合士大夫階層讀者的一貫傾向有關。
四、古與今:中國傳統音樂的文人立場
學堂樂歌是一場由文人發起并主導的音樂運動,其中以留日學生為代表的文人音樂觀引領主流思潮,文人對于傳統音樂的認知和態度,對此后中國音樂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古樂已亡”說——曾志忞和政論的文化立場
很多雅俗、中西問題的糾葛,源于對古今關系的判斷。20 世紀初,雖然有梁啟超、黃遵憲所推行的“俗樂改良”運動,但是中國“古樂已亡”的觀點,在當時大行其道。曾志忞多有此類言論:“漢以來,雅樂淪亡,俗樂淫陋”?《樂理大意·序》,《江蘇》(東京)1903 年第6 期,第63 頁。“吾中國素有樂也,而今淪亡不再矣!”?《樂典教科書》“自序”,廣智書局(上海)1904 年版。其重視雅樂、輕視俗樂的“雅俗觀”十分鮮明。曾文再次重申此類看法,政論也兩次援引道:“自夫雅樂既亡,正聲闃寂”“吾國樂典已亡,既不能以通行之詞曲,填作國歌”。由此可見,中國傳統音樂已亡所以不拋自棄,已經成為很多文人的共識。
更有甚者,認為此時的中國音樂實為“亡國之音”[21]匪石《中國音樂改良說》,《浙江潮》(東京)1903 年第6 期,第4 頁。。從政論“寶常聽樂,知隋將亡,斯正今日之現象矣”的論述可以看出,《申報》也是支持該論斷的。比較1899年該報政論《雅樂復古說》[22]載《申報》1899 年9 月21 日,第1 張。中“崇雅抑俗、排斥西樂”的觀點,可見其立場變化之顯著。直接原因是《申報》于1905 年為順應變法立憲潮流,撤換因循守舊的主筆黃協塤,改組后留學回國人員在編輯部占了很大的比例,[23]付琳茜《清末報律頒布前后〈申報〉的反應》,《新聞世界》2012 年第4 期,第150 頁。報社輿論導向、文化立場發生巨大轉變。
《申報》政論只是社會輿論的縮影,“古樂已亡”說的根源存于社會深層肌理之中:第一,“古樂”及傳統樂教無法滿足新式學堂的亟需。自漢代以來,中國傳統教育制度里一向沒有音樂這一科目,導致沒有一套完整的音樂體系來應付時代巨變,[24]劉靖之《中國新音樂的緣起、發展和風格》,載劉靖之《論中國新音樂》,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9 年版。這是中國傳統樂教的自身缺陷。第二,文人的身份立場和價值觀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傳統觀念中,文人大多認為音樂不是一門學科,并且崇尚雅樂而蔑視俗樂,這導致其傳統音樂素養有限且帶有認知偏狹,“對于中樂并不研究”[25]李榮壽《西洋學校唱歌教學之略史》,《音樂季刊》1924 年第4 期,第2 頁。成為普遍現象,所以在遇變革需求之時,棄中就西、薄古厚今也就極為決然和徹底。
(二)從《國學唱歌集》到《昨非錄》——李叔同音樂觀的嬗變
與曾志忞具“革新性”的立場不同,李叔同早期樂歌編寫注重傳統詩詞和傳統音樂的運用。在留日之前,痛心于“《樂經》云亡,詩教式微”[26]《國學唱歌集·序》,參見注⑦,第21 頁。,他寄希望以“中體西用”來改變現狀,所以于曲調選用上中西、古今、雅俗兼顧,視野極為寬廣。但他此時的音樂觀,于中樂一方基礎并不牢固,于西樂一側認識也不完全,所以在赴日近距離接觸西方文化后,這種觀念很快有了變化。
1905 年秋東渡日本后,李叔同感喟道:“不佞航海之東,忽忽逾月,耳目所接,輒有異想。”[27]惜霜(李叔同)《圖畫修得法》,《醒獅》1905 年第2 期,第71 頁。他開始在音樂、美術、戲劇等領域大膽嘗試,人生觀和藝術觀也都隨之發生了轉向。[28]豐子愷《我與弘一法師》,載豐陳寶等編《豐子愷文集》(第六冊),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 年版,第401 頁。其音樂方面的變化,鮮明表現在李文《昨非錄》中,稱為“余懺悔作也”,還在文末稱:編寫《國學唱歌集》為“第一疚心之事”希望“毋再發售,并毀板以謝吾過”。這一言論明確否定了此前的《國學唱歌集》,而棄如敝屣之原因卻未道出。學界對此有兩種推測:孫繼南認為,《昨非錄》中批評的我國唱歌集“皆不注強、弱、緩、急等記號”,以及“大半用簡譜”這兩大弊端,在《國學唱歌集》中都存在,李叔同因此而棄之;[29]孫繼南《李叔同——弘一大師的音樂教育思想與實踐》,《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1 年第1 期,第62 頁。戴嘉枋則以李叔同此后再沒有采納過中國傳統音樂曲調進行樂歌創作為依據,認為他是在日本受西方音樂文化中心論的影響而不再偏著于“古調”,所以放棄了《國學唱歌集》。[30]同注?,第3 頁。
從李叔同此后的音樂行為看,放棄《國學唱歌集》極可能受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他于1936 年又作詞出版了一本“有表情記號”且“用五線譜記譜”的《清涼歌 集》[31]弘一法師作歌,劉質平等作曲《清涼歌集》,開明書店印行(上海)1936 年版。;他此后僅有的兩篇音樂文論《西洋樂器種類概說》和《唱歌法大略》(續篇名為《唱歌法大意》),都是西方音樂知識的普及性介紹,不僅再沒用中國傳統曲調編寫樂歌,而且再沒有論及中國傳統音樂的文論。所以戴嘉枋的觀點可能更深刻觸及該問題的根源,即李叔同音樂觀的嬗變。
結 語
如前所述,李、曾二人音樂觀之分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樂歌歌詞的雅俗和處理西方原曲調的原則。而二人的思想共識,即學習西樂,而放棄中國傳統音樂。政論除歌詞的雅言傾向外,旗幟鮮明地支持二人棄中就西的音樂觀念。通過觀照歷史會發現,此時的棄取并非只是藝術上的承風向慕,而更多的是受到時代的驅動和裹挾,以致學習西樂十分“急迫”,而舍棄中樂就尤為“徹底”。
清季,以《申報》為代表的近代中國報紙已然形成一種獨立的、可以引動朝野的“輿論”勢力。而此時的清廷迫于內外壓力,也急于推行變法來維護統治,一時間“朝設一署暮頒一法令”“文告急如星火”[32]梁啟超《上濤貝勒書》(1910 年2 月),載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以教育為例,“原擬用10 年的時間逐步以學堂代科舉,而不過一年,便不能等待學堂制的成熟,就在1905 年把實施了至少千年以上的科舉制徹底廢除”[33]羅志田《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轉折(上)》,《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3 期,第14 頁。。局勢刻不容緩,而倉促之間,將西方“現成”的音樂和教育模式直接“拿來”,要比重新建立傳統樂教體系“便捷”得多。甚至這種“拿來”也待不得認真研判、逐步推行,只能先全面鋪開以求最速,似乎在西樂“亟相輸入”[34]出自曾文,1905 年第14 號,第55 頁。后,中國音樂之發達已“計日可待”[35]出自政論。。這些觀念和舉措將西樂及學校唱歌形式迅速推廣,起到了宣傳思想、開啟民智之功效。但操切之中,“教”與“學”亂象叢生:習得一知半解而好為人師,不知作曲法即作曲,不識調號即翻五線譜為簡譜,欲學一門樂器于數旬間,音階半通、手法未熟即開始表演……這些“亂象”導致樂歌課全面鋪開數年后,“求一小學唱歌教師而不可多得”[36]出自曾文,1905 年第20 號,第68 頁。“求一書一課之完全,亦甚難也”[37]出自曾文,1905 年第14 號,第57 頁。。樂歌先驅們在提倡西學之時,也在多方呼吁音樂教育的規范化:撰寫文章,發行期刊,出版唱歌集、曲譜、教學法,譯介西方文論等,可見音樂家的報國之志和憂民之心。
音樂教育一方面“急迫”學習西方,而另一方面則“徹底”拋棄中樂:“古樂已亡”“社會音樂已不可救”“亡國之音也”……中國音樂似乎只能在學習西方之時,“白手起家”了。但中國傳統音樂被學校教育所拋棄,并非音樂發展的自覺趨向,也不是文化比較后的優勝劣汰,更不取決于音樂家的個人好惡,而是在政治、文化全面取舍之際,被視為千年積弊,不待仔細研究即一并剔除了。
這種急迫而徹底的棄中就西,能否令中國音樂真正發達并取得應有的國際地位?樂歌先驅之間一直存在思想分歧和觀念轉變,其外部更是批評之聲不絕于耳:自20 世紀20 年代,曾志忞開始重新反思樂歌之古今關系,回歸傳統的趨向十分明顯;曾經常住中國的德國音樂家衛西琴(Alfred Westharp),在1914 年樂歌方興未艾時便指出:中國學習西方音樂,也沒學習到點子上,因為“歐洲之真先進……莫不了然知保存國種特性,為教育之一大事”[38]〔德〕衛西琴(Alfred Westharp)著,嚴幾道(嚴復)譯《中國教育議》,《庸言》(天津)1914 年第2 卷第3 號。。衛氏很多極端保守觀念不合時宜,但此言論卻發人深思。
學堂樂歌具有重要的啟蒙及開拓意義,為中國“新音樂”之先聲!對政論、李文、曾文進行追蹤和比較,反復推敲、品味樂歌先驅的思想要義和心路歷程,有助于反思歷史,審視當下,放眼前路。這也正是以新史料為契機,再度辨析經典文論的目的與意義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