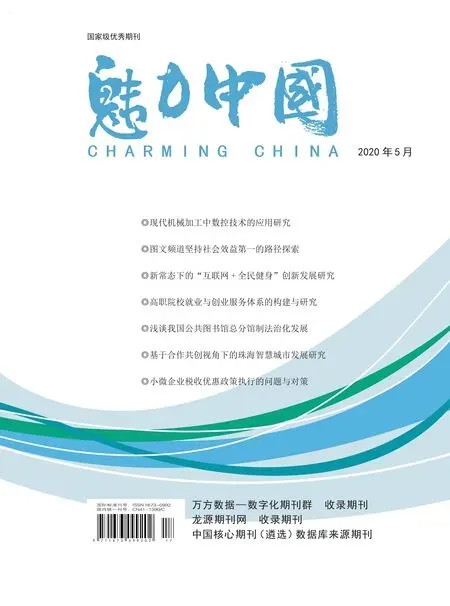意識形態與兒童文學翻譯研究
(河南城建學院外國語學院,河南 平頂山 467000)
一、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現狀
國外兒童文學翻譯的研究先驅當數瑞典人克林伯格(Gote Klingberg),他于1986 年出版著作《譯者手中的兒童文學》,較為系統地研究了兒童文學翻譯過程、問題及對策。以色列學者佐哈爾·沙維特(Zohar Shavit)同年出版著作《兒童文學詩學》,提出以目的語為中心對兒童文學翻譯進行研究。1995 年芬蘭學者Tiina Puurtinen 的《兒童文學譯作中的語言可接受性》一書采用描述性方法對芬蘭兒童文學翻譯的語言規范進行了考察。2000 年,芬蘭另一位學者瑞塔·艾提蘭(Ritta Oittinen)出版了專著《為兒童而譯》,首次提出為兒童而譯的觀點,強調了譯者和兒童讀者的地位。英國著名學者Gillian Lathey 于2006 年、2010 年分別出版專著《兒童文學翻譯讀本》《兒童文學中的譯者角色——看不見的講故事人》,對過去三十年的兒童文學翻譯成果進行了系統梳理,并描述了英國兒童文學翻譯史,提出了兒童文學翻譯中的意識形態問題。以上主要是學者專家的個人研究,國外大規模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出現在2003 年,加拿大雜志《媒它》(Meta)出版了一期“為兒童而翻譯”專號,共有25 篇學術論文。2005 年12 月,英國倫敦召開了一次兒童文學研究的國際會議,會后,出版了論文集《沒有兒童是孤島:兒童文學翻譯》,研究了兒童文學翻譯的諸多問題。
國內的兒童文學翻譯相對落后。國際舞臺上幾乎聽不到中國學者的聲音,國內的學術研究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亟待提高。目前國內的專著僅有三部,1997年李保初的《日出山花紅勝火——論葉君健的創作與翻譯》;2010 年李麗的《生成與接受——中國兒童文學翻譯研究(1898-1949)》;2013 年喻海燕的《陳伯吹兒童文學翻譯思想研究:以改寫理論為視角》。通過檢索中國知網的論文,可以看出近年來兒童文學翻譯研究數量在不斷增加,但總體質量還需提高,發表在核心期刊的文章不足十篇。
二、意識形態與兒童文學翻譯的關系
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總體上處于邊緣地位,意識形態概念的引入,可以拓寬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的范圍。首先將意識形態納入翻譯研究視野的是巴斯內特(Susan Bassnet)和勒弗菲爾(Andre Lefevere),從而使意識形態和翻譯相互關系的研究成為了一個熱點。羅特曼(Yury Lotman)是這樣描述意識形態的,“框架性觀念,它由某個社會在某個特定時期可以接受的思想觀點和態度構成,讀者和譯者通過它接近文本。” 《現代漢語詞典》對意識形態的解釋是:“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形成的,人對于世界和社會的有系統的看法和見解,哲學、政治、藝術、道德等是它的具體表現。意識形態是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在階級社會里具有階級性。也叫觀念形態。”總的來看,意識形態的內涵涉及到了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意識形態是一種企圖,會通過敘事宣傳或強加某種社會政治態度給讀者,同時也會反映作者有意或無意的觀念和信仰。這在兒童文學中尤其明顯,因為文本需要影響兒童的生活,并引導兒童的社會化。”(約翰·史蒂芬斯:2010:5)兒童文學中的意識形態主要通過敘事直接或間接地呈現在兒童讀者面前。換句話說,兒童文學文本中的意識形態或顯而易見,或暗含在文本中。普遍認為兒童文學的功能之一是促使兒童的社會化,因此兒童文學是一個具有意識形態的特殊文本,能夠明顯或潛在地影響讀者。
三、意識形態對兒童文學翻譯文本的選擇影響
兒童文學的創作與翻譯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不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譯本很難通過審查并出版,這就決定了譯者在選擇翻譯文本時會考慮能否出版發行的問題。各歷史時期不同的意識形態,都會影響兒童文學翻譯的選材。由于具有現代意義的中國兒童文學所走過的是“一條先有外國兒童文學的譯介和外國兒童文學理論的引入,后有兒童文學創作的道路”(李麗,2010:23),選擇翻譯什么樣的文學文本就顯得影響重大。本文擬分四個時段對翻譯文本做意識形態方面的描述,分別是清末民初(1898-1919)、民國時期(1911-1949)、新中國前50 年(1949-1999)、21 世紀前20 年(2000-2019)。前兩個時段以李麗女士著作《生成與接受——中國兒童文學翻譯研究(1898-1949)》所提供的翻譯編目為基礎,后兩個時段沒有專門的研究,只能從現有的著作中管窺一二。
第一階段清末民初(1898-1919)的翻譯篇目只有131 篇/部,翻譯文本主要來自于歐洲(81 篇)、亞洲(20 篇)、美洲(6 篇)、區域不明(24 篇)。這一時期的兒童文學翻譯活動比較零散,大多是從英語和日語轉譯。翻譯的作品主要有以下幾類:法國凡爾納和日本押川春浪的科幻小說;以及《一千零一夜》、《伊索寓言》等經典著作。清末民初有代表性的譯者當屬林紓、魯迅、包天笑、孫毓修。其中林紓譯《希臘名士伊索寓言》、魯迅譯《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包天笑譯《馨兒就學記》(即《愛的教育》)、孫毓修編譯《童話》。這一時期的翻譯作品以科技翻譯為主,兒童文學只是零散出現。
第二階段民國時期(1911-1949),兒童文學翻譯篇目有460 篇,比第一階段有所增加,考慮到時間段跨越39 年,比第一階段時間多了17年,實際增加書目有限。這一階段的兒童文學翻譯來自于歐洲(342 篇)、亞洲(48 篇)、美洲(69 篇)、非洲(1 篇)。翻譯作品以俄國(蘇聯)、英國、美國、法國、丹麥作品為主。這一階段中國文學正從封閉式的發展融入世界文學的潮流,經歷了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歷史時期,如五四運動、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兒童文學譯介的第一個高潮期是五四時期,也是中國現代意義的兒童文學產生期。30 年代后,中國社會形勢急劇變化,左翼文學聲勢浩大。兒童文學翻譯參與了這一歷史進程。革命斗爭中產生的翻譯作品反映了戰爭需要,這一時期的翻譯作品內容主要是戰爭與兒童的故事和科學文藝,成為30 年代、40 年代兒童文學譯介的中心。
第三階段新中國前50年,可分為兩個時期:新中國成立至文革結束(1950-1977)和改革開放至20 世紀末(1978-1999)。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兒童文學翻譯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下,兒童作為“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受到高度重視,翻譯文本的選擇基本趨向于教育方向,即共產主義教育,翻譯服務于教育兒童,并配合各項中心運動,整體上這一時期的翻譯文本選擇比較單一。改革開放的春風吹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兒童文學翻譯進入了數量井噴時期。這一時期,翻譯活動突破了教育工具論的束縛,走向了多元價值時代。
第四階段21 世紀前20 年(2000-2019),進入21 世紀,兒童文學翻譯有了新的發展。翻譯的數量和質量大幅提高,同時呈現出新的翻譯熱點。圖畫書的翻譯引進成為這一時期的耀眼明星,從翻譯到本土創作,圖畫書又一次見證了兒童文學走過的道路,即先出現翻譯,再有創作。人們耳熟能詳的翻譯作品大多出現在這一時期。如《愛心樹》《野獸出沒的地方》《逃家小兔》等等。除圖畫書外,翻譯出版了大量兒童文學其他類的作品,如科幻小說、童話、百科、立體書等,風靡全世界的魔幻小說《哈利波特》系列就是21 世紀初翻譯出版的。還有無數的兒童經典名著得到了重譯,煥發出新的生機。
四、意識形態對兒童文學翻譯策略的應用影響
意識形態不僅影響了翻譯文本的選擇,也影響到譯者的翻譯策略和翻譯技巧,是歸化還是異化?是增譯還是刪減?是改寫還是對等?好的譯本需要對翻譯策略、翻譯方法進行研究。兒童文學是為兒童創作的,作家和譯者需要考慮目標讀者的需求和特點。兒童讀者的語言、接受能力、社會心理和美學判斷與成人有很大的不同,譯者的工作就是考慮這些不同并找出適當的策略來達到完美翻譯。不同時期的意識形態對譯者翻譯策略的影響是肯定的,語體是兒童接受文學作品的決定性因素,兒童文學有自身獨特的語體特征。這一語體特征是保證兒童文學可接受性的首要因素。鑒于兒童的接受能力,翻譯語言朗朗上口,具有較強的節奏感和音樂性則更有吸引力。兒童童趣的創造是兒童文學翻譯的本質。風趣幽默的筆調,用富于兒童特色的語言來表現兒童的生活和心理,可以引起兒童的共鳴。優美的語言和動人的情節能夠永遠吸引兒童,譯者要再現詩化的語言,語言應該簡單、形象、優美,同時在目標語中綜合運用多種敘述方法。
五、意識形態對兒童文學翻譯理論研究的影響
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大量翻譯引進了國外優秀的兒童文學著作,翻譯文本從一開始就是中國兒童文學的一大來源,如今也繼續影響并推進著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然而,兒童文學翻譯實踐的盛況并沒有迎來兒童文學翻譯理論研究的熱潮。與實踐相比,理論研究規模小、數量少、質量也尚需提高。不過,值得慶幸的是,上世紀末本世紀初,越來越多的學者把眼光轉向了這一領域,理論研究成果在不斷增加。意識形態的引進正在影響兒童文學的翻譯研究,同時影響中國兒童文學的創作和兒童觀的轉變及發展。
兒童文學翻譯實踐方興未艾,理論研究也應該迎頭趕上。新時代意識形態作用下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會更廣闊。
六、結語
意識形態對兒童文學翻譯的影響是無庸置疑的,影響的方式多種多樣,影響的程度有大有小,大到影響文本的選擇、題材的選擇,小到影響具體翻譯方法的運用。意識形態和詩學對翻譯文本進行的操縱性改寫或隱或顯,但卻無法消除。意識形態的引入給翻譯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有效的研究視角,翻譯研究從翻譯標準的框架里跳出來,轉而研究文本之外的因素,從單純的語言層面上轉向研究語言外的文化、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的制約因素。翻譯不是一方凈土,沒有遠離政治、意識形態的斗爭和利益的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