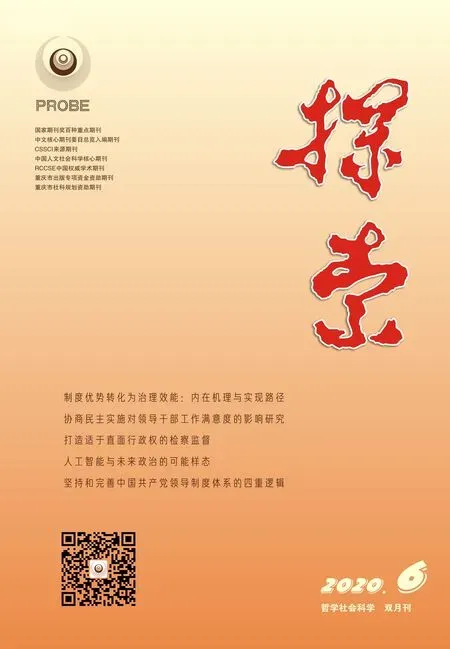協商民主實施對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的影響研究
——基于12省區市領導干部的問卷調查
董石桃,李 強
(廣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廣東廣州510006)
1 問題的提出
民主的本意是民治政府,其實際運行則取決于政治管理者和民眾的互動方式。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全世界范圍內民主的理論和實踐迎來一種協商式轉向,這種協商式的轉向本質上是國家治理過程中政治管理者和民眾互動方式由單一的競爭性選舉,向強調平等、審慎和對話雙向多元互動轉變。從內在的運行結構來看,協商民主包含著“領導干部”和“公眾”兩大主體,在中國語境中主要對應著中國政治體制中黨的領導和群眾路線兩大核心要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而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工作路線,協商民主是連接黨的領導和公眾的關鍵環節。整體上,中國的協商民主過程呈現雙向特征:一方面包含著自下而上的協商參與,即“從群眾中來”的公眾參與;另一方面包含著自上而下的“逆向政治參與”[1],即“到群眾中去”,領導干部走下去主動和公眾協商參與互動,深入群眾之中,體察民情,聽取民意,汲取民智。毛澤東將這種模式視為“最基本的領導方法”[2]897,習近平將其發展為“領導下訪”的有益創舉[3]79。由此觀之,和西方僅僅將協商民主作為代議制民主補充形式不同,協商民主是中國民主政治運行的基本形式,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在中國協商民主運行過程中,領導干部不是被動地,而是主動地聯系群眾、發動群眾,在雙向的協商對話互動中,領導干部有時甚至發揮主要作用。協商民主實施過程中領導干部的工作滿意度,在一定程度上顯示領導干部對進一步推動協商民主發展的信心、態度和動力。因此,協商民主實施對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對協商民主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在實際運行中,協商民主運行績效如何,一方面可以通過民眾的滿意度來予以考察。這方面已經受到學術界較多關注和研究,很多文獻將民眾的民主滿意度視作保持民主的決定性因素和合法性基礎,一般通過檢驗民眾對公共部門績效的認知以及對政府的信任來確認公眾的民主滿意度。另一方面可以通過領導干部的工作滿意度來考察,學界對此卻關注很少。
事實上,政治領導對民主發展的重要影響,是政治發展和組織行為研究的經典主題。布萊克強調政治領導對民主發展的動力作用[4]67。亨廷頓同樣非常強調政治領導在民主進程中的作用,他甚至斷言:“當有智慧、有決心的領導人去推動民主發展的時候,民主就能從應然變為實然。”[5]380英格爾哈特認為,“有效的民主不僅反映名義上有多大程度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而且反映了官員在多大程度上實際尊重這些權利”[6]151。組織行為理論家羅賓斯則認為一個人的工作滿意度水平高,對工作就可能持積極的態度;工作滿意度低,對工作就可能持消極的態度[7]144-145。總之,政治精英的民主取向是民主發展的一個重要驅動因素[8]。此外,較多學者非常重視協商民主中政治精英權威的作用[9],強調領導權威和協商民主的內在兼容和中國傳統,及其現代創新的可能[10]。黨的十九大報告也明確指出協商民主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11]30,這種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在協商民主實踐的微觀層面上,就體現為是否有效推動領導干部的工作,是否提高領導干部工作的滿意度。
因此,協商民主實施中領導干部的工作滿意度如何,一定程度上顯示了協商民主能否有效促進領導干部工作的有效開展,也就能直接反映中國協商民主實際運行的有效性程度及績效。此外,領導干部的工作滿意度也能顯示領導干部后續對于推進協商民主實施的動力如何。如果協商民主的實施不能改善領導干部的工作滿意度,一方面可能顯示協商民主實施有效性不足,另一方面也會造成領導干部推進協商民主的內在動力不足。因此,從動態發展來說,在協商民主實施過程中,領導干部的工作滿意度既是已有協商民主實施所影響的因變量,也是未來協商民主發展的自變量。
那么,當前協商民主實施對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如何,這種影響對協商民主發展的解釋有何理論意義?本文基于全國12個省級行政區領導干部的抽樣調查數據,通過OLS、序次Logit以及廣義序次Logit等計量模型,將協商民主實施作為自變量,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作為因變量展開研究,試圖從領導干部這一行為主體視角,分析協商民主實施對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的影響,揭示協商民主發展的基本動因和發展趨向。
2 理論基礎、研究假設與變量選取
當前對于中國協商民主發展的解釋整體偏向功能主義視域。“功能需求”是功能主義的核心意蘊,本質上是從“他者”來解釋事物發展,因而功能主義主要基于“滿足”觀點來解釋事物存在的意義和價值[12]。對于中國協商民主的發展,功能主義視角主要分析協商民主對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作用,認為政府選擇和推動協商民主發展取決于協商民主對于經濟社會發展、調和各類利益訴求、促進現實問題解決的效用等[13],強調協商民主對于外在“他者”之社會治理、經濟發展、矛盾調和的作用。功能主義重視協商民主實施的外在效用,卻容易忽視主體內在動因及其行為表現,無疑存在一定的缺陷。這也是費孝通在社會學理論上從功能主義到強調“社會是一個具有自己獨立需要的實體”的分析,乃至發展到關注“具體現象的規律性”的特殊主義的原因[14]。具體到協商民主發展的解釋,如果僅僅局限于功能主義的解釋,一方面由于功能主義的目的論傾向,容易導致協商民主發展的工具主義傾向;另一方面容易注重外在的“他者”解釋,而忽視協商民主發展中行為主體內在的動因及由此導致的行為變化。
因此,在協商民主發展的解釋上,有必要超越功能主義的視域,從行為主義的視角來解釋協商民主發展的內在動因和未來趨向。行為主義學派強調“專注環境和行為之間的互動關系”[15],尤其是斯金納強調“研究人的行為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對人的行為以及社會行為的預測和控制”[16]212。社會學習理論則認為“有機體和環境的互動是一個持續存在的過程,經由認知結構的發展和自我控制,人影響環境,同時,也為環境所影響”[17]22,學習過程就是行為-認知-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政治行為主義強調研究過程中人的政治態度和行為規律,側重政治人的心理、動機、價值等內在變量對政治發展的影響分析。總體上,行為主義意味著用跟行為相關的變量來解釋社會問題,強調從主體和外在環境因素的互動來解釋事物發展。從組織行為學來看,分析協商民主實施對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的影響,是從行為主義角度[18]拓展協商民主發展解釋的一個重要切入點。因此,從理論上講,本文是拓展協商民主發展的行為主義解釋的一種嘗試。本文基于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的歸因,從協商民主實施的外在環境因素和過程性變量入手,將協商民主實施的具體要素分成四種,包括實施主體、實施情境、實施方式和實施成效。接下來,我們在文獻綜述的基礎上,提出初步的研究假設。
2.1 協商民主實施主體、情境和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
泰勒(Taylor)最早提出工作滿意度的概念[18]。霍波克(Hoppock)將工作滿意度界定為員工心理與生理兩方面對環境因素的滿足感受[19],即員工對工作情境的主觀反應,此后隨著霍桑實驗開創的行為科學發展,工作滿意度成為管理理論框架中的要素。赫茲伯格(Herzberg)研究發現,影響工作滿意度的因素包括工作本身和工作環境兩個方面,并確認了工作滿意度和績效之間的聯系,即滿意導致高績效,不滿意導致低績效[20]。羅科(Locke)認為工作本身、工作待遇和工作環境對工作滿意度具有重要影響[21]。金順熙(Soonhee Kim)對公共部門的研究表明,領導在工作中運用參與管理的方式是影響工作滿意度的重要因素[22]。但是,蘇鐸(Staw)和羅斯(Ross)[23],以及斯佩卡特(Spector)和奧唐納(O′Connell)[24]研究表明,工作滿意度具有個體特質性。阿維(Arvey)等也強調了個體因素對工作滿意度的解釋效應,但工作滿意度40%到60%的變異量決定于情境因素[25]。協商民主的實施由領導干部推進,根據工作滿意度的理論分析,作為協商民主的實施主體,領導干部的個人特質對領導干部的工作滿意度有重要影響,我們可以根據包括性別、年齡、學歷等個人信息在內的人口學變量來予以測量。同時,人員的組織特性和外在環境影響是預測工作滿意度的重要指標。協商民主的實施處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不同的政府級別,擔任不同的行政職務(行政職務是一種社會角色,角色本質是一種社會期待,并在特定的社會場景中完成角色任務,因此,我們將具有角色內涵的行政職務級別納入實施情境因素中),領導干部所在的政府部門所處的區域等,都是影響協商民主實施的重要社會情境因素。據此,我們可以提出如下假設:
H1: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協商民主實施中領導干部個人因素對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具有顯著影響;
H2: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協商民主的不同實施情境對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具有顯著影響。
2.2 協商民主實施方式、結果和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
領導理論研究表明,領導方式會對下屬的工作行為和態度產生重要影響,其中,正向影響如提升組織忠誠度、建言行為、工作滿意度和工作績效等[26],負向影響如導致下屬離職傾向和反生產行為等[27],從而影響工作滿意度。金順熙(Soonhee Kim)對公共部門的研究發現,領導在工作中運用參與管理的方式,同時員工意識到參與了戰略制定,與工作滿意度呈正相關;主管在戰略制定方面和員工有效地溝通與高工作滿意度呈正相關,因此,工作的運行和實施方式是影響工作滿意度的重要因素[22]。也有針對中國的實證研究直接驗證了領導方式和干部自身工作滿意度的關系,其中任務關系型領導方式和干部自身的工作滿意度存在顯著性關聯[28]。在中國,協商民主通過決策聽證會、干部定期接待群眾、干部熱線電話、黨務會議向群眾或群眾代表開放、接待群眾信訪、多部門聯席協商、黨務政府機關定期收集群眾意見、通過網絡問政平臺與群眾協商、群眾代表對黨委主要領導工作進行年終評議等方式進行,增進了協商民主參與主體之間的相互理解,有力地促進了社會共識的形成,從而提高領導干部的工作滿意度。此外,從程序正義角度看,佩特曼(Pateman)[29]、沃倫(Warren)[30]、費倫(Fearon)[31]等人的研究表明,公眾個體的影響力和政治的信任度與政治合法性認同呈正比,公眾決策參與的程度和決策認同和信任呈正比,錢伯斯(Chambers)等認為協商方式的公開與理性程度才與合法性認同呈正比[32]。林德(Lind)和泰勒(Tyler)[33],泰勒(Tyler)[34]和布雷德(Blader)[35]等人的研究表明,協商民主作為一種民主方式本身就能帶來公平感,能夠提高公眾對決策的認同(滿意感),公眾政策合法性認同的提高反過來也能夠提高領導的有效性,增強領導干部的工作滿意度。據此,我們可以提出如下假設:
H3: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協商民主的實施方式對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具有顯著影響。
協商民主研究的另一個視角是強調結果正義。有研究表明,協商民主使集體決策掌握更多的信息資源,大規模充分的討論可以吸收新的和小眾信息[35],協商民主擴大信息獲取來源,最終可以提高決策的質量[36],從而能夠提高政府的績效。這種績效一方面使公眾獲益,提高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另一方面也提高政治體制運行的經濟和政治績效。此外,通過協商民主方式,讓公眾在利益相關的公共事務管理活動中有更多的參與,公眾在政治協商過程中能夠表達自己的觀點,參與者不僅權衡自身的利益,還要考慮他人的意見,從而能夠減少社會的矛盾沖突,增強社會穩定。協商民主的實施推動了經濟、政治績效和社會穩定等良好政府績效,最終一方面提高領導干部的工作成就感,另一方面也使其在個人職位升遷中獲得更多的機會,從而提高其總體工作滿意度,據此我們提出如下假設:
H4: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協商民主的實施結果對領導干部的工作滿意度具有顯著影響。
2.3 變量選取
有學者對領導干部的協商民主實施滿意度和公眾協商途徑及其實施周期的關系進行了研究[37]。我們認為,這僅僅是考察了影響的單一維度,領導干部對協商民主實施的滿意度的影響因素不僅限于公眾參與途徑的影響。事實上,協商民主的實施包含多重因素,包括實施主體、實施情境、實施方式和實施成效。在本文中,我們試圖按照協商民主“由誰實施—在何種環境中實施—如何實施—實施結果如何”的邏輯進行。本文設定的自變量包括:(1)由誰實施,涉及的是實施主體,即領導干部自身特質;(2)在何種環境中實施,涉及的是協商民主實施的情境,即領導干部實施的場域或角色特征;(3)如何實施,涉及的是協商民主的實施方式,即具體的實施形式和途徑;(4)實施結果如何,涉及的是協商民主實施的績效,即最后實施的社會效果。因變量為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的基本關系如圖1所示。

圖1 協商民主實施和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間的變量關系
3 數據來源與結果分析
本文的數據來源于陳家剛教授主持的2013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研究”課題組實施的“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問卷調查”,由原中央編譯局、清華大學、中山大學合作完成。該課題組抽樣調查了代表中國全部6個主要地理區域的12個省區市。該樣本強調的是副處級或縣級以上領導干部。2015年3月至6月,課題組向12個省級黨校參訓黨政領導干部發放問卷2 880份,完成有效問卷2 223份。剔除部分變量缺失值后,本文的樣本數量為1 712個。本文樣本中受訪者的平均年齡為47.2歲;他們的平均工作年限為20.3年,在現在的崗位上平均工作了5.4年。受訪者在不同的部門工作,包括黨委、政府、人大、政協、司法系統和國有企業。受訪者中女性的比例是21.73%,男性為78.27%,90%的受訪者擁有大學或以上學歷。受訪者中副處級干部的比例為29.21%;正處級干部的比例為45.09%,副局級干部的比例為16.82%。
3.1 協商民主實施主體因素對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的影響
第一,協商民主實施對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影響在不同年齡上存在顯著差異(H1a)。本文發現在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不管實施協商民主的頻率如何,領導干部對工作感到很不滿意的概率均隨著其年齡的增加而增加,對工作感到非常滿意的概率均隨著年齡的增加而降低。在各個年齡點上,協商民主實施的頻次越高,隨著年齡的增加,領導干部對工作感到很不滿意的概率增長十分迅速;同時,協商民主實施的頻次越高,隨著年齡的增加,領導干部感到非常滿意的概率緩慢降低。進一步的研究發現,經常實施協商民主情境下領導干部對工作非常滿意曲線與經常實施協商民主情境下對工作很不滿意的曲線相交于50歲左右。在領導干部50歲之前,經常實施協商民主帶來的工作“非常滿意”的概率的增加超過“很不滿意”概率的增加,而在50歲之后則相反。因此,若考慮當前的工作滿意度將反作用于干部未來推行協商民主的動力,推行協商民主過程中保持干部隊伍年輕化有重要意義。
第二,協商民主實施對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在性別上存在顯著差異(H1b)。本文發現,隨著實施協商民主頻次的增加,男性領導干部對工作比較滿意的概率逐漸減少,對工作非常滿意的概率逐漸增加;而女性領導干部對工作比較滿意和非常滿意的概率逐漸增加。而且不管實施協商民主的頻次如何,男性領導干部對工作非常滿意的概率顯著高于女性領導干部相應的概率;而女性領導干部對工作滿意程度為一般的概率顯著高于男性領導干部相應的概率。
第三,協商民主實施對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在文化程度上存在顯著差異(H1c)。本文發現在其他情況都相同的條件下,領導干部文化程度為高中時,他們的工作滿意為很不滿意和不太滿意的概率非常低;隨著協商民主實施的頻次的增加,他們對工作感到比較滿意的概率逐漸減小,感到非常滿意的概率逐漸增加,呈現出比較滿意的概率先大于而后小于非常滿意概率的總體趨勢。領導干部的文化程度為大專、本科、研究生時,隨著協商民主實施的頻次的增加,他們的工作滿意度為比較滿意和非常滿意的概率逐漸增加,但比較滿意的概率始終大于非常滿意的概率。綜合來看,不管領導干部的文化程度是高中,還是大專、本科、研究生,實施協商民主的頻次越高,對工作比較滿意和非常滿意的概率越高。
3.2 協商民主實施情境因素對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的影響
第一,協商民主實施對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在職務級別上存在顯著差異(H2a)。本文發現在其他情況都相同的條件下,對所有級別(副處級、正處級、副廳(局)級、正廳(局)級)領導干部,隨著實施協商民主頻次的增加,領導干部對工作很不滿意、不太滿意的概率逐漸降低;而比較滿意,非常滿意的概率逐漸增加。我們還發現隨著職務級別的提高,實施協商民主的頻次對領導干部工作比較滿意和非常滿意概率的影響變得更加明顯。這說明在高職務級別領導干部中間實施協商民主對工作滿意度增強效應更加顯著。
第二,協商民主對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在工作單位類型上存在顯著差異(H2b)。本文發現,首先不管工作單位類型如何,隨著實施協商民主頻次的增加,領導干部對工作感到很不滿意、不太滿意、一般的概率逐漸降低;領導干部對工作感到比較滿意、非常滿意的概率上升。其次,從工作單位類型來看,政協、法院、檢察院領導干部,相對于其他工作單位的領導干部而言,感到很不滿意、不太滿意、一般的概率相對來說更低;感到比較滿意、非常滿意的概率相對來說更高。因此總體來看,隨著協商民主頻次的增加,政協、法院、檢察院領導干部相對于在其他工作單位的領導干部的工作滿意度提高得更快,從而使得實施協商民主對于政協及法院、檢察院領導干部的工作滿意度的增強效應高于在其他單位類型工作的領導干部的增強效應。
第三,協商民主實施對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呈現出顯著的地區差異(H2c)。本文發現,北京、福建、河南、廣西等省區市實施協商民主有助于提高領導干部的工作滿意度,而在天津、吉林、浙江、貴州、云南、陜西等省區市實施協商民主,對于領導干部的工作滿意度則沒有顯著的影響。實施協商民主是否對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有顯著影響似乎和經濟發展程度以及區域沒有直接聯系。例如,北京和天津雖然在空間距離上相距很近,經濟發展程度相似,但在北京實施協商民主有助于提高領導干部的工作滿意度,而天津并不顯著。又例如,廣東和廣西兩省區的空間距離很近,在廣西無論是偶爾實行協商民主,還是有時或者經常實施協商民主,都對領導干部的工作滿意度有顯著的影響;但是廣東只有經常實施協商民主,才有助于提高領導干部的工作滿意度。協商民主對領導干部的工作滿意度的影響所呈現出的地區差異可能與當地的文化與傳統有關,這有待于后續研究深入探索其原因。
3.3 協商民主實施方式因素對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的影響
目前各地各級政府實施的協商民主共有九種途徑,分別是(1)決策聽證會;(2)干部定期接待群眾;(3)干部熱線電話;(4)黨務會議向群眾或群眾代表開放;(5)接待群眾信訪;(6)多部門聯席協商;(7)黨委政府機關定期收集群眾意見;(8)通過網絡問政平臺與群眾協商;(9)群眾代表對黨委主要領導工作進行年終評議。每種形式均使用“1=從不;2=偶爾;3=有時;4=經常”來描述開展協商民主的情況。為了簡潔且有針對性地研究協商民主,本文借鑒林莞娟和秦雨構建綜合性指標的方法[38],生成了一個描述協商民主的綜合指標。具體而言,本文將協商民主的9種途徑的各項評分進行加總,再除以總項數并取整,從而開展協商民主的頻次仍然可以使用“1=從不;2=偶爾;3=有時;4=經常”來描述。
第一,經常實施協商民主與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H3a)。我們先使用最小二乘法(OLS)作為基準,簡單直觀地呈現實施協商民主與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之間的關系。表1第一列,我們僅加入實施協商民主綜合頻次;第二列在第一列基礎之上繼續控制領導干部個人因素(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和政治身份);第三列繼續控制協商民主的實施情境(領導干部工作單位類型)和領導干部的職級;第四列繼續控制協商民主的實施結果。本文發現,無論如何添加控制變量,有時和經常實施協商民主,相對于從不實施協商民主而言,顯著地增加了領導干部的工作滿意度。

表1 協商民主與工作滿意度(OLS估計)
第二,協商民主的不同實施方式對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存在異質性(H3b)。我們仍使用OLS方法作為基準,分別對協商民主的各種途徑進行回歸。表2各列采取了與表1第四列相同的模型設定,但為了簡潔明了,本文僅僅報告了協商民主實施情況的系數。表2第一列報告了通過開展決策聽證會途徑(A)實施協商民主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回歸結果顯示,相對于從不開展決策聽證會的參照組而言,偶爾開展決策聽證會與工作滿意度正相關,但并不十分顯著;但我們發現“有時”和“經常”開展決策聽證會均顯著地增加了領導干部的工作滿意度。第二列報告了以干部定期接待群眾形式(B)實施協商民主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其余各列以此類推,結果也較為相似。唯一不同的是,本文發現通過接待群眾信訪途徑(E)實施協商民主對工作滿意度沒有顯著的影響。本文還將所有9種協商民主途徑同時納入OLS回歸方程,其結果與表2沒有顯著差別。我們仍然發現除接待群眾信訪外,其他8種協商民主形式與工作滿意度正相關,而接待群眾信訪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為負。總之,綜合表1與表2的結果說明,雖然個別形式的協商民主對領導干部的工作滿意度沒有顯著影響,但總的說來實施協商民主提高了領導干部的工作滿意度。

表2 不同形式的協商民主與工作滿意度(OLS回歸)
OLS方法雖然簡單直觀,能幫助我們直截了當地觀察協商民主與工作滿意度之間的線性關系,因為每個變量的回歸系數即表明了變量對工作滿意度的邊際影響。然而OLS忽視了工作滿意度是一個序次變量,即1~5從低到高表示出從很不滿意到非常滿意的排序。與OLS線性回歸方法相比,更好的研究方法是使用極大似然估計的序次Logit回歸這一非線性方法。該方法可以通過潛變量推導。其理論邏輯是,我們不能觀察到領導干部使用何種規則評價其對工作的滿意度(),但我們能夠觀察到領導干部的工作滿意度(1~5)。潛變量與解釋變量xi的線性模型如下:

yi由潛變量根據以下規則來定義:

其中γ1<γ2<γ3<…<γM為待估計的參數,稱之為切點 (cutoffpoints),yi取每一個指標的概率如下:
Pr(yi=k1|xi,β,γ)=F(γ1-xiβ)
Pr(yi=k2|xi,β,γ)=F(γ2-xiβ)-F(γ1-xiβ)
Pr(yi=k3|xi,β,γ)=F(γ3-xiβ)-F(γ2-xiβ)
…
Pr(yi=kM|xi,β,γ)=1-F(γM-xiβ)
其中kj,j=1,…,M,為定序變量。在本文中,M=5,k1=1,k2=2,…,k5=5,表示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數值越大表明工作滿意度越高。例如,5表示領導干部對工作感到“非常滿意”,而1表示領導干部對工作感到“很不滿意”。
F是εi的累積分布函數,當εi服從Logistic分布時,Yi>j的概率為:

序次Logit模型暗含的假設是各變量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是平行的,即每個變量對很不滿意、不太滿意、一般、比較滿意和非常滿意的影響均相同((3)式中的β并不隨著j改變)。這一平行回歸假設常常被違背。本文運用龍(Long)和弗里茲(Freese)①J.Scott Long,Jeremy Freese.Regression Models for Categorical Dependent Variables Using Stata[M].TX:Statapress,2014.的檢驗方法,檢測結果顯示,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以及政治身份為中共黨員等變量對工作滿意度不同的水平有不同的影響(限于篇幅未報告)。針對平行回歸假設被違背的現象,已有文獻在序次Logit模型的基礎上發展出了廣義序次Logit模型。該模型不需要平行回歸假設,從而允許變量對不同滿意程度的影響可以不同(βj可隨著j的改變而改變)。

為便于比較,本文在表3的A與B部分分別報告了序次Logit模型和廣義序次Logit模型的回歸結果。A部分第一行表示,在其他情況都相同條件下(以其他變量都處于均值條件下計算),若從不實施協商民主,工作滿意度為很不滿意、不太滿意、一般、比較滿意、非常滿意的概率分別為3.1%、5.9%、33.5%、52.3%和5.2%。余下三行的結果以此類推。(4)-(1)顯示,其他情況均相同條件下,經常實施協商民主相對于從不實施協商民主將提高領導干部對工作感到“比較滿意”和“非常滿意”的概率,降低“很不滿意”和“不太滿意”的概率,如表3所示。

表3 協商民主與工作滿意的概率(序次Logit模型和廣義序次Logit模型回歸)

(續表3)
表3B部分報告了在放松平行假設的廣義序次Logit回歸結果。與A部分不同的是,在其他情況均相同條件下,(4)-(1)顯示經常實施協商民主相對于從不實施協商民主,領導干部對工作感到很不滿意的概率反而增加了8.1%,但領導干部對工作感到非常滿意的概率增加了19.4%。因此,實施協商民主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存在異質性:并不是提高協商民主的實施頻次就一定會提高工作滿意度,而是經常實施協商民主增加了很不滿意的概率,同時也增加非常滿意的概率。只是非常滿意概率增加的幅度超過了很不滿意的幅度,才在總體上提高了工作滿意度。總之B部分的結果說明,放松平行假設確有必要。
3.4 協商民主實施結果對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的影響
本文發現,協商民主實施結果與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正相關(H4a)。從領導干部對協商民主的實施成效的判斷來看,認為協商民主能夠改善政策實施效果的領導干部對工作的滿意程度相對高于那些認為不能改善政策實施效果的領導干部。具體來說,若領導干部認為協商民主能夠改善政策實施的效果,在其他情況均相同的條件下,他們對工作感到很不滿意的概率相對較低,而對工作比較滿意和非常滿意的概率相對較高;相反地,若領導干部認為協商民主不能夠改善政策實施的效果,在其他情況均相同條件下,他們對工作感到很不滿意的概率相對較高,而對工作感到比較滿意和非常滿意的概率相對較低。從領導干部實施協商民主的頻次上來看,經常實施協商民主的領導干部相對于從不實施協商民主的領導干部,他們對工作感到比較滿意和非常滿意的概率更高,而且這一關系尤其對那些認為協商民主能夠改善政策實施效果的領導干部顯著。相反地,在那些認為協商民主對政策實施效果改善不大和不能改善政策實施效果的領導干部中,經常開展協商民主反而降低了他們對工作感到比較滿意和非常滿意的概率,增加了他們對工作感到很不滿意和不太滿意的概率。因此,在認為協商民主能夠改善政策實施效果的領導干部中推進實施協商民主的頻次,將有利于提高領導干部的工作滿意度。
4 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運用調研數據和OLS、序次Logit以及廣義序次Logit等計量模型,對協商民主實施對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的影響進行了實證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結論。
第一,協商民主實施主體因素對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的影響顯著。從年齡來看,領導干部對工作感到很不滿意的概率隨著其年齡的增加而增加,對工作感到非常滿意的概率均隨著年齡的增加而降低。在各個年齡點上,協商民主實施的頻次越高,領導干部對工作感到滿意的概率越高。這意味著需要結合各地實際,針對不同的協商對象、領域、問題、組織方式等,進一步細化細則,在推行協商民主過程中要推動領導干部隊伍年輕化。在性別上,男性領導干部對工作非常滿意的概率顯著高于女性領導干部對工作非常滿意的概率,但女性領導干部對工作滿意程度為一般的概率顯著高于男性領導干部相應的概率。為此,協商民主實施對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在性別上無須確立傾向性的政策。在文化程度上,不管領導干部的文化程度是高中,還是大專、本科、研究生,實施協商民主的頻次越高,對工作滿意的概率越高。但是文化程度高者比較滿意的概率更大。為此協商民主實施中,領導干部的選拔須重視提升文化程度。
第二,協商民主實施情境因素對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的影響顯著。從職務級別來看,隨著職務級別的增加,實施協商民主的頻次對領導干部工作比較滿意和非常滿意概率的影響變得更加明顯。為此,我們須重視職務級別高的領導干部推動協商民主的能動性發揮。從工作單位類型來看,政協及法院、檢察院工作的滿意度高于在黨政部門工作的滿意度。政協協商、司法協商對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提升效應相對要好,為此,我們須重視協商民主在調節社會矛盾和綜合社會治理中的重要意義,進一步提升黨政部門協商對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同時加強行政協商的探索發展。從地區差異來看,實施協商民主是否對領導干部的工作滿意度有顯著影響和經濟發展的程度沒有直接關聯,而可能與當地的文化與傳統有關。為此,協商民主實施后期須重視政治文化、地方文化以及政治生態因素的影響,這種影響可能是隱匿的、深層次的。
第三,協商民主實施方式因素對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的影響顯著。從實施方式來看,決策聽證會、干部定期接待群眾、干部熱線電話、黨委會議向群眾/群眾代表開放、多部門聯席協商、黨委政府機關定期收集群眾意見、通過網絡問政平臺與群眾協商、群眾代表對黨委主要領導工作進行年終評議這八種協商方式都和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正相關。這說明八種協商民主方式對提高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都有積極意義,需要繼續加大力度推進實施。唯一不同的是,接待群眾信訪途徑實施協商民主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為負或者不顯著。這可能由于信訪工作承載了相對復雜的功能[38],在工作上需要面對大量的負面信息和突發事件,從而影響其工作滿意度[39],因而表明信訪需要進一步制度化、法治化。
第四,協商民主實施結果因素對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呈現正向影響。調查結果顯示,協商民主的有效性達78.97%,但是實施協商民主對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存在異質性:經常實施協商民主一方面增加了很不滿意的概率,但另一方面也增加了非常滿意的概率,而且非常滿意概率增加的幅度超過了很不滿意概率的幅度,并在總體上呈現出“經常”相對于“從不”實施協商民主而言提高了工作滿意度。協商民主實施過程中需要重視內在的異質性和不平衡,在實踐過程中不能簡單地以協商實施頻次來評價協商民主的實施,而是將協商民主實施質量提升作為核心和根本。
從理論上來說,本文是試圖超越協商民主發展的功能主義解釋,拓展協商民主發展的行為主義解釋的初步嘗試,致力于從協商民主實施的外在因素和領導干部這一主體內在“工作滿意度”動因的關系出發,探索協商民主實施對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協商民主行為主義的解釋路徑強調的是政治行為者在民主過程中的角色和作用,尤其突出政治領導者的作用。這種研究路向可以在行為主義政治學和政治精英論中找到悠久的理論淵源。但是已有的行為主義理論研究更多的是描述民主過程以及政治行為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往往難以闡明這一角色背后的因果邏輯。跟條件論和建構論相比,行為主義路徑的理論建構往往比較薄弱。領導干部工作滿意度變量在協商民主發展中的引入可以深入到政治行為的內在動因分析,一定程度上可以從行為主義角度彌補協商功能主義研究的不足。下一步我們將進行回訪和跟蹤研究,并對研究結論展開進一步的分析,以期使這一模型能夠得到更為深入的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