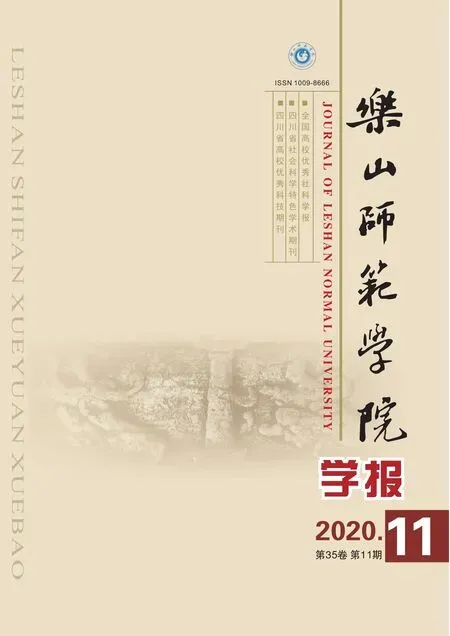白居易詩歌中“直”類意象與其思想變遷探析
郭聰穎
(南京信息工程大學 文學院,江蘇 南京 210044)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生于今河南新鄭。因晚居香山,故自號香山居士。《新唐書》說他聰敏穎悟、過目不忘,“敏悟絕人,工文章”[1]4300。貞元中更是以27歲的年齡一舉得第,“擢進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1]4300。詩人在左拾遺任上以“事無不言”“論執強鯁”為皇帝所器重,但同時也得罪了宦官權貴。元和十年,白居易因詩稿被誣遠放江州,回遷后心境大變,自述:“既失志,能順適所遇,托浮屠生死說,若忘形骸者”[1]4304,“暮節惑浮屠道尤甚,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1]4304,思想漸傾佛道。這一特殊的思想變動過程不僅見諸于歸山結社等行動的“顯筆”,更于創作過程中的意象選擇、情感變化等隱處有彰。
一、白居易詩歌中“直”類意象的基本類型
追尋“直”字字源,“直”字在《說文解字》中解為“正見也”,下文徐鍇注曰:“,隱也。今十目所見是直也。”[2]634這一點也可以從“直”字的甲骨文字形中得到印證:“直”字的甲骨文()形似一只眼瞼上有豎線的眼睛,表示目不斜視。與其他同樣描述事物的物理特征的字不同,“直”字并非依附于事物的某種可見特性,而是表達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抽象概念,其字源義上的這種特性就使其對搭載和表達象征意義留有了更寬廣的空間。
同時,“直”字在文學作品中的應用同樣具有特殊的文化意蘊。
“中國文化是人類文化的早熟”[3],作為文化重要的載體的中國文學也呈現著一種“早熟”的特征。具體表現之一,就是“以物比德”審美觀念對中國詩歌中自然事物描寫的重要影響。胡家祥先生曾這樣界定“比德”的概念;“即將自然現象與人的精神品質聯系起來,從自然景物的特征上體驗到屬于人的道德含義,將自然物擬人化”[4]。在這種特殊的審美規則和中國含蓄內蘊的獨特表達方式的雙重內化下,中國文人往往把自己對于美好品德的追求放在對自然事物的某些相似特征的喜愛和向往上,并將自然事物人格化;這也就賦予了“曲”“直”“剛”“柔”這些普遍的物理特征以獨特的意味。具體到白居易身上,這種以物比德的審美范式就完美地應用于他“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5]的文學主張中。其欣賞和描寫自然事物極少單純停留在對物象表層化和結構化的審美和敘述,而更多是由理性思維出發,去探討物象所具有特征體現出來的人化的品質和精神。
所謂意象,就是“融入了主觀情意的客觀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觀物象表現出來的主觀情意。”[6]即詩歌中可被劃分的、同時含有詩人主觀情感投射以及客觀形態的名詞性詞語或詞組。而“直”字及其在詩歌中所修飾的名詞性詞組恰巧完美地貼合這一標準,這也是本文提出“‘直’類意象”這一定義并加以探討的理論根據。
《全唐詩》中所收錄白居易的3009首詩歌之中,共計有105首在詩題或內容中含有“直”字,再依照上文中提到的標準排除掉作為名詞、副詞、連詞和介詞使用的不在本文討論范圍之內的詩歌,共計36首。“直”既然作為一個特殊的形容詞在詩中使用,那么它所修飾的意象自然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相似。為探討使用“直”字所修飾的意象在選擇和情感表達上的異同,我將這36首詩按照意象的性質分為植物類(7首)、工具類(4首)、人物類(14首),其余出現頻率不高或情感表述并不十分強烈的11首歸入其他類。
二、從“直”類意象內涵變化看白居易思想變遷
日本學者丸山茂就曾直言白居易詩歌的創作的一大特點就是慣于將自己的日常生活細節以及其時的心境寫入作品,導致其詩歌實際上是一部部“回憶錄”:“一首首歌詠人生一幕的詩歌一作某種匯集,就成為原原本本地再現作者全部品性的‘因緣’。”[7]詩人也曾在《醉吟先生傳》(卷七十)中直言:“凡平生所慕所感,所行所喪,所經所遇所通,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中,開卷而盡可知也,故不備書。”
白居易這種個人經歷與詩歌創作的互動影響也在其含“直”類意象詩歌作品上有所體現。將36首作品編年后以812年白居易母喪返鄉和818年量移忠州的兩個人生轉折點為界[12]劃分為三個階段,我們可以發現每一階段作品中“直”類意象的政治隱喻和感情表達都有一定共性,各階段之間也隨著詩人個人經歷和人生哲學的變化而有所差異。
第一階段為公元800—811年,詩人從盩厔小尉一路擢升至左拾遺兼任翰林學士,共有含“直”類意象詩歌作品16首,作品與生平整體表現為“直”主導思想并指導社會實踐;第二階段為公元812—818年,詩人先因母喪退居渭上,回朝后又被羅織罪名遠謫為江州司馬,期間共有作品9首,可概括為詩人“直”的理念與現實實踐割裂期;第三階段為公元819—842年,白居易量移回朝重為近臣,共有作品11首,表現為其思想和行為在“中隱”中回歸統一。
在早期理想與現實高度融合階段,詩人“直”類意象使用最為頻繁、詩歌情感昂揚向上,主要書寫自己對剛直不阿、寧折不彎的思想品質的向往以及以己之力促成元和中興的儒家濟世理想;詩歌語言尖銳鋒利、咄咄逼人,多新樂府詩,諷喻詩是詩人這一時期的創作主流。遭貶江州后,詩人陷入儒家“兼濟”理想與中唐“獨善”全身的現實矛盾之中,思想多有搖擺,“直”類意象詩歌數量大幅減少。一方面詩人仍然認可儒家“入世”“濟世”理想的正確性;但另一方面又對統治者的賢明以及政治的公正產生質疑,創作了大量倒向佛道的玄言詩。晚年重新啟用后,詩人徹底確立“中隱”的政治思想觀念。筆下的“直”字漸漸不再具有情感寄托以及象征諷喻的作用,描寫意象由實轉虛,“直”類意象與其以物比德的審美價值脫節。每階段的詩文文本細讀以及具體論述如下:
(一)“孤直當如此”:“直”理想的建構與實踐
1. 出仕與風塵走吏(800—808年)
詩人出仕在一個好年份。安史之亂引發的余波稍稍平息、政局穩定向上,貞元十八年韋皋更是以維州之戰擊敗吐蕃,給長期來犯的吐蕃及回紇以震懾,奏響唐軍的末代盛歌。整體社會的回彈無疑給無數知識分子以匡扶社會重現盛唐以信心和責任感,新及第的白居易自在此列,這一點也充分體現在了他此時期的詩歌創作之中:
(1)這一時期詩人尤其偏愛“直”類意象使用。年平均數量為2.3首,僅次于在任左拾遺的政治最高峰時期;且詩中反復重申雖然官職微賤,仍希望以己之力祛邪扶正,為唐代中興奉獻自己的一份力量的愿望。如《有木詩八首八》(卷一)中詩人自比為丹桂,雖然礙于年輕和職位低微“干細力未成”,“重任雖大過”,還沒有能力承擔大的責任或有顛覆性的建樹;但強調了自己孤傲高潔、忠心為國“不容凡鳥宿”“直心終不曲”;所以“縱非梁棟材,猶勝尋常木”;希望得到匠人,也就是現實世界中的統治者的重用。
(2)大量搭配工具類意象,占總數的57%。工具類的劍與筆兩種意象對于詩人來說,本質上都是他直指宦官污吏以及社會黑暗的有力武器。筆是具象化的,象征著作為文官的諫言有所生效;劍是抽象化的,是政治黑暗、皇帝為宦官所挾的中唐現實里,作者對統治者和體制的失望以及自己文人身份的無力感具有反彈性質的偏激表現。所以以直修飾工具類意象詩歌的感情普遍是激進的,除了喜愛、欣賞和憐惜,還往往對劍和筆這兩類相當于自己某一部分象征的工具有所代入和共鳴,表現出“寧為玉碎”的決絕之感。例如《折劍頭》(卷一):
拾得折劍頭,不知折之由。一握青蛇尾,數寸碧峰頭。
疑是斬鯨鯢,不然刺蛟虬。缺落泥土中,委棄無人收。
我有鄙介性,好剛不好柔。勿輕直折劍,猶勝曲全鉤。
詩人描寫這個故事的意圖在于最后兩句,表達自己是賞識折劍的“伯樂”,并直露地表示自己認為剛勝于柔、直勝于曲;寧愿效仿寶劍直折隕落也不愿意像鉤刃一樣委曲求全,為外物所改變。表達了自己寧折不彎的政治抱負。又如《李都尉古劍》(卷十二)中認為君子應當像匣中寶劍一樣,生來就要胸懷大抱負,不為小的利益所奔走驅使,并懷有隨時為理想而死的信念(“可使寸寸折,不能繞指柔”“勸君慎所用,無作神兵羞”)這無疑與我們所了解的后期以“中隱”思想而著稱的白居易大不相同。
2. 擢在翰林,身是諫官(809—811年)
809年升任極受皇帝重視的諫官近臣左拾遺任上并兼任翰林學士的白居易,不僅積極大量進諫如降系囚、蠲租稅、放宮人、絕進奉、禁掠賣良人等一系列民本思想為主的諫言并一一得到了皇帝的采納和稱贊(“居易文辭富艷,尤精于詩筆。自讎校至結綬畿甸,所著歌詩數十百篇,皆意存諷賦,箴時之病,補政之缺……章武皇帝納諫思理,渴聞讜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為學士”[9]);還走在了彈劾奸佞之臣的第一線上(《論裴均違制進奉銀器》等),與此同時,女兒的降生還有妻兄(楊汝之)的升任也成為官場之上意氣風發的詩人強大的心里后盾。如果無視官職品級的高低,單論在任成就的多少和詩人的政治積極性與統治者重視程度的配合的話,可以說這一年是白居易一生之中政治生活無疑的頂峰了。
本時期“直”類意象詩歌的藝術特點主要體現在:
(1)積極進取;詩歌中政治諷喻意義增強,直指統治者
這一時期憲宗對白居易政治理念的認可和對其的提拔重用無疑使自身對所任官職的認同感及自身的責任感得到了明顯得增強,反映在作品之中,比起正面的贊美和歌頌,這一階段詩人的作品尤其是諷喻詩大開針砭之門,開始大規模的對并不完美的現實進行不留余地的譏諷。甚至直指封建統治者。正如《新樂府 紫毫筆》(卷四)一詩中所說,“君兮臣兮勿輕用,勿輕用,將何如。臣有奸邪正衙奏,君有動言直筆書。慎勿空將彈失儀,慎勿空將錄制詞。”作為言官要愛護手中那支筆,也就是要愛護自己作為刀筆吏的職責,既然要說要寫,就要一針見血、切中肯綮。
又如《賀雨》(卷一)中雖然也對皇帝從自身做起夙興夜寐減少朝貢、積極賑災進行了歌頌(乃知王者心,憂樂與眾同)。但也在大旱降雨風調雨順的積極盛世中認真思考政治形勢,并沒有一味的吹噓,而是適時地為“天聰”潑了一盆冷水,君明臣忠自然是社稷之福,但登基之處的維持是簡單的,困難的是長久的維持清平的狀態(“君以明為圣,臣以直為忠。敢賀有其始,亦愿有其終。”),結合憲宗元和末年的政治崩盤,可以說詩人的思考是十分現實到位的。再比如810年因摯友元稹冤貶而作的《和答詩十首和陽城驛》(卷二)中詩人用“誓心除國蠹,決死犯天威”一句,不僅表達了自己為國除害的決心,并且直白的將所謂國蠹與統治者劃分為了同一陣營。這種對朝堂結黨營私風氣以及唐憲宗庇護宦官現象不滿的流露就變得更為明顯。
(2)修飾意象偏好上,朋友和自身遭遇成為該時期描寫的一個中心
這一時期所創作的九首含“直”類意象詩歌中有八首中心修飾意象都是人物。朋友一直都是詩人作品中的重要的命題。而“直”這個形容詞在中唐這樣一個黑暗的政局里難免帶上了許多“過剛易折”的意味,白居易一方面欣賞和佩服朋友們剛直不阿的品行,另一方面又痛心其時“直筆”與“剛腸”不僅不能得到重視和褒揚,甚至往往因此招致禍愆。
以《哭孔戡》(卷一)為例,詩人開篇痛陳“洛陽誰不死,戡死聞長安。我是知戡者,聞之涕泫然”,以逝者知己的立場營造了一個極具情緒化飽含憤怒與力量的開篇,但這種憤怒并不是筆直的發泄,而是在開局的爆發后有明顯的回撤,而這種回撤明顯是由于現實社會與詩人所接受的儒家理想社會范式之間的出入所引起的。人人都說在清明的時代“非義不可干”、“其道直如弦”的孔戡應該“在朝端”,“居憲府”,這也是詩人心目中認定的明主忠臣的儒家社會理想范式,但好友卻“沒齒為閑官”,“斂葬北邙山”,這樣的矛盾使詩人感到憤怒之余還帶來了困惑,在他此前一路順遂高歌猛進的政治事業體驗中,始終對對他有知遇之恩的憲宗予以極高的評價,但身邊好友一個個不得重用、遠謫、暴卒的悲劇結局又使他警醒懷疑,如果沿襲近千年的儒家范式是不會錯的,那么錯的是誰呢(“謂天果愛民,胡為奪其年”)?再結合《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四》中孔戡極諫而卒的記載(“戡每秉筆至不軌之言,極諫以為不可,從史怒… …戡不調而卒,贈駕部員外郎。”)很明顯詩中所歸罪的“上天”就是暗示常常自稱為天之嫡長子的封建統治者;詩人藏在文間殷切的質問著“茫茫元化中”的“執如此權”者唐憲宗為何對孔戡一般“平生剛腸內,直氣歸其間”的賢者忠臣視而不見。這種不顧自身安危的奮筆直書自然是因為詩人身上有著濟世安民的責任感,不過也有對友情的珍惜和對友人的痛惜。
對此,詩人曾在《與元九書》中說道:
凡聞仆《賀雨詩》,眾口籍籍,以為非宜矣;聞仆《哭孔戡詩》,眾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游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遍舉。
不相與者,號為沽譽,號為詆訐,號為訕謗。茍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誡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為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
“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而在含有“直”字的八首人物詩中,有六首都是寫給詩人現世的親朋。也是由此,我們能感到詩人在寫及這一類詩篇時感情有所回撤,不再像工具類、植物類那樣恣肆而外顯。在強硬表達“直諫從如流,佞臣惡如疵”(《和答詩十首和陽城驛》(卷二))的同時也有“常恐國史上,但記鳳與麟”(《贈樊著作》(卷一))的擔憂,和“謂天果愛民,胡為奪其年”(《哭孔戡》)的困惑與不滿。詩人既從理性上贊賞和欣賞朋友們的寧折不彎,又難免在感性上希望自己的朋友能在政治亂局中得以保全,“每惜若人輩,身死名亦淪”(《贈樊著作》)。這種“獨善”與“兼濟”的矛盾伴隨了詩人大半生,直至中隱思想的確立方有所緩解。
俗話說: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這里的“理”就是指物理。由此可見,物理知識的重要性。實際上,高中物理知識與我們的實際生活具有極其密切的關系,更是進行電能、熱能、核能等科學研究的基礎學科。隨著課程改革的不斷深入,在核心素養語境下,如何幫助學生找到學習的方法,使他們掌握提分的技巧,就成為當前高中物理教師亟待解決的問題。接下來,本文將闡述在高中物理教學中有效的學習方法和提分技巧。
(二)“拙直不合時”:理想與現實的矛盾與背離(812—818年)
元和六年(811年)四月,白居易的母親白陳氏在長安宣平里逝世,此時任京兆府戶曹參軍的白居易尊制丁憂,離職與家人回到故鄉下邽料理喪事。詩人沒想到的是四年的丁憂期間朝堂的形勢已天翻地覆,除服回朝擔任閑職的白居易積極諫言遭到了誣陷與彈劾,終于在元和十年(815年)遠謫江州。這一次的巨大打擊對詩人的思想轉變產生了極大影響,“兼濟”的理想與只能“獨善”的現實矛盾使詩人時刻在尋求解決和出路,這種矛盾與搖擺也體現在了作品之上:
1.對早年行為的回顧與反思
“一朝歸渭上,泛如不系舟”(《適意二首一》(卷十三));此次借為母丁憂暫時掛冠重歸故里的白居易自進士及第以來第一次有了大段的空白時間,賦閑無事的詩人自然就會對自己近十年來的仕宦生涯進行回顧和總結。而反復思考之下,他發覺,自己仕途的多舛恰是他引以為傲的剛直的性格和行為舉動所引起的(“早歲從旅游,頗諳時俗意。中年忝班列,備見朝廷事。作客誠已難,為臣尤不易。況余方且介,舉動多忤累。”《適意二首二》(卷十三)),歷數十年仕宦,詩人捫心自問自己一直都是按照理想中的“直道”在從政和生活,但卻一再受挫,此時置身事外重返閑適的田園生活,從政的想法與改革的熱情自然也就有所消退(“直道速我尤,詭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內,消盡浩然氣。”《適意二首二》),與此同時故鄉下邽優美的田園風光以及與親朋好友重聚,閑適的田畝也助長了這一消退過程(“憶為近臣時,秉筆直承明。春深視草暇,旦暮聞此聲。”《聞早鶯》(卷七)),使白居易有了棄世隱居的念頭(“自從返田畝,頓覺無憂媿。蟠木用難施,浮云心易遂。悠悠身與世,從此兩相棄。”《適意二首二》)。
對仕途的幻滅感,想要及早退步抽身的頹唐情緒成為這一時期詩作的主要情感基調。這種消極情緒的上升與其作為主導的積極入世思想就形成了對抗和矛盾,并也為后來佛道思想的入侵提供了條件。
2.對現實的態度:從抵牾到調和
將詩人分別作于公元817年所作的《偶然二首一》(卷十六)與公元810年所作的《哭孔戡》進行對比,我們就能感受到白居易在這一階段對“直”認識的有趣轉變。同樣都是描寫“直臣遭疑”這一事件,同樣都將統治者難測的心意比喻成“天”的變化。早年的白居易對這個“天”的態度是不滿,同時所采取的行為是質問,但經歷七年官場的磨礪和碰壁,詩人開始與莫測的天意逐漸達成和解。面對“直”的屈原遭疑沉江和“賢”的賈誼遠謫的兩場“冤案”(“楚懷邪亂靈均直,放棄合宜何惻惻。漢文明圣賈生賢,謫向長沙堪嘆息。”),詩人不再對爭吵和質問,反而安慰自己說人事的反復變化哪有什么稀奇的,即使是天象觀測也沒有什么十拿九穩的,月亮離開畢星雖然是下雨的征兆,有時不也不能驗證嗎(“人事多端何足怪,天文至信猶差忒。月離于畢合滂沱,有時不雨何能測。”)。從中我們就可以看出詩人早年激進有為的政治信念的一種消解,經歷了丁憂的除服不詔和《看花》、《墮井》的莫須有罪名,時任江州司馬的白居易雖然仍在地方實踐并貫徹自己一直以來的民本思想,但其中激進忘我的色彩已逐步暗淡,詩人早年所恪守的“孤直當如此”的社會信條已逐步回撤成對道德修養的個人要求,不再要求朝堂和統治者給予重視和回報;而這種對統治者要求的降低正是詩人對唐憲宗失望以及對“元和中興”無望的體現。這種色彩上的蛻變在詩人818年寫作的《江西裴常侍以優禮見待又蒙贈詩輙敘鄙誠用伸感謝》(卷十七)中表露的更加直白:
一從簪笏事金貂,每借溫顏放折腰。長覺身輕離泥滓,忽驚手重捧瓊瑤。
早年極具政治熱情的詩人在此階段已將仕宦描述成了“折腰”“泥滓”,并以市馬為喻,略帶苦澀的調笑自己年近半百,回朝的機會渺茫。整首詩的前三聯都透露出憂憤苦澀的謫遷意識,似乎作者已經對朝廷完全失去了信念;但最后一聯峰回路轉,一掃前文低沉情緒基調,開始設想有朝一日能夠重回朝堂在長安與友人相見,并表明自己雖然歷盡仕途坎坷,但壯心與直氣仍得到了保存。進,詩人對朝堂的信念感已經嚴重回落;退,“壯心直氣未全銷”的詩人又不甘于在地方敷衍度日。另外有趣的是,詩人812年所作《適意二首二》中又有“胸中十年內,消盡浩然氣。”之句,這種理想上的回撤與行動上的矛盾成為這一階段作品最主要的特征。
3.儒釋道的融合與對立
如上文所述,此時的詩人陷入了理想與現實、“直”與“隱”的思想困境,而于其時,尚未探索出“中隱”之道的詩人找到的解決方案就是投身宗教,希望從佛老的空無思想中尋求解脫的方法。如《酬贈李煉師見招》(卷十六)一詩,就將道家的“長生”與十數年的坎坷仕途對立起來,表明自己遠離世俗功利的決心。“幾年司諫直承明,今日求真禮上清。曾犯龍鱗容不死,欲騎鶴背覓長生。”到詩人814年所作的《游悟真寺詩》(卷六),就更將詩人自小所受的儒家文化教育與講求頓悟的南宗禪法、道老思想融匯一爐,得出昔日里行動舉止“拙直不合時”的結論,并下定決心“終來此山住,永謝區中緣”。
我本山中人,誤為時網牽。牽率使讀書,推挽令効官。
既登文字科,又忝諫諍員。拙直不合時,無益同素餐。
身著居士衣,手把南華篇。終來此山住,永謝區中緣。
真正的歸隱山林詩人當然是做不到的,但對于佛老思想的吸收,和對儒家中庸思想的提取,的確構成了白居易后面所秉持的“中隱”思想的雛形。
(三)“直致櫻桃樹已枯”:思想與行為在“中隱”中重歸統一(819—842年)
從元和十年被一紙詔令下貶江州到元和十三年得以量移(唐朝人得罪貶竄遠方,遇赦改近地,謂之量移[10])有望回朝之間的的三年貶謫時光里,中唐政局動蕩、人事也有大的調整,但昔日站在皇帝身邊身處政治最中心的白居易卻被遺忘在了江州。這三年目睹變革卻無法參與其中的經歷不斷消耗和磨損著詩人的政治熱情,以至于在量移忠州、入刺蘇杭,得到機會重為近臣后他對政治參與和變革的熱情未得到回溫。如果說身在棄置之地使詩人還有含冤被貶的牢騷、對朝堂有所關注,那么反而正是冤屈得以洗刷、重為近臣解開了他對朝堂最后的心結;配合著中晚唐宦官專政腐爛不堪的政局使詩人的政治熱情歸于寂滅。
大和九年“甘露之變”爆發,一場鏟除閹黨的謀局演變成宦官挾持天子大肆屠戮士大夫的政治悲劇。而本應參與其中的詩人,因辭官分司遠離長安恰巧從中全身而退。慶幸之余,以白居易為首的一批東都文人對政局的悲觀也達到了頂峰。從此詩人頻繁請辭重要職位,官職于白居易而言不過是“不勞心與力,又免饑與寒。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中隱》(卷二十二))的一處寄放身形求取“伏臘資”的隱居之所。
終于在經歷了言行一致急諫激進的青年、矛盾反復的中年之后,詩人的思想行為又一次在晚年求索得到的“中隱”之中再次得到統一。此時也就意味著“直”類意象在詩人整個詩歌創作生涯之中的認可降到了最低點,表現在作品之中即政治象征意味減少,閑適詩數量超過諷喻詩,作品整體情緒由積極轉為消極。
1.對仕宦的心灰意冷:“直”類意象象征意義被稀釋
該特點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這一階段的“直”字所修飾的意象漸漸流于虛空而不實寫,意象類型統計中該階段72.7%的意象均被劃分到了“其他”類,不再具有明顯得感情寄托和象征作用。如“瞿唐呀直瀉,滟滪屹中峙”和“直沖行徑斷,平入臥齋流”描寫的是“水”;“碧縷爐煙直,紅垂佩尾閑”、“孤煙生乍直,遠樹望多圓”描寫的是“煙”;“緩聲展引長有條,有條直直如筆描”、“信意閑彈秋思時,調清聲直韻疎遲”描寫的是樂音。
“直”這個字與其象征意義和比德審美價值在詩人的筆下漸漸稀釋和脫節了。
2.中隱的確立:閑適而且消極
情緒和審美的變化我們在詩人806年新宦所作的《云居寺孤桐》和812年矛盾期所做的《栽松二首 二》(卷十),以及842年半俸“退休”時所作的《宴后題府中水堂贈盧尹中丞》(卷三十六)中就能得到深切的體會。
同樣是修飾植物類意象,年輕時詩人見到挺拔剛直的梧桐想到“直從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無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孤直當如此”,默默許下自己如同自萌芽而“直”、從毫末而“高”的梧桐一樣做好本職、不斷進取,為“永和中興”貢獻一份自己的力量。而當在仕途中不斷沖撞碰壁,四十一歲的詩人見到門前屋后栽種的翠竹卻感到一陣悲戚,“愛君抱晚節,憐君含直文”,愛憐之下也對直竹的另一命運有所設想“知君死則已,不死會凌云”。但到了耄耋之年,人生的最后關口,對仕途失去憧憬的詩人總結一生的經驗教訓只得勸慰同席,“莫言楊柳枝空老,直致櫻桃樹已枯”。不要說柔韌彎曲的楊柳白白到老沒有意義啊,櫻桃樹就因剛正不阿而枯萎了。從這三首作品之中我們就可以清晰看到情感漸漸消極,宦情日減。
除此之外,這一時期詩人還有很多具有出世思想傾向的句子。窮極一生,既有過人臣之極亦有過遠謫的谷底,最終詩人所得到的,所追求的,也許就是《履道新居二十韻》(卷二十三)中所表達的:濟世才無取,謀身智不周。應須共心語,萬事一時休。
三、“直”的表意“綏靖”與詩人的中隱之道
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古往今來,生活在亂世之中經受政治理想與現實生活之間巨大落差而造成的矛盾痛苦的文人不在少數,但白居易是其中極為特殊的一個。這里的特殊并非指在政治理想破滅后無心戀闕以山水自娛耳目的“中隱”選擇,而是由早年間積極進取到晚年間詩人對自己的選擇都抱有絕對的自信和坦然。對于白居易早年激進晚年安樂的生活選擇,謝思煒先生曾評價其“除了政治上積極進取和較強的責任感之外,還有自私、消極、奴性、可鄙的另一面”[11],對于這種“自私”“奴性”與“可鄙”,晚年詩人并不是不知道(如“十兩新綿褐,披行暖似春…回看左右能無媿,養活枯殘廢退身”《能無愧》(卷三十七)),但他極好的消解和悅納了這種“自愧”,并且毫不矯飾的加以表達。這也是“直”類意象在詩人作品中得以呈現出前后期如此巨大的表意差異或者說表意“綏靖”的深層次原因,白居易自身的生存哲學絕對自洽,由此,他既有在作品中袒露的自信,也表現出自信的袒露。
在《與元九書》中白居易曾對摯友言及自己的生存哲學:“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為云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卷四十五)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出,白居易將外部條件與自身所恪守的道德準則割裂開來;外在的環境是“時”,內在的準則是“道”;對詩人來說,來自外部環境的認可只是自身價值判斷的充分不必要條件,他所認定的“道”不僅堅定地指導著其自身的生活實踐,并且還作為自身價值判斷的錨點。政治清明,自然要“陳力以出”,做云中之龍和乘風之鵬;但如果政途黑暗佞臣當道,也未必要不顧自身安危地直言極諫,即便“奉身而退”也是南山霧豹、高飛鴻雁,不應予以否定。也就是說,江州之變后的詩人的進退有據,根源上不在于行為的改變而是規則的改變,即價值標準的重新認定。從遵循傳統儒家道德規范,在以陶淵明為首的大隱避世和以岳飛為代表意象的自戕全道的拉扯之中跳脫出來,制定了自己的“桃花源”;從追求統治者以及親朋故友的認可到在自己設定的心境中尋求解脫和超越。這就是他的標準,無論是“進”還是“退”,都由心中之“道”作為支配,而不是去支配“道”;這種“道”就是超越和支配是非、禍福的心理本體。而詩人晚年的這種人生哲學筆者認為對莊周的“逍遙無待”思想有所繼承和發展。
王先謙先生曾言:“無所待而游于無窮,方是《逍遙游》一篇綱要。”[12]莊子認為人想要達到“逍遙”這一最高境界核心在于無待于天下,而如何做到“無待”呢,莊子在《逍遙游》中沒有直接進行回答,姑且以后人王夫之的解讀作為妄議一二:“無待者,不待物以立己,不待事以立功,不待實以立名。”[13]不將自我與外物對立,做事不以建功立業為唯一目的,與外界交往依憑本性觀其本質、不妄立名目;總之,做人要順勢而為、適性而行。晚年的白居易正式這一思想的實踐家。
本文從字源探析和漢民族“以物比德”的審美傳統出發,對白居易詩歌中“直”類意象的定義及研究價值進行了界定和明晰,并圍繞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理念、嘗試結合作品情感內涵研究與創作者思想轉變研究兩個命題;通過對白居易詩歌中“直”類意象的類別、時期、數量、密度、積極或消極的情感狀態差異進行對比分析得出詩人的思想變動曲線,并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探究從“激進”到“中隱”的背后,白居易“平衡-斷裂-平衡”的知行體系所體現出來的獨一無二的生存哲學建構——在自己設定的心境中尋求解脫和超越。“人生處一世,其道難兩全。賤即苦凍餒,貴則多憂患”,普天之下,大被廣廈的少陵野老與種豆南山的靖節先生畢竟都是人生的少數,對白居易“中隱”人生哲學的重拾也是對現代人當下尋找精神出口的一個好的嘗試。
注 釋:
①本文所引白居易詩文皆出自參考文獻[6],為免繁縟以下只隨文標注卷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