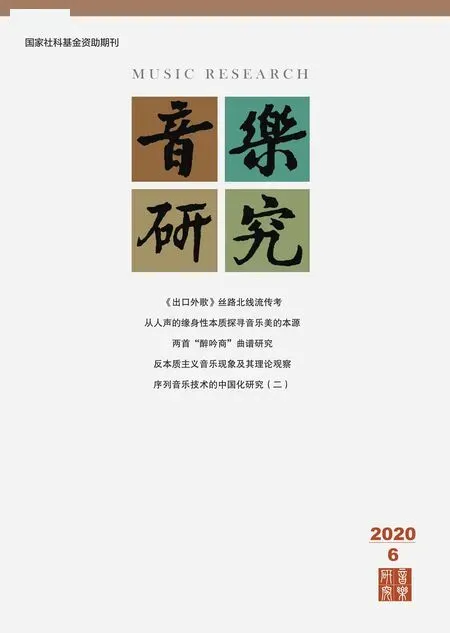三種伴奏形式與三種表述模式
文◎張振濤
在戲曲樂隊待了六年,還真沒把伴奏這檔子事兒往深里想。“跟腔包調”“托腔保調”天天講,好像無甚大道理。戲曲、曲藝,莫不如此。大學期間為管弦、聲樂彈鋼琴伴奏,接觸了一批協奏曲、奏鳴曲及藝術歌曲、歌劇選段。這讓筆者深感鋼琴伴奏與戲曲伴奏的差異。西方伴奏獨立性強,許多部分簡直就是獨奏曲。第一次為圣-桑小提琴《引子與回旋隨想曲》彈伴奏,老師對我大聲嚷嚷:“這段鋼琴是獨立的,你自己彈,不用顧小提琴”。這使我一下子回過神來,原來我不是伴奏,是主角。筆者真正把中西伴奏當作一個問題來思考,是在從事民族音樂學的田野調查之后。河北省保定市淶水縣南高洛音樂會有種念誦方式稱“對口”。所謂“對口”,就是笙管樂與誦經(文壇)的兩撥人“口對口”。其實,旋律一模一樣,按西方說法,管子和嗓子同聲同律,是大齊奏。但樂師認真地講,笙管是“伴奏”。這讓筆者意識到,樂師所說的“伴奏”,是指以“經文”為主、笙管為輔的主從關系,其定位根本不在音樂上。中國伴奏與西方伴奏,傳統伴奏與現代伴奏,各有定位。中國的托腔保調與西方的并駕齊驅,傳統的主客分明與現代的互為主從,是兩股道上跑的車。
世界音樂讓我們遭遇到另一類“伴奏”——共鳴弦——嗡嗡作響,持續彌漫,渾然一體,妙不可言。將其比之中國烘托則不恰,喻之西方多聲又不宜。其特點是既全面覆蓋,又不求獨立;既吞沒主弦,又突出旋律。這是否可以稱為“伴奏”或者根本不是我們定義的“伴奏”?三廂比較,中國伴奏之輔助性,不言自明;西方伴奏之獨立性,不喻而立;共鳴弦介于兩者之間,亦不立而成。“發現他者才能看清自己”。三個觸點,讓我們獲得了一個更大也更有理趣的話題。
一、戲曲伴奏
1971 年,筆者進入山東省呂劇團樂隊演奏小提琴。1949 年前,呂劇伴奏只有一把墜琴。50 年代“戲改”,呂劇成功上演了影響全國的《李二嫂改嫁》,一躍成為全省第一劇種;鳥槍換炮,加進二胡、琵琶、揚琴成“四大件”,配置來自梅蘭芳的京劇改革模式,更大改觀,始自移植“樣板戲”。各地劇種無不搬用“欽定模式”,樂隊標配—弦樂器:第一小提琴(4),第二小提琴(3),中提琴(2),大提琴(1),貝 司(1);木管:長笛(1)、單簧管(1)、雙簧管(1)、巴松(1);銅管:圓號(2)、小號(1)、長號(1)。
樂隊是皮,配器是瓤。交響之門開,主弦之聲塞。若非政治掛帥,難免不發生“是以音樂為主還是以觀眾聽戲為主”這一持續不休的論戰,自然也會引發一小群“落伍”藝人與新型樂手之間的對壘。具體說,演奏墜琴的年輕主弦,適應新體制,幕間曲、前奏與較長間奏,停下來,聽樂隊造勢;唱腔開始,與演員同步進入,或者說為“找不到調”的演員提供“扶手”。年紀較大的主弦,難以適應,樂隊一起,找不到入口。主弦跑調,演員找不到北,亂成一鍋粥。多虧指揮連比畫帶敲打譜臺,老人家“連滾帶爬”才找到入口。這類情況時常發生,惹得樂手直撇嘴。從此,配器再不敢把墜琴寫得太獨立。墜琴進入時,樂隊拖長音或干脆停下來,免得麻煩。
更難適應的是演員。老式伴奏成長起來的演員,哪里駕馭得了大樂隊,樂隊一響,根本找不到調,迎面相撞,人仰馬翻。原來是演員想什么時候開腔就什么時候開腔,想拖多久就拖多久,節奏是根“猴皮筋”,由著性子來,主弦跟著就行。這與楊蔭瀏回憶天韻社吳畹卿教授昆曲伴奏的方式是一樣的。①楊蔭瀏《吳畹卿先生小傳》:“吳畹卿在教學中,對于唱曲和伴奏,極為重視,學生學到一定程度,就要他們學會‘脫本’隨著唱者的歌唱進行伴奏。他認為只有這樣學生才能充分發揮樂器的表達能力,依唱腔的高、低、遲、速,自如地進行托腔,使伴奏與歌唱絲絲入扣、融為一體。”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編《楊蔭瀏全集》(第4 卷),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 年版,第17 頁。
現在,天翻了,不是樂隊聽演員,而是演員聽樂隊,樂隊讓你進,你才能進。記得一位老演員,記不住復雜過門,樂隊全奏,猶豫不決,入不了戲。樂隊哄場,他急得臉紅脖子粗,怒目開罵。指揮耐著性子,哄大家一而再再而三地練習。殘酷現實,逼著老戲骨習慣新方式。不光樣板戲令演員不敢說三道四,一大沓工工整整的總譜更讓不認識譜的演員心生敬畏。面對政治、權威、現代、科學,高壓重重,誰敢反抗?找不到調,敢怒不敢言,面對一大堆常常叫錯名的西洋樂器,惶悚難辨!文明沖突,讓藝人分裂!
新型配器,一言以蔽之,就是盡量不與唱腔相同。一班人馬,步調一致,既烘托主旋律,又不盡一致。管弦樂使地方戲音樂獲得音效。唱詞有風吹草動,長笛走句;劇情有行軍打斗,小提琴快弓;一號人物深思遠慮,大提琴獨白;他(她)心潮起伏,豎琴滾滾而來;他(她)豁然開朗,樂隊全奏。凡此種種,皆有法可依。從樣板庫存中抽取、對號,是圖解音樂的極端形式。不能否定現代京劇的樂隊寫法,這是熟悉傳統的作曲家把京劇與現代管弦樂結合從而獲得奇效的新路子。其中并非沒有漂亮音響,也并非沒有豐滿配器。《智取威虎山》楊子榮唱段《打虎上山》前奏,《紅燈記》李玉和主要唱段《雄心壯志沖云天》伴奏,《龍江頌》江水英唱腔《細讀了全會公報》,《杜鵑山》柯湘唱段《家住安源》《亂云飛》的配器等,效果非凡,渲染氣氛,鋪陳意境,已可獨立成篇。如果不是編排于特定劇情,如果可以刪除“不合時宜”的唱詞,這些作品均可列入經典。我們不會退化到臉譜時代,學術評判也不再囿于涂脂抹粉或胡亂抹黑。不能不說,那些唱段讓音樂家十分振奮。
必須說明,一般人從收音機聽到的唱腔,是經過處理的,唱詞清晰,主次分明。樂隊只在過門、間奏才放開音量。實際效果,遠非如此。筆者在北京“人民劇場”看過北京京劇院演出的《紅燈記》,主要演員浩亮(李玉和)、劉長瑜(鐵梅)和高玉倩(李奶奶),都是一流好嗓子。但現場唱詞,遠沒有收音機清楚。筆者懷疑,觀眾若無基本背得過的前提,頭一回看,能否聽清?這應了民諺“弦裹音,聽不真”。這是現代與傳統的最大矛盾。樂隊壓唱詞的案例到處可尋。
1952 年,上級給定縣秧歌團派來了作曲人員,幫助定縣秧歌改進戲曲音樂,還給增設了樂器。但直至20 世紀90 年代,秧歌戲的演出進入高潮時,演員和觀眾雙方還都要求拋掉樂器,直嗓大喊。這時,臺上唱詞的人和臺下聽詞的人,都盡情盡興,如醉如癡。藝人說:“樂器治嗓子”,意思是跟著樂器正規演唱,限制了他們的即興發揮。觀眾說:“樂器一響,聽不見詞”,意思是加了樂器,聽不準藝人的真嗓清唱,這不合乎原來的口耳交流習慣。②董曉萍、〔美〕毆達偉(R.David Arkush)《鄉村戲曲表演與中國現代民眾》,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8 頁。
老百姓可不管什么音樂獨立與不獨立,他們聽的是唱詞,雖然現代戲并不在乎能否獲得老百姓作粉絲。上述案例,有典型性,老百姓聽的是戲文,而非這里加一句長笛,那里進一段豎琴的“美容”音效。專業音樂家覺得好的,老百姓覺得花里胡哨;老百姓認可的,專業音樂家覺得單調。鄉村草臺上唱“姹紫嫣紅”,不如說“花紅柳綠”更讓鄉民明白!再說,民間劇團也沒有財力置辦那么多樂器。如同《紅樓夢》大觀園的趙嬤嬤所說:“誰家有那些銀子買這個虛熱鬧去”。
此類“矛盾”的田野報告很多。廣西來賓市興賓區壯族師公戲伴奏,就是一把二胡,專業音樂家覺得單調,加入大樂隊,卻發現觀眾根本不買賬,于是又恢復單調。伴奏本是扶助的小我,突變大我,必遭唾棄。20 世紀末,鄉土模式正以極快速度全面顛覆音樂家自50 年代以來努力了60 多年的戲改成果。樂隊保持自主權,是戲改主要內容之一。盡管以演員為主的體制在現代戲中被有目的地抑制,但在鄉村依然受喜歡。這個話題在樣板戲退場、老戲恢復后,差不多又回到原點。
二、鋼琴伴奏與歌劇伴奏
西方伴奏大致分兩類:一部分與中國相似,稱“主調音樂”;一部分與中國不同,稱“復調音樂”。扼要敘述可能把復雜問題簡單化或教條化,但我們只能扼要敘述。
“主調音樂”,旋律為主,伴奏烘托。古典音樂基本屬此類。典型的如舒伯特《小夜曲》、埃爾加《愛的禮贊》、莫扎特歌劇《女人善變》。莫扎特《圓號奏鳴曲》的鋼琴伴奏,基本是固定音型打拍子,強拍處墊和弦。引子間奏,偶爾突出一下,轉折過渡,如同戲曲過門的“鑲邊”“填空”,不喧賓奪主,中國人較習慣。
“復調音樂”不同,藝術歌曲的鋼琴伴奏獨立性很強。如舒伯特《鱒魚》(后改為《A 大調鋼琴五重奏》),鋼琴六連音與八度跳躍,塑造鱒魚形象,與獨唱旋律完全不同。聲樂套曲《美麗的磨坊女》的伴奏與歌唱也多有不同,《死神與少女》鋼琴在低音區敲打,描述死神形象,陰森可怖。在和聲框架下,聲樂和鋼琴各行其是,這是藝術歌曲的特點。
更典型的是歌劇,如《藝術家的生涯》詠嘆調《冰涼的小手》《為藝術為愛情》的伴奏完全獨立。習慣于“主調音樂”的聲樂學生,沒有提示音,一張口要準確唱出伴奏,非經訓練,根本難以做到。筆者為他們彈伴奏時,最頭痛的是彈了十遍八遍他們也找不到入口,甚至找不到音高,筆者只能死記暗藏內聲部的音高,而且還要特別彈響一點。這讓學生備嘗辛苦,也讓筆者懂得,歌劇藝術非經長期訓練難以應付,找不到調的背后是中國人難以適應但必須適應的依靠伴奏的習性。
第三種類型,介于兩者之間,如法國作曲家儒勒·馬斯奈歌劇《泰伊斯》主題《冥想曲》(也譯為《沉思曲》)。少年時演奏過單獨抽出來的小提琴獨奏,也彈鋼琴伴奏,分解和弦,從低音涌向高音。2018 年,筆者第一次在國家大劇院看實況《泰伊斯》,了解到原來主題貫穿整個后半場。一首歌既可以獨奏呈現(第一遍為小提琴獨奏,豎琴伴奏),又能作為不同于獨唱聲部的伴奏存在(類似古諾在巴赫《C 大調前奏曲》上衍生出《圣母頌》),還能相互交叉,分鑣并轡,真是絕妙無比。這讓筆者對早年熟悉的獨奏延伸出的“副產品”刮目相看。馬斯奈充分發揮了一支好旋律的勢能,生發出多重意境。
瓦格納時代,樂隊進入樂池,音量盡量不掩演唱,主腔之外,還留有巨大空間,充分表達器樂音效,這成為瓦格納巨型樂劇不同于一般歌劇的突出看點。他筆下的樂隊,時而伴奏,時而主奏,無終旋律,并行交替,很難再用主旋律、伴奏概念劃分了。
2014 年9 月21 日,筆者在國家大劇院歌劇廳看了中央歌劇院演出瓦格納歌劇《齊格弗里德》,2017 年看了《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2018 年又看了《紐倫堡的名歌手》,深切感受到歌唱家的專業化水準,在樂隊全無提示的地方,歌唱家也能脫口而出,毫無障礙。
伴奏差異,反映觀念。獨立精神是西方藝術形態的支撐,不為伴奏而伴奏。“愷撒的歸愷撒,上帝的歸上帝”。布魯爾(Brewer)提出的“最佳特性理論”認為,集體認同源于“個體的包容需要”和“個體的異化需要”兩種相反動機的平衡機制。“個體的包容需要”,即個體期望成為集體一員并獲得同化的需求;“個體的異化需要”,指個體渴望與他人不同的特殊需求。西方伴奏呈現的,即是該理論所解釋的兩種并行不悖的需求。
三、沒有任何樂器以這種方式壟聚焦點
初聽印度音樂,為共鳴弦的奇特效果嘖嘖贊嘆。指板一側,安裝一排烘托襯墊的輔弦,明彈一弦,陰持數韻,延音余韻,繁復多端,既烘托旋律,又不干擾旋律,渾厚豐滿,轟然作響。這是南亞、阿拉伯地區音樂的突出特征,說和聲不是和聲,說非和聲又是和聲,完全不同于“主奏是主奏、伴奏是伴奏”的劃分。
印度西塔爾琴(Sitar)的底部有兩個巨大葫蘆型共鳴箱,寬大琴頸上有20 多個可移動的環形金屬音品,上層系6—7 根旋律弦,4 根主弦,3 根共鳴弦,下層系13 根共鳴弦。低音維納琴(Veena,或薩拉斯瓦蒂·維納Sarasvati Vina)系列,是印度弦樂的龐大家族,兩只(有的三只)巨大葫蘆形共鳴箱,震震而動,復層共鳴。更令人震撼的是,演奏組合中,在維納琴側后方,一定要配備一件坦布拉(Tambura,一種長頸彈撥樂器)。兩根弦或四根成雙的坦布拉,通頸無品,不奏旋律,自始至終,撥弦共鳴。這種固定搭配,把嗡嗡作響的音效發揮到極致。
蒂莫西·賴斯《保加利亞音樂》一書描繪了東歐的“加杜爾卡”:
“加杜爾卡”為短頸梨形體,由一整塊木頭制成,宛如一把大湯勺。一塊薄的木質音板黏合在中間碗狀挖空的琴體上。用以演奏旋律的三根粗鋼絲從頸頭部的木質音栓穿過琴馬直到系弦板。大約八根更細的琴弦位于三根演奏弦之下,調音位主要的旋律音高。這些弦并不被直接撥動,而是與演奏音高同時振動,這極大地增加了音量、共鳴和樂器音色的豐滿度。③〔美〕蒂莫西·賴斯著,張玉雯譯,管建華審校《保加利亞音樂》,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2016 年版,第39—40 頁。
烏克蘭標志性樂器“班杜拉琴”(或譯“班德拉”Bandura,俄文бандура),有50—60 根豎系共鳴弦,初看像豎起來的揚琴。左臂抱琴,左手探到琴頭外,如同彈豎琴,右手撥動琴板上琴弦,反手拉動粗弦以作共鳴。
北印度弓弦樂器薩朗吉(Sarangi),前排3 根主弦,下置10 根共鳴弦,指板左側16 根共鳴弦。伊朗熱瓦普(Robab),4 根主弦,12 根輔弦。西奧伯琴(Theorbo)在常規琉特琴上附加超長琴頸,排列20 余根共鳴弦,單獨發展為長雙頸琉特琴。西騰琴(Cittern),也是數軸桿側,懸弦如繩。
多一根是一根,多一聲是一聲,一排不夠,再加一排,弦外之音不但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成為缺不得、少不得的音響主體。筆者于2010 年在布魯塞爾樂器博物館,2011 年在法國巴黎音樂城,2017 年在日本浜松樂器博物館,2018 年在牛津人類學博物館,2019 年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國家音樂博物館,看到鋪天蓋地的共鳴弦樂器,品種之多,超出想象。若再把遍布歐洲的風笛持續音,以及延續至西方作曲家作品中的持續音劃入視野,會看到了一個分布于中亞、南亞、歐洲的龐大家族。同類異域,跡同事殊,音響形態完全顛覆了我們的伴奏觀念。
四、多余的一組弦
有篇散文題目叫“多余的一句話”,不妨改為“多余的一組弦”。它的確不是中國意義上的伴奏,也不是西方意義的和聲。近年來,蒙古雙聲得到學術界廣泛關注。馬頭琴、弓弦潮爾和庫姆孜,都有低音弦,持續作響,形成實音弦主奏附加合音共鳴的音效。徐欣、蕭梅的研究,讓合音現象獲得了跨境的景深。蕭梅談道:
比如形制為兩根五度定弦關系的主奏弦與6—12 根輔弦的哈密艾捷克;以一束馬尾弦主奏,另外張10—12 根鋼絲共鳴弦的刀郎艾捷克;一根主奏弦與9—17 條輔弦的薩它爾;還有彈撥樂器熱瓦普和彈布爾等都具有相同的主奏+輔弦結構。它們盡管各具特點,但其輔弦的功能皆與主奏弦構成相對固定的和音,因此更準確地說,它們并非輔弦,而是共鳴弦。有意思的是,上述艾捷克與薩它爾與蒙古族弓弦潮爾的追求類似,即以豐富的泛音與基礎音結合。有意思的是,在有關艾捷克和熱瓦普的資料中,亦可見關于它們從伊朗等地傳入后增加了共鳴弦的記載。如馬成翔在對清代史料的梳理中,指出艾捷克最早起源于伊朗,公元14 世紀以前傳入中亞,流傳在撒馬爾罕、布哈拉等地。以后傳入喀什,增加了共鳴弦,形成了有共鳴弦的艾捷克形制。盡管我們現在在十二木卡姆的樂隊中看到的艾捷克,是近代以來改良了的去掉共鳴弦,而將主奏弦增加為4 根的樂器,但刀郎艾捷克和哈密艾捷克卻保留了清代以來的形制。刀郎熱瓦普也有早期兩根皮弦彈奏、后發展了共鳴弦的經歷。④蕭梅《文明與文化之間:由“呼麥”現象引申的草原音樂之思》,《音樂藝術》2014 年第1 期,第46 頁。
以此而論,漢族彈撥樂器同樣可以找到共鳴弦痕跡。如南音琵琶、蘇州評彈琵琶、陜北說書琵琶和云南洞經琵琶,它們的第四根弦基本不彈,其中同樣隱藏了中亞乃至風靡地中海文化的共鳴弦痕跡,其遺風遺緒,依然可辨家族身影。置而不彈的孤懸之弦,終于對接到廣闊的共鳴弦世界,充滿疑惑、不敢妄下結論而懸著的心,也落到了肚里。如此連接,令學術界冒出來許多要說的話。夏凡在博士論文中提到共鳴弦的地方有數處,她描述道:
如熱瓦普的共鳴弦。以喀什熱瓦普為例,第一根外弦為旋律弦,緊挨的第二根弦也可當旋律弦,也可當共鳴弦,之后五根都是共鳴弦。傳統喀什熱瓦普為五根弦,熱瓦普演奏家達吾提·阿吾提(1939—)在此基礎上加入兩根共鳴弦,喀什熱瓦普變為七根弦,定弦順序為:C4—G4—D4—A4—E4—B4—F4。兩根共鳴弦加入,與演奏曲目有關,古典熱瓦普終止音,常落在#F 和B 上,加入#F 和B 共鳴弦,變得明亮。如《卡迪爾·麥吾蘭》,終止音為B,若無共鳴弦B,完全不同。可見,共鳴弦不僅起到改善音色作用,還能改善延續局限性,“民族味道就出不來”。⑤夏凡《有品樂器律制形態研究》,中央音樂學院2011 年博士學位論文。
“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⑥劉勰著,周振甫注釋《文心雕龍注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年版,第518 頁。。共鳴弦定弦,一般為主弦五八度,主屬基頻,恒定敏捷。一般人不在意也不關注定律問題,雖然聽的、唱的、彈的無不與此有關。熱瓦普、艾捷克、薩它爾,大名鼎鼎的冬不拉,須臾不離的卡龍,孤懸之弦都有預設。對普通人來說,音樂是個數字有限且因為有限而有點幼稚的世界。持續振蕩、折騰得熱熱鬧鬧的數十根弦,靠什么規律發揮音效,無人深究,寧愿相信“閑置”的弦無關痛癢。其實,共鳴弦必須經過計算,才能如人所聽的那樣和諧悅耳。夏凡提供了共鳴弦定音與實踐掛鉤的例證。
是什么促使了地中海文化圈五弦里拉發展到60 余根弦共鳴弦的雪球效應?這不能不讓人注意到該區域音樂文化占主導地位的宗教性。宗教儀式需要迷幻聲響,共鳴弦混響,余音裊裊,洋洋盈耳,作用于人耳的感受,就是讓聆聽者超越世俗世界。主弦以少為多、輔弦以弱為強的過人之處,就在于提供了宗教所需的聲景。朦朧造境是其存在理由。如此看來,信仰沉迷與共鳴弦之間確實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筆者禁不住把這類音效與“非遺”展演上的木卡姆表演聯系起來。彈撥爾、都塔爾、卡龍,在一群來自南疆莎車、身強體壯的老頭手中爆發出巨大感染力;表演者或盤腿而坐,或屈膝而跪,昂頭閉目,放聲高歌,如處無人之境。活力無窮的維吾爾族老漢,與中國音樂研究所樂器陳列室簡其華拍攝于50 年代的圖片相接續。那組懸掛圖片中,一位跪坐拉奏艾捷克的維吾爾族老人,凹進去的深目和囧囧發光的眼神,令筆者至今難忘。粗糙的手,就是琴弦上急速如飛的手,就是唱到興頭上抹抹嘴再端起“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手。諸弦復合、轟鳴大作的音效,正是文化現場所需要的。
我們習慣于音響的清晰度,乃至怨懟某些樂器的致命“弱點”是余音不能立刻“停擺”。中央民族樂團排練過程中,筆者聽過幾位指揮抱怨坐在前排的揚琴音響,形容其音響太“臟”。盡管改革揚琴可以加踏板,但手腳并用,難以普及。話說回來,揚琴若不嗡嗡作響,就沒了特點,然而,一旦進入樂隊,優點變缺點,擾亂純凈,令眾人不得安寧。這一度令指揮們進退憂虞,欲舍之不取,則慮其懷怨;欲待之合勢,則苦其稽延。如果把此點作為一個不同文化體相互適應的問題看待,就深刻地反映出古老的共鳴弦樂器與現代樂隊追求之間難以彌合的矛盾,并從中窺探大量附帶共鳴弦的彈撥樂器被排除于現代樂團之外的根結。一件樂器能否進入現代管弦樂團,能否成為總譜中的一個聲部,已經成為行情、等級以及社會認可度的標志,也成為該類樂器在現代命運中通蹇禍福的標志。
我們基本上屬于不懂伊斯蘭音樂文化的人。談起歐洲音樂,筆者憑借少年時拼命學西方樂器的一點底氣還能多少說幾句;談起印度、伊斯蘭樂器,根本說不出什么道理,甚至觀念中隱含著對不“干凈”音響的敬而遠之。從小種下的嫌棄共鳴弦“臟”的音響觀念,難道不是單一文化觀與西方中心主義的余音裊裊?即使在民族主義越來越淡,世界文化越來越普及的當代,這樣的觀念依然存在。我們曾以學習鋼琴、小提琴作為一種值得自豪的身份,但如今,單一實踐已經成為我們身上的“負資產”。從來不曾碰過甚至不曾見過的印度與阿拉伯樂器,使我們對其音響難以解讀乃至產生親切感;看到印度音樂家拉維香卡雙目緊閉的陶醉及其家班的其樂融融,我們只能隨心向往之,卻完全不懂。不懂語言,無論我們花多少精力關注博物館的印度與阿拉伯樂器,都沒有能力解讀既不懂演奏也不懂理論的共鳴弦世界。
大部分中國人對伊斯蘭文化的認知,明顯比不上佛教文化或基督教文化,這不完全是“偏見”,更主要的是“無知”。而這,與我們的博物館數量太少,且視野狹窄不無關系。⑦陳平原《大英博物館日記》(外二種),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 年版,第88 頁。
關鍵時刻、關鍵會議,發揮了作用。上海音樂學院召開的琉特琴專題會議,帶來了許多信息。陳自明《世界民族音樂地圖》(2007),也提供了大量資料。如果多一些像上海音樂學院召開的琉特琴會議,多一些像蕭梅、陳自明一樣開啟新知的朋友和老師,如果早一點具備人類學知識,那么,學者的聽覺會發育得更全面一點。
結語:三種伴奏、三種模式
伴奏在一個層次上是音響,在另一個層次上是行為,在更高層面上則是處理主屬關系的準則。伴奏與其說是三種事實,不如說是三種文化模式的表述形式。保腔不只是伴奏,更是文化觀念和社會結構的反映。托腔、包腔、裹腔,講究的是與主旋律步調一致。如同戲曲劇團“鼓老”嚷嚷的:“另立門戶,找死呀!”什么叫主旋律,什么叫烘托,什么叫紅花,什么叫綠葉,主輔分明,植根于中國觀眾獲取信息的基本習慣,更根植于中國人講究秩序的倫理觀念。“統帥專一,人心不分,
號令不二,進退可齊,疾徐如意,氣勢自壯。”⑧司馬光《資治通鑒》卷16,中華書局1956 年版,第7545 頁。整齊寓意,深意存焉。如此看來,伴奏就成了解讀集體無意識的繩結。開始并未打算將伴奏確立為某種模式,卻無意間看到了三種法度。此前未及感悟,蓋因不具備世界視野和成論理據,而新的理據也可以把早年經歷變成敘述資源。
康拉德《什么是全球史》⑨〔德〕塞巴斯蒂安·康拉德著,杜憲兵譯《什么是全球史》,中信出版集團2018 年版。概括道:新的全球史是將現象、事件和進程置于全球脈絡中,超越民族主義和歐洲中心論。他提出三種全球史:作為萬物歷史的全球史;作為聯系史的全球史;以整合概念為基礎的全球史。
人類學從微小入手,開膛破肚,探視藝術形態背后的社會類型。漢族以整齊劃一為核心,西方以并行不悖為核心,印度、阿拉伯地區則以眾籌共振為核心。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觀中國伴奏,則覺世界所長與所闕;觀世界伴奏,則覺中國所長與所闕。上覽歐洲體制以為則,下觀共鳴弦體制以為律,中國形態不言自明。標本的意義在于醒目,別殊類,序異端,“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⑩同注⑧卷3(一),中華書局1956 年版。。將對立坐標,納入闡述,就能對跨文化解讀提供基料,或許這也算新型全球史的微型切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