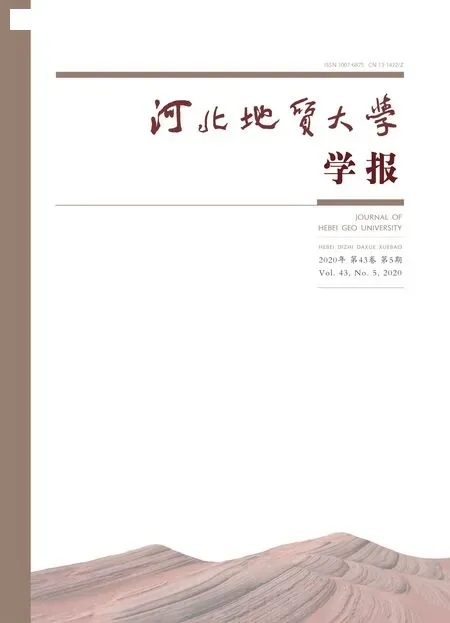中國省域層面低碳、環保與發展的協調性對比分析
鄭林昌,張亞楠,付加鋒
1.河北大學 經濟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2;2.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北京 100012
0 引 言
低碳、環保和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低碳和環保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最重要表征。低碳、環保與發展三者之間存在一定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關系,同時低碳、環保與發展之間又存在一定的耦合作用機制,低碳活動能夠促進環保和發展,環保活動能夠帶來低碳和發展,協同推進低碳、環保與發展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正處于“高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階段,人們在追求物質消費的基礎上,對生存環境、生態文明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生態文明建設和高質量發展更需要低碳、環保與發展之間的協同,經濟社會發展不應該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同樣保護生態環境、推動節能減排也不能阻礙經濟社會的發展,當然更應重視低碳和環保之間的協同效應。
協同理論最早由德國物理學家哈肯提出,他認為性質不同的相對獨立的子系統通過一定的合作可以實現在宏觀尺度上的功能結構,從而推動系統從無序—有序、有序—有序的轉變。當前“協同”這一概念已被應用于各個學科、多個領域。早期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協同方面[1-4],近年國內外學者開始關注節能與減排的協同、大氣污染與溫室氣體減排協同等。1998年美國環保局(USEPA)就啟動了國際協同控制分析項目(CAP),IPCC第二次評估報告中測算了在控制溫室氣體的同時所產生的局地大氣污染減排效益[5],第三次評估明確提出了控制溫室氣體與污染物減排的協同效應[6];J.Jason West、Patricia Osnaya(2004)和Yeora Chae、Sangyeop Lee(2007)等對各自國家相關環保保護政策協同效應進行了測算,發現實施環境保護活動能帶來相應溫室氣體排放的減少[7-8]。我國學者在此方面也有大量研究成果,比如環保部政研中心、田春秀(2006)等對大氣污染與溫室氣體排放協同控制效應進行了深入研究[9],劉勝強(2012)、鄭繼良(2018)等對環境污染物減排的協同控制效應進行了測算[10-11]。盡管當前已有相關研究開始關注節能、減排與經濟發展的協同[12-14],不可否認的是相關研究仍主要集中在環保與發展協同、低碳與發展協同以及低碳與環保協同控制等方面,宏觀層面測算低碳、環保與發展系統之間協同性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少。
1 低碳環保發展指數指標體系
文章沿用前期研究所采用的指標體系構建方法構建地區低碳環保發展指數指標體系,即繼續采用專家咨詢、敏感指標篩選等方法構建城市低碳環保發展指數指標體系,最終構建的指標體系共包括3項二級指標、7項三級指標和13項具體指標;繼續采用以往均值權重賦值方法對指標進行賦值,具體指標體系及其相關權重見表1[15-17]。

表1 地區低碳環保發展指數指標體系及權重
2 數據來源、數據處理與模型構建
2.1 數據來源與數據處理
所用數據主要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能源年鑒》《中國環境年鑒》以及各地區統計年鑒。由于缺乏西藏地區部分環境和能源統計數據和港澳臺地區的統計數據,評價樣本地區為30個。
(式1)

由于各項指標值的量綱相差較大,為了便于各項指標之間的對比,采用線性比例法進行無量綱化處理。

(式2)
2.2 地區二氧化碳排放測算
地區(全國)終端能源消費二氧化碳排放量=各種能源消費實物量×各種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電力終端二氧化碳消費+熱力終端二氧化碳消費,各種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因子詳見表2。

表2 地區二氧化碳排放測算涉及主要能源的碳排放因子
其中,電力終端二氧化碳消費=電力終端消費實物量×電力調入結構×全國平均火電比重×全國平均火電排放因子+電力終端消費實物量×(1-電力調入結構)×本地火電比重×本地火電排放因子,熱力終端二氧化碳消費=熱力終端消費實物量×熱力排放因子。
2.3 低碳環保發展指數評價模型
δ年度低碳指數(Low Carbon Index)評價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式3)

δ年度環保指數(Enviroment Protection Index)評價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式4)

δ年度發展指數(Development Index)評價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式5)

δ年度低碳環保發展指數(Low Carbon-Enviroment Protection-Development Index)評價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δLEDIi=η低碳δLCIi+η環保δEPIi+η發展δDIi
(式6)
其中,η低碳、η環保、η發展分別為低碳指數、環保指數和發展指數的權重。
2.4 指數協調性測算模型
為考察低碳、環保與發展系統之間的協同,借鑒相關研究成果[18-19],結合低碳指數、環保指數和發展指數特點,設計耦合度模型來衡量指數之間的相關程度,如式7。

(式7)
式中,C為指數1與指數2之間的耦合度,其大小由U1、U2決定,C越大兩指數之間的耦合性越好。U1是樣本地區指數1評價得分與地區指數1評價得分均值的比值,U2是樣本地區指數2評價得分與地區指數2評價得分均值的比值,K為調節系數,考慮指數得分情況,取K=2。
為區分指數間是高水平協調還是低水平協調,引入協調度模型,用來衡量系統之間的協調度。

(式8)
其中,D為兩指數之間的協調度,D值越大兩者之間的協調性越好;T為兩指數的綜合協調指數,反映兩者對協調度的貢獻,由于U1和U2是相應樣本指數得分與指數得分均值的比值,某些樣本的T值可能大于1,故D值也可能大于1;α、β分別衡量兩指數的重要程度,在此認為同樣重要,α、β取值為0.5。
借鑒其它相關研究成果中協調度(耦合協調度)類型劃分方法和劃分標準,考慮協調度評價得分及其分值聚集程度,將協調度劃分為五大類別:高度協調、中度協調、低度協調、不協調和很不協調,具體劃分標準如表3所示。

表3 協調度劃分標準
3 地區低碳環保發展指數評價
3.1 低碳指數
低碳生產指數:低碳生產指數不僅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等有關,同時與地區能源利用結構也密切相關。2016年,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的北京、廣東、重慶的低碳生產指數評價得分相對較高,而能源資源相對豐富的內蒙古、新疆和寧夏等地區的低碳生產指數評價得分相對較低。相比2005年,2016年低碳生產指數評價得分增加的地區有27個,地區低碳生產指數總體有所優化。低碳生產指數地區間差異不斷增加,評價得分的離散系數由2008年的0.38,逐步增加到2016年的0.47。從空間上看,低碳生產指數具有“南高—北低”和“東高—西低”的特征,東南沿海的海南、廣東、福建等是低碳生產指數的高地,西北地區的新疆、寧夏、甘肅等省份低碳生產指數得分較低(見圖1)。

圖1 2005—2016年中國地區低碳生產指數空間分布示意圖
低碳消費指數:低碳消費指數受居民消費水平、能源利用結構的影響較大,2016年,居民消費水平、化石能源使用比重相對較低的四川、海南和云南等地區的低碳消費指數評價得分較高,化石能源使用比重相對較高的內蒙古、寧夏和新疆等地區的低碳消費指數評價得分相對較低。正是如此,低碳消費指數在空間上表現出了“南高—北低、西高—東低”的分布特征,東部沿海省份低碳消費指數低,多數中西部省份低碳消費指數評價得分要高。近年來我國居民生活消費能力和消費水平日趨提升,人均碳排放強度與日俱增,各地區低碳消費指數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北京除外),地區間低碳消費指數的差異相對穩定(見圖2)。

圖2 2005—2016年中國地區低碳消費指數空間分布示意圖
低碳資源指數:低碳資源指數與自然環境有著較強的相關關系,2016年福建、吉林和云南憑借著活立木儲量豐富的優勢,低碳資源指數評價得分排名前三,而氣候自然環境資源條件相對較差的青海、寧夏和新疆低碳資源指數評分較低,排名后三。正是如此,低碳資源指數在空間上總體呈“塊狀分布”的分布特點,西北地區低碳資源指數表現最差,長江以南地區低碳資源指數表現最好,華北地區低碳資源指數表現一般。動態看,近年所有樣本地區活立木儲存量均有所增加,低碳資源指數也有相應增加;低碳資源指數地區間的差異不斷縮小,2005年指數評價得分的離散系數0.89,2009年離散系數下降到0.82,2013年又下降到0.77(見圖3)。

圖3 2005—2016年中國地區低碳資源指數空間分布示意圖
低碳指數:2016 年,福建、四川和云南等地區的低碳指數評價得分較高,而寧夏、新疆和山西等地區的低碳指數評價得分較低,福建低碳指數評價得分是寧夏的9倍多,低碳指數區域差異較大。相比2005年,2016年有20個地區的低碳指數評價得分有所增加,這些多數是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的省份,其它10個地區的低碳指數評價得分則有所下降,除海南外,其它省市均位于中西部地區。低碳指數地區間差異明顯,2016年指數評價得分的離散系數0.45,不過這種地區差異性近年并沒有明顯變化。空間上看,低碳指數“南北差異”格局明顯,北方除黑龍江、吉林和北京表現相對較好,其它地區低碳指數表現都不好,南方大部分地區低碳指數表現都不錯,河南、湖北、貴州的低碳指數要小于周邊省市,在空間上形成一個塌陷區(見圖4)。

圖4 2005—2016年中國地區低碳指數空間分布示意圖
3.2 環保指數
環境污染指數:環境污染指數評價得分相對較高,且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表現出了高度相關性。2016年,北京、上海和天津的環境污染指數評價得分分別為267.73、24.32和102.63,位居前三;寧夏、青海和新疆等西北欠發達省份的環境污染指數表現要差很多,評價得分僅為12.80、14.48和16.23,位居后三。空間上看,環境污染指數在空間上呈“東高—西低”的分布特征,江蘇、上海、海南等東部沿海省份的環境污染指數評價得分較高,吉林、山東、河南、湖北、四川等地區的環境污染指數表現一般,新疆、青海、寧夏等地區的環境污染指數評價得分較低。動態變化看,相比2005年,2016年所有樣本地區的環境污染指數評價得分均有所上升;環境污染指數地區間差異卻一直增加,2005年指數評價得分離散系數為0.57,到2016年離散系數增加到1.00(見圖5)。

圖5 2005—2016年中國地區環境污染指數空間分布示意圖
環境管理指數:2016年,山西、新疆和寧夏等地區的環境管理指數表現較好,天津、廣東和吉林等地區的環境管理指數表現較遜色,山西環境管理指數的評價得分約是天津的17倍,環境管理指數地區差異明顯。由于各地環境治理壓力、環境治理重視程度、財政實力等不同,2005—2016年有20個樣本地區的環境管理指數有所提升,另外10個樣本地區的環境管理指數有所下降。空間上看,地區環境管理指數空間分布相對分散,但總體具有“北高—南低”的分布特征,新疆、內蒙古、青海、寧夏、山西、北京等地區的環境管理指數評價得分較高,重慶、湖南、廣東、海南、福建、上海等地區的環境管理指數評價得分較低(見圖6)。

圖6 2005—2016年中國地區環境管理指數空間分布示意圖
環境質量指數:2016年云南、福建和海南等地區的環境質量指數評價得分較高,河南、山東和河北等地區的環境質量指數評價得分較低,最高評價得分與最低評價得分相差僅有7.41,各地區評價得分的離散系數只有0.22,環境質量指數區域間差異并不大。受工業環境污染、氣候因素等因素影響,中部地區多數省份的環境質量評價得分相對較低,華北南部省份的環境指數評價得分更低,在空間上形成了中間塌陷帶。動態看,近期我國地區環境質量指數總體惡化,相比2005年,2016年有25個地區的環境質量指數評價得分有所減少(見圖7)。

圖7 2005—2016年中國地區環境質量指數空間分布示意圖
環保指數:環保指數評價得分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表現出了較高相關性,2016年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的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區,環保指數評價得分相對較高,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貴州、云南和青海等地區的環保指數評價得分相對較低,在空間上環保指數形成了“東部高—中部低—西部更低”的分布特征。2005—2016年,各地區環保指數評價得分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長,環保指數改善趨勢明顯;但環保指數區域差異性有所擴大,2005年地區指數評價得分的離散系數為0.24,到2016年離散系數增加至0.69(見圖8)。

圖8 2005—2016年中國地區環保指數空間分布示意圖
3.3 發展指數
地區發展指數空間分布相對分散,總體具有“東部高—北部高—中部低—西部低”的特征,東部沿海多數省市發展指數評價得分都比較高(河北、海南和廣西除外),內蒙古、遼寧、北京的發展指數評價得分也比較高,其它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省市發展指數評價得分較低,它們在我國疆域版圖上形成了廣闊的“平原”。近年,我國地區發展指數總體有所優化,所有樣本地區發展指數評價得分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尤其北京、天津和江蘇等地區增幅較大;地區發展指數差異性有所縮小,2005 年各地區發展指數評價得分的離散系數為 0.47,到2016 年離散系數降到 0.40(見圖9)。

圖9 2005—2016年中國地區發展指數空間分布示意圖
3.4 低碳環保發展指數
2016年,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地區的低碳環保發展指數評價得分相對較高,而青海、甘肅和貴州等地區的指數評價得分相對較低,指數評價得分的方差6 261.05,離散系數0.44,指數地區間的離散性并不大。不僅如此,近期低碳環保發展指數總體改善趨勢明顯,2005—2016年所有樣本地區的低碳環保發展指數評價得分均有所上升。不過地區低碳環保發展指數空間分布格局相對分散,總體而言,沿海地區多數省市的低碳環保發展指數評價表現較好(見圖10)。

圖10 2005—2016年中國地區低碳環保發展指數空間分布示意圖
4 地區低碳、環保與發展的協調性分析
考慮低碳環保發展指數系統性,測算低碳指數、環保指數與發展指數之間的協調度,分項指數測算低碳生產指數與低碳消費指數之間的協調度。為考察經濟活動低碳減排與經濟活動污染物減排是否協同,測算低碳生產指數與環境污染指數之間的協調度。
(1)低碳指數與環保指數:2016年,北京、廣東、海南、福建、浙江、湖北6省(市)低碳指數與環保指數的協調度均大于1,它們是高度協調區;上海、江蘇、廣西、吉林、陜西、重慶、安徽、湖南、江西、河南、天津的協調度介于0.9~1之間,為中度協調區;四川、山東、黑龍江、貴州、云南、遼寧的協調度介于0.8~0.9之間,為低度協調區;低碳指數與環保指數協調度介于0.5~0.8之間的地區有甘肅、內蒙古、河北、青海、山西、新疆6省,為不協調區;寧夏低碳指數與環保指數的協調度為0.47,為很不協調區。相比2005年,2016年協調度增加的地區有:北京、廣東、浙江、湖北、上海、江蘇、湖南、河南、天津、山東,其它地區的協調度有所減小,總體來看低碳指數與環保指數之間的協調性有所變差(見表3)。

表3 2005—2016年地區層面低碳指數與環保指數協調度變化
(2)低碳指數與發展指數:2016年,低碳指數與發展指數之間的協調度大于1的地區有北京、福建、浙江、廣東、吉林、重慶、湖北和江蘇,它們是高度協調區,上海、黑龍江、湖南、山西、海南、江西、四川、天津、安徽和廣西屬于中度協調區,遼寧、河南、山東、云南和貴州為低度協調區,甘肅、河北、內蒙古、青海、山西、新疆、寧夏屬于不協調區。相比于2005年,2016年有12個地區的協調度有所減小,這些地區多數位于我國中西部,廣東的協調度沒有變化,協調度有所增加的地區有17個,這些地區多數位于我國東部,總體看兩指數協調性增加的地區多于減少的地區(見表4)。

表4 2005—2016年地區層面低碳指數與發展指數協調度變化
(3)環保指數與發展指數:2016年,北京、上海和天津兩指數間的協調性最好,位居前三;高度協調區有8個,其中7個位于東部地區;中度協調以上的地區有16個,占總體一半以上;低度協調的地區有12個,不協調的地區有兩個(云南和貴州),低度協調區和不協調區除河北和遼寧外,其它地區均位于中西部。相比2005年,2016年以北京、上海、天津為代表的10個地區的協調度有所增加,廣東和內蒙古的協調度并沒有變化,其它18個地區的協調度有所降低,可以判斷:環保指數與發展指數之間的協調性總體有所降低(見表5)。

表5 2005—2016年地區層面環保指數與發展指數協調度變化
(4)低碳生產指數與低碳消費指數:2016年,低碳生產指數與低碳消費指數高度協調區有14個,占評價樣本地區總體的近一半,陜西、吉林、江蘇和貴州屬于中度協調區,河北、遼寧、山西、新疆、內蒙古和寧夏屬于不協調區,上海、山東、甘肅、黑龍江、青海和天津為低度協調區,由此可見,低度協調區和不協調區不僅局限于中西部地區的省市,東部地區省市也在低度協調區和不協調區之列。2005—2016年,低碳生產指數與低碳消費指數之間的協調度增加與減少的地區數量一致,北京、貴州和上海等14個地區的協調度有所增加,海南、新疆和青海等14個地區的協調度有不同程度的減小,河北和福建兩指數之間的協調性并沒有發生變化(見表6)。

表6 2005—2016年地區層面低碳生產指數與低碳消費指數協調度變化
(5)低碳生產指數與環境污染指數:2016年,北京、上海、廣東、天津、浙江、海南、福建、江蘇、湖北兩指數之間的協調度均大于1,屬于高度協調地區,湖南、河南、重慶、山東、吉林、陜西、廣西為中度協調地區,安徽、四川和江西屬于低度協調地區,河北、遼寧、黑龍江等11個地區為不協調區。動態變化看,相比2005年,2016年低碳生產指數與環境污染指數之間的協調度增加的地區有10個,占全部評價地區的1/3;貴州的協調度并沒有發生變化;其它19個地區的協調度有所下降。從空間角度看,協調度并沒有明顯空間分布格局,協調度增加的地區既有東部地區省市,也有中西部地區省市,協調度減少的地區空間分布也是如此(見表7)。

表7 2005—2016年地區層面低碳生產指數與環境污染指數協調度的變化
5 結 論
綜上可以得到以下主要結論:
第一,東部沿海地區低碳指數呈增長態勢,中西部部分欠發達地區低碳指數則有所減小,總體看低碳指數有所增加;低碳生產指數增長趨勢明顯,低碳消費指數下降趨勢明顯,低碳生產指數與低碳消費指數出現了背道而馳的局面。從空間上看,低碳生產指數空間上有“南高—北低和東高—西低”的分布特征,低碳消費指數具有“南高—北低、西高—東低”的分布特征,低碳資源指數在空間上總體呈現出塊狀分布的特點,在三個指數共同作用下,低碳指數呈現出了“南高—北低—中間塌陷”的空間分布特征。
第二,近年來我國地區環境污染指數持續快速增加,環境管理指數在2013年出現了拐點(在此之前指數持續增加,之后指數有所下降),相反環境質量指數在2013年卻出現了大幅下降,總體來看環保指數還是表現出了逐步增加的態勢。從空間上看,環境污染指數呈“東高—西低”的分布特征,環境管理指數呈“北高—南低”的分布特征,環境質量指數表現出“南北高—中間低”的分布特征,在三個指數共同作用下,環保指數在空間上呈現出“由東向中向西降低”的分布特征。
第三,各地區發展指數均有所增加,且增幅較大。發展指數在持續增長的同時,各地區之間的差異不斷縮小。發展指數在空間上表現出了“東部沿海高—西部地區低”的分布特征。
第四,低碳指數一直保持著較大的區域差異性,環保指數的區域差異性持續擴大,由較小區域差異性增大為較大的區域差異性,發展指數地區間的差異性并不大,并且差異性總體有所縮小。
第五,低碳指數、環保指數與發展指數之間的協調性相對較好,總體看東部地區的協調性較中西部地區要好,低碳指數與環保指數、環保指數與發展指數之間的協調性總體有所下降,低碳指數與發展指數之間的協調性總體有所增加。相比而言,中西部地區的低碳生產指數與低碳消費指數之間的協調性要好于東部地區,但這種協調性總體有下降趨勢,即中西部地區在低碳減排與環境污染物排放強度下降之間可能出現了背道而馳的局面;低碳生產指數與環境污染指數之間的協調性并不好,不協調地區多集中在中西部地區,且協調性總體有下降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