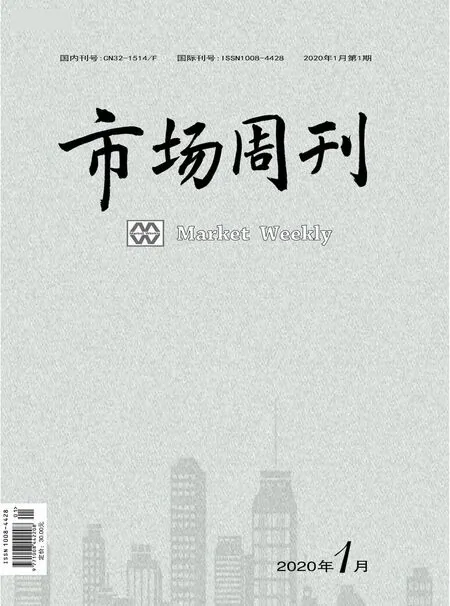用戶創造內容的著作權法保護
葛麗華
一、 用戶創造內容的概念
用戶創造內容,也即“User Generated Content”(英文簡稱“UGC”)。 UGC 作為互聯網技術與數字技術下的新興產物,在各國立法上并沒有明確的概念說明,在理論界,UGC 更是眾說紛紜,至今沒有達成共識,但是對于UGC 概念的界定是分析傳統著作權制度不足和探求著作權法保護路徑的前提,因此正確理解UGC 的核心內涵則顯得至關重要。
2007 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信息經濟工作組沒有直接定義什么是UGC,但是列舉了三個核心要素:一,所創造的內容能夠在網上公開給其他用戶使用;二,體現出一定的智力創造;三,是在專業的慣例和經驗以外的創造。
維基百科將UGC 定義為:由用戶而非傳統媒體或制片公司創造的在線內容。 這一定義更加強調UGC 的主體是網絡用戶而排除以盈利為目的主流媒體或制片公司。 這一定義較經合組織更加模糊,對于所創造的內容是否能夠在網上公開給其他用戶使用沒有規定,只規定內容為在線,同時對于智力創造的程度也沒有進行細致的規定。
歐盟委員會信息社會項目《UGC:支持多人參與的信息社會》對UGC 進行了拆分定義:所謂“用戶”,是指任何能夠創造、修改、集成和發布內容的個體;所謂“創造”,包括創作、修改、集成和發布;所謂“內容”:包括形成的視頻、圖片(照片和圖畫)、音樂、其他音頻、文本、游戲、虛擬物品等等。 同時,UGC 還需考慮用戶對于內容的編輯和添加的程度、用戶想要分享其內容的程度,用戶是否想通過內容來獲得一定回報。總體比較來看,歐盟委員會關于UGC 的概念范圍比前者更寬闊,范圍也更廣。
國內關于UGC 的定義主要可以分為兩類:一,將其視為一種網絡應用模式,包括但不限定于對原作品的使用。 趙宇翔、范哲、朱慶華認為UGC“泛指用戶在網絡發表的由其創作的任何形式內容,是Web2.0 環境下新興的網絡信息創作與組織模式”。 Shim 和Lee 認為內容還包括對既有內容的直接使用,譬如拷貝。 二,UGC 是在已有作品之上進行創作的行為。 譬如學者熊琦認為UGC 是“在已有作品上增加新內容的方式在線創作和傳播之行為”,用戶即“user”更應該側重于對他人作品的使用,若僅僅是用戶的原創,則這里的用戶更加是“owner”的角色。
關于UGC,文章認為應主要考慮四點:首先,UGC 的主體是不以營利為目的的非主流創作者,正如大部分學者認可的那樣,應為業余者,若用戶受雇于主流創作媒體,則其產生的內容就不應定義為UGC。 其次,UGC 應是利用他人作品進行再創作的行為,若是用戶的原創,則所生問題并沒有因為其是在網絡環境中產生而跳出著作權法保護之外,反而由于用戶利用了原有作品,在原作者和創作者之間造成的沖突是傳統版權法所未能妥善解決的,鑒于文章的思路,筆者將UGC限定在使用了已有作品的行為。 第三,所創造的內容應當具有一定限度的創造性,但不要求達到著作權法中關于作品的“獨創性”高度,也即,單純地將他人的表達通過無任何創造性或選擇性的復制、截取等行為不能算作UGC。 最后,UGC是一種以互聯網為媒介進行傳播的行為,其創作的內容得以在互聯網的自由空間實現共享。 綜上所言,筆者認為,UGC是不以此為業的普通用戶,在他人作品基礎之上,融入自己的創造性智力成果,產生并在網上進行傳播的行為。
二、 用戶創造內容對傳統著作權制度的挑戰
為了促進文學、藝術、科學領域的繁榮發展,法律賦予貢獻出智力勞動的作者以著作權,主要包括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并且規定著作財產權可以轉讓,從而使作者獲得經濟激勵,起到鼓勵作者和市場上的潛在創作者發揮腦力勞動的效果,貢獻出自己的智力成果。 他人使用作者的作品應當獲得作者的許可并支付報酬。 然而,互聯網的普及使得用戶在享受這些智力成果的同時,也生發出利用這些已有作品進行再創作和傳播的愿望,海量的資源為網絡用戶們提供了表達與創作的便利,卻也給作品權利人帶來了不可估量的經濟損失,Web2.0 時代背景下,用戶創造內容的泛濫對傳統著作權制度造成了沖擊。
(一)用戶創造內容的創作與傳播行為對作品法定權利的挑戰
用戶創造內容主要是網絡用戶利用已有的作品或者作品片段、元素進行再創作,包括利用已有的文字作品、音樂作品、影視作品、美術作品等,通過加入自己的思想、融入自己的創造,以剪輯、改編、重新編排等方式衍生出一個新的作品,并且通過各大社交平臺進行發布,使得他人可以接觸甚至繼續進行轉發。 由此可見,對于已有作品不可避免的涉及復制、演繹和傳播行為,而這些權利均是受著作權控制的行為。
關于著作人身權,網絡用戶進行創作時往往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是落入權利人專有權利范圍內的,因此往往沒有標注原有作品名稱和作者姓名,這一行為侵犯了作者的署名權;或者在利用作品過程中,由于出于有趣或者其他原因,故意丑化詆毀原作品的行為也時而有之,這一行為侵犯了作者修改權和保護作品完整權。
關于著作財產權,前已談及,用戶創作內容的方式決定了其至少會侵犯作者的復制權、改編權、信息網絡傳播權等。其中最為值得注意的是,用戶創造內容中還泛濫著大量的所謂致敬經典的同人作品,這些行為因為創作者并沒有將所產生的作品進行盈利,并且其本身也是出于對原作者及其作品的喜愛,因此,原作者即使心中不滿,但是由于缺乏著作權法的明確規定,也往往不得不采取容忍的態度放棄維權。 伴隨著原本為了保護作品而存在的著作權法的無能為力,原作者們也只好一聲嘆息。
(二)用戶創造內容對著作權法許可制度的挑戰
用戶創造內容并不僅存在于互聯網環境中,在Web2.0時代到來之前,由于有限的傳播技術,專業制作流媒體的商業媒體控制著文化產品的復制、演繹和傳播,商業主體與著作權人之間依據著作權法的規定,由商業主體向著作權人繳納許可使用費用,從而獲得相應的著作財產權,雙方權利義務可以得到很好地踐行,彼此之間各取所需,著作權法上的目的得到實現。 期間,雖然也有用戶未經權利人許可擅自用已有作品進行創作,但由于傳播技術的限制,通常不會對權利人的經濟利益造成重大影響。
然而,Web2.0 時代的到來打破了這一平衡,傳統傳播模式下的創作者、傳播者、消費者身份變得不那么彼此獨立,創作與傳播行為也因為互聯網技術和數字技術的發展而變得“平民化”,每個人都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意愿、觀點,自由傳播自己所形成的“作品”,造成作品使用的范圍和方式的不確定性很大,原作者也難以通過互聯這張“網”找到侵權人,更不必說要求網絡用戶事先取得權利人的許可。
用戶創造內容對于傳統著作權制的挑戰表明了并非是互聯網時代社會公眾無視法律的態度更甚,缺乏著作權保護意識故意與著作權法對抗,而可能是著作權制度與社會發展水平相脫節,忽視了大量社會公眾有著使用已有作品進行再創作的需求。 因此,為了從根源上解決這一問題,應重新審視現有著作權法在兩者之間的價值衡平,在立法層面查找并解決失衡的問題。
三、 用戶創造內容合法性的解釋途徑
著作權制度在誕生之初的目的并不是獎勵做出智力貢獻的創作者,根本目的是為了繁榮文化市場,所以為了激勵其他潛在創作者,賦予作品創作者以著作權,任何人使用作者的作品都應當取得作者的許可,并支付報酬。 又因為任何作品的創作都不是完全脫離現有作品而憑空產生,一部偉大的作品往往是在大量的前人作品啟發或是素材借鑒之上產生的,同時也為了廣大社會公眾能夠享受到這些精神產品,迎合公眾的特殊需求,著作權法又規定了法定許可制度和合理使用制度,以防止創作者為了盈利,借助強大的道德優勢和法律賦予的權利,專為個人之盈利,不顧社會公共利益的需求。 由于法定許可是指法律直接規定的給予使用者的一種特別許可,即不經作者及其他著作權人同意而使用其已發表的作品,對于用戶創造內容,著作權法并沒有這樣的規定,因此,只能通過合理使用的途徑嘗試解釋用戶創造內容的合法性。
(一)合理使用解釋的困境
我國《著作權法》對于合理使用采取了列舉式的立法模式,第22 條列舉了合理使用的十二種情形,且沒有設置兜底性條款,并且也缺乏相關的司法解釋,導致很多利用他人作品的行為符合著作權法宗旨,卻因為合理使用條款的僵化而不能被認定為合法。 試圖將用戶創造內容行為合法化,就不得不考慮該行為的性質,由于用戶創造內容涉及創作和傳播兩個行為,所以與這一情形相近似的也只能用《著作權法》第22 條第二項的“為介紹、評論某一作品或者說明某一問題,在作品中適當引用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來加以擴大解釋適用,但是合理使用都要求對原作品進行少量或適當地引用,也即個人使用+適當引用,這就與用戶創造內容的實際產生矛盾,因為網絡用戶創造內容往往更加注重分享自己的價值理念,而非專為個人享受,那么強行適用著作權法的合理使用條款進行無疑是將用戶創造內容這一行為進行抹殺。 雖然《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21 條也規定,“依照著作權法有關規定,使用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的已經發表的作品的,不得影響該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損害著作權人的合法利益。”但該條仍然是建立在《著作權法》所列舉的12 種合理使用情形,無法單獨用以解釋用戶創造內容的合法性,判斷用戶創造內容的規則的僵化和司法解釋的缺位這兩個制度上的缺陷意味著立法者需要重新審視我國合理使用的規定,尋求其他解釋路徑。
(二)建議引入轉換性使用的解釋路徑
關于轉換性使用的內涵,王遷教授在他的《著作權法》一書中定義為:對原作品的使用并非為了單純地在再現原作品本身的文學、藝術價值或實現其內在功能或目的,而是通過增加新的美學內容、視角、理念,或通過其他方式,使原作品在被使用過程中具有了新的價值、功能或性質,從而改變了其原先的功能或目的。 簡言之,轉換性使用產生的作品不同于原作品,具有了新的價值、功能或性質。 這一概念最早是美國法院在認定合理使用時法官造法的產物,但也僅僅是用來認定合理使用第一個要素是否符合①,即使用的性質和目的,是否構成合理使用仍需要考慮其他三個要素。 不同于美國的四要素理論,我國在認定合理使用時遵循了國際條約的三步檢驗法,第一,合理使用只能是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使用,這里的“某些特殊情況”應當是非營利性的、為社會發展需要而不得不使用的。 第二,合理使用不得與作品的正常利用相沖突。 第三,不得損害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 三者缺一不可,否則不能稱之為合理使用。 雖然在具體實務中,已經有法院采用了轉換性使用來認定合理使用,但作為成文法國家,仿照英美法系的方法雖不失為一種良好的借鑒,但在立法與司法上卻飽受質疑。 因此,必須明確轉換性使用在我國合理使用制度中的解釋方法,為之后的立法與司法提供夯實的基礎,從而為解決類似符合合理使用的案件提供判決的依據。
用戶創造內容的特點在于用戶往往是大篇幅使用已有作品進行重混行為,并且將所產生的新內容進行網上傳播,這一行為因為超越傳統合理使用制度的“適當引用”“部分引用”而難以被認定為權利的例外,而轉換性使用將重心放在“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上,即使用目的非為再現原作品的價值,使用方式是通過增加作品的新表達、新意義、新功能。 這與當下全民眾創的實踐情形恰好契合。
通過符合轉換性使用的使用目的和適用方法的要求,進而認定構成合理使用只是解決了用戶創造內容的行為不構成對原作品的侵權,也即解決了用戶創造內容的“創造行為”的合法性問題,然而,用戶創造內容后并不像傳統的合理使用行為一樣,前者更多的是通過傳播分享所創造出的“作品”來行使自己的表達自由,甚至可能因為新作品而獲得一定的利益,但這并不影響合理使用的成立,只要網絡用戶在“創造”內容時是以不同于原作品的使用目的,增加了自己的新理解,具有了新的價值,即認為構成合理使用。
總結而言,通過轉換性使用認定用戶創造內容構成合理使用,無須拘泥于傳統合理使用制度對于引用數量的要求,也打破了對于構成合理使用不得進行商業性行為的規定,有利于促進互聯網“眾創文化”的繁榮,激發全民智力創造的活力,符合互聯網時代民眾自由表達的意愿。
四、 結語
將用戶創造內容進行合法化體現了保護民眾自由表達的要求,但著作權法卻不能以犧牲作品權利人的法定權利為代價,因此著作權法應當在用戶的興趣表達與作者的權利保護之間進行平衡。 轉換性使用的引入,通過使用目的和使用方法兩個核心要件,將符合“轉換性”的用戶創造內容予以肯定,但同時也要符合我國著作權制度中“不得影響該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合理地損害著作權人的合法利益”兩個要求,將西方的經驗借鑒到我國著作權體制中來,在我國著作權體系下進行解釋,為立法活動與司法實踐提供合法性前提,在保障用戶表達自由的同時也兼顧權利人的經濟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