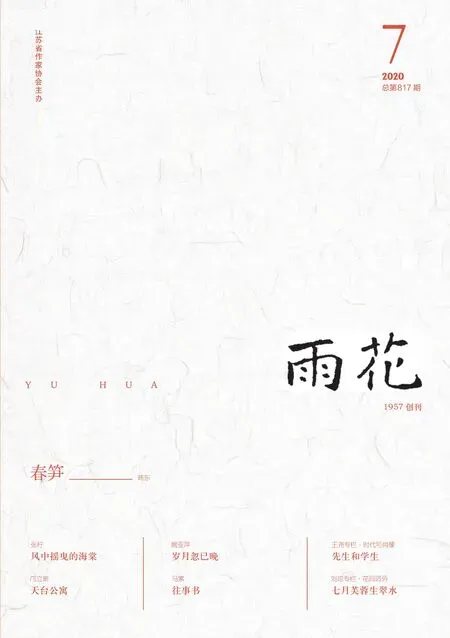歲月忽已晚
金農(nóng):寂寥抱冬心
金農(nóng)畫(huà)過(guò)一幅《月華圖》,小立軸,高116 厘米,寬54 厘米。泛黃的宣紙上,畫(huà)面的上端,高懸一輪散發(fā)著七彩光芒的滿(mǎn)月,滿(mǎn)月的內(nèi)部,以淡墨為主,濃墨為輔,簡(jiǎn)單勾勒了幾筆陰影,神似廣寒宮里寂寞了幾千年的玉兔,桂樹(shù)和嫦娥的幻象。畫(huà)卷的右下方有金農(nóng)自己的題跋:月華圖畫(huà)寄墅桐先生清賞七十五叟金農(nóng)。這幅畫(huà)現(xiàn)在由故宮博物院館藏。《月華圖》想要傳遞出一種什么樣的情感?是孤獨(dú)么?已經(jīng)七十五高齡且皈依佛門(mén)的金農(nóng),還會(huì)為孤獨(dú)所困么?是人與自然的合體么?金農(nóng)先生的主張是一個(gè)人獲得了超然于物象之外的自由之后,重新回到現(xiàn)象中來(lái)。隱于自然,或高于自然,皆不符合他的哲學(xué)主張
古老的月亮被詩(shī)人們傳誦了幾千年。有“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壯美;有“明月幾時(shí)有,把酒問(wèn)青天”的惆悵;有“行宮見(jiàn)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的愁恨……哪一輪月亮,和金農(nóng)畫(huà)中的月亮一樣務(wù)虛、簡(jiǎn)單、直陳?仿佛抽去所有的支撐物,只留下一個(gè)精神坐標(biāo),縈繞于心的,不僅是眼睛所見(jiàn)置身于畫(huà)中,猶如置身于虛幻之境,身體失重,飄向迷茫,飄向無(wú)盡,唯有在虛無(wú)中,才能感覺(jué)到生命的真實(shí)存在,以及那光影斑駁的月亮的真實(shí)存在。張庚在《國(guó)朝畫(huà)征錄》里評(píng)價(jià)此畫(huà):非復(fù)塵世所見(jiàn),蓋皆意為之。也有人評(píng)價(jià)此畫(huà)毫無(wú)藝術(shù)性可言,如小孩子的涂鴉之作。瑞士畫(huà)家保羅·克利有一幅《月光》與金農(nóng)的《月華圖》有異曲同工之妙。藍(lán)色的夜空,一輪澄黃滿(mǎn)月懸掛在高處月亮在遠(yuǎn)離人間的地方,不參與敘事,又指向無(wú)盡。比金農(nóng)晚出生二百年的畢加索說(shuō):“我用了四年時(shí)間,畫(huà)得像拉斐爾一樣好;但用盡了一生時(shí)間,才能像孩子那樣畫(huà)畫(huà)。”
汪曾祺似乎不太喜歡金農(nóng)。他在小說(shuō)《金冬心》中這樣描述:陳聾子剛要走,金冬心叫住他:“不忙。先把這十張燈收到廂房里去。”陳聾子提起兩張燈,金冬心又叫住他:“把這個(gè)——搬走!”他指的是堆在地下的《隨園詩(shī)話(huà)》。陳聾子抱起《詩(shī)話(huà)》,走出書(shū)齋,聽(tīng)見(jiàn)冬心先生罵道:“斯文走狗!”陳聾子心想:他這是罵誰(shuí)呢?
乾隆二十年(1755年),借園的主人李方膺邀請(qǐng)金農(nóng)、袁枚、沈鳳三人于借園雅集。然而,那日雷聲大作,暴雨如注,友人都來(lái)不了。李方膺在惆悵的情緒里,鋪紙,研墨,作了一幅《梅花長(zhǎng)卷》,并在題記上寫(xiě)下這件事。
幾日后,一個(gè)被洗滌得纖塵不染的清麗月夜,三人來(lái)到借園。幾壺老酒,幾碟小菜,幾位老友,飲酒賦詩(shī)。李方膺離席,取來(lái)自己前幾日等友人不遇所作的《梅花長(zhǎng)卷》。在沾了露水與月華的石桌上徐徐展開(kāi),請(qǐng)友人們題詩(shī)。自己從懷中掏出一支長(zhǎng)笛,吹起來(lái)了。月下的笛聲那樣柔和,空靈,娓娓動(dòng)聽(tīng),且余韻繚繞,透著一種塵世難得一見(jiàn)的高貴和孤寂。老友們聽(tīng)得癡了,呆了。一曲終了,才想起來(lái)要題詩(shī)。
袁子才寫(xiě)下:秋夜訪(fǎng)秋士,先聞水上音。半天涼月色,一笛酒人心。三更揮手別,心與七弦期。
金農(nóng)寫(xiě)下:人生天地乃借鏡,即事抒懷本無(wú)定。李侯折柬招借園,同人俱是梅花仙。淋漓潑墨寫(xiě)斜橫,老干新枝共幾丫。
……
詩(shī)題畢,友人們共飲一壺茶。清明的月色中,搖曳的樹(shù)影隨風(fēng)拂過(guò)石桌表面,與浸于暗影中的石桌側(cè)面形成明暗對(duì)比,宛若澄澈水底的神秘境界。面對(duì)此情此景,他們陷入寂然。不知是誰(shuí)先打破了沉默,聊起讀書(shū)的話(huà)題。袁子才因?yàn)轶w內(nèi)的酒精起作用了,他自詡為席間讀書(shū)最多最深之人。這下就引起鄉(xiāng)黨金農(nóng)的不痛快了。金農(nóng)若有所思地端起茶盞,汲了一小口,目光一直落在杯沿上方,慢悠悠地說(shuō):“君藏書(shū)在櫝,我與佛同龕。”
袁子才聽(tīng)了這話(huà),氣得不行。礙于朋友面子,又不得發(fā)作,簡(jiǎn)直坐立不安,臉色一會(huì)兒白,一會(huì)兒灰,胡亂找個(gè)理由退席。日后,他一旦逮著機(jī)會(huì),就在文章中罵金農(nóng)是“野狐禪”。
金農(nóng)這次借機(jī)罵袁枚,是不是因?yàn)樗?qǐng)?jiān)对诮鹆陰兔κ圪u(mài)他制作的畫(huà)燈,而袁枚卻以一封“奈金陵人但知食鴨脯耳,白日昭昭,尚不知畫(huà)為何物,況長(zhǎng)夜之悠悠呼……”的書(shū)信婉拒了金農(nóng),才引起金農(nóng)的不滿(mǎn)?
金農(nóng)的畫(huà)燈雖然在袁枚這兒碰了一鼻子灰,在另一個(gè)人那里卻很暢銷(xiāo)。這個(gè)人就是年方二十四歲的少年才子羅聘。
一連幾日,金農(nóng)和啞妾在街市上賣(mài)燈,快收攤時(shí),總有一個(gè)溫文爾雅的年輕人從北邊走來(lái),把他的畫(huà)燈全部買(mǎi)下,有多少買(mǎi)多少。年輕人一走,啞妾就對(duì)金農(nóng)比劃,覺(jué)得這里面有蹊蹺。金農(nóng)想想也對(duì),把燈攤交給啞妾照看,自己一路尾隨著那個(gè)年輕人,行至彌陀巷,年輕人進(jìn)了門(mén)。金農(nóng)先生站在窗口看了一會(huì)兒。一個(gè)娉娉婷婷的年輕女子,提來(lái)一盞蠟燭,兩人在燭光下把畫(huà)燈逐個(gè)小心翼翼地拆開(kāi),燭火搖曳的陰影在這對(duì)佳人年輕光潔的額頭上如水波一樣輕輕蕩漾開(kāi),他們把有皺褶的畫(huà)紙用手掌輕輕壓平,然后,對(duì)著畫(huà)紙上的畫(huà)開(kāi)始虔誠(chéng)臨摹。
金農(nóng)悄無(wú)聲息地離開(kāi)了。
這里是羅聘和方婉儀的家。羅聘與方婉儀都是年少成名,一個(gè)擅畫(huà)梅竹,一個(gè)擅畫(huà)花鳥(niǎo),在揚(yáng)州城里小有名氣。羅聘一直想拜金農(nóng)先生為師,他對(duì)金農(nóng)先生的才學(xué)簡(jiǎn)直是頂禮膜拜。奈何托人帶了幾次信都石沉大海。此番,金農(nóng)先生為貼補(bǔ)家用而賣(mài)燈,方婉儀就讓羅聘去買(mǎi)燈,借機(jī)接觸金農(nóng)先生。
金農(nóng)從彌陀巷回到燈攤前,集市散了。燈火熄滅,啞妾收拾妥當(dāng),倆人把東西裝上車(chē)。金農(nóng)在前面拉,啞妾在后面推。樹(shù)影婆娑的靜夜,車(chē)輪駛過(guò),在濕漉漉的街上發(fā)出咯吱咯吱聲,拋下兩條閃著寂寞微光的轍痕。颼颼的涼意鉆進(jìn)金農(nóng)的長(zhǎng)袍里,他躬肩縮背,拉著車(chē),走進(jìn)黑夜更深處。
近日登門(mén)催債的人漸多,字畫(huà)在揚(yáng)州巿場(chǎng)也漸漸滯銷(xiāo)了。一籌莫展之時(shí),冬心先生靈光一閃,揚(yáng)州人愛(ài)玩燈,干脆賣(mài)畫(huà)燈吧,他負(fù)責(zé)畫(huà),另雇一人扎,以此來(lái)填補(bǔ)虧空。
袁枚這樣描述金農(nóng)的日常生活:“忽供雞談,忽歌狗曲。或養(yǎng)靈鬼,或籠蟋蟀。揮甘始之金,餐李預(yù)之玉,識(shí)齊恒公之尊,蓄童汪锜之仆。”《小倉(cāng)山房詩(shī)集》和《墨林今話(huà)》中也寫(xiě)道:“蓄一洋狗名阿鵲,每食必投肉寮食之”;“賣(mài)文所得,歲記千金,隨手散去”;“饑來(lái)得錢(qián)亦復(fù)賣(mài),飽則千金不肯賈”……
讓羅聘頂禮膜拜的金農(nóng),金冬心先生,被譽(yù)為“揚(yáng)州八怪”之首。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出生于浙江杭州,家境優(yōu)渥。早早就以詩(shī)文成名有一次,金農(nóng)的父親帶金農(nóng)到杭州的長(zhǎng)明寺游玩,見(jiàn)識(shí)了寺中珍藏的畫(huà)僧貫休所作的十六軸菩薩圖像。菩薩的低眉斂目,向內(nèi)凝聚的力量,以及周身散發(fā)出的神性之美,深深打動(dòng)了金農(nóng)。這種宿命般的邂逅點(diǎn)亮了少年心中的燈塔,仿佛混沌的世界對(duì)他開(kāi)啟了一扇隱秘之門(mén)。
少年金農(nóng)拜大學(xué)者何焯為師,何焯也是皇八子胤禩之師。作為康熙時(shí)代文壇的領(lǐng)袖人物,何焯不僅擁有一流的才學(xué),還積攢了豐富的人脈和政治資源。自視甚高的金農(nóng)也唯何焯馬首是瞻。金農(nóng)對(duì)金石碑版、繪畫(huà)的愛(ài)好,正是在何焯門(mén)下學(xué)習(xí)時(shí)養(yǎng)成的。
金農(nóng)在何府學(xué)習(xí)不到兩年,家中傳來(lái)父親去世的消息,他必須回家奔喪,學(xué)業(yè)暫時(shí)中斷。父親去世后,家境日益蕭條。也正是這個(gè)時(shí)候,老師何焯因政治斗爭(zhēng)失敗而獲罪,下獄險(xiǎn)些喪命。后來(lái)雖然獲釋?zhuān)桓锶チ艘磺泄巽暎瑳](méi)多久就郁郁寡歡而逝這對(duì)金農(nóng)的打擊極大。他似乎看不見(jiàn)希望了。禍不單行,金農(nóng)自己又生了一場(chǎng)病,沒(méi)有收入,連飯都沒(méi)得吃了哪里有錢(qián)治病。病床上的金農(nóng)想起自己英才早發(fā),如今卻一事無(wú)成,落差懸殊,心生悲涼。感覺(jué)自己真的墜入了人生的凜冬。他想起崔國(guó)輔的“寂寞抱冬心”之語(yǔ),便為自己取名號(hào)為“冬心先生”。
病愈后的金農(nóng)暫時(shí)收斂了讀書(shū)走仕途之志向,開(kāi)始了一邊賣(mài)書(shū)法篆刻作品,一邊游山玩水的生活。金農(nóng)三十四歲時(shí)出游揚(yáng)州,那時(shí)候的揚(yáng)州文壇是一個(gè)活躍的買(mǎi)賣(mài)市場(chǎng),只有靠卓越的作品去贏得人氣,才能在揚(yáng)州文壇存活。金農(nóng)初到揚(yáng)州遇冷,作品無(wú)人問(wèn)津。他在杭州時(shí),與丁敬、吳西林并稱(chēng)“浙西三高士”,但揚(yáng)州這個(gè)競(jìng)技場(chǎng)不好混,全國(guó)各地的文人雅士都薈聚于此等待買(mǎi)家。
揚(yáng)州濃郁的文化與宗教氛圍,以及一幫志同道合的朋友們,還是吸引了金農(nóng),他決定在揚(yáng)州終老。
金農(nóng)在揚(yáng)州賣(mài)了一段時(shí)間作品,手中有了些錢(qián)財(cái),又計(jì)劃云游四海了。友人汪士慎、馬曰璐、厲鶚等人為他送行。汪士慎寫(xiě)送別詩(shī)一首,名叫“送金壽門(mén)”,寫(xiě)道:“詩(shī)人性情慣離家,小別衡門(mén)落照斜,明日馬蹄踏芳草,梨花風(fēng)雨又天涯。”在雨打梨花落滿(mǎn)地時(shí),金農(nóng)北上進(jìn)京了。
金農(nóng)進(jìn)京,名為游覽山川,實(shí)為參與時(shí)政,實(shí)現(xiàn)自己的人生目標(biāo):建功立業(yè),重建金氏一門(mén)。然而,他在京城待了有大半年,也見(jiàn)了不少達(dá)官顯貴,但沒(méi)人愿意為他牽線(xiàn)搭橋。雖然口袋里錢(qián)財(cái)已快見(jiàn)底了,他還是不急著返回,執(zhí)著地穿梭于京城的各個(gè)府邸之間,送人字畫(huà)、硯臺(tái)、金石,可惜均無(wú)回音。金農(nóng)在悲憤之中寫(xiě)下“懷抱名刺,字跡漫滅”。理想再一次泯滅,金農(nóng)身無(wú)分文了,怎么回家都是個(gè)難題。最后,思來(lái)想去,他賣(mài)掉了隨身攜帶的好友高翔用隸書(shū)書(shū)寫(xiě)、汪士慎鐫刻的寫(xiě)經(jīng)硯,才換得返程的路費(fèi)……
金農(nóng)中年時(shí)游歷全國(guó)達(dá)十五年之久。他不斷地從周遭的新事物中汲取營(yíng)養(yǎng),內(nèi)化為詩(shī)歌、書(shū)法之靈感。他雖然沒(méi)有實(shí)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卻在行萬(wàn)里路中摸索出一條屬于自己的創(chuàng)作路徑。他的詩(shī)與書(shū)法在這一時(shí)期呈創(chuàng)作井噴之狀,題材新穎,手法創(chuàng)新,所見(jiàn)所思,化為創(chuàng)作靈感汩汩而出。
金農(nóng)再回到揚(yáng)州時(shí),成為揚(yáng)州文壇的領(lǐng)軍人物。有一年暮春,一位大鹽商在平山堂設(shè)宴賞花,金農(nóng)為座上賓。揚(yáng)州鹽商財(cái)力雄厚,又重文化,愛(ài)結(jié)交文人雅士。席間,主人以“飛紅”為行酒令,要求眾賓客所吟的詩(shī)作中,必須有“飛”和“紅”二字。一輪下來(lái),眾賓客也都答上來(lái)了。臨了,輪到主人了,主人思考了半天,急得額頭沁出汗珠子來(lái),慌了,好對(duì)子全給前面的人說(shuō)了。“柳絮飛來(lái)片片紅。”主人好不容易擠出一句。
眾賓客愕然,柳絮不是白色的嗎?怎么就變成“片片紅”了?“答得不對(duì),不通,自罰三杯!”
主人那個(gè)尷尬啊,抓耳撓腮,羞赧不已,正不知如何應(yīng)對(duì)。
關(guān)于這段公案,汪曾祺在小說(shuō)《金冬心》中有精彩的描述:
“諸位莫吵,此詩(shī)自有出處,是元人詠平山堂的詩(shī)句。冬心先生站起來(lái),朗誦全詩(shī),‘廿四橋邊廿四風(fēng),憑欄猶憶舊江東。夕陽(yáng)返照桃花渡,柳絮飛來(lái)片片紅。’大家一聽(tīng),全都擊掌,好詩(shī)!如此尖新,卻又合情合理,定是元人之作,而非唐非宋,到底是冬心先生,元人的詩(shī)我們知道得太少了,慚愧慚愧!”
乾隆元年(1736年),四十九歲的金農(nóng)赴京城參加“博學(xué)鴻詞”科應(yīng)試。說(shuō)實(shí)話(huà),他的心里很虛,上一次赴京遭遇的打擊還沒(méi)有消彌。他怕萬(wàn)一名落孫山,丟了面子。就在這樣的心態(tài)下,他去考試了。他不是一個(gè)人去的,他的手中牽了一只洋種小狗,在一眾正襟危坐的應(yīng)試者中間,格外醒目與反叛。監(jiān)考官都不知道怎么處理,因?yàn)椤緵](méi)遇到過(guò)先例。小狗汪汪叫,金農(nóng)捏緊繩索,表情悠然自在,仿佛只是參加一場(chǎng)郊游活動(dòng)。至于他是不是以此舉來(lái)掩飾內(nèi)心的慌亂與不自信,就不得而知了。
考試結(jié)果出來(lái)了,金農(nóng)名落孫山。
在知天命的年紀(jì)經(jīng)歷落榜,金農(nóng)的人生發(fā)生了轉(zhuǎn)變,徹底斷了仕途之念。以詩(shī)文書(shū)法聞名于天下,他打算以后賣(mài)畫(huà)謀生了,畢竟,賣(mài)畫(huà)收入更多些。他雖然沒(méi)有系統(tǒng)學(xué)習(xí)過(guò)繪畫(huà),但天賦異稟,或者說(shuō),藝術(shù)是相通的,一出手就是大師水準(zhǔn)。
金農(nóng)六十四歲時(shí)在《畫(huà)竹題記》上,題了一段話(huà):“予今年學(xué)畫(huà)竹,竹之品與松同,總要在象外體物之初耳。”這與莊子的超現(xiàn)實(shí)主義有很大的區(qū)別。莊子在《宋元君將畫(huà)圖》里描述一位畫(huà)師:“解衣盤(pán)礴,裸袖握管,君曰:可矣,是真畫(huà)者也。”莊子追求的是“無(wú)為”,是拋下一切的純精神性的自由,是“解衣盤(pán)礴,裸袖握管”之后,什么都不畫(huà)。而金農(nóng)卻是在獲得超然于物象之外的精神自由之后,仍舊回到現(xiàn)象中來(lái),回到物之初畫(huà)竹,比較竹與松的品格。是一個(gè)從物出發(fā),到精神,再到物的過(guò)程。這樣也就能理解為何金農(nóng)在皈依佛門(mén)多年之后,仍以七十六歲的高齡,向南巡揚(yáng)州的乾隆皇帝呈進(jìn)詩(shī)表。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金農(nóng)七十一歲,收羅聘為徒。老妻去世后他亦遣散了啞妾家仆,一個(gè)人棲身于揚(yáng)州西方寺的兩間破敗的偏室里,試圖在佛教中尋求性靈的自由。少年時(shí)隨父親在杭州長(zhǎng)明寺邂逅的菩薩畫(huà)卷,與他內(nèi)心的情感形成了某種照應(yīng),一條向佛之路,在他的心里業(yè)已緩緩開(kāi)啟。
西方寺始建于唐代永貞年間,位于揚(yáng)州駝嶺巷西側(cè)。初建時(shí)敷描的丹青色,以及廟宇內(nèi)部艷麗的濃彩淡繪都已經(jīng)褪色,剝落,化為齏粉。滿(mǎn)眼望去,破窗爛墻,蛛網(wǎng)綿密。金農(nóng)在墻壁上題寫(xiě):“無(wú)佛又無(wú)僧,空堂一盞燈。”
清涼的月光下,西方寺的正殿前金農(nóng)與羅聘師徒二人無(wú)言地站在寺檐下的暗影里,門(mén)洞處的光落在彩繪剝落的佛像上,有一種沉穩(wěn)細(xì)微的光華而明與暗的對(duì)比,使得佛陀的五官更立體,流動(dòng)的衣褶里,似乎透著些微的呼吸。他們不約而同跪下來(lái),雙手伸直拱合,俯頭到手,從身體到靈魂無(wú)比虔誠(chéng)、無(wú)比投入地叩拜起這個(gè)博大的同行者、引路者。
金農(nóng)稱(chēng)自己是“如來(lái)最小弟子”。而弟子羅聘亦步亦趨,稱(chēng)自己是“今世畫(huà)人前世僧”。師徒經(jīng)常沏一壺清茶,對(duì)坐于西方寺庭院里的石凳上,探討佛法與藝術(shù)。
金農(nóng)晚年的創(chuàng)作以畫(huà)佛寫(xiě)經(jīng)為主,《無(wú)量壽佛》是其中一幅,畫(huà)面上,一個(gè)身穿紅色袈裟的和尚雙腿盤(pán)坐在石階上。和尚左手握著拂塵,右手食指微微抬起。八字眉下,眼睛半睜半閉。和尚安靜地端坐著,寬大的袖籠在風(fēng)中飄蕩,有一種精神性的深邃、平和與強(qiáng)韌,無(wú)言地教誨著蕓蕓眾生。
還有一幅叫《色設(shè)佛相圖》的偉大作品,畫(huà)中,佛陀閉合著嫻靜的雙眼,袈裟皺褶所用的線(xiàn)條是金石味的書(shū)法用筆,如刀刻一般的力度,有一種壓倒性的魅力。如果有一個(gè)人背負(fù)沉重的苦難而來(lái),在與這幅佛像邂逅之后,一定能獲得心靈的慰藉與寧?kù)o。佛陀的袈裟隨著雙手合掌的動(dòng)作而微微掀起,面部表情平和、樸素。高挺的鼻梁下面,被胡須包裹著的柔和的嘴角微微上揚(yáng),仿佛在為我、為眾生而祈愿。圍繞在佛陀四周的,是金農(nóng)寫(xiě)下的二十多行、七百余字的創(chuàng)作背景。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六月二十四日,是弟子羅聘的夫人方婉儀(白蓮)女史的生辰。金農(nóng)七十六歲了,身體狀況也很差。但是,他還是去彌陀巷的“朱草詩(shī)林”參加了這次雅集。
那一晚的雅集設(shè)在“朱草詩(shī)林”的回廊。涼風(fēng)習(xí)習(xí),月色清朗。金農(nóng)坐主賓席,老友鄭板橋坐在他旁邊,然后依次是蔣士銓、吳敬梓、羅聘等。此時(shí),老朋友汪士慎和馬曰琯馬曰璐都已作古了,袁枚遠(yuǎn)在金陵。朋友們見(jiàn)一面少一面了。他們都老了。就連寫(xiě)下“杭州只有金農(nóng)好”的老朋友鄭板橋,看上去也有些力不從心了。他與板橋先生“杯酒言歡,永朝永夕”的場(chǎng)景,仿佛就在昨天。而歲月的流逝如此之快、之急,怎能不令人傷感?夜色里,掛在回廊柱子上的一個(gè)個(gè)橢圓形紙燈,一直連向無(wú)盡,仿佛要把金農(nóng)的目光引向無(wú)限深邃和無(wú)邊無(wú)際的遠(yuǎn)方。
酒過(guò)喉嚨,年邁的金農(nóng)體內(nèi)有了灼人的熱量。他于醉眼蒙眬中看見(jiàn)弟子羅聘和他的愛(ài)妻年輕明亮的臉。想起了佛家“此死彼生,流轉(zhuǎn)不息”的教誨。金農(nóng)釋然了。他瞇起眼睛,在微光中看見(jiàn)了一片幻影,他無(wú)聲地穿過(guò)幻影,步履輕盈、矯健,仿佛重回年輕時(shí)光。他走進(jìn)一座空無(wú)一人的佛堂,殿里稀稀落落掛著幾條經(jīng)幡,里側(cè)有三個(gè)門(mén)洞,每一個(gè)門(mén)洞里都有一尊羅漢,每一尊羅漢都慈悲地凝望著他的靈魂。忽然,供案上的燭芯里爆出一朵朵細(xì)碎的火花,拼湊出一座七彩蓮花寶座,將佛堂映得絢麗多姿。在一片神圣靜默的金光里,一位臉上漾著平和微笑的佛陀從金農(nóng)面前經(jīng)過(guò),流動(dòng)的袈裟里,留下絲絲縷香息。金農(nóng)在這似夢(mèng)非夢(mèng)里感受到了自性的通透,不禁老淚縱橫,世間種種妄念俱滅。
那佛陀雙手合十,盤(pán)腿,從高處緩緩降臨于蓮花寶座。
方婉儀:我與荷花同日生
清晨的薄光下,方婉儀坐在庭院里陷入沉思,幾朵粉色的牽牛花兒散落在池塘的水面上,花瓣上有些晶瑩的水珠,滾來(lái)滾去,盈而不落。婉儀對(duì)著花瓣輕輕呵一口氣,水珠沿著鋸齒形的花邊流動(dòng),從最細(xì)微處沁入花瓣的肌理,洇溢出淡淡的煙霞,染暈了水面。婉儀凝視這一幕,目光隨著流動(dòng)的煙霞,慢慢沉潛于水底,靜水深流,花朵映于水鏡中,忽明忽暗,忽深忽淺。
這夏日晨曦的圖景讓她失魂落魄。她想喊出來(lái),想與人分享,想吟詩(shī),想流淚,想歌唱,想跳舞,又覺(jué)得最好還是自己珍藏吧。困擾她一夜的問(wèn)題終于找到答案了。一陣清風(fēng)吹過(guò),抖動(dòng)的枝杈在空氣中發(fā)出細(xì)碎的回響。
她把牽牛花從水里打撈出來(lái),放入小木桶,進(jìn)屋。
這是一個(gè)三廂房,中間是堂屋,左側(cè)房間里有一張梳妝臺(tái),四張?zhí)珟熞危粡埓竽敬玻覀?cè)的房間里放著一張書(shū)桌,上面有筆墨紙硯,夫君羅聘剛完成的《梅花圖卷》也攤在書(shū)桌上。堂屋后面,還有三小間。
昨夜,羅聘畫(huà)完《梅花圖卷》的最后一筆,沒(méi)有興奮之情,他一言不發(fā),坐在窗前陷入沉思,月光將他的影子拉得纖瘦、寂寥。婉儀提著衣裙輕輕走過(guò),她看著書(shū)桌上的畫(huà)卷有半個(gè)時(shí)辰之久,揣摩,思量,總覺(jué)得有一點(diǎn)缺憾,花瓣與枝葉之間的過(guò)渡,少一點(diǎn)細(xì)節(jié)。丈夫羅聘已經(jīng)名滿(mǎn)天下登門(mén)買(mǎi)畫(huà)的人絡(luò)繹不絕。她把困惑放心底,這一夜輾轉(zhuǎn)反側(cè),難以入睡。
婉儀把粉色牽牛花花瓣摘下,用小木棒輕輕搗碎,將溢出的細(xì)細(xì)的汁液,蘸在筆尖,對(duì)著畫(huà)卷上的梅花逐個(gè)細(xì)致點(diǎn)染。暈染了花汁的梅花圖花朵與枝葉間有了層次感,多了一點(diǎn)點(diǎn)顏色,整個(gè)畫(huà)面都鮮活了起來(lái)。羅聘醒來(lái),看到以花汁洇染而增色的畫(huà)卷,心中大悅,對(duì)夫人很是欽佩。他在畫(huà)卷上題寫(xiě):“予畫(huà)此卷三日始成內(nèi)子白蓮展觀再四,嫌其不甚分明晨起,乃摘牽牛花,浸汁,漬其花槲令觀者一目瞭然……”
方婉儀生于1732年6月24日這一天按民間的說(shuō)法是荷花娘娘的生日。婉儀有“淤泥不染青青水,我與荷花同日生”之詩(shī)句,她為自己取別號(hào)為“白蓮居士”“白蓮”。婉儀自幼雖然家境貧寒,但仍習(xí)詩(shī)書(shū)畫(huà),祖父父親都是讀書(shū)人。她的詩(shī)與畫(huà)名滿(mǎn)揚(yáng)州,曾經(jīng)有個(gè)大鹽商想以二十兩銀子的價(jià)錢(qián)買(mǎi)下婉儀的一幅閨中之畫(huà),被拒。她還著有《學(xué)陸集》《白蓮半格詩(shī)》。當(dāng)她嫁給少年才子羅聘后,因?yàn)榉蚓膭e號(hào)為“兩峰居士”,她就為自己取名號(hào)“兩峰之妻”,隱身于夫君背后。
生在閨閣之中的方婉儀是傳統(tǒng)的女性,自幼所受的教育就是崇尚女子的賢德。羅聘出售的畫(huà)作,有許多為夫妻合作,或婉儀代作。婉儀的畫(huà)更注重局部的細(xì)節(jié),從微小的細(xì)節(jié)里提取一條鮮活的生命脈絡(luò)。從她臨摹的一幅題為“張憶娘簪花圖”就可見(jiàn):畫(huà)卷上,天色將晚,前有層巒疊翠,后有大河潺潺,揮舞的墨點(diǎn)仿佛兩三只振翅欲飛的寒鴉。茅屋里,隔窗眺望的張憶娘,羅紗裙間的皺褶,眉目之間的幽寂,左手簪花一笑時(shí)眼底的哀怨,這些微小的細(xì)節(jié),都被方婉儀捕捉到了,落在紙上,構(gòu)成了這幅畫(huà)卷的靈魂。
1762年的6月24日,是方婉儀的三十歲生辰。金農(nóng)與鄭板橋幾乎是一前一后走進(jìn)了羅聘與方婉儀位于彌陀巷的家中。此時(shí)的金農(nóng)已經(jīng)風(fēng)燭殘年,羅聘攙扶著老師金農(nóng),“咚,咚,咚”的點(diǎn)地而行的聲音從彌陀巷由遠(yuǎn)及近地傳來(lái);在揚(yáng)州賣(mài)字畫(huà)的板橋先生也搖著紙扇子走過(guò)來(lái)了,他也叩響了“朱草詩(shī)林”的柴門(mén)。揚(yáng)州城里數(shù)得上名號(hào)的書(shū)畫(huà)家、詩(shī)人幾乎都來(lái)羅家了。鄭板橋送了一軸石壁叢蘭圖,并題寫(xiě)了四句話(huà):“板橋道人沒(méi)分曉,滿(mǎn)幅畫(huà)蘭畫(huà)不了。蘭子蘭孫百輩多,累爾夫婦直到老。”金農(nóng)先生留下的賀詩(shī)是:“謝家才女夸門(mén)第,嫁得王郎女夫婿,不但能詩(shī)詠絮工,能畫(huà)能書(shū)妍且麗。”
那一晚的“朱草詩(shī)林”星光燦爛。詩(shī)人們飲酒作詩(shī),畫(huà)家們對(duì)月潑墨。庭院里,婉儀站在流水潺潺的荷花池邊,池內(nèi)淡粉色的荷花與她穿著的水粉色綾羅長(zhǎng)裙相得益彰。她抬頭,向懸掛在青藤樹(shù)枝頭的月亮望去,稀薄的光影如細(xì)雨般被風(fēng)兒從高處盈盈吹落,落在她的發(fā)梢上、裙裾里。回廊里,她的丈夫羅聘與老師金農(nóng)先生、鄭板橋、吳敬梓、蔣士銓同坐一桌,酒性正酣,談性正濃。孩子們?cè)阪覒蛲嫠!6嗝疵篮玫囊环鶜q月圖景,她希望時(shí)間能定格,希望能把這一刻緊緊抓牢。然而,借著微濛的月光,她輕吟出的卻是蘇軾的:“此生此夜不長(zhǎng)好,明月明年何處看。”一陣涼意穿過(guò)她的身體。月亮從枝頭隱去,薄霧籠罩夜空。
時(shí)間到了1778年的除夕之夜,明亮的燭火下,羅聘、方婉儀帶著三個(gè)孩子齊上陣,繪制一幅畫(huà)作。六尺的花綾幛額平整攤開(kāi),羅聘畫(huà)梅,婉儀畫(huà)牡丹,女兒畫(huà)菊花,兩個(gè)兒子畫(huà)幽蘭。紙上,墨汁漸漸洇開(kāi),花朵漸次綻放。他們筆下的梅花、牡丹、菊花、幽蘭,雖神韻不一,卻氣質(zhì)相近。一家人用丹青妙筆潑出一個(gè)花團(tuán)錦簇的春天。
畫(huà)畢,一家人圍著桌子吃團(tuán)圓飯,桌上擺著美酒佳肴。婉儀端起酒杯,贈(zèng)夫君一首詩(shī):“推敲解仆吟除夜,渲染兒工畫(huà)歲朝。樂(lè)事人間如此少,勸君滿(mǎn)飲酒千瓢。”羅聘看著面色憔悴、咳嗽不止的妻子,想起她初嫁的歡顏,他曾為那段甜蜜時(shí)光留下一首《自度曲》,詩(shī)中寫(xiě)道:“采菱港口少風(fēng)波,兩頭纖纖同唱歌。吳娘初嫁,新婦雙娥。斜陽(yáng)未落,忽飛晚雨;歸也遲遲,悄無(wú)人影;想瓜皮小艇,去不多時(shí)。”念往昔,往昔已灰飛煙滅。他忽然感到了一陣心疼。這些年,他經(jīng)常出遠(yuǎn)門(mén)賣(mài)畫(huà),結(jié)交達(dá)官顯貴,游山玩水,到處逢場(chǎng)作戲,留她一人枯守青燈。他眼眶紅了,端起酒杯一飲而盡。
窗外,大雪紛飛。
夜深了,孩子們?cè)缫讶胨蚓治礆w。這些日子他幾乎都在小玲瓏館。家中的生活越來(lái)越艱難了,夫君的字畫(huà)賣(mài)出的銀兩,大部分被他拿去買(mǎi)金石古董了,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拿回來(lái)貼補(bǔ)家用。方婉儀不得不每天算計(jì)著過(guò)日子,琢磨著怎樣才能用最少的錢(qián),讓全家過(guò)得體面些。她從早到晚像陀螺一樣轉(zhuǎn)動(dòng)不停,也像陀螺一樣,沉默隱忍。她收斂起自己的七彩光芒,換上粗衣布衫,用曾經(jīng)握畫(huà)筆寫(xiě)詩(shī)的纖纖素手打掃屋子,操持三餐。作為一個(gè)主婦,她只能先關(guān)心生活的本質(zhì):食物與衣服。
窗外起風(fēng)了,方婉儀坐在梳妝臺(tái)前縫制衣裳,窗戶(hù)噼噼啪啪,她停下手中的活,望著這間空蕩蕩的屋子,燭火搖晃,將她的身體、梳妝臺(tái)、床椅、書(shū)桌,一起投射于斑駁的墻壁上,從鏡子里望去,床椅的陰影矗立在窗戶(hù)上方,宛如一座空城。
婉儀輕嘆一聲,走到書(shū)桌前,打開(kāi)抽屜,把夫君剛完成的《鬼趣圖》輕輕展開(kāi)。每看一次,她都激動(dòng)得無(wú)以言表。這些年,折磨了他很久的素材,他終于畫(huà)出了,這是前無(wú)古人的創(chuàng)舉。她相信,哪怕就憑這一幅《鬼趣圖》,羅聘的名字也將載入史冊(cè)。
八幀小圖,每一幀都有“別趣”。婉儀看著第三幀。畫(huà)面的遠(yuǎn)景是一個(gè)穿橙色上衣、煙灰色長(zhǎng)裙的女子依偎在一個(gè)穿灰色長(zhǎng)袍、手執(zhí)蘭花草的男子懷中,倆人在耳語(yǔ)。周?chē)潇F繚繞隱隱約約可見(jiàn)山巒疊嶂的倒影。一個(gè)白無(wú)常身著白袍,頭戴黑白相間的高帽,手握著白紙扇,掩面竊笑,在前方,側(cè)身偷聽(tīng)他們的談話(huà)。他笑他們太癡狂,都死到臨頭了,還你儂我儂甜蜜相擁的戀人,臉上沒(méi)有慌亂之色他們的眼里就只有彼此,根本無(wú)視白無(wú)常的存在。即將共赴黃泉或十里相送的戀人,再一次握緊彼此的手。
婉儀坐在黑暗里,感覺(jué)一切都像潮水一樣,正以緩慢的、難以察覺(jué)的速度離她而去。風(fēng),越刮越大。
她的咳嗽更嚴(yán)重了,她用手帕緊緊捂著嘴巴,怕吵醒在對(duì)面廂房里熟睡的孩子們。大風(fēng)撲咚撲咚地敲打門(mén)扉,丈夫回來(lái)了嗎?她打開(kāi)門(mén),一陣涼風(fēng)灌了進(jìn)來(lái),燭火撲哧撲哧搖晃幾下,終于熄滅了。又一陣猛烈的咳嗽和鉆心的涼意占領(lǐng)了她的身體,手帕上的鮮血被黑夜染成深紫色。她卻突然感到了平靜,仿佛旅程快要走向終點(diǎn)。曾經(jīng)懸著的一切都已塵埃落定都在她的心里找到各自的歸宿。黑暗中,她對(duì)萬(wàn)物投以長(zhǎng)長(zhǎng)的一瞥。
當(dāng)方婉儀的生命之花被束縛于封建禮教而快要枯萎時(shí),與她同時(shí)代的一位名叫勒布倫夫人的法國(guó)宮廷女畫(huà)家,在歐洲的上流社會(huì)正聲名鵲起同樣是極具才華的女畫(huà)家,方婉儀只能囿于傳統(tǒng),以夫?yàn)樘欤彝橹仉[身于彌陀巷。哪怕只留下了極少數(shù)的幾部作品,也被袁枚寫(xiě)進(jìn)了《隨園詩(shī)話(huà)》:“閨中也樹(shù)千秋業(yè),未許山人獨(dú)擅明”。而勒布倫卻夫人被邀請(qǐng)至凡爾賽宮為瑪麗王后畫(huà)肖像,成為宮廷御用畫(huà)師,并先后去往了意大利、奧地利、普魯士、俄國(guó)、英國(guó)、瑞典,以畫(huà)女人的肖像為主,為她們定格了易逝青春的姿影。勒布倫夫人的肖像畫(huà)細(xì)膩,對(duì)于情緒的描摹非常準(zhǔn)確。在洛可可風(fēng)格統(tǒng)治的時(shí)代,留下眾多新古典主義杰作。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五月,羅聘又要赴京城。病榻上的婉儀掙扎著起床,為丈夫收拾行囊。單衣幾件,長(zhǎng)袍幾件,帽子幾頂,布鞋幾雙,早就備下了。一針一線(xiàn)都是出自婉儀之手,絲絲縷縷的針腳間,傾注了她無(wú)盡的牽掛與愛(ài)戀。婉儀四十八歲了,她很纖弱,又很堅(jiān)強(qiáng)。彼此明白,此次的告別,將是最后的告別。
為何要走?為何不留?
婉儀知道,羅聘此次赴京,是為了“兩淮鹽引案”。羅聘上一次在京城時(shí),因老師金農(nóng)生前摯友錢(qián)載介紹,與人稱(chēng)“相國(guó)”的東閣大學(xué)士英廉攀上了些交情。這次他就是受大鹽商江春之托,去英廉的府邸當(dāng)說(shuō)客,爭(zhēng)取讓“兩淮鹽引案”盡早結(jié)案,讓鹽商們重新參與市場(chǎng)買(mǎi)賣(mài)。
羅聘臨走前,婉儀從枕頭下取出一頁(yè)詩(shī)稿交給他,這是她寫(xiě)的告別詩(shī):“病得清涼減四肢,膏肓終恐誤秦衣。自知死亦人間事,多是秋風(fēng)搖落時(shí)。握手哪堪此離別,雨昏輕浪掛帆遲。病中不用君相憶,夜夜孤燈枕燭倚。”詩(shī)稿上有大朵大朵的淚漬洇開(kāi)的痕跡。羅騁的心被揉碎了。這個(gè)被疾病耗得氣若游絲的女人啊,她曾經(jīng)像揚(yáng)州城里荷花池的荷花一樣鮮嫩、蓬勃、高潔。她的詩(shī)、書(shū)、畫(huà),均不在他之下,為數(shù)不多的作品一直受人追捧。當(dāng)年,她拒絕了無(wú)數(shù)達(dá)官顯貴,下嫁于家境貧寒的他。婚后,又為了成全他,她心甘情愿將自己從詩(shī)書(shū)畫(huà)的理想國(guó)中抽身,投身于柴米油鹽的生活現(xiàn)場(chǎng)。而他卻不能送她最后一程。他在心底一聲長(zhǎng)嘆:婉儀,我負(fù)了你!他握著妻子溫?zé)岬氖郑瑴I眼相望,無(wú)語(yǔ)凝噎。他亦以詩(shī)回贈(zèng):“出門(mén)落淚豈無(wú)情,君病空床我遠(yuǎn)征。默默兩心誰(shuí)會(huì)得,明知見(jiàn)面是他生。”婉儀輕輕扭過(guò)頭,閉上了眼睛,不再看他。“走吧,走吧,來(lái)生再見(jiàn)!”她的心里默念。繼而,涌起了一種無(wú)可所失者才有的力量,這力量充盈了她的全身。她想起多年前為姑母寫(xiě)的詩(shī),如今看來(lái),也是獻(xiàn)給自己的挽歌啊!生命的圖景一樣地荒涼,區(qū)別只在于細(xì)枝末節(jié)處吧。“景掩衡門(mén)剝啄稀,空齋臥病思依依。看成榮羅今何在,味盡酸咸昨已非。終古雙帆無(wú)息影,到頭一夢(mèng)有深機(jī)。青山不解悲霜簪,人自營(yíng)營(yíng)鳥(niǎo)自飛。”
羅聘離家的第十三日,農(nóng)歷五月十九日,方婉儀終于走到生命的盡頭。那一夜,庭院荷花池內(nèi)的荷花盡數(shù)凋零。花瓣像雨點(diǎn)一樣,隨著流水散去。仿佛在為她而哀悼,為這一位曾經(jīng)寫(xiě)下“淤泥不染青青水,我與荷花同日生”的荷花女王而哭泣。
病榻上的婉儀已陷入了昏迷。她的身體變得如紙片一樣輕薄,從床上升起,穿過(guò)一團(tuán)團(tuán)黑霧,輕輕墜落于一片黑暗叢林。地上落滿(mǎn)枯枝敗葉,還有很多低矮的枝椏半掩埋在潮濕的土壤里。她一只手持著丈夫畫(huà)的梅花卷,另一只手提著衣裙緩慢前行,她的繡花鞋濕了,每走一步都傳來(lái)一陣咔嚓咔嚓的聲響。
叢林深處有一座小木屋,正在黑夜里閃著微光。鳥(niǎo)兒在深夜寂靜的叢林里翔舞。她更加小心翼翼地踩下每一步,她在野花和枝葉間穿行,露珠兒落在她的頭發(fā)上、衣裙上,她全身濕漉漉的,她也不覺(jué)得涼。掉落的藤蔓絆住了她的腳,她動(dòng)不了。她掙扎,跺腳,輕輕一躍,她發(fā)現(xiàn)自己居然飛了起來(lái)。她在低空飛翔,素色的衣裙里灌滿(mǎn)了涼風(fēng),經(jīng)過(guò)嘩嘩作響的垂楊柳,她泥濘的雙腳輕輕落地,站在了小木屋前。
木門(mén)虛掩,她蹲下,用裙擺擦去繡花鞋上的泥土,然后,輕輕推門(mén)而入。她日夜思念的那個(gè)人,她魂?duì)繅?mèng)繞的那個(gè)人,從床上一躍而起,他的臉被微光點(diǎn)亮,身體其余的部分仍然沉浸在黑暗里。他怔怔地望著她。而她,也不能更進(jìn)一步了,只能倚在門(mén)框上望著他。他們沒(méi)能如《鬼趣圖》上那樣緊緊相擁。從門(mén)框到床邊,是他們無(wú)法逾越的障礙,是一個(gè)亙古的懲罰,是生與死的距離。他們體內(nèi)仿佛都吸入了太多悲傷,彼此相對(duì)無(wú)言。她一抬頭,看見(jiàn)了白無(wú)常正站在窗外等她。她幽幽嘆一口氣,千言萬(wàn)語(yǔ),只化作一句:“我,滇南去矣!”飄然而逝,只留下一縷淡淡的荷香。他在黑暗中揮舞著雙手,徒勞地想要留住她。
羅聘:倦鳥(niǎo)歸巢
奈保爾在小說(shuō)《米格爾大街》里描繪了一個(gè)叫沃滋沃斯的乞丐詩(shī)人向一個(gè)小孩子兜售自己的詩(shī)作,他問(wèn)小孩子,你喜歡自己的媽媽嗎?小孩子說(shuō),她不打我的時(shí)候,喜歡。他從后褲兜里掏出印有鉛字的紙片對(duì)那孩子說(shuō),這上面是一首描寫(xiě)母親的最偉大的詩(shī),我打算賤賣(mài)給你,只要四分錢(qián)。奈保爾知不知道兩百年前的中國(guó)有一個(gè)落魄的文人,名叫羅聘,曾干過(guò)和沃滋沃斯一樣的事。
那是1779年8月,羅聘在京城這是他第二次來(lái)京城。羅聘寄身于蛛網(wǎng)綿密的廟宇之中。這一天,廟里來(lái)了一個(gè)揚(yáng)州人,他告訴羅聘,他的妻子方婉儀已于農(nóng)歷五月十九日去世了。他想起五月在濟(jì)南途中做的那個(gè)夢(mèng):婉儀手持梅花卷,對(duì)他說(shuō),我滇南去也。羅聘恍然大悟,那是婉儀托夢(mèng)于他了。他的胸口涌上一陣劇痛霎時(shí),他感到天旋地轉(zhuǎn),床、窗框書(shū)桌、人,筆墨紙硯,都紛紛錯(cuò)位了仿佛置身于另一個(gè)維度里。他痛苦地閉上了眼睛。他在婉儀病入膏肓?xí)r離家,沒(méi)盡到為人夫的責(zé)任,心里又羞又愧。
他要回?fù)P州,現(xiàn)在就走。
趁著她墳前的泥土還潮濕著,趁著墓碑旁的荒草還未叢生,趁著她的魂魄還未離散,他要在她的墳前長(zhǎng)跪不起,向她懺悔,哭她這一生的委屈與付出,為了操持一個(gè)貧窮的家,耗盡才華,耗盡血淚。然而,怎么回去呢?此時(shí)的他,正處于囊中羞澀的狀態(tài),上一幅字畫(huà)賣(mài)的銀兩才被他花得精光,下一幅還沒(méi)有賣(mài)出去。從京城到揚(yáng)州,兩千多里的路程,先走陸路,后走水路,路上就要兩個(gè)月的時(shí)間,路費(fèi)從哪里來(lái)?
羅聘在寺廟里思來(lái)想去,決定去找他的好朋友、內(nèi)閣大學(xué)士翁方綱。到了翁方綱家中,羅聘將妻子怎么去世,怎么托夢(mèng)于他,以及他在什么情況下離開(kāi)妻子,全部告訴翁方綱。聽(tīng)得翁方綱熱淚盈眶。然而,他沒(méi)有拿出銀兩給羅聘作路費(fèi)。是羅聘沒(méi)有明說(shuō)?還是翁方綱裝糊涂?或者,翁方綱也跟羅聘一樣囊中羞澀?秀才人情紙半張,翁方綱走到書(shū)桌前,思索了一會(huì)兒,提筆,為方婉儀寫(xiě)了首挽詩(shī),寫(xiě)得情真意切:“萬(wàn)卷梅花,一卷白蓮,其畫(huà)也禪,其詩(shī)也仙;吾文冰雪兮,與此石俱傳……”羅聘看到挽詩(shī),仿佛在猝不及防的狀態(tài)下被擊中了一般,癡傻了,失語(yǔ)了,心魂被抽走了。隔了很久,才痛哭起來(lái)。翁方綱也和好朋友一起哭。
夜深了,電閃雷鳴,風(fēng)雨交加。羅聘躺在床上,輾轉(zhuǎn)反側(cè),腦中不斷浮現(xiàn)妻子幽怨憔悴的臉。一會(huì)兒責(zé)怪他,一會(huì)兒原諒他。他感覺(jué)自己被置于了烈火之上。閃電接踵而來(lái),猝然的光絲在黑暗中編織一張亮閃閃的網(wǎng),劈頭蓋臉朝他撒來(lái),他跌跌爬爬地離開(kāi)床榻。仿佛靈光一現(xiàn)般,他想,既然自己的畫(huà)暫時(shí)賣(mài)不出去,是不是可以把妻子的詩(shī)手抄一份,拿出去碰碰運(yùn)氣?興許,有人會(huì)同情他們夫妻情深,施舍點(diǎn)銀兩。唉,想他羅聘在揚(yáng)州書(shū)畫(huà)界,隨著鄭板橋、黃慎的去世,“揚(yáng)州八怪”就剩下他一人了。雖然受“兩淮鹽引案”的影響,揚(yáng)州經(jīng)濟(jì)遭遇重創(chuàng),但求他畫(huà)作的還是大有人在。而在京城,卻落得個(gè)要乞討路費(fèi)的境遇。
感慨歸感慨,他還是看到了希望,豁出去了,為了婉儀,做什么都值得。他顫顫巍巍地點(diǎn)燃一根蠟燭,上半身從黑暗中浮出。他提著蠟燭來(lái)到書(shū)桌邊,研墨,鋪紙,用娟秀小楷記錄下方婉儀的詩(shī)作。好不容易捱到天亮,羅聘來(lái)到一位曾經(jīng)跟他買(mǎi)過(guò)畫(huà)的權(quán)貴家附近,左徘徊,右思量,雖然在寺廟里已經(jīng)下定決心,但真正實(shí)施起來(lái),還是不容易。他既拉不下文人的臉皮,又苦于口袋空空,理智與情感不停交鋒,一會(huì)兒理智勝出,一會(huì)兒情感勝出,兩者幾乎打了平手。他幾百次要叩響人家大門(mén),又幾百次收回手。眼看就晌午了,人家的鍋灶已升起裊裊炊煙。不能再拖了,羅聘想。他拍拍長(zhǎng)袍上的灰塵,輕輕叩響門(mén)環(huán),感覺(jué)心臟就要蹦跶出來(lái)了。
他被拒絕了。主人說(shuō),我不買(mǎi)詩(shī),就關(guān)上了門(mén)。
羅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街上的,仿佛一個(gè)空心人。賣(mài)糖葫蘆的,賣(mài)豆腐腦的,賣(mài)古玩字畫(huà)的,表演雜耍的,叫喚聲在京城的街頭此起彼伏。他有一種錯(cuò)覺(jué),仿佛走在揚(yáng)州天寧寺附近,一直向前走,就能走到彌陀巷的家中,婉儀做好了午飯,等他回家。八月澄澈的光,落在他的長(zhǎng)袍上,他感到了無(wú)盡的深寒,絲絲縷縷滲入他的毛孔,他的骨血,他的心。
回到寺廟中,羅聘展開(kāi)自己的《鬼趣圖》,這是一幅以濕紙畫(huà)法創(chuàng)作的畫(huà)。畫(huà)面冷峻飄渺,陰森寫(xiě)意。八幀小畫(huà),每一幀畫(huà)上的小鬼看上去都是極度荒誕,怪異,拿腔拿調(diào),卻又無(wú)魂無(wú)神。濃墨淡彩間,緊湊又疏離,極具張力。每一幀畫(huà)都似乎有所指,又似乎都無(wú)所指。荒,慌,惶。羅聘看著《鬼趣圖》,心頭涌上了深深的無(wú)力感。他想控訴,想?yún)群埃肱叵K蝗^打在寺廟的破墻上,血,滲了出來(lái)。他仰頭長(zhǎng)嘯一聲。世態(tài)炎涼,他想起好友蔣士銓之語(yǔ):“人生都作圖畫(huà)看。”人與鬼,哪個(gè)有情,哪個(gè)無(wú)義?
羅聘枯坐著,墻角傳來(lái)老鼠的啃噬聲,屋梁時(shí)不時(shí)發(fā)出木頭開(kāi)裂的聲音,灰塵在光線(xiàn)里簌簌落下。他又想起婉儀,想起她三十歲生辰時(shí)的光彩動(dòng)人;也想起他離家時(shí),夫妻以詩(shī)贈(zèng)別的凄慘場(chǎng)景。羅聘如鯁在喉。長(zhǎng)歌當(dāng)哭,他鋪紙,研墨,把人生之無(wú)奈、之悲憤,全部?jī)A注于筆端,在紙上寫(xiě)下:乍欣良朋至,旋使我心悲。道我室中人,永與君別離。因思出門(mén)日,遲遲復(fù)遲遲。執(zhí)手話(huà)床笫,泣涕交相垂。枕畔見(jiàn)墨痕,集句成別詩(shī)。達(dá)生寓詩(shī)意,死以秋為期……婉儀,既然我無(wú)法回到你的身邊,無(wú)法用衣袖擦亮你的墓碑,就讓我以這首詩(shī)哭你送你吧!二十七年的恩愛(ài)夫妻就此別過(guò),婉儀,你在世的孤獨(dú)那么深,那么重,都是我的錯(cuò)。等我!終有一天我會(huì)躺在你的身邊,日日夜夜陪你……
羅聘于1779年冬天回到揚(yáng)州此時(shí),“兩淮鹽引案”的余波已漸漸平息,備受重創(chuàng)的揚(yáng)州經(jīng)濟(jì)重新煥發(fā)生機(jī)。揚(yáng)州畫(huà)壇恢復(fù)了往日的繁華羅聘的聲望達(dá)到巔峰,成為揚(yáng)州畫(huà)壇第一人,“揚(yáng)州八怪”的總結(jié)性人物羅聘受老師金農(nóng)的影響,晚年也不畫(huà)鬼,改畫(huà)佛。集羅聘一生藝術(shù)之精華的《鬼趣圖》早已名揚(yáng)天下了。先后得到沈大成、袁枚、紀(jì)昀、蔣士銓翁方綱、張問(wèn)陶等一百多位學(xué)者的題跋。唯獨(dú)他自己,在《鬼趣圖》上未題一字,未發(fā)一聲。
袁枚一個(gè)人就題了三首詩(shī)。其中一首寫(xiě)道:“我纂鬼怪書(shū),號(hào)稱(chēng)《子不語(yǔ)》。見(jiàn)君畫(huà)鬼圖,方知鬼如許得此趣者誰(shuí),其惟吾與汝。”因?yàn)椤豆砣D》,以及曾經(jīng)與金農(nóng)交好的舊交羅聘被袁枚引為知己。羅聘寫(xiě)過(guò)一封《乞米帖》給袁枚。說(shuō),家中無(wú)米了趕快送米來(lái),只要米,不要錢(qián),送米是雪中送炭,送錢(qián)是鄙夷貧賤。袁枚趕緊派人去送米油給羅聘。羅聘開(kāi)心地在紙上寫(xiě)道:“炊煙看乍起,高情獨(dú)感君。”羅聘來(lái)到袁枚的隨園,打算給袁枚畫(huà)一幅畫(huà)像,袁枚的家人坐在一旁觀看,這個(gè)說(shuō)胡須長(zhǎng)些,那個(gè)說(shuō)眉眼再開(kāi)闊些。羅聘不語(yǔ),畫(huà)完就走,飯也不吃了。袁枚的家人看過(guò)畫(huà)像后大失所望,覺(jué)得羅聘徒有其名,根本不像嘛。袁枚知道,家人追求的是形似,而羅騁追求的是神似。畫(huà)像初看是不太像,但是越看越像。袁枚說(shuō):“世上有兩個(gè)我,一個(gè)是家人眼中的我,一個(gè)是兩峰眼中的我。”
在畫(huà)鬼之前,羅聘畫(huà)梅、畫(huà)蘭、畫(huà)竹,畫(huà)鬼之后,畫(huà)佛。他畫(huà)什么都能畫(huà)出千種風(fēng)流,畫(huà)出與別人不一樣的風(fēng)姿。畫(huà)梅,繁處縱橫交錯(cuò),簡(jiǎn)時(shí)疏影橫斜,蘊(yùn)含蓬勃的生命力。畫(huà)鬼,打破規(guī)制,使不登大雅之堂的鬼,第一次呈現(xiàn)于世。羅聘追求神似,追求寫(xiě)意,在荒誕中隱含某種殘酷、離散之美,使得這荒誕更加離群索居。維也納的分離派大師席勒在筆墨的表現(xiàn)力上與羅聘有些類(lèi)似。畫(huà)佛,羅聘深得金農(nóng)筆墨與思想之精髓。羅聘筆下的佛相,袈裟上的皺褶,長(zhǎng)長(zhǎng)的外眼角向斜上方挑去,或講經(jīng)說(shuō)法,或拈花一笑,或冥思,或念經(jīng),皆有幽妙、不可言說(shuō)之趣。
金農(nóng)對(duì)羅聘的影響延續(xù)一生。老師離世后,他操辦了老師的身后事。收集,整理出版老師的作品。老師和妻子,是他這一生中最重要的兩個(gè)人。如今,這兩個(gè)人都離他而去了。但他并不孤獨(dú)。他明白生命的底色是空無(wú)。相遇與相伴只是歲月大風(fēng)中的幾粒微光而已。總有一天,他會(huì)乘風(fēng)去見(jiàn)他們。他一直記得老師臨終前對(duì)他的寄語(yǔ):“聘年正富,異日舟屐遠(yuǎn)游,遇佳山水,見(jiàn)非常人。”
1789年,羅聘第三次遠(yuǎn)赴京城。這次他帶著小兒子一起到京城賣(mài)畫(huà),羅聘一家皆為畫(huà)師。此時(shí),羅聘成為書(shū)畫(huà)界公認(rèn)的大師。他在宣武門(mén)外琉璃廠觀音禪寺一安頓下來(lái),求其畫(huà)作之人就紛至沓來(lái)。而京城那些一流的文人雅士,如:翁方綱、張問(wèn)陶、法式善、吳錫麒、王文治……都是羅聘的好朋友,他們經(jīng)常在一起雅集,飲酒、賦詩(shī)兼潑墨。從1789年到1796年,是羅聘一生中的高光歲月,他的性情得到了徹底的釋放。活著就是須盡歡,是醉眼看人間,是揮毫潑墨,是在暗夜里用粗糙的手掌細(xì)細(xì)摩挲那金石古玩之美。他要痛飲生命最后的瓊漿。
個(gè)人是時(shí)代的鏡像。當(dāng)羅聘的人生由極盛走向衰敗時(shí),時(shí)代的交接棒也將完成歷史的交接。1796年的正月初四,已經(jīng)八十六歲高齡的太上皇乾隆,要舉辦“千叟宴”。這也是一次政治試水,太上皇乾隆依然掌握著朝中大權(quán)。所邀之人必須符合兩個(gè)條件:一,公卿貴族六十歲以上者;二,民、兵七十歲以上者。羅聘不是公卿貴族,年僅六十四,不符被邀條件,卻被邀請(qǐng)了。一個(gè)揚(yáng)州的老畫(huà)師,以外來(lái)者身份獨(dú)領(lǐng)京城畫(huà)壇之風(fēng)騷,出入于公卿貴族之府,并被賜予了如意壽杖。皇子、皇孫、皇曾孫、皇玄孫,紛紛向他行酒。他曾在一幅梅花圖的題記上寫(xiě)下這一盛況:予今年春正月初四,躬逢千壽宴,蒙恩賞杖物,恨未畫(huà)此橫斜疏影之態(tài),進(jìn)供御覽也。
這是羅聘一生中最后的一章交響曲。
也是乾隆的謝幕之作。
從1789年到1798年,羅騁居京城已經(jīng)九年多。他漸漸感到這樣每日折花載酒,半是清醒半是醉的生活,自己有些力不從心了。老畫(huà)師萌生了返鄉(xiāng)之意。而且,時(shí)間長(zhǎng)了,人們對(duì)他的新鮮感也過(guò)去了,他的畫(huà)滯銷(xiāo)了。京城友人勸他:“異地之賞音已少,故山之招隱方殷。鳥(niǎo)倦須還,鱸香可慕,能尋夙約,來(lái)話(huà)舊游……”
一時(shí)間,羅聘要離開(kāi)京城的消息傳開(kāi)了。
第一波上門(mén)的是畫(huà)商,羅聘支了人家銀兩,還欠著幾幅畫(huà)。
第二波上門(mén)的是酒館老板,羅聘欠了人家酒菜錢(qián),把冬衣全部典當(dāng)了還債。
第三波上門(mén)的是金石古玩商,羅聘把鞋襪、被褥,筆墨紙硯,能典當(dāng)?shù)娜康洚?dāng)了,還是還不清債務(wù)。
……
從前,踏破門(mén)檻的,是求畫(huà)的雅士,現(xiàn)在,踏破門(mén)檻的,都是催債之人。
人生是一個(gè)輪回。跟二十年前一樣,羅聘再次陷入沒(méi)有返鄉(xiāng)路費(fèi)的窘境。不一樣的是,二十年前他還有出門(mén)想辦法借錢(qián)或乞討的勇氣,如今,他反倒看開(kāi)了。該怎樣就怎樣吧,命運(yùn)自有安排。在京城的這些年,尤其前幾年,他賺了很多錢(qián),也花了很多錢(qián)。他不會(huì)算計(jì)錢(qián)財(cái)過(guò)活。羅聘想起自己的老師金農(nóng),生前也是千金散盡,死后竟無(wú)錢(qián)下葬。他苦笑,看來(lái),自己不但師承了老師藝術(shù)上的造詣,也師承了老師的人生境遇。
說(shuō)來(lái)也很奇怪,從方婉儀死后羅家一門(mén)似乎在理財(cái)方面都很欠缺羅騁與小兒子身陷京城,大兒子在揚(yáng)州得到消息了,也沒(méi)有辦法接父親和弟弟回家。因?yàn)椤矝](méi)錢(qián)。直到這件事被羅聘做鹽運(yùn)使的朋友曾賓谷知道了,才資助羅騁的大兒子趕赴京城,把父親和弟弟接回?fù)P州家中。
偉大的旅程即將走到終點(diǎn)。
18世紀(jì)最后一個(gè)夏天(1799年)一日午后,病了有些時(shí)日的羅聘掙扎著從床上爬起來(lái)。他拄著拐杖站在朱草詩(shī)林的庭院里,陽(yáng)光像針一樣穿刺著他的眼睛。他用手擋住額頭,半瞇著眼,蹣跚而行,每一步都回蕩起歲月的殘骸之音。他的衣服太緊太熱了汗珠從他的毛孔里細(xì)細(xì)地沁出,他解開(kāi)衣領(lǐng),更加小心翼翼地踏下每一步他走到庭院里那棵近百年的老樹(shù)前停了下來(lái)。他凝視著細(xì)碎的枝葉在半空中形成的翠綠華蓋。想著自己的一生以及老師金農(nóng),愛(ài)妻婉儀的一生都包含在它的年輪里。斯人已離去,而它卻依然有著傾瀉而下的、飽滿(mǎn)的生命力。快見(jiàn)面了。他的眼眶濕潤(rùn)了,蒼老的喉管里發(fā)出了幽微的一聲輕嘆。
一個(gè)無(wú)盡的下午。
一生只在轉(zhuǎn)瞬之間。朋友們離去不再回來(lái)。羅聘平靜地站在生命的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