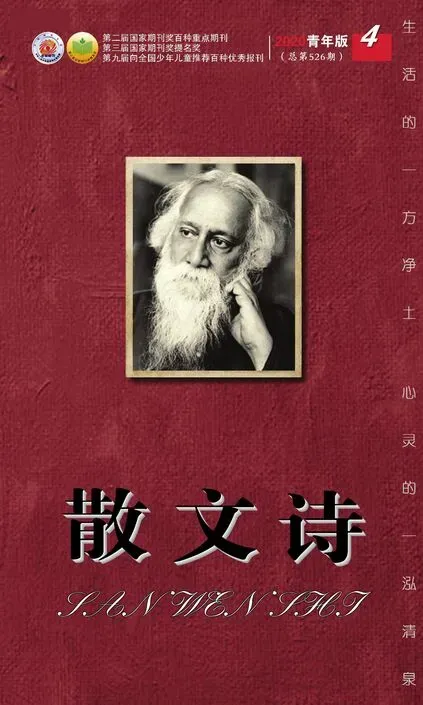創(chuàng)作手記:在詞語(yǔ)中認(rèn)識(shí)自己
2020-11-22 09:43:52藍(lán)格子
散文詩(shī) 2020年8期
當(dāng)我把不同時(shí)間寫(xiě)下的這幾個(gè)多以事物之名命名的作品像石榴籽一樣羅列、整理在一起時(shí),倒真有些將詞語(yǔ)錯(cuò)置的意思了。寫(xiě)這組作品的時(shí)候也并沒(méi)有刻意為之成為一組或是“某種風(fēng)格的表述”,但現(xiàn)在回想起來(lái),這一個(gè)個(gè)被我重新處置的“詞語(yǔ)”卻是有一些共通特質(zhì)的。無(wú)論是《蘆葦》《樹(shù)》《石榴》這樣的自然之物,還是《水晶球》《雨刮器》這樣的社會(huì)之物,我都將它們放在了一個(gè)和人對(duì)視、對(duì)談的位置,我想,每一種事物呈現(xiàn)給我們不同的面貌,也有自己的“性情”,當(dāng)我們把自己和事物互換位置,甚至互換身份、互動(dòng)的時(shí)候,才可能理解事物的“語(yǔ)言”。我所理解的寫(xiě)作,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人與自我、周邊事物、自然、世界之間的關(guān)系問(wèn)題,而寫(xiě)作本身就是我們看待自己和世界,去處理這些關(guān)系的過(guò)程。我知道,這和閱讀有一定相似之處,即使我們努力地“設(shè)身處地”,獲得了心靈的共振,也無(wú)法完全“感同身受”,但或許這個(gè)不斷認(rèn)識(shí)自我、認(rèn)識(shí)世界,將詞語(yǔ)錯(cuò)置的過(guò)程以及過(guò)程中的豐富性和可能性正是寫(xiě)作的迷人之處所在,同樣,也是閱讀的樂(lè)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