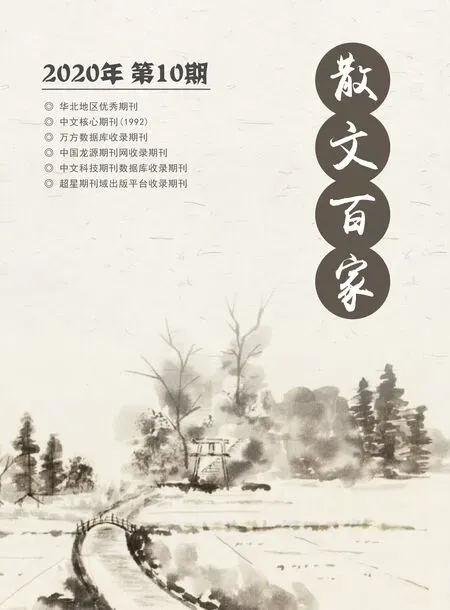睡蓮中的哲思
王楚雨
華南師范大學(xué)
睡蓮,浮葉型水生草本植物。在它誕生之時(shí),就仿佛接受了眾神的祝福,成為純凈又妖艷的化身。純凈,代表了女神般的圣潔,妖艷,又折合了妖精般的魅力。
老家曾經(jīng)有一缸池水,里面種了兩株睡蓮,小時(shí)候我喜歡趴在缸邊,看著它們圓潤的葉子在水中靜謐地漂動(dòng)。在清涼的水氣中,柔嫩的花瓣翕動(dòng),向幼年的我傾訴著玄之又玄的東西,最后成為童年回憶中珍貴的剪影。所以去日本旅行的第一天,我最想看到的莫過于地中美術(shù)館里珍貴的五幅《睡蓮》,當(dāng)然,他們因偉大的作者莫奈而出名。
在眾人的印象里,莫奈比起梵高、比起畢加索,生平也許過于貧乏無味,與刻板印象里藝術(shù)家叛逆、出格、熱烈敏感而追求極致的形象有些出入。
說起梵高,人們會(huì)想起那個(gè)熱情又孤獨(dú)的孩子。他的梨花、他的星空、他的黃房子、他的向日葵、他的烏鴉飛過的麥田像他本人的人生一樣寂寥而傳奇。那痛快的畫法,用靈魂書寫的酣暢淋漓的粗獷,洗刷眼睛般漂亮的顏色,不舒服,卻震撼。
說起畢加索,又帶著神秘意味的抽象,或是用強(qiáng)烈而流動(dòng)的線條帶給人們虛擬世界的感情,或是呈現(xiàn)層層分解的幾何化平面表象,隨心所欲的構(gòu)圖和毫無邏輯的筆法,同他本人的桃色舊聞一樣奇怪又捉摸不清。對(duì)不同藝術(shù)風(fēng)格不斷求索和創(chuàng)新的熱忱,貫穿了畢加索的一生。
我不了解莫奈,滿懷欣喜地期待與他的作品見面。可了解了他的一生之后,才終于理解了為什么這位偉大的畫家終其一生都在記錄光、描繪光、追隨光。在建筑設(shè)計(jì)師安藤忠雄一手打造、與自然融為一體、所謂“看不見”的建筑里,他的五幅《睡蓮》混著海浪拍打礁石的聲音,就這樣安靜地等候著造訪的人。一位畫家和一位建筑設(shè)計(jì)師,他們仿佛心靈投契、一拍即合,一個(gè)追求光的靈動(dòng)多變,另一個(gè)追求光的無限。光,在藝術(shù)里成為他們忠實(shí)的伴侶,甚至矢志不渝的信仰。
在穿著白大褂的展員帶著日本味兒的英語的指導(dǎo)下,我們脫去鞋子,走進(jìn)了藏著五幅《睡蓮》的展廳。安藤忠雄是一個(gè)利用光線的天才,用柔和的乳白色燈光營造出神圣的氣氛。我赤腳站在白色石子鋪成的地板上,好像踩在北極的冰山上,被早上的太陽溫暖著。莫奈的五幅《睡蓮》則好像真的睡美人一般,帶著朦朧的筆觸和光影的變幻,湊近了甚至能聽到她們均勻而甜美的呼吸。
我在展廳里緩慢移動(dòng)著,眼睛被畫兒給吸走了,在明明暗暗的色彩中,仿佛和一個(gè)孤獨(dú)的老人在睡蓮池邊一待就是一天,四周被精心打造的水池包裹,打開了深藏于心的“第三只眼睛”。
早上的睡蓮是清新可人,天真爛漫的,到了傍晚,才逐漸變得莊重起來,直到晚上,在月光的映襯下,清冷的氣質(zhì)一覽無余,又因?yàn)楹冢@得神秘而不可靠近。鋪天蓋地的、可愛的小小蓮葉,像苔蘚一樣長滿了池塘,讓人被突如其來的靈巧和細(xì)膩擊中,好像能感受到生命中的所有浪漫和美好,在一天之內(nèi)因?yàn)樘栁恢玫淖兓鴵Q了模樣。灰暗的、濃烈的、朦朧的、無法訴諸語言的全部情感,都被莫奈留下來,以睡蓮。
我從未想過印象派的溫暖柔和可以如此堅(jiān)定有力,因?yàn)檫^多的數(shù)量容易顯得畫作只是機(jī)械的重復(fù),但《睡蓮》的每一筆卻又飽含豐富的靈魂。
地中美術(shù)館的《睡蓮》是莫奈晚年的作品,從屬于一個(gè)系列,它并不僅僅只有地中美術(shù)館珍藏的五幅,可以說這五幅連個(gè)零頭都算不上,因?yàn)槟我还伯嬃硕偎氖@接近二百四十二幅畫耗費(fèi)了他三十年的光陰,包括修建園子和種植照顧他的睡蓮們,白內(nèi)障也沒能摧毀他繼續(xù)畫下去的信念和對(duì)哲學(xué)中無限性的追索。想讓一個(gè)瞬間留下來的心愿不斷膨脹,于是藝術(shù)成為了莫奈唯一通往生命永恒的道路。
可惜,追求光的人,也往往不能擺脫黑色的影子。光與影,光明與黑暗,好像永遠(yuǎn)纏繞在一起。也許是命運(yùn)喜歡與天才開玩笑,視音樂為生命的貝多芬失去了聲音,視色彩為生命的莫奈失去了色彩。在生命的漫長征途中,偉大的藝術(shù)家們一直在與終極的謎底作斗爭。
平常的二百四十二幅畫對(duì)一個(gè)畫技高超的畫家來說也許也并不算什么,難得的是二百四十二幅的每一幅都不盡相同,而靈動(dòng)非常。一個(gè)上了年紀(jì)的人對(duì)著睡蓮畫了三十年還饒有興致,失明了也割舍不下,怕是在夢(mèng)里都想著睡蓮,和睡蓮談著戀愛。跳躍的光斑和瀟灑自如的筆觸下,你能感覺到色彩只是媒介,或者通往更高形式的一種手段。
走出展廳的一瞬間,人們都瞇著眼睛,感到一陣恍惚。
美術(shù)館的出口是紀(jì)念品商店,里面有各種藝術(shù)作品再創(chuàng)作生產(chǎn)的周邊。印著睡蓮的明信片和眼鏡布、小徽章都很漂亮,我和友人沉浸在睡蓮的美麗中,最后一張明信片也沒帶走,而是買下了一個(gè)莫奈的石膏小頭像,這個(gè)石膏小人微微噘著嘴,好像不太高興的樣子。我想起中學(xué)美術(shù)課本上莫奈的畫像,那一張他年輕些,卻也是皺著眉,露出無辜又苦惱的眼神。
他仿佛不善于向世人親自表露感情,所以他的溫柔格外不易察覺。詩人雪萊曾為他寫了一首詩,“他清澈而優(yōu)雅的眼神,在眺望蔚藍(lán)的天空時(shí),會(huì)把它當(dāng)成是和我們生命同等的色彩去觀察。”
地中美術(shù)館外的小徑,在粗壯樹木的隱秘掩映下,突然撞見一小片愉快生長的睡蓮,在樹葉縫隙透過的陽光下呼吸,似乎是從館里的畫中跑出來的精靈,像是在挽留,又像是告別。
曾經(jīng)有一個(gè)男人就這樣深情地望著它們,畫下它們的樣子,親手為世人制造一場(chǎng)溫柔異常的美夢(mèng)。我想,在所有和花有關(guān)的夢(mèng)里,這一場(chǎng)睡蓮之夢(mèng)是我最不想醒來的。
- 散文百家的其它文章
- 對(duì)外漢語網(wǎng)絡(luò)教學(xué)模式探索與分析
- 運(yùn)用分析工具改進(jìn)學(xué)科服務(wù),助力高校雙一流科研發(fā)展
——近年來川渝圖情學(xué)術(shù)年會(huì)論文案例述評(píng)及反思 - 小學(xué)低段特殊課文如何做好識(shí)字教學(xué)
——以統(tǒng)編版一下《咕咚》為例 - 認(rèn)知語言學(xué)對(duì)翻譯的影響
——一項(xiàng)基于文獻(xiàn)1997-2019 統(tǒng)計(jì)的考察 - 劉禹錫《秋詞》詩畫賞析
- 分層教學(xué)法在高中體育教學(xué)中的應(yīng)用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