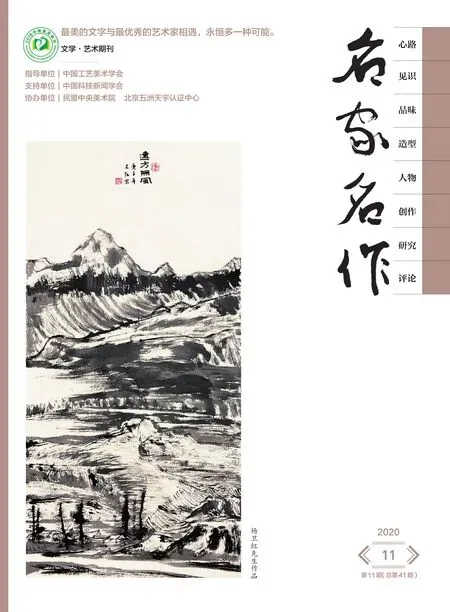林懷民《行草》中“極簡主義”的表達方式
陳心怡
《行草》是由云門舞集創始人林懷民先生編創于2001 年的現代舞劇,作品以書法為靈感,書法追求筆墨的簡練、心境的平和體現出的簡而不繁、靜而不燥,與舞蹈動作極簡主義的設計理念不謀而合,開啟新的審美道路。在極簡主義下找到了與書法、太極等經典的中國文化傳統元素融合的創作手法,運用書法氣韻帶動極簡的筆畫走勢,舞者用純粹的身體表達出極簡主義下強烈的內在。舞蹈動作的回歸原點結合舞美與音樂的“極簡主義”設計,沒有多余的雜亂,給人帶來純粹、樸素的感覺。
一、極簡主義與后現代舞蹈
極簡主義是20 世紀50 年代出現在藝術領域的一種表現形式,即去符號化,理性嚴密,沒有繁復的元素,不追求形式的復雜,不通過豐富外表來填滿舞臺以及舞者與觀眾的身心。用極度的簡約讓觀眾體驗到更多的內在感受,通過不斷做減法,摒棄各種裝飾動機保留下事物的本質,從而體現一種純凈簡約之美。極簡主義通過對藝術領域的內容、形式、手段等進行最大程度的簡化[1],其“簡”并不是對“量”的削減,而是對復雜化進行升華,達到“少即是多”的效果,并能表達出最豐富的思想與主題。所謂“極簡主義”和“簡單”是不同的,藝術的極簡主義追求的是一種純粹的、無雜質的藝術表現效果和視覺沖擊,而不是幾個動作和幾段音樂那么簡單。
“后現代舞蹈”和“現代舞蹈”明顯分界是在20世紀60 年代,在19 世紀末現代舞停滯不前導致新舞蹈家的發展空間范圍不斷縮小,優秀的舞蹈家也不斷減少,從而出現了后現代舞蹈時期。后現代舞蹈相對現代舞既有明顯的連續性和繼承性,又有巨大的斷裂性和差異性。所謂后現代舞或新先鋒派舞,指的就是自20 世紀60 年代那代人開始的新興的舞蹈流派。由于“賈德遜教堂劇院”的產生,引領了大量的小劇場的出現,為后現代舞蹈家提供了大量的舞蹈實踐。中國的后現代舞蹈主要源于德國舞蹈劇場,不注重技術有多完美和肢體是怎么舞動的,注重的是我們為何舞蹈,給舞蹈注入了另一種人文氣息,開始呈現大眾化的趨勢。后現代舞蹈的創作手法、審美理想、舞蹈語言及訓練體系都比現代舞更靈活和自由,追求再度返回舞蹈表現主義的傳統,常常運用即興創作和動作實驗等方法,以追求常演常新的演出效果,以打破往日的神秘感,主張“一切動作都是舞蹈”,從生活到各個藝術領域等進行探索,運用開闊的視野和明晰的思路,不斷加大生活實驗的舞蹈“量”,展現不同的多極化格局。“哲學上篤信中國道家‘無為’學說,以及信奉‘大音希聲,大禮必簡’極簡主義學說”[2],與當時的極簡主義的藝術表現形式相聯系,因而在后現代舞蹈中采用極簡主義,言簡意賅地傳達藝術思想,將舞蹈回歸最初始的狀態,達到世間事物的本質,所有的事物精簡到最簡單,創造出一種純粹的舞蹈魅力。
二、《行草》舞蹈語言中極簡主義的表達
(一)“極簡”下純粹的外在表達
該作品不管是表演還是舞者的練習都是從“永”字開始的,從“永”字的筆畫中尋找舞蹈語言的基本要素,“《行草》對中國舞蹈語言體系的貢獻在于它回到了‘根’‘本’”[3],簡化了各種裝飾動機,保留下最本質的動作。那么如何將動作回到極簡呢?這要從訓練說起,除了中國古典舞和西方現代舞技術最基本訓練之外,太極、氣功、打坐、書法是必不可少的,目的是以靜心的方式讓舞者回歸到大自然中感受純粹的事物,體驗日常生活狀態,追求內在寧靜并喚醒本心,以多元化的角度去感受舞蹈。這些訓練使舞者的身體以開放的姿態將太極的動中求靜和書法的練心則靜等辯證思想灌入他們的體內。從呼吸開始,“氣沉丹田”“一動俱動”讓舞者認清自己的重心。舞者以丹田部位作為動作根源模擬書法的動勢,隨著丹田吸氣延伸至指尖帶動著身體達到最大限度的延展后,再伴隨著吐氣快速松懈,放松下來的身體并不是整個垮倒,而是在快接近地面時戛然而止,產生穩扎重實的身體。
從視覺角度來說,極簡主義的設計意味著思想被帶回了本原,沒有繁復的形式追求,讓觀眾的視線更加專注于演員的表演。作品中舞者的身體與大自然親密合作,從放松的身體中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順應自然”被編導用得恰到好處。創作此作品時編導提出了一個關鍵的觀念:“我要的是Vibration 不是Choreography。”[4]林懷民認為具體的動作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感受自己的內心,重新發現身體并回到動作本身,在身體的各種表達去中尋找舞蹈自身的存在,并從律動中發覺身體動作的原發意義,將僵硬的身體變得流暢和自然。
(二)“極簡”下強烈的內在表達
達·芬奇說過:“簡單即終極的復雜。”在最簡單中去反射最復雜。《行草》在表面的簡約下表達出的是虔誠的思想,充滿著自然的力量,展現人們思想的最高境界。極簡主義的舞蹈動作其實不是單純的簡約,它簡而不薄,通常給觀眾無限的想象空間,簡而繁盛。而作品中最為顯著的動作特色是運用書法氣韻帶動極簡的筆畫走勢,舞者如同毛筆般將充滿韻律的線條呈現在觀眾面前,快慢勻速的舞蹈語言要求動作要輕松柔和、身心放松、心中毫無雜念,達到連綿不斷的動態走勢,用簡單的音符傳遞人與人之間的美好,讓觀眾體驗到獨特而生動的線條藝術和自然流露出古典文化的意蘊。極簡主義下的舞蹈《行草》,更像是一場行為藝術。舞者在演出的開篇、結尾與高潮,沒有用復雜的情感埋伏去表現,從而調動控制著觀眾的情感體驗,而是盡可能地剩下身體的純粹演繹,脫離身體感官,走向形而上學之追問。
《行草》主題始終圍繞著中國古代人與自然和諧的哲學理念,體現出靜謐與和諧。整部作品用極簡來表達舞與自然、生命與萬物。通篇用沉靜的意識作為內在節奏,連綴著每個各不相同的筆畫走勢,整部作品看不到程式化的動作設計,每個連接動作在極簡主義的形式下表達強烈的內心,通過書法來釋放身體和靈魂,讓自己沉淀,《行草》作品在舞臺上所營造的安靜的氛圍使觀眾在觀看過程中心靈得以釋放,感受到極簡主義強烈的內在表達。
三、《行草》舞美與音樂中極簡主義的表達
(一)極簡的舞美設計
舞美、燈光、服飾構成的舞臺視覺效果不多不少地呈現出極簡主義風格。《行草》的舞臺猶如一張白紙,女舞者身著純黑衣服和褲子,男舞者上身裸露下身同樣著純黑褲子,不加一點點修飾,給人干凈的感覺,整體猶如白色宣紙上起舞的漢字,通過白色幕布和極為簡約的黑色服裝來展現書法藝術,是對書法簡約元素的充分運用。“黑色”的舞者猶如毛筆的墨汁在“白色”的宣紙上隨著筆韻進行揮灑,不斷變化舞姿自由地流動,給觀眾不停切換書法筆畫的視覺。背景字帖每一頁的切換和書法筆畫的每一筆跨越了間隙連為一體,“白”追著“黑”,“黑”追著“白”。在極度昏暗和安靜的劇場里,在黑白布景、頂多淡黃、近乎白色的燈光構成的靜態空間里,裹著黑色的舞者,不斷發出強烈的直接的帶有個人特征包含身體的信號,帶動觀眾的身體與內心不自主地產生感應。
《行草》極簡的舞臺布景和素雅的服裝以及純凈的意象都具有極強的極簡主義色彩。沒有繁復的元素,不追求形式的復雜,不通過豐富外表來填滿舞臺以及舞者與觀眾的身心,相反,簡約與干凈讓觀眾凈化心靈。追崇極簡之美,視覺上主張一切從簡,而內在的實為精髓,舞臺的干凈利落使人一目了然,黑、白更加突出了舞者的肢體語言,為他們的表演最大可能地提供了空間。
(二)“大音希聲”的舞蹈音樂
在創作《行草》之前,云門舞集的藝術總監林懷民給作曲家翟小松講述了一段奇特的心理體驗過程:“有一次,在印度的一棵菩提樹下打坐禪定,一片葉子從面前落下,當他打完坐時此葉已然枯萎,頓感時光寂兮寥兮,不知今夕何夕。”聽聞此言,瞿小松當下便說這和他的創作經驗一下子就連通了。兩人一拍即合,于是,在他本人看來是“氣息最悠長、最松”、在他人看來幾分鐘里只有一個音符的《行草》誕生了。在舞劇音樂中,翟小松使用了獨奏大提琴與三位打擊樂手,作品分為九段,創作這九段的具體要求中最多的就是“極慢、極簡、極靜,有極多極的長的靜默,按時宇宙的呼吸”。《行草》中的音樂不僅有呼吸聲還有大量的留白,如在“吐納”這個段落中用很少的音符來擴大音樂的空間,呼吸的韻律填補了音樂的空白,以“空”表“無”把復雜的信息簡單化,透露出一種生命靈氣的藝術境界。
作品中的音樂看似簡單卻蘊含著大能量。翟小松從他的音樂中表現出怡然自得的寧靜心境,在中國文化傳統中追憶古人與大自然之間的聯系,具有回歸原點的色彩。
四、結語
上文便是筆者對林懷民《行草》中“極簡主義”的表達方式作出的簡單論述,舞蹈本體追求純粹的舞蹈和身體的回歸,舞美追求黑白色彩的極簡主義視覺,舞蹈音樂追求“大音希聲”寂靜的極簡主義聽覺,視覺上簡單又復雜。對現代作品而言我們應竭力挖掘其創造的潛力,理解其創造的動機。《行草》從中國書法中悟出的創作理念結合“極簡主義”最后落實在現代舞上,體現了當代藝術的多元化,符合當今世界的開放性和多元性,它是在傳統藝術中汲取養分,開出的新的形式的變種花卉,探索出獨樹一幟的肢體語言表達方式,體現出編導跨界融合的創新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