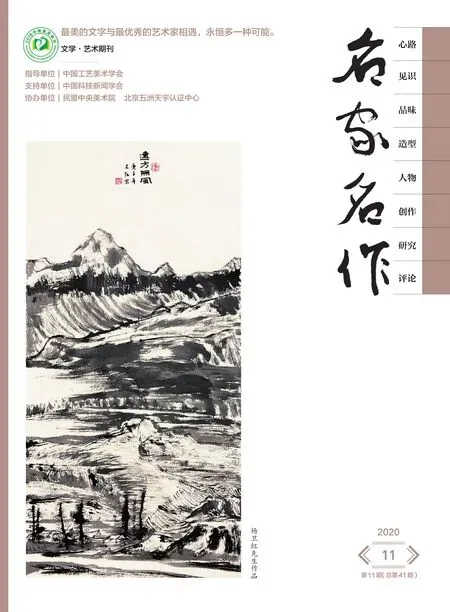《漫長的告別》中的概念隱喻
曹 霞
一、引言
作為唯一一位載入世界文學經典史冊的偵探小說大師,雷蒙德·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 1888——1959)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不可撼動。他不僅開創了硬派偵探小說的強悍傳統,而且在小說中將社會性和文學性有機結合,使之成為一種藝術形式。《漫長的告別》一經出版就斬獲了埃德加·愛倫·坡獎,與《了不起的蓋茨比》等齊名。在作品中,錢德勒使用了大量的隱喻,向世人展示20 世紀40 年代的洛杉磯風貌,以及城市中人與人之間的靈魂交流。歸納、分析這些隱喻及其功能,有利于深入認識錢德勒的語言風格和敘事特點,進而了解其作品的文學性和美學價值。
二、概念隱喻概述
隱喻又稱“暗喻”,是文學創作中常用的修辭手法。兩千多年前,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就從語言層面展開了隱喻研究。根據索斯凱斯(Soskice)的定義,“隱喻是一種修辭,通過這種修辭,我們能夠使人通過一種事物聯想起另外一種事物”[1]。因此,隱喻可以理解為通過對比和類比機制,用一種事物去理解和體驗另一種事物,或者用熟悉的事物幫助自己理解相對陌生、復雜的事物。
隨著認知科學的發展,現代隱喻學已經從語言現象層面走向了思維層面。其代表人物萊考夫(Lakoff)和約翰遜(Johnson)指出,“我們日常生活中處處都充滿了隱喻,不但滲透在語言里,也滲透在思維和活動中,我們借以思維和行動的普通概念系統在本質上是隱喻的”[2]。如例句“As I walked through the wilderness of this world”,就是概念隱喻“Life is a journey”的創造性使用。它將已知的具體概念映射到未知的抽象概念領域,獲得多重感知體驗,形成對未知事物的具象認知和表達,來豐富已有的概念和思想,把握事物之間的范疇和關系。
文學作品中的概念隱喻可分為本體隱喻、結構隱喻和空間隱喻。這些隱喻通過映射功能,刻畫鮮明的人物形象,揭示作品的主題思想,使讀者讀懂作者的寫作意圖,更準確地把握作品內涵,從而提高文學欣賞能力和認知水平。
三、《漫長的告別》中的概念隱喻
(一)本體隱喻
在人類的認知經驗中,如果想向對方解釋一種陌生的事物,或傳達一個新的觀點,首先選擇的是交際雙方都熟悉的事物或觀點。如例句“我趕不上現代生活的步調”,就是用個人生活中走路的速度(有形)來比喻現代生活的節奏(無形),并形成一種對比,來表達說話者對現代生活節奏的認識。聽者結合自己的生活認知,能感受到說話者在這句話中的情感表達,即生活節奏太快,有些力不從心。這種將具體事物映射到抽象事物的物化活動,就是本體隱喻。
《漫長的告別》不同于其他偵探小說之處,在于它濃厚的文學性。在文字搭建的游戲中,隱喻扮演著重要角色。雷蒙德·錢德勒非常善于用具體的事物和經驗來描述,讓人身臨其境、感同身受、拍案叫絕。如在描述西爾維婭時,使用了下列本體隱喻:
(1)“那個姑娘看了他一眼,眼神足可以戳進他的身體,再從后背透出四英寸來。”
(2)“語氣冷淡得連一片意式冰淇淋放她身上都化不掉”。
(3)“她用不銹鋼一般的聲音說。”
(4)“他只是一條迷路的狗。也許你可以幫他找個家。”[3]
上述本體隱喻形象地刻畫了人物形象。西爾維婭出身富足家庭,父親是傳媒大亨,億萬富翁,在黑白兩道都是舉足輕重的人物。這給了她高傲的資本。在金錢就是權力的社會里,她高高在上,犀利的目光如同刀一樣,戳穿了服務員外強中干的本質。對社會地位低下的人,她是不屑一顧的,甚至把無能的丈夫視為可隨時拋棄的動物。借著人們對冰淇淋、不銹鋼的認知,讀者可以感受西爾維婭的冷漠無情,可謂入木三分。
(二)結構隱喻
結構隱喻是用一種建構性高的、清楚描繪的概念去建構另一概念[4],王寅認為“隱喻中始源概念域的結構可系統地轉移到目標概念域中去,使得后者可按照前者的結構來系統地加以理解”[5]。
雷蒙德·錢德勒在《漫長的告別》中有一句話,“人生不過是一場大雜耍表演。”[3]這句話讓人想起了莎士比亞在其喜劇《皆大歡喜》中的臺詞:“世界是一個舞臺,所有的男男女女不過是一些演員,他們都有下場的時候,也都有上場的時候。一個人的一生中扮演著好幾個角色。”[6]顯然,前者是后者的一個次級映射。在“世界是舞臺”這個映射中,人對應演員,人生對應舞臺,人的行為對應舞臺上的演出。將“舞臺”這一熟悉的事物映射到“世界”這一未知的抽象事物,讓人產生無限聯想。雷蒙德·錢德勒巧妙地借用了這一映射,生動地描繪了韋德舉辦的雞尾酒會。酒會上,形形色色的人物登場,人人大聲講話,卻都舍不得放開酒杯,喧囂的表象下,掩蓋著上層社會的齷齪與骯臟交易,以及人性的虛無和猥瑣。“大雜耍表演”是對有錢人生活奢靡腐化的諷刺,更是對當時那個到處充滿銅臭味的社會的抨擊。
(三)方位隱喻
方位隱喻也叫空間隱喻,是指同一系統內部按照上——下、內——外、前——后、深——淺、中心——邊緣等空間方位組織起來的隱喻概念[7]。人們將對情緒、社會地位等的感受投射到空間方位概念上,使未知的抽象概念具象化。
在《漫長的告別》中,雷蒙德·錢德勒大量使用“上——下”方位隱喻來折射社會現實,讓讀者切實感受那個年代洛杉磯的社會萬象和人際關系。上下維度是人類最早掌握的空間關系。在認知心理中,為了掙脫從上往下垂直方向的地球引力,人們對從上往下方向的延伸賦予了消極含義,而對從下往上方向的延伸賦予積極含義,因而出現了“快樂為上,悲傷為下”“強者為上,弱者為下”“量多為上,量少為下”等隱喻意義。例如:
(1)他把我關起來,想證明什么?
(2)他是老大,是贏家,一切都在掌握之中。[3]
處于優勢的強者具備操控能力,處于劣勢的弱者則被人操控。例1 中,警方用手銬將馬洛銬上,因為警方找不到案件的線索,僅憑一個電話號碼就把馬洛關進重刑犯牢房,嚴刑逼供。象征公平公正的法律制度,在權力面前形同虛設。普通民眾只能服從,因為警察有權力這么做。“lock up”折射的是警方濫用權力這一事實。在例2 中,他(哈倫·波特)是報業大亨,在政界、金融界、警界、白道、黑道都是公眾人物,一通電話就可以讓馬洛的偵探執照被吊銷。他一方面操控報業,通過販賣各種丑聞、犯罪、性、聳人聽聞的新聞和金融性廣告來牟取暴利,另一方面又利用自己的特權來掩蓋個人隱私,翻手為云,覆手為雨,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under control”這個向下的方位隱喻揭露了美國社會所謂“新聞自由”的丑惡本質。
四、結語
隱喻是人類感知世界、交流情感的重要認知手段。通過將一個具體概念映射到另一個抽象的源域,人類完成了新概念的建構,豐富了想象力,并賦予語言思想性和文化性。雷蒙德·錢德勒在《漫長的告別》中,使用本體隱喻、結構隱喻、方位隱喻,向讀者展示了20 世紀40 年代美國洛杉磯的城市風貌,描述了人們對友誼、愛情、金錢、權力的不同態度。大量隱喻刻畫了生動的人物形象,揭露了美國的社會現實,賦予偵探小說文學性和社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