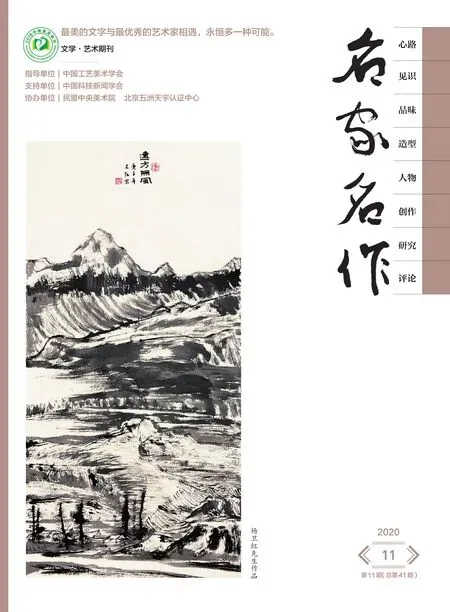論隱喻的詩性智慧
陳玲玲
本文所談論的隱喻不僅僅是修辭學意義上的隱喻,更主要的是人類精神活動層面的隱喻。以下將從人類學和詩學的角度分別對隱喻的觀念和詩性智慧進行論述。
一、人類學:隱喻是人類基本的和原始的思維方式
隱喻是人類基本的和原始的思維方式。人類面對陌生的世界最初就是運用早期的隱喻思維來認識新事物,表達新的經驗。法國人類學家列維·布留爾在《原始思維》中對人類原始思維進行了描述,他指出人類的原始思維具有原邏輯的和神秘的性質,構成這個思維的集體表象是受互滲律支配的。“原邏輯”不是說原始思維沒有邏輯或者不合乎邏輯,而是指它遵循跟現代邏輯結構不一樣的特殊邏輯。“原邏輯”不是說原始思維是非邏輯的或反邏輯的,它只是遵循互滲律而對事物的矛盾律不關心。原始思維對事物之間的相似和聯系更感興趣,認為事物之間存在神秘的“互滲”:互相關聯、作用、感應、影響。“互滲”是原始人類按照自己的觀察和體驗對事物之間具有的某種神秘關系的一種聯想,用以解釋事物之間的因果關系。現象的發生是在一定的神秘性質的條件下由一個客體傳給另一個的神秘作用的結果。這種在原始思維的運作中起主導作用的“互滲律”帶有隱喻性質。“互滲”與弗雷澤在《金枝》中提出的原始巫術思維“相似律”和“接觸律”的特征相類似,物體通過某種神秘的感應(基于相似或接觸的聯想)相互作用。
現代邏輯思維排斥一切直接與它矛盾的東西,同一關系只能建立在對象完全相同的基礎上(a 是a,a 不是非a)。而原邏輯思維把相似的東西看成是同一的東西,同一能建立在事物間具有相同屬性的基礎上(a 即是非a,只要a 與非a 在某一屬性上是相似的)。比如人與他的畫像,事物和它的名稱等都被原始思維看成是同一的東西。不僅如此,不僅相似即同一,事物還能通過接觸、轉移、感應、遠距離作用相互滲透和包含,使有生命體與無生命體互通,主體與客體互通,認為自己同時與可見和不可見的存在物生活在一起,這種思維想象到的東西都包裹著神秘因素,事物的發生都是由神秘的和看不見的力量引起的,它使原始思維帶有神秘的性質。
列維·布留爾認為在原始人類的思維中有一種受神秘的互滲律支配的集體表象,“這些表象在該集體中世代相傳:它們在集體中的每個成員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引起集體中每個成員對有關客體產生尊敬、恐懼、崇拜等感情。”[1]這些集體表象構成了個人的意識和知覺,它們通過存在物和客體之間的互滲而相互關聯。集體表象涉及的東西有:住宅、武器、植物、動物、睡眠、疾病、死亡、夢、天體的升落、云、降雨、打雷、石頭等。
原始思維這種“原邏輯的和神秘的性質”使原始人類所感知到的外部世界與我們所感知的世界不同,他們知覺到的是物物相通,生命萬物間有神秘的聯系。他們相信自己與某種動植物,與風和雨一類的自然現象,與星座、太陽、月亮有神秘的血緣或親緣關系,社會集體與其周圍的生命群體有親族關系。列維·布留爾考證巴西北部的一個部族稱他們自己是水生動物,而鄰近的一個部族則自夸是紅金剛鸚鵡。斯賓塞和紀林研究過澳大利亞土人認為太陽是巴伽農女人,以一定的親族關系與部族的其他所有氏族聯系著。我們看到在原始思維中,人既可以是人,又可以是長著漂亮羽毛的鳥,太陽既可以是太陽,又可以是有親族關系的女人,他們實際上是同一的。原始思維具有把不同事物同一化的作用,使運用一種事物去隱喻另一種事物成為可能。隱喻思維正是建立在原始思維的原邏輯的和神秘的性質基礎上的,在產生初期,它與原始思維實際上是同一種活動。
原始民族最初就是運用早期的隱喻思維來認識未知事物,表達新的經驗。他們的概念性極其微弱,邏輯思維還不發達,只能用已知事物的具體意象來表達未知事物,傳達自己的某種朦朧感受,他們憑自己的感官印象接觸、體會外界事物,思維方式未脫離具體事物和形象。兩種不同事物之間的聯系是通過類比和聯想發現它們的感性現象之間的某種相似性建立起來的,用已知的具體意象來表達新的事物和經驗,認識就得到了增進,這實際上就是隱喻思維的過程。
隱喻從根本上來說是在兩個不同事物之間建立聯系,用一個事物來理解另一個事物,用一種事物替換另一種事物。人類早期的隱喻思維只關注事物的外在現象的相似性,并不考慮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原始民族最初就是運用這種原始感性的方式來認識世界的。我國馬王堆出土的帛畫中,在太陽中間站立的是一只三腳烏鴉(金烏)。鳥的形象同時也是太陽的化身,它們的羽毛就是光線變成的。“巨蛇勾勒出大地表面的形狀;‘小花蟬’的鳴叫產生了聲音;甲蟲在水面上飛舞便誕生了河塘;綠色的蚱蜢孕育了草原,因為它們蹦到哪里,哪里就長出青草;‘黑暗的女主人’貓頭鷹閉目入睡時夜幕便降臨了。”[2]
人類原始的隱喻思維帶有普遍性,諸如神話敘述、詩歌創作、圖騰信仰、巫術禮儀等都是帶有隱喻性質的活動。原始民族把世界想象成整體,覺察不到事物之間的區別和對立,有時即使覺察到了也不感興趣,因此可以單數與復數同一部分與整體統一,也可以允許同一個事物在同一時間存在兩個或幾個地方。原始的隱喻思維是具體的整體的思維。隱喻所產生的基礎即世間萬物皆是我們身體的一部分,所有動植物的生存環境都是我們身體的一部分,彼此息息相關、聲氣相通。
二、詩學:隱喻是人類詩性智慧的代表
文學藝術遵循著人類早期的隱喻思維和語言的模式,讓我們的思考投向詩和文學藝術的審美空間,詩人的心靈在本質上仍然是神話時代的心靈,維柯把神話時代人們的心靈態度稱為“詩性智慧”……“渾身是強烈的感覺力和廣闊的想象力”,[3]認為正是在這些推理能力薄弱的人們那里產生了真正的詩性的詞句,表達出最強烈的情感,具有崇高的風格,令人驚奇和贊嘆。人類的詩性智慧無疑與從事藝術活動的心靈態度相吻合,諸如強烈的感受性、情感性,對宇宙、自然的詩意想象,對世界的直覺的感性的反映,這些都帶有藝術思維活動的色彩。
神話與詩就是人類對世界詩性反映的產物,是人類詩性智慧的產物。人們認為自然現象和事物也和自己一樣有生命、有情感,通過想象賦予它們某種人的外在形態和性格,賦予它們內在生命,創造出詩和神話,并對世界作出象征性的解釋,這體現出人類早期的隱喻思維。比如人們把天想象為一個巨大的有生命的物體,把打雷扯閃想象為一些體力極強大的人在發怒,用咆哮來發泄他們的暴躁情緒,并稱之為天神或雷神。在中國創世神話——盤古神話中是這樣描述的:“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千八歲,天地開辟,陰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氣成風云;聲為雷霆;左眼為日,右眼為月,四腳五體為四極五岳;血液為江河;筋脈為地理;肌肉為田土;發髭為星辰;皮毛為草木;齒骨為星石;精髓為珠玉;汗流為雨澤……”[4]
在神話的詩意想象之中,在人類詩性智慧里蘊含著人類思想的原始隱喻,即天人合一的原始隱喻。因此隱喻是作為人類精神活動存在的,人與自然的隱喻關系為詩和其他藝術提供了創作源泉。萬物息息相通,生命萬物間神秘的相似性使詩人的靈感和幻想得到更充分的發揮。這是人類詩性智慧和隱喻思想的意義所在。詩人們以全部的心靈和感官去領會外界的一切,進入我與物同,人與外部世界同一的境界,萬物相通,互相呼應,詩和藝術正起源于此:
自然是一座殿堂,那里的活柱石
不時傳出一些隱隱約約的話語;
人們在這象征的樹林里來來去去,
樹林子以親切的目光向你注視。
仿佛是來自遠方的悠長的回音,
終于融匯入自然的幽深的懷抱;
仿佛是浩漫無際的星夜和白晝,
香氣、顏色和聲音在此呼彼應。
有些香氣新鮮得如兒童的肌膚,
柔和得如雙簧管,翠綠得如牧場;
另外一些——爛熟了,還自矜豐富。
那永無止境的品物在不斷擴展,
如同龍涎香、麝香、安息香和篆煙香,
一起歡唱著心靈和感官的狂想。
(波德萊爾《呼應》)
“‘在世界的兒童期,人們按照本性都是崇高的詩人’,神話或詩的創造在原始社會中都是全民族的事”。[5]難怪詩人和藝術家對一去不返的神話時代向往懷戀,恨不能徜徉林野、放浪海天,從而恢復人與自然的原始親緣關系,找回人類原初的生命智慧,體驗人類思想的原始隱喻——通向美的自由想象之路。
韋勒克和沃倫在《文學理論》中指出:“文學的意義與功能主要呈現在隱喻和神話中,人類頭腦中存在隱喻式的思維和神話式的思維這樣的活動,這種思維是借助隱喻的手段,借助詩歌敘述和描寫的手段來進行的。”[6]文學藝術遵循著人類早期的隱喻思維和語言的模式,雖然抽象推理思維由于能深入事物的本質,探究事物的內蘊逐漸取得了優勢地位,但在需要直觀形象、詩意想象、強烈情感的藝術活動領域,隱喻卻大放異彩。隱喻思維和語言在表現人類精神世界和感情體驗的復雜性,揭示文學藝術的內在意味和深層意蘊等方面顯示了其特殊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