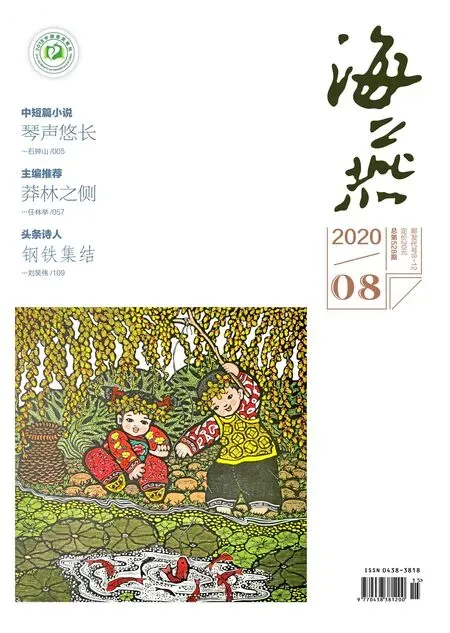消失的稻田
文 程婧銘
一
辦公樓對面有一片荷塘,荷花凋敝。日光照耀下,荷葉稀稀疏疏地立著,葉邊蜷縮,綠意慢慢消褪,水面上漂浮著一層黃綠色油脂。荷葉與一小片樹林巧妙地遮擋住了遠方的一片開發工地,我曾嘗試繞開這塊遮擋走近看看,村子里幾只盡責的野狗,兇猛地吠叫,把我遠遠地嚇了回去。
一日清晨,好奇心再次驅使我別停下腳步,保持目不斜視,不去想那幾條虛張聲勢的野狗,悶頭跑過村中那棵缺胳膊的杉樹,跑過窩在沉睡小屋里的野狗,跑過村頭小溪空空的洗衣埠。成片的稻田從村頭鋪開延伸至四周的山腳,根莖被鋸得高低不平,黃色地表上夾雜著一塊塊焚燒留下的黑色,泥土中的稻香在霧氣中散開,愈發濃郁。幾只母雞踩著悠閑的腳步,在巡視這片領地,頻頻點頭收下領地進貢的糧食,然后扭扭身子抖動羽毛,并不停下腳步。鴨子從田埂上搖搖擺擺地走進隊伍當中,少了些領主的氣勢,只能對那些巡視過的領土復查一番,和兒時的我一樣。
那時候早晨4點鐘,我會在迷迷糊糊中聽到二姑尖尖的嗓門亮起,窗外走廊的燈火點亮了墨色的夜,聽見奶奶招呼人們吃早飯,又囑咐他們帶上大壺茶。一陣窸窸窣窣之后,家里恢復安靜,只剩下爺爺奶奶與我。一頓回籠覺后,我快速爬起跑去田里,大人們已經開始打稻,少了沉甸甸的稻穗后,稻草們整整齊齊地一垛垛列隊站立著,我只能游走在隊列之間撿拾殘存的戰利品。
爺爺常給我一些小生意做。清明時用高價收購我采的野茶,拿著他給的樣品,我和小伙伴們把山上看得見的兩葉一芽都摘了下來,勉強湊了兩斤不到的鮮葉。板栗倒很實沉,踩著涼鞋揉搓它刺猬樣的外殼,裂開小口后,小心地將兩根食指放在小口的邊緣,慢慢往兩邊拉,取出精心呵護著的板栗。丟進嘴里一咬,帶有細密短小茸毛的硬殼瞬間開口,露出嫩黃清甜的果肉。我總是打著飽嗝將僅剩的板栗賣給爺爺,也不到兩斤。雙搶時我負責撿被遺留的稻穗,這回兒不用擔心重量,爺爺按工時結算工錢。我喜歡撿整根的稻穗,一根十來公分的稻稈上,幾十粒金黃瘦長的稻谷緊緊挨著,像是突然喊停卻來不及止住腳步擠在一塊兒的小孩們,仰頭彎腰笑個不停。還有些散落在田里的稻谷我是不撿的,交給小雞小鴨們進行第三輪清掃。
好奇心隨著歲月流逝愈發強烈,我不再滿足撿稻穗的活兒,對插秧、割稻躍躍欲試。插秧時節,氣候適宜,不需要起早摸黑干活,但皖南的稻田里布滿了水,總是泥濘的,需要高高卷起褲腿光著腳丫踩著軟糯濕滑的地里。奶奶說水田里有血吸蟲,會鉆進腿里。這名字讓我想到那紅彤彤肉粉色細長的小蟲鉆進腿里吃我的血的情景,頭皮發麻。我確定血吸蟲一定就和我想的一樣令人毛骨悚然,于是站在田埂上擔心著站在那布滿血吸蟲的泥濘里的大人們,絕口不再提插秧的事。
割稻子我可不怕,曬干了的田里我可以穿著鞋子走進去。鄭重接過彎彎的鐮刀,看著爸爸示范并幫我割出塊兒空地。只見他左手一把撈過一片稻稈,鐮刀“刷”地一聲齊齊割下,切口平整,稻稈在手上一個翻轉整齊地落在身后。多簡單,我左手一把抓住緊挨著的幾株稻稈,有些扎手,松開。手不夠大少抓幾株,右手提起鐮刀向左下方割去,沒有刷刷的利落,但勉強割下了第一把稻子,開心地沿著給我劃分的一綹地繼續割。不知在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左手小拇指突然被割傷,爸爸笑著說:“你這是殺雞呢,中午給大家補補。”有了第一年的經驗后,每年我都會殺一次雞,每次都是左手的小拇指。
打稻機是我最期望使用的工具,總盼望著大人們可以將這項光榮的工作交給我。我負責將摞好的一捆捆稻子遞送到打稻機的臺子上,慢慢地我挪到他們中間,雙手扶住臺子,雙腳放在踏板上跟著他們的踩踏上上下下,滿足不已。慢慢地我站上踏板,雙手抓緊一把稻稈,將稻穗放在翻滾著的帶著無數整齊排列的鐵環上,手順著腳的節奏翻轉著稻子,谷子一粒粒跳落機箱里。通常一個上午三個人能完成一畝地的收割和打稻工作,趁著天還不算太熱,帶稻谷回家,洗個冷水澡吃個中飯,飽飽地睡上一覺。
操作風車的工作是一項細活,大多時候由慢性子的爺爺干。他站在風車前,一手緩緩地搖著鐵質手柄,一手搭在那截可上下調節稻谷流速的木條上,稻谷從車頂的漏斗里進去,秕谷糠皮雜草從左側的風口中吹出,飽滿的谷粒從身前的小嘴里流出掉進籮筐里。他有時候也會把這活兒交給我,自己站在一旁耐心指導,手不能搖得太快,風力太大好谷子會被吹跑會篩不干凈;也不能搖的太慢,風力不夠吹得不夠干凈;檔位不要調節得太快,下谷速度太快,你的速度跟不上。看似輕松的活兒,里面那么多的講究和門道,我按照爺爺的速度搖起來,是最為保險的方式。
最放心交給我的活是:曬谷。家里備有整套齊全的工具,竹編的曬谷墊、翻曬用的曬谷耙、收谷用的長柄木鏟和大簸箕。早起掃干凈院子,鋪開墊子,將籮筐里的稻谷倒上去,有時墊子不夠就直接倒在地面上,用耙子將它們均勻地鋪在墊子上,接受陽光的暴曬。夕陽斜照,用木鏟將稻谷歸攏在一起,遠遠起跑加速,提起大簸箕沖向谷堆,將簸箕往內一插,瞬間裝滿,倒回籮筐里。曬谷的時候最怕下雨,夏天的雨下得突然,下得蹊蹺,明明陽光明媚,卻笑著落下一陣豆大的雨滴,一家人頓時忙碌起來。趕不及的時候,就將墊子的四角對角收折,將稻谷歸攏在中間,然后折疊墊子蓋在上面,取來塑料布給它擋上。等我們跑回屋檐下喘息時,雨水澆濕炙熱地面的氣味撲面而來,雨又剎那間止住。
二
穿過飄著稻香的田野,踩著壩基跳過淺淺的小河,鉆進過腰的芭茅野草,露水不經意滑入空空的腳踝,掃過陣陣涼意,爬上堤岸,裸露的黃土地上,明黃色機械在不知疲倦地翻著土地,臨時搭建的藍頂房子里走出三三兩兩的紅色安全帽。望著眼前的工地,低頭瞥見被打濕的黑色鞋尖粘滿了土黃色的泥土,我迷失了方向,腳下的土地變回當年的稻田,蘆葦間的嬉笑打鬧,那一刻忐忑不安偷來的玉米還掛在墻上,成了能剩下的最鮮活的記憶。
爺爺住院的前一天早上,他依舊五點起床,穿好之后,坐在窗前聽廣播看報紙,然后進餐廳用早飯。飯畢,摘下假牙仔細刷洗一遍,裝進嘴里后進屋拿起藍色塑料圓梳,對著小圓鏡,從前向后仔細地梳理著頭發,就像給牛套上犁一壟一壟地慢慢耕,將雜草翻進土里,將蚯蚓翻出地面。發根順著梳動的方向變黑變亮,過不了多久,爺爺理掉發梢的銀發,就又有一頭烏亮柔順的短發。他放下梳子,取過一頂黑色鴨舌皮氈帽,慢慢地戴在頭上,緩緩走出門,和奶奶打了聲招呼,便出門了。他照例繞到村后的田里、地里轉上一圈,突然有了興致,沿著新開的大路去了鄰村,他聽說那兒新建了一座植物園。
秋風蕭索,氣溫驟降,兩個多小時后,爺爺回到家便有些頭疼,呼吸不暢。第二日便去醫院住了下來。從外地聞訊趕回來的我,以為爺爺只是上了年紀,肺部功能不足,無法應付突如其來的壞天氣,感冒會比年輕人嚴重些。走進病房,握住爺爺的手,滿是溝壑的手心和稻子一樣,有些扎人,手背是柔軟松弛的麥色表皮,上面布滿了深淺不一的斑點。爺爺靜靜地躺著,溺愛地望著我說:“你來了啊,孩子呢?”我俯看著他,忍不住伸手輕輕摸了他的頭發。爺爺是家里最有威嚴的卻也是最溫和的人,話不多總是微笑著。這是我第一次摸這些即將變黑的頭發,很柔軟,香香的滿是溫暖的香味。一天之后,情況很不好,家人決定將他送進ICU試試。他渾身插滿了管子,連說話都費力,目光總看著玻璃外,看見我們出現就微微抬手示意我們進去,只一周他的頭發白了。他走了,那一年他88歲。
爺爺走后,那些地失去了天天看望它們的人,日漸荒廢。奶奶被接進城里之前,將地交給了村里的人耕種。頭一年,村里人說每年每畝給我們400斤稻谷作為租金,第二年變成了300斤,第三年變成了200斤,第四年奶奶說給100斤就成,你拿去精心耕種就可以,村里人怎么也不同意,說一定要交200斤。可第五年他們不種了,地徹底荒蕪了。有時,我會帶孩子們去爺爺說過的那塊最好的地邊走走。每年爺爺都在這塊地里育秧,站在田邊望著青青的秧苗一點點地拔高,他文弱的背影就靜靜地倒映在這水面之上,與青山融合在一起。
皖南山區的地大多依山傍水。依山,劃分的界限鮮有直線,彎彎曲曲的田埂勾勒著各自的領土;傍水,田肥,灌溉方便,相對貧瘠的地要更小些。最初分田到戶時,村里根據田的好壞、遠近劃分,好的壞的、遠的近的互相搭配著分配到每家每戶。我家的田地被劃分在了村莊外東南西北四個區域,最遠的地位于山上開挖出來的梯田,除了奶奶,我們家誰也無法說清楚這些地兒都分布在哪兒了。
這和北方的完全不同。第一次去位于中原大地的先生家,他騎著摩托車載著我穿出整齊的村莊,駛入一條兩旁植滿楊樹的小道。周邊一望無際的麥田,青綠色泛些金黃的麥浪,在晚霞中一波一波地蕩漾,我好像迷失在當中。下車站立,久久不愿離去。前不久再次回去,那片麥浪已被橫平豎直的大道取代,在無數高樓當中,先生竟分辨不清自己的老家被放在哪條馬路背后了。
三
幸好,在這片工地上,我找到了被卡車碾軋的車轍。順著車轍,朝著西方被太陽映照成粉色的山體,我找到了回去的路。經過鎮里的新時代文明實踐廣場時,一對老夫妻正將三輪車上的化肥袋子一一抬到廣場中間,倒出黃澄澄的稻谷。這兒真是一個曬谷的好地方,足有兩個足球場那么大,背山、枕水、沒有房屋和高山遮擋。白天鮮有人至,只有晚上才會熱鬧起來,鎮上的人們集聚在這兒跳著廣場舞,或是乘涼聊天溜娃。看來他倆今年收成不錯,廣場換上了靚麗的黃色,豐收的色彩洋溢在臉上,手里不停揮動著耙子翻動著飽滿的谷粒。
收新谷,打新米,最美味的是大鍋灶里米湯和鍋巴。掀開木頭鍋蓋,米湯咕嘟咕嘟冒著水泡,撐得大大的又炸了似地跳進去等待再次漲起。奶奶拿出藍邊碗,碗底鋪上厚厚一層白糖,大湯勺一舀,沸騰的米湯落入碗中,瞬間平靜,融化成甜甜的牛奶。添幾把柴火,湯汁收盡,取火再悶多時,香香脆脆的鍋巴便可以和著曬得出油的辣椒醬,成為餐桌上的美味。
周末有朋友問:“你們那兒還有沒收割的稻子嗎?”我答道:“都割了。”問她為什么打聽這些,她發來一張照片。一位可愛的姑娘站在稻田里,甜美的笑容、白色的衣裙、金黃的背景,組成一幅絕美的畫面。稻田,確實是適合攝影的場所。秋季,黃色的稻田、藍色的天空、紅色的晚霞,最基礎最純凈的色彩,匯聚在一起,正是一幅天然之作。
這些年,荒廢的地兒逐漸煥發新的生機。靈山的向日葵花海、婺源的油菜花海每年都吸引著無數游客前去觀賞,人們喜歡以成片的農作物做背景進行攝影創作,回憶兒時與黃土與農活相伴的生活。百日菊是很容易成活生長的植物,扔一把籽兒在地里,它可以肆意綻放,鎮上的一片荒地也撒了百日菊種子。到了稻子成熟的季節,百日菊在陽光下開得越發艷麗,一朵朵孤零零的花朵,不需要綠葉的映襯,鋪就一片靚麗的海洋,身處其中的人,臉上洋溢著歡樂。節后農人們挖除百日菊,翻整地面,趕著時節種上油菜,來年春天這兒換上一片黃色的花海,又是一番美景。鎮上的老街,有一家老油廠,每時每刻那兒都飄浮著濃郁的油香,油菜花落之后,油菜籽便可以被收割送去這兒,加工成健康的菜籽油。
或許某個秋日,黃昏中,穿著一襲白裙的我,在老家的那片稻田當中,能再次看見爺爺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