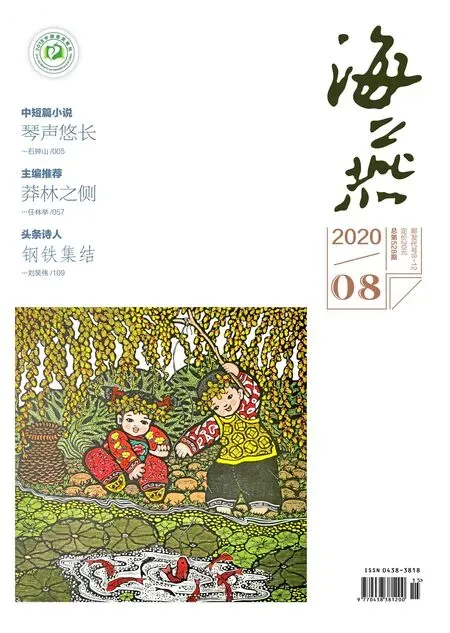讀詩記(二)
文 劉向東
借助多種文化的歷史想象力
德里克·沃爾科特,生于加勒比海岸圣盧西亞島,他的作品建立在多元文化背景之上,具有廣泛的國際影響。
新世界
那么在伊甸園之后
還有什么新奇之物嗎?
哦,有的,第一串汗滴
使亞當敬畏。
自那以來,他整個肉體
便只好浸泡在咸咸的汗水中,
以感受季節的交替、
恐懼和豐收;
快樂盡管來之不易,
但那至少屬于他自己。
蛇呢?它不會銹死在
樹木盤錯的枝丫上。
蛇羨慕勞作,
它不會讓他孤獨。
他們倆會看著榿木的
葉子變成銀白色,
看著櫟木染黃十月。
所有的東西都能變成金錢。
所以當亞當乘坐方舟
被放逐到我們新伊甸園,
那被創造的蛇,也盤身舟中
給他做伴;上帝希望如此。
亞當心生一念。
他和蛇共同承擔
伊甸園的喪失,應該有所獲得
于是他們創造了新世界。它看上去還不錯。
(西川 譯)
此詩取材于《圣經》,但卻是一支人的贊歌。我們若知道圣經故事,理解起這首詩就相對容易。《圣經》中有關失樂園的故事是這樣的:
上帝創造了萬物之后,在第六日造人。他按照自己的形象用塵土造出一個人,起名“亞當”(字面的意思是“人”)。上帝將亞當安頓在伊甸樂園里,他允許亞當食用所有樹上的果子,只有“善惡樹”上的果子除外,若不然,就會喪命。上帝見亞當孤單,就在他入睡時從他身上取出一根肋骨,造成一個女人做他的伴侶。亞當一覺醒來,看見女人非常高興:“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夫妻二人 ,赤身裸體,天真爛漫,并不覺得羞恥,過著無憂無慮和諧美滿的生活。
在上帝所造的生物之中,蛇是最狡猾的。一天,它對女人說:“善惡樹上的果子鮮美異常,吃了也不會死的。上帝所以不讓你們吃,是怕你們吃后心眼明亮,知善惡,辨真假,就跟上帝一樣智慧了。”女人的心動了,于是吃了一顆禁果,果然鮮美異常,便勸亞當也吃了一顆,食后二人頓時心明眼亮,知善惡,辨真假,而對自己赤裸的身體,羞恥之心頓然而生 。
當上帝漫步樂園時,他們便藏了起來。這樣,上帝知曉了二人偷食禁果的事,他要實施威嚴的懲罰:引誘人的蛇被罰永世在地上爬行,吃土;女人被罰生育時備受苦痛,對丈夫俯首聽命;亞當被罰,“從今以后,土地要給你長出荊棘的蒺藜,你必須終年勞苦,汗流滿面,才能從地里得到吃的,勉強維持溫飽。這樣勞碌終生直到死后歸土”。事后,亞當給妻子起名“夏娃”,意謂大地上眾生之母。上帝給這對有罪的夫妻做了獸皮衣服,然后將他們逐出伊甸園。這首詩正是從“伊甸園之后”展開的,人離開了神的呵護,開始承擔自身的命運了。人會沉浸在悲郁和絕望中嗎?生命的歷程還會有“新奇之物”嗎?——“哦,有的,第一串汗滴,使亞當敬畏。”人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力量,雖然他們的肉體浸泡在咸澀的汗水中,他們經歷了四季輪轉,風霜雨雪,恐懼和豐收。但畢竟不是靠神,而是靠自己的雙手創造了自己的生活,“快樂盡管來之不易,但那至少屬于他自己”。
蛇呢?它的狡猾是否只代表邪惡,而不同時喻示著對人的智慧和獨立感的贊賞?看起來,詩人并不簡單認同傳統的“圣經釋義學”的說法。他寫道,“它不會銹死在,樹木盤錯的枝丫上,蛇羨慕勞作,它不會讓他(亞當)孤獨”,他們倆會看著美麗神奇的樹葉變成潔白的純銀和明麗的金黃色。他們相信勞動會創造生活的必需,“所有的東西都能變成金錢”。
基于對《圣經》進行詩性的“解釋學循環”,詩人認為,亞當是人的泛指,因為下面“方舟”的故事只是亞當的子孫經歷的——乘坐的方舟上之所以有蛇與之為伴,是“上帝希望如此”。人理應知善惡,辨真偽,心明眼亮,樹立自己的尊嚴。如果發現的智慧竟被視為禁區,那人還算什么人?人艱辛生存,但是人的價值也正體現在這里。
詩人將一場曠古的懲罰,變作了人類尊嚴和價值的偉大揭幕式。人以他的勞動和智慧,創造了大地上的文明,“共同承擔,伊甸園的喪失”。詩人肯定了人的尊嚴和光榮。
請回望并展望這屬于人的新世界吧,讓我們與詩人一道高傲地說:“它看上去還不錯。”
德里克.沃爾科特還把荷馬史詩中的故事置于自己的想象之中,在古代希臘群島與現代加勒比海之間架起了一座相通的橋梁——
這個句子的盡頭,雨會開始飄下。
雨的邊線上,是一張帆。
慢慢地,群島自帆的視野消失;
一個種族對港口的信仰
也駛入了迷霧。
十年的仗打完了。
海倫的頭發是一片烏云,
而特洛伊已是煙雨茫茫的海邊
一只盛滿白灰的火坑。
細雨漸密,像豎琴的絲弦。
一個目光陰沉的男子用手指扣住雨絲,
把《奧德賽》的第一行輕輕撥響。
——《新世界地圖之一:群島》
(阿九 譯)
全詩以雨開始,又以雨結束,“在這個句子的盡頭,雨會開始飄下”。詩人的心緒在這里就被體現出來了。動筆寫詩,才剛剛寫下第一個句子,象征著感傷和憂愁的“雨”就開始飄落,直到這首詩的結尾,雨依然沒有停止并且更加密集了。“雨”這個意象的使用使得全詩貫穿著憂郁而沉重的基調,而灰暗曚昽的細雨邊緣,“是一張帆”。帆在這里是什么?
如果島嶼象征著人們渴望的精神家園,那么“帆”應該代表回家的工具——船。“島嶼”在人們的想象中,常含有一種浪漫的性質,在許多神話中,島嶼也是永生之地。但是由于戰爭的發生,人們慢慢地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園,所堅守的信仰也漸漸變得迷茫。
而十年的戰爭結束后,卻留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美麗的海倫頭發上也滿是戰火紛飛后飄落的灰燼,特洛伊也成了“一只盛滿白灰的火坑”,靜默在煙雨茫茫的海邊,承載著十年戰爭的回憶和數不清的傷痛。詩人沒有用血腥的場面來描繪戰爭的殘酷,而是用“海倫的頭發”來寫戰爭帶來的后果,真是絕妙的想象,而且在審美的同時也給了讀者極大的震撼。
詩歌結尾繼續寫雨,而且把雨的形狀寫得別致而又傳神:“豎琴的絲弦”,仿佛讓我們看到了細雨的飄落,并感受到了雨絲的緊迫和密集。“一個目光陰沉的男子用手指扣住雨絲,把《奧德賽》的第一行輕輕撥響。”這個目光陰沉的男子是誰?能夠拔響《奧德賽》的人也只有盲詩人荷馬吧?但這里也是詩人的自比,他要唱出自己的史詩給世人聽。而以雨絲作弦,哪里是彈奏詩歌,這分明是在撥動讀者心底深處的那一縷柔情。這樣詩中就有了畫,有了音樂,更有了詩人的情懷。詩人仿佛就站在歷史的深處,跨越了遼遠的時空,幽幽地看著這一幕壯烈的悲劇,而偉大的盲詩人荷馬則站在他想象的頂端。
雖然這篇《群島》只是詩人以神話和史詩為題材的眾多長詩中的一首短詩,但窺一斑而知全豹,我們已經能夠看出,他把現代加勒比海的精神融進了荷馬史詩的框架中,并借助多種文化的歷史想象力,得心應手地完成了來自故島穿越時空的偉大藝術,詩人沃爾科特無愧于一個偉大的稱號——加勒比的荷馬。
西川還譯過沃爾科特的另一首詩《力量》:
生命將不斷把草葉砸進土里。
我羨慕這暴力;
愛情是鐵。我羨慕
碎浪和巖石之間的野蠻的交易,
它們之間互相理解。
我甚至可以理解
奔跑的雄獅與驚懼的雌鹿之間的約定,
她眼中含有某種對恐怖的默許。
我將永遠不能理解的
是這只野獸,他寫下一切
并且自詡為生命的核心。
詩人寫這首詩歌的時候,心情一定輕松又欣慰,那是他發現了自然和人間萬物內核后的驚奇和欣喜。這也是詩人對生命經歷種種恐怖與驚懼后的理解和總結。雖然他下筆很狠,但對萬物間的強暴和對抗卻充滿了驚喜和默許:生長的生命與不斷砸進土里的草,相互對抗又互相依賴的碎浪與礁巖,還有恐怖的追逐中找到了平衡和滋味的雄獅與雌鹿,這讓他感到一種力量的鼓蕩。這力量沒有強與弱,或者說強與弱共同構成了這種無形而又永恒的力量,萬物就在這種力量的推動下,和諧而強健地繁衍與生息。這也是作者內心的節奏,剛健與溫馨像音律慢慢地起伏著。同時因洞悉了這永恒的秘密,詩人自己也充滿了霸氣和強悍,自詡為野獸和生命的核心,而那令自己自豪驕傲的激情和無盡的驅動力讓他不斷創造并寫下這一切。(也有其他版本把結尾理解成自然之力)
整首詩歌像一組蒙太奇鏡頭,跳躍簡約而又急促勁健。這勁健不是子彈也不是長劍,而是壓縮成體積很小的鐳,蓄滿了炸藥和毀滅性的殺傷力。
“直接就是”的詩
日本詩人谷川俊太郎的詩歌是為人生的,不是詩歌沙龍里只適合詩人小圈子互相切磋的晦澀玩意兒。
從根本的性質上來說,詩歌當然是想象和虛構的世界的藝術,但我們也還是可以區分側重于存在的具象的詩歌與側重于虛構的想象的詩歌。詩歌與世界的關系當是隱喻的關系,但我們還是可以區分,“直接就是”的詩歌和象征的詩歌、存在主義的詩歌和現實主義的詩歌。谷川俊太郎的詩歌,是“直接就是”的詩歌,也是感覺的詩歌。
活著,是谷川俊太郎詩歌的一個基本主題。亞洲20世紀的歷史,“活著”被如此強烈地意識到,恐怕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他的幾乎所有詩篇,都是帶著憂傷來寫的。
詩歌是為人生的,而不是為詩歌的。在谷川俊太郎的詩歌中,現代派、詩歌中的種種主義只是技巧、方法、知識,而不是詩歌本身。
因為是為人生而寫,他的詩歌使人熱愛生活,感激生命。
大人的時間
孩子過了一周
會增加一周的伶俐
孩子一周之內
能記住五十個新詞
孩子在一周之間
可以改變自己
然而大人過了一周
卻還是老樣子
大人在一周之間
只翻同一本周刊雜志
一周的時間
大人只會訓斥孩子
(田原 譯,下同)
有些詩很好,但不必闡釋。經常被批評家闡釋的詩,未必自動等于好詩,只不過有很大的闡釋空間而已。這首《大人的時間》是不需要闡釋的好詩。好在哪兒?好在真,有發現,有活力,有生氣灌注。面對這樣的詩,在“懂”之前,我們已被感動,已感覺到來自脊梁骨和內臟的親和,已經開始思索自身。
《樹》也是這樣:
看得見憧憬天空的樹梢
卻看不見隱藏在土地里的根
步步逼近地生長
根 仿佛要緊緊揪住
浮動在真空里的天體
那貪婪的指爪看不見
一生只是為了停留在一個地方
根繼續在尋找著什么呢?
在繁枝小鳥的歌唱間
在葉片的隨風搖曳間
在大地灰暗的深處
它們彼此地糾纏在一起
或許需要多說幾句的,是《小鳥在天空消失的日子》:
野獸在森林消失的日子
森林寂靜無語 屏住呼吸
野獸在森林消失的日子
人還在繼續鋪路
魚在大海消失的日子
大海洶涌的波濤是枉然的呻吟
魚在大海消失的日子
人還在繼續修建港口
孩子在大街上消失的日子
大街變得更加熱鬧
孩子在大街上消失的日子
人還在建造公園
自己在人群中消失的日子
人彼此變得十分相似
自己在人群中消失的日子
人還在繼續相信未來
小鳥在天空消失的日子
天空在靜靜地涌淌著淚水
小鳥在天空消失的日子
人還在無知地繼續歌唱
在20世紀50年代初,谷川俊太郎曾寫下這樣的詩句:“人類在小小的地球上,睡眠,起床,然后勞動,有時想和外星成為好朋友,宇宙人在小小的外星球上,做些什么,我不知道,或許睡沉,或許起床,或許勞動,但有時也想和地球成為好朋友,那是毋庸置疑的事情,萬有引力,是相互吸引孤獨的力,宇宙正在傾斜,所以大家彼此尋求相知……(《二十億光年的孤獨》)。這種“孤獨”雖不乏憂郁,但骨子里卻有一種天真健康的透明感、樂觀主義的通向未來的想象力。
然而,文明史急驟而兇猛的步伐,很快就使詩人的憂郁改變了方向:人類為了實現“科技圖騰”“后工業”的貪婪的未來的烏托邦,不惜濫用自己的智慧,使大自然破碎,流血、耗盡。詩人年輕時曾仰望宇宙的視線,現在不得不正視地球上正在發生的更急迫的災難了。未來主義的圖騰的“行話”開始失去魔力,后工業文明所允諾給我們的“美麗新世界”,變成了令人憂慮的難愈的創傷。生存環境的污染、惡化,世界沙漠化的速度,動植物種滅絕的速度,生物鏈的斷裂,資源的匱乏……都在提醒人們覺悟:未來主義的“洪鐘”是否同時也是趨赴絕境的喪鐘?人破壞了自己與大自然“同一性”的鏈條,就等于要將自己也連根拔起。要知道,大自然的起訴和審判不是垂直降臨的,而是每時每刻細碎、孤寂地以“無聲”嗚咽著,直到有一天它甚至無力以“無聲”的痛苦來嗚咽時,我們也就隨之一道消亡了。
詩人是“報警的孩子”,他望著大地、海洋、天空,警醒地攝取了那些“無聲”的痛楚信息。“野獸在森林消失的日子,森林寂靜無語,屏住呼吸”“魚在大海消失的日子,大海洶涌的波濤是枉然的呻吟”,“小鳥在天空消失的日子,天空在靜靜地涌淌著淚水”,……然而,自詡為宇宙精華、萬物靈長的人,卻蒙昧地“繼續相信未來”無知地繼續歌唱。
人類為爭取更好的生活環境奮斗,最后走向了它的反面。
這首詩在平靜的語調中壓入了十分沉痛的寓意,破碎的大自然的哀愁,與人類僭妄的行為形成鮮明對比。詩人沒有以大聲疾呼的方式去宣諭真理,而是以“幾何學式的干凈和透明”道出內心的痛楚和憂慮。這種安靜的聲音,與詩人所要表達的“寂靜無語”“枉然的呻吟”“靜靜地涌淌著淚水”的感情也達成了高度和諧。
看似平凡的事物中蘊含了神秘
看似平凡的事物當中,其實蘊含了神秘。詩人就是能夠說出這種神秘的人。
瑞典詩人哈利·馬丁松的《尺蠖》是一首以小見大的詩,它貌似來自詩人對動物世界的一次細察,而其中刻畫的某些細節卻成為人生的生動隱喻。在詩人的筆下,自然界也是一個富有人情的世界。
在開滿花朵的樹上
飄蕩著蜜蜂悠揚的合唱。
瓢蟲,一顆裝飾樹葉的活的珠寶,
分開緋紅的背脊飛去,
把自己的命運
交給含著花蕊清香的空氣。
尺蠖爬到葉子邊緣,像一個疑問,
支起兩只嫩黃的短足:向葉外蕩去,
向空茫的宇宙尋找棲處。
風聽見了,讓樹枝靠近它,
伸出樹葉的手,接它過來。
(李笠 譯)
這首詩先后寫了三種小動物:蜜蜂、瓢蟲和尺蠖。蜜蜂和瓢蟲共同構成第一節,尺蠖獨占一節。
詩中對蜜蜂的描寫只有一句,卻寫得很有質感。也許詩人并沒有看到蜜蜂,卻真切地聽到了它們的合唱,這種合唱自然是指蜜蜂舞動翅膀時發出的聲音。詩人說它們飄蕩在開滿花朵的樹上,巧妙地把聽覺與視覺融合在了一起。
詩中對瓢蟲的描寫尤其細致,首先把它比成“一顆裝飾樹葉的活的珠寶”,這不僅表明了瓢蟲與樹木的依賴與裝飾關系,而且揭示了它是一種動態性的存在。接著詩人就對它的動作展開細描,其中有兩個關鍵詞,一個是“分開”,一個是“交給”。“分開”之所以比“飛”重要,是因為它不僅是“飛”的前提,而且比“飛”更具體:“分開緋紅的背脊”賦予展翅這個動作以鮮明的色感,準確地說,是賦予靜止的“背脊”以動感。而“交給”則是個虛擬動詞,因為事實上并不存在命運的“交給”,只有瓢蟲的飛翔,這樣寫旨在交代瓢蟲的方向,或者說是歸宿:“含著花蕊清香的空氣”,瓢蟲向著花蕊飛翔,花蕊散發著清香,因此,瓢蟲飛翔在“含著花蕊清香的空氣”里。
以上所寫的瓢蟲其實是為寫尺蠖所做的準備。這個判斷的基本依據是詩人寫瓢蟲時用的是“交給”,而在寫尺蠖時用的是“接”,這兩個動作無疑形成了一個遠距離的回環。就此而言,前面所寫的瓢蟲可以視為尺蠖的替身,而且這一節也存在著一個和“交給”類似的詞“蕩”,卻寫得更加具體。這首詩以尺蠖為名的原因正在于此。在這里,尺蠖其實就是一個人的象征。經過探索和困惑,尺蠖為了找到自己理想的歸宿,終于邁出了關鍵的一步:“向葉外蕩去”。這就像雜技表演中冒險的拋空動作,弄不好會兩頭落空,然而所幸的是,尺蠖處于一個和善的世界。當尺蠖完成這關鍵的一跳時,風把附近的樹枝吹得離它近些,并讓樹葉伸出它的手,把尺蠖接到另一個世界。因了自然的仁慈,尺蠖才找到詩性的棲所。此詩在簡短的片段中營造出動人心弦的意象,因而令人一見難忘。
讀過此詩,我忽然想起我所見過的“吊死鬼”,也就是馬丁松筆下的尺蠖,隨手寫下《尺蠖:讀馬丁松同題詩》:
看你正在桑葉上爬
退一步,進兩步
到了葉子邊緣
的確如詩人的那個疑問
像是要向葉外蕩去
向空茫的宇宙尋找棲處
但是風
并不讓桑枝靠近你
另一片葉子也懶得伸手接你過去于是你把一根晶亮的絲
與陽光擰在一起
讓身體悠然垂下來
游蕩著,游蕩著,轉體,屈身
你用你的身體架設拱橋
化作青枝之上的青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