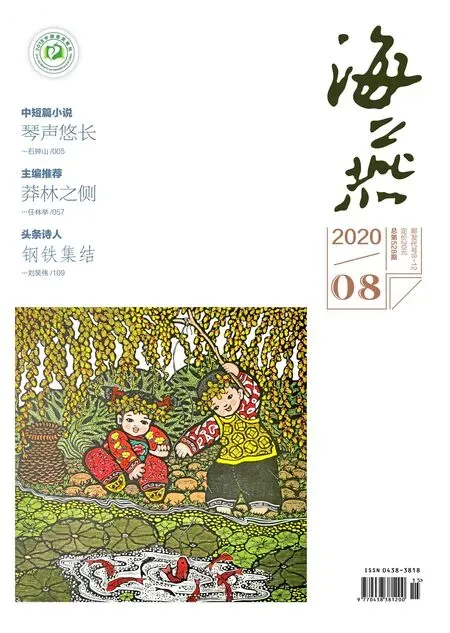一種改變的方式(外一篇)
文 尹光磊
一個人改變命運(yùn)的方式有很多,我靠寫新聞報道改變了人生。這是一種本能的企圖,卻同樣“務(wù)實而昂揚(yáng)”。
我初中畢業(yè)后到鎮(zhèn)里的高中只念了一年書,1982年趕上了一個就業(yè)的機(jī)會,自然也就無緣走進(jìn)高考的考場改變自己的命運(yùn)。當(dāng)時我在一個偏遠(yuǎn)的公社信用社當(dāng)農(nóng)金員,小地方閉塞,一度十分苦悶。
一天早晨,從睡夢中醒來時,仿佛有一種欣喜在心頭,萌生要進(jìn)城的想法。路遙《人生》中的主人公都是我們這些鄉(xiāng)土子孫們的代言人。我們當(dāng)年是那樣迫切地想吃商品糧,想生活在城市。一些閱讀以一種出人意料的方式開始影響了我。那個年代,人們樂于談文學(xué)。許多作家通過寫小說,成功進(jìn)了城。于是,發(fā)誓要離開。怎么離開?和他們一樣通過寫小說,調(diào)進(jìn)城里?顯然不行,因為我的閱讀少,生活積淀不厚實,還寫不成小說。只能悶頭練筆,從寫通訊報道開始。好在工作當(dāng)中,特別是鄉(xiāng)下,有許多需要報道的事情,寫稿播發(fā)和發(fā)表還算順利。一兩年間,在縣廣播站、地區(qū)報社乃至自治區(qū)級的報刊播發(fā)或發(fā)表了大量的新聞稿件。我常常記起那時在公社大喇叭底下收聽縣廣播站廣播自己寫的報道的情景。寫著寫著,漸漸有了一點(diǎn)名氣。
到了上個世紀(jì)80年代,生產(chǎn)隊一夜之間成為歷史,被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所取代,分田到戶。恰逢改革開放新時期,那時我工作,我讀書,我寫作,我戀愛。時至今日,我對那時每天騎自行車往來各村屯放貸收儲的情景歷歷在目。1985年初,我所在的鄉(xiāng)領(lǐng)導(dǎo)想通過“招聘”的方式讓我去當(dāng)團(tuán)委書記,縣農(nóng)行卻把我調(diào)到城郊一個鄉(xiāng)鎮(zhèn)信用社任主任,最后的選擇還是在經(jīng)濟(jì)金融行業(yè)。業(yè)內(nèi)躬耕本職,但還是繼續(xù)寫稿投稿。在瑰麗的希望中,我要依靠這支筆面向遠(yuǎn)方,問訊鄉(xiāng)野的同時,仍在尋覓那城市綠樹的枝丫。
坦白說,我那時的寫作,尤其是寫新聞報道稿件,帶有一定的目的和功利性。青澀年華,就想通過寫出點(diǎn)名聲,上邊有人要,找通道離開農(nóng)村,同時還可掙得一些稿費(fèi)貼補(bǔ)家用。時間不長,我調(diào)進(jìn)了通遼縣城,在一家銀行工作。
此地原是蒙古族達(dá)爾罕王的領(lǐng)地。清朝時,康熙大帝和乾隆皇帝都來過這里,乾隆皇帝還留下有“塞牧雖稱遠(yuǎn),姻盟向最親”的詩句。光緒初年,有幾戶漢族人遷到這里開荒,于是便在這茫茫的荒原上出現(xiàn)了一個村落,也有了雞鳴、犬吠、馬嘶……人們給這個村落起了一個美妙的名字——“白音太來”(蒙古語:富饒?zhí)锏氐囊馑迹:笠蜻@兒地處遼河沿岸,故改稱通遼。也算是近一個世紀(jì)的光景,這里幾經(jīng)興廢,稱鎮(zhèn)改縣變市。
早在1982年,我寫了一首小詩《我的希望》,發(fā)表在《中國農(nóng)村金融》雜志上,責(zé)任編輯名字叫汪樂。到通遼后,又在《科爾沁文學(xué)》發(fā)表了長詩《給一位老軍人》。當(dāng)時《哲里木報》不斷地發(fā)表我的新聞稿件和文學(xué)作品。我那時在寫稿子的同時,也斷斷續(xù)續(xù)地讀了一些文學(xué)名著和文學(xué)創(chuàng)作談一類的文章。譬如流沙河的《寫詩十二課》,我將它用牛皮紙包起書皮,后來還是被一位同事借走,再也沒有回到我的身邊。那時讀書及各種報刊,遇到好文章,每每手抄或剪貼,薈存數(shù)集,便于閑暇間誦吟揣摩。因為熱衷寫作,有機(jī)會接觸了當(dāng)時通遼縣乃至哲里木盟頗有些名氣的徐福鐸、王金堂、郝桂林和劉同樂等,確有許多溫情的記憶和激勵,特別是徐福鐸寫的發(fā)表在《中流》(1990年第8期)上報告文學(xué)《她的中國心》對我后來的報告文學(xué)創(chuàng)作影響較大,作品中人物美好的心靈始終蟄居在我的靈魂一隅。
1991年,我調(diào)到了首府工作,在一家國有銀行先是做小報編輯,之后,又在一家全國性的行業(yè)報當(dāng)上了記者。記得那時,在呼和浩特的街頭巷尾,隨處可見拂地的垂柳隨風(fēng)飄舞。特別是中山路兩側(cè)的柳樹,那份裊娜,那份風(fēng)姿綽約,更讓青城平添了許多色彩。更多的精神體驗人也自然隨之輕盈了許多。每座城市都有屬于自己的性格和表情,從不同的建筑中解讀城市的神態(tài)和氣韻,在和人們的接觸中感受他們的生活態(tài)度與憧憬。
科學(xué)在于發(fā)現(xiàn),是猜想,研究的是物;文學(xué)在于情感,是聯(lián)想,研究的是人。我后來對寫報告文學(xué)的興趣愈來愈濃,漸漸地對故事、對美、對趣味,有了新的思考。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歌詠行業(yè)的人和事,并得以有機(jī)會走遍內(nèi)蒙古的大小旗縣,對北方的草原、山林、沙漠等諸多圖景都留下很深的記憶,自然也就有了許多的隨想,特別是對“公宴”“會議干部”諸如此類敢于鞭撻,并開始關(guān)注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惡化,對“沙暴”產(chǎn)生了憂慮。陸續(xù)發(fā)表了《建新之路》《呵,呼倫貝爾》《草原沉思錄》和《守望阿拉善》等作品。后來,又完成了電視政論片《大地·金魂》的解說詞和紀(jì)實散文《“中英街”隨想》。
其間,1993年,我被總社派往革命圣地延安采訪,寫出了報告文學(xué)《延安,世紀(jì)末的渴望》。該文發(fā)表以后,引起了較大的社會反響。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里,該報就收到全國各地為延安“希望工程”許多捐款,僅江蘇徐州市一家銀行職工就捐款5萬多元。這篇作品在這家報社當(dāng)年的好作品評選活動中獲得了一等獎。時任自治區(qū)文聯(lián)副主席哈斯烏拉以《作家的責(zé)任和良知》為題發(fā)表了一篇短文。現(xiàn)輯錄于此:
當(dāng)“用優(yōu)秀的作品鼓舞人”成為黨和國家對文學(xué)創(chuàng)作亮起一面鮮麗旗幟的時候,所有“經(jīng)營”文字的工作者,都回首追尋的屐跡、翹望迢迢征途,以作家的責(zé)任和良知面對時代,面對生活,面對紛繁的選擇。
似有一面亮亮的期待,照映著年輕的蒙古族作家尹光磊。他時時背負(fù)著歷史的重托,深情而剛毅地掮起屬于自己的責(zé)任——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以虔誠于生活的良知,把盛世的美好和世紀(jì)的渴望濃濃地集于筆端。
當(dāng)十幾年前便熱衷于金融和文學(xué)的尹光磊,在去年以尋找輝煌為己任,深入到并不遙遠(yuǎn)的“紅都”延安后,以作家的機(jī)敏和慧眼,在“白云”姑娘交不起50元學(xué)費(fèi),窘迫中凄然賣血求學(xué)的感召下,毅然選擇了探索坍塌的校舍和“聰明”們的心靈。面對四千多失學(xué)兒童,他感到自己的心似欠債般的顫抖,于是他看到了貧窮的罪惡和未來的希冀。這篇《延安世紀(jì)末的渴望》如泣血的杜鵑,講述著那一片黃土地的輝輝煌煌和仍未治愈的沉疴。
一篇傾注心血的文章,理應(yīng)得到社會的贊譽(yù)。當(dāng)我得知,由于這一腔“渴望”,能使全國各地特別是金融戰(zhàn)線的職工傾囊相助,許多捐款已匯至延安地區(qū)的“希望工程”。看到這一切,我作為《延安,世紀(jì)末的渴望》作者的故舊和文友,與他分享快慰,并不斷審視自己的責(zé)任和良知,為哺育我們的人民一輩子多做好事,多做實事。勤奮筆耕,為社會多奉獻(xiàn)豐富的精神食糧。
1994年9月,中國作家協(xié)會《民族文學(xué)》雜志社、內(nèi)蒙古文聯(lián)與作協(xié)聯(lián)合召開了“尹光磊報告文學(xué)作品討論會”,這一年的12月我加入了中國作家協(xié)會。翌年當(dāng)選為內(nèi)蒙古第五屆作協(xié)全委會委員。
1995年上半年,我在總社的安排下又到南方一些發(fā)達(dá)地區(qū)進(jìn)行采訪,寫出《托起金夢之光——當(dāng)今三大金融投資熱潮透視》和《大上海,飛翔的金融夢》等多篇報告文學(xué),陸續(xù)在《金融時報》等有關(guān)報刊上發(fā)表。1995年12月30日《中國城鄉(xiāng)金融報》第四版江蘇鎮(zhèn)江一位讀者來信——給“老記”們捎句話:“尹光磊是草原的遼闊注定孕育出你雄渾的氣魄。”這句話,直到今天還在鼓舞和激勵著我。
將近十年的時間,我立足于金融事業(yè)搞文學(xué)創(chuàng)作,有了許多留存記錄,在出版《寶和軒文存》之前,我曾在沈陽出版社、內(nèi)蒙古人民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等幾家出版社出了7本小書,大多開本較小,裝幀樸素,有幾本還是鉛字印刷的。《寶和軒文存》是我從這些書當(dāng)中篩選形成的,多為舊作,未作修改,只是增加了兩篇文章,其中包括《中國環(huán)境報》責(zé)任編輯冷霜早些年給我的一封來信。后來,我又當(dāng)了記者站站長,連續(xù)兩年被評為該報的“十大優(yōu)秀記者”之一。1996年,被《法制日報》社評聘為主任記者職稱。
懷揣夢想,落實規(guī)劃,通過不停地找尋,我的人生已悄然發(fā)生了變化。因為始終走在追尋的路上,成長就這樣發(fā)生了。告別舊我,獲得了心性的明朗與開闊。寫作,是一種打撈和提煉,需要有足夠的耐心和沉浸。在人生的萬千形態(tài)中,自由率性的生活方式,無疑是最有吸引力的一種。
共老
我們住在依山瞰海的星海長島。圍合的建筑分布,沉穩(wěn)內(nèi)斂,各種樹種編排其間,有的樹冠廣展,有的矮墩墩擠成一團(tuán)深綠。圍合著兩塊不小的綠地,連同透著美感的雕塑。背靠區(qū)域地標(biāo)摩天大廈,左依蓮花山,右傍馬欄河,南向不遠(yuǎn)處便是無邊無際的海。
出了小區(qū)西門,便是馬欄河運(yùn)動公園。在長長的環(huán)形跑步道上,偶爾見到三五結(jié)隊慢跑的年輕人,卻常見鍛煉的中老年人。一對對上了些年紀(jì)的男人女人,不時從身邊走過,有的走著走著,便在青灰色的石階或木制長椅上坐下來。看著他們很少熱烈地說著什么,或仰望或凝視,仿佛在回望或盼望著什么。生活是每一天都要過的日子,人們就這樣一路走來。
愛人已退休,仍舊有一種清雅高華之美,豐潤飽滿的臉上,化著淡妝,晚上拍臉、貼面膜,像是功課。一段時間以來,妻子常常染發(fā)。原本黑黑的頭發(fā)里已經(jīng)埋藏了很多白發(fā),究竟是怎樣一根根悄悄變白的?
她幫襯了我大半輩子,對子女更是投入了最溫存細(xì)膩的愛!家居蓮花山一脈,使我想起佛經(jīng)用來形容蓮花的四個詞:“一香、二靜、三柔軟、四可愛”,其純凈明艷,寬大的荷葉像一把遮陽的傘。去年,我請求去職下派,減少了很多做總行高管時的忙碌。工作之余,接續(xù)文緣,總有讀不完的書。
我們決定出來,然后再經(jīng)常走走,機(jī)緣巧合來到這兒。早上,燦爛的陽光撲進(jìn)來,我打開窗簾,看窗外那片現(xiàn)實的風(fēng)景。過往的記憶,在時過境遷之后,就像黑白照片一樣,帶著原本的美感,已轉(zhuǎn)化為心酸而甜美的回憶。
和她相識,是我一生最美的遇見。上個世紀(jì)80年代,它永遠(yuǎn)存在我的夢里。原哲里木盟通遼縣最東部,一個小小的鄉(xiāng)村,與愛人經(jīng)熟人介紹相識,繼而便是愛的溫?zé)崤c萌生的理想交織,一切都是那么柔軟而干凈,所期許的更多的是詩意和遠(yuǎn)方。
那是一個暮春的夜晚,我走進(jìn)媒人的家里,去開始一場老式的相親。岳父岳母先前就到了。其實,岳父是真正的媒人。那天我身著藍(lán)色中山裝,頭戴灰色的前進(jìn)帽,在炕沿落座后莫名其妙地還抽了幾根煙。待她出現(xiàn)時,我一下子怔住了,這時我看到:一個梳著干練短發(fā)、姿態(tài)優(yōu)雅、容貌美麗的女子走了進(jìn)來……這一幕構(gòu)成了永遠(yuǎn)的瞬間。她在屋里走過來走出去,我們相互看見了,相互微笑,然而無言。
岳父是他們那個公社村屯中最有威望的鄉(xiāng)賢,寬厚仁慈,多年來不論哪家有個大事小情,他都被請去做執(zhí)事。誰家和鄰居鬧了矛盾,哪家兄弟們分家,他都去主持,說些公道話。去年冬月,他過世了,追憶潸然。
我和愛人結(jié)婚快35年了,縱然是生活里有許多的磕磕絆絆,這就是互相在意的生活,內(nèi)心并不缺少恩愛的元素。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樣樣都是她打點(diǎn),家里方方面面都是她在料理操持。她為我和我們的孩子付出了太多。愛人,原來是最高檔的保姆、全方位的CEO,只是沒發(fā)薪水而已。
我們在一起我很少被要求做家務(wù),吃完晚飯,筷子一丟,潛回書房,裝模作樣。生活當(dāng)中有她對我的提醒、勉勵和期許。年輕時,還幫我抄過稿子。她是我生命的運(yùn)氣,從我見到她的那一刻起。只是,我很少這樣說。如果我們是夫妻,不是怨偶,我們會朝夕相處,會同船共渡,會如影隨形,會爭吵、會和好,會把彼此的命運(yùn)緊緊纏繞。
因為有你,所以美好,生活當(dāng)中處處展現(xiàn)出溫煦和甜美。因為你的善良,或者說是全部的愛,還是因為愛而激發(fā)的無與倫比的耐心,我們常常得到的不是一時的一屋子的陽光明媚,而是那份持久的愜意和迷醉!看看周圍白頭偕老的夫妻,無一不是因為相互欣賞相濡以沫因情而長久的,這種情是親情加恩情!后來才知道,原來愛情必須轉(zhuǎn)化為親情方可持久。
妻說即便老了,我仍然選擇善良。因為她明白,因果不空。她的胸襟大,感情深重而執(zhí)著,她的生命如此大吐芬芳。樂者心自怡,她的孝道、仁慈不動聲色。近來我注意到她的動作慢了,毛病增多了,她常常需要一句輕柔的話、一個溫暖的眼色。看著妻子,我想起一個詩人這樣的詩句:“如果一個人慈若花朵/悲若春雨,那么/你就是先覺/不是佛也是佛。”
黃昏來臨,一側(cè)的山的形狀更加篤定而清晰,腳下的河像一條發(fā)亮的絲帶,如萬片碎金動蕩閃爍。
老,不會放掉任何人。我們相視而笑,我們的眼睛不如以前明亮了,頭發(fā)變白且稀疏見頂了,皺紋從額頭拉倒了嘴角。我們經(jīng)歷了很多,這種人生由淡淡的悲傷和甜甜的幸福組成……
日子是自己的。日子依舊,人心依舊;觀世安穩(wěn),歲月靜好。每個人都有屬于自己的生活,都值得精心對待,都值得放進(jìn)足夠的美、浪漫和溫暖,畢竟人生無法從來。
正如早些年,我們一起在森林公園見過的兩棵銀杏樹,同承雨露,共斗霜雪,共生共老,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