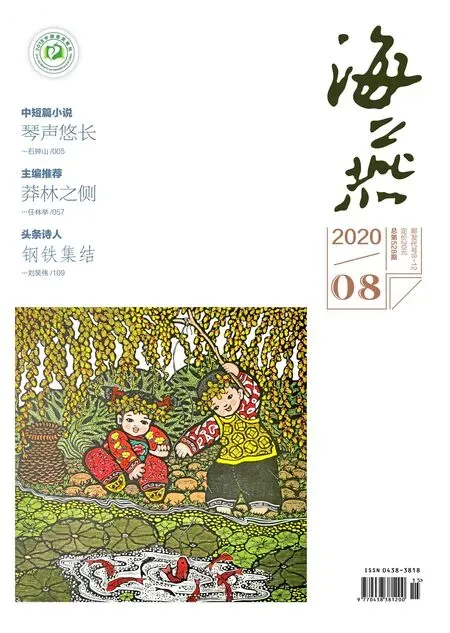黃昏里的男孩
文 劉鵬艷
我是在一個夏日的黃昏抵達小鎮的,鎮上沒有我想象中那種熱火朝天的喧騰,但也并不特別枯寂。有一些人走來走去,三三兩兩的,偶爾會說上兩句話,顯示出生活的盲目和隨機。一些攤子不規則地散布在街邊百無聊賴,覆蓋著經年的灰塵,飲料盒、方便面袋子、明星畫片和廉價小首飾上都落滿了一層可疑的歲月的證據。如果我不翻看手機上的日歷,會誤以為穿越到了上個世紀,這樣我就走在上世紀的邊境小鎮上,見證了某種在時間深處逝去的風情。
我身上的背包已經有些破舊了,這些年我背著它走遍了邊境線上的每個小城鎮,在每一處經過的地方徘徊彳亍,像警犬一樣用鼻子去偵緝每一種可能。但都一無所獲。我沒有灰心,我很小的時候就啟動了我的決心,不找到他決不罷休,就算這輩子沒可能見到他,總還有下輩子,下下輩子,我就不信他躲得了那么久。除非他從未存在過。
他當然存在。這個混蛋!我母親這么罵他,他當初來到她的世界里向她求歡,茍且之后還有了我,但不久之后就消失了,像從未存在過一樣。我母親告訴我,你不如當他死了。我卻從小伙伴的嘲笑和街坊鄰居的竊竊私語中理解到另一種含義,他沒死,還活得好好的,只不過換了個地方,換了種身份。這些我都不在乎,我只是想知道他到底長什么模樣。每個人都有父親,我也不例外,所以我想看一眼我的父親,告訴他:“我從一出生就開始找你了。”然后從他面前昂然走掉。
一刻也不停留地走掉。
據說我父親給了我一雙三角眼,還在我臉上留下一掛香腸似的厚嘴唇。看到這些我母親就生氣,但她又沒辦法不喜歡我,因為我挺直的鼻梁、濃密的眉毛和近乎完美的流線型鵝蛋臉都是她的杰作。她把我父親的照片都燒掉了,所以我只好對著鏡子里的三角眼和厚嘴唇在心中摹繪他的樣子,以便多年之后走遍千山萬水去尋找這個莫須有的男人。
他曾經出現在邊境的某個小鎮上,這是我得到的唯一有價值的線索,所以,我把邊境上的小鎮都走了一遍。得到這個消息,還是二十多年前的事,那時我七歲,有人勸我獨居多年的母親往前走一步,因為“那個混蛋已經在那邊有了老婆孩子”。我母親沒說相信,也沒說不信,她只是抓住剛從門外瘋玩回來的我,使勁地用一條濕毛巾在我前胸后背和大腿小腿上抽打附著在衣服上的灰塵,啪啪有聲,邊抽,邊罵:“你還知道回來呀,你怎么不死在外面!”說實話,我母親抽我的力度還不夠我淌眼淚,所以我只是扭著身子,嗷嗷叫喚:“二蛋他們都回家了嘛,我也回來吃飯嘛。”我母親氣極反笑:“你倒不傻呀,知道吃飯要找親媽。”
這印象極深,我好像就是從那時候起,知道親媽和后媽是不一樣的,推而論之,親爸和后爸大概也不能一樣,所以我母親從未起過心思給我找個后爸,我非常尊重她的選擇。
我母親把我養到十八歲,我如愿以償地考上大學。
其實也不是我如愿以償,應該是我母親如愿以償。她多年的心愿就是培養一個優秀的兒子,考大學能證明我的優秀,所以她十八年來的努力都是朝著這個方向做加速運動,越是逼近高考,越是加強教育:“你長點出息,好好考哇!”
我考得不錯,她笑了,笑的時候細密的魚尾紋在臉上蕩漾開來,我忽然發現她那張好看的臉竟滄桑得猶如盛唐時代留下來的敦煌壁畫,隨時要剝脫的感覺。
果然,她笑著笑著,眼淚就掉下來了,一個字、一個字莫名其妙地往外蹦:“你看我把你兒子養得多有出息,你看不到了吧?你沒那個福氣!這是我的兒子,我的!”
我看著我母親,她的帶淚的笑和帶笑的淚都讓我惶惑,這么多年,我還以為她把我父親忘掉了呢。她很少提他,提起來也是捎帶著鄙夷和不屑的表情,好像有他沒他都那么回事兒。“想你爸嗎?”她心情好的時候也會問我。“不怎么想。”我通常都這么回答。因為確實不知道想父親是怎么一回事,好像打我記事起,父親就已經消失了,根本沒來得及在我年幼的心里埋下思念這種玄妙的東西。
但我知道我是有父親的。
這個執念一直陰魂不散,以至于后來好長時間我都無法放下。大學一畢業,我就開始策劃如何尋找父親。我母親聽說后,瘋狂地笑起來:“你找他?你找他干什么呢?你需要一個父親的時候已經過去了,現在你的任務是找個好老婆,然后自己成為一個父親。”
我承認我母親說得極有道理,她獨自一人把我培養成大學生,就說明她是一個多么明理的人。她不會被感情左右。她總是跟我講道理。她說自己年輕的時候,因為不講道理,光講感情,所以吃了天大的虧,這個巨大的虧空,一輩子都難以彌補。
我聽了我母親的話,暫時放下了尋找父親的念頭。倒并不是我信服她的道理,而是,我不能違背她的感情。這還真是矛盾。
一直到兩年前,我母親無疾而終,我才終于把藏在床底下很多年的背包掏出來。
說起來我母親是個有福氣的人,她在睡夢中笑著上了天堂,這回臉上沒有掛著斑駁的淚。她這一輩子走得艱難,但并不像別人想象中那么壓抑。她是個敢愛敢恨敢哭敢笑的人,認準了一條路,就閉著眼走到黑,心無旁騖,目不斜視,倒比常人多出十分的簡單和痛快。我平靜地葬了她,平靜地背上包,踏上尋找父親的旅程。
我在一個夏日的黃昏抵達了邊境小鎮。這個小鎮和我走過的無數個小鎮沒有什么區別,平庸,瑣碎,人和物事都鍍著一層氣味陳舊的包漿,摸上去又滑又涼,像是被時間扔在深處的一條蛇。
這條蛇早就僵死過去了,任后來在它身上加諸什么樣的創傷,都沒有任何生活反應。直到一個男孩從黃昏的小鎮上跑過,它仿佛一下子蘇醒過來,嘶嘶地吐著信子。
啊嘔——啊嘔——
男孩一邊跑,一邊發出這樣暢快的聲音。我看著他在一輪下墜的太陽上面奔跑,腳底生風,像是踩著風火輪的紅孩兒。只是沒有兩條小辮兒,他頂著個西瓜太郎的發型,齊劉海兒蓋在腦門上,無論從前后左右哪個方向看過去,都像扣了半個西瓜。
他跑過的時候,我們倆短暫地對視了一眼,相互都有些吃驚。
好像是照鏡子的感覺,我看看他,他看看我,一雙三角眼和一掛香腸似的厚嘴唇,在彼此的瞳仁里油然而生,竟然那么自然。
不過他跑得太快了,我還沒來得及招呼一聲,他已經從我眼前倏忽而過,小馬駒兒一樣撒著歡跑遠了。我就這么怔怔地看著他一路遠去,在視線里一點點變小,越來越小,越來越小……當他變成一粒豌豆那么大的時候,忽然一陣濃重的睡意席卷了我,我心想壞了,剛想伸出手去,把那顆豌豆拈起來,咕咚一聲,我向后栽倒,就這么在馬路邊上無遮無攔地睡著了。
醒來時天已經透黑,我打算從地上爬起來,卻發現自己睡在一張柔軟的床上。有人推門進來,擰亮了燈。橘黃色的燈光灑下來,照在粉藍格子床單鋪就的床沿上,幾乎是同時,一個溫柔的聲音和燈光一起落下來:“你醒啦?”
我抬起身子,望向那張秀美的臉,鼻梁挺直,長眉入鬢,光潔的額頭在燈下折射出圣母般的光暈。我尷尬地笑笑:“不好意思,我有發作性睡病,給您添麻煩了。”
她“哦”了一聲:“我還以為你暈過去了,怎么還有這樣奇怪的病?”
“是有些奇怪,”我揪著床單說,“這很難解釋,也許有遺傳的因素。”
“你父親也這樣?”
“不知道,在我母親印象中好像沒有,不過他們在一起的時間很短。”
她表示理解地笑了笑,轉而問我:“這樣挺危險的吧?”
“是有點,不過至今我還活得好好的,這得感謝你這樣的好人。”
就在我向她表示感謝的時候,一個孩子滿頭大汗地跑進來:“媽,他醒了嗎?”
我們的目光撞在一起,那孩子一副驚喜的表情,我朝他點頭笑笑。
“這是我兒子藍朵,是他叫人幫的忙。”她把那個男孩拉到身邊,目光里盛著母親的贊許。男孩有些不好意思地躲在母親身后,越過他母親的肩頭,閃閃爍爍地向我望過來。
“你頭上磕了一個大包!”他雙手圈出一個“雞蛋”,比劃著對我說,“有這么大。”
這是個很健談的小男孩,喜歡恐龍和各式戰斗機,和我聊起侏羅紀和二戰的時候頭頭是道。不久我們就廝混得相當熟絡。“藍朵,”我鼓勵他,“來一段兒吧!”這時候他就會聲情并茂地背上一段《空中大戰》的解說詞:
——漢斯,我打中他了!
——別著急,它跑不了。
兩架梅塞施密特戰斗機正在圍攻一架蘇聯海鷗戰斗機。援兵意外出現,另一架海鷗戰斗機趕來援救,并向敵機發起了攻擊……德國人停止了對受損戰機的攻擊,轉向新的目標。蘇聯戰機已經身中數彈,但梅塞施密特戰斗機仍無法將其擊落。駕駛海鷗戰斗機的是列奇卡洛夫中尉,他在戰爭爆發的第一天就接受了戰火的洗禮……
“藍朵,你長大了是想當飛行員嗎?”我問他。“不是啊,我想當主播。”這個理想倒是讓我有些訝異。“你是說做一個播音員?”我向他進一步確認。“那多沒意思,要和粉絲互動哇,天天有人打賞才好玩呢。”他興高采烈地搖著腦袋,全然不顧母親在一旁打擊他的積極性:“你就不怕被人扔臭雞蛋吶!”“不怕呀,我可以扔回去,嘻嘻。”
據說七年前藍朵的父親就跑到境外去了。
“在歌廳里玩,不知怎么就和人戧起來,結果失手捅了人,只能跑出去。”藍朵的母親提起自己丈夫的時候,臉上的表情很模糊,看不出是悲是喜,是憂是懼。這個粗糙的邊陲小鎮缺乏精致的故事,人們迫于生活在邊境線上跑來跑去,誰家也不特別在意別人的閑事,諸如隔壁突然多了一個外埠新娘,或者對門的男人討了兩國老婆,這樣的事當閑話傳兩遍就味同嚼蠟了,怎耐得住經年累月的磨蝕?到最后這些新聞都成了舊聞,漸漸變成生活本身。藍朵的父親就是這樣,提起他,所有的人都已經很平靜了,包括藍朵。
藍朵說父親走的時候他有三四歲了,是有些印象的,父親把他扛在肩膀上騎大馬,使他比父親還要高些,能看到很遠的地方。后來父親離開他們,母親就不能夠做這樣有趣的游戲,實在是很遺憾。不過母親有母親的辦法,她和藍朵扮演劍龍媽媽和三角龍寶寶,分食家里僅有的幾枚爛蘋果,這樣就連上門討債的人都不好意思再找他們母子的麻煩了。被藍朵父親捅成重傷的那家人,又哭又罵地堵在門前,藍朵母親低著頭說:“你們看家里有什么值錢的,就搬走好了。”她抱著藍朵,坐在門口的小凳上,老老實實、清清白白的。人家看看他們母子,又看看空蕩蕩的小屋,砸了一臺破電視機出氣,終于走掉了。
家里那臺舊電視機被砸掉之后,藍朵就沒有動畫片看了。所以他還是恨那些人。母親告訴他:“你莫要恨他們,你可知道,人家的爸爸因為你爸爸再也起不來了,全家人都傷心得很哩。”藍朵說,“那我爸爸呢?”“他呀,跑出去掙錢唄,掙了錢好還人家呀。”“那要掙多少錢呢?”“很多很多的錢,所以一時回不來了。”“一時是幾時?”“三五年吧,或者更長一些……”如今,藍朵扳著指頭算起來,父親離開有七年了。那真是很大一筆錢,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還得清。如果還不清,父親就不能回來,他覺得自己當了主播的話,賺錢可能會快一些。
藍朵母親望著兒子笑,但是從側面看過去,可以看到她發紅的耳根后面,幽幽地沉淀下來一些苦澀的渣滓。
我起初賠著笑,越笑越勉強,終于笑不下去,只覺嘴里發苦,睡意朦朧。毫無征兆地,我又咕咚栽了下去。恍惚中我那已經安息在虛無中的母親和眼前這位年輕的母親疊成了一架重影的老式戰斗機,留在我腦際的最后一幕是,她們的機翼都遭受了重創,在蒼灰的天幕上費力地拉出一道滾滾濃煙,但仍苦苦盤旋著,久久不愿墜毀……
我回到了我母親身邊。她拿著一條濕毛巾,一邊用力抽打我的褲腿兒,一邊高門大嗓地教訓我:“長點出息吧,瞧這一身的灰!”
她抓住泥猴子一樣的我,把我摁在書桌前。“還有幾天考試,嗯?你算算還有幾天?”她的眉眼里滲出焦慮憂傷的企盼,拔絲般的破音讓我的心尖兒不由得發顫。我捧起了書,把成串的公式和符號往腦子里塞,然而并不能集中精力。它們太狡猾了,往往是我把這段兒剛塞進去,那段兒又流出來了。我的腦殼變成了被洞穿的腹腔,那些公式和符號組成的編碼串兒仿佛不斷流出體外的大腸。我抓了一把,又抓了一把,皺著的眉頭痛苦地鎖在一起。上了鎖就好了,外面的人進不去,里面的人也出不來。虛空中有股硫磺味兒,熏得我母親跌了個筋斗,她一邊叨叨著,一邊走出房間。留下的話把子被我捏在手里,她說:“你把書吃掉吧。”我是不怕吃書的,我怕消化不良,我一緊張就消化不良,已經拉了幾天肚子。我母親給我燉了雞湯,一絲不茍地用勺兒舀掉了最上面的一層金黃色的油花,以為我會受用一些。不過我的肚子不如我的腦子會耍滑頭,它那么誠實,依舊拉個不停,一點兒也不認為對不起她。
我母親這些年付出了太多值錢的東西,青春,耐心,好脾氣,體面的婚姻,一一都投注在我身上,換算出來就只剩下大寫的“出息”二字。因而我必須考上好大學,讓身邊的人都看看,我母親的兒子多么有出息。我甚至沒資格對我母親說一聲對不起,要是我這樣說了,我母親說不定會歇斯底里,扯著自己的頭發大哭,把對我父親的怨艾和對歲月的仇恨都化成一支支穿腸毒箭,射得我體無完膚。不過此刻,我不是已經腸穿肚爛了嗎?我滑稽地看看自己的身體,沒有創口,卻有黏稠的異質流進流出,在這個無數莘莘學子摩拳擦掌的夏天,它發出濃烈的惡臭。
去學金融吧。這是我母親給我的建議,她認為這個行當日后一定有前途。金融這個詞兒,她大概也不是很明白,不過用老百姓的大白話來講,應該就是錢。有錢是好事兒,這些年她為了錢吃盡了苦頭,天然地好這一口兒。說起來,一個單身女人拉扯一個孩子,太不容易了,雖然不完全是錢的事兒,但總覺得缺錢。“要是有錢就好辦了,”她總是這么跟我說,“我能給你找最好的補習老師,上最好的學校,做最好的教育規劃。再往后,你自己就知道路怎么走了,做人上人,找份好工作,別人見了都夸,說你媽教育得好,有出息。”
這簡直是她的宗教。
我是沒辦法篡改她的宗教的。她用十八年來創建、鞏固和發展她的教義,到如今冰凍三尺,堅硬如鐵,我只能奉為圣經,專心修煉。不過我始終在尋找機會,幻想來一次破冰行動,哪怕停留在意淫的階段,對我的人生終究是一種可貴的“求真”。多年來我不斷被我母親催眠,她要求我做人一定要首先“求實”,求實的意思就是以解決眼面前的問題為第一要務,該讀書的時候讀書,讀出好成績;該工作的時候工作,找份好工作。
她又來給我送雞湯了。
我正為背不上來昨天剛記下的單詞而心煩意亂,看到雞湯,煩得不行,手一揮就打翻了湯碗。當啷一聲,母親的心似乎碎在地板上,愣住了。我也嚇了一跳。我的本意不是這樣的,我只是想讓她把它端走,就連揮胳膊的距離都是經過目測和心算的,沒想到正中她的雞湯,像是急于打翻一碗毒藥。
空氣凝固在那個點上。
現在回想起來,高考前我的那場噩夢似乎還在繼續,既沒有終點,也沒有起點,就那么無始無終地漫漶在時間軸上。也許從我一出生就開始了,要么可以追溯到更遠,我父親還沒來得及向我母親求歡之前,我母親悄悄芳心暗許的時候。轉過身往后看,可以看到更遠一些的地方。我二十歲,我三十歲,我老了,我在生命的盡頭,我等著一場莊嚴的謝幕,等著命運向我道歉。但沒有,沒人向我承認錯誤,我只好歸咎于自己的懦弱和無能。
遙遠地凝視那個十八歲的年輕人,我撫觸著他身上看不見的創口,溫柔地告訴他,你跳下去吧,你有權利這樣選擇。然而年輕人不敢,他覺得他沒有這個權利,他的母親含辛茹苦,受盡人世的奚落和歲月的侮辱,他如何辜負?就這樣,他痛苦地徘徊在閃爍著“中國人民銀行”幾個霓虹大字的金融大廈的天臺上,徘徊了一整夜,終于還是從樓梯間一級一級地走回地面上。
母親并不知道這驚心動魄的一夜,反正這么多年他已經體貼地隱瞞了很多內心的秘密,也不在乎夏夜里這么一場不為人知的隱秘廝殺。廝殺的結果是,他心里那個“求真”的小人兒被暫時殺掉了,只剩下“求實”的小人兒,躊躇滿志地陪著他上考場,不,確切地說,是殘酷的戰場。
那以后,正如他母親所說的,一切都順了,他只要按著這條路走下去,就好。他愿意人們圍著他的母親贊嘆,“嚯,你兒子真有出息呀!”或者,羨慕地討教育兒方法,“你怎么能養出這樣好的兒子?”他的母親呢,在人群里笑瞇瞇的,一副心滿意足的表情,微微地還有些得意,覺得這輩子值了,真是揚眉吐氣。他也笑起來,心底卻有苦澀的沉渣泛起,倒是和多年后他在邊境小鎮上遇到的另一個單身母親的笑容有著某種神似。
我再次醒來,藍朵站在床邊,正伸出一根手指,放到我的鼻子底下。和睡癥發作時一樣,我睜眼的時候毫無預兆,藍朵的西瓜皮腦袋突然塞進我的視野,我們倆都嚇了一跳。
“你睡了整整一天吔。”藍朵的聲調夸張地往上揚,眉毛也跟著跳起來。他說我突然又睡著了,不過這回他們知道我的毛病,就沒上回那么擔心。可是我睡了那么久,他又不得不來試探我的鼻息,看我是否還活在夢里。這真是個善良的好孩子,我摸摸他的頭,柔順的黑發從我指間穿過,像是穿透一眼清泉。
我們倆已經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說起來算是忘年交,但我覺得他就是我的弟弟,或者是另一個我。我問藍朵,有沒有想過去找爸爸?他搖搖頭,不用找呀,他會回來的。我很奇怪他為什么這么篤定,他說爸爸不回來還能到哪兒去呢?他現在不回來是因為他要掙很多很多的錢還給人家,如果錢還上了,他還有什么理由不回來呢?我一時難以回答他。
確實,我回答不上他的問題。我打小兒思考的問題就是,如果父親不回來,我是不是該去找他。還從來沒想過,父親總有一天會回來的。
我要告訴他,一個成年人選擇回家或者不回家,總是有很多理由,甚至不需要理由。我說不出口。藍朵相信他的父親總有一天會回來,他的母親就是這樣帶著笑容告訴他的。所以我也愿意相信。藍朵還看不出母親的笑容里滲著淡淡的哀婉,那朵長在母親臉上的微笑在陽光下總是閃閃發亮。他的母親善解人意,我和她聊起我母親時,她也往往露出理解和寬容的微笑。我不禁無稽地想,如果她是我的母親,也許我就不會在邊境線上徘徊至今。
一條線而已。
但是我怎么也跨不過去。
藍朵像他父親,他拿了他父親的照片給我看,儼然是成年的藍朵。相比起來,我和藍朵的那幾分相像,更像是影子的影子。我們第一次相遇時那種照鏡子似的驚訝,現在已經變淡了,優柔地彌散在黃昏的空氣里。
我先前覺得藍朵的母親和我母親也有幾分相像,后來仔細再看,除了挺直的鼻梁,她們很少有像的地方。她們是兩個如此不同的母親,而我和藍朵,是兩個如此不同的孩子。
“還繼續找下去嗎?”藍朵母親問我。她知道了我的故事之后,很同情我不時昏睡過去的身體里那個禁錮了幾十年的執念。她鼓勵我說找找也好,興許就找到了呢。
“要是找不到呢?”我問她。我母親總這樣問我,現在我反過來問這個年輕的母親。
“找不到,就是緣分斷了。”她嘆口氣,“和咱家的情況差不多,回不來,就是斷了。”
“你覺得他還能回來?”
“不知道,他身上背著案子,可能要躲一輩子。那人當年是沒死,可也沒挺過兩三年。年紀輕輕的,到底還是歿了,要不是我家那口子,人家且活著呢……”
聊著話兒,夜就深了。我早先睡過了頭,毫無困意,卻不好意思再拉著藍朵母親閑聊。藍朵已經四仰八叉地倒在床上,占了床鋪的大半邊。他母親笑笑,說這孩子睡覺不老實,你湊合吧。我忙說不打緊的,是我占了他的鋪。他母親就站起來,踢踢踏踏地趿拉著拖鞋回另一間房去。
說起來,她一個單身女人,膽子竟不小,敢讓我留宿在這里。
“昨晚上,你睡也睡過了嘛。”她跟我開玩笑。推來推去,收了我五百塊錢,算作酬謝和這兩晚的住宿費。“我看你和藍朵也有緣,他和你親得很。小孩子精怪著呢,他既然留你,我也不怕你住下。”她笑笑,坦蕩蕩的。
我在燈下支著頭想心事。
好多年前的事了,一樁一件地涌上來,摻在迷蒙的夜色里,像兌了水的酒,饒是隔著久遠的歲月,還是讓我暈眩。我想不出我父親的樣子了,但知道他有一副高大的個頭。也許是我的想象,我母親連我父親的照片都銷毀得那么徹底,當然不會和我聊他的身材。我只是憑空覺得那是一個高大的父親。小時候胡亂猜測,長大了以后,看到鏡子里長手長腳的自己,越發肯定那個男人的基因在我身體里是空前活躍的,因為我母親個頭嬌小,不說話的時候像只蜂鳥。但她很少不說話,一旦說起話來氣勢如虹。她用大嗓門跟看不順眼的人吵嘴,用大嗓門教訓我,還用大嗓門討價還價。她有很多女朋友,那些女朋友有的和她一樣沒有丈夫,有的有丈夫卻跟沒丈夫一樣,她就指導她們和她們的丈夫做斗爭,說想要過好日子就得兵不厭詐。我奇怪她怎么會有那么豐富的斗爭經驗,若論起來,她在實踐方面基本上是一窮二白,但她給她的女朋友們開家庭務虛會,提供的理論指導往往讓女朋友們茅塞頓開。她一輩子也沒個正經工作,但說起話來條理清晰,以點帶面,像個工會主席,女朋友們都愿意往她這兒跑,我家一度成為婦女集會的中心。
我母親是個偉大的母親,為了養育我,她擺過地攤,賣過早點,倒騰過服裝。她說做買賣靠的是人緣兒,所以,必須以女朋友們的家務事為己任。只要女朋友們喊她幫忙,她從不推辭,像捉拿小三兒這樣的事,往往手到擒來。她把孤兒寡母的日子過得風生水起,沒有一個人敢小瞧她。不過她還是非常鄭重地找我談話,說我們孤兒寡母要被人瞧得起,最終還是取決于我有沒有出息。我要是沒出息,周圍的人就會看笑話:瞧瞧,兒子被她給養廢了吧。那么她這一輩子,就算白活了。我覺得她的邏輯有問題,可又不敢給她挑毛病,對一個含辛茹苦的母親來說,她心里那個比天還要大的問題,就是到底能不能養出個有出息的兒子吧。
她從來沒跟我說過,可我心里明白極了,她人生的大劇里有這么一句頂重要的臺詞:丈夫沒了,她還能扛得住,若是兒子廢了,她的天可就塌了。這天我在金融大廈的天臺上吹著夜風徘徊的時候,想到最多的,就是我母親的這句從沒有說出口的人生臺詞。我從天臺的這頭兒走到那頭兒,亮著“中國人民銀行”幾個霓虹大字的金融大廈像一把劍,筆直地插在市中心那條最繁華的馬路上,往下望一眼,暈得厲害。我到底把跨出去的半只腳剎在了天臺的欄桿上。
大學畢業后,我穿起了西裝,打起了領帶,開始每天出入金融大廈,讓我母親喜出望外。考入中國人民銀行不比考大學容易,但我做到了,接到入職通知的那天,我母親喜極而泣。這就是她心目中“有出息”的兒子的樣子吧,我也笑出了眼淚。我始終沒告訴她,那晚我在金融大廈的天臺上往下張望的復雜心情,也沒告訴她,我每天西裝革履地去金融大廈上班,又懷著怎樣的心情。
一直到我母親去世,我都是她心目中應有的樣子。
太陽升起來了,我背上行囊,準備再次出發。
藍朵追上來問我:“你要去哪里?”
我摸摸他的西瓜頭,望著太陽初生的方向:“去最近的邊檢站。”
藍朵的母親也跟過來送行,往我手里塞了兩個煮熟的雞蛋,笑微微地道別:“祝你好運。”
昨晚在燈下,我做了這個決定,不管結果如何,我要跨過那條線。我辭職出來跑了兩年多,一無所獲,但并沒有灰心,在見到藍朵和他的母親之前,我還對那個藏在心里很多年的小孩子信誓旦旦地說:“我一定要找到他!”可是藍朵和他的母親讓我看清了那個小孩子,他卡在那道生命的裂隙里很多年,一直不肯長大。如今是時候讓他跨過那道生命線了。
我打算過境看一眼,到那邊的小鎮上轉一轉,也許意外地碰到他,也許碰不到,這都不重要了,然后我就返回故鄉,去我母親長眠的地方,繼續做一個務實的人。
做出這個選擇之后我長噓一口氣,像是多年的懸掛有了著落。太陽從背后照過來,我展開手中的地圖,背部聳起的影子在地圖上投下一座山巒的輪廓。目光所到之處,密密麻麻都是匿名的生長。
這條邊境線很長,如果從地圖上看,能夠彎彎曲曲地勾畫出一條驚人的、與生命重合的天然脈絡,但是站在地平面上,它就是與地面無異的一處空白,無論是邊境線的左邊還是右邊,看起來都沒什么區別。倘若行走時沒有那么一座儀程似的邊防檢查站,我都不知道該如何判斷怎樣才算是跨過了那道線。
在出入境檢查處排隊時我有些百無聊賴,拿起手機埋頭瀏覽新聞,突然前方一陣騷亂,層次豐富的大呼小叫、雜沓的腳步和推搡亂作一團。有人高聲喊:“抓住他!”接著是紛亂中的本能,誰在驚恐地奔逃,四下里圍追堵截,摁倒在地,“咔嚓”一下上手銬的聲音。
“就是他!”眾人都圍上去,抻著脖子看值班民警指認一個灰頭土臉的人。
“帶走!”灰頭土臉的人被押著走了,眾人還在抻著脖子看,好像能看出什么名堂。其實什么也沒看見,連那人的面目也沒瞧清楚。有人四面打問,后面的問前面的,左面的問右面的,終于得到確切的消息,說是那人犯了案潛逃多年,在境外換了身份,在當地還娶妻生子,以為時隔多年沒事了,誰知剛入境就被逮個正著。這些信息都是零散的,無聊地碎在空氣里,東一塊西一塊地拼湊起來,恍惚是個大新聞的模樣。大家都有些興奮,仿佛自己見證了什么偉大的奇跡。
輪到我了,檢查人員敲著玻璃問我要證件,我還張著嘴陷在震驚里。不會是藍朵的父親吧?我沒來由地想,竟有這么巧!也可能不是,都七年了,我剛打算出境,正碰上他入境?我腦子里一團漿糊,想著藍朵,想著藍朵的母親,和剛剛被押走的這個面目模糊的男人有什么關系?有個小孩子溺水似的從時間的洪流里掙扎著冒出頭來,他的母親在岸上費勁地執著一個長柄的尼龍網,大概想用這不趁手的器具去撈他,無奈怎么也撈不起。另有一個面目模糊的男人飄過來,踩著看不見的滑輪,飄飄忽忽地,腳也隱在虛空里,像鬼魅。他離得近,看著小孩子卻不伸手,就這么看著他越掙扎越徒勞,漸漸地沒了頂……
咚咚地,又有人敲玻璃,證件從小窗里遞出來,我一驚,接過來點頭哈腰地往外走。走到外面,一抬頭,看見天,還是那片天。回身望望,邊檢站卻是在身后了。那么我是走過來了。那個人呢,他也走過去了吧?
總歸都是在那條邊境線上發生的事,我抱著腦袋琢磨,那條線,有人想過去,有人想回來,都犯難。這時候,邊境線就不是邊境線了,成了心里的坎兒。人要是邁不過那道坎兒,就得兜兜轉轉好多年。
一晃眼,又過去好幾年。我做回了那個務實的人,像我母親說的那樣,好好工作,找了個好媳婦,成為一個好父親,就連莫名其妙的睡癥,也很少再發作。黃昏時我下班回家,絢爛而柔和的霞光里,有個溢著奶香味兒的肉團子撲過來,摟著我的脖頸子叫:“爸爸。”我給他說他奶奶的事,也給他說他爺爺的事。說奶奶的時候,我信手拈來,滔滔不絕,他坐在我的膝蓋上咯咯地笑;說爺爺的時候呢,我得想想,想到一段兒說一段兒,他也咯咯地笑。爺爺是個大長腿,有勁兒,能把奶奶扛在肩上,奶奶在爺爺肩上又捶又打,可還是被爺爺扛進了洞房;后來有了爸爸,夜里爸爸生病,也總是爺爺扛著去醫院,奶奶一路小跑跟在后面;爸爸病愈以后,就喜歡上了騎大馬,騎在爺爺的肩膀上,比爺爺還高,看得還遠……我漸漸在故事里相信,父親并沒有離開我,他只是換了個方式,讓我長成一個父親。那個叫藍朵的男孩呢,他也長大了吧?不知道他的父親有沒有回家,不管怎么樣,他遲早也會長成父親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