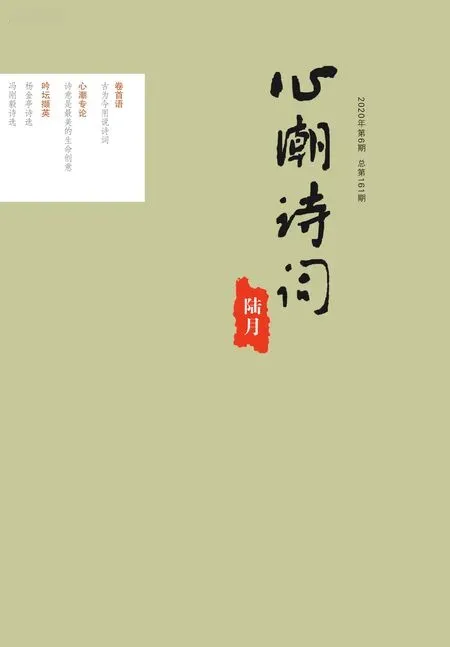古為今用說詩詞
段 維
毛澤東在《致陸定一》這封信的附語中提到了“古為今用”的問題,講的是如何繼承我國古代優秀文化遺產,使之為現實生活服務。那么對于詩詞來講,這句話就更為貼切。因為今天的詩詞依舊保持著形式上的“古體”,這樣今與古更是相互依存,無法分割。
那么我們今天創作詩詞應該怎樣“宗唐尚宋”或是“超唐邁宋”呢?這個設問有點籠統。我們不妨先分析一下唐詩宋詞到底有些什么特點。初唐是近體詩逐步確立的時期,這時律體是新的,比較自由的非律體則是舊的,很多時候新與舊又不易區分。像崔顥的《黃鶴樓》雖被《唐詩三百首》作為七律的開卷之作,其實它是介于七律與歌行之間的一種新舊過渡性作品。我們現在欣賞它,正在于它既有律體的整飭頓挫,又有非律體的質樸渾厚。人們常說盛唐詩氣韻高華,自然渾成,宛如天籟,但我們若是仔細分析盛唐諸家作品,其實也是風華各具的。他們的可貴之處在于能全力擺脫模式,不但擺脫齊梁模式,就是他們自己的創作中也沒有模式可言。一詩有一詩之風格,一詩有一詩之意境。難怪錢志熙教授發出感嘆:“何謂盛唐,此即盛唐;什么叫藝術之盛,這就叫藝術之盛。”其后的中晚唐,詩的整體氣格在減弱,但也并非一無是處。比如在煉字的苦吟方面,在寫物的窮情方面,在技巧的翻新方面,都呈現出局部超出盛唐之勢。對于詞來講,晚唐的“花間調”令詞極盡描寫閨房兒女怨別之能事,婉轉動人,以致具有一種可以使讀者產生對賢人君子不得志于時的幽約怨悱之情的聯想。柳永對花間調既有繼承又有開拓,創制了善于鋪敘的長調慢詞,催生了蘇東坡、辛棄疾具有豪情壯彩的“詩化之詞”。即便如此,蘇辛詞中之佳制,依舊是那些能于超曠豪邁中含蘊深遠、耐人尋繹的屬于詞之特美者。到了周邦彥、姜夔、吳文英、王沂孫的“賦化之詞”,更加注重表達技巧的安排和對情懷寄托的強化,但依舊不脫詞之“要眇宜修”之特質。至此可以說,一朝有一朝的風尚,一人有一人的標格,但詩詞的根脈從來就不是割斷的,優秀的詩人詞家都是結合自己的特點和氣質去吸收他人之長,從而形成自己卓然鶴立的特色。
眼下討論“同光體”比較熱烈,眾說紛紜。其實,在清末民初詩壇,對“同光體”的論爭就沒有停歇過。比如對其代表人物陳三立的評價,就陣線分明。如傅尃在《說詩一昔話》云:“七律莫盛于唐,宋代繼之,遂開新響。山谷,其一大宗也,近人惟陳散原能為之。”而柳亞子則在《民國日報》陸續發表長文,勸人不要作陳三立、鄭孝胥之“馴奴”,摒棄宋詩和清人學宋之作。朱璽在《中華新報》發表《論詩斥柳亞子》,贊譽鄭孝胥、陳三立詩,嘲笑柳亞子不識詩壇派別。胡樸安則發表《與柳亞子書》,支持柳亞子對同光體的批評,指斥陳三立、鄭孝胥為“鬼之下流”,“其所謂詩,絕饒鬼趣。”其實,同光體作者主要是抱持“不墨守盛唐”的態度,力推主體學宋,或兼學唐,但學唐則主要趨向于中唐的韓愈、孟郊、柳宗元,而不是盛唐的李白、杜甫。實際上,這個群體每個人的詩也是各具“風骨”的,且哀時傷世之思往往與老杜深長暗合。我們對待某些詩詞流派不要看他們怎么說,而要看他們怎么寫,然后從具體作品中吸取營養來滋潤自己。
詩詞當為時代而歌,這其中的時代指的是內容,而詩詞表現手法則具有普適性,應該古為今用,人為我用,最終目標是寫出具有思想境界和藝術水平,且體現鮮明個性和核心價值的佳作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