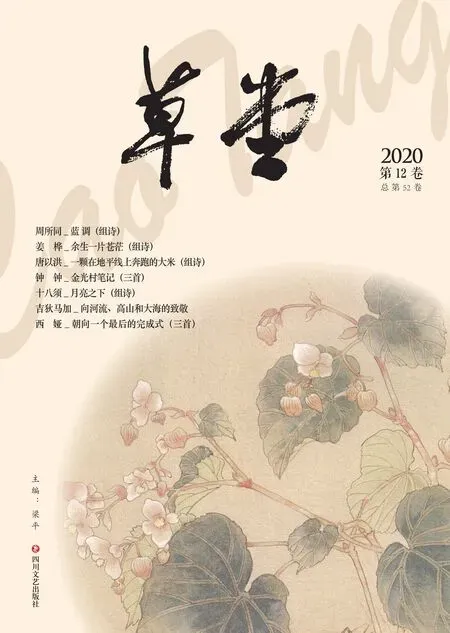塵世深處(組詩(shī))
◎段新強(qiáng)
[寒露]
凌晨最涼的那顆星光
還沒(méi)有熄滅
此刻,就掛在父親的額頭上
……哦,確切地說(shuō),是父親
在用全身的力氣噙著它,就像噙著自己骨頭里
一滴清白的秋色
它照著玉米,大豆,野菊花
照著大片割倒的寂靜,照著父親
一遍遍彎腰抱起大地
它也把自己照著,照著一粒細(xì)微的
喜悅,被人間蒼茫的塵埃
悉心收藏
[冬日里浣洗衣服的母親]
貼著隆冬的腹部,挨著鄉(xiāng)村的胸口
母親彎腰走下最低的河床,人間袒露出
蒼老、柔弱的部分
一件衣服——哦,是一條河
此刻在母親的懷里:溫順,安靜
浸滿風(fēng)塵的身體,被母親握在手心,反復(fù)揉洗
細(xì)密的針腳,一次次膨脹又收緊,隨著一顆心
把干凈又還給貼身的生活……田野上遼闊的積雪
也仿佛是母親一把把洗出來(lái)的,有些疲倦的白
薄薄地覆蓋著世間
身子再低一些,整個(gè)冬天就從骨頭里退出了
雙手再搓疼一點(diǎn),枯萎的春天
就會(huì)在棉布上再次伸展枝葉,吐出花香
從未走出過(guò)大山的母親,一件衣服就幾乎
攤滿了她的一生,就像浣洗自己的命運(yùn)
她淘盡了一條河的冷暖,卻在一個(gè)冬日的早晨
總也直不起她瘦小的腰身
[那個(gè)坐在北風(fēng)中的人是我父親]
那個(gè)佝僂著身體,像一塊黃土被風(fēng)從地縫里
吹出來(lái)的人是我父親
那個(gè)像一塊石頭,死死壓著田角,生怕一地薄薄的希望
被風(fēng)刮走的人是我父親
那個(gè)已記不清多少次了,風(fēng)一來(lái),就把十指深深
摳進(jìn)土里,化身為一棵茅草的人,是我父親
那個(gè)風(fēng)一來(lái),就溫順地讓風(fēng)揪著花白的頭發(fā)用力撕扯的人
是我父親
他好像一輩子就為了等那一場(chǎng)場(chǎng)北風(fēng),好像沒(méi)有他
那些風(fēng)中高高的嘶吼,低低的哭泣,還有長(zhǎng)長(zhǎng)的嘆息,就無(wú)處安放
好像沒(méi)有他,那些風(fēng)中呼嘯的雷霆,尖利的刀槍,還有兇惡的逼問(wèn)
就無(wú)人擔(dān)當(dāng)
而風(fēng)一吹,他就只能伸直了脖子用力咳,用整個(gè)瘦小蒼老的身體咳
他那張從不愿低下的老臉也被風(fēng)吹得一次比一次黑,一次比一次模糊
只有閃爍在眼眶里的兩粒微小卻清晰的陽(yáng)光,讓我認(rèn)得出那是
我的父親
[母親的電話]
已記不清有多少個(gè)0379 區(qū)號(hào)的電話,淹沒(méi)在
我的一大堆話單里,未曾激起一點(diǎn)點(diǎn)漣漪
也不堪回想無(wú)數(shù)個(gè)麻木的夜晚,風(fēng)
深情地匍匐在肩上,我卻聽(tīng)不出那是誰(shuí)的呼吸
——今夜,從握住電話開(kāi)始,我就在笨拙地回憶
母親往日說(shuō)話的語(yǔ)調(diào)和說(shuō)話的樣子
……哦,不知什么時(shí)候
豪爽剛烈的母親,說(shuō)話變成了今天電話里怯怯的口氣
天天還在下地勞動(dòng)的母親,竟成了我回憶里的部分
時(shí)間還在分分秒秒地奔走,還在一點(diǎn)點(diǎn)拉長(zhǎng)我和家的距離
六十四歲的母親還剩下多少守望,可以填補(bǔ)空寂的光陰?
舉目遠(yuǎn)望,黑夜就像鐵打的天涯
一輪下弦月亮了又亮,仿佛拼盡了最后的力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