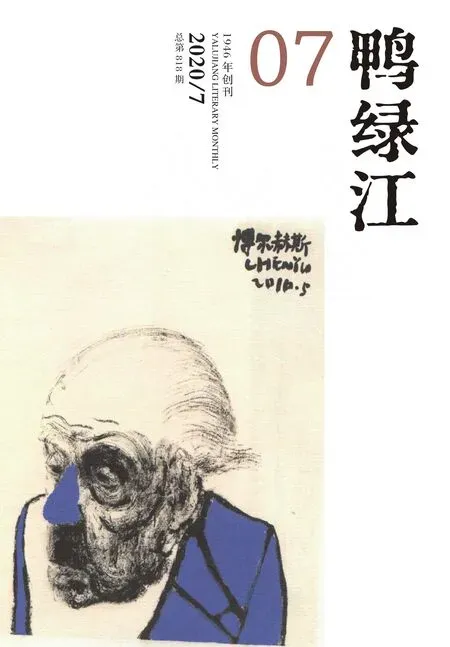北方青春的另一種抒寫(評論)
——評高翔的小說《七月,養蜂人》
吳曉東
高翔的小說《七月,養蜂人》又一次讓人看到了以東北為底色的青年文學的新景觀。小說講述的是成年人在跨向真正成熟與世俗臨界點時的糾葛故事,它不是回憶青春的悵然所得或所失的反思文學,更不是青春燃燒的激情表達。作者似乎在自覺不自覺地用青春時期特有的陰郁與哀傷,在一段撲朔迷離的故事中,表達了他對于面對成人世界的恐慌與年少時光的苦澀留戀。
小說的敘述方式更像是一部微型電影,回映了兩位主人公的高中與大學故事。但與以《致青春》為代表的青春回憶影視文學不同的是,小說并沒有陷入以激情、初戀、義氣等關鍵詞為核心主題設定的套路之中,而是用陰郁的墨黛色濾鏡更換了青春文學的黃綠色底色。主人公李棟棟的角色設定就奠定了小說的基調,他從高中起就是家長口中“別人家的孩子”,他與其他孩子不同的是,缺少了青春的激烈與生命力,卻多了一項特殊的能力——顫抖。小說描寫了三次李棟棟的顫抖場景:一次是作為鄰居時的初見,讓“我”見識了人生的另一面;第二次是在校長將他的課桌從理科班搬離時,讓“我”見識了社會的另一面;第三次是在同學的電話里,他想要當著校長的面強奸校長女兒時,讓“我”見識了人性的另一面。正是由于“顫抖”,讓李棟棟的人生缺少了選擇的可能性,在他內心深處隱藏的是無可奈何的人生選擇。他因為自己莫名其妙的生理原因,無法對抗來自社會的無形力量,青春時期該有的生命張力被消解得蕩然無存。也正是因為這個毛病,他無法適應當下的社會與生活,雖然娶妻生子、求學晉級,極力維護纏繞周身的社會光環,卻體會不到搏浪擊水的甘苦冷暖,也無法欣然享受煙火生活的生色犬馬。他憎恨文學專業,卻必須靠它標簽化自己;他會寫詩,能夠用十分文學的方式表達,卻又在厚重現實與虛無理想的拉扯中無法真正沉浸。小說似乎在揭示這樣一個主題:青春的傷痛,不僅會是時代留下的遺憾,是情感遺失后的酸楚,也還可能是人性里暗藏的一個陰謀。
小說的主體結構按照交流方式的不同大致可以分為前后兩個部分:通信,見面。兩種交流方式就是兩個時代的寫照。寫信的方式是古樸的、過時的,但又代表著青春;見面擼串的交流方式是當下的,卻代表著傳統的、世俗的。小說在第一部分中,用非常簡潔的方式描述了五封信的內容。李棟棟與“我”聯系上時,有“我”的電話號碼,但卻堅持要“以寫信的方式”進行交流,在他的眼中,寫信意味著“人情味兒”。他逃避人與人的交流方式,在他思想深處認為“碰面等于關系的實質性建立,人與人,只要建立起實質性聯系,就會產生暴力”,進而導致“自由”消失。信作為一種交流方式,可以給交流雙方創造一個非實時的溝通空間,在這個空間里我們可以任意設定自己,而這種設定往往是舒緩的、美好的,也就是李棟棟所認為的那種所謂的“自由”,作者身處當下,切身體驗著以高速網絡為支撐的便捷交流方式。它消除了人與人之間的界限與空間,人們無法構建起更加豐富的自己,只能是遵循屏幕法則,按照“人設”生存。“我”在信中的表達也是“自由”而平等的,沒有了人與人見面后的社會性真實。然而在第二部分里“我”與李棟棟面對面溝通時,雖然“我”用酒的迷狂力量,建構起另一個類似信一樣的溝通的場域,但卻沒有像信那樣給對方留下思想反芻的空間與想象澄化的時間,于是交流陷入紛亂生活的“一地雞毛”,甚至“我”與李棟棟還引發了誰瞧不起誰的社交誤區。人與人的社會屬性開始在這里赤裸裸地暴露出來,情緒開始變得陰郁、不再美好,它吞噬了最后一絲屬于青春的氣息。當“我”離開時,既沒有請求李棟棟讓他幫忙賣蜂蜜,也沒有按之前的想法給他留下四罐蜂蜜,而是只留下了禮節性的兩罐。
這部小說用生活的真實性取代了以往書寫青春文學追求浪漫格調的理想性。東北的生活與描寫,體現出一種作者在剛剛離開后便開始探索的尋根之感。通過這部小說,記憶與想象共存的原鄉世界,在虛擬與現實的體驗中被構建起來了。東北文學往往容易被貼上“工業”“冬雪”的標簽。由于近幾年新東北作家群的崛起,以及東北喜劇文藝的大量輸出,東北文學的潛在力量逐漸彰顯出來。《七月,養蜂人》這部小說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將東北文學另一道可以獨樹一幟的“森林風景”展示出來。我們不是說這種文學風景是空白的,而是作者在這樣的年紀,以帶有青春情緒的筆觸去感知、理解切實的東北文化和生活,是極為難得的。許多人都是在離開家鄉許久后,才開始對家鄉的深入反思與書寫,而對東北自然景觀的描摹又往往陷入大開大闔的“東北風”式表達窠臼,這種表達常被批評為是粗淺的。小說從養蜂人的視角切入,諸多細節被自如地嵌入到故事的敘述之中,既不刻板也不做作。小說不再像許多青春那樣,有了不再是虛化到看不清晰的背景,這也讓小說在表達理想與現實、青春與成熟的潛在主題時,使對比度更加強烈,增加了小說中人物與故事的顆粒感。
如果,小說將“我”的講述內容適當削弱,不對李棟棟的言行進行過多定論式評價,對于信的內容采用直引的方式呈現,也許能使李棟棟的形象更加豐滿,“我”的形象也更加合理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