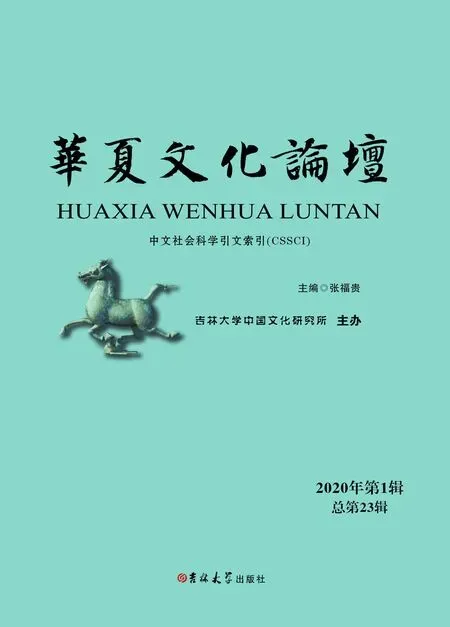場景構建視域下的日常化網絡直播
萬書亮 沈雨潔
在全民直播的浪潮中,網絡視頻直播正在產生新型的媒介文化。伴隨著社會大眾的參與熱情被深度激發,公眾在社交、認知、表達、集體規范等諸多層面也發生了改變。截至2019年6月,“網絡直播用戶規模達4.33億,較2017年底減少2533萬,用戶使用率為47.9%,較2017年底下降6.8個百分點”①CNNIC.第42~44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902/P020190318523029756345.pdf.。從大趨勢來看,2018年的“網絡直播行業與正處風口的短視頻相比,無論是投資價值、用戶規模、廣告收入等數據,還是頭部生產力、板塊活躍度、社會影響力等指標都相形見絀”②王建磊:《2018年網絡視頻直播發展研究報告》,《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No.10(201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6月版.。目前來看,體育、游戲、真人秀、演唱會仍是直播行業凸顯價值的頭部領域,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直播與娛樂基因的天然關聯。在直播亟須向外界展示更多的深層價值與意義時,對娛樂屬性的過度聚焦和釋放,對行業的長遠發展是不利的。所以,本文所思考的一個核心問題是:網絡視頻直播究竟還帶來了什么價值?
在“全民直播”的背景下,生產者身份的全面放開以及內容類型的無所不包導致上述“開車、走路、聊天、吃飯”等生活流的內容頻頻呈現在平臺之上,這些略顯隨意的內容非常龐雜、散亂、無序,但又是很具體和真實的存在,有學者將其總結為“日常化直播”并提出其包括的三種類型:生活流直播、獵奇直播和功用直播①王建磊:《如何滿足受眾:日常化網絡直播的技術與內容考察》,《國際新聞界》,2018年第12期。。本文從布爾迪厄的場域到梅洛維茨的場景系統,再到羅伯特和謝爾的“場景時代”,通過梳理既有的“場景理論”,揭示日常化網絡視頻直播所構建的傳播場景的方式、特點和功能,為網絡直播的新媒體內涵提供一個便于理解的視角,最終試圖說明:架設一定場景,即基于一定時空之下,借助移動互聯網和社交傳播工具,最大化滿足社會群體觀賞需求等。利用場景進行傳播,最大的好處在于能夠促進各種“賦能”的產生,而網絡視頻直播本應在這方面大展身手。
一、“場景”再審視:從“關系”到“適配”
在傳播學研究史上,“場域(field)”與“景觀(spectacle)”是與場景的本意較為接近的概念。“場域”是法國思想大師布爾迪厄構建的社會學理論中的核心概念,他將一個場域界定為一個網絡,存在于各個位置共同組成的客觀關系中,每個位置都是客觀限定的。②[法]布爾迪厄,[美]華康德:《反思社會學導引》,蘇國勛主編,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122頁。這一定義突出了場域的客觀性,因其是一個整體的關系網絡,關系網絡中產生的人類活動都是由每一個鮮活的有自主意識的人類做出的,而不同場域的慣習是不同的,即“性情傾向系統”③朱國華:《習性與資本:略論布迪厄的主要概念(上)》,《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各有不同。每個場域均與之慣習相匹配,但兩者之間較為復雜,僅用“決定”“被決定”的關系進行界定遠遠不夠,因其更多的是一種依托實踐活動架設形成的“建構”關系;布爾迪厄同時強調,“場域不僅是社會科學的最基本對象,更代表著研究活動的起始點”④同上。。也就是說,場域中的個體作用并未被明顯強調,其更側重于整體,場域的核心便是平衡個體和整體關系。當下的輿論場、媒介場、新聞場等概念可以說都是從“場域”衍生而來,在這里,“場”是各種力量凝聚的所在,它關注的是各種權利或資本(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在社會結構中的分布與權重。
同樣為法國學者的居伊·德波提出了景觀社會的觀點。其認為,景觀的本意是指可視化景象,但同時,其也可延伸為具有主體意識的刻意性作秀活動。德波借此概括他眼中所認為的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性質,他認為:“現下社會,最不缺的就是生產條件,景觀在社會中即指代涵蓋所有的生活整體,生活作為一個景觀整體,其所涵蓋的所有事物均化為表象。”⑤[法]居伊·德波:《景觀社會》,王昭風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頁。他尤其引入了大眾傳播媒介的角色,指出人類所處世界的真實性不同以往,“現實世界是飽含傳播技術手段創設和加工的社會的再度呈現”⑥王梅芳,劉華魚:《景觀社會:一種視覺傳播化的統治》,《當代傳播》,2017年第3期。。德波的景觀概念對后世研究影響深遠,他依然從關系的視角去研究社會,社會離不開視覺傳播,那么景觀的堆砌就無法形成社會,“景觀只能成為一種介質,用于映射人類社會錯綜復雜的關系網絡”①[法]居伊·德波:《景觀社會》,王昭風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99頁。。同時,他帶著批判的眼光對傳播中的視覺化進程和蘊藏于背后的意識形態因素加以審視,最終得出這樣的結論:“意識形態的頂點便是景觀”②王梅芳,劉華魚:《景觀社會:一種視覺傳播化的統治》,《當代傳播》,2017年第3期。。
20世紀80年代,在社會學家戈夫曼提出的“擬劇理論”的啟發下,傳播學者梅洛維茨進一步提出了“場景(situation)”這一新型概念。戈夫曼關注的是社會生活互動是如何在“建筑物的有形界限”③歐文·戈曼夫:《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黃愛華,馮鋼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頁。內發生的,而梅洛維茨定義的場景是經由電子媒介的介入而形成的“信息環境”。在《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中,梅洛維茨表示:電子媒介(以電視為主要代表)深入發展過程中,信息流動超脫物理空間、固定場所的局限,在電子媒介尚未出現時,人們只能接觸近距離場景,但在電子媒介出現后,這一局面被打破,非近距離場景也能呈現在人們眼前,文化價值觀的流動更加迅速、快捷,地域差異性很可能被逐步削弱乃至不復存在。
梅洛維茨提出的核心觀點是“信息流動的模式決定了人們交往的性質”④[美]約書亞·梅洛維茨:《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肖志軍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30頁。。信息流動模式變化帶來新的場景的誕生,而新場景的誕生則帶來新的行為、新的群體和新的價值觀。這一邏輯線條的重心在于充分肯定電子媒介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新媒介“具有改變人們已然形成的社會角色認知的作用,因其可轉化不同群體所接觸到的不同場景”⑤[美]約書亞·梅洛維茨:《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肖志軍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30頁。。
2014年,美國科技作家羅伯特·斯考伯和謝爾·伊斯雷爾在其合著的《即將到來的場景時代》中展示了基于互聯網時代所產生的場景建構,他們認為,場景架構過程中,大數據、移動設備、社交媒體、傳感器、定位系統會產生五位一體的聯動效應,共同架構其現實世界的場景。由此,學者們紛紛對網絡時代語境下的場景展開了研究。如果說在傳統媒體時代,場景被理解為一種由傳者定義的信息環境,那么在新媒體時代,場景主要轉變為“基于受者心理和行為需求的情境營造”⑥嚴小芳:《場景傳播視閾下的網絡直播探析》,《新聞界》,2016年第15期。。2015年,國內學者指出,廣義的場景是一個整體的環境氛圍,既包含物理空間,也包含在行為與心理產生的基礎上形成的空間環境,人們階段的行為特征及具體需求都是由場景所決定的,空間環境、用戶實時狀態和生活習慣、社交氛圍共同構成了場景;移動互聯網語境下傳播的本質是基于場景的服務,即“在特定情境下進行個性化、精準信息服務適配”⑦彭蘭:《場景:移動時代媒體的新要素》,《新聞記者》,2015年第3期。。加深對特定場景中的用戶的理解,“運用個性化精準推送服務最大化滿足用戶需求,完成適配過程”⑧蔣曉麗,梁旭艷:《場景:移動互聯時代的新生力量——場景傳播的符號學解讀》,《現代傳播》,2016年第3期。;適配水準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信息服務發現、整合、推送能力的影響”①彭蘭:《場景:移動時代媒體的新要素》,《新聞記者》,2015年第3期。。
至此,學術視野中的“場景”內涵被不斷充盈,呈現出從傳者構建到受眾參與,從地理空間到實體與虛擬相結合的轉向,一方面,“場景是依托社會關系所產生的,但同時其又創造出新的社會關系,并被社會關系所創造出來”②包亞明:《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8頁。;另一方面,今天各種新媒介所營造的場景,必須“完成適配”才能更好地體現其傳播價值和商業價值。
二、日常化直播:無意促成的社會動員
米爾佐夫的《視覺文化導論》中,文章一開始就提出了這樣的觀點,熒幕上發生的一切的總和就是現代生活的映射,盡管這非通俗所說的日常生活,但毫無疑問的是,其已然構成了日常生活。米爾佐夫表示:“現代化的城市社會無法脫離視頻監控,視頻監控越來越普遍地出現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均被無處不在的攝像鏡頭所監控著。”③[美]尼古拉斯·米爾佐夫:《視覺文化導論》,倪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頁。在此條件下,人們的視覺性經驗將進一步凸顯。
攝像頭繪制出了生活常態,除此之外,不具備其他功能,視頻直播的出現則改變了這一點。2015年,Meerkat和 Periscope主動依托視頻直播,令無數網友在線上看見了他們的生活狀態。在我國,網絡視頻直播首先從游戲行業開始,進而蔓延到其他領域。隨著直播產品(移動端)、直播頻道(PC端)的爆炸式增長以及直播內容的日常化、廣泛化,網絡平臺上充斥著大量人們自主分享的生活常態,包括人們工作等多面的生活內容,進而呈現出生活的萬千姿態與社會文化的多樣性。
當前,網絡用戶各類媒介消費行為中,觀看直播已然成為主流方式。傳統媒體運營過程中,電視直播主要應用于記錄大型事件或事發突然的事件,線上視頻直播則不然,其涵蓋面廣,充斥著大量商業教程,包括教育培訓等。視頻直播擁有海量視頻資源,其寬泛的內容、公開化的生產者身份的特征共同造就了現代化直播平臺的社會價值:
第一,網絡視頻直播帶來了新的職業身份:主播。這里的主播不同于電視媒體的主持人,而是泛指每一個使用直播平臺的內容生產者,是一個平民化的概念,在理論上誰都可以做主播。無論是專業的女主播還是素顏出鏡的普通群體,其在攝像頭支架前均展現出了最自然、真實的一面,其對直播技術的掌控和運用也是非常熟練的。
第二,網絡視頻直播給予了每個個體公開分享生活的權利,唱歌、聊天、開車、吃飯、睡覺、運動、娛樂等一切生活、工作中的日常經歷都能搬上直播,看似非常簡單和單調的畫面,只要在視頻平臺上開播,就會有人圍觀。
第三,網絡視頻直播的地理場景轉換到了客廳、廚房、大街、餐廳、演唱會甚至衛生間等,司空見慣的生活空間或主流的消費空間都成為生產者的創作舞臺,甚至很多時候空間本身成為展示的焦點:當C哩C哩舞火爆流行,在重復的旋律和一致的動作背后只是背景場面在不停切換;當“鄉村愛情故事”頻頻上演,農村的土炕、田野、瓦房、糞坑等場所成為另一個視覺重心……空間的豐富多變帶來了看點,也帶來了包羅萬象的線上世界圖景。
綜上,當今時代是全網直播的時代,信息生產、傳播不再由專門的媒體所壟斷,每一個個體均能通過注冊直播平臺進行日常化直播,盡管其空間環境并不是特定的,也沒有具體的腳本設計、專業設備等,但其仍然可將日常生活的常態借助網絡直播的形式分享給大眾,直播內容可能是冗長、繁雜的,但卻都是生活的實際常態。日常化網絡直播當下并沒有一個嚴謹的學術定義,在現實中是一個非常開放的概念。諸如吃一碗面、打一場球、走一段路等這些生活流的內容都屬于這一范疇,呈現的直播內容真實性較強,沒有社會生活具體表現的限制,從商業價值、社會意義方面進行探討的話,其實際上并沒有什么價值,但其帶動的產業規模是龐大的;從社會動員的角度來說,這種并非通過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達成的群體卷入現象,更值得從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多重視角研究其內在機理,至少,這也從一個側面表明了網絡視頻直播的生命力所在。
三、直播構建場景:儀式化帶來深度沉浸
按照梅洛維茨的觀點,電視媒介通過對異時異地的場景的再現,使人們高效地獲得知識與經驗,從而使地理結構帶來的文化差異性走向消弭。從這個意義上說,“電子媒介重新組織了社會環境”①[美]約書亞·梅洛維茨:《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肖志軍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97頁。。許多實際生活常態本來并不會輕易地暴露于鏡頭之下,但在視頻直播技術的支持下,其具有了可視化功能,這就表明,場景構建過程中,直播技術的地位非同小可,值得重點考察的是:網絡視頻直播是如何構建場景的以及到底構建出怎樣的場景?
(一)直播構建場景的方式
網絡視頻直播依循著三個層面來構建場景,分別為形式(界面)、內容和空間(場面)。
第一,網絡視頻直播在構建場景過程中,依托現代化技術,逐漸發展成為一種功能強大的超級文本,直播窗口不僅涵蓋視頻影像,更為視頻觀看用戶設置了專門的控制面板,用戶可發送文字彈幕、道具圖片等,同時,一些話題性較強的直播窗口中,還會由于用戶持有不同的見解、觀念而發生口水大戰、道具大戰等。上述情況均已成為視頻直播觀看用戶的話題熱點,彈幕文字的出現也增強了用戶的觀看體驗,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視頻本身內容的功能性,用戶互動成為直播的核心所在。這一情形類似于德里克·德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在其《文化肌膚:真實社會的電子克隆》一書中所論證的:人們觀看電視的行為,僅僅是依托電子書掃描設備這一媒介產生的,人們做出的一系列反應均產生于電視呈現的光束。②[加]德里克·德克霍夫:《文化肌膚:真實社會的電子克隆》,汪冰譯,河北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2頁。直播時代下,視聽文本進一步升級,人們的觀看體驗得到了升級,其擁有了觀看反饋的權利。視頻直播互動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直播構型,用戶在界面場景中憑借各種互動方式享受更加高級的觀看體驗,極大地滿足了自身的娛樂化需求,電視播放則無法滿足用戶這一需求。
第二,從內容層面來看,日常化直播的內容相對流于膚淺,比如某手機直播平臺顯示,一個無人機的鏡頭對準了某高校女生宿舍的窗戶,隨后在接近一個小時的時間里,畫面依然是那扇模糊不清的玻璃——這就是直播的全部內容,而這樣的直播引起了十幾萬用戶的圍觀。顯而易見,模糊的玻璃并不是人們關注的重點,直播主體所刻意營造的人們對玻璃后面場景的集體想象與彼此感染才是真正的“看點”。除此之外,對于持續性生產的日常直播來說,哪怕是直播吃飯、走路這樣的內容,顏值、聊資、異于常人的個體能力等,都是該類直播內容的看點。而用戶對于內容場景的沉浸,實質上是對主播進行一種情感表達,構建一種社交關系。
第三,直播所依托的實體空間很多時候也是一種精心設計過的場景呈現。以吃播為例,某女主播直播吃飯,畫面背景呈現出活力,粉色的墻面,各類家具的主色調也是粉色,并有多個可愛玩偶擺放在身后,畫面中還出現了一把放置于角落的吉他,①參見http://compaign.tudou.com/v/XMzk0MTQ4MzA3Mg==,2019-12-10.上述場景布置傳達的信息在于:女主播的生活常態是一個干凈整潔、熱愛音樂的活力少女。直播平臺中許多女主播致力于閨房設計,盡管,其直播的場景屬于隱私范疇,但當其隱私的生活場景全部敞開,用戶便能夠直觀地感受到屏幕背后主播的生活環境,仿佛真的親臨其境,進一步了解了主播的個人生活,這樣一種空間化的沉浸是一種超真實的感受,盡管這里呈現的場景不一定是真實的。
綜上,直播所構建的場景囊括了形式層面、內容層面以及空間(場面)層面,既包含場所與景物(道具)等硬要素,也包括空間與氛圍等軟要素。更重要的是,對于直播這種媒介形態而言,其超級文本形態和精致的交互設計,也構成了用戶重要的使用場景。在這種立體的環境氛圍下,即使是日常化的直播,用戶也表現出更投入的觀看熱情和沉浸的欲望。直播場景設置的魅力在于,以走路為例,這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人類肢體行為,平時大眾也不會過多關注,但當直播畫面呈現的是在香榭麗舍大街,一位優雅迷人的女士緩緩走來,此時,屏幕上綻放了滿屏的鮮花,播放著優雅的背景音樂,觀看用戶第一時間便能感受到這一場景所帶來的畫面感和迷人的場景魅力。
(二)直播構建的場景特征
如上所述,直播從形式、內容和空間三個維度塑造了全新的場景,接下來我們考察這樣的場景具備怎樣的特征。
1.場景的儀式感
社會學家涂爾干曾提出互動儀式理論,其認為,“社會動力來源于互動,個體形象的社會化呈現無法脫離社交活動”②Durkheim,E..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New York:Free Press,1965:56.。提及互動,自WEB2.0開始啟用,“用戶自主發布”模式僅限于文字、圖片,相比網絡視頻直播的豐富互動形態而言較為單一,視頻直播中,在文字圖片的基礎上出現了彈幕、表情包、語音等一系列增強用戶體驗的互動工具,在VR(虛擬現實)、AR技術的支持下,調動用戶肢體行為也能在直播中呈現,完成了空前的互動;道具使用成為互動策略實施的重中之重,盡管道具只是虛擬工具,但這并不妨礙其完成利益分配,視頻直播場景下,道具是最普遍的互動工具,可輔助用戶更快捷地表達個人情緒和情感。
道具使用這一新型互動方式為視頻直播帶來了新的儀式感,如雙擊點贊、關注、虛擬禮物打賞等,看似簡單的操作,實則蘊涵了人類關系的互動和情感。比如打賞其實是用戶對于媒介的主動使用行為,他們通過打賞來獲得自身的價值認同與情感認同,除此之外,網絡直播圈用語趨于豐富,包括“老鐵666”等口號,不熟悉直播圈子的人自然無法理解,但其實際上“彰顯著直播儀式”①洪葉:《論網絡直播場景共同體的形成》,《視聽界》,2017年第9期。。彈幕刷屏是直播常有的,這也是用戶觀看視頻直播反應的直觀呈現,具有一定的儀式感,受眾獲得一致的認同感便來源于這些看似普通的互動行為。
2.場景的即視感
視頻直播在互聯網的孕育下誕生,首先具備移動互聯網的先進基因。不過,它把互聯網反應敏捷的特點再度進行優化,從“及時”升級為“實時”,時空的同步性、同一感成為直播技術的最突出表征。用戶切換直播間時,呈現的直播內容仍然同步于上一個直播間,這便是直播技術發展過程中帶來的更深層次的即視感。
直播場景所帶來的即視感,打破了時間空間的界限,促使時空共存。單就時間而言,時間不再是一個單一的抽象數字,也無法阻隔人們不同生活模式的同時呈現,時間的概念在視頻直播中被削弱,成為無差別的生活常態模式的呈現;單就空間概念而言,視頻直播拓寬了人們的社交領域,打破了現實空間的界限,同時又不脫離現實空間而存在,用戶沉浸于時空環繞的虛擬場景的架設中,但又并非完全隔離于現實生活,反而造就了一種非常深刻的更加直觀的“存在而又不存在”的體驗。
3.場景的融合性
梅洛維茨在提出場景融合概念的時候,著重論述的是電視媒介將有形地點、信息獲取的聯系性進一步削弱,私人與公共場景在這一過程中得到轉換,在大眾媒介的作用下,私人信息也可共享于公共場景。其中,“后臺前置”②賈毅:《網絡秀場直播的“興”與“衰”》,《編輯之友》,2016年第11期。是一個重要的步驟,它最終推動了公共場景與私人場景的融合。
實際上,網絡直播平臺帶來了更大的開放力度,在日常化直播中,一些主播是主動將自己或他人的私人生活(場景)展現在屏幕前,與電視時代觀眾只能觀看不能干涉不同,任何觀者都可以參與進這個“后臺”的呈現方式、內容和走向。如某平臺上一位滴滴男司機通過接空姐訂單,在駕駛過程中直播空姐,按照觀看直播用戶的問題向不知情的空姐進行提問與引導,這種混合了(司機)表演與(空姐)真實反應的方式受到大批用戶追捧。通過這樣的案例,我們似乎可以推論:在手機攝像頭所到之處,原本的后區有可能全部轉為前區,網絡視頻直播的出現使得現實場景繼續融合和演變。
與此同時,傳統生活常態也出現在視頻直播中,包括普通的吃飯走路等;在視頻直播中火起來的主播也會在線下參與各種社交活動,實現線上直播線下活動的共同掌控。這就表明,網絡上的虛擬生活并非現實生活,但其又是造就了現實生活中的真實生活本身,直播的題材非常寬泛,互動環節也非常多樣化,直播界限逐漸打破虛擬化網絡世界的概念,網絡與現實的交叉性更強。據此,線上場景與線下場景的融合,是網絡視頻直播帶來的第二層融合。
(三)直播場景的功能
在一般的理解中,直播的畫面是主觀的、生動的、創造的,至少經由直播技術的包裝還呈現出一定的形式設計感,因而直播中呈現的生活流與攝像頭冷冰冰地記錄截然不同。因為場景的生成以及其具備的“儀式感”、“既視感”和“融合性”的特征,用戶在觀看日常化直播時,一定程度上也會包容其無聊和無趣的特性,從這一點出發,直播場景首先具備可供消費的功能。當下如此五花八門、光怪陸離的直播內容足以證明這一點。而上述場景、行為明顯區別于傳統電子媒介,尤其當個體的私密通過某種方式予以公開化,更滿足了人類固有的好奇心與窺探欲。
除此之外,我們注意到,日常化直播的主播們,他們也會關注一些身邊的不平事、好玩事和瑣碎事,這種對與自身相關的公共空間、事務的展示和交流,“也是平民直播者與觀者在網絡平臺對自身話語權的爭取、表達與回歸”①尚帥:《視頻化社會:從直播新聞到直播生活》,《新聞知識》,2016年第7期。。確實,直播的出現賦予了每個個體述說、觀看的權利。諸如評價他人、論述他人闡述的觀點等直播內容,實際上是大大小小的熱點集合,不同熱點推動著另一個熱點的產生,塑造了新的話題點,營造了相當復雜的直播熱點模塊。網絡視頻直播逐漸形成一個新的框架,在框架中,有人扮演信息生產者,有人扮演信息傳播者,每個人都在全力地表演和展示,而圍觀者則對品味相投或者感情上偏好的人表現出支持。在這一個過程中,直播用戶有可能會省去自我思考的過程,但不可否認的是,僅從結果來看,他們又接受了意見領袖對公共事務的認知,也在一定程度上鞏固及完善了自身的知識結構——這是直播場景所具備的認知功能。
最后,網絡視頻直播是基于移動終端所產生的,在網絡直播中,空間距離被打破,觀看者和直播視頻的主體所產生的行為愈發偶然和隨意,同時,手機作為個人媒體的私密性使主播或用戶都可以更加真實地表達自我。這樣兩個特征極大地增強了場景設計中的浸潤功能,因為用戶對任何一個場景的切入都是不確定的,他必須要通過深度的沉浸、熱情的交互才能改變這種不確定性——如果他想達成某種目的的話。無論是社交,還是純娛樂,直播平臺都構建出了易于沉浸的場景,也致力于不斷引導用戶深入地使用直播。事實上,綜合網綜、網劇、PGC、短視頻等所有互聯網視聽形態來看,還是網絡視頻直播打造了最具沉浸感的使用體驗——人們在觀看直播的時候,除了觀看內容,還有時刻生發的、不斷沉浸的情感。
四、小 結
本文從場景構建的視域下審視網絡直播,得出以下幾點結論:其一,即使是無顯著意義的日常化網絡視頻直播,也在技術和文化的雙重塑形下,構建出場景感極強的傳播儀式,在儀式之下,信息的重要性不再明顯,社區的參與感和共鳴感才是核心價值;其二,日常化直播所構建的場景具備消費性、認知性和沉浸性,其源于在商業、資本和市場的共謀之下,導致的“后臺前置”、價值迷失等失序令直播場景體現出更高的獵奇感、審異性;其三,直播用戶除了時間的投入,實際上還付諸了情緒和情感,這使得本來純物理性的場景空間,因為情感的流入,充滿了真實的感染力和豐滿的意義,也間接推動了年輕人群社交關系的結構性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