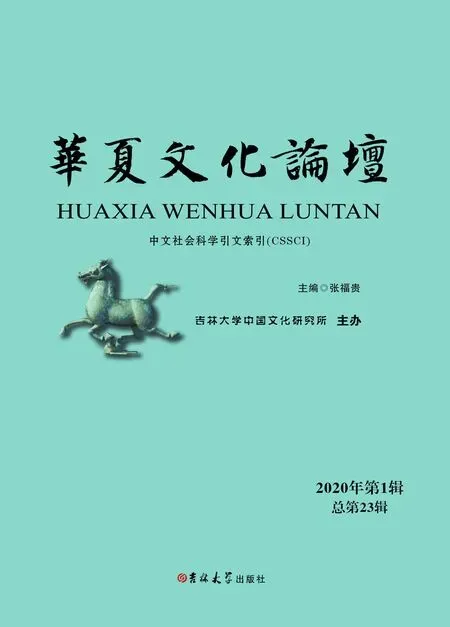意象、氛圍、生命
——阿城的詩意書寫
馮譯萱
【內容提要】在對阿城小說的細讀和觀念的梳理中,可深切感受到一種上承古典詩學意象、下接世俗詩性人生的詩意美感。他不僅將傳統的詩意美學融匯于作品文本,還生發于創作的過程之源,延伸至生命的態度和感知體驗中。討論研究阿城的詩意敘述,有利于使我們在拓寬詩意格局的同時,得到人生美學的啟發。
馬克思在論述文學批評原則時指出:“文學應當接近真實和實際領域,而不應漫無邊際地飛馳遐想;文學應具有形式、尺度和凝練;人們可以從偉大的文學作品里覺出一種真正的詩意。”①[英]柏拉威爾:《馬克思和世界文學》,三聯書店出版社,1980年,第26頁。可見,詩意是偉大的文學作品中必不可缺的素質。在中國這個“詩的國度”,人們更是慣于將“詩意”作為小說評判的藝術標準。陳平原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分析道:五四作家、批評家喜歡以“詩意”許人,似乎以此為小說的最高評價。②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25頁。正是在那些或明亮、或平淡、或頹廢的詩意書寫中,鑄就了魯迅、廢名、沈從文、張愛玲、郁達夫等一代文學大家所開創的輝煌時代。
所謂詩意,是小說對中國詩歌傳統所繼承的一種審美特質。不止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所表達的性情心態,更在于作品所營造的感覺、氛圍,模糊而又無以言表,卻能促使人在閱讀后產生一種沖擊心靈的力量。承襲中國詩歌傳統,現當代小說的書寫歷史中雖有斷裂,但仍保留下了這種詩意傳統。至20世紀80年代初,詩的意識再次大規模進入小說,“一時之間,小說的傳統敘述方式驟然瓦解了。大量詩的觀念與詩的技巧有意介入并且改組了作家熟悉已久的‘敘事’,情調、意緒、氣韻、意境、瞬間印象,這些詩的臣民大批進駐小說,安營扎寨”③南帆:《沖突的文學》,江蘇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95頁。。作為八十年代文學的代表人物,阿城始終因自覺的傳統文化意識而為人頌聲載道。這種傳統文化意識不僅表現于作品書寫的文化觀念,更體現在他作品所蘊含的藝術特征內。基于長久以來對傳統詩歌的熱愛和研究,阿城在創作中時常自覺地或無意識地流露出濃烈的詩意敘述特征。他以文字編織出一種意象,在營造的氛圍中表達感覺、抒發情感、開創意境。這也使他的文章擁有了深刻的帶入感和體驗感。
與同時期的文學創作者相比,阿城在小說的詩意書寫中,顯然是道高一籌的——上承古典詩學意象、下接世俗詩性人生。他始終堅守著對于古典文學盡可能的承接和延續,這也是學界普遍將其歸納入“尋根”的原因之一。無論在其創作中,還是在相關文學討論中,阿城始終秉承不以主觀色彩影響他人,盡實的客觀展現出一個真實,透過意象的摘取、氣氛的烘托,促使人們發生聯想或思考,展現出對于古典詩意的完美詮釋。于此,本文將探源阿城的詩性觀,深入分析其對于意象、氛圍、生命意識三個方面的詩意表現,在文本細讀和現實考察的交叉映照中,對阿城的“詩意”做出立體研究。
一、詩性的意象表達
在阿城的知識構成中,《詩經》和《史記》是其極重要的組成部分。他曾說:于是凡有關《詩經》的書我都買,歷年積有四十多本。①阿城:《脫腔》,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135頁。而在諸多文章和訪談中,阿城更是談及自己對于《史記》的理解和偏愛。他在與諾埃爾·迪特萊(法國)的通信中寫道:“中國文學傳統基于詩,而散文文學傳統則基于《史記》,《史記》是具有文學特點的各種描寫的開端。”②[法]杜特萊,劉陽:《不可能存在的小說:阿城小說的寫作技巧》,《中國文化研究》,1994年04期。《史記》在對浩瀚歷史長河的鮮活書寫中,根植社會生活的繁雜人事,意在傳達千百年來傳統文化思想的氣韻和靈魂,其詩意的表達讓后人在千百年的流轉中,仍能真切感受到他們充沛的情感,遂才得到魯迅“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的盛贊。正是這些厚重文化沉淀的濡染,使得阿城在自我創作中愈加注意自己對于感覺、意象的詩意把握。他自己評價《遍地風流》系列短篇:因為是少作,所以“詩”腔外露,做作得不得了。可見阿城自知,并自覺地在書寫時埋下詩意。阿城最終選擇了筆記體小說的文類表達方式,同時具有詩、散文、隨筆和小說的特征,與其閱讀影響和詩意的審美追求也不無關系。
阿城不僅將詩意書寫進自身的文學創作中,看待其他文學作品時,他也常懷詩意,如他分析《紅樓夢》之所以成為古典小說的頂峰,是因“曹雪芹將中國詩的意識引入小說”③阿城:《閑話閑說》,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98頁。。對于現當代文學創作的評論,亦是常以詩意為尺:湖南何立偉是最早在小說中有詩的自覺的;山西李銳、北京劉恒則是北方世俗的悲情詩人④阿城:《閑話閑說》,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143頁。;南京蘇童在《妻妾成群》之前,是詩大于文⑤阿城:《閑話閑說》,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145頁。。他評價《受戒》是一種恢復了詩意的散文小說⑥阿城:《脫腔》,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62頁。,而朱天文的《荒人手記》有點像李賀寫詩①阿城:《脫腔》,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87頁。;孝賢的電影語法是中國詩②阿城:《文化不是味精》,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102頁。;而費穆的《小城之春》、張愛玲的《太太萬歲》、石揮的《我這一輩子》其實是西方詩和東方詩的混合③阿城:《文化不是味精》,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103頁。其中,阿城對何立偉的小說《白色鳥》評論最為細致:“何立偉屬于開始發表作品就是成熟的作家之一。他的成熟表現在他的小說有一種詩意,所說的詩意當然不是七八十年代充斥中國小說的文藝腔,他的小說中的詩意屬于中國古典詩歌中那些典雅生動的意象的當代表達。這篇小說的詩意人物與環境,隱藏著一個殘酷的事實,所以小說結束時,你當可體會為什么小說通篇籠罩在‘正午’這樣一個反差強烈的意象中。”④阿城:《脫腔》,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64頁。如此之高的評價,正是源于阿城對于詩意美學的認同。在其文本創作中,也深刻地蘊含著這種詩性的意象表達。如孔慶東說:“語言上向古詩詞中的無我之境靠攏。在這方面,應該肯定,阿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甚至比有意要用唐詩格調來寫小說的何立偉還要高出一籌。”⑤孔慶東:《47樓207》,中國文聯出版社,2012年,第141頁。可見,阿城對傳統的詩意表達懷有一種近乎虔誠的鐘愛。
1999年冬,阿城與眾多知名文壇作家相聚在成都郫縣(現為郫都區),開展一場關于“詩意的年代”的討論,參與者有林白、陳村、徐星、須蘭、趙玫、方方、丁天、王朔、馬原、棉棉、余華。雖然這次筆會以電影《小說》的拍攝為契機(電影《小說》又名《詩意的年代》,導演呂樂于1999年拍攝后并未上映,2007年入圍2007年威尼斯電影節地平線單元,2012年第31屆香港國際電影節首映),但作家們的討論交流始終真實地以自我認知為中心,衍生出關于時代、經濟、個體生命等眾多因素與詩意的關系。對于詩意每個人有不同理解:陳村認為,由虛無的追求變為在破碎混亂的現實中尋找趣味更具詩意;方方將當下生活比喻為打油詩,認為經過歲月的沉淀,可在回憶中品味出更深刻的詩意;丁天認為,物質和金錢的需求似乎將現代生活中的詩意消磨殆盡了,當下擁有一輛車是詩意;王朔則提出,人生沉淪到底打破限制才能看到詩意,才能感受到不同尋常的人生;還有馬原無用的人生的詩意、林白個人意識為中心的詩意;等等。相比大家以自我生命體驗為依據,暢想出關于生活中詩意的思考,阿城的論述則更具“史”味,旁征博引,展現出別樣的詩意。他以古代“歌詠言,詩言志”為依據,說明詩區別于歌,并非直接情感的抒發,而是在行文中產生一種不能用語言表達的東西,即意象。這種無法清楚描述的意象,便是中國詩歌傳統中所展現的詩意。以阿城所言,當代詩歌的沒落,源于當代小說成為時代新意象的新載體。詩意自清末開始,經五四新文學、新時期文學等階段,早已融入描寫當代生活的小說中,現在任何生活都會產生詩意,且不論它是善、惡、好、壞、有德、非德,終究是存留在我們生活之中的。
在雜文《詩與歌不同》中,阿城對詩和意象的概念做出更為明晰的闡釋:“中國很早就對詩另有獨特的要求,才產生了歌與詩的本質區別,即詩須產生意象,以至‘詩言志’的傳統雖然還在,但對什么是詩的判定已轉為‘產生意象的抒情散文才是詩’。”①阿城:《脫腔》,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132頁。而他所談及的意象,并非現代漢語中一般所指的物化的藝術形象。“什么是意象?意象就是韻文詞句排列后,碰撞出一二不能再用其他語音敘述出來的東西,比一般說的感受、情緒要高的東西,王國維稱它為‘境界’。”②阿城:《脫腔》,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132頁。由此而言,意象應是根植內心、發乎情而產生的一種感覺和境界。王昌齡在《詩格》中提出物境、情境、意境三個概念,將對于物、情、意的表現明確指向為相關的境界,即由意象衍生出的詩意。阿城的整體創作意識正是在這種詩性的意象上建構起來的。
在《遍地風流》中,我們可清晰察看到阿城小說對于詩性的意象表達。王德威在北大授課時,曾以阿城的《遍地風流》為例,討論“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的課題。他誠言:“對我而言,我覺得阿城的成就更在于這一本薄薄的《遍地風流》上。”這本“新時期以來的一本奇書”是“我們討論中國現代抒情創作的非常重要——而且是一個必要——的部分”③王德威:《抒情傳統于中國現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第200頁。。抒情傳統于此,便是傳統詩學意象的表現。他將感覺融進數百字的短小篇幅,使每一個故事都獨具神韻,帶來震撼人心的力量。精準節制的語言,幾乎不帶有主觀色彩的描述和任何形容,還現實以真實,卻能感受到溢出紙面的情感,隱晦地蘊含著厚重的詩意。如畢飛宇所言:好的短篇應該是“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遍地風流》如是。
“彼時正年輕”和“雜色”兩部分中,幾乎每篇小說都在描述人們日常中的事物,“大門”“布鞋”“寵物”“提琴”“大風”“白紙”等,這些看似無足輕重的普通意象,卻引申出那個年代在人們心中留下的烙印傷痕。地球物理專業的挖煤工,黑脖子黑臉唯有屁眼兒是白的;山氣日夕佳的秋天,被批為流氓的農婦卻凍得奶頭青紫;莊嚴肅穆的天安門廣場,王建國終于站在五星紅旗下,卻是撒著尿流著淚;一頓飯一斤半的大胃遇得機會到糧庫上班,卻離不開家里的母牛;養不成寵物的金先生最終與一窩老鼠相互為伴;還有火葬郭處長時烤熟的黃豆、孫仁之收到的莫名其妙的白紙、張武常那張繡著毛主席詩句的被子;等等。阿城以“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的態度,將“風流”二字完全下放到民間,以最鄙俗的意象勾畫出世間景象,形成其獨特的詩性表達。“這些描述世俗日常生活的小說直至現在仍然保留著當時流行文學無法比擬的詩意。”④潘文峰:《論阿城小說的啟示》,《文學評論》,2007年第3期。秉持“天地不仁,各自好自為之”的冷峻,阿城為我們細數了一眾平凡如螻蟻,殘喘在傖俗粗糲的世事間的人事。故事中那些不雅的、殘暴的、慘烈的場面看似區別于中國傳統抒情詩學,但是從文學特質而言,這實則是阿城刻意而為的另一種詩性的意象書寫。“他必須要寫到這么粗俗,這么狂野,才能用來作為某一種抒情藝術形式的反省,以及對文類本身的批判,以及接之而來的超越。”⑤王德威:《抒情傳統于中國現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第200頁。如王德威所言,故事在這里成為“衍生的抒情美學”中的一種渡口,如《一千零一夜》般為我們講述一個個寓意深刻的故事,鋪就一張張走向不同的支脈,觸及世間百態的紛雜人生,歸根結底卻凝匯于同一根筋骨,訴說著沉痛的哀思,在蔓延的詩意中尋探那個年代留下的印記。
他以直白流水的方式講述那些普通的故事,卻總能在強烈的意象反差中令人猛然警醒。如小說《春夢》:童年時萌動的愛情散發著甜美的味道,顧直安對曉霞青澀朦朧的情感,卻在時代的運動中變為侵犯毀滅她的緣由。結尾“曉霞光著的兩條腿上是第一次的血,蒼蠅飛起來的時候,沒有血的地方是安直夢里的白”。現實的殘酷血腥與童年夢想般的美好形成強烈的意象反差,紅與白的色彩交疊,涂抹出濃烈的悲涼。
鮮明的意象反差引人深思,而某些平淡無奇的意象書寫中,亦可窺見厚重的思考。和滿街走的女孩子都差不多的小玉準備去插隊了,孤身一人的她不愿放棄一直相伴的鋼琴,眾人費九牛二虎之力將琴拆開托運,最終卻因螺釘丟了,鋼琴變為一堆廢品。“拉弦鋼板靠在隊部的墻上,村里的小孩子用小石頭扔,若打中了,嗡的一聲,響好久。”(《小玉》)戛然而止的結尾令人感到意猶未盡。阿城常常在敘述中突然為故事畫上句號,然而那層意蘊卻如同回蕩在山谷的聲響,縈繞耳畔,引發回味和深思。鋼琴的嗡鳴聲最后仿佛回蕩在耳邊,激蕩起人們沉痛的憂思和對于文化斷失的遺憾。對于小玉而言,鋼琴是她父母離去后與她相伴成長的精神寄托;對于時代而言,鋼琴則表現出那個荒誕年代里文化的斷裂,一切由古至今人們所傳承的文化,都漸漸變為堆砌在角落中的廢品,在勞作中變為無用的存在。另一篇小說《大門》中,阿城同樣以一座寺廟的大門寄予對文化的思考,伴隨著象征中華民族的滔滔黃河,在兩種傳統文化意象的交織回響中,展露那個時代對于青年思想和古老文化的迫害。
二、詩意的氛圍營造
阿城仿若一位內功深厚的絕世高手,云淡風輕地描述出一個故事,卻能產生觸動心靈的力量。他牽引著讀者,在一步步行進間,凝練起一團云霧,聚集起人們的思緒和情感,直到故事結束,好像用一枚無形的針扎破氣球,云霧散去,于是人們也在解脫中體味到一種詩意。詩意不僅存在于意象,更融匯于感受的氛圍。如同李清照的“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雖無物可循,卻能在言語的氛圍中感受到徹骨的悲涼。關于詩意的氛圍表達,古人在《詩經》中便早已有運用。《詩經》中所使用的“興”的表現手法,便是以“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產生一種氛圍,為主題服務,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或“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借河間啼鳴相伴的雎鳩,營造出柔情的曖昧之意,由艷烈明媚的桃花,烘托出浪漫喜悅的氛圍。不同于詩歌的是,杜甫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寄喻國破家亡的黍離之悲,阿城在小說中表現出的,則并非某種單一的純粹的感念,而是糅雜著許多不同的、微妙的、復雜的意象,只能在妙不可言的氛圍中體悟詩意的印記。
《樹王》是阿城代表作“三王”中詩意最為濃重的一篇。小說通篇籠罩在一種凝重的氛圍中,以樹、人、生命、良知奠定了主題的基調,運用神秘主義色彩,將樹與人之間牽連起無形的羈絆。帶著溫熱脈搏的群山大樹,供養著無數飛鳥走獸的生命。信奉革命號召的大好青年們,卻不明自然的力量和規律。在那個無法辨別“好樹”與“壞樹”的年代,似乎也不從區分“好人”與“壞人”的差別。隨著以李立為首的知青們大肆砍伐山林,破除迷信,推進新建設,逐漸激化起與肖疙瘩的矛盾,層層鋪展開肖疙瘩心懷愧疚的往事,突顯出知青們對于革命指令的盲從。最終肖疙瘩用生命為代價的抵抗,喚醒了“我”與讀者們的良知。“數萬棵大樹在火焰中離開大地,升向天空。正以為它們要飛去,卻又緩緩飄下來,在空中相互撞擊著,斷裂開,于是再升起來,升得更高,再飄下來,再升上去,升上去,升上去。”震撼的詩意環境帶動出一種沉痛的氛圍,仿佛有一種東西也從心底里升騰起來,在胸腔膨脹,沸騰擁堵在喉嚨間,幾乎噴涌而出。反思著人們所堅持的“正確”,呼喚著那個時代人們內心丟失的空白。小說結尾,肖疙瘩尸骨上生出片片白花,“也能看到那片白花,有如肢體被砍傷,露出白白的骨”。看似蒼白實為厚重的寓意,將人與自然在貌似疏離卻合二為一的交織中,釀就出各種糾葛的迷茫、惆悵、困惑、苦痛、醒悟,帶來解脫并存留下不盡言表的詩意,直到故事戛然而止,凝重的氛圍卻籠罩心頭,久久無法揮散。
《棋王》《孩子王》中對于氛圍的詩意營造亦斑駁可見。《棋王》通篇將“我”對于人生意義的思索追尋寄蘊在時代的壓迫感和現實的束縛感的裹挾中,隱露著苦悶的氛圍,主要表現在人物的刻畫和環境的描繪上。與傷痕文學不同,阿城“寫文革而不著眼于它所造成的傷痕,而把它們化為一種沉重的時代氣氛、藝術氛圍”①李星:《搭訕的溝回——讀阿城的〈棋王〉〈孩子王〉〈樹王〉》,《小說評論》,1985年第12期。。小說通過對“我”和王一生的人物刻畫,映照出那個時代語境下人們精神世界的消解。王一生對棋的癡迷反照著時代精神文化生活貧瘠的愁苦,對吃的執著影射著現實生活貧困的悲苦。而小說中的“我”作為一個旁觀的講述者,始終有一種晦暗不明的欲望在心頭涌動,“說不清楚,但我大致覺出是關于活著的什么東西”。直至看過王一生棋對九人的一場大戰,才頓悟得“衣食是本,自有人類,就是每日在忙這個。可囿在其中,終于還不太像人”的價值感悟。王一生的吃與棋,表現出時代的饑餓和文化的堅守,而“我”的思考則深化出生命價值備受壓迫的沉重的時代氛圍。在那個充斥著語錄和勞作的年代,人們淡卻了生活的價值意義,無所謂精神的追求和自由,受困于日復一日的苦悶現實。所以,一盤微小的棋局才能在平淡的日子中掀起軒然大波,而“我”在沒有書籍、電影的境況下深切感受到精神的荒蕪。
除了人物的刻畫,在環境描寫中也可感受到這種氛圍描述。小說開篇:“車站是亂得不能再亂,成千上萬的人都在說話。”簡單的一句場景描述卻充分顯現出紛雜錯亂的時代背景下,蕓蕓眾生的離別悲歡。混亂的不止車站,更是人心,是當時所處的時代。小說以一個嘈雜的場景蓄勢并鋪墊出苦悶的時代氛圍。而那場著名的九局連環車輪大戰是故事的高潮,同時也是“我”對于人生價值追尋的突破。阿城以動靜相交的氛圍凝聚起飽滿的情緒張力,亙古的感受從歷史的塵土中蘇醒,現實的生活無限延續,動與靜映襯碰撞,生發出對于人生價值意義的詩意追尋。中國古典詩學善于以動襯靜、化靜為動,講求動靜相宜。車輪大戰中場外“數千人鬧鬧嚷嚷,街上像半空響著悶雷”的情境與場內紋絲不動,只有喉結許久才動一下的王一生構成強烈的動靜反差,緊張的氛圍烘托出這場棋局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感念現實和打撈歷史的交織中,“我”追念起目瞪口呆的劉邦項羽、尸橫遍野的黑臉士兵和提斧野唱的樵夫,生與死的意義得到昭示。
在《孩子王》中,阿城則以一種明暗對比的沖突感表現出感傷的氛圍。如阿城所言,《孩子王》是以一位知青教師的授課方式表現了面對強制的要求而不合作的態度。小說中的“我”初到教室,灰暗而簡陋的桌椅與孩子們閃爍光亮的眼睛形成鮮明對比,凸顯出在那個艱苦的環境中,孩子們對文化知識強烈的渴望之情。在沒有任何設備條件的情況下,“我”企圖根據自己的理解傳授給孩子們最為實用的知識,然而最終卻被組織不認同而罷去了教師的職位。離開時,室外暴烈的陽光和教舍門內黑黑的景象再一次形成強烈的明暗沖突,自然的光亮將孩子們的教室突顯得更為黑暗,暗喻出教育在那個時代環境中的黯然,孩子們的未來更是缺少了光明和希望。“我”對于孩子未來的生活和體制管理下的教育只能表現出無力和傷感,只有以不合作的態度表明自身的堅守,而這一切也只能在明烈陽光和黑暗教舍的對比中,化為傷感的氛圍。
不止《樹王》《棋王》《孩子王》,阿城在其他諸多短篇中亦常常通過氛圍的營造表達情感的詩意。如《節日》,以孩子們天真爛漫的玩樂營造出輕悅的氛圍,卻在浪漫星光和凜冽火光的交融中,顯現出革命戰亂對生命的殘忍無情。季紅真對短篇《樹樁》同樣評價道:“作者在這一個個虛與靜的氛圍中,集結起飽滿的情緒張力,像宇宙時空般永恒的生命價值的意識,便從平凡有限的人生具象中緩緩升起,暗示出豐富的語義內容。大有‘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詩學境界。”①季紅真:《宇宙·自然·生命·人——阿城筆下的“故事”》,《讀書》,1986年01期。他將詩意融于字里行間的氛圍,只有酣暢淋漓地暢讀至尾,才能在心頭升騰起一種感覺,無以言表卻感受至深。可見,阿城通過詩意的氛圍營造,不僅表達出自身的情感和思考,更構建起小說獨特的格調。
三、詩意感覺的生命意識
阿城的小說之所以能給人以震撼的力量,是因為他所講述的、描繪的,并非刻意造作的故事,而是內心感覺的詩意流露。他早已將詩意情懷融匯于自身生命意識的感覺之中,那些澎湃的情感、厚重的體驗、幽深的思考,經由故事散發出來,通過文字鏈接到讀者的內心,產生感同身受般的共鳴。這種飽富詩意感覺的生命意識,不僅存在于他面對萬事萬物所思考的角度、態度,同樣影響了他情感體驗的表現方式與寫作方法。
文字是情感的表達工具,情感才是小說的內核。關于寫作方法,阿城評價自己的創作,就是無關方法,而是將整個的心理現實和心理經驗糅和起來,凝練為自己的心理狀態,以字詞符號的組合流淌而出。讀者之所以在閱讀后產生了或喜、或怒、或哀、或痛的情感,是因為感受到文章所傳達的狀態感覺,這種狀態感覺的形成正是基于他詩化的生命意識之上。
不同于現代派豐富的技巧性表達,阿城的敘述拋離結構主義、意識流、夢幻等藝術技巧,以最簡單直白的線型方式進行表達,順時推進,始終由狀態牽引著故事自己發展,而非自己刻意編造情節環境。“我自己寫的時候有種狀態……你起先也不知道要寫點什么,你也不清楚要說點什么,但是有一種欲望,就像肚子里在練氣功,從丹田里開始走氣了,走上來走到四肢;或者就像里面的水慢慢滿了,到這兒就要流出來,就有狀態了。但一切都是比較模糊的,不能用邏輯去把它分解開,那么坐下來把鋼筆打足了水,把挺白的紙給攤開,[車站是亂得不能再亂],就這么寫下去吧,基本狀態還是寫寫寫,寫到氣數已盡,氣完了,就結束了。”①阿城:《談談我的創作》,《香港文學》,1986年第14期。在阿城的文學經驗中,寫作無關方法,而是文字對于感覺狀態的詩意流露。如王曉明所言:“在具體的描寫上,他總是注意記述原始的感覺,盡量摒除理智的分析和判斷。”②王曉明:《不相信和不愿意相信的——關于三位“尋根”派作家的創作》,《文學評論》,1988年第4期。
反觀“彼時正年輕”及“雜色”諸篇可以發現,小說開頭幾乎都是由人名講起,敦敦實實,不耍花腔,做出一句真實的介紹。《小玉》開頭是:“溫小玉,一九六八年的時候十六歲。”《覺悟》的開頭是:“覺悟是老俞的釋名。”《噩夢》的開頭是:“老俞愛笑,沒有什么可笑的時候,老俞也是笑笑的。”簡短的介紹性文字,如同在宣紙中央落下清晰的一滴墨,隨后自然地暈染開來,甚至衍生出一幅壯闊浩瀚的圖景。順延著作者的狀態前行,我們看到溫小玉在鋪著素花被面的鋼琴上熟睡的模樣,看到覺悟蓄著頭發和人解說自己名字的模樣,看到老俞幾近癡狂的傻笑模樣。這一切看似不正常的狀態,卻都在阿城感覺的書寫下,展現出別樣的意蘊。小玉的鋼琴在上山下鄉的過程中,如同任何具有文化印記的事物一樣,斷裂了意義和價值;覺悟誠心修行后終成高僧,最終卻無法理解現世中“提高共產主義覺悟”最淺白的道理;老俞那不合時宜的令人心驚膽戰的大笑,原來是“文革”中緩解噩夢,落下的毛病。在作者的感覺狀態的牽引下,我們逐漸將故事看似簡白的外衣剝離,深入到那些關于時代、關于人性的主題,看似淺顯,卻蘊含著發人深省的力量。所以才有評論道:“讀他的小說,很難把握以因果為序的線性情節,使你不釋于懷的,往往是那些難于復述的瑣屑之處……恰恰是這些‘閑筆’構成了阿城小說中特有的氛圍和境界。”③蘇丁,仲呈祥:《論阿城的美學追求》,《文學評論》,1985年06期。所謂一千個讀者便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阿城的自然書寫總是展現我們以一個真實。他不予置評,不加形容,任由讀者根據自身生活經驗和情感體驗獲得各自的感受,享受一種詩意的閱讀。
阿城的詩意書寫不僅表達融匯于作品文本之中,發生于創作的過程之源,更延伸至他的生命意識和生活態度里。正是這種秉承著對于生活的詩意情懷,才使得他在創作中展現出一種超脫功利的、充滿古典意趣的境界。這種對于生活的詩意情懷,最集中地體現在《威尼斯日記》的書寫里。與其說《威尼斯日記》書寫的是威尼斯的風貌民俗,不如說它寫的是阿城關于人生的態度、意趣之所在,借威尼斯蜿蜒的河流、雜錯的街巷、別致的鐘樓、華麗的建筑等影射出來,彌漫著藝術的芬芳。在世俗日常的生活中,糅雜進想象性、隱喻性的思考,為客觀世界覆蓋上一層詩意的色彩。
《威尼斯日記》是阿城受意大利官方邀請,旅居威尼斯三個月中所記錄的隨感。日記的形式更為真實而細膩地展現出阿城的思維印記和切身感受,讓我們更好地體會到他對事物的觀察角度、文化心理構成和獨特的審美形式。阿城對藝術仿佛具有天生的敏感,他總能將東方的、西方的、古典的、現代的各方藝術融通,尋到關聯。例如,“威尼斯像‘賦’,鋪陳雕琢,滿滿當當的一篇文章”,期間摻雜著歌劇、雕像、咖啡、電影、《教坊記》、《紅樓夢》,甚至NBA賽事等眾多關于藝術和世俗生活的內容。那些獨具西方藝術形態的所見所聞總能引發出對于中國古典文化的聯想,期間遍布諸多充滿趣味的冷知識。雖然看似無章法可循,卻能從中感受到一種源自心靈的飄忽的詩意想象。
生活中的詩意情懷不僅體現于阿城豐富的喜好興趣,更體現在他對事物的觀察和捕捉中。在觀察中體味生活,在思考中幻想出關于生命的諸多趣味,這種精神自足式的歡樂或許源自知青時期苦中作樂的習慣。年輕氣盛的阿城曾游蕩在偏遠的邊境小鎮,每日勞作、放牛,現實貧困卻換來了相對自由的精神世界。在阿城的回憶中,似乎總能出現一幅他仰望著天空發呆的場景,實則頭腦中或許早已展現出一片意趣盎然的景象。在平淡的時光中發現趣味,在閉塞的環境中享受自在,獨創一方詩意的世界,阿城將情懷變為習慣,延伸至隨后的生活歲月中。在《威尼斯日記》中更隨處可拾見他的詩情趣意。“那個傾斜的鐘樓,鐘敲得很猖狂,音質特別,是預感到自己要倒了嗎?我特地穿過小巷尋到它腳下,仰望許久。它就在那里斜著,堅持不說話,只敲鐘。它大概是威尼斯最有性格的鐘樓。”將威尼斯廣場上的鐘樓比作一個獨特的、猖狂的角色,接連用“預感”“不說話”“性格”擬人化的詞匯賦予鐘樓以人格色彩,仿佛兩個生命在對視交流。他特意穿過小巷尋到鐘樓腳下,仰望,觀察。對于鐘樓的想象,對事物的好奇感,亦是他生活中詩意感覺的展現。詩意不僅限存于生活中對于藝術、文學的多種體驗,更深植于靈魂,反射在看待事物的角度和對世界的情緒。還有那生動形象的比喻:“肖邦彈琴的最大音量,是中強(mf),而我們現在從演奏會得來的印象則肖邦是在大聲說話。”將通俗的事件加以趣味化的形容,帶來忍俊不禁幽默。拋開現實的諸多束縛,阿城總能在頭腦中開創出一片屬于自己的詩意棲居地。
四、結語
從創作到生活,阿城上承古典詩學意象,下接世俗詩性人生,秉持正統“史”味詩學傳統,深入觀照到自身文學創作的點滴之中,以“語言的外在律動與作品氛圍的內在律動恰到好處地發生了共鳴”①蘇丁,仲呈祥:《〈棋王〉與道家美學》,《當代作家評論》,1987年第2期。,傳達出他所追求的感覺和境界。無論是感覺流動的自然書寫方式,還是生活中無所不在的詩意情懷想象,阿城的“詩意”書寫已然根植于生命生活,綻放于文學創作所表達的情緒感覺之中。其文中對于意象氛圍的刻畫,總能在故事結束后,讓人體味到一股撞擊心靈的力量。在阿城的腳步中追尋詩意,不僅讓詩學傳統在當代小說中得以復位,更讓我們體味到內心自由、靈魂豐富的人生美學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