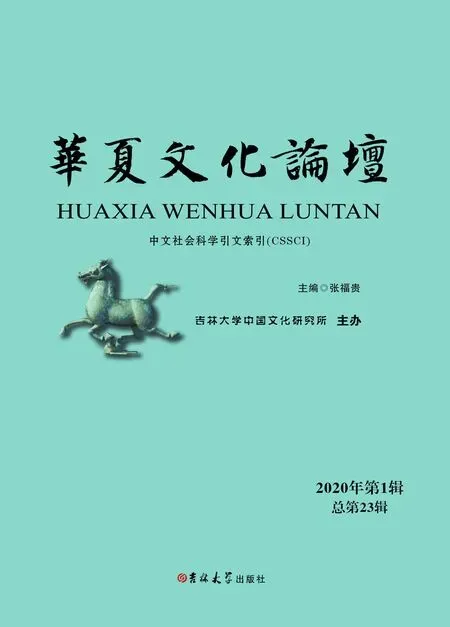“慎言觀”視域下孔子的情感傳播觀念研究
林 凱 謝清果
【內容提要】在語言傳播方面,孔子主張“慎言”,而這種“慎言”觀念背后是各種德性情感在主導:有天道之情的敬與孚,也有人道之情的仁與信等,這些德性情感支配著天與人、人與人之間的“慎言”傳播。語言作為一種具有文化意義的符號,是天與人和人與人溝通的媒介,孔子用譬喻的語言傳播風格以及使用雅言的方式來傳遞德性情感,實現德性情感的互動、共鳴。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在這種德性情感傳播中,孔子的目的在于通過“慎言”來培育個體德性的修養,強化階級之間的互動交流,保持社會秩序的穩固,建構新的理想社會。
《論語·季氏篇》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①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第174頁。文中《論語》的引文均來自此版本。作為繼承周公思想、延續周禮制度的孔子面對這種“禮崩樂壞”、僭越社會規矩的行為是厭惡和抵制的:“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論語·雍也》又言: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于今之世矣。”面對社會失序行為,孔子試圖用其仁政思想來扭轉這一局面,建構新的符合周禮的社會秩序。從語言方面上看,“祝鮀之佞”就是巧言,而“宋朝之美”就是令色。那么祝鮀之佞與宋朝之美便很少有仁的品質,但卻可以大紅大紫,十分顯赫。②畢寶魁:《〈論語〉“不有祝鮀之佞”章本義辨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這違背了社會禮的規范,也就是損德缺仁的表現,正如孔子所言“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
語言作為日常交往的符號,是天人之間和人與人之間交流傳播的重要媒介,它能夠表達人的思想和觀念,也能夠傳遞人的情感和態度,由此改變對世界的認知、提升人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水平。我們通過孔子周游列國及其對弟子教誨的歷史實踐來看,語言成為其游說君王、教化弟子、傳播仁政思想的主要媒介,由此體現了語言強大的說服力和教化的社會功能,這種功能主要是通過語言表達的內容、語言傳播技巧等來完成的。這種滲透于日常交往的語言傳播功能對人的思想和品德的塑造往往具有“潤物細無聲”的效果,常常具有看似細微而殊難抗拒的影響,①沈立巖:《先秦語言活動之形態觀念及其文學意義》,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31頁。正如孔子所言:“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論語·顏淵》)因此,他在交往中是極其注重語言的表達和運用的,整體上看是一種“慎言”觀念。從表面上看,孔子所倡導的“慎言觀”是對語言傳播功能的認知和重視,實際上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孔子對社會等級制度的維護,也就是說,語言傳播不僅不能對社會秩序造成破壞,而且還應該成為恢復周禮、構建新的社會秩序的有力工具。進一步看,“慎言觀”是孔子順應天道、修行人道的德性情感的體現。我們從“巧言令色,鮮矣仁”這句話可以看出,語言和仁這種德性情感是聯系在一起的,語言的表達是內在情感的一種外在表現,在筆者看來,孔子的“慎言觀”背后是德性情感的促動,德性情感成為語言傳播和人際交往行為的基礎動力。基于先秦儒家這種思想背景,本文也將從語言和情感傳播的角度入手來考察孔子“慎言觀”對語言的運用及其背后所體現出來的情感傳播(交往)的內在理路,從本質上探討孔子仁政思想的傳播內涵。
一、“慎言”交往觀及其情感溝通功能
語言作為人類溝通的媒介符號,具有明顯的情感溝通功能和社會傳播效應。而孔子對待語言和使用語言傳播具有特定內在邏輯,形成“慎言”的交往觀念。
(一)孔子的“慎言”交往觀念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②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4版),中華書局,2016年,第1220頁。這是孔子對語言的媒介性質、傳播功能以及語言傳播的謹慎態度。從社會傳播效應來看,《論語·子路》載: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如果說,語言能夠像上文所說的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則有可能產生“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傳播效果。《系辭上傳》有言:“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③黃壽褀、張善文:《周易譯注》(新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705頁。面對語言強大的社會傳播效應,孔子一直都主張在交往中慎重對待語言的傳播。《艮》卦六五爻辭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④黃壽褀、張善文:《周易譯注》(新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579頁。語言傳播應該遵循一定的規則才能消除悔恨,取得較好的社會效果,正如《周易折中》引龔煥云:“艮其輔,非不言也;言而有序,所以為‘艮’也。”⑤黃壽褀、張善文:《周易譯注》(新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579頁。也就是說,這里體現的不是不言,也不是妄言,而是要根據一定規則慎重對待語言傳播。《說苑·敬慎》曾記載孔子關于慎言的故事:“孔子之周,觀于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鳴其背曰:古人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必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這告誡人們慎重對待言語,這里反映出春秋時人際關系中傳播的復雜性。①鄭學檬:《傳在史中:中國傳統社會傳播史料選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第31頁。《論語》中也記載了大量孔子關于“慎言”的言論,譬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而已”(《論語·學而》)、“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論語·子張》)、“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論語·子路》)、“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論語·里仁》)、“仁者其言也讱”(《論語·顏淵》)。從根本上說,這是矜慎內斂、克制自省的精神的體現,更是先秦儒家維護周禮、踐行嚴格的等級制度和禮樂制度中的德性情感的反映。②沈立巖:《先秦語言活動之形態觀念及其文學意義》,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7頁。
(二)語言作為情感溝通的媒介
“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③[晉]范甯:《春秋谷梁傳》,中華書局,1985年,第134頁。也就是說,人能夠運用語言符號是人之為人的本質特征,人可以傳播接收語言符號進行有意義的交流。從口語傳播的角度來看,語言依靠聲音的表達,承載人的思想和價值觀,而聲音的高低起伏則能反映和表達人的內心情感。在孔子所處的春秋末期,語言在社會交往,尤其是在政治生活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功能上,沈立巖認為,“它可以以經驗或神秘的方式影響言者個人和國家的命運,而旁觀者也可以從中窺見這一命運的征兆;它是人格修養和思想情感的不可缺少的表現方式,也是鑒別一人之德行高下和智能賢愚的重要依據。”④沈立巖:《先秦語言活動之形態 觀念及其文學意義》,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8-399頁。筆者以為,在遵從周禮、修己體仁的春秋時期,語言的情感功能是尤其明顯的,這是由于春秋社會人際交往的雙方是在嚴密的等級制度下,以相應的社會身份進行交流,語言傳播活動都須遵守一定的規范和約束,而這種遵循實際上是一種內心情感的體現,或者說是內在情感的約束促進語言規范化傳播和表達。而春秋時期這種內在德性情感的外在表現就是孔子所倡導的“慎言”,也就是說它體現了一種慎重的態度,正所謂:“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論語·憲問》)由此看來,情感可以滲透到整個語言系統,語言系統的幾乎任何可變的方面都是表達情感的渠道和載體。⑤Elinor Ochs and Bambi Schieffelin:Language has a heart,Text,1989(09):7-25.
其實,按照卡西爾的說法,“語言最初并不表達思想或觀念,而是表達情感和愛慕的”,⑥[德]卡西爾:《人論:人類文化哲學導引》,甘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第44頁。“言語有不同層次,最初和最基本的層次顯然是情感語言。人的全部話語中的很大一部分仍屬于這一層”。⑦[德]卡西爾:《人論:人類文化哲學導引》,甘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第49頁。也就是說,語言承載情感的信息要先于語言表達思想和意義,誠然如斯,語言尤其是口語表達,語言的聲音、詞匯、句子等都是情感表達的有效形式,交流雙方通過識別語言中攜帶的情感信息進而協調自己的行為,從而進行順暢的交流。“人情不同,其辭各異”,飽含情感的語言能夠在不同場合、時間和對象上進行入情、合情的傳播,提高語言的傳播效果,實現交流目的。①尚愛雪:《語言的情感化和情感化的語言》,《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刊),2002年第1期。可以說,語言是人際交流的媒介,更是人類情感溝通的橋梁。
不過我們也看到,孔子也曾表達過“無言”的思想,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孔子用四季更替、萬物生長這種“無言”現象來闡釋天道運轉的規律。語言是橋也是墻。“言”可以傳情達意,也會阻礙交流。②邵培仁:《傳媒的魅力:邵培仁談傳播的未來》,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4頁。這也許可以解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傳·襄公二十四年》)中語言的重要性在立德、立功之后。筆者以為,對于其中的原因我們可以這樣思考:孔子對于道的認識更多在于“體認”,而思想和情感的表達更需要語言作為媒介和載體,語言傳播成為體道、悟道的一個階段,對于孔子所倡導的順承天道、仁愛人道的理解和感悟需要自身的沉浸式體悟。
二、“慎言”交往的情感動力
情感可以作為社會行動的觸發因素。③Du Bois,John W.and Elise Karkkainen:Taking a stance on emotion:affect,sequence,and intersubjectivity in dialogic interaction,Text and Talk,2012(32):433-451.孔子主張“慎言”就是在一定情感的支配下形成的社會行為。張景云認為“慎言”作為儒家傳播的一條重要原則受到“五常”的約束,其中,“仁”對言論要求:隱惡揚善、謙遜忍讓,主張木訥、反對巧辯。“義”對言論要求:傳播者內心和諧中正,言談的內容、程度、方式以及時機要根據具體情況而定,將“義”作為選擇傳播對象的依據。“禮”對言論要求:恪守禁忌、符合社會角色的要求、言談態度謙恭、反映“仁”的內在的要求。“智”對言論要求:傳播者的條件、傳播內容的準確性、傳播時機的確定、傳播效果。“信”對言論要求:真實、恰當,“言”與“行”相匹配。“慎言”的實質是通過“五常”倫理制約傳播,維護社會秩序。④張景云:《“五常”與儒家“慎言”傳播思想》,《國際新聞界》,2007年第2期。這是張景云從“五常”的德性情感這個角度進行的歸納總結。筆者以為,“五常”是從人道或者說社會倫理道德層面推動人與人之間的“慎言”行為。在本文中,我們結合孔子承延周公禮制思想以及孔子倡導的仁政理念,將孔子“慎言”行為背后的情感推動力歸納為天道之情和人道之情,從與天溝通和與人交流兩個層面揭示“慎言”交往觀念及其背后的情感動力。
(一)天道之情:敬與孚
這里的天道之情指的是孔子對上天和對君王敬畏的德性情感。這里的“敬”應該要追溯到西周初期周人敬畏上天的思想,這種思想在《尚書》中多有記載,譬如“在后之侗,敬迓天威”,“以敬忌天威”,①[唐]孔穎達:《尚書》,中華書局,1998年,第103頁。“爾尚敬逆天命”,②[唐]孔穎達:《尚書》,中華書局,1998年,第113頁。等等。徐復觀指出:“‘敬’是始終貫穿在周初人的一切生活之中的,這是直承憂患意識的警惕性而來的精神斂抑、集中,及對事的謹慎、認真的心理狀態。這是主動的、反省的,因而是內發的心理狀態。……周人建立了一個由‘敬’所貫注的‘敬德’‘明德’的觀念世界,來察照、指導自己的行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這正是中國人文精神最早的出現;而此種人文精神,是以‘敬’為其動力的。”③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22-23頁。“敬”成為了推動周初人與上天溝通的情感推動力,也只有這種敬畏的德性情感才能承受天命。孔子承延了西周這種對上天的敬畏之情,如《論語·季氏》中有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這種對天的敬畏之情可以說是人與上天的互相確認:“上天的意志最終在人的行為和成就中實現自己,但它不是一種確然無疑的恩命;人通過時刻敬畏、戒懼的自我反思、自我校準去接近它、領會它——天命其實是關于自己道德能力和人類崇高價值的信念,它是由人的道德行為去顯明和成就的。”④李憲堂:《“天命”的尋證與“人道”的堅守:孔子天命觀新解——兼論孔子思想體系的內在結構》,《文史哲》,2017年第6期。除此之外,這里的“敬”也體現在孔子在等級分明的階級中,也就是說,社會成員應該遵守等級中的禮制,對社會這種等級制度抱有敬畏之情,不能逾越和破壞,諸如始終恪守君臣之禮等。這種對上天對等級禮制的敬畏之情使得在與上天和人際交往中慎重運用“語言”。應該注意的是,這些敬畏的情感應該來自于內心的真誠,也就是說不管是與上天相互確認的敬德保民的行為還是遵守等級制度的遵禮行為,都需要發自內心去實踐,應該始終如一地遵守天道和人道。這種真誠的情感,筆者以為就是“孚”的內涵。
孚在《周易》的二十五個卦中都有出現,其以“孚”“有孚”等形式出現,其主要意思是“孚”是一個君子的內在德性,是一種美德。《周易·觀卦》“有孚颙若”,馬融釋曰:“孚,信;颙,敬也。”⑤黃壽褀、張善文:《周易譯注》(新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70-271頁。《說文》“信,誠也”“誠,信也”⑥[漢]許慎:《說文解字》,中華書局,1963年,第52頁。。所以“孚”具有“誠信”的意思,但是這里的“誠信”在筆者看來是一種心中始終秉持的德性情感,是至真至誠的情感,而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的誠信、信任情感(這種含義將在下文探討),朱熹曾經辨析“孚”字與“信”字意義的區別說:“伊川云:‘存于中為孚,見于事為信。’”⑦[宋]黎靖德:《朱子語類》(第3版),中文出版社,1984年,第2969頁。也就是說“孚”更強調內心真誠的情感,而如果體現于外則是一種“信”的情感。《中孚》卦的《彖》傳可以解釋這一點,《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也就是說,中心誠信,譬如柔順處內能夠謙虛至誠,而剛健居外又能中實有信;于是下者欣悅而上者和順,誠信之德惠化萬邦。⑧黃壽褀、張善文:《周易譯注》(新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652頁。“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其業。”①黃壽褀、張善文:《周易譯注》(新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83頁。言辭的傳播要出于誠摯的情感,這是積累功業的一種體現,“敬”和“孚”是君子承應天道、積累功業所應秉持的情感,更是在與天人溝通中主導“慎言”的內在德性情感。
(二)人道之情:仁與信
“仁”與“信”就是仁愛和信任(也包含誠信的含義)的情感,這是人道之情的主要體現,在本文中人道之情是從人際交往層面去重新劃定的。從“仁”的角度來看,“仁”是孔子治國理政的核心,在本文中“仁”是一種仁愛情感,它是人最基本的倫理道德情感,是德性情感的一種。《說文解字》:“仁,親也,從人從二。臣鉉等曰:仁者兼愛,故從二。”②[漢]許慎:《說文解字》,中華書局,1963年,第161頁。這也就是所謂的“仁者愛人”,也就是說“仁”需要體現在人與人的相互交流之中,相互關愛才能體現這種情感,而且在孔子看來,“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基于這樣的愛憎分明的情感,因此,在語言上應慎重表達意見和看法。可以說,“仁”是人性固有的一種溫情和暖意,這種溫情和暖意只有施之于他人才獲得實現,……在孔子這里,仁不是孤立的個人行為,而是一種相互敞開、相互成就的群體行為,這種群體行為共同構成了人類整體存在的超越性。③李憲堂:《“天命”的尋證與“人道”的堅守:孔子天命觀新解——兼論孔子思想體系的內在結構》,《文史哲》,2017年第6期。仁愛情感是貫穿于孔子一切社會交往行為中的,這是推動人際交往和傳播的核心情感。而關于“仁”的內容,孔子認為,“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孔子說:“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論語·陽貨》)其中,“信”的情感也是屬于仁愛情感的范疇,但是因為“信”與語言傳播有更直接的聯系,“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④[晉]范甯:《春秋谷梁傳》,中華書局,1985年,第134頁。語言與人的誠信和信任之情是緊密相關的,它能體現一個人的內在德性情感。因此,本文單獨對這種情感作闡釋。
晁福林就《詩論》的簡文分析過孔子誠信的語言觀念——言所當言。上博簡《詩論》第二十八簡中記載:“《(墻)又(有)薺(茨)》,慎密而不智(知)言。”晁福林認為《墻有茨》反映了夫妻之間應該慎言,但同時也應該“知言”,也就是說夫妻之間的言語交流也要有誠信。對此晁福林引用郭店楚簡《六德》第三十七號簡加以論證,第三十七號簡的簡文講道:“君子言信言爾,言煬(誠)言爾,設外內皆得也。其反。夫不夫,婦不婦,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⑤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88頁。這里強調了君子應當講誠信之言,這樣對人對己皆好。如果不講誠信之言,那就會出現君臣、父子、夫妻關系不協調的違禮局面。夫妻的枕席之言雖然還不能說就是“慎獨”之言,但卻是與之接近的。孔子認為就是夫妻之間也應當講誠信之言,而不可以隨意胡說。……但是孔子認為怕泄露于外而慎言,并非達到了“知言”的標準。君子應當做到的操守之一,就是慎獨,就是言所當言,即誠信之言。①晁福林:《上博簡〈詩論〉研究》,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1043頁。筆者以為,夫妻之間的交流害怕泄露而慎言,但是語言傳播終會泄露,所以孔子認為,最根本的還是應該講求誠信。應該說,“慎言”是誠信交往的一種體現,誠信和相互信任之情更加要求交流雙方應該“慎言”而不是用“巧言”進行傳播交流。
可見,在人際交往中“知言”——誠信地運用語言交流是至關重要的,孔子強調的“信”是建立人際信任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諸如《論語·學而》:“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同時“信”也是決定人在社會生存的重要條件,如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信”意味著,“自我”與“自我”之間通過對共同信用機制的維護,減少人際的摩擦和內耗,最終建立起一種人生道義上的相互承諾關系。故而孔子說“信則人任焉”(《論語·陽貨》)。②李憲堂:《“天命”的尋證與“人道”的堅守:孔子天命觀新解——兼論孔子思想體系的內在結構》,《文史哲》,2017年第6期。因此,人的誠信之情也是推進人際“慎言”交往的重要內在德性情感之一。
三、孔子情感傳播的語言路徑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論語·季氏》)在與君子交往中應該注意時機、察言觀色、要充分表達等傳播技巧,當然也需要規范語言表達的內容,謹慎地使用語言進行情感交流。在孔子遵從周禮、以德性情感為基礎的人際交往中,德性情感作為一種內在動力規范著語言的表達和傳播,在這種規范中,語言作為一種修辭符號自然形成了外在的表達路徑和傳播方式,引起雙方的情感共鳴,促進交流。
(一)“譬喻”:情感傳播的語言表達方式
孔子的“慎言”傳播觀念,其實也包括善于運用語言進行交流傳播的內涵。我們知道,語言是一個復雜的符號系統,具有意義模糊性和解釋性等特征,它總能在具體的語境中被使用并且產生直接意義(denotative)和隱含意義(connotative)。③胡春陽:《人際傳播學:理論與能力》,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68頁。這說明了語言的傳播功能,它能夠直接表達一個事物,也能夠以一種暗指或比喻④[美]郝大維、安樂哲:《孔子哲學思微》,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9頁。的方式來表達,也就是說為了能夠更好地傳達思想,擴展語言的傳播功能,就必須采用修辭。⑤鐘肇鵬:《孔子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143頁。比如,在《論語》中我們看到了孔子在使用語言時經常運用譬喻的手法,譬喻的交流乃是孔子教育的主要方式。《論語·子罕》記載,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為政》篇載,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孔子以此來比喻為學要持之以恒,君王要用德治才能實現人心歸附,等等。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對比的修辭手法,如: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我們通過《論語》發現,孔子大量通過比喻、對比等譬喻的形式來傳遞他的思想,這擴展了語言的表意空間,更有利于受眾進行聯想和解讀。
孔子使用“譬喻”的語言表達方式,一方面以自身作為類例推己及人,把“譬”提升到“仁之方”的高度(郝大維與芬格萊特等認為這種“推己及人”的譬的方式,含有一種推己及人的“恕”的情感,是一種敬意的行為①[美]郝大維、安樂哲:《通過孔子而思》,何金俐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54-355頁。);另一方面從“德”的視角視察自然,將溫潤縝密的美玉對應君子“仁”“智”“義”“禮”“忠”“信”的美德,對應“天”“地”與“道”“德”的本性。這樣,“譬”就不再是一種以類相喻的普通表達手段,而是一種充滿象征意味的言說方式,由此形成“君子比德”的話語傳統。②崔煉農:《孔子思想的傳播學詮釋》,湖南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45-147頁。這種話語傳播方式主要的目的在于通過話語隱喻的方式來表達對上天、君王的參照學習,以及對上天和君王的美德頌揚,以此為參照不斷提升自身的德性水平,從而達到教化的目的。孔子試圖在溝通行為中通過敬意行為再現歷史或當下的美德。這一再現不是借教義和信條,而更多依靠的是經驗的古老資源——行動及其情感氛圍。③[美]郝大維、安樂哲:《通過孔子而思》,何金俐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73頁。在榜樣或參照對象的激發下,傳受雙方建立一種呼應和共鳴,這也揭示了譬喻的另一種含義,也即隱喻的形式,這種形式運用于溝通行為就會喚起交流者獨特的情感體驗。
進一步來看,這種隱喻表達情感體驗的“真”體現在溝通者之間:“讓有耳能聽者自己傾聽。”④[美]郝大維、安樂哲:《通過孔子而思》,何金俐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66頁。一方面這種“真”能夠在現實中有可以參照的榜樣,另一方面這種參照榜樣用譬喻的方式能夠讓每個人都能理解和接受,從而將上天或圣賢的德性真實地落實到傾聽者的身上,可以說,這種譬喻的話語傳播方式能夠實現撒播效應,這一點與耶穌的布道有相似之處。耶穌在三篇對觀福音(《馬太福音》13、《馬可福音》4和《路加福音》8)中都以布道者的形象出現,并以“播種者的寓言”進行布道。耶穌認為,播種者撒播的種子落在不同的土地上,大部分種子不會結果,只有少數能結出果實。這種“撒播”的傳播方式具有自我反思能力,由此,耶穌說:凡有耳者,皆可聽,讓他們聽吧!⑤[美]約翰·杜翰姆·彼得斯:《對空言說:傳播的觀念史》,鄧建國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7年,第75頁。這里的撒播顯然需要傳播受眾發揮主體性去接收信息和自我解讀其中的含義,實現與他者互動。因此,在孔子“譬喻”的傳播方式上,能夠將德性情感撒播在話語交流中引起受傳者的互動,而且隱蔽地將社會等級思想融入其中,在無形中起到規范和引導社會秩序的作用,但其中最重要的在于引導和激發傳受雙方關于德性情感的共鳴,從而調整他們的社會交往行為。
(二)“雅言”:情感傳播的語言材料
《禮記·王制》載:“五方之民,言語不通”⑥[清]孫希旦:《禮記集解》(全三冊),沈嘯寰,王星賢點校,中華書局,1989年,第360頁。,不同地區語言是不相通的,因此,孔子主張應該學習雅言:“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論語·述而》)鄭玄注:“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義全,故不可有所諱。”①何晏集解,皇侃義疏:《論語集解義疏》,中華書局,1958年,第93頁。雅言,就是為了克服語言不相通而制定的標準的語言、語音、語義等,當然對孔子來說,這是為了傳播他的仁政思想,推廣禮樂制度。
在具體的傳播實踐中,孔子鼓勵弟子們學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字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而且如果不學詩,則無以言。(《論語·季氏》)一方面,孔子在教習詩、書、禮儀和執行禮儀的過程中采用雅言;另一方面,孔子傳承了西周雅言賦誦的方法,不僅誦讀,而且弦歌。②崔煉農:《孔子思想的傳播學詮釋》,湖南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42-143頁。在這些學《詩》的諸多功能中,我們主要考察學習《詩》這種雅言材料對于情感的激發和傳播的意義。誠如上文所言,誦讀和弦歌的方法能夠將《詩》這種雅言的情感功能發揮出來。《詩》可以興,也就是《詩》能夠激發人的內在激情和心志,這是情感表達和傳播的起點。《詩》可以群,也就是誦讀和傳播可以讓眾人一起參與詩歌的創作和誦讀。孔子主張“泛愛眾而親仁”(《論語·述而》),也即教育的普遍化和仁愛的廣泛施與,《詩》為百科知識的淵藪、人生經驗的教科書,對于知識的增進、性情的陶冶、意志的引導具有極大益處,能在一個“無辭不相接,無禮不相見”③[清]孫希旦:《禮記集解》(全三冊),沈嘯寰,王星賢點校,中華書局,1989年,第1299頁。的社會環境里產生合群親眾的效果。而且作為藝術的詩歌,還特具一種情緒的感染和共鳴機制,沉吟涵泳之間,足以令人心動神馳、潛移默化以臻于思想、情感的同化與調諧之境。④沈立巖:《先秦語言活動之形態觀念及其文學意義》,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4頁。這里的“群”不僅是表明《詩》的學習和傳播對象具有廣泛性,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在群體的學習中引起情感共鳴,由此,《詩》中的內涵以及所蘊含的德性情感得以傳播和內化。
與此同時,《詩》可以“怨”,也就是可以抒發不滿的情緒,《說文》有言:“怨,恚也。”⑤[漢]許慎撰:《說文解字》,中華書局,1963年,第221頁。孔子雖以“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論語·顏淵》)、“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論語·述而》)自勵,但并不主張掩飾個人的真實情感,正如:“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論語·公冶長》)在他看來,情感只宜善加引導和調節,而不能強行去壓抑,所以禮“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⑥[清]孫希旦:《禮記集解》(全三冊),沈嘯寰,王星賢點校,中華書局,1989年,第1281頁。,詩歌則為情緒的宣泄提供了理想渠道。⑦沈立巖:《先秦語言活動之形態觀念及其文學意義》,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5頁。通過詩的語言抒發和傳播情感,實際上也是能夠讓情感在禮的規范下得到合情合理的傳播和抒發,這對于穩定社會秩序是有積極意義的。總的說來,雅言的運用能夠讓相應社會階級在社會交往中應付自如,實現有效交際,應該說,雅言的運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社會交往的空間。
四、結語
孔子“言傳身教”并且“述而不作”,可以看出,言說式的口語傳播是孔子所倚重的一種傳播形式。在當時書寫媒介不發達的情況下,語言對于信息傳播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在語言傳播方面,孔子主張“慎言”的交往觀念,這是孔子對于語言傳播的深刻認識。語言作為一種符號系統在先秦時期擔負著特殊社會整合溝通功能,在孔子遵循的尊王忠君的先秦社會背景下,面對禮崩樂壞的社會變革,“慎言”需要對社會秩序進行反思:語言傳播不應對禮制造成沖擊,不能造成社會失序,換句話說,慎言的目的在于通過口語傳播系統在一定程度上維護社會秩序。而在孔子的觀念中,慎言始終是與德聯系在一起的,而且德處于基礎和首要的地位,德引領著語言的傳播方式和語言內容的選擇,以此傳播禮樂制度和仁政思想以及達到雙方德性情感的互動和交流。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慎言觀”對于孔子關注語言的社會傳播效果及其作為人際交往媒介具有重要意義,在語言媒介作用下促成傳受雙方德性情感的交互傳播,從而塑造言行合一、具有圣賢人格和德性情感的君子或圣人,以此通過語言傳播和情感交往來建構甚至維持社會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