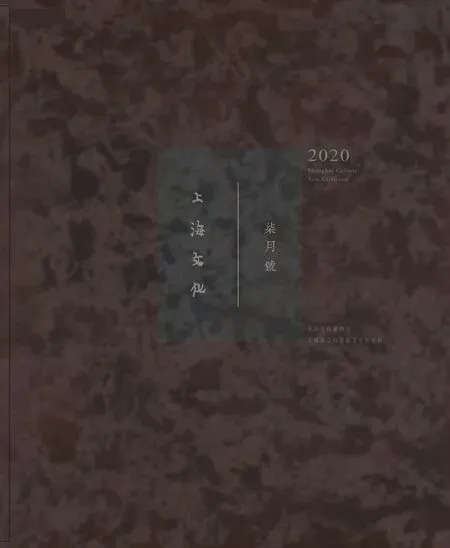當代小說中敘述者的地位①
阿多諾 叢子鈺 譯
因為需要在幾分鐘的時間里,長話短說地談談小說作為一種形式的當前狀況,所以我只能勉強選擇問題的一個方面來談。我想談的是敘述者的地位問題,如今它已經變成了一個悖論:講故事是不可能的,但小說在形式上仍然需要進行敘事。小說是資產階級時代特有的文學形式,從《堂·吉訶德》祛魅的經驗世界開始,小說一直負責對純存在進行藝術加工。現實主義是小說的本質,即使是那些就題材而言是幻想小說的作品,也是試圖通過幻想來暗示現實。小說的這種發展可以追溯到19世紀,并且在今天已經加速到極點,但這種發展方式已經變得疑點重重。從敘述者的角度來看,這一過程是通過主體論發生的,任何未轉化為主觀存在的物質都不存在,結果讓史詩的客觀性或物性也不存在了。比方說,如今如果誰還像施蒂夫特②那樣沉溺于具體的現實,追求物質現實的飽滿和可塑性——這種物質的現實先是被謀劃出來,然后又被虛心接受了——誰就不得不用照貓畫虎的架勢,讓作品沾染了工藝品的味道。作者會為說了謊而感到內疚,在謊言中,人出于愛把自己交給世界,因為假定世界是一個有意義的世界。結果,說出口的卻是帶有地方商業化色彩的、令人難以忍受的媚俗之辭。從主體的角度來看,困難也同樣巨大。正如攝影的出現讓繪畫的日子越來越難,小說也面對著報告文學和文化產業,尤其是電影的挑戰。這意味著小說應該集中在報告文學所不能處理的問題上。然而與繪畫不同的是,小說受語言所限難以從客體中解放出來,結果呈現出一種報告的假象:所以喬伊斯常認為,小說拒絕現實主義,就等于拒絕喋喋不休的語言。
通過把喬伊斯的作品稱為是怪異的、特立獨行的、武斷的來反對他,并沒有什么說服力。生活經驗——生活是唯一使敘述者的立場成為可能的東西——的同一性已經瓦解,不再具有內在的連續性。只需要注意一下,對于一個參加過戰爭的人來說,用人們講述自己冒險經歷的方式來講述這個故事是多么的不可能。如果敘述本身表現得好像敘述者已經掌握了這種經驗,那么聽眾就會顯得不耐煩,充滿懷疑。“坐下來讀一本好書”這樣的想法已經過時了,其原因不僅在于讀者注意力不集中,而且在于故事的內容和形式。因為講故事意味著有一些特別的話要說,而這恰恰是被管理的世界、標準化和永恒的同一性所不允許的。敘述者含蓄地表示世界的進程本質上仍然是個性化的過程,擁有沖動和情感的個體仍然與宿命擁有平等的力量,內向的人仍然能夠直接做完某事,這些看似與意識形態無關,卻正是意識形態本身。隨處可見的廉價傳記文學是小說形式自身消解的副產品。
這類作品在心理學領域占據了一席之地,但也同樣受限于文學的物性危機。心理小說的主體性內容就在它的眼皮底下被搶得七零八落:當記者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學小說贊不絕口時,他在作品中的成就對科學而言,尤其是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來說早已不算什么新發現。不過,他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溢美之詞可能沒有抓住要點:就其作品在心理學上達到的水平而言,它是一種從本質上對知性型人物進行分析的心理學,而不是對我們常見那種經驗型人物進行分析的心理學。正是在這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前衛的。不僅是通訊和科學控制了一切積極的、有形的事物,內向者的真實性也迫使小說打破經驗型人物的心理,去呈現本質及其對立面。社會生活過程的表面越緊密和無縫隙,它就越掩蓋其本質。如果小說想要忠于現實主義的遺產,并講述事物的真實面貌,它就必須通過復制偽造的現實主義來實現摒棄它的目的。一切個體關系的具體化過程,將人的品質轉化為潤滑油,為的是讓社會機器平穩運轉,普遍異化與自我異化需要名副其實的稱呼,在藝術的諸形式中,只有小說堪當此任。從18世紀菲爾丁創作出《湯姆·瓊斯》開始,小說就把活生生的人類與其僵化狀態之間的沖突作為真正的主題。在這個過程中,異化本身成了小說的一種美學手法。因為個人和集體彼此疏遠的程度越深,彼此之間的關系就越神秘莫測。小說真正的沖動本是試圖破解外在生活的謎題,現在變成了對本質的追求,而這種本質,在社會交往所造成的日常隔閡的語境中,現在看來是加倍地令人感到困惑和陌生了。現代小說中的反現實主義時刻,即其形而上學的維度,是由其真正的主題所引發的,在這個社會中,人類既被彼此撕裂,也被自己撕裂。審美超驗所反映的是對世界的祛魅。
小說家有意識的思考并不是這一切的出發點,我們有理由認為,小說家的思考對藝術作品并無益處,正如赫爾曼·布洛赫③的那些野心勃勃的小說。相反,形式中的歷史變化在一些作者那里引起了特定的敏感性,他們就像工具一樣揭示出在作品中哪些形式是需要的,哪些必須禁止,作家作為工具的水平決定了其創作的能力。在厭惡報告文學形式方面,沒有人能出馬塞爾·普魯斯特其右。他的作品屬于現實主義和心理小說傳統的分支,導致小說在極端主體論中發生了解體,這一路線再發展下去就是雅各布森的《尼爾斯·萊恩》④和里爾克的《馬爾特手記》⑤,但它們與普魯斯特已經沒有經驗意義上的歷史關聯。更嚴格地說,小說越是堅持外在事物的實在性,堅持“這就是它本來的樣子”,小說的每一個字就越變成純粹的“似乎”,就越成為現實主義和現實之間的對立。作者無法避免的內在要求——他確切地知道發生了什么——需要證據,而普魯斯特的精確性達到了無中生有的地步,他的顯微級邏輯術使生物的統一體最終分裂為原子,為審美知覺器官提供了所需要的證據,又沒有超出形式的限制。他不可能一開始就把一些不真實的事情說成是真實的。出于這個原因,他周而復始的工作開始于對入睡的回憶,整個第一卷都只是對此的說明,當美麗的母親沒有給男孩一個晚安之吻時,他就會難以獨自入睡。敘述者建立了一個內部空間,這樣他就不用邁出錯誤的一步進入這個陌生的世界,這是一種失態的行為,這種失態會以一個假裝對這個世界很熟悉的人的虛偽語氣表現出來。這個世界被毫不矯揉造作地吸引進了這個內部空間——這一技巧被命名為“內心獨白”——而在外部世界發生的任何事情,都是以在開篇呈現睡著的那一刻的方式呈現的:作為內部世界的一部分,意識流中的一個時刻,受到普魯斯特作品中懸置的時空客觀秩序的保護,不接受任何反駁。例如,德國表現主義小說古斯塔夫·薩克的《一個流浪的學生》⑥,盡管有著完全不同的出發點和不同的精神,但它的目標與《追憶逝水年華》是相似的。在主角埃里克·施密特史詩般的冒險中,小說只描繪那些具體的事物,而這些事物只有在其完整的狀態下才是具體的,結果是抵消了史詩基本的物性范疇。
傳統小說的思想在福樓拜的作品中可能得到了最真實的體現,我們可以將之比作資產階級劇院里有三面墻的舞臺,這種舞臺造成了一種幻覺。敘述者先是拉開了序幕:讀者要參與到正在發生的事情中去,就好像事情是真實存在的。敘述者的主體性在產生這種幻覺的力量——在福樓拜那里——和語言的純潔性中,通過把語言精神化,把語言從它所介入的經驗領域中移除。在反映論中有一個嚴厲的禁忌,這讓它成為反對語言客觀純潔性的基本罪。⑦今天這個禁忌,連同它所代表的虛幻的特性,正在失去力量。人們經常注意到,在現代小說中,除普魯斯特之外,紀德的《偽幣制造者》、托馬斯·曼晚期作品或是穆齊爾的《沒有個性的人》,形式的純粹內在性都得到了突破。新的反映論與福樓拜時代以前的反映論幾乎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后者是道德上的:作者要么支持,要么反對小說中的人物。新的反映論則反對表象的謊言,實際上也就是轉而反對敘述者自己,作家作為一名特別警覺的事件評論員,試圖糾正他無法避免的前進方式。對形式的破壞內在于形式本身的意義之中。直到現在,托馬斯·曼所用手法的形式建構功能才能得到完全的理解,他那謎一般的反諷技巧不能簡單歸結為譏諷,作者以一種反諷的姿態推翻了他自己的表述,拋棄了他正在創造某種真實的東西的主張,然而,這種主張是任何語言,甚至他自己的語言,都無法逃避的。曼顯然做到了這一點,也許是在他的晚期作品中,在《神圣的罪人》和《黑天鵝》⑧中,作者通過愛情主題,運用其特別的語言,表達了敘述具有的偷窺屬性,揭示了幻覺的非現實性。這樣一來,如他所說,藝術作品就變回一個崇高的笑話,這種狀態既缺少樸素性,又是返樸歸真的,它以一種與反映論完全無關的方式,把幻覺當作真理來呈現。
在普魯斯特的作品中,評論與行動是如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以至于兩者之間的區別消失了,敘述者正在攻擊他與讀者關系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審美距離。在傳統小說中,這種距離是固定的。現在它在變化,就像電影里攝像機的角度:有時讀者被留在外面,有時被評論帶到了舞臺上,帶到后臺和道具間。這些極端案例——和典型案例相比,我們從這些極端案例中能更多地了解當代小說——屬于卡夫卡徹底消除距離的方法,他用“震驚”效果摧毀了讀者通常靜思默想地閱讀小說時的安全感。卡夫卡的小說也是對世界的一種預期反應,在小說所預見的那個世界里,沉思變成了笑柄,因為持久的災難不再允許任何人成為作壁上觀的局外人,它也不允許任何藝術家在美學上模仿這種立場。審美距離崩潰了,即使是那些寫下“生而為人,我很抱歉”的作家,也聲稱要去如實報道災難。他們的作品揭示出意識狀態的弱點,這種意識狀態太過短視,無法容忍其自身的美學表達,而且也產生不出適應這種表達的人類。然而在最前衛的作品中,消除審美距離是對形式本身的一種要求,它是打破前景關系,揭示掩藏其背后事物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它揭示出反者道之動。想象也不一定會像卡夫卡小說中那樣取代現實。他不適合成為一個典型。但現實與想象的區別在典型之中是被消除了的。我們時代的偉大小說家有一個共同特征,在他們的作品中,通過“如其所是”的描寫,出乎其自身意料地產生了一系列的歷史典型,在普魯斯特的意識流、卡夫卡的寓言和喬伊斯的史詩謎題中都是如此。創作者表示自己不受具體表現的約束,同時也承認自己的無能;他承認在獨白中間,世界的無上力量重新出現了,這樣就產生了另一種語言,這種語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從敘述語言的殘余物中提煉出來的,它是一種在事物之間進行聯想的變質語言,這些事物也存在于無數與敘述語言相疏離的大眾的語言之中。四十年前,盧卡奇在《小說理論》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是否是未來史詩的基礎,或者也許它們本身就是未來史詩?事實上,當代不錯的小說,算上那些通過其自身動力突然變得收斂的作品,都是消極的史詩。它們是一種自我清算狀態的證明,一種與前個體狀態相融合的狀態,這種狀態似乎保證過一個充滿意義的世界。這些史詩與所有當代藝術一樣,都是模棱兩可的:它們所反映的歷史傾向,其目標究竟是回歸野蠻還是人性,并不是由它們來決定的,而且許多史詩都對野蠻狀態感到太親切了。任何一件現代藝術作品都值得以和諧和放松為樂,但是現代藝術毫不妥協地體現了這種表達的純粹性,并將所有的沉思之樂趣都融入其中,從而為自由服務——這正是平庸作品所背叛的東西,因為它無法見證自由主義時代個人的遭遇。這些作品既不屬于“藝術介入”和“為藝術而藝術”之爭,我們也不用判斷媚俗藝術究竟是理性的還是娛樂的。克勞斯曾經提出這樣一種觀點:在他的作品中,以物質的、非審美的現實形式表達出來的每一種道德,都是完全按照語言的法則,以“為藝術而藝術”的名義獲得的。當代小說的形式從本質上要求廢除審美距離,從而向現實的無上力量投降——想要改變這個現實是不可能靠改變一個藝術形象就夠的,而只能在現實中去做出改變。
? 本文最初為在柏林RIAS(美占區廣播電臺)上的講話,發表于《音調》雜志,1954年5月。譯自Notes To Literature, VolumeⅠby Theodor Adorno,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以下皆為譯者注。
? 阿達爾貝特·施蒂夫特(1805-1868),奧地利小說家,施蒂夫特早期受德國浪漫派的影響,后來卻日益傾向古典主義,擅長細節描寫,對人與大自然關系的刻畫細致入微,其中、短篇小說被認為是畢德邁爾風格(一種源于19世紀的德奧設計風格,相對于洛可可風格而言,是一種比較務實的風格,較少裝飾性,講究簡單舒適)的典范,一戰后名聲日隆。著有《素描集》、《彩石集》、《晚來的夏日》、《維提科》(長篇小說)等。
? 赫爾曼·布洛赫(1886-1951),奧地利作家,與弗蘭茨·卡夫卡、羅伯特·穆齊爾和維托爾德·貢布羅維奇被米蘭·昆德拉稱為“中歐四杰”。1931年完成并發表代表作《夢游人》三部曲。1945年,出版《維吉爾之死》。
? 《尼爾·律內》創作于1923年,作者J.P.雅各布森(1847-1885),丹麥詩人、小說家,曾影響過里爾克與托馬斯·曼等德語作家。譯文可參見《英漢對照名家小說選第二集》伍光建選譯,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小說講述一位無神論者在現實世界的悲慘命運。他的一生由于不信教而充滿了悲劇和打擊,直到在一場戰爭中身亡時,主人公雖醒悟到他悲劇的緣由,卻仍不向宗教妥協。
? 《馬爾特手記》全名為《馬爾特·勞里茨·布里格手記》,是奧地利詩人、作家里爾克的筆記體小說。小說敘述一個出生沒落貴族、性情孤僻敏感的丹麥青年詩人的回憶與自白,某種程度上即是作者自身的寫照。小說由七十一個沒有連續情節、不講時間順序的筆記體斷片構成,這些斷片有共同的主題——孤獨、恐懼、疾病、死亡、愛、上帝、創造等。
? 古斯塔夫·薩克(1885-1916),德國作家,在他去世后不久,其作品才首次被印制,小說《一個流浪的學生》出版于1917年,在文學界引起了短暫的轟動,并受到了諸如雷馬克、榮格、托馬斯·曼和阿多諾等作家的贊譽。
? 此處意為,審美反映論中存在著一個基本問題,就是要求通過純潔的語言來制造出幻覺,讓讀者感到眼前的事情是真實發生的。真實的反映也要求作者使用的語言必須是純潔透明的,讓讀者感受不到作者主體的強烈風格,這種語言的純潔性使語言本身顯得好像是客觀存在的東西,其實是經過了作者主體過濾的主客混合物。因而當反映論本身遭到質疑的時候,語言本身的客觀性也難辭其咎。
? 《神圣的罪人》、《黑天鵝》為托馬斯·曼兩部作品的英譯本名,即《被挑選者》(1951)與《受騙的女人》(1953),前者與《大騙子克魯爾的自白》是作者的最后兩部長篇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