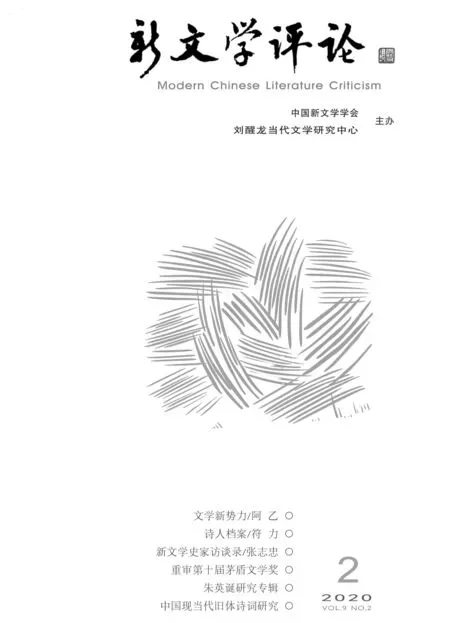北平下的彷徨
——論朱英誕的漂泊詩思
□ 陸之超
“我常自嬉,謂家在江南也在江北;我個人卻生長于津沽與北京——我家寄籍是宛平”①,在朱英誕筆下,“北平”一直作為“江南”的“他者”而存在著,作為地理坐標的“北平”與“江南”這一心靈坐標在身為漂泊者的朱英誕詩歌中互滲交錯,彰顯出詩人與其所處境遇的微妙隔閡的精神懸浮狀態,如何突破這種困境,成了詩人創作生涯中的重要命題。居伊·德波的景觀社會概念認為:景觀社會及其空間是徹底異化的與主體精神分裂的社會與空間,空間遷移與心理地理坐標的背離,將會導致個體對所處境遇產生微妙的疏離感與懸浮感。身處“北平”,心在“江南”的空間錯置感對朱英誕詩心的生成乃至主體生命的構建產生了多維度的影響;在這種錯置狀態下,對現實坐標的“漂泊”感就此生成。本文以居伊·德波的景觀空間理論為基礎,以該視角來探討朱英誕詩歌世界中漂泊主體的身份轉換、漂泊詩思下北平形象的演變以及詩學家園的構建問題,以期進一步理解這位“隱沒的詩神”的內心世界與文本內核。
一、 漂泊下的身份轉換:從“思鄉游子”到“無根的流浪人”
“若然,你要問我出身,我該怎樣回答?”②朱英誕在《神秘的逃難》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在漫長的詩人生涯中,朱英誕始終以“江南人”自居,其祖上在江南為官數代,在武昌城內有一藏書樓,其族譜又在如皋刻印成書。“家在江南也在江北”是詩人對自我身份的注解,然而地理位置與心靈坐標的背離卻導致了詩人對自我身份構建的疑惑——詩人自始至終從未離開過中國北方,“北平”作為一個地理符號在激發詩人濃重的鄉愁的同時,也讓朱英誕陷入了“身心兩地”的漂泊困境。這種困境的發生關涉著空間領域和心理地理學兩個維度,伊凡·齊特齊哥拉夫在進行心理地理學研究時這樣寫道:“先生,我們來自另一個故鄉,我們討厭城市。”“另一個故鄉”所衍生出的情感困境隨著時間的變化與漂泊狀態的轉換,最終導致了詩人在漂泊處境下由“江南游子”向“無根的流浪人”身份的轉變:
在北京這兒,深刻體驗到“寂寞人前”的況味……可怕的狂風……搖撼著紙窗木屋,以及江南游子的魂魄的……③
——1936年《〈小園集〉自序》
1932年朱英誕考入北平民國學院,在寫下這篇自序時 ,在北平已然居住了4年,然而“江南游子”的身份認同始終沒有改變,北方的大風搖撼著他的內心,“可怕”是其在異鄉的情感注腳,郁結的鄉愁啃噬著詩人年輕的靈魂,“歸而不得”的心理境遇由此產生:
描摹著北平的天藍
描摹著北平的天藍/描摹著北平的天藍/最高的時候/最高的山/在你的頭上/月正圓/最快的帆的船
聽見了林中的大風/感到更大的寧靜/而你投下一個黯淡的花影/給我的心的嶺頭
如何描摹北平的天藍?詩人將筆觸投向天空的最高處,在最高山的頭頂,只有一輪圓月孤懸。“月是故鄉明”,“我”看著這輪明月,心中渴望著以“最快的帆的船”回到心中的故鄉。然而這終究是不可能的,樹欲靜而風不止,北平林中的大風呼嘯,搖撼著游子的魂魄,月光照在山嶺上,投下了黯淡的花影,也照在了游子的心上。“我”望著北平的天藍,卻只看見了代表故鄉的明月,風帆不動,心卻如月下孤山一般,黯淡如花。
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年歲的增長,這種情感上的困境產生了微妙的變異,詩人對“北平”的看法有了奇妙的變化:
我在北京居住了二十五年了,但是對于古城的好處仍是覺得不太容易說清楚……因為習慣了,也不甚懷念江南江北的故鄉了……“小劫如風吹已過”,我的心情正是如此……北京有一點容易看到的美妙……④
——1956年《記青榆》
二十多年后,詩人對于江南江北的故鄉卻已然是“不甚懷念”了,對待“故鄉”的心情不再如多年以前那般搖撼震動,而是“小劫如風吹已過”。“小劫”出自梵語,指的是提婆達多受地獄苦報之期間,或指釋尊一劫之壽限,在佛家中代表著漫長的歲月,“故鄉”這一符號在詩人心中流轉千遍,卻最終也如風吹過,讓人“不甚懷念起來”,而先前“可怕”的北平,卻在詩人心中有著容易看到的美妙,雖只是一點,卻也折射出“江南游子”這一身份符號在詩人心中開始逐步消解,詩人似乎開始以北平為家了。
有趣的是,雖然心理坐標與地理位置的長久背離在某種程度上療愈淡化了朱英誕的“江南懷鄉病”,但北平卻終究無法成為詩人繾綣靈魂的真正歸宿,由此帶來的問題便是詩人對于自我歸屬的困惑:
民廿一年夏,我初回北京……看起來或許近似夢游病,我自己卻知道:不過是“游子澹忘歸”罷了……現實與幻美如此深妙的交錯……至此,在“詩的天空”下,我避免了超詩的理想主義的危機。⑤
——1973年《〈春草集〉后序》
不同于從前那個渴望以“最快的帆的船”歸鄉的游子,也不同于那個在北平度過二十五年歲月,感懷北平“美妙”的詩人,朱英誕此時重新拾起了“游子”的身份,雖然清暉娛人,北平的風光仍然對詩人有著深刻的影響,江南故鄉的秀美卻也揮之不去,現實與幻美相互交錯,北平終究不是家,身為游子的“我”卻也忘記了歸鄉的路,在“詩的天空下”,詩人不再執著于返鄉的歸途,而是默默承認了自己身為“無法歸鄉者”的現實,避免了理想主義的危機,卻又在無形之中帶來了迷惘的詩思。
不難看出,心理坐標江南與地理位置北平的長久割裂與背離,激起了詩人對于自我游子身份的消解與重構——精神還鄉的不斷重臨在北方的朔風與時間的浸染下逐漸遠去:從“江南游子搖撼的魂魄”到“忘歸游子”,“還鄉”這一心理癥候逐漸衍生成“無根者”的自我言說:
枕上作
我愿意我的生命如一張白紙/如圣女有她的天堂/日出如昨晚的落霞/我苦于我不知道啊/哪兒是我的家……⑥
“我苦于我不知道啊/哪兒是我的家”,這是詩人對自我身份歸宿的終極質問,圣女有她的天堂,落霞伴生著日出,所有事物都有著屬于他們自己的終極歸宿,可“我”呢?“我”空有著屬于“家”的記憶,然而這“家”卻并不真實存在著,歲月在“我”的生命上留下了屬于她的色彩,卻讓“我”始終無法觸及,“我”陷入了深沉的迷惘之中。正因為如此,“我”渴望著自己的生命如白紙一般,了無牽掛,這樣超詩歌的理想主義是注定不可能實現的。當無根的迷惘取代了懷鄉的夢囈,“無根的流浪人”便取代了“江南游子”,成了朱英誕的詩歌注腳。
從“思鄉游子”到“無根的流浪人”,身份的變化并非單純由于時間向度的延長而產生,心理坐標與地理位置的二元對立的單一結果。回望朱英誕的一生,其人歷經革命失敗,抗日軍興,隨著北平的淪陷,當地的文人們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種“無根”的集體共情之中。作為身陷淪陷區的“留守者”,朱英誕自始至終都游離于時代的主潮之外,然而他對自我身份的不斷發現與重構,恰恰是時代在詩人內心留下的深層次刻印,也是大環境下朱英誕對個體精神與人類共性的敏銳感知所帶來的結果。對自我主體意識的深入發掘,給予了朱英誕詩歌獨一無二的現代性品格。
二、 漂泊詩思下的故鄉投影與再造
波德萊爾認為:“詩不是再造自然,而是創造與自然具有‘契合’關系的超自然的理想世界。”⑦一個從未離開過北方的人,又如何在自己的詩歌中懷鄉呢?在朱英誕的詩歌世界中,作為“江南游子”的詩人努力探求北平這一“異鄉”與內心“故鄉”的契合成分,試圖以此“投影”來療救內心的“懷鄉病”:
晚雨旋晴
……/這時候北平黃昏,像江南/翠尾掃開三月雨……
今年的春天·北平
惟有我的寒碧的小園/像心臟,是最后的一點彌留/實現的夢;江南如在眼前了/當梅子黃熟的時候……
北平曲(二)
長長的街道上平靜的步履/長長的小溪水岸柳飄遠的/長長的北國天深深的邊際/那江南的貴客低低的口笛
這些詩歌在“北平”“江南”之間反復閃回交錯,詩人構造出了北平——江南的意象遷移與交錯,“北平的黃昏、北平的小園、街道、小溪”是詩人面對自然時作為“洞察者”“猜測者”以一種心靈非凡感知所探尋到的語言意象,如同馬拉美所說的“客觀事物”與“意象”、艾略特說的“客觀對應物”一樣,從朱英誕的詩歌中我們看到了西方象征主義詩歌的某種奇妙特質,給予其詩歌以非凡的表現魔力與審美體驗,現實與超現實在詩人的筆下相互重疊,暗含了其生活與精神層面的嵌合維度,“我愛北京,是愛這里特有的秋高氣爽;但是也愛北京的深巷,還有幽居:‘綠蔭生畫寂’,宜于我追懷我的詩的故鄉”⑧。這里的“愛北京”是為了更好地“追懷故鄉”,懷鄉之思至此生根發芽。
事實上,這種懷鄉方式自古有之:“蜀國曾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聲夢斷楚江曲,滿眼故園春意生。”然而“下亭漂泊,高橋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北平”在朱英誕的詩歌世界中成為“客觀對應物”的同時,也是他的“楚歌”“魯酒”,雖得一時清歡沉醉,卻終究“曲高和寡”“酒難消愁”,僅僅作為故鄉投影的北平終究無法療救詩人的懷鄉癥候,隨之而來的便是在北平黑暗長街與墻頭上的惘然游蕩:
孤獨者之歌
各個星座都在我視野里啊!/肉體大可哀——/這是什么樣的墻垣/既推不倒,也不能飛越?/北京的紅墻?/天上的銀漢?/孤獨是一個麗日嗎?/我沉淪于那深林之夜里/誰夢著我是一片月?/任憑日全蝕/月全蝕
原本與詩人思鄉情感相契合的北平在此發生了突變,高聳的“紅墻”矗立在詩人的內心世界,北平上空的“銀漢”隔絕了江南的“日”“月”,誰來拯救詩人?誰又夢著他這個孤獨的江南游子的魂魄?紅墻高聳,銀河廣闊,卻把詩人拘束在一方狹小的“深林之夜”中,詩人想推倒、想飛越這些障礙,卻只能唱出那屬于孤獨者的歌聲,“歸而不得”的沖突在此出現了,“北平”不再是“江南”這個烏有之鄉的投影符號,它在詩人無限的追索中獲得了新的獨立意義:
秋花落
只留下一片影/但歲月無窮/夏天是這樣長長的/像北平的大街一樣長/如此靜默/等待著一場大雪嗎/談談厭倦的故事吧/像冬夜的夢一樣長長的
如同前文所說的那樣,原本作為詩人故鄉的北平,在與“江南”的糾纏互滲中上升成了一個生命、精神震蕩狀態的載體。北平的“影”籠罩在詩人心頭,它的街道漫無邊際且靜默無言,如同冬夜寒冷的夢一般沒有盡頭。漂泊的盡頭依舊是漂泊,“語言的產生/并不能增加或減輕/人類沉默的痛苦”⑨,詩歌對還鄉病的療救終究還是失敗了,“還鄉”的意象契合逐漸變為“無根”者身份錯置的心理沖突。在這樣的沖突中,詩人對“北平”表現出了彷徨無措的心理狀態,進而陷入了時而緬懷時而清醒的雙重困境。
隨著詩人漂泊狀態的空間性持續,這樣的文本性沖突終究還是發生了某種顯著的變化,“北平”的心理指涉第三次有了根本性質的蛻變,如同“游子澹忘歸”一般,詩人與“北平”迎來了某種程度上的心理上的和解:
古城
讓窗飾靜觀你走過/讓商標的孩子引逗母愛/在城市中稍稍停留/快樂的陽光仍高視闊步吧/黃昏的右手卷為風/我也收攏我的黑綢的傘/啊/古城的大街上逡巡/我平靜地走著如在家中
“北平”上空無際的“銀漢”消失了,“快樂的陽光”照耀了下來,詩人走出了《孤獨者之歌》中的那片“深林之夜”,看見了孩子、母親以及古城的大街。北平所象征的“紅墻”轟然倒塌,“平淡沖和”之氣氤氳而起,詩人在詩歌的生成過程中獲得了在“北平”這一古城的寧靜。
百寶箱
……在大街上/正如在平安的家里一樣/走著……
北平大街(二)
步履平靜如在家室/流水伴著垂柳遠去/長長的藍天隨了紅墻/也如流水的流向天邊
“北平的大街”不再如“夏天”一般悠長無盡,詩人的步履不再是孤獨者的彷徨踉蹌,他步履平靜得如在家中,“紅墻”再次出現,卻已沒了先前的高聳,藍天取代了遼闊的銀漢,詩人對江南的思念不再橫亙在心頭,而是如同流水般流向了天邊。
黃昏
疏林的后面無人/寂寞的落日的遠村/我喜歡北平的黃昏/街談巷議里/則有人們來往著/我喜歡北平的黃昏/隱隱的青山啊/夜夜是這時候
先前“長長的”“如冬夜的夢一般”的北平大街消失了,詩人反復運用“家”一詞來表現自己的生存狀態,不同于先前詩歌中“江南—北平”的意象交錯與感官互滲,詩人直白地表達了對“北平”的喜愛之情,北平不再是江南的一面鏡子,也不再是困囿自身的地理牢籠,它成了“江南游子”的“家”,先前文本所表現出的詩人與北平的沖突狀態似乎在此徹底消失了。然而,即使詩人意圖通過“喜歡”“如在家中”這樣的表達來獲取與北平在某種程度上的緩和,賦予其新的詩思路徑與想象空間,但詩人的“無根基狀態”依舊沒有改變:
夕陽
……/胸襟上無須簪野花/這兒是你的家,但無所謂家/荒村野店里沒有悲愁/這兒也無須系著紅旗的酒招牌
“無所謂家”,“沒有悲愁”,即使“小劫如風吹已過”,詩人“無根者”的身份構成依舊沒有任何改變,巨大的空虛感困囿著詩人的內心,代表江南的“野花”“紅旗的舊招牌”在北平“夕陽”的映照下呈現出寂寥的姿態,作為“家”的北平、作為“家”的江南都沒有存在的必要了,頗有杜甫“近侍即今難浪跡,此身那得更無家”(《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的詩情。
從投影到再造,朱英誕對北平的描摹,突破了單純情感的線性維度。折射出在歲月的砥礪下,作為“無根者”的詩人雖開始拒絕先前的彷徨心理狀態,然而“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鶻突,而得滿足得寧帖也極難,所夢想之神圣境界恐不可得,徒以煩惱終其身已耳”⑩。朱英誕在表現出釋然態度的同時,分泌出淡淡的愁緒,這種愁緒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先前的鄉愁,而是詩人在反思自我生存狀態,明白始終無法突破心靈世界的桎梏時所產生的巨大的空虛感,“北平—詩人—江南”三者互相糾纏,帶來的是情感上的復雜轉變:悲愁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對生命境遇的深沉思考。
三、 漂泊中的突圍:從“以詩還鄉”到“以詩為家”
尼采認為,擺脫人生的根本煩惱和痛苦有兩條出路:一條是逃往認識之鄉,另一條是逃往藝術之鄉。樂天有詩云:“心泰身寧是歸處,故鄉何獨在長安。”(《重題》) 事實上,“以詩還鄉”早已有之,陶潛寫《桃花源詩并記》描繪了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社會,這里人民安居樂業,民風淳樸,家家富足,“怡然自得”之象令人神往,然而“桃花源”只是詩人的精神之鄉,他在自我描繪的精神樂土中獲得了心理上的快慰,無論是“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閑適,還是“狗吠聲巷中,雞鳴桑樹顛”的悠然,都展現了詩人以詩還鄉的精神追求。朱英誕受陶淵明影響頗深,無論是“這時候北平黃昏/像江南/翠尾掃開三月雨”(《晚雨旋晴》)這般對“北平”這個借居故土的江南化描繪,還是“我所愛的漁人在哪里/桃花依舊/田舍空了/捕魚的人兒呢/不見”(《懷古》)這般對夢中“江南”的創造性想象,都是對自我漂泊困境突圍的有力嘗試。
然而,相較于古人,朱英誕對“故鄉”“家”的追尋顯得更為深入。心靈與地理坐標的錯位造成了朱英誕“無根者”的主體生成與精神家園的缺失,無論是江南還是北平都無法填補其“無根”的精神困境。當“以詩還鄉”無法滿足朱英誕對“家”這一文化符號的追求時,詩人便不再一味模仿古人將“詩”單純地作為滿足“還鄉”欲求的工具,而是作為“家”本身而存在著,完成了從“以詩還鄉”到“以詩為家”的創造性轉變:“唯有詩是曇花/它還諸一點溫暖給我/……但江南永遠隔在霧里以致霧會變成了雪……”(《試茶》),從而實現了對傳統的超越。
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中針對知識分子的流亡話題提出過這樣的觀點:“如果在體驗那個命運時,能不把它當成一種損失或要哀嘆的事物而是當作一種自由,一種依自己模式來做事的發現過程,隨著吸引你注意的各種事物、興趣,隨著自己決定的特定目標所吸引,那就成為獨一無二的樂趣。”雖然流亡與漂泊并不相同,但二者都讓知識分子們進入了“無所依靠”的精神狀態,面對與自我精神世界徹底分裂的社會空間,陷入“無依靠”困境的詩人又該如何突圍?居伊·德波認為突破的方式之一便是“構建情境”,所謂“構建情境”便是“為了彌合人們的內在精神分離與分裂,為了摧毀平庸化的日常生活所建構的虛假迷人景觀,必須重新建構人們真實的生存情境,必須使人的生活重新成為真實的生存瞬間”。當詩人意識到自己“無根者”的身份事實時,他便不再追尋靈魂的地理歸宿——“這兒是你的家/但無所謂家”(《夕陽》),轉而探索屬于自己的,獨一無二的靈魂歸宿——使生活重新成為真實的瞬間,即詩歌本身作為家園的存在價值:
我在北京度過的三十年間,移居過四次,而五個居處是都夠不上稱作一個小園的,于是我就渴望地幻想我的詩的局面是一座小園了。
——1966年《小序》
對于北平的“小園”,朱英誕是這樣解釋的:“北京,——改稱北平是什么時候的事情?這兒,除了園林深密,幾乎小門深巷家家宅邊有古樹,家家各自形成一個小園……古老的理想‘不取高深,但取曠敞’與當我的繞屋的籬園,更無根本的不同了。”在朱英誕看來,“北平”的“小園”與“繞屋的籬園”沒有“根本的不同”,然而三十年后,在北平移居四次的他,為何稱“五個居所是都夠不上稱作一個小園的”?對此,朱英誕給出了這樣的解釋:“小者,自己也,小園也就是那古老的‘自己的園地’吧?”歸根究底,雖在北平居住了近乎一生,朱英誕卻始終未能尋得“自己的園地”,于是詩人開始幻想“詩歌”本身便是屬于自己的園地了:
水邊商籟
我仿佛悲哀我是沒有家的人/(事實上證明也是如此)/于是我愛自己有自己的鏡子/一個不認識的人和我親密/對語,——但,不許握手!/一個潔凈空曠的世界隔離著/我們,你和我;于是我愛我的/船兒經過,我也愛我的/風經過/也愛我的/樹林經過: 卻不愿想到那死/正如一個受著自殺的誘惑的女兒/而對花睡去/我也愛著/花是我的一面鏡,啊遨游的孩子,/青青天如果是蒼苔/小園里寂靜是繁華的愛! 唉!
這首小詩,是朱英誕以詩歌為家園的最佳注腳,它描繪了一個無家之人,歷經愛、孤獨、死亡,卻依舊堅定尋找屬于自己的精神家園,屬于自己的愛的個體形象。在詩歌中,“我”的內心活動恰恰對應著詩人對“北平”或者說“心理家園”的尋找歷程:
詩歌開篇就表明了“我”是一個沒有家的人,“家”指代的自然是內心的遙遠的江南園地,然而事實上詩人永遠不可能回到那里,于是便流露出了“悲哀”的詩情。“我”試圖從“北平”這一面鏡子中汲取屬于江南的鄉味,“不認識的人”便是詩人想象中屬于江南的自我——可以與之親密、對語,卻永遠無法觸碰彼此。“潔凈空曠的世界”指代著巨大而又無法彌合的時空間距。“一個潔凈空曠的世界隔離著/我們/你和我……”這里詩人凸顯了“你和我”被這個巨大“世界”隔離的事實,這種隔離是如此的遙遠與絕望,以至于詩人不再追索鏡子中的美好,轉而探求“船、風、樹林、睡花”的美妙之處,“于是我愛我的/船兒經過/我也愛我的/風經過/也愛我的/樹林經過……”。這里的詩句有著兩種理解方式:一是詩人愛船、風、樹林的同時,它們也深愛著他,二是詩人愛著這些事物,得到的卻只是沉默的回音。詩人顯然自身也陷入了迷惘與空虛,“卻不愿想到那死,正如一個受著自殺誘惑的女兒/而對花睡去”,詩人最終仍是愛而不得,他感受到了巨大的痛苦與迷惘。此時,另一面鏡子出現了,“花”帶著詩人沉沉睡去,如孩子一般遨游天空,之后夢醒了,詩人的小園中充滿著他愛的事物:船、風、樹林、睡花……卻始終以沉默回應著詩人,“唉”代表著詩人從夢中回到現實,巨大的空虛感擠壓著其脆弱的心理時所發出的哀嘆。
詩人在這首詩中,通過對自我意識的超驗表達完成了對詩歌園地的尋找——漂移中的無家者與鏡中的自己進行著超時空對話,“船、風、樹林、睡花”等在此時由單純的意象上升為其詩歌小園中的構建符號,詩人試圖通過構建這樣的一個詩歌小園,來刺透漂泊境遇所帶來的空虛,抵達詩性內部借以撫慰自身。雖然對于這樣的嘗試,詩人始終報以消極的態度,“愛與不愛”成為詩人熱衷探討的話題,對詩歌園地的熱愛能否反哺自身,讓自己最終取得精神上的補足語慰藉?或許只能以“唉”這樣的嘆息作結,但其在漂泊命運中對于詩歌內部世界的不斷構建和調整,對自我主體的重構與對話,仍在一定程度上舒緩內心難以釋放的無力感與空虛感,同時為其詩歌增添了超越現實與時空的巨大美感。
在《小園集》的跋中,詩人對其創作這樣評價道:“私意以為即此可見少年時之純凈,對人間瑣屑如之和抵抗而復不自覺。”在詩人看來,其詩歌創作本身便是“無根者”自身以“少年”這一飽含情緒的精神載體對人間瑣屑的“抵抗”,“以詩為家”便是對自我困境反抗的一種姿態,這樣的抵抗并非刻意為之,而是歷經歲月磨礪,人世數載之后不自覺之結果。作為時代大潮之外的“無根流浪者”,朱英誕清楚地認識到內心的困境,并將自我的詩學理想、情感流動注入詩歌當中,以期到達詩歌家園的彼岸,或許這條道路永無盡頭,如同《藍天》中所描繪的那樣,“人間的瑣屑的道路/美好而又艱難的道路/永日伸長——”,但朱英誕的抵抗姿態也促成了其較高的詩學成就與現代性品格,其作為“無根者”的漂泊詩思為我們理解他的詩歌提供了一條幽暗的小道。
注釋:
①朱英誕:《神秘的逃難》,《我的詩的故鄉》,北岳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103頁。
②朱英誕:《神秘的逃難》,《我的詩的故鄉》,北岳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頁。
③朱英誕:《〈小園集〉自序》,《我的詩的故鄉》,北岳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5頁。
④朱英誕:《神秘的逃難》,《我的詩的故鄉》,北岳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38頁。
⑤朱英誕:《〈春草集〉后序——紀念寫詩四十年》,《我的詩的故鄉》,北岳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68~69頁。
⑥朱英誕著,王澤龍主編:《朱英誕集(第一卷)》,長江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32頁。本文朱英誕詩歌均出自王澤龍主編的《朱英誕集》第一至五卷,不再另注。
⑦陳太勝:《象征主義與中國現代詩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頁。
⑧朱英誕:《〈小園集〉自序》,《我的詩的故鄉》,北岳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5頁。
⑨北島:《語言》,《北島作品精華本》,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38頁。
⑩胡適:《追憶志摩》,《云游:徐志摩懷念集》,蘭亭書店1986年版,第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