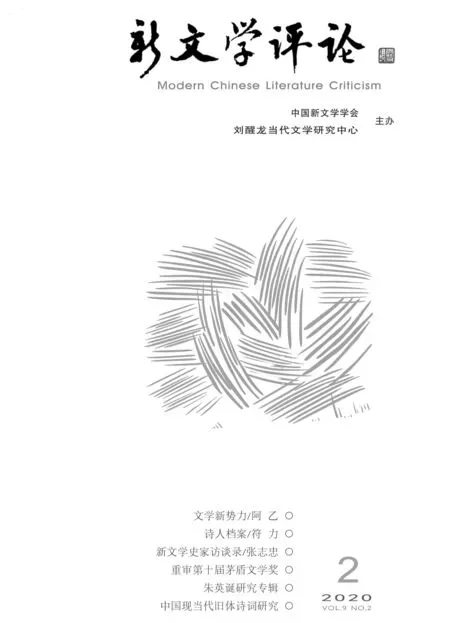以詩還鄉
——論朱英誕的懷鄉詩
□ 任詩盈
故鄉是從古至今的中國文人筆下的一個常見意象,依戀故土是世間萬物之本性,懷念故鄉更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一種民族文化心理結構,在歷代文學作品中被反復書寫。“五四”以后,隨著西方現代文明的傳入與發展,“故鄉”的圖景雖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懷鄉”的傳統雖然出現了斷裂,但在這種斷裂之中也保持了一定的連續性。這一特征在20世紀30年代京派文人的創作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在魯迅等啟蒙主義作家為故鄉祛魅之后,京派文人重新為故鄉賦魅。不僅如此,受到現代文明的影響,他們也以新的視角重新發現故鄉的美,用新的手法書寫著故鄉。同為京派文人的朱英誕也不例外。但區別于其他京派詩人,其懷鄉詩的特殊之處在于想象大于親驗。并非地道“鄉下人”的他一直筆耕不輟地書寫著未曾身至的故鄉江南,甚至將生活過的京津等都市田園化,以詩的方式實現精神還鄉,在荒誕虛無的都市文明之中構筑起“詩的故鄉”。
一、 虛實之間:想象大于親驗的故鄉圖景
故鄉,從地理學的角度來說,主要是指曾經生活過的地理空間;從詩學的角度來說,它包括在這一空間里真實存在的人、事、物等記憶。朱英誕常自嬉“家在江南也在江北;我個人卻生長在津沽與北京——我家寄籍是宛平”①。朱英誕于1913年生于天津,后舉家遷至北平,祖籍江西婺源,寄籍江蘇如皋,家在武昌有藏書樓。從地理空間上來說,朱英誕的故鄉不止一個。在詩中,他反復書寫的故鄉也不止一個。
朱英誕于1913年出生于天津,家在河北首善里,他在津門居住了19年。津沽是朱英誕有跡可循的故鄉。他曾在自傳《梅花依舊》中記錄過一段去西沽村春游的經歷:“我們幾伙伴從河東一個什么地乘船西行,經金剛橋,過大紅橋,不遠就舍舟登岸,一片桃花楊柳黃土,進入視野,令人心曠神怡。這便是著名的西沽村。”②這段經歷也被他寫成了《西沽春游》一詩——“我喜歡小船,搖籃;沿著駝崗/我喜歡碧綠的河流,母親至上:/當我上岸的時候鐘聲彌漫/桃花,楊柳,黃土,波浪!”碧河、桃花、楊柳、黃土、波浪,詩人筆下的西沽之春美好而愜意。郊游打開了孩童自由的天性,他用四個“我喜歡”表達對西沽之春、自由自在的郊游的喜愛與留戀。而這樣的經歷實際上在他的童年中并不多,他曾說,“我只有一個童年值得‘細論’”③,那便是童年與“野孩子”的野趣游經歷,但很快這種自由自在的游玩經歷便被家里人嚴禁了,之后他只能在家中院里讀書、學戲。再加上中學時期罹患淋巴腺結核休學,像“西沽春游”那樣的經歷便更少了。所以,幽居讀書實際上占據了朱英誕童年的大部分時光。而幽居讀書時的窗外之景也被他寫成了《西沽村晨》一詩,透過那一扇“夢窗”,詩人望見“鳥鳴于一片遠風間/風掛在她的紅嘴上/高樹的花枝開向夢窗/昨晚暝色入樓來”,詩人表面寫鳥、風、花、樹,實際上卻是寫夢幻之景,“望晴空的陽光如過江上/對天空遂也有清淺之想”,詩人貪戀的是天空的自由。朱英誕童年在津沽的記憶其實并不如他詩中所寫所憶的那般美好,所以他筆下的津沽雖然有實在之景,但也是想象大于親驗的;他詩中的津沽是鳥語花香、自由自在的,也是帶有淡淡感傷的。
而夢中的江南永遠停留在春天,“江南夢也是江南春”(《暗香》),“江南永遠是春天的故鄉”(《鄉愁》)。江南的春天大多是三月的暮春時節,當朱英誕入夢時,“夢里云彩伴一片風帆/更遠了三月江南”;直到他漸漸衰老,他也始終懷想著“暮春三月,如夢的江南!”。在他的夢想中,暮春三月的江南是繁花盛開的,“江南的茶花香了,/我應該回到故鄉去了”(《白日》),“而魚啊不可脫于淵,/海棠的紅浪,懷戀啊江南!”(《江南》);也是草長鶯飛的,“暖暖的綠草在夢中生長,/江南的家于我是陌生的異鄉”(《夜春詞》),“又是暮春三月了,三月了,/江南的草兒如何? /走近我們的憂愁里啊,/她們將依舊發綠”(《草》),“燕子們輕快地飛舞/早已經成了江南的夢”(《飯后》)。詩人夢中的江南春是美好的,但也是寄托著淡淡憂愁的,海棠自古就是游子鄉愁的象征,春草也在憂愁里發綠,所以游子也多半是徘徊的。《靜寂》中,“江南的游子仍自在徘徊”;《春夜》中,“夜是游子依舊在江南的道上”;《細雨》中,“遠方的游子又徘徊了”,或許是因為“故鄉不可見”(《懷江南江北故鄉》),“我苦于我不知道啊/哪兒是我的家/游子是他鄉的點綴”(《枕上作》)。“徘徊的游子”也有朱英誕自己的影子,他曾說:“我愛江南,雖然我不甚喜雨。傳說中的江南黃梅天氣的那種沉悶,確實把我的懷鄉病打消了大半。”⑤對于故鄉江南,朱英誕在向往中又有些猶豫。
從古典詩人到京派文人,雖然他們對故鄉的懷念存在虛構的成分,但他們筆下的故鄉無不是他們出生與成長過的地方。然而,朱英誕的懷鄉詩中卻多是想象大于親驗的經驗圖景,具有夢幻的色彩。弗洛伊德說:“夢不是指在我們意識的倉庫里貯存的一部分觀念蘇醒,而另一部分還在沉睡。相反,夢是完全有效的實打實的精神現象,換句話說,夢是欲望的滿足。它可以被嫁接到清醒的精神活動鏈中,作用于這個高度錯綜復雜的心智活動中。”⑥夢是潛意識欲望的滿足,朱英誕對故鄉江南、津沽的書寫某種程度上滿足了未曾到過江南的他對江南的向往,也滿足了從小幽居讀書的他對于窗外世界的渴望。
二、 與古為新:源于古典傳統的詩性體驗
詩意的想象必須源出有自,否則便會如空中樓閣一般難以成立。每一個現代詩人實際上都是古典詩詞傳統或顯或隱的接受者,或多或少都會受到傳統的“先在”影響。對故鄉江南未曾有親驗、對津沽鄉野鮮少有記憶的朱英誕對故鄉的想象大多來自從小熟讀古典詩詞的詩性體驗。
朱英誕出身于書香世家,家學淵源深厚。他是朱熹的后裔,父親和母親都曾寫過舊體詩詞,祖母更是能一字不落地背誦白居易的《長恨歌》。年幼時曾讀過私塾,“四書五經”是必備科目。在自傳《梅花依舊》中,他也曾自述:“讀詩史,于屈、陶、二謝、庾信、李、杜、溫、李,乃至元、白以及歷代諸大名家,我無不敬愛至極!但人性難免有其偏至,自覺對山谷、放翁,特感親切;幼時經名師指教,書法山谷,據說很有點意思,故終生不改。”⑦屈原、李白、溫庭筠、李商隱等歷代名家都是朱英誕不勝喜愛的古典詩人。在《江南》一詩中,開頭“秋多悲哀啊古昔的事,/夢之來也像春日遲遲”便讓人想起杜甫《登高》中的“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江南的春天是江南夢,/浮云滿載著游子的光陰;/日落了天更暖了,/春天的夢啊海一樣深”又化用了李白的“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春天的夢啊海一樣深,/春天的藍水流向遠空”更是對白居易“春來江水綠如藍”一句的延伸,詩中鴻雁、落花、明月、柳絮、關山等意象都是古典詩詞中具有鄉愁色彩的常用意象。朱英誕的曾祖父曾在江西一帶游宦,在武漢武昌有一座藏書樓。他所說的“江南”從地理學意義上看應指江西婺源和湖北武漢,但在他的詩中,“江南”卻沒有具體的所指,他對“江南”的想象多來自文學的“江南”。地理區劃上的“江南”在中國的歷史上經歷了多次變遷,但唯一不變的是其對于歷代中國文人知識分子的審美意義和精神文化內涵。文學中的“江南”在歷代文人墨客的不斷書寫之下成為山清水秀、人杰地靈的詩意棲居地,白居易筆下“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的江南讓人不得不憶,韋莊筆下“春水碧于天,畫船聽雨眠”的江南讓人流連忘返,這些古典詩人筆下的“江南”既有共性,也有特性。文學中的“江南”實際上是歷代讀者之精神與作者當時之心境的融合,朱英誕筆下的“江南”也是如此。
深厚的古典詩詞積累為朱英誕的詩意“樓閣”提供了想象的基石,但他對故鄉的懷念卻不是為了復古。朱英誕擷取了“江南”美好而憂愁的一面,并融合進自己的人生經歷,將之升華為現代人共同的生命體驗。江南于朱英誕而言,并不僅僅是一個祖籍上存在但自己未曾踏上的故土,還是“詩的故鄉”、精神的家園,他對“江南”也并不只有懷想這一種情緒。《詩的故鄉》中,他寫道:“江南,/詩的故鄉,/我懷想”,但在具體寫江南夢時,他筆鋒一轉,又寫道:“幸福的旅客,/多么令人羨慕,在山水里徜徉,/落在我的夢中了/你們卻不知道”,在羨慕回鄉的旅客的同時,又表現出對懷鄉情緒的一種智性玄思:當你回到故鄉時,對故鄉的美好想象和向往也就隨之消失,這種情緒是悲喜交加的。又如《樂園放逐——夢回天北望天南》:“我將愿望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而死于懷鄉病/時間渴望我們的平原和語言/哀愁著以致于死。/但這些打攪我的清夢者/知更鳥或是夜梟/因為,這里有我的鄉土的氣味/當我已經沒有了鄉愁的時候”,朱英誕渴望“夢回天北望天南”,但知更鳥或是夜梟驚斷了他的鄉夢,夢斷的他并不像古代懷鄉詩人那般只是憂愁沮喪,因為隱士的心境讓他無論身居何處也能嗅到“鄉土的氣味”。
無論是沈從文的湘西邊城,還是廢名的黃梅故鄉,京派文人在懷念他們的故鄉時,大都是一種回望的姿態。然而,朱英誕對于他的故鄉,卻始終是一種眺望的姿態。朱英誕一生主要生活在京津兩地的城市之中,但在城市的深巷小園里眺望故鄉江南,他卻并不覺得遺憾。在《梅花依舊》中,他曾自述:“摩詰云:‘江南江北送君歸’,不幸,我卻從未到過江南,更不要說江北的如皋了。但我似乎有點冥頑不靈,并不覺其為憾事,那是因為我很愛北京,——自然的老北京。”⑧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北平是一處特殊的空間。1928年,國民政府南遷,改直隸省為河北省,北京為北平⑨。北京從國都變成了地域性城市,政治中心地位喪失,經濟命脈幾近中斷,城市化進程也因此放緩。政局的動蕩和大量城市資源的流失也造成了部分文人南遷,北平文壇出現短暫的“荒漠化”。但滯留在北平的學院派知識分子擔負起了文化重估和再造的使命,他們創辦刊物、興辦文學系,使文化教育帶來的相關經濟利益成為北平的“生命線”。在北平學院派知識分子的共同努力下,北平文化中心的地位不但沒有動搖,反而得到了加強。與鄉村相比,北平的城市化水平仍然相對較高,數百年作為國都的歷史積淀使這座城市具有了獨特的人文風貌;而與新興的大都市上海相比,它又相對缺乏現代都市色彩,保留了自然的一面,常居北平的朱英誕發現并深挖了這一面。1932年回到北平的他看到“全城都在綠樹覆蓋下。天安門前,御河橋南,白石鋪路,馬纓花清香沁人心脾,其細膩風光與前門箭樓之雄偉,不知何以那么諧調!”⑩,他將這些自然之景和歷史之韻升華成了筆下的詩意,寂寞的深巷、長長的紅墻、玉泉山的塔影都成了他詩中的“常客”,曾經繁華的北平變成了一座安靜的“空城”,“長長的街道沒有盡頭”(《北平大街(一)》),“步履平靜如在家室”(《北平大街(二)》)。
都市與鄉村并存的人文地理環境讓北平有了與江南類似的詩情畫意,但冬春季惡劣的自然天氣仍然是無法改變的客觀現實。北平的詩意來自都市與鄉村并存的地理環境,更源于朱英誕平靜而自然的隱士心境。北平“冬春雨季的大風,那種可怕的狂風,像一團棕黃色的大霧,而又聲震屋瓦的搖撼著紙窗木屋,以及江南游子的魂魄的,虎虎的大風,刮起來時,屋里的燈光卻更明亮,心境卻更平靜,冬天的,春天的狂風,就是它似乎也來得自由自在,自然而然!”面對北平冬春季肆虐的狂風,朱英誕非但不感到煩悶,反而多了一份悠然自得。這份悠然自得實際上也來源于古典詩詞傳統的陶冶。眾多的古典詩人之中,陶淵明當屬朱英誕心頭之最。早在童年啟蒙時期,朱英誕便和陶淵明結下了不解之緣。《桃花源記》是他的父親在他幼年時教授的窗課之一,《蘇書陶集》更是他童年時“偶竊閱之”的一本詩集。隨著年歲的增長,朱英誕對陶淵明的好奇也逐漸轉變成理解、喜愛甚至欽慕。他曾說:“予酷喜陶詩,拜讀過四十年,亦惟此將終其身不去手耳。”他不僅在詩中多次贊頌陶潛之氣節、化用陶潛之詩句,更重要的是他從陶淵明的詩學實踐中悟出了藝術的真諦。《桃花源記》是被朱英誕熟讀多遍的陶潛作品,清代陳朗山楷書的《桃花源記》更是被他一直懸掛在床頭。《西沽春游》一詩中的西沽村并不像一個北方的鄉村,更像是陶淵明筆下的桃源世界。朱英誕認為陶淵明創造的桃花源是一個超現實的心靈世界,他所追慕的不是古風,而是陶淵明的隱士心境。這種隱士心境讓他即使沒有“歸園田居”,也能盡得“田居之樂”。
高潮看到田卓站在落地窗戶前,望著窗外,抽著煙,似乎在思索著什么。晨曦柔柔地照射進來,裊裊升騰的煙霧中,田卓如瀑的秀發窈窕的身姿顯得超凡脫俗,恰似一幅絕妙的剪影。高潮心里一下子產生了沖動,想悄悄走過去,從背后輕輕地擁抱一下田卓。但高潮沒敢造次,他想到了紅光滿面鶴發童顏的馬老。盡管馬老有意想把高潮和田卓往一起扯,但越是這樣,高潮越覺得田卓跟馬老的關系深不可測。
江南與京津在地理學意義上分屬中國南北,在文學意義上也有截然不同的文化內涵,但朱英誕卻發掘了它們共同的詩意。古典傳統給予朱英誕的不僅是一種對故鄉的詩性體驗,更是一份“大隱隱于市”的隱士心境。
三、 歸趣現代:都市文明之中的精神還鄉
在《略記幾項微末的事——答友好十問》一文中,朱英誕曾說:“外來影響與傳統不能偏廢,歸趣仍在現代,這更是自明的事。”置身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都市北平之中,任何對于故鄉的懷念都不可能是傳統詩思的自然衍生,特別是對于朱英誕這樣一個七十年人生中只有三段短暫鄉村經歷的詩人而言。
朱英誕對都市北平的田園性書寫實際上來源于其久居京津等都市之中的現代性體驗。正如吉登斯所說:“我們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個可怕而危險的世界。這足以使我們去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麻木不仁,更不是一定要去證明這樣一種假設:現代性將導向一種更幸福更安全的社會秩序。”現代性具有雙重性的指征,一方面它使生活和交往更加便利,另一方面又具有一定的危險性和陰暗面。久居都市之中的朱英誕洞察到了這一面。他筆下的都市是個“不夜城”,這個“不夜城”“完全是灰色的墻垣/遮攔在眼前(夜來,/他們消失了。)而腳步/遂永無休止//但只有高聳的廣告牌/點綴著虛無的天和海/那些星辰更高了,吸煙的女郎;/它們是一些虛無主義者/……那旋舞的燈火是一些狡兔/它們有著太多的洞窟/而我慶賀著肉體,‘可愛的/你美好的廢墟’!”(《不夜城》),“不夜城”里的墻垣是灰色的、燈火是如狡兔般迷幻的、都市女郎是淫蕩的,整個城市都充滿著波德萊爾式死水腐城的氣息;都市的“白晝里也頹廢如夜”(《都市小景》);現代都市于朱英誕而言更像動物園里的樊籠,他“不明白為什么一定要/把人們送空中,/然而再推落到地下”(《都市在夢中》),在都市里,他看不見自然的風,只看見煙囪里的煙和風吹過建筑工地時翻起的土潮。所以他恐懼,他“對‘汽車文明’驚奇著”“像穴居人的不安定”(《只要還是生存著》);他選擇“遙望都市的燈火”(《夜之寶藏》),他對都市文明是反思的,“而這時候我的沉思會靜靜升起,它將高過那數層的都市的樓了”(《第一個記憶》),一個“高”字說明了他對都市文明反思的超越性。同時,相較西方的現代都市,現代中國的都市文明的特殊之處在于它本就是殖民經濟下的畸形產物。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雖然城市化水平不高,但是城市化帶來的問題卻十分突出,而且時刻面臨著戰爭的威脅。“和平在哪兒?/戰爭在哪兒?/這微弱的蠕動,/在民眾看來;更微弱了,/所謂‘外交’和和平”(《只要是還生存著》),和平的不可得使肉體的生存都變成一件困難的事情,現代文明的侵蝕又使人們失去精神上的支撐。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都市北平是安靜的,也是落寞的。這座“古城”就像艾略特的“荒原”,承載著朱英誕對人類歷史的宏大反思和現代性焦慮。朱英誕在北平深巷中書寫著《鄉愁》:“夜深,我醒來,傾聽/那布谷鳥/從遠方飛到南方/(你叫得太坦率啊)/帶著柳樹憂郁的濃香,/這兒,與你無關,/幽居的微光?//唉,被自然遺棄的/人類啊,應該明白/你是主人還是客子?/裂帛的笛,竹嘯/恐嚇著沉睡的原野/而大笑?//春天,什么時候告別的/雷音從來不驚夢中人/江南永遠是春天的故鄉/這兒,花開花落都是寂寞的;/夢也永遠存在/于清醒的肌肉里。”布谷鳥已經從遠方飛到南方,可詩人仍在北方;柳樹在古典詩詞中本就有思鄉之意,可南方的柳樹濃香卻與幽居北方的詩人無關;“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李白《春夜洛城聞笛》),深夜的笛聲是最能觸動懷鄉之情的,可詩人卻將其夸張成一種恐嚇的情緒;故園江南永遠是美好的春天,而詩人身處的北方,無論是哪個季節都是落寞的。朱英誕融合了象征主義筆法,從感覺出發,抓住夢醒時分的那一剎那,調動眼、耳、鼻等多種感官甚至肌肉記憶去描寫對故鄉的復雜情緒。這首詩中雖然全篇都不見都市的身影,但一句“唉,被自然遺棄的/人類啊,應該明白”卻道出了詩人想表達的已不僅是古代懷鄉中的思鄉愁緒,更是對自然風物、鄉土文明的一種依戀。詩中的“江南”不只是詩人祖籍上的故鄉,更是一種鄉土文明、古典傳統的指稱。
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傳入,的確給現代中國的發展帶來了“良方”,但這種“良方”也有“副作用”。現代化的機器生產在帶來物質文明進步的同時,也擠壓了精神文明的生存空間。于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象征主義詩人而言,象征主義更多的是一種技法與風格,詩人多在“世紀末”的憂郁頹廢情緒中尋找認同。但于三四十年代的京派詩人而言,象征主義則更多的是一種寫作哲學,他們不僅對象征主義的寫作技巧進行了融會貫通,還對其背后的文學觀念和思想背景作了更深入的把握與理解。他們并沒有像他們的西方現代主義“老師”那樣走向荒誕虛無,而是在古典傳統中找到了調節緩解“副作用”的“藥方”。
于朱英誕而言,這“藥方”是古典傳統中的隱士心境,也是哲學意義上的“詩”。朱英誕發現,都市文明荒誕虛無的背后是實證主義哲學的興起。實證主義哲學逐漸取消了哲學的批判向度,它全力擁抱現實,把各種形而上學、先驗論和唯心主義當作蒙昧主義的落后思想加以反對。所以,他對以“唯物論”“實用論”為代表的“工具理性”充滿了懷疑,他認為這實際上導致了精神文化的退化。現代哲學變成了一種“觀念”,而現代社會則成為“觀念”的世界,理性擠占了感性的空間,所以《挽歌》一詩的副標題是“先是生活,次是哲學吧”,這個“吧”字充分體現出一種游移不定。于朱英誕而言,如果哲學是一種“理性”的“觀念”的話,那么詩更像是一種感性的哲學,“歷史像流水逝去,/哲學像山果墮落;/惟有你啊,詩啊,/讓城市化作農村”(《詩》)。在諸多文體和藝術門類之中,詩歌可以執行偉大的思想任務。崇尚智慧的朱英誕認為“詩”是“智慧事業”的一種,它能“幫助‘實用的再生力,再生,再生不已’,而與‘促進人類社會永恒福利’之各種‘智慧事業’并行而不悖”。朱英誕認為的“智慧”實際上象征著人類精神中某種永恒的東西。在“皮肉都須仰仗鋼鐵”的年代,詩歌能夠讓人并不只像一個呆板無味的機器一樣活下去,它代表了人類更高的追求。在詩的世界里,他發現了古典與西方兩種傳統的某種契合之處,無論是他朝思暮想的江南抑或是他崇拜的陶淵明構想的“世外桃源”,實際上都是具有超越性的精神世界。詩是朱英誕還鄉的途徑,更是其還鄉的目的,“詩”與“鄉”是同構的。在“哲學像山果墮落”的年代里,詩就是精神的發源地。
朱英誕懷念的故鄉實際上是多元的精神發源地,帶有一種“生命原鄉”的性質。朱英誕渴望用懷鄉的方式、用詩的方式構筑起精神家園,但同時他也明白“在鄉下重建都市”是虛妄的事情,因為“一個鄉下孩子來到都市/(學本事到鄉下去重建都市?)/才不服水土”(《都市在夢中》)。政治經濟中心的南移,一方面讓北平在現代化浪潮之中保留了一份雍容與寧靜,為朱英誕的懷鄉書寫提供了自然與人文環境;另一方面也讓北平變成了一座“孤城”,增加了它被現代社會秩序拋離的風險,加深了朱英誕的焦慮。朱英誕深知,現代文明的發展是不可逆轉的事情,僅憑個人的力量難以扭轉其荒誕虛無一面給人帶來的消極影響,想要回到鄉土文明的田園牧歌時代不啻堂吉訶德式的幻想。所以,他只能無奈將詩歌轉化為一種完全個人化的“生存哲學”,通過詩歌的方式回到精神的故鄉,用以抵抗精神的死亡。
注釋:
①朱英誕著,王澤龍主編:《梅花依舊——一個“大時代的小人物”的自傳》,《朱英誕集(第九卷)》,長江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542頁。
②朱英誕著,王澤龍主編:《梅花依舊——一個“大時代的小人物”的自傳》,《朱英誕集(第九卷)》,長江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549頁。
③朱英誕著,王澤龍主編:《梅花依舊——一個“大時代的小人物”的自傳》,《朱英誕集(第九卷)》,長江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547頁。
④文中引用詩歌均來源于王澤龍主編的《朱英誕集》第一至五卷,長江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
⑤朱英誕著,王澤龍主編:《〈小園集〉自序》,《朱英誕集(第一卷)》,長江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209頁。
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若初譯:《夢的解析》,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97頁。
⑦朱英誕著,王澤龍主編:《梅花依舊——一個“大時代的小人物”的自傳》,《朱英誕集(第九卷)》,長江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540頁。
⑧朱英誕著,王澤龍主編:《梅花依舊——一個“大時代的小人物”的自傳》,《朱英誕集(第九卷)》,長江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542頁。
⑨吳惠齡、李壑編:《北京近代高等教育大事記》,《北京高等教育史料》,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 第408頁。
⑩朱英誕著,王澤龍主編:《梅花依舊——一個“大時代的小人物”的自傳》,《朱英誕集(第九卷)》,長江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5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