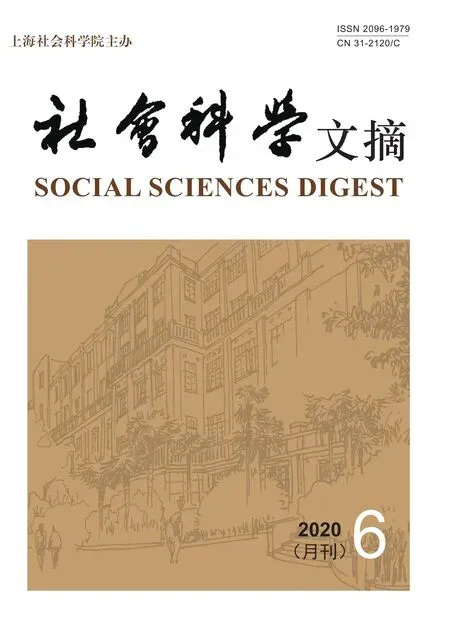非繳費型養老金:“艾倫條件”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變遷與改革出路
文/鄭秉文
“非繳費型養老金”是指來自財政轉移支付的養老金,是相對于繳費型養老金而言的另一種養老金形式。而繳費型養老金是指國家以立法的名義建立的養老保險制度。從資格條件上講,非繳費型養老金一般可分為家計調查式、普惠式;從待遇計發方式上,可分為定額式和最低養老金補差式;從歷史淵源和發展現狀看,它最早誕生于1891年的丹麥,只比其鄰居德國首創的繳費型養老金晚兩年,最近的非繳費型養老金是2013年誕生于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公共福利金,截至2014年,全球已有113個經濟體引入建立了非繳費型養老金制度。
從上述定義看,中國目前似乎還不存在非繳費型養老金,討論這個話題似乎不合時宜,因為在過去5年里,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社會保險階段性降費持續至今。其實不然,中國目前有一支非繳費型養老金: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下簡稱“城鄉居保”)。
問題的提出:城鄉居保投資改革的深遠意義
建立于2009年的城鄉居保與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下簡稱“城鎮職保”)一樣,采取的也是統賬結合模式,其養老金由基礎養老金和賬戶養老金兩部分組成。其中,基礎養老金每年直接由政府全額支付;賬戶養老金由個人繳費形成,地方提供一定的財政補貼,實行完全積累制,統籌水平以縣市統籌為主,全部存儲在地方銀行,以金融機構人民幣一年期存款利率計息,低于同期CPI水平,處于貶值風險之中;從理論上講,賬戶基金存在著隨時被用于支付基礎養老金的可能性,這就意味著制度正處于“搖擺”之中,DC型(繳費確定型)完全積累制的個人賬戶有可能像城鎮職保的個人賬戶那樣,存在著走向名義賬戶(NDC)的潛在“風險”。
但是,2018年和2019年人社部和財政部連續聯合印發了3個文件,明確規定各省(區、市)城鄉居保基金分三批于2018、2019和2020年完成委托簽約和啟動投資體制。筆者認為,賬戶養老基金投資改革完成之后,城鄉居保成為名義賬戶的可能性幾乎將不復存在,投資改革使基礎養老金作為非繳費型養老金制度模式趨于定型,這就將一個“老話題”再次推向前臺,即統賬結合的城鄉居保的制度屬性究竟是保險制度還是福利制度。
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城鄉居保存在的一些問題正逐漸顯露:一是在社會輿論和普羅大眾那里,城鄉居保的養老金水平自然要攀比城鎮職保,很容易導致城鄉居保參保人的心理落差;二是從財政負擔的角度看,未來幾十年里城鄉居保替代率與城鎮職保“拉平”的可能性幾乎沒有,但其基本訴求將成為城鄉居保的焦點之一;三是城鄉居保參保人必將經歷一個從滿意到比較滿意,再到不滿意的過程,2009年建立新農保時農民歡呼政府打破千百年來“養兒防老”的傳統,但當第二、三年他們沒有看到像城鎮職保那樣每年上調待遇水平時就逐漸開始產生不滿。對此,多年來,許多學者對城鄉居保的屬性提出質疑,認為目前制度屬性“名不符實”的模糊狀態不利于其長期發展,認為城鄉居保明顯存在著制度定位不準確、過度依賴財政補貼等制度結構問題。一位學者型官員認為,城鄉居保的福利化程度已超過90%,福利剛性使得城鄉居保與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模式的初衷漸行漸遠,過度福利化使財政壓力增大,城鄉居保攀比城鎮職保的趨勢將不可避免,在基層調研中常常聽到很多基層政府反映說,要求“同城同待遇、同制度同待遇”的呼聲越來越多,地方財政壓力很大,希望中央政府加大轉移支付力度。該學者型官員發出城鄉居保“向何處去”之問,呼吁城鄉居保完全福利化的情況不符合目前中國國情,也是不可持續的,城鄉居保不能丟棄個人和家庭的基本養老責任,為此提出將城鄉居保的基礎養老金改為“養老津貼”的建議。
筆者認為,既然投資改革之后,城鄉居保基礎養老金“非繳費型”養老金地位將逐漸定型,并與保險制度漸行漸遠,為進一步明確城鄉居保的制度屬性和功能定位,同時也為進一步強化各級財政的預算約束,防止福利剛性及其進一步泛化,將基礎養老金適時改為“養老津貼”不失為一個長治久安的改革趨勢。
文獻與理論: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變遷與“艾倫條件”約束
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經歷了起起落落的曲折發展道路:1986年老農保開始試點,1992年正式推出,1999年出現停滯,2009年建立新農保,2011年建立城鎮居保,2014年新農保和城鎮居保合并為城鄉居保,2018年開始實施投資,2020年全國范圍完成投資體制改革,至此,城鄉居保最終趨于定型。在農村養老保險制度35年的發展歷史中,老農保1999年經歷了長達10年的停滯期,新農保2009年建立前后又經歷了幾年的“新”“老”兩個養老保險的制度疊加、銜接、更迭的過程。在同一社會政策領域出現如此曲折并最終“新”“老”兩個制度版本實現更替的情況,這在中國改革開放史上是不多見的。
(一)DC型完全積累制“老農保”的誕生與停擺
老農保的啟動始于1986年,截至1995年已覆蓋30個省份1400多個縣市,26個省份制訂了地方法規,參保人數近5000萬人。到1999年,全國參加老農保人數超過8000萬人,累計收取保險基金184億元;1998年向60萬人發放養老金2.5億元,人均42元。但1999年老農保不得不停辦。在老農保“停辦”10年之后的2009年正式建立新農保,這標志著老農保退出歷史舞臺,效仿城鎮職保的統賬結合型新農保開始履行其歷史使命,非繳費型的基礎養老金正式引入并運行至今。
(二)“艾倫條件”對“新”“老”農保嬗變的三個深層解釋
學術界對中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變遷的原因進行了分析,有代表性的觀點可歸納為以下八種:機構改革論、管理體制論、基金貶值論、金融風險論、資源結構論、政府責任缺失論、發展階段論、制度供給低效論,等等。但從經濟學來看,老農保的淡出也好,新農保的誕生也罷,甚至今天城鄉居保投資改革也都算在內,中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35年的變遷史可用一個定理予以解釋,那就是艾倫條件:在GDP高速增長并帶動社會平均工資高速增長的條件下,建立個人賬戶式的長期儲蓄型養老金制度必定是不受歡迎的,因為從經濟學理論上講,根據艾倫條件,作為生物收益率的社會平均工資增長率與人口自然增長率二者之和大于實際利率時,DC型完全積累制的養老金制度就必定是不可取的,這時,DB型現收現付制則是有效率的,可實現資源配置的代際帕累托最優。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GDP年均增長率9.5%,按不變價格計算比1978年增長了34倍;在經濟高速增長帶動下,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978年的人均171元提高到2019年的30733元,扣除價格因素,增長了23倍,年均增長率超過8.5%;同期中國人口年均自然增長率為0.9%;相比之下,農保基金在銀行協議存款的利率扣除通脹因素之后大約在2%~3%左右,大大低于生物收益率,他們之間存在6至7個百分點的差距,作為鎖定60歲退休日的長期儲蓄,在復利的作用下,距離滿足艾倫條件相去甚遠,這是“老農保”難以“存活”下去的根本原因。
概而言之,艾倫條件作為一個經濟學定理可以從另一個側面對中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35年歷史嬗變的三次重要變革做出很有說服力的解釋。
第一次是1999年老農保被“叫停”。很顯然,這個決策是正確的,對經濟和社會的“止損”也是及時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艾倫條件是不可能被滿足的:從1983年人民公社制取消、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即刻崩塌,到2003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立,在長達20年里沒有財政能力建立醫療保險,農民連看病都沒有醫保報銷制度,遑論“遠水不解近渴”的養老保險。
第二次是2009年建立新農保,將非繳費型養老金引入并作為制度主體。這個制度設計所針對的正是為了避免重蹈老農保違背艾倫條件的覆轍,用財政性的、“現收現付”的辦法來避開艾倫條件的約束。于是,新農保成功了。從“新”“老”兩個制度銜接的及時性來看,在2009年建立新農保也是適時的。
第三次是此次啟動的城鄉居保基金投資改革。與10年前的2010年養老金能否“入市”投資的輿論環境和認知水平相比,今天我們畢竟沒有了這些觀念上的束縛和無休止爭論的困擾,實行市場化和專業化的投資體制是為了提高收益率,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艾倫條件。
概而言之,從1986年試點開始,農村養老保險的制度變遷的背后是一只看不見的手在發揮作用,決策者下意識地始終圍繞如何滿足艾倫條件而曲折前行,這是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不斷試錯”過程,其中我們積累了經驗,當然也有教訓。
(三)非繳費型養老金的引入對艾倫條件的三個印證
如果說1999年停止老農保的深層原因可被解釋為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外部環境下,農村建立DC型完全積累制養老保險不能滿足艾倫條件,那么,2009年前后出現的建立新農保的熱潮并提前完成全覆蓋的目標就可被解釋為只有引入非繳費型養老保險才是唯一的正確政策選項;這個事實從反面做出的另一個解釋是,雖然在理論上講,在農村建立繳費型的DB型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沒有政府補貼)應該是可行的,能夠滿足艾倫條件,但在現實中必將也是行不通的,因為農民收入水平低,繳費能力差,組織化程度低,流動性強;退一步講,即使建立起來,2009年至今10年的繳費收入數據顯示,按他們現有的繳費能力和水平,在現有人均養老金待遇水平條件下,只夠支付當年養老金支出的四分之一左右,政府依然還需大規模轉移支付,這樣的DB型現收現付制顯然更不可取,與目前由政府全額支付非繳費型養老金的籌資結構相比顯然是下策。這個“復盤”告訴我們,在中國農村建立養老保險制度,一方面不能違背艾倫條件,否則要受到懲罰,另一方面在理論上可以滿足艾倫條件的保險制度模式在現實中也不可能實現,所以現階段在中國農村建立養老保障制度只能選擇非繳費型制度。
學界普遍認為非繳費型養老金在城鄉居保中的引入是成功的,這個事實反過來可以被認為是對艾倫條件從三個不同情景進行了一次印證。
第一個情景是當艾倫條件不能被滿足時,DC型完全積累制養老保險制度或是像老農保那樣不得不主動退出,或是令其存續下去,但逐漸走向“破產”。這個情景的印證結果已被普遍獲得認可。
第二個情景是當艾倫條件不能被滿足時,決策者可以決定放棄繳費型養老保險制度,代之以實施非繳費型養老金制度,以期滿足艾倫條件。這個情景的印證也被10年后的2009年啟動的新農保所確認。
第三個情景是當艾倫條件不能被滿足時,統賬結合的城鄉居保將面臨兩個選擇,即或是像統賬結合的城鎮職保那樣,將其本來的FDC個人賬戶變形為NDC的名義賬戶制,或是堅守FDC個人賬戶的初衷,建立投資體制,實施專業化投資,阻斷滑向NDC的通道,令基礎養老金定型為非繳費型養老金。
在未來幾十年里,定型的“FDC個人賬戶養老金+非繳費型養老金”面臨的不確定性主要有兩個挑戰:一個是“小挑戰”,即賬戶養老金的投資效率是否足夠高,以至于能夠滿足艾倫條件的要求,否則賬戶養老金只能忍受一定的貶值風險;另一個是“大挑戰”,即基礎養老金定型為非繳費型養老金之后所面臨的巨大財政壓力,這取決于城鄉居保的制度屬性與功能定位問題的重塑。
基本收入理論:非繳費型養老金改為“養老津貼”的理論基礎
既然城鄉居保的基礎養老金在較長時期內采取非繳費型養老金的形式,就不如將其改為養老津貼更有優勢,從近年來再次流行的“基本收入理論”來看,順勢將其改為養老津貼更有利于未來財務可持續性,而不是相反,非繳費型基礎養老金轉為“養老津貼”不僅是恰當及時的,也是符合邏輯的。“基本收入”理論是指政府保證每個公民獲得的最低收入(MI),也稱為“全民基本收入”(UBI)、公民收入(CI)、最低保證收入(GMI)。
(一)“全民基本收入”理論再度流行及其思想淵源
基本收入理論近些年來再度受到追捧,主要是有四個原因。一是芬蘭政府于2017至2018年實施了為期兩年的試驗,成為全球首例以政府名義將基本收入理論付諸實施的國家級試驗案例,引起世界普遍關注。二是人工智能、自動化和全球化發展十分迅速,傳統就業市場受到極大沖擊,一些世界級的新技術發明者和所有者紛紛發表支持言論。臉書共同創始人扎爾伯格、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特斯拉和SpaceX創始人伊隆·馬斯克的積極支持與響應。三是此次新型冠狀肺炎全球大流行,基本收入理論再次成為一些國家熱捧的明星理論。美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等重災區一些政治和公眾人物呼吁或提出請愿書,要求提供基本收入,以拯救生命。四是基本收入理論思想淵源歷史悠久,對很多群體具有深刻的影響。該理論可追溯至500年前的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等。20世紀80年代以來,歐洲和北美的基本收入理論得到了長足發展。
(二)“全民基本收入”理論的政策含義
基本收入理論被認為是一個激進的政策主張,其基本政策建議是每月向社區所有成員發放現鈔補助金,無需任何經濟狀況調查,不附加任何條件,補助金的水平應足夠高,以免除社會成員生活的經濟不安全感。該理論的思想體系跨越多個學科,不同意識形態的學者看法存在一定差異,根據斯坦福大學哲學系教授朱莉安娜的一項最新的權威解釋,基本收入可歸納為五個主要特征:第一,發放的福利是現金,不是實物;第二,發放的對象是個人,不是家庭;第三,發放的方式是無條件的,不是有條件的;第四,發放的范圍是普惠式的,不是家計調查式的;第五,發放的期限是定期的,不是一次性的。
(三)“養老津貼”與“全民基本收入”的區別
基本收入理論認為,現代社會是一個利益相關者社會,每個利益相關者都享有利益相關權。對不同的利益相關者應建立相應的利益相關者基金,對一個國家來講,應該制定利益相關者計劃。因此,全民基本收入這個概念之下存在四個“表親”:基本津貼、負所得稅、工資補貼、保障就業。其中,如把某一類“基本津貼”的發放范圍限制在某個年齡段就成為“部分”全民基本收入。歐盟和OECD至今還沒有任何成員國實施這樣的制度,因為其成本非常高昂。全額的基本收入離現實世界還很遙遠,就在身邊的是部分基本收入,在中國,非繳費型養老金改為養老津貼就應該成為部分基本收入的一個經典案例或最佳實踐。
行為經濟學:非繳費型養老金改為“養老津貼”的現實意義
2019年召開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的要求,在城鄉居保基礎養老金定型為非繳費型養老金之后,將其改為“養老津貼”完全符合四中全會精神。改為養老津貼之后,從法理上看,非繳費型養老金更加名副其實,不但回歸其本源,而且更加“坐實”了財政的法律責任;從參保人利益相關者的心理看,城鄉居保參保人的心理預期和全社會的預期都將有所改變,在觀念上使之與保險制度相對“脫鉤”,重塑國民的保險觀念和保險文化;從制度功能定位上看,重新界定城鄉居保基礎養老金的制度屬性之后,其攀比對象城鎮職保將自然“消失”,可緩解中央和地方的財政壓力,在未來地方財政形勢日趨嚴峻的預期下更顯得十分必要;從財政和保險的邊界來看,福利與保險“劃清界限”之后,有利于規避保險制度福利化傾向,意味著“財政”與“保險”相應分開,福利的歸福利,保險的歸保險,養老保險追求的應是精算平衡原則,養老津貼體現的則是國家父愛主義原則,發揮的是“兜底功能”。
(一)“養老津貼”的行為經濟學詮釋
美國行為經濟學家理查德·泰勒教授的“心理賬戶”原理非常通俗地解釋了城鄉居保基礎養老金改為養老津貼的必要性。美國是20世紀70年代開始逐漸使用信用卡的,此前人們在家庭理財和制訂家庭預算時往往把現金裝在不同信封里,一個信封裝租金,一個裝買食物的錢,一個裝水電費等,相當于把錢貼上了不同“標簽”。這個故事說明,同樣都是錢,但卻分屬不同“心理賬戶”。泰勒在康奈爾大學任教時經常跟經濟系的同事打牌,賭注很小,他對比了賭場上賭徒打牌贏錢的故事,如果是用“莊家的錢”賭就似乎并不把贏的錢當“錢”看,因為是拿賭場的錢而不是自己的錢在賭博。人們在賭場還會經常看到“雙兜”心理賬戶的情況,就是一個人帶了300美元去賭場玩,贏了200美元,這時他會把300美元放在一個兜里,認為這些錢是自己的,而把贏的那200美元放在另一個兜里準備繼續下注。為此,泰勒教授還專門做了一個實驗,證明了存在“莊家的錢”效應,其結論就是,每當存在兩個明顯的參照點時,例如,存在起點時的情況與當前所處的情況,“莊家的錢”效應就會發生。泰勒教授講的故事和實驗結果揭示了這樣一個道理:“雙兜”心理賬戶也好,“莊家的錢”效應也罷,都是特定心理賬戶的結果,背后有一只手在掌控,那就是違背了錢的可替代性的原則,從本質上講,不管錢放在哪個地方、哪個兜里、是不是“莊家的錢”,花起來應該是一樣的,只是錢上貼的“標簽”變了,心理賬戶也隨即就變了。行為經濟學的這些試驗結果證明,同樣的錢,貼上不同的“標簽”,這些錢就會立即分屬不同的心理賬戶了。
雖然城鄉居保基礎養老金是非繳費型養老金,但貼的標簽是“保險”,其分屬的心理賬戶就必然是“保險箱”,屬于“莊家的錢”,而在養老津貼概念下,標簽變了,其分屬的心理賬戶就變為“父愛主義”,屬于給自己的錢。非繳費型養老金改換“標簽”在管理體制上并未觸動制度結構和運行流程,容易操作,法律程序簡單,僅產生少許“菜單成本”,如用行為經濟學“助推”原理來解釋,那就是舉手之勞、順勢而為之事,但產生的效果則可明顯改變參保人對這支非繳費型養老金的心理預期,其攀比和財務可持續性問題頓時得以釋然。
(二)“養老津貼”的財務可持續性
中國城鄉居保的基礎養老金是典型的部分全民基本收入,因為其標準大大低于國家貧困線,將其改為養老津貼可被視為是對基本收入理論的一次重要實踐,其現實意義在于改變了非繳費型養老金的“參照點”,即從城鎮職保轉向國際慣例,緩解了其財務可持續性的壓力預期。養老津貼有兩個指標對其財務可持續性產生較大影響。
第一個指標,養老津貼的替代率水平。城鄉居保參保人中絕大多數為農村居民,城鎮居民僅為2300萬人,占參保人總數的4.4%,鑒于此,本文以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基準測算基礎養老金替代率更加符合實際。自2009年城鄉居保建立以來,其基礎養老金替代率基本維持在10%左右。這個替代率水平與發達國家非繳費型的養老津貼的差距不是很大,只低幾個百分點而已。
第二個指標,養老津貼支出規模占GDP比重。國際勞工組織將幾乎所有提供養老津貼“支出占GDP”數據的國家列出,共計41個經濟體,其結果顯示,支出規模最低的哥倫比亞、新西蘭和肯尼亞三國分別只占GDP的0.02%,最高的國家格魯吉亞是3.70%,均值是0.66%,中值是0.33%。中國非繳費型養老金的支出水平0.32%處于中值水平,低于均值水平;但在“中組”里,中國非繳費型養老金支出水平仍處于中值水平,與其均值水平也相差無幾。
替代率水平和支出占GDP比重這兩個指標顯示,作為養老津貼的中國非繳費型養老金在對標國際時基本處于合理區間,與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基本是相適應的,未來的財務可持續性壓力預期不是很大。
(三)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增設”“養老津貼”的公平性
城鄉居保基礎養老金改為養老津貼之后,相對于城鎮職保來講似乎存在一個公平性問題,即城鎮職保制度中退休人員沒有養老津貼,統籌養老金是由雇主繳費形成并支付的,是保險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
從公共財政的角度看,上述問題確實涉及兩大制度間的平衡和公正問題。事實上這個問題可以圓滿解決。從1997年城鎮職保統一制度以來,中央和地方每年對該制度進行轉移支付,20多年來年均轉移支付規模大約相當于當年養老金支出的15%左右,從1998年至2018年累計轉移支付4.88萬億元,這就意味著,2018年底全國基金累計結余的5.09萬億中幾乎全部來自財政。換言之,如果沒有每年各級財政介入,一些基金余額“見底”地區的養老金將難以足額發放,即養老金里面已經“內含”了財政補貼。
問題恰恰在于,20多年來城鎮職保養老金制度獲得的財政轉移支付是“暗補”,退休人員并不知情,就沒有形成一個“心理賬戶”;如果將其改為“明補”就可成為一個數額不菲的“養老津貼”心理賬戶。例如,以2018年為例,全國范圍的財政轉移支付“均攤”到1.18億退休者身上大約月人均500多元,在全國企業月均養老金2628元中占18%,相當于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5.3%,略高于農村居民11.4%的替代率。所謂“明補”是指將每年的財政轉移支付在名義上單獨列出一份養老津貼,與城鄉居保一樣,城鎮職保“增設”養老津貼的做法僅增加一些“菜單成本”而已。城鎮職保“增設”養老津貼不僅使參保人增加了一個“心理賬戶”,提高了他們的“獲得感”,而且還改善了公共財政為參保人帶來的“客戶體驗”。
結束語:四個邏輯關系
根據上述分析中國非繳費型養老金的構思和脈絡,這里再次強調艾倫條件、基本收入、心理賬戶、養老津貼這四個關鍵詞在本文中的邏輯關系:艾倫條件作為一只看不見的手,是中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演變和最終引入非繳費型養老金的根本原因;城鄉居保基礎養老金作為非繳費型養老金順勢改為養老津貼是破解目前制度屬性和財務可持續性預期的重要選項;基本收入理論是“植入”養老津貼制度中的一個理念支撐;心理賬戶原理是解析城鄉居保和城鎮職保兩個制度“建立”養老津貼概念的最佳詮釋。
(一)“艾倫條件”對中國養老金制度模式選擇的補充解釋
在中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35年變遷史中,艾倫條件是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入非繳費型養老金是其結果之一。但是,城鎮職保面臨同樣的國情,甚至其名義生物收益率高達14.8%,為什么新農保經歷了停擺、重建、引入非繳費型養老金的曲折過程,而城鎮職保的統賬結合制度的初始狀態卻保留下來?原因很簡單,農村養老保險規定農民自愿參加,而城鎮職保在實際運行中,企業參保行為則受到嚴格約束,企業雇員參保相當于是強制性的。盡管如此,城鎮職保的個人賬戶經過13年的艱苦努力也未能做實,最終不得不放棄實賬積累(FDC)的制度設計初衷,轉而實行名義賬戶(NDC),其根本原因之一也是艾倫條件這只看不見的手的原因。
(二)基本收入理論和心理賬戶原理對養老津貼的理論支持
定型后的城鄉居保制度將在較長時期內成為城鄉居民尤其是農村居民的兜底性制度。2019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0.6%,到2050年將達到80%;農村人口將從2019年的5.52億降到2050年的2.7億,城鎮人口將從8.5億增加到10.9億。這就意味著,以非繳費型養老金為主體的城鄉居保給財政帶來的壓力將逐漸下降,為提高非繳費型養老金替代率水平騰出了空間,同時隨著城鎮化率的不斷提高,城鄉差別逐漸縮小,多數農民轉換為城鎮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職工,少數在農村就地過渡為農業職工,城鄉二元結構的養老津貼水平終將走向統一,這就需要將基于基本收入理念的養老津貼制度盡早“植入”社會保障制度之中,由此對那些早就存在的既定的財政補貼重新貼上養老津貼的“標簽”是十分重要的,它將給城鄉居保和城鎮職保帶來正外部性。
(三)“養老津貼”產生兩個正外部性有益于穩定預期和穩定社會
城鄉居保和城鎮職保的演變軌跡均可歸結為三個發展階段。城鄉居保的三個階段是從“實賬繳費確定型完全積累制+0”到“實賬繳費確定型完全積累制+非繳費型養老金”,再到“實賬繳費確定型完全積累制+養老津貼”,即從(FDC FF+0)到(FDC FF+NCP),再到(FDC FF+OAA);城鎮職保是從“實賬繳費確定型完全積累制+待遇確定型現收現付制”到“名義繳費確定型完全積累制+待遇確定型現收現付制”,再到“名義繳費確定型完全積累制+待遇確定型現收現付制+養老津貼”,即從(FDC FF+DB PAYGO)到(NDC+DB PAYGO),再到(NDC+DB PAYGO+OAA)。如果說前兩個階段是被動地受到艾倫條件約束的結果,那么第三階段應是主動“植入”基本收入理論的體現。其中,在第三階段,城鄉居保的基礎養老金“改為”養老津貼和城鎮職保“增設”養老津貼對這兩個制度均可帶來正外部性,這是引入心理賬戶概念后在零成本增加的條件下對兩個制度的“增益”,對穩定這兩個制度財務可持續性及其參保人預期將產生外溢效應,是促進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的一個改革選項,是完善兜底性民生建設的一個成本低廉的制度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