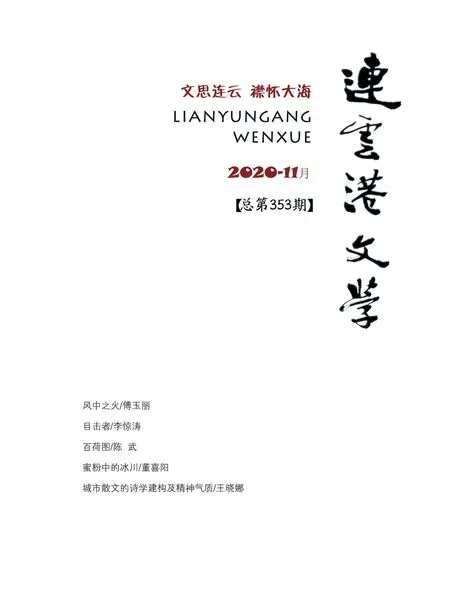父親的酒杯(外六首)
汪玉淇
十年前,父親是一把錘子
把生活的釘子敲進自己的血肉
我們的希望來自他
黑夜里不滅的煙頭
二十年前,父親是一根扁擔
挑起沉甸甸的病妻和嬌滴滴的兒女
他咽下我們的眼淚
給自己準備好一瓶紅花油
而三十年前啊
父親是一支優雅的笛子
清越的笛聲可以穿透云層
未來在他眼里
是一片輕盈的羽毛
沒有人過問父親的酒杯
就像命運從未征詢過我們的意見
梅 雨
氣壓像踩在腳底的一塊鐵板
梅雨季是一場漫長的水下憋氣
樓下
琴鍵敲出濕淋淋的音符
我聽到肖邦的喘息
困倦在咖啡的濃稠里打滾
鍵盤滴滴答答
是青石板偷偷告訴我雨巷的密碼
站在窗口望天
一條金魚吐出一串氣泡
此刻,你會不會想起某個人
像心里永遠也擰不干的毛巾
可有些事
正悄悄腐爛在角落
即便重見天日
我們的記憶已長滿霉斑
喜 鵲
梧桐枝丫間碩大的巢穴
仿佛冬日的黑眼圈
我已經無法捕捉狡猾的睡眠
我沒有什么喜事可告訴你
你也不用來嘲笑我
你的喳喳聲斜斜地插在我的窗口
比凌遲的刀子更閃亮
為什么人們總是不吝惜贊美
把縹緲的希望寄存在你身上?
可我的脊背發涼
當你響起一陣咳嗽——
野 菊
瘦瘦高高的秋陽
疊成豐腴的金黃色
它們在枯草之上舞蹈
荒蕪里不起眼的點綴
路邊的塵埃很厚
它們卻有一把好骨頭
可以和霜花媲美
剪下倨傲的腦袋
它們在我的杯子里
也能綻放自如
在野菊面前我只有羞愧
我不能單腳跳舞
也難以忍受生活的刀斧
記憶也會塌方
一個沒有露水的早晨
當意識從暗夜的床底蘇醒
那些曾經熟悉的名字
在別人口中變成一個個陌生的石頭
我知道某種東西正從我生命里撤退
悔恨的泥石流在體內洶涌
原來記憶也會塌方
我蹩腳的悼詞已經擬好
用蘆花來修飾衣領
撒一把黃葉做紙錢
為那些死去的活著的又死去的記憶
我愿追隨一匹閃電
我愿追隨一匹閃電
即使被燒成慘白的煙灰
它在夜的被子里翻滾
攪亂城市昏沉的睡意
它脾氣暴躁
撕裂天穹
劈開烏云的頭顱
它不留情面
讓一棵樹露出雪白的筋骨
給房子點一把火
嚇唬還在外面逗留的人
即使這樣
我還是想抓住它的尾巴
鋸開生活的麻木
落 枕
是昨夜風的背叛
還是夢里愛的重傷
早晨脖子不再聽大腦的使喚
我們總是被一些疼痛揪住
才肯停下來審視自己這架機器
為關節鉚上螺絲釘
骨縫里加點潤滑劑
再給皮膚覆一層膜
修修補補又可以重新上路
可惜痛感消失
我們又迷失在瑣碎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