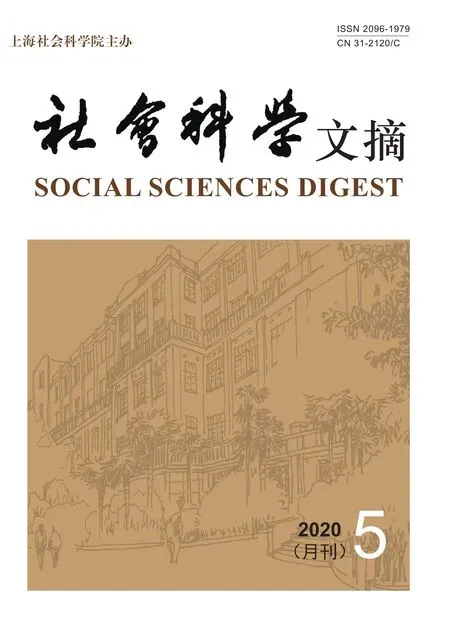性別互動論:基于“做性別”視角的探討
文/王晴鋒
1987年,坎迪斯·韋斯特(Candace West)和唐·齊默爾曼(Don Zimmerman)發表《做性別》(Doing Gender)一文,指出性別不是“我們是什么”,而是“我們做什么”。該文的顛覆性意義在于,它強調社會互動的重要性,性別成為不斷進行的社會互動之產物,從而揭示性別研究中一味強調社會化以及結構取向存在的缺憾。學術界關于“做性別”視角的爭論與反思過程中產生了另兩種解釋范式,即“消解性別”和“再做性別”。這三者對性別的施為方式具有不同的理解,但它們都是關于性別不平等的微觀機制研究,都認為性別的建構或解構是在互動過程中實現的。本文以“做性別”視角作為理論出發點,結合“消解性別”和“再做性別”視角,在此基礎上提出“性別互動論”,以此探討性別不平等運作的微觀機制。
“做性別”的理論意涵
在西方歷史上,女性主義提供了一種質疑、反抗和顛覆既有性別設置的意識形態。第二波女性主義的貢獻之一是從觀念上區別“生理性別”(sex)與“社會性別”(gender),即區別與性別范疇相關的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及其相應的社會文化意義。此前人們普遍認為生理性別是先賦的,由荷爾蒙、生理機能以及解剖學構造等生物學因素所導致;社會性別被認為是后致的,通過社會、文化和心理等方式建構。然而,關于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這種簡單區分容易造成困惑,因為生物過程與文化過程之間的關系極為復雜,生理性別很難被看作是某種“給定”,社會性別也不完全是“后天獲得的”。韋斯特和齊默爾曼試圖對傳統的性別觀念進行理論重構,他們將“社會性別”重新理解為一種嵌入在日常互動中的“慣例性達成”。因此,社會性別不是特征叢或角色,而是某種“社會施為”的產物。“做性別”是指“制造女孩與男孩、女人與男人之間的差異,這些差異不是自然的、本質的或生物的。一旦構建了這些差異,它們便被用于強化性別的‘本質性’”。“做性別”里的“做”(do)意指行動,它具有強烈的實踐導向,包括展演、執行、實現,以期產生現實效果。而且“做”是進行時,強調性別是在正在進行的社會互動過程中不斷被創造出來的,它是一種情境化行為的管理活動。韋斯特和齊默爾曼還指出“做性別”的四類資源:社會場景中的物理設置及其制度化框架、選擇性的匹配實踐、互動情境以及關于規范化的性別行為的認同展現。
互動過程中實現的性別類型與特定情境密切相關,共同在場的他人根據規范性的性別觀念對個體實踐進行評估。在這種情況下,性別范疇發揮著認知工具的功能,行動者以之闡釋情境性的社會行為,決定接受還是質疑特定性別氣質的實踐。韋斯特和齊默爾曼將性別構想為一種“達成”,一種后天獲得的情境性行為的屬性,從而將注意力從個體內在的特質轉向互動領域。性別既是社會設置的結果,又是其基本原因,同時也是將最根本的社會分工形式(性別分工)進行合法化的手段。“做性別”涉及一系列社會感知的、人際互動的和微觀政治的活動,它們以各種方式被投射成性別氣質的“本質”表達。換言之,盡管是個體在“做性別”,但它亦涉及制度層面,這是因為不僅個體自身體現出復雜的社會關系和情境性位置,而且其有關性別系統的“儀式習語”也習得自制度文化。互動參與者將各種不同的活動組織化,以反映或表達性別,并以同樣的方式理解他人的行為。由于社會被兩性之間的“本質”差異所分割,而且它們在性別范疇中的位置既是密切關聯又是強制的,因此“做性別”是不可避免的。
性別研究的范式轉變:從結構性規定到互動式達成
傳統的觀念認為性別角色通過社會化實現,它將性別視為后天習得的和展演出來的角色或地位,個體性別角色的扮演取決于他/她所處的社會結構位置以及與該位置相關聯的期待。性別社會化理論傳達出這樣一種觀念,即盡管認為社會性別是“后天獲得的”,但到了某個年齡段它就會變得定型、穩固和靜止,這事實上變得跟生理性別一樣。也即,它將社會性別簡化為生理性別,同時抹除了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之間的區分。簡言之,社會化理論即使在摒棄了生物決定論之后,也仍將性別視為社會性生成的個人特質。
20世紀中后期,學術界關于性別的理論建構和反思通常遵循兩條路徑:一是提出新的性別范式,二是重新闡釋“社會性別”概念,賦予其新的內涵。在建構新的性別理論范式方面,美國社會學家馬爾科姆·沃特斯(Malcolm Waters)提出關于男性支配的性別系統理論(Masculine Gender-System),它重新整合傳統父權制理論的重要要素,并囊括男性統治下性別系統的基本變體形式,以重構男性統治的觀念。沃特斯的分析主要涉及家庭領域和公共領域之間的關系,他從兩個維度進行探討:家庭/公共領域的結構分化程度,即經濟和政治等公共實踐與私人實踐在時間、空間以及社會背景中的分離程度;因果關系的首要性,即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決定性別系統總體結構的相對程度。沃特斯將父權制-男權制、直接型-擴展型這兩個維度進行交互分類,形成性別系統的四種類型,它們共同構成關于男性統治的分析圖式。
第二條路徑是對“社會性別”這個概念重新進行闡釋。例如,帕特麗夏·馬丁(Patricia Martin)通過重新審視社會制度的基本特征,并將社會性別與之進行比較,認為性別也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社會制度”。類似地,羅伯特·康奈爾(Robert Connell)認為,社會性別是“一種集體、制度(社會設置)和歷史過程的屬性”。而艾麗斯·楊(Iris Young)將性別重構為一種“連續體”,這種集合體形式有別于群體。群體指由具有自我意識、彼此相互承認的個體組成,它有明確的目標、期待和價值觀等,成員之間存在統一的關系。而連續體的成員沒有統一的意圖和屬性,也并不意味著具有相同的身份,甚至沒有具體的特征或條件可以判斷個體的成員資格和連續體的邊界。通過將連續體的觀念引入性別研究,楊旨在表明“女性”一詞可成為用于表達特定社會聯合體的社會范疇,而且不需要所有女性都具有共同特征或面臨相同的情境,就能夠將她們視為一個社會集合體。
這些新的理論觀念拓寬了性別研究的思路和視野,但此類研究通常是結構、制度或文化取向的。20世紀60年代以來,性別研究和女性主義理論對性別之社會屬性的強調導致的一個結果是過于強調性別的結構性維度,即使對個體性別角色行為的研究也被高度制度化,忽略情境性、互動以及能動性。與這些研究取向不同,韋斯特和齊默爾曼不是簡單地將性別視為個體屬性或結構性產物,而是認為它是在與他人互動過程中實現、完成或達到的某種狀態。通過“做性別”過程,性別系統的成員不斷地再生產不平等的兩性關系,同時也將社會文化差異自然化。將性別關系視為“進行過程中的達成”意味著不能將它們與社會行動之間的關聯性以及互動情境割裂開來。總之,社會性別是社會成員在日常生活中持續進行的、情境性的、例行化的達成。“做性別”視角通過將性別置于社會互動之中,探討性別系統是如何運作的,尤其是如何生成并維持不平等的權力關系。“做性別”視角標志著性別研究領域一場無聲的范式革命,它使社會性別從一種結構性的或命定的屬性轉變成為一種“互動式達成”。
“做性別”的反身性視角:“消解性別”與“再做性別”
數十年來,“做性別”已成為性別研究的重要概念,隨著學術界廣為接受該視角,它也遭致一些批評。例如,弗朗辛·多伊奇(Francine Deutsch)指出“做性別”常被用于闡明性別關系如何維系,尤其是傳統的男性氣質及其行為如何壓制和規訓女性氣質;它更多地用于描述傳統性別意識形態的維持,而不是變遷,因而成為一種關于性別遵從、性別守舊和性別維系的理論。由于“做性別”的研究取向過于強調差異的形成過程,它反而合法化了基于性別范疇的歧視與不平等。多伊奇認為,既然性別系統是人為地在互動過程中持續不斷地“做”出來的,那么也可以“消解”性別系統。“消解性別”是指在日常互動中徹底顛覆或破壞原有的性別結構,這種性別結構主要表現為本質主義的二元對立,并以各種方式否定社會定義的性別氣質。其他有些學者也持類似主張,只是她們的表述略有不同,諸如“解構性別”“去性別”以及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消解性別”等。
除了“做性別”和“消解性別”這兩種研究取向之外,還存在“再做性別”。它是指在互動過程中改變或擴展與性別相關的各種規范,重新定義與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相關聯的屬性,改變人們施加在男性與女性身上的各種角色期待,從而挑戰本質化的性別特質及其權力結構。與“消解性別”不同,“再做性別”沒有廢除“社會性別”作為一種分類設置的策略。另有一種觀點認為,“做性別”“消解性別”和“再做性別”可以同時存在。例如,凱瑟琳·康奈爾(Catherine Connell)通過研究自我認同為跨性別者的個體在工作場所如何協商、管理性別化的互動,描述了跨性別者不同的經驗類型。跨性別者打破了關于性別范疇的傳統假定,他/她們根據是否公開出柜有著不同的現實經歷或實踐策略:未公開出柜的跨性別者更符合“做性別”范式,而公開出柜者更多地符合“消解性別”和“再做性別”范式。康奈爾將后者的這種互動式性別達成稱為“做跨性別”。盡管跨性別者試圖“消解性別”或“再做性別”,但他/她們的話語和行為仍會以各種方式被重新闡釋,從而使之符合或強化既有的性別二元性。在這種情境下,跨性別者必須決定是繼續掩飾還是表明他/她們在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性別范疇之間的不一致性。在該過程中,他/她們將形成一種基于性別定位/關系結構(作為跨性別者)而產生的意識,這個過程便是“做跨性別”。根據情境的不同,“做跨性別”既可能表現得像是“做性別”,也可能表現得像是“消解/再做性別”,從而實現遵從抑或抵制性別規范的目的。
“性別互動論”:一種微觀性別理論的生成
以上闡述了三種關于社會性別的觀點,即由韋斯特和齊默爾曼提出的“做性別”,由巴特勒、多伊奇等人倡導的“消解性別”以及由康奈爾等人主張的“再做性別”,這些微觀性別研究范式可被統稱為“性別互動論”,它在性別是“互動式達成”這一核心原則下理解性別壓迫系統的內在運作機制,以期挑戰既有性別設置的合法性,最終達成性別系統變遷之可能性。性別互動論有兩個思想來源,一是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性別思想,二是哈羅德·加芬克爾(Harold Garfinkel)的常人方法學。此外,20世紀60年代以來,歐美學術界關于種族、族群、階級以及性態等研究也為性別互動論提供了思想基礎,這些研究為弱勢群體聲張權利,探索從互動-制度、能動性-結構的不同層面探討弱勢境遇。
互動系統本身是中立的,它既可以是生成和維持性別不平等的場域,也可以是消解、抵制性別不平等和權力關系的場域,也即在互動過程中顛覆性別二元對立。性別互動論不僅僅為了描述性別壓迫是如何生成并維系的,更重要的在于變革,也即在互動的實踐關系中改變不平等的性別關系設置。性別互動論具有四個特征。第一,注重過程性,即詳細闡釋“做性別”“消解性別”或“再做性別”的過程。性別不平等無處不在,對過程性的強調旨在揭示性別不平等系統是如何生成并維系以及如何可能消解的。第二,強調互動式達成,它是一種以微觀行動和社會關系為基礎的理論,同時也強調情境性。第三,聚焦于能動性,包含了抵制、反抗和挑戰,而不僅僅是如何維系既有的性別規范;有關性別系統的反抗與性別系統的維系力量同樣普遍和重要。第四,未忽略宏觀的結構性因素,也即它聯結了行動-結構之間的要素。性別互動論認為,社會性別系統是不穩定的、脆弱的社會事實,需要各種力量不斷地去維護、修飾和鞏固。
性別互動論強調性別呈現以及性別意義的制造過程,它使人們關于性別不平等的意識變得更加敏銳化。它的激進之處在于:性別關系的變革無需經歷漫長的等待,它可以是日常生活中每時每刻都在進行的變化。因此,女性革命不再是一場“漫長的革命”。每一個男女互動的場域都可以成為性別斗爭的戰場,每個人在每一次情境性互動中都可以成為平權運動的斗士。我們毋需等待自上而下的制度變革,更何況對個體而言真實又富有意義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行為舉止和切身的主體(間)感受(即使是制度變革,最終的成效也需要落實到個體層面),它體現在言語溝通、舉手投足、衣著打扮、眼神儀態等。因此,無論在思想還是行動上,都必須脫離制度性、結構性的依賴,而強調個體自身的能動性并充分釋放這種能動性。在這種情形下,每個人都成為斗爭的原點,每個人都是權利的主體,而且也必須為自己賦權。性別互動論強調日常生活的變革和個體生活處境的切實改善,它不排斥制度性變革,但制度并非保障個人權益的唯一途徑,甚至不是衡量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唯一標準。由此,日常生活的互動系統成為抵制、反抗和變革的主要場域,并不斷產生示范效應和連鎖反應。從人際互動開始捍衛每個人自身“人之為人”的最基本權利,從而徹底改變規范性的性別觀念。
結語
“做性別”視角探討了互動過程如何維系包括性別差異/歧視在內的社會不平等關系,這種理論取向揭示出互動秩序是如何維系的以及社會支配的本質。“做性別”產生了性別研究的范式轉換,并將性別不平等的生成、維系和消解落實到具體的互動組織。有關該視角的保守性批評產生了關于“消解性別”和“再做性別”的爭論。本文將“做性別”視角以及相關衍生性的微觀分析視角整合起來,統稱為“性別互動論”。性別互動論有助于抵制傳統的性別關系,打破階序性的性別設置,探究性別平等的可能性,最終促進系統性的社會變革。
在中國的語境以及實踐中,“做性別”視角亦具重要意義。日常生活中各種形式的父權制和性別歧視往往隱藏在性別平等的表象之下,不時地以各種轉化或偽裝的方式顯露出來,而且它們通常發生在面對面互動的場域。換言之,制度化、結構性的力量有時顯得較為粗糙和遲鈍,無法完全管控微妙的性別平等問題,它需要微觀層次更敏銳、細致入微的力量介入。作為微觀研究取向的“做性別”不直接涉及宏大的制度及其變革,而聚焦于個體在特定情境中即時的能動性,因而是促成性別平等的另一股重要力量。個體性的弱勢可分為制度性弱勢與情境性弱勢,以往的研究大多關注前者,“做性別”視角關注的是后者。當然,制度要素和情境要素不是二元對立的。譬如,在中國的性別實踐中,“做性別”可以采取不同的資源動員方式,就話語層面而言,個體行動者在性別互動過程中可以動用國家和意識形態的合法性話語為己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