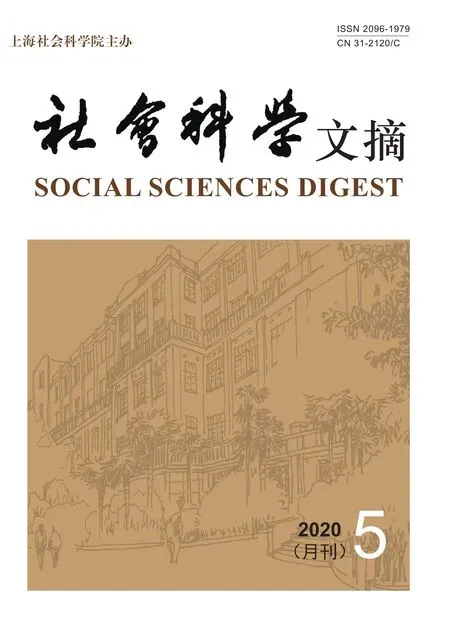復雜性研究與拓展社會學邊界的機會
文/喬天宇 邱澤奇
孔德在創立社會學時便強調,相較于天文、物理和化學現象,社會現象具有復雜性。他把社會類比為有機體,并認為與研究非有機體不同,對社會有機體的研究要借助整體去觀察部分。盡管孔德的觀念后來被斯賓塞、涂爾干等繼承并強調,但實際上社會學家們在很長一段時期并沒有找到應對復雜現象的有效方法,對社會現象復雜性的認識僅停留在哲學觀念上。
值得社會學家們驕傲的是,社會學者從來沒有停止過對復雜性的關注。只是社會學的關注與作為一個專門學術領域的復雜性研究相比,仍然顯得零星與分散。多數社會學者對當下科學界的學術進展與成果了解不足,更沒能很好地跟進與做出貢獻。
復雜性與社會現象
復雜性現象廣泛存在于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20世紀80年代,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復雜性幾乎同時進入研究者視野。復雜性研究從誕生之日起就注定是一個多學科交叉的領域,自然科學中的物理學、生物學、計算機科學和社會科學中的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都在其中尋找著各自的議題。
從事復雜性研究的學者們往往會先對復雜系統的一些基本特征給予明確描述。社會現象復雜性的來源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啟發式行動、適應性行動、行動者間的互動、反饋機制、行動主體的異質性和不確定性。
涌現性是討論復雜性時一定會涉及的概念,也是復雜性的另一個十分重要的特征。簡單講就是整體不等于其組成部分的線性加總。宏觀系統是行動者互動的后果,可是宏觀系統的屬性和功能并不存在于較低層次的行動者身上;行動者還會依環境而適應性地調整行動,并重新作用于環境,進而導致宏觀后果發生動態演化。
在社會科學中,經濟學更早參與了對社會現象復雜性的討論。在阿瑟等經濟學者的努力和推動下,復雜經濟學的知識體系已初步搭建起來。與經濟學相比,社會學雖然也有很多研究涉及復雜性,但關注卻失之零散,尚未形成系統的知識體系。社會學對復雜性的早期涉獵散見于經典理論家的討論。
探索復雜性的方法及其演進
針對行動者間的互動,社會科學已發展了相對成熟的分析工具,有學者認為,基于圖論和社會網絡的結構分析和基于博弈論的行動分析是探索社會現象復雜性的有效工具。
博弈分析的確能夠將行動者間的相互影響納入,但是需要依靠嚴苛的假定,如行動者完全理性。如果放松假定,后續分析則需要使用更繁難的數學工具。博弈模型無法處理行動者間的互動結構。為此,有學者嘗試將社會網絡分析與博弈論相結合,但也只能有限度地解決復雜演化問題。
進化博弈分析允許放松傳統博弈分析的一些假定,其所應用的差分或微分方程建模也適宜開展動態分析。但只能處理一些簡單的復雜性現象;再復雜一點,差分或微分方程求解也會遇到困難。
為進一步探索復雜性問題,研究者們希望尋找既能避免已有方法缺陷,又易于運用的替代性工具。圣塔菲研究所主張的基于行動者建模(agent-based modeling,ABM)已成為復雜性研究的最主要工具。研究者可以利用計算機編程靈活模擬行動者的行動與互動,觀察可能產生的一系列社會后果,更好地理解人類經濟與社會活動中涌現出來的模式及動態。元胞自動機和多行動者建模是ABM的兩種具體形式。
在理論研究中,這種計算模型更利于幫助我們探索因果關系發生的機制。ABM可以被看做是一種理論實驗,研究者能通過“理論驅動的調參”來觀察某些社會現象出現的必要或充分條件。在政策研究中,應用計算模型也有利于制定更加科學的決策,幫助政策制定者選擇更優的政策條件組合。
社會學近期對復雜性的探索
進入21世紀后,一些運用復雜性研究理念、方法和模型工具討論社會學議題的研究成果開始在主流期刊上出現。本文嘗試使用社會學的兩大經典范疇——行動和結構——對這些研究進行概括和梳理。這些研究的共同點是都關注宏觀層面的涌現性后果,且都較成功地將微觀與宏觀聯系起來,并非單純討論行動者的微觀選擇,或僅對宏觀結構進行分析。
(一)對行動的研究
1. 集體行動的發生
默頓將由行動者虛假情境定義導致真實后果發生的過程稱為“自我實現的預言”。謝林較早使用模型語言對自我實現的預言進行了分析。他借用核物理工程學中的臨界質量模型,對如起立鼓掌等集體行動發生的機制進行解釋。格蘭諾維特構建了一個與此類似的“門檻值模型”,重點考察了臨界閾值(即門檻值)為正態分布的情況,并在后續的文章中對模型進行了拓展。
現實中的集體行動還會有組織行動者參與,組織與個體間也會發生相互作用。福勒等的研究同時涉及個體行動者選民和組織行動者政黨,試圖回答為什么投票作為集體行動會發生,以及為什么政黨會按特定的方式選擇選舉綱領等問題。
創新的擴散也可視作集體行動的后果。達夫昂特等在拓展格蘭諾維特門檻值模型的基礎上,研究了創新在組織間擴散的過程。近些年還有學者基于管理咨詢技術被廣泛采用的背景,利用計算模擬考察了咨詢提供者的流動以及企業與他們之間的匹配和雙邊互動等如何影響創新擴散。
2. 新行動者的出現
論及組織行動者,從公司組織、政黨到民族國家、國際聯盟,無一不是由成員個體組成,卻都在組織層面具有采取一致性行動的能力。這種一致性行動的能力來自哪里?新行動者的出現,其實同集體行動一樣,都可以看作是宏觀涌現的結果。
組織決策是組織采取一致性行動能力的體現,也是最重要的一種組織行動,科恩和馬奇等人針對組織決策行動的“垃圾桶模型”屬開創性研究,也是社會學家參與復雜性研究的又一早期代表作。
阿克塞爾羅德關心新政治行動者的出現,想回答諸如民族國家和區域聯盟等政治共同體是如何從一群更小的政治行動者的集聚和相互作用中涌現的。還有研究者關注新經濟行動者的出現。阿克斯特爾開發了一個公司內生的模型。模擬得到的團隊規模服從齊普夫分布,與對美國公司人員規模數據的經驗分析結果一致,規模變化率的分布也與此前的經驗發現吻合。
帕吉特與合作者們借鑒化學反應視角,分析了經濟生產系統的涌現和進化。他們利用計算模型考察了網絡結構、復制與學習模式以及企業搜索能力等對經濟生產系統涌現的影響。帕吉特和鮑威爾通過總結近二十年的相關研究成果,同時吸收化學和生命科學的思路,提出了一種理解組織和市場涌現的新思考框架。
(二)對結構的研究
1. 社會的分化
社會分化是社會學的經典議題,但很少有研究會將社會分化的宏觀結構與微觀過程聯系起來,從微觀行動者的互動中討論分化的生成性涌現。這類研究可進一步分為兩類:一類關注群體在空間上的分化機制,是對謝林種族隔離模型的延續和擴展;另一類關注社會經濟特征的分化,以及為什么會呈現出特定的形態。
福塞特把社會距離作為另一種解釋機制引入謝林模型,強調空間競爭和城市中不同社會群體間的互動,不同的社會群體可以來自不同的職業、地位、文化和興趣等。
如果說福塞特的研究是從“依據什么做選擇”的角度改進了謝林模型,布魯赫等人則是從“何時,做什么樣選擇”的角度進行改進。謝林假定的偏好函數是兩段式的,即個體偏好只存在一個閾值。布魯赫等考察了多種偏好函數形式,發現只有當偏好函數為兩段式時,高水平的居住隔離才可能發生;當偏好函數為階梯形或連續形時,出現的居住隔離程度較低。
至于財富等社會經濟特征在人群中的分布,早在20世紀初,帕累托便發現,意大利人的財富擁有狀況服從冪律分布(power law distribution)。財富狀況服從冪律在當時的很多國家都存在,與政治、稅收等社會制度設置無關。安格爾將不平等過程置于微觀交換和競爭中考察,為財富不均衡分布的形成提供了一種解釋。近些年,這一問題還引起了很多自然科學家的興趣。這些研究對財富分化給出了若干種可能解釋,共同點是都試圖用微觀互動和動態過程解釋財富分布的生成。
在現實社會網絡中,人們擁有朋友的數量同樣存在巨大分化,朋友數量也多呈現冪律分布。巴拉巴西和艾伯特基于馬太效應,提出了偏好依附機制,并經數理分析和計算模型雙重檢驗,發現偏好依附是解釋無標度網絡冪律特征形成的關鍵機制。薩爾加尼克等利用線上數字實驗證明,流行度也會在行動者彼此影響的條件下呈現冪律分布,盡管特定產品流行與否具有偶然性且不可預測,但冪律的規律性在每次“歷史重演”中十分穩定。
2. 制度的起源和維持
制度是社會學最為關注的宏觀設置。對制度從哪里來,社會學有一種回答認為它是在微觀互動中自發演化生成的。阿克塞爾羅德將規范存在性問題轉化為程度性問題,從行為角度對規范進行界定,并對其涌現開展討論。研究發現,當在博弈架構中引入元規范機制之后(即對拒絕懲罰進行懲罰的規范),規范會成功地建立起來。對于制度如何維持,又如何擴散和影響等問題,阿克塞爾羅德通過模擬文化間的相互影響,討論了文化差異性的持續。森托拉等討論了為什么不受歡迎的規范會流行,為此他們區分了信仰規范與執行規范行動。他們發現行動者局部嵌入和狂熱者空間集聚會加劇虛假規范執行,小世界網絡則會抑制。另一項研究專門討論了網絡結構對文化多樣性的影響。
拓展社會學邊界的機會
克里斯塔基斯曾在《紐約時報》發表短評,認為社會科學近幾十年間停滯不前,原因在于沒有參與科學前沿,因此是時候搖動它一下了。他主張社會科學要敞開懷抱,把大部分力量部署到自然與社會交叉的新領域之中。復雜性正是這樣一個前沿交叉領域。進入21世紀以來,盡管社會學者與復雜性研究之間的互動增多,在理論和研究成果上也有一定的積累,但令人遺憾的是,復雜性研究及相關進展并沒得到大多數社會學者的關注。一些社會學引為經典的理念與復雜性研究秉持的觀念盡管有相似之處,卻也存在距離和張力。本文認為,擁抱復雜性正為我們提供著拓展社會學邊界的新機會。
(一)運用復雜性視角理解當下社會
技術是推動社會變遷越來越重要的力量。近二十年間,ICT的發展對社會變遷帶來了極深遠的影響。關注復雜性能夠幫助我們認識這些社會變遷,對當下社會形成更深入的理解,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理解影響社會的技術發明和應用。ICT發展催生了許多新技術發明,對這些技術發明的應用也正在改變著生產和生活。社交網絡、交易平臺、人工智能等都是ICT推動下得以應用并產生廣泛影響的技術發明,它們都與復雜性有著十分密切的關聯。
第二,理解技術變遷給社會帶來的影響。技術的社會化應用使其不再只是效率工具,而是開始進入到社會關系之中,以更具復雜性的方式影響著社會。
第三,理解社會形態特征的變化。關注復雜性意味著更應注重從行動者之間的互動入手刷新對社會的理解。社會學從不缺乏互動視角,過去關注的更多是局部互動。從復雜性視角看,可以將當下社會理解為一個全局互動的社會,人類整體處于高度互動的狀態。復雜性理論與方法為理解高度互聯社會的行動和動態提供了基本視角和框架,幫助我們認識由高度互聯帶來的社會后果。
(二)用復雜性思維認識社會學的基本問題
如果說我們能從現實角度看到擁抱復雜性對社會學的價值,那么從理論角度,運用復雜性思維對拓展社會學邊界的意義又是什么呢?
在自身演進以及與社會科學其他學科的理論互動中,社會學理論似乎面臨著兩種困難。一種是微觀到宏觀轉換的問題,這被科爾曼視為社會學的核心任務,但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近年一些有影響力的社會學者再度提及微觀到宏觀的轉換問題,并將該問題與復雜性研究關聯。社會如何從行動者的微觀互動中涌現,可以看作是運用復雜性思維對“社會何以可能”這一基本問題的重新理解。
社會學理論面臨的第二個困難是在與主流經濟學的對話中遇到的。社會學強調社會化對行動者的影響,傳統上卻傾向于接受行動者完全內化了規范的假定,被稱作“過度社會化”;新古典經濟學理論與社會學中的理性選擇理論則是社會化不足,被認為陷入了“低度社會化”的誤區。格蘭諾維特較早指出了這兩種極端理論狀態的存在,主張采用嵌入性觀點,避免二者的缺陷。一方面,嵌入性觀念推動了社會學中網絡研究的發展。由于復雜性研究對互動的強調,網絡思想很快被其吸收并在復雜性研究的其他學科中擴散,反過來又促進社會學網絡理論朝著關注多重和動態性的方向發展。阿瑟曾認為,“低度社會化”的新古典經濟學是復雜經濟學的一個特例,我們或許也可以認為,“過度社會化”的傳統社會學處在另一個極端,也是充分接納了網絡思想、運用復雜性思維的社會學的一個特例。
(三)在復雜性研究中重塑社會學研究方法
一些社會學者曾嘗試發展理論工具,解決微觀與宏觀之間斷裂的難題,但都并不成功。在經驗研究中,多層次分析技術可用于駕馭宏觀環境對微觀行動的影響。但是對微觀行動如何演化為宏觀圖景,常規統計方法幾乎無能為力。有學者認為,傳統社會學推崇的案例研究方法有可能通過揭示微觀社會機制,實現解釋宏觀的目標。但案例研究較難對宏觀后果進行有效測量,也難以在微觀行動與宏觀圖景之間建立可確證的路徑。ABM是呼應需求的方法創新,它能克服統計分析與案例分析的局限,開啟了一種“扎根于實用主義和復雜性的新范式”。
除了ABM類的計算模型,參與復雜性研究的社會學者還采用了更多新穎的研究手段,如挖掘與分析在線大數據、實施線上數字實驗等。這類研究也被歸入計算社會科學的范疇,它們不再滿足于在理論上探索導致宏觀涌現的微觀機制,而是更具經驗性地觀察社會行為的復雜模式,或對理論模型進行驗證。對于國內的社會學研究方法教學而言,增加應對復雜性問題的計算思維與方法等相關課程模塊,應當說已迫在眉睫。
當然,社會學與復雜性研究的互動也受到很多限制性約束。復雜性研究內部也存在張力甚至激烈的爭論。盡管存在諸多困難,社會學仍應以更加包容開放的心態,廣泛開展學科間的交流與合作,在這樣一個社會現象的復雜性越來越凸顯的時代,跨出傳統的邊界,回應時代的呼喚,對復雜性這一既古老又嶄新領域進行積極的探索和勇敢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