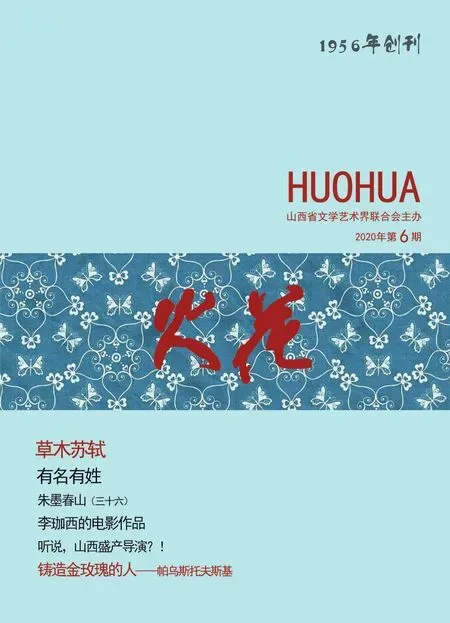抱愧母親
——紀念母親逝世三十周年
郭存魁
母親,多么神圣的字眼,但我一直不敢輕易觸碰她。轉眼間,她老人家離我們而去已經三十年了。這些年來,每遇弟妹們在一起時對母親的追憶,或者看到她老人家的遺像,時或看到電視節目中再現的母親形象時,我內心五味雜陳,說不出的滋味,淚水就會奪眶而出。也許自己真的老了,感情竟脆弱到如此程度。幾次想把這種情感訴諸筆端,就是寫不下去,但歲月告訴我,不能再拖下去了。那就硬著頭皮,打開塵封的記憶,去觸碰一下這至圣的字眼,讓不值錢的淚腺,隨著筆觸也來一次宣泄,權當對母親的祭奠。
一
母親,胡金嬋。山西和順縣后營村人氏。
1928年戊辰年生。外祖父、外祖母生舅父胡福元,姨母胡改嬋和母親兄妹三人。舅父為長,母親為次,姨母行三。外祖母早喪,外祖父另娶。母親在世時經常用“有了后娘就有了后老(爹)了”來評說前續后繼之家,其實這也是她自家的寫照。舅父年長后當兵(南下干部,80年代去世,去世前是三門峽鐵路局機務段領導),姨母送人,母親一直在馬連曲舅舅家和富裕村姑姑家寄養,這大概是她老人家的童年檢索。稍長后在馬連曲做了宋姓家童養媳,再后來成為村里土改中的積極分子,還當過村婦聯主任。我小時候,母親經常教我唱“左權將軍家住湖南醴陵縣,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之歌,估計就是她參加革命時經常唱的。也就是在那個時期結識了父親,共同的理想信念加之頻繁的工作環境,碰撞出了愛情火花,我很賞識他們那時革命思潮的膽識,盡管輿論對解除原來婚姻充滿非議,但他們還是毅然決然走到一起,組成了新的家庭。我是他們婚后第一個結晶,之后母親又生了兩個弟弟,五個妹妹,加上母親早夭的遺腹女和之后夭折的一男一女,共生了11個子女。自從母親和父親成家后,她辭掉了村婦聯主任的職務,退出“政界”。所經歷的是相夫教子,不僅經歷了擔驚受怕的農村“反右”“社教”“文革”各種政治運動,更主要帶我們渡過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吃食堂、三年自然災害,一直到改革開放前的貧困生活。在這種歲月里,不僅把我們撫養成人,還供我們上學。兄妹8人,除我是父親在世時成的家外,其他的弟妹成家全是母親一手操辦的,為了這個家,母親耗盡了她平生的力氣,于1990年5月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享年63歲。
二
1990年陰歷五月,突然收到二弟的來信,信中只寫了四五行字,主要告我,母親高血壓多年,近期血壓又低了。如此簡單的表述,讓我很是警覺,并咨詢了省軍區魏大夫,他也說這不是好征兆。記不清當年武警山西總隊機關在集中學習什么重要文件了,侯小保政委在動員會上宣布,誰也不準請假。但我未顧及這些,向政治部領導請了假,就直奔太原長途汽車站,乘車回和順縣城。那時太原往和順,一天只發一趟長途。到和順汽車站時,正趕上和順發青城的客車,到松煙下車徒步8里路,回到村里,這是我回家最順的一次。因為太原到和順的長途時間很不確定,很少能趕上和順發往青城的那趟車,多數時間我都是徒步回家的,那時年輕,不就是50里路嗎?這次順得讓我始料未及,像是專等我的。
話說回到村里,著急往家里趕,走到關爺廟時,突然聽到身后有人說,“那不是你大哥嗎?”一回頭是我母親,是五妹陪著她在二弟家吃完飯往家走。那天母親穿戴得非常整齊,天藍色的夾襖格外突顯,步子穩健,精神很好,看不出半點病的樣子。見母親如此狀態,緊繃的神經松弛下來,說笑著陪母親回到老院。母親忙著給我做飯,做的是我愛吃的河撈面,母親在我吃飯期間,把我的洗臉水倒在院里梨樹旁,站著望著天際愣了一會兒,好像在思索什么。待母親回屋在小凳子上坐了下來,我邊吃飯邊給母親說:“媽,聽說您血壓又低了,我帶的藥,您按時吃下去,會好的。”我說著,就見母親身體向后仰。我急忙抱住了她,待她蘇緩過來,扶在炕上。兄弟們趕忙把村里三個赤腳醫生請來會診,他們提出兩種意見:一是人不行了,準備后事;二是到許村衛生院進一步確診。我怎么也無法接受這個事實,我讓三弟到許村請醫生,請來的是我在農醫班的同學張建國院長,他讓我們馬上到鄉衛生院急救,在這期間,其他妹妹妹夫也都趕來了。趕忙備好擔架,把母親抬到鄉衛生院,我一路上給母親搭話,她還清醒,等到衛生院吸上氧,情況就逆轉了,母親的呼吸一陣陣急促起來,一直處于昏迷狀態。鄉衛生院沒有路燈,院外漆黑得伸手不見五指,貓頭鷹一陣陣凄厲的叫聲在上空徘徊,讓人頭皮發麻。院里醫生一陣慌亂,最后在王院長胸腔按壓,掐人中無果的情況下,對我說,趁老人還有一口氣,趕緊抬回去吧,我們盡力了。就這樣,我的兩個弟弟和兩個妹夫抬著母親,我一路呼喚著,在夜半時分回到家里,換上老衣。當時不敢大聲哭泣。村里有規矩,人死后不能進村的,就這樣停了一個小時后,才把積壓于胸的悲聲放出來。
天明后,在村里報了喪。村里沒有固定的治喪組織,都是親朋好友自發組織起來的。村里的長輩也好,平輩也罷,他們沒有多余的客套,把我家的事當作自家事一樣,各個環節,井井有條。先看發喪工夫,再打棺木彩畫,停喪期間的祭祀,吊唁活動有條不紊進行。我擬了電報稿,記不得讓誰去松煙拍的電報,一直到出殯也沒把妻兒等回來,那時也沒有電話。等我回到太原把黑紗給妻兒佩戴上時,他們才知道原委。妻子把電報給我看,看到不知所云的電文,讓我一頭霧水,錯在哪了?是我當時擬電文字寫得潦草了,還是發報人不識字,業務馬虎不得而知,這是一件憾事。打發母親時除了我家妻兒未回,其余姊妹,侄兒侄女,甥男甥女都在。當時忙忙碌碌,混混亂亂,一切按治喪程序走完,把母親送入墳塋和父親合葬,入土為安,告一段落。
三
真正使人悲痛的不是在事件中,等喪事辦完后,安頓好弟妹回到太原,從給妻兒戴上黑紗的那一刻起,情緒就控制不住了,先沒去政治部銷假,就把自己在樓上關了7天,那才叫痛定思痛。母親就這樣走了,走得悄無聲息,未留下任何遺言,好像是專等見我一面,等我吃了她給我做的最后那頓飯,她才心安理得這樣走的。要知道這次回家是這樣的結局,我這次回得多么不值,我好悔啊。
1990年母親在太原過的年。過年那天,我們戰友互相串門拜年時,都拱手給母親打招呼,“大娘過年好!”母親回答“可好哩”,我們都笑了。那年冬天,她和我大兒子在一屋住,經常給兒子說,算命先生告她,63歲是個坎,如果她不在了,讓我兒子回去給她老人家舉紙幡送葬。妻子給我說過兩次,我沒在意,好端端的說這不吉利,不要信那一套。在太原期間,她還背著我們把壽衣備了,這些我都一無所知。那年是過了年立的春,立春那天,她在床上躺了一天,和我說,這節令真厲害,讓我特別難受,吃了藥也不管用。春節過后,下部隊前,我給母親買了些藥,等我下部隊回來,母親已經回老家了,說是該養種了(種地),急著回去的。那年她還催著五妹辦婚事,這些前兆我一點都沒察覺,壓根也沒往那里想。給母親辦完后事,整理遺物時,在柜頂放著被老鼠啃去的多半箱方便面,那是她回家時我妻子給她買的。但她一直未舍得吃,也沒舍得給在家的侄兒侄女和外甥們吃,說是怕我的孩子回去吃不慣家里飯,專門給他們留著的。這一樁樁,一件件,一幕幕不時浮現在我眼前,我怎么就沒有察覺呢?
昨天看到母親時還相見甚歡,今天怎么就陰陽兩隔了呢?我一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在為母親守靈的第二天上午,我不由自主掀開她的臉蓋,仍舊像睡著一樣安祥,只是從鼻孔中滲出些許血液,我輕輕擦拭著,不忍再打擾她老人家了,安息吧,母親。醫生說母親得的是腦溢血,村里鄉親們傳言,說母親是見了我高興死的,我有什么值得母親如此激動呢,連命都不要了。
我20歲離開家,到母親病故這20年來,我為母親做過什么,值得她老人家如此高興呢?我當兵走后,父親就得病了,那是1971年,一直到1978年父親去世。父親得的是賁門癌,1976年以后就臥床了,是母親的精心伺候才活了那么多年。父親每逢吃飯就吐,特別難進食。每逢吃飯時,總是用被子把頭蒙上不忍看家里人吃飯。母親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每天總要等到父親吃進去一點才作罷,否則就陪父親熬著,天天如此。父親病故這天大的事,她一個人默默承擔,竟是沒告我。在給兩個弟弟、五個妹妹成家中,都是她一人咬緊牙關挺了過來。三妹給我說過,每當遇到難過的坎兒,母親都要到父親墳前哭訴一番。她也知道死人幫不了忙的,只是為了發泄心中的塊壘。發泄過后,還得一個人掙扎前行。在旁人眼里她是剛強的,能干的,利索的,好像什么事情都沒誤下過,什么事情都難她不住。憑心而論,我為母親不敢說完全沒分擔過,只是實在太微乎其微了,真的不如兄弟姊妹們做得好。我二弟雖成家另過,不在一起住,但幾乎每天都要給母親問安。母親在世時多次給我念叨過二弟的孝敬和耿直,就連母親最后一頓午餐都是二弟孝敬她老人的。三弟其實在家沒少干活,只是脾氣不好,把他辦的好事給抵消了大半。妹妹們跟母親都親。1974年我探家,大妹妹也就十三、四歲,一大早就替母親燒炕做飯,做好飯后才到許村上學。記得我像她那么大時,也往許村跑校上學。有一次,母親做飯晚了,我哭著就走了。相比之下,我沒他們懂事,如果這也能使她老人家高興的話,那就是母親對我的偏愛。我在部隊吃得好,穿得暖,他們在家過著很貧困的日子。但每次探家,母親都要竭盡所能給我做好吃的,完全不顧及弟妹們的感受。冥冥之中,我急著趕回去吃了母親給我做的最后一頓飯,這是老天給母親的機會嗎?如果這也使得她高興的話,她老人家付出的是生命的代價,留給我的是永遠的痛啊。
四
我1971—1978年在山西孝義縣中隊服兵役。最高津貼掙到15元。那時唯一能做的就是省吃儉用,適時給家里寄些錢,以備急用之需。入伍第一年,一個月6元津貼費,到年底攢50元寄回家,以后年年如此。記得1978年接兵期間,是我回家過的入伍以來第一個春節,那時正是父親病重期間。歸隊時,母親背著父親哭訴著對我說,你看你大還能成人嗎?我也不知怎么安慰她老人家才是,就把僅有的50元錢交給母親以備不測。給妻子留了5元錢。到縣城問同鄉朋友借的路費才回的部隊。為此妻子頗有意見。1978年5月份父親病故,當年底母親又接著給二弟辦了婚事。那年10月我提干到嵐縣中隊任指導員。也未回去,愧疚之余,我把僅存的70元錢打算寄給母親,又怕妻子知道了鬧意見。經過反復考慮,把錢寄給我最信任的后營大舅胡喜元,讓他轉交母親。不想這位舅父大人來了個照單全收,想幫也未幫上,也是我未處理好愧疚母親的。我于1984年提升營職干部隨軍,把妻兒帶到太原。除有一年,太原鬧地震沒回家過年外,母親在世之時,我都帶全家回老家過年。記得有一年,大年初一,不到五更就讓小侄女叫了起來,跟他們一起放鞭炮,點旺火,祭祖。母親還備了一桌豐盛的酒菜,受全家熱熱鬧鬧團聚的歡樂氣氛所感,我豪飲幾杯就醉了。等吃飯時,母親把我叫醒,隨即遞給我一盅酒讓我飲,我問其故,母親笑曰:這叫“回魂酒”,喝了就沒事了。想不到她老人家還有這種經驗。其樂融融的日子,多么值得懷念啊。母親在世時,也常來太原小住。她也很喜歡城市生活,回老家后,常跟鄰居們說,太原如何如何大,晉祠如何如何古,夸耀中幸福感溢于言表。母親過世后,不用說過年,就是平常我也很少回家,除非弟妹家辦事,但也都是來去匆匆,是弟妹們不熱情嗎?不。在我們家,弟妹們視兄嫂如父母,他們都愿來太原小住,家里有什么事情,總是第一個先告我們,解決的理想與否不論,作為兄長擔當還是有的。我不是不想回家,只是不知我牽掛的人和牽掛我的人在哪里。陰陽兩隔的魂魄找不到安頓之所。俗話說得好,父母在家就在,父母不在了,實際意義上的家就變成了鄉愁,回去后留給自己的全是失落感,這種情感實在想不出用什么語言去表述。
五
我住的老院,自三弟買上新房搬出后賣給二妹。這許多年來,二妹已進城居住了,大門常鎖著,房子也漸破敗。但每次回去,總要到老院看看,這是生我養我之所,因為那里有我的童年記憶,有我對父母的不盡思念。院里那棵梨樹是父親栽種的,它和三弟同庚,說來也快60年了。
我20歲走出這院子,現雖世事滄桑,物是人非,在這里我能看到,每逢臘月,母親在燈下為我們弟妹縫衣衲鞋的身影,直熬到大年三十深夜還在趕活兒,目的是到大年初一讓我們都穿上新衣新鞋,這個影像可謂刻骨銘心,那時不懂事的我們哪里知道,我們過年,母親是在過關啊。因此我在母親過世后的棺木上把唐孟郊的詩錄了下來:“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這是我獻給母親唯一的一件作品。
我14歲那年,被許村完校選中滑翔員。本縣體檢過關后,到平定縣復檢時,因鼻炎打了下來,當我趕回家時,醫生正給母親診病,我喊了一聲媽,她馬上醒了過來,她是舍不得我走啊,這種牽掛,每當回到老院都猶昨在耳。
1965年,我以許村完校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因家境困難上不起松煙中學,輟學在村務農。夜晚,母親還讓我把學過的書看上一遍,以免荒廢學業。回到老院總能記起燈下陪讀的母親身影。
兒時放學回家,總急著問媽媽要吃的,每逢這時,媽總是先給在地里勞動未回的父親舀出一碗飯扣上,溫在火臺上,然后才讓我們吃。遇有好吃的,如水果、燒餅類,總是按兄妹人數平均分著吃。類似讓梨故事,也沒有少在我弟妹間演繹。因為弟妹多,父母還要下地勞動,大的照看小的,形成了我們家不成文的規矩被傳了下來。在大躍進時期,農村多快好省要落實到,看誰出勤早,看誰土地挖的深,看誰汗出的多,否則就得扛黑旗,挨批。那時父母根本顧不上家,我常給不足1歲的妹妹穿衣、喂飯、陪她玩。那時我也只有8虛歲,二妹妹就是我二弟看大的,以后如此類推。歷史上的名門望族家風是靠祖輩家訓傳承下來,一般人的家風全都是父母的言傳身教。我母親口貴話不多,但她的行動就是一種無形的力量,感染著我的一生。
在這種艱難歲月,在逆境中成長起來的我,漸漸懂得了擔當,因為我是長子。那是個缺吃少穿的歲月。父親和弟弟在村勞動,中午只能吃上看不見面團的菜窩窩。就這干糧,小妹妹們也只有看的份。那時我任民辦教員,苦輕,比不得體力勞動,中午總是喝些湯飯,就跑到學校睡覺去了。母親發現后,近乎央求地哭訴,讓我把干糧吃下去才算作罷。后來我到城里上學,每周能改善一次,我把白饃饃攢下來帶回去給弟妹們享用,每到這時,體會的是做兄長的自豪,在老院父母教會了我成長……
去年陰歷八月十五,馬連曲文華苑建成剪彩。受村干部之邀,作為村民代表發言。這是村里鄉親們對我的認可,更是對父母的認可,說明我這個游子沒給父母丟臉。這使我又一次在老院駐足,想起一連串的往事,想到離我遠去的父母。我常在思索,有的東西隨著時光的流逝,將漸行漸遠,最后消失在時光隧道里。但有的東西隨著時光的流轉、歲月的打磨反倒越加清晰起來。留在我們的精神世界里,成為一種永恒,形成一種價值。這就是我對母親的記憶。回到太原,寫了《想你了,故鄉的明月》發表在《山西日報》上,這是獻給母親的心聲啊。時光荏苒,年矢每催,一晃自己步入古稀之年,回望這輩子,功業上雖平淡庸常,做人做事上倒不虧欠什么,也沒有覺得對不住誰的,唯一抱愧的是母親。
情動形言,訴不完的母愛。
發乎心聲,涕零不知所云。